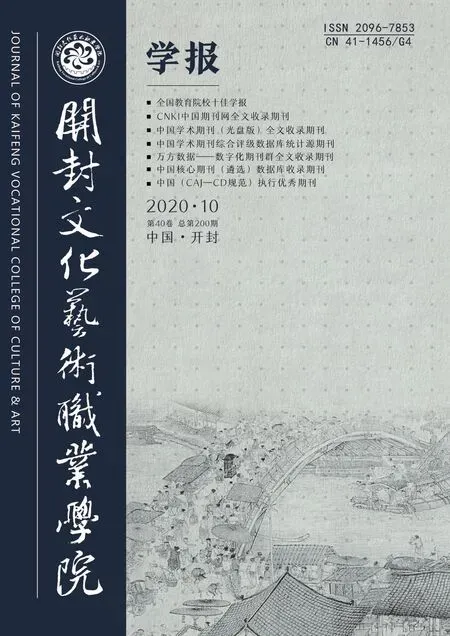绽放于永夜的恶之华
——经典叙事学和修辞叙事学视野下的《白夜行》浅析
吴延安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白夜行》这部久负盛名的推理悬疑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叙事性作品。小说以一对少男少女的灰色人生与草蛇灰线式的复杂情感为主线,通过最后的悲恸命运向我们展现了 “苍白的永夜,靠着吞噬与践踏他人幸福为食粮的自我救赎之路将永无破晓”。抛开思想揭示和社会文化批评的角度,分析叙事结构与修辞叙事[1]在小说文本中的客观展现,以及话语场域内的叙事创意与人物性格张力,会得到不一样的文本阅读体验。
一、叙述语态的神秘性
《白夜行》中的案件始于20 世纪70 年代,终于90 年代,时间跨度达19 年之久。时间跨度之大必然造成登场人物之众与情节推进之快,通过内叙事层的有限视角进行通篇流水账式的叙事显然是过于冗长且乏味,而如若纯粹利用外叙事层中全知全能的侦探视角对整个案件进行提纲挈领的解析从而顺利解决事件又难免落入俗套之嫌。那么,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作者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呢?
首先开篇描写道,笹垣警官在烤乌贼饼店中瞄到报纸中写着:
“三月时,法院对熊本水俣病作出判决,与新泻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痛痛病合称四大公害的审判,就此全数结案。”[2]3
从该历史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正是1973 年3 月20 日的时间点。
然后是小说的第3 章第1 节,场景中提及《银河铁道 999》和 “太空侵略者”。前者于1979 年改编成电影,后者则是日本著名游戏公司南梦宫在1979 年推出的街机游戏。作者将特摄片和游戏这样的流行文化因素作为特定标志,标明了本已模糊的时间刻度,使读者顿悟自案发竟已过去7 年之久。作为类似桥段还有第9 章第2 节描写高宫诚家中电视播放的1988 年3 月24 日 “中国上海近郊的火车相撞事故” 相关报道。此外,相关的 “彩蛋” 在文中比比皆是,不再一一赘述。
作者在这里抛弃了烦琐而冗杂的纪年进行时间明示,转而采用人物对话与剧情细节暗示,使读者在文本阅读中不至于模糊了时间,又增加了阅读趣味性,足见作者统驭时间之功力。
在把握时间技巧的同时,作者同样不忘在建构故事与人物上下功夫。通过对书中所有案件的梳理,笔者将对剧情推动起重要的叙事序列进行如下展示:
六个致死案件:第一,桐原洋介死亡事件(涉及人物:桐原亮司、西本雪穗、笹垣润三、古贺刑事、桐原弥生子、松浦勇);第二,西本文代自杀/他杀事件(涉及人物:西本雪穗、田川敏夫);第三,西口奈江美死亡事件(涉及人物:桐原亮司、西口奈江美、园村友彦);第四,今枝直巳死亡事件(涉及人物:桐原亮司、栗原典子、筱冢一成、今枝直巳、菅原绘里);第五,松浦勇死亡事件(涉及人物:桐原亮司);第六,唐泽礼子死亡事件(涉及人物:桐原亮司、唐泽雪穗)。
三个性侵事件:第一,藤村都子性侵事件(涉及人物:桐原亮司、西本雪穗、秋吉雄一、菊池文彦);第二,川岛江利子性侵事件(涉及人物:桐原亮司、西本雪穗、筱冢一成);第三,筱冢美佳性侵事件(涉及人物:桐原亮司、西本雪穗)。
两个泄密事件:第一,Submarine 游戏版权盗窃事件(主要涉及人物:桐原亮司、西本雪穗、中道正晴);第二,筱冢药品的商业机密泄露事件(主要涉及人物:桐原亮司、栗原典子)。
以上事件单元与相关行动者,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分析文本结构内部叙述者与受述者的叙事交流[3]。纷繁的事件通过闪回、滞顿、并行、回忆,将“已知角色” 陌生化等多种手段,带出了不同的叙述者和受述者,极大丰富了读者接收的案件信息,却丝毫不显得无聊和多余。因为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都惊人地涉及共同的人物:桐原亮司与雪穗。与其说是独立的案件,倒不如说是以异故事者的角度向我们展示同故事者所没有甚至不敢展示的叙述。
与此同时,庞大而复杂的文本信息也充斥着大量的不可靠叙述[4]。东野圭吾借人物之口,使用一系列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解读以及不充分评判来限制读者的思维路径。在这里,读者仅能依据叙述者的叙事功能和人物功能之间的距离来判断叙述者的阐述话语是否可靠。但此时限知视角已不再是推理过程的负担,它一方面使得多重的主观判断产生认知矛盾,加大了思考的难度;另一方面,恰恰因为这一限知视角,反而不断通过多人称的视角拼凑,达到几近全知全能的零聚焦效果。
费伦如此阐释叙事进程的含义:“一个叙事建立其自身前进运动逻辑的方式(叙事处于动态的第一层含义),而且指这一运动邀请读者做出各种不同反应的方式(叙事处于动态的第二层含义)。”[5]90如果说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选择借助故事和话语的差异来推动解释叙事运动的逻辑得以展开,那么修辞叙事则是通过文本动力(即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和读者动力两股力量的动态交互来推动其发展。
最终读者正是通过鉴读众人物在事实轴(即事件/ 信息报道)、知识轴(事件/ 信息解读)以及价值轴(价值评判)三轴上的叙述差异与修辞伦理,抽丝剥茧地深入案件,逐步解析文本与故事。最终使得一开始只是平面人物的桐原亮司与雪穗通过多章节和他人称叙述不断的 “填充空白”,逐渐被塑造为一个缜密冷峻又藏有一份扭曲爱恋的复杂男性,和另一个靠吞噬与攫取他人为生、蠕动在高雅独立外衣下的悲剧女性。
二、时间上的叙事审美
在《白夜行》中,第6 章末尾,继西口奈美江的离奇死亡带给读者的错愕之余,故事很快到了第7 章,期间作者故意隐去了具体的历时。开篇画风骤转,作者从一份原本与前章剧情风马牛不相及的商业申请书凌空起笔,重新引出高宫诚这个稍着笔墨而几近被读者忽视的角色。大学时代的舞蹈社对应现在的大家族企业东西电装公司,而学生时代的社团副社长则对应着如今高层骨干这一显赫社会地位。在这段文本语境中的雪穗和高宫诚也早已是距离婚礼只剩两周的未婚夫妻。
“整整四年啊。” 诚喃喃自语,他指的是与雪穗交往的时间。[2]231
而此刻读者满脑的疑惑与惊讶只能被高宫诚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语一笔带过,继而通过倒叙为我们娓娓道来雪穗和高宫诚的相遇、相识和相恋。
由此可见,短短几个章节的剧情推进带来了巨大的时距[6]。过往信息的重拾,是对现有主要事件的极大呼应与信息补充,使得读者的阅读体验产生滞顿,进而引发对事件的重新思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维紧跟着跌宕起伏的情节跳转不断推导与重演,可谓极尽迂回曲折之能事。
与此相对应的预叙也被作者多次采用,为读者提供内视角人物尚未获知的信息,进而激发强烈的好奇心来探寻角色内心活动的张力。例如:在绘里和笹垣发现今枝失踪多天之前,亮司与典子商量的对话早已将在家中卫生间谋害今枝的作案细节叙述出来,以及利用典子的身份窃取筱冢药品的企业机密等。
而重复叙述的代表性例子便是在书中被多人提及的 “雪穗生母之死” 事件。从雪穗本人与好友川岛江利子的闲聊,到补习老师中道正晴与雪穗养母唐泽礼子的对话,以及侦探今枝直巳接到委托调查雪穗背景的过程中,这个陈年疑案乍一看并不对当前的事件拥有任何显著影响,却又犹如幽灵般在故事时间里挥之不去。这个细节仿佛时刻提醒着读者,牵动起敏感的神经,使之不得不屏息凝神地留意事态的发展。
如此一来,“顺序” 所带来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倒错现象,“时距” 所造成的故事时间长短波动现象以及 “频率” 的叙述密度差异为读者开启了一条暗线,从而试图通过它厘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三、多重视角的交错感
在案发后,笹垣警官经过排查找到了西本家,女主人公雪穗就此初登场。“雪白脸颊上的肌肤如瓷器般细致” 的样貌与出乎外表的乖巧懂事给笹垣警官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后面对盘问,对比母亲文代的惊慌失措,小雪穗更是显得格外沉稳冷静。作者利用警官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 “聪明” 的与年龄有些不符的漂亮小女孩,这个初印象同样也给后续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预埋下了伏笔。
然后到了第1 章的末尾,我们顺着物业管理员田川敏夫的视角再度回到雪穗身上。
西本雪穗还站在脱鞋处。玄关的门开着,逆光让他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妈妈死了吗?” 她又问了一次,话里夹杂着哭声。[2]50
此时的故事背景是雪穗声称忘带钥匙寻求田川的帮助,但回到家映入两人眼帘的却是文代 “自杀身亡” 的场景。在田川眼中,此时的雪穗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失去母亲的普通小女孩的孤苦与无助,雪穗带着哭腔的话语更是令他不容怀疑这份 “流露的真情”。受内视角所限,我们看不清雪穗此刻的表情,而田川本该同情雪穗却不自觉露出一个难以言说的表情。
等到第2 章第1 节时,跟随着秋吉雄一的偷拍镜头,我们发现原本的 “西本雪穗” 在这里已经变成了 “唐泽雪穗”:
“唐泽雪穗的头发略带棕色,发长及肩,发丝仿佛有一层薄膜包覆,绽放出耀眼的光泽。”[2]53
经历丧母的雪穗很快就被唐泽礼子收养,寥寥数笔便刻画出了之前雪穗所不具有的优雅与光彩,暗示雪穗成功实现了一次重要的阶级跳跃,悠闲的校园生活让我们看到她非常适应现在的中产阶级生活,与上一章末尾失去生母的悲伤形成了强烈反差。从后续剧情回溯,若是知晓此时表面上的劫后之幸只是雪穗所有工于心计的预谋之一,亲人和友人的生命也仅是她用于改变阶级的筹码,不禁让人汗毛直立。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内聚焦[7]的一个显著优点:仅靠单个视角无法详尽描写人物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从不同的维度叙述故事进程。由此引发的则是叙事判断问题。正如费伦在《活着就是讲述》中指出,阅读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伦理活动[8]20-21,或者说叙述是各种伦理相遭遇的场所[8]23。因此,叙事文本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具有伦理维度,以至于在相关叙述中叙述者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的伦理取位[9]。
例如:桐原亮司,在屉垣警官眼中,他是一个阴鸷沉郁的嫌疑犯;在粟原典子眼里,他是与自己互舐伤口的孤独男人;而从园村友彦的视角来看,他则是一个行事诡秘但值得信任,相依相托却无法靠近的朋友。
又如:雪穗,在正晴眼中,她是一个成绩优异的乖乖女;在高宫诚眼中,她是一个精明干练但又捉摸不透的魅力女性;在一成眼中,她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调查对象。
作者通过众多角色的主观认知与价值评价,最大限度使主人公的性格丰满与立体化。
结语
再度细品小说封面的剪纸图案,一个小男孩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一前一后在苍白的天空下行走着。
标题的意象便以这样一幅图景向我们展示:
白——多形容女性,这里的色调是内心极度荒芜的苍白。
夜——暗淡阴沉,性别上更偏向阴性,这里代表的既是沾染血腥与罪恶的攫取与掠夺,也是一种永无破晓的精神压抑与生存绝望。
行——两人执手漫步,缓缓而行,然已无归路,生存无望。
这组冷色调的意象体系恐怕也正是男女主人公人生的最佳诠释:断线之风筝于坠毁之际终获自由,孤独的瓷娃娃沐于艳阳下永囚心狱。那份他们用一生罪恶与痛苦所浇灌的恶之华,或许只能留于那个永夜继续绽放。
叙事学选择将作品的文本意义同内质结构紧密联系起来而拒绝所谓超验的个人性灵,这无疑是对文学神秘化观念的巨大冲击与解禁。纵观全书,若以立体构型将全书叙事的创意具象化,则是一种“鱼骨架”式叙事布局[10],即以中间的脊骨为主线剧情,两侧蔓生出若干小骨刺;每根骨刺既可作为独立支线剧情自成一脉,又可以鱼尾作为时间起点,依次汇入脊骨,按照主线剧情的承转继起共同指向鱼头(即结局)的位置。在如此多维动态交互式的叙事架构下,作者拒绝了从主干延伸至枝蔓的传统叙事,转而从自各枝蔓的末端展开超越日常时间的叙述,最后纷纷收束至主干,将故事娓娓道来的同时丰满了人物塑造与情节建构。作者如此醉心于 “可信的不可能之事” 的极尽阐释,在剧情上满足读者追求官能刺激的猎奇心理的同时,无疑呈现了一场令人大饱眼福的 “叙事魔法” 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