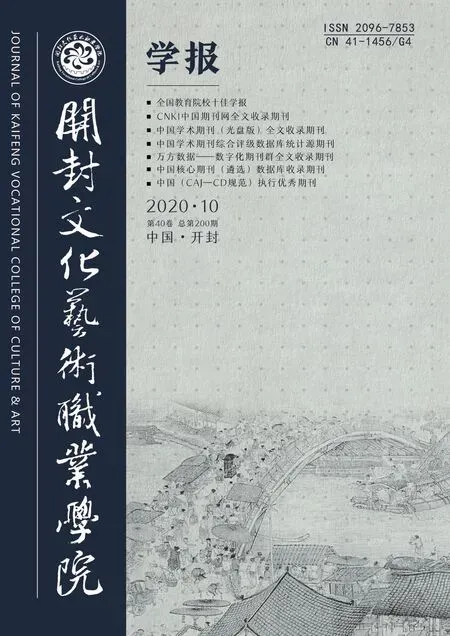从记名权看魏晋文学的自觉
王文静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一、先秦时为作者文章冠名的情况
先秦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著作非《诗经》莫属,然而那个时代只有诗没有诗人。因为《诗经》时代写诗不署名,《诗经》能明确考知作者的诗数量很少。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1]34,《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1]57,这里的 “吉甫”“家父” 是最早用诗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诗人,但他们的姓名并非十分具体和准确,生平也不可考。这种普遍的现象说明当时社会还缺乏为诗人记名的意识。
先秦时期诗作不署名,也与作者、诗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有关。屈原用楚国诗歌形式创作出了《离骚》等一系列作品,屈原本人也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享有记名权的幸运者,然而这与他特殊的社会地位不无关系[2]27。社会尊重大人物的习俗使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大人物的姓名以及生平事迹更容易随其作品而流传于世,同时,这一习俗又像一只无形的手抹去了其他作品创作者的姓名。
二、汉以来及曹丕《典论·论文》中文章记名权的发展
汉以后诗歌记名的现象逐渐增多,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等是《史记》中记载的一些有作者的作品,表现出作品的记名逐渐从帝王下移到臣子。获得记名的诗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总体比屈原有所下降,呈现出汉朝人初步具有了给诗歌记名的意识。汉初司马迁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使一般人物也可以出现在史书中,人物成为整部史书写作的聚焦点。这一新的史学观也反映出新的社会思想,即重视个人价值,尊重个人创造力。但这种意识还是受到限制的,记名的范围仍然比较狭小,多数还是皇帝身边一些有迹可考的人物,如枚乘、司马相如等。其他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仍无法知晓其作者,如《汉乐府》《古诗十九首》。
发展到建安曹魏以后,诗人的记名权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中国一部诗歌史变成了有姓名可查的诗人的创造史。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便可窥其端倪:“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3]362儒家非常珍惜人的生命,包括在世时肉体的生命以及人死后精神的生命。佛教相信轮回,认为人不仅有现世,还有来世,不过中国人并不是十分相信有来世,而是向往死后的不朽[4]153。对于文章之经国之大业,以前的思想家、文论家的作品中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根据曹丕《典论·论文》后面的叙述也可知他是把重点转移到了文章对于个人的不朽之盛事上。“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3]362人的生命是会结束的,人的荣华也是会消逝的,它们都有一定的期限,那么作者是靠什么流传于后世呢?“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3]362。这既是对个人创作的肯定,也是对自己创作潜能的激发,使古人立言不朽的潜在意识得到了强化。进一步推论,要想实现 “三不朽” 中的立言不朽,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者取得作品记名权。如果没有给作者以充分的记名权,那么作者想凭借自己的作品流传于世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在魏晋乱世作家对记名权有了更进一步的追求。曹丕对记名权的肯定还表现在他在《典论·论文》中首次列出建安七子的名字,论述了作家作品间的关系,以简要的语言指出其创作特点、长处和短处,甚至说《典论·论文》就是以作家为主体的,因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气说、文体论都是由作家评论而生发的,这进一步强调了在文学发展中作家作为主体的重要性。在《与吴质书》中,曹丕列其中六子,给他们整理遗作时都是署名的,如果不为作者记名,我们便很难归纳出每个作家的风格习气,很难知其人而论其事,也缺少一种读其文而思其人的只属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超越时空的独特审美感受,不知元瑜之书记翩翩,不知公幹之逸气冲天,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此外,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记载:“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3]864丁敬礼的话反映了当时人借文章以垂世的强烈心理[5]48。可见,《典论·论文》所谓文章是 “不朽之盛事” 绝不仅是曹丕个人的看法,而是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
三、魏晋诗歌记名现象普遍发展的原因
首先,人的意识进一步觉醒,追求作品的所有权如实地归于个人而不是归于集体的无名氏。这从本质上来说是承认作者个人的文学创造力。
其次,与汉代相比,魏晋以来作家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文学才能被视为一种天赋而普遍受到重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提及:“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6]326即为文是需要一定文学天赋的,不可强制。因此,文人多以文才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7]864(曹植《与杨德祖书》)这种文人以文学才能互争长短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章进一步受到重视,文人地位提高的社会风气。这就不能不激发作者进一步为自己争取记名权以求流芳后世的强烈愿望。
再次,与个人传名意识的增强有关。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长年的战乱使人人都处于不安之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8]54的荒凉,再加上政治斗争的残酷,使敏感多思的诗人更加觉得朝不保夕,“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9]198是那个时代诗人们无力的叹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更促进了诗人对身后名的向往,把 “经国” 和 “传名” 结合起来,写作既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既是为现世也是为身后。如此孜孜不倦躬耕于诗歌园地,既能使他们暂时忘却个人遭际的不幸,又可以想到生前不得意但身后可以借助自己的作品而被世人尊重缅怀,于是对诗歌记名的态度就更加自觉和热忱。
四、记名权促进了文学的自觉
魏晋文学的自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是对文学的各类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三是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自觉,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对个人诗歌冠名之后诗人便会自觉地追求文学之美,换句话说就是 “文责自负”。诗歌有了记名权之后作品便有了归属,人们必定会对其作品进行评价,更何况魏晋正是文学批评繁盛之时,久而久之人们自然会对作品整体进行高低优劣之分。诗人为了赢得 “生前身后名”,再加上那时儒学衰落,人们对文学之美便有了自觉而又热烈的追求。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说记名权的普遍发展确实激发了作家创作的热情,促进了魏晋文学的自觉,甚至提高了文学作品的质量。
从东晋葛洪对传统的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3]362进行修正可以看出,其实他是把立言与立德、立功等量齐观了,把文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拥经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补末化。”[10]357(《嘉遁》)记名权使得古人强烈的垂世不朽的观念得到增强,这就使处于乱世的人们更愿意把著述立作当作一种精神的寄托以求后世有知音。因此,即使在经国意识相对薄弱的时期文学照样也可以蓬勃发展;即使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岁月里,也有更多的人愿意投身于文学创作。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记名权从帝王下移到臣子再普及到一般作者确实推动了魏晋文学的自觉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