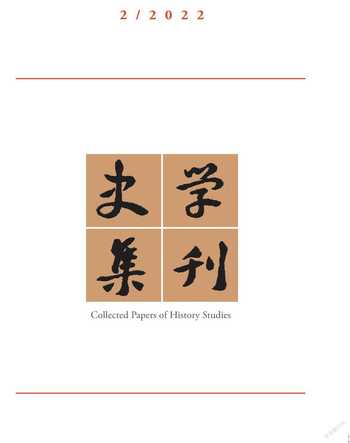战国楚简公文书人名记写形式论议
张淑一 明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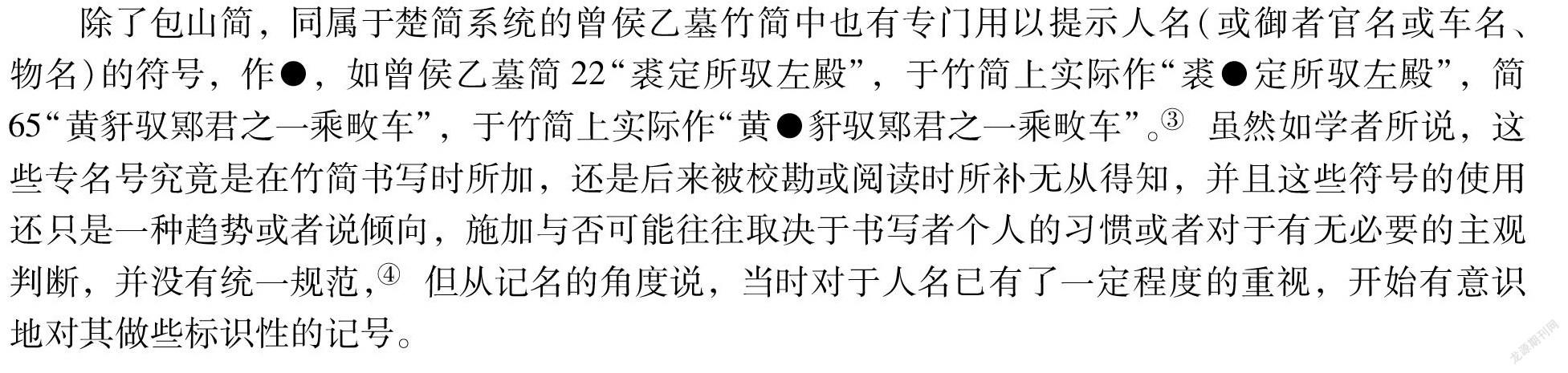
摘 要: 战国楚、秦简公文书在人名记写上都表现出某些一般性的规律。《包山楚简》公文书人名记写包括某地之人+姓名、某人之人+姓名、某官+姓名、某族+名、某人之子+名、某人之奴、某王之+名、某客+姓名、单称官职、单称封号诸种形式。不同的记名方式区分了个体,同时进行了社会分类。楚简公文人名记写有省略情形,包括省略属地信息、省略姓氏、案件审理者自署名的省略和无规律省略。楚简中还有提示人名的符号。楚简公文记名对多数人都记姓和名,秦简则多记名而不称姓,只在特殊情况下另外加姓作为补充。楚简人名记写习惯可能承自周人制度,与秦简相比,更有利于达到识别个体的目的,以及保证公文作为行政工具的效率。
关键词: 包山楚简;秦简;记名;姓氏
在已出土的战国文书类简牍中,除了卜筮祷祠记录、遣册赗书等私家文书之外,与司法、行政相关的公文书也占据很大部分,楚简以《包山楚简》为代表,秦简以《里耶秦简》《岳麓秦简》为代表。秦简、楚简公文书的性质有所差异,但都涉及大量的人名,并且在各自的人名记写中已经表现出某些一般性的规律。而公文书对于所涉及之人名的记写,属于公文程式的一部分,目的在于通过特定的语言文字,区分和识别不同的个体,以满足司法或行政活动的需要。学界对战国楚、秦简公文书的研究,多是依据文书内容探索其所包含的行政或法律制度、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社会治理等方面,①很少从公文程式本身进行探究,尤其未见从公文人名记写角度进行的考察。本文从人名记写形式最为复杂的《包山楚简》出发,会同其他楚系简牍,归纳推求楚简公文书人名记写的基本形式及相关特征,并与秦简记名进行比较,对二者作为政务工具的效率进行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之“人名”,是就广义人名而言的,即把所有出现在战国公文书简当中能够起到指称某一具体人物作用的名号都作为“人名”,包括姓名、私名、某些人物的官职,以及一些封君的封号。本文所涉有关包山楚简的释文,主要依據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所著的《包山楚简》②
及陈伟等综合整理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包山2号墓简册(附签牌)》③
的意见,个别采自他人之说,会给出相应的说明。同时为排印方便,本文引述楚、秦简文或青铜器铭文、异体字、通假字均直接以通行字形式出现,合文直接以析书出现,个别已残字用“□”表示。
一、包山简公文书人名记写基本形式
包山楚简公文书简共196枚,原整理者根据对篇题的认识和内容分析,分为七类:简1-简13,为有关查验名籍的记录;简14-简18,为有关名籍告诉及呈送主管官员的记录;简19-简79,为受理各种诉讼案件的时间与审理时间及初步结论的摘要;简80-简102,为关于起诉的简要记录;简103-简119,为贷金籴种的记录;简120-简161,为一些案件的案情与审理情况记录;简162-简196,为各级司法官员审理或复查诉讼案件的归档登记。参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包山2号墓简册(附签牌)·(一)文书》,第2页。为免冗繁,下文在引述简文材料时,不再一一交代其属类背景。
1.某地之人+姓名。这是包山简公文书中最常见的记名方式,其中又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某地之某里人某”,如简62的“安陆之下隋里人屈犬”,简90的“繁丘之南里人龚忄求、龚酉”,简120的“下蔡荨里人余猬”等。其中“安陆”“繁丘”“下蔡”皆为楚国县名,“下隋”“南”“荨”为相应的县所辖的里名,“屈犬”“龚忄求、龚酉”“余猬”为该地人的姓名。另一类为“某人(或某族)之州人某”,如简173的“邓军之州人娄适”,“适”字从汤余惠释,参见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简84的“肤人之州人陈德”,简181的“应族之州人孙之”等。其中“邓军”为领有该州的人名,“肤”“应”为领有该州的家族名,“娄适”“陈德”“孙之”为隶属于该州者的姓名。再一类为“某邑之人某”,如简169的“湛母邑人屈就”,简124的“司丰之夷邑人桯甲”,简174的“鄜邑人阳越”等,“湛母”“夷”“鄜”皆为邑名,“屈就”“桯甲”“阳越”为邑人的姓名。
有时,“某地之人+姓名”会将被记录者的职业也记录下来,如简80“少臧之州人冶士石亻巨”,简95“卲无害之州人鼓鼗张恘”,“冶士”当为从事冶炼铸造之士;“鼗”,《仪礼·大射》记载“鼗倚于颂磬西纮”,郑玄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宾至摇之,以奏乐也”,(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一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9页。“鼓鼗”当为以摇奏鼗为职业者。
有关里、邑、州三者的区分,陈伟认为:里、邑大致处于同一层级,邑可能为乡野中的地域组织,里可能是城邑中的地域组织,二者应都是楚国郡县制下的地方行政区划;“州”则属于与封君制对应的行政组织,是作为封君的食邑或官员的俸邑而存在。参见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93页。因之无论“里人”“邑人”,还是“州人”,都属于按地域划分的居民,包含在“某地之人+姓名”记名方式之下的,都是楚国政府控制下的编户民。
2.某人之人+姓名。这也是包山简公文书常见的记名方式,如简29的“鄝莫嚣之人周壬”,简38的“射叴君之人南、邓敢”,简131的“秦景夫人之人舒庆”等。其中“射叴君”“鄝莫嚣”“秦景夫人”,是后面所接“南、邓敢”“周壬”“舒庆”诸人的领有者,后者应为前者的依附人口。据简文看,领有者与被领有者大多为异姓,但是也有同姓者,如简91的“周霰“霰”字从刘钊释,参见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东方文化》(香港),1998年第1-2期合刊。之人周雁”。二者同姓的情况可能如《管子·问》所谓:“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清)戴望:《管子校正》卷九《问》,《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47页。被领有者是领有者的贫贱族人。
“某人之人+姓名”是与“某地之人+姓名”相对的,对照简84“圣夫人之人宗、宗未”与简179“圣夫人之青邑人黽曰”,及简38“射叴君之人南、邓敢”与简86“詹阳君之萰隀邑人紫”两组简文,可发现“某人之人+姓名”与“某地之人+姓名”在记名方式上边界清晰,绝不混淆。依照陈伟的观点,前者表示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后者表示地域上的领辖关系,参见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110页。不同的记名方式是为了区分这两者。
3.某官+姓名。这也是包山简公文书中常见的记名方式。如果是中央机构的官吏,就直接记为官职+姓名,如简7的“大莫嚣屈阳为”,简5-简6的“新官娄履犬、新官连敖郙趞、奔得”,简12-简13的“士师阳庆吉”等;若是地方官吏,则在官职之前再加上其所任职的地名,如简40的“蓍陵司败阳非”,简53的“临阳之邑司马李何”,简59的“长沙正龚怿”等。而如果是某官的下级僚属或某封君的私人官吏,则会更详细地标出其所隶属的官员或封君的名号,如简22的“司马之州加公李瑞、里公隋得”,简51的“阴侯之正佐胡疽”,简54的“喜君司败史善”等,以与其他官吏做进一步的区分。
4.某族+名。如包山简3的“之少僮盬族一夫、一夫,处于匡路区湶邑”,简10的“复阝上连嚣之还集廖族衍一夫,处于复阝国之少桃邑”,其中的“”“”“衍”为三人之名,“盬”“廖”为三人所属的族名。包山简32有“以所死于其州者之居处名族致命”之说,“族”即姓氏。上述三人的完整姓名本为“盬”“盬”“廖衍”,但在名籍登记文书上,却记作“盬族”“盬族”和“廖族衍”,根据包山简2-简3:“令彭围命之于王太子,而以登人所幼未登之玉府之典”的记载可知,这是将该地因年幼而未进行登记的人纳入编户系统,同时简3直称“少僮”,也证明了此三人的未成年身份,因此这种“某族+名”的记名方式,应是专门针对之前因年幼而不曾登入名籍、现今正式入籍者的记法。之所以不直接记录其姓名,而以“某族某”为称,应是这种登记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文书记录时也强调是哪个家族的哪些人被登记进来。
5.某人之子+名。这是包山简名籍类公文书专门针对家生奴隶的记法,简7-简8有“喜之子庚”“庚之子日舀”“日舀之子疕”的记载,喜—庚—日舀—疕为连续四代的父子关系,四代人皆为臧王之墨的奴隶。该四代人被写进文书的缘由,是楚王“命大莫嚣屈阳为命邦人纳其溺典”,因而“臧王之墨以纳其臣之溺典”。“溺典”,刘信芳解释为“没有正式户籍的人口典册”,也就是奴隶的主人为奴隶所造的私家名册。刘信芳:《包山楚简司法术语考释》,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这些奴隶不以姓名而以连续的“某人之子某”的形式被登记,可能是奴隶本身姓氏不详,《礼记·坊记》即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五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2页。私家名册为了明确奴隶的血缘关系和代际传承,不得不使用父子连名制的方式。而楚国官府在对私家人口进行登记时,也保留了相关痕迹,以标志其家生奴隶的身份。《汉书·陈胜项籍传》:“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军,大败之”,“奴产子”,服虔注:“家人之产奴也”,颜师古注:“犹今人云家生奴也”,《汉书》卷三一《陈胜项籍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90页。足见对家生奴隶进行单独归类是从先秦到隋唐的一贯做法。
6.某人之奴。也作“某人之侸”,这是包山简司法类文书专门针对奴隶的记法。如简20的“周惃之奴”,简42的“公孙幸虎之侸”,“侸”指未成年奴隶。对于女性奴隶,则作“某人之妾”,简83有“嗌阳公会伤之妾”的记载。因为奴隶与马、牛等牲畜一样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没有独立人格,与奴隶有关的案件也以其主人为人格主体,因此这类公文书记名也以标记其所属的主人为重点,对奴隶个人连私名也不记。
7.某王之+名。包山简7有“臧王之墨”,董珊认为“臧”通“庄”,“臧王之墨”与出现于其他文献中的“龚王之卯”“景平王之定”“昭王之諻”“武王之童胡”等一样,“墨”“卯”“定”“諻”“童胡”是各人的私名,“某王之”表示他們分别是楚庄王、共王、平王、昭王、武王的后代,用上述楚王的谥作为族称。参见董珊:《出土文献所见“以谥为族”的楚王族——附说〈左传〉“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的读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130页。其说若成立,则“某王之+名”是对“以谥为族”的楚王室后裔的专门记法。
8.某客+姓名。这是包山简以事纪年简中才有的记名方式。如简7“齐客陈豫贺王之岁”中的“齐客陈豫”,简12“东周之客许糹呈致胙于栽郢之岁”中的“东周之客许糹呈”。此外,望山1号墓简5“郙客困刍问王于栽郢之岁”中的“郙客困刍”,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望山1号墓简册》,第271页。新蔡葛陵楚简甲三27的“齐客陈异致福于王之岁”中的“齐客陈异”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葛陵1号墓简册》,第400页。等,同于此类。“客”表示该人非楚国人,是他国派往楚国的使者。楚国有以别国使臣来聘或进行其他活动的事迹作为纪年的传统,李天虹指出,相较于楚以本国人事迹纪年时该人的官职和姓名皆记载得很完整(如包山简103的“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中的“大司马昭阳”,葛陵楚简甲三36“大莫嚣阳为战于长城之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葛陵1号墓简册》,第395页。中的“大莫嚣阳为”等——笔者按),楚以他国使者的活动纪年时皆不称其人官衔,只称某客+姓名,“客”成为区分内外的标志。李天虹:《严仓1号墓墓主、墓葬年代考》,《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而不同地点出土的楚文字材料如鄂君启节和包山楚简在同一年里都用同一事纪年,说明这种纪年法只有通过国家统一颁行才能实施。楚简公文书在相关记载中也称“某客+姓名”,应属于对国家所颁布的纪年格式的照录。
9.单称官职。包山简23有“九月癸丑之日不将阴大司败以盟阴之櫰里但无有李竸思,“櫰”“竸”从刘信芳释,参见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第38、39页。阩门有败”的记载,其中的“阴大司败”就是单称官职;简26有“八月癸巳之日不将阳邑大夫以廷,阩门有败”的记载,其中的“阳邑大夫”也是单称官职。此外简12的“子左尹”,简103的“子司马”,简133的“子宛公”,皆为“子+官职”的形式,“子”为表敬之词,“子左尹”是楚左尹署官员对左尹昭陀的尊称,“子司马”“子宛公”等则是相关案件当事人在诉状中对曾经受理过其案件官员的尊称。
10.单称封号。包山简1有“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的记载,其中“鲁阳”为地名,鲁阳公为被分封于该地封君的封号,《淮南子·览冥训》记载“鲁阳公与韩构难”,高诱注:“鲁阳,楚之县公……今南阳鲁阳是也。”(汉)刘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注》卷六《览冥训》,《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89页。此外,简125有疋阳公,简38有射叴君,简54有喜君,简86有羕陵君等记载,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君也都单称封号。
据上,包山简公文书记名形式相当复杂,其中原因,表层上看是因为文书涉及多个人群,包括编户民、奴隶、官吏、王室后裔、外国使臣、封君等,文书对不同人群的名字要做出不同形式的记写;深层原因在于楚国社会当时正处于由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楚已开始以郡、县、州、里等地域组织划分居民,但地域组织中仍存在相当成分的分封制残余,公文简记名因之也时而呈现地域领辖,时而呈现血缘世系,时而呈现人身隶属和封君制因素,带有浓厚的新旧交错时代的印记。
尽管形式复杂,但其在社会学上来说是有意义的,“专名把其所指称的事物转变成符号,扩大了人的想象空间,人们不用总是通过直接经验认知某事或者某人,在许多情况下通过符号即可认知”。纳日碧力戈:《姓名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包山简公文书中的人名记写实际上就是将一般性的人名转变成符号的过程,转变之后,人们通过相应的记写,便可确知人名背后的意义,如通过“某地之某人某”,便可确知其为以地域编户的齐民;通过“某人之某人某”,便可确知其身份上隶属于某人;通过“某族某”“某人之子某”“某王之某”等,则可确知其背后的血缘世系和代际传承。不同的记名方式不仅区分了个体,同时进行了社会分类。
二、记名中的省略与提示符号
为了表达的简洁或书写的省事,《包山楚简》公文书记名中还有省略的情况。具体说,就是当一个事件中的某些人名在前面已经记录过详细信息,后面就会承上省去一个或几个成分。
有时是省略属地信息(部分或全部),如简63的“鄵之市里人殷力可”,简184再出现时便作“鄵人殷力可”;简150的“正阳之酷里人卲”,简193-简194再出现时便作“正阳卲”;简12的“郜室人某瘽”,简13再出现时只作“某瘽”;简121的“下蔡关里人雁女返、东邗里人场贾、荑里人景不害”,简123再出现时只作“雁女返、场贾、景不害”。
有时是省略姓氏,如简2的“令彭围”,简5再出现时便只作“令围”;简60的“射叴君之司马周驾”,简38再出现时便只作“射叴君之司马驾”。简38在序号上看起来在简60之前,但序号只是简牍整理者编连的先后顺序,不一定是当时文书记录的先后顺序。
当同一案件被反复记录时,案件当事人的属地或姓氏信息可能都被省略,如简46贷金案的当事人“越异之太师越儥”,简52再出现时便只作“越异之太师儥”,省略了姓氏,至简55再一次出现时,则只作“太师儥”,连属地也省略了。
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省略,是案件审理者自署名的省略,如简35的案件审理者署名“匡得”,简32、简37、简76等的案件审理者署名“旦塙”,简23、简43、简44、简45、简50等的案件审理者署名“秀不孙”,这些人本来的身份是掌狱讼之正,因此较为完整的署名应该是“正+姓名”,如“匡得”于简29便作“正匡得”;“秀不孙”于简31便作“正秀不孙”;“旦塙”于简27则作“正旦塙”。而从全部司法文书簡中的署名来看,案件审理者最规范的署名方式应该是“正+姓名+志之”,如简21有“正旦塙志之”,简39有“正疋忻志之”。但这些人可能由于长期署名,出于简省,在可能的情况下便尽量简化,直到简之不能再简的单记姓名。不过相对于某些简文对某些案件当事人的记名连姓都省略、只剩一个名来说,他们的署名至少姓名都是齐全的,这应该也是楚简公文书在案件审理者署名规范上的最低要求。
在包山简公文书记名当中,还有一些好像看不出规律的省略,如简82的“舒快讼吕坚、吕热、“热”字从李零释,参见李零:《古文字杂识(五则)》,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吕怿、吕寿、吕卒、吕瞢,以其不分田之故”,简101的“章越讼宋亻咼以拒田”,以上两简中无论作为原告的“舒快”“章越”,还是作为被告的“吕坚”“吕热”“吕怿”“吕寿”“吕卒”“吕瞢”“宋亻咼”,都是在并无上文的情况下只记姓名,省略了其他身份信息,令人看不出他们的地域和身份属性。又简73的“仿令坚”,简85的“缶公德”,简12的“漾陵大邑痎、大驲尹师、寻阝公丁、士师墨”,简115的“令尹子士”“太师子佩”,这些都是在并无上下简文提示的情况下直接省略了官吏们的姓氏,只记名或字。
有时即使在同一案件中,包山简对不同的人名在记法上也有区别,如前文简5-简6在地进行名籍登记的案件,其中的“新官娄履犬、新官连嚣郙趞、奔得”完整记录了姓名,但同一条简中的“新官师瑗、新官令越”却只记了名,而省略了姓。曾有研究者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前三者资历浅而后两者资历深,不称姓是表敬的意思。巫雪如:《包山楚简姓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6年,第245页。然而无论是先秦还是后世都没有以单称私名表示尊敬的情况,恰恰相反,单称私名仅存在于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当中。
笔者以为,这些看似无规律的省略,实际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现今所掌握的包山简公文书只是当时所有公文书的一部分,不能因我们只见到其中的一部分,就认为文书记录者也没有前后文可供参照。二是文书记录者的个人行为,为图省力,他们根据自己对被记录者的熟悉程度做出省或不省的决定,熟悉者就省略其他身份信息,只记姓名,甚至连姓都省略,只记名或字;不熟者则记录全部信息,以免淆乱。无论哪方面原因,都反映了包山楚简公文书记写还处于公文发展的早期阶段,还带有较强的随意性特征。
在包山简公文书中,人名之后还时而出现或平书或略微斜书的点状符号,如简90的“景得讼繁丘之南里人龚忄求龚酉谓杀其兄”,于竹简上实际写作“景得讼繁丘之南里人龚忄求-龚酉-谓杀其兄”;简63的“九月癸亥之日鄵之市里人殷力可受其兄殷朔执事人早暮求朔力可不以朔廷阩门有败”,于竹简上实际写作“九月癸亥之日鄵之市里人殷力可受其兄殷朔-执事人早暮求朔-力可不以朔廷阩门有败”;简152的“右司马适命左令
正之”,于竹简上实际写作“右司马适-命左令正之”。这些点状符号,包山简整理者最初认为是表示行文断句的“分句号”,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包山二号楚墓简牍概述》,第9页。但陈伟指出,这其实类似于新式标点中提示人名或者地名的专名号“——”。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25页。
除了包山简,同属于楚简系统的曾侯乙墓竹简中也有专门用以提示人名(或御者官名或车名、物名)的符号,作●,如曾侯乙墓简22“裘定所驭左殿”,于竹简上实际作“裘●定所驭左殿”,简65“黄豻驭鄍君之一乘畋车”,于竹简上实际作“黄●豻驭鄍君之一乘畋车”。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493页。虽然如学者所说,这些专名号究竟是在竹简书写时所加,还是后来被校勘或阅读时所补无从得知,并且这些符号的使用还只是一种趋势或者说倾向,施加与否可能往往取决于书写者个人的习惯或者对于有无必要的主观判断,并没有统一规范,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27页。但从记名的角度说,当时对于人名已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开始有意识地对其做些标识性的记号。
三、与秦简公文书人名记写的比较
与楚简公文书人名记写程式有对照意义的是秦简公文书。秦简在年代上多数属于战国晚期,经过秦国对各项制度的变法统一,秦简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记写格式,即使是出自非秦国故地的公文书(如出土于故楚地的里耶秦简),也都遵守着相似的规范。
秦简公文书人名记写与楚简的共同处是也会注意记录相关人员的乡里官职爵位等信息,不同处在于,楚简除了封君、家生奴隶、王室后裔这些特殊并只占很少数的群体外,对大多数人都记姓名;而秦简则是对绝大多数人都只记名,基本不称姓。
如《里耶秦简》8-154正面:“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问之,无当令者,敢言之。”背面:“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邮人得行。圂手。”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编著:《里耶秦简[壹]》“释文”,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在这份文书中,无论发文者“迁陵守丞都”,公文传递者“邮人得”,还是抄手“圂”,都只记官职或官职+名,而不记姓。
又《岳麓秦简(三)》“识劫案”:“十八年八月丙戌,大女子自告曰:‘七月为子小走马义占家赀。义当□大夫建、公卒昌、士伍、喜、遺钱六万八千三百,有券,匿不占吏为赀。有市布肆一、舍客室一。公士识劫曰:‘以肆、室予识。不予识,识且告匿赀。’”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在这份文书中,无论控告人“大女子”,的儿子“小走马义”,被控告人“公士识”,还是相关人员“大夫建”“公卒昌”“士伍”等,都是记作身份+名,而不记姓。此外如睡虎地秦简,虽然其是成文律令的摘抄记录及经过整理的关于司法制度的教习书籍,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并不是真正的一手文书资料,但其在对一手文书档案的模拟中还是保存了只记名的特征。
与秦简有继承关系的汉简,如《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十年七月辛卯朔甲寅,江陵余、丞骜敢谳之。乃五月庚戌,校长池曰:士伍军告池曰:大奴武亡,见池亭西,西行。池以告,与求盗视追捕武。”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这里的“江陵余”“丞骜”“校长池”“士伍军”“大奴武”等,也都只记名而不记姓,踵接秦简的记名方式。
目前所能见到的秦简公文书记名称姓,只在秦户籍简中出现过,里耶户籍简K27:“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妻曰嗛,子小上造□,子小女子驼,臣曰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这一户的户主姓蛮,在记名时予以了体现。又简K17:“南阳户人荆不更黄□,子不更昌,妻曰不实,子小上造悍,子小上造,子小女规,子小女移”,这一户的户主姓黄,在记名时也有所体现。据《商君书·境内》,秦国编定户籍之法,是“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清)严可均校:《商君书》卷一九《境内》,《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3页。出于国家控制国民的刚性要求,户籍文书不得不对国民的身份信息做尽可能全面的登记,因此才记姓,即便如此,也是只登记户主的姓,户主兄弟姐妹和子女的姓尚可由户主推知,但户主母亲和妻子的姓都能省则省。
笔者推测,楚简公文书人名记写重视姓氏的习惯,可能承自周人的制度,因为在带有一定公文书性质的西周册命封赏类青铜器铭文当中,人名大多都称氏,如《班簋》:“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甹王位,作四方亟,秉繁、蜀、巢,令赐铃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铁人伐东国
疒 骨戎,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第4341号。铭文中的毛伯、虢城公、毛公、吴伯、吕伯、毛父等,皆作氏+爵称或尊称的形式。又如《颂簋》:“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三卷,第467页第4332号。铭文中除了被册命者“颂”称名外,其余宰引、尹氏、史虢生等人亦均称氏。
而西周春秋时代的“氏”,其实就是战国以后的“姓”。春秋战国之际,发生过“姓氏合流”的大变革,春秋以前的“姓”和“氏”,统一变成了战国以后的“姓”;春秋以前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称法,也统一转为战国以后无论男女都称“姓+名”的形式。参见张淑一:《姓氏合流论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因而虽然西周金文记名称氏与楚简记名称姓表面上好像不同,但本质上一致,后者对前者应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目前尚不清楚秦简公文书记名多只记私名的做法源于何处,是秦国变法之后对周制的变革,还是秦人原有的习惯,皆不得而知。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等大臣上书秦二世,称“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页。也和秦简一样都是只称名而不称姓。
秦简只记名而不记姓,应该同是出于记写省力的考虑,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识别重名者,大概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假如有同属于甲乡的王乙与李乙,在只记名的情况下,都被记为“甲乡之乙”,一旦发生案件,如何对二者进行有效区分?如果不能区分两者,则势必会对司法或行政工作造成影响。《战国策》秦二“秦武王谓甘茂曰章”载:“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踰墙而走。”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卷四,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18页。可见在当时,因同乡同名而出现案件讹误的情况并非不存在。西汉并有名为审食其、郦食其、赵食其者,《史记·项羽本纪》“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索隐:“郦、审、赵三人同名,其音合并同,以六国时卫有司马食其,并慕其名。”《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22-324页。则若记录不合理,更为复杂的多人重名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
为了避免同名者相混淆,从汉代的做法看,必要时还是要加上姓进行区分。《汉书·霍光传》载霍光等人联名奏罢昌邑王刘贺:“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曰:‘丞相臣敞……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李奇注:“同官同名,故以姓别也”。《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9-2940页。蔡邕《独断》谓汉代百官上书“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按“同姓”当为“同名”之误。参见蔡邕:《独断》,《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页。奏书前面的几人均只称名,但因前面已经有了一位“臣胜”,至夏侯胜时不得不加上他的姓“夏侯”,称他全部的姓名以免于淆乱。
又《后汉书·鲍昱传》记载鲍永之子鲍昱拜司隶校尉,光武帝诏其晋封胡人,鲍昱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光武帝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后汉书》卷二九《鲍昱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22页。也就是说,按照惯例,汉代通官文书是不署官员之姓的,但光武帝为了让人知晓鲍昱乃鲍永之后,特意在文书上注明了他的姓,可见还是要用加姓起识别的作用。
汉承秦制,汉代的做法如此,秦代很可能也是这样做的,即虽然公文书记名一般只记私名而不记姓,但在必要时还是会加上姓以作补充。只是,当公文书面对的不仅是霍光上疏或鲍昱传诏这类只有少数公卿百官的场合,而是面对全国吏民时,单纯依靠这种小修小补恐怕就不足以弥缝程式疏阔的漏洞,会出现各种问题。
相比之下,楚简的年代虽然比秦简早,但其公文书对大多数人皆记录完整姓名的做法却更显合理,更有利于达到识别个体的目的。毕竟,公文书作为国家治世临民的工具,精确呈现个人信息以保证效率,是其最基本的使命。
责任编辑:王坤鹏
A Discussion of the Form of Noting Names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in
Chu Bamboo Slip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Also a Comparison with Noting Names in Qin Bamboo Slips
ZHANG Shu-yi,MING J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China
)Abstract: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Chu and Qin Bamboo Slips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show some general rules in the writing of names. The Chu Bamboo Slips are represented by Baoshan(包山)Chu Bamboo Slips, while the Qin Bamboo Slips are represented by Liye(里耶)and Yuelu(岳麓)Qin Bamboo Slips. The noting of names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Baoshan Chu Bamboo Slips includes different styles including a certain place plus name, a certain persons subordinate plus name, an official position plus name, a family plus name, a certain persons son plus name, somebodys slave, a certain kings plus name, guests plus name, an official position only or titles only, etc. Different naming methods not only distinguish individuals, but also carry out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contrast, there are different forms of omission in noting names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Chu Bamboo Slips, including the omissions of territorial information, surnames, omission of the judges signature of a case and some other irregular omissions. There are also some symbols to indicate the names of people in in the Chu Bamboo Slips, which means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names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to some extent at that time. Noting names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 of Chu Bamboo Slips records the surnames and given names of most people, while Qin Bamboo Slips mostly records private names instead of surnames, which is only added as a supplement in special cases. The habit of recording names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Chu Bamboo Slips may have been inherited from the system of the Zhou Dynasty. Compared with Qin Bamboo Slips,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dentifying individuals and ensure the efficiency of official documents as administrative tools.
Key words:Baoshan Chu Bamboo Slips; Qin Bamboo Slips; noting of names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2.0020
收稿日期:2021-04-12
作者簡介:金洪培,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朝关系史;冯英盾,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
① 参见周延云、宫同文:《建国以来国内外徐福研究述评》,《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赵志坚:《〈史记〉中有关徐福史料的考察》,《古籍研究》,1995年第4期;文贝武、黄慧显:《论徐福东渡日本的必然性》,《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2期;李岩:《三神山及徐福东渡传说新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等。
② 参见牟元珪:《朝鲜半岛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从远古到徐福东渡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编:《韩国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25页;杨万娟:《徐福、韩终东渡传说小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17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436-449页;张云方:《徐福文化及徐福文化研究的意义》,《中日关系史研究》,2010年第1期等。
1770501186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