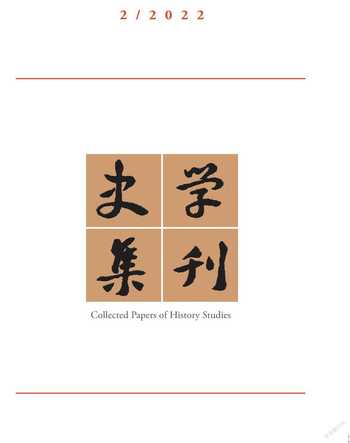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罗检秋

摘 要: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 乾嘉文治;经学;庙堂儒学;信仰世界
关于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论者多聚焦于闭关锁国、科技停滞以及文字狱诸方面,①而对乾嘉两朝在学术及信仰领域的文治偏失关注不够。康熙朝国力渐强,朝野学术互动频繁。清廷在汲取民间理学时,重建庙堂儒学,实现了治统与道统的统一。乾隆朝军事上仍有所作为,但与民间的学术隔膜渐深。较之康熙朝,乾隆帝和嘉庆帝的崇儒、研经流于形式,朝中缺少硕学鸿儒,庙堂理学停滞不前。同时,乾隆帝和嘉庆帝沉溺于礼佛敬神,信仰迷茫。大小官吏多因循怠玩,苟且偷安。这些都加深了潜伏的危机,乃至道光以后积重难返,不能走出历史盛衰的循环。学界对乾隆朝经筵和编书禁书多有研究,也涉及乾嘉汉、宋之学的变化。②但关于乾嘉两朝文治的本质特征,尤其是朝野学术关系仍待探讨,而清廷的信仰世界更值得注意和研究。本文就这些方面再加论析,以探寻历史真相和清朝兴衰原因。
一 、朝野经学貌合神离
清初民间理学复兴后,康熙帝关注民间学术态势,汲取了民间理学精华。在此基础上,清廷彰明道统,实现了治道合统的政治文化格局。但至乾隆年间,民间学术已非清初旧貎,江南学术主流已从理学转向汉学。乾隆朝崇尚经学,似乎与民间汉学不无契合,然而二者思想上多异其趣,甚至背道而驰。
乾隆初年既尊程、朱理学,又倡导经学,其举措包括经筵讲学、广布经书、以经取士、荐举经师、访求遗书等,从而延续了康雍文治的措施,并稍加调整。乾隆初年荐举经学人才偏重形式,最后仅荐举了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授以国子监官职,而许多民间经学家如惠栋等人皆摒弃未取。可以说,乾隆帝的主旨并非发现经学人才,而多出于附庸风雅,做出崇儒重道的姿态。这与康熙朝选拔、重用儒臣已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帝认为“视前明《大全》之编,仅辑宋、元讲解,未免肤杂者”,与康熙帝御纂的《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相去悬殊”,故于乾隆元年(1736)即敕各省刊刻御纂经书。《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乾隆元年四月辛卯条,《清实录》第9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8页。乾隆三年(1738),又谕训科考当以经义为重,士子应“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乾隆三年十月辛丑条,《清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4页。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敕词臣重新校刻《十三经注疏》。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乾隆南巡时强调“经史,学之根柢”,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藏于江宁、苏州、杭州的著名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乾隆朝的编书机构,前有三礼馆,后有四库馆。三礼馆持续19年之久,前后馆臣共百余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开四库馆,延揽通经博古之士,给予官职、俸禄,从而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向。章学诚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指出:“三十年来,学者锐意复古,于是由汉、唐注疏,周、秦子纬而通乎经传微言,所谓绝代离辞,同实殊号,阐发要妙,补苴缺遗,可谓愈出而愈奇矣。至四库馆开,校雠即为衣食之业。” (清)章学诚:《与钱献之书》,(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94页。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民间学者已经转重考证汉、唐注疏,虽然开馆校书为“衣食之业”,但在此过程中,民间学者崇尚的经学考据、由宋返汉的学术走向也对朝廷有所影响。收藏《四库全书》的扬州文汇、镇江文宗、杭州文澜三阁成为江南图书的聚积传播中心,于学术文化亦不无裨益。
经筵在乾隆朝延续下来,但实质內涵已有变化。康熙经筵上,君臣切磋理学,互有问答。讲臣常贯通经术和治术,涉及治平之策。朝纲独断的乾隆帝不愿像先祖那样接受“启沃”,而好发御论。乾隆三年首次经筵乾隆帝就大发御论,被讲臣颂为“以惟精惟一之心,成中和位育之治,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圣训精微,诚足昭示万世,臣等不胜钦服”。《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乾隆三年二月丙午条,《清实录》第10册,第31页。并且,乾隆帝反对讲臣言政:“朕命翰林科道官轮日进讲经史,本欲研究经术,阐明义理,以淑心身,以鉴兴废。而诸臣讲论,往往阑入条陈。若实有裨政务,则亦何害?要不当借端立说,以逞私见也。”《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七,乾隆十一年十月丙戌条,《清实录》第1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0页。由此可知,乾隆帝一开始就君师兼作,圣王自命,这自然无须儒臣们开导、建言,也不可能关注民间的学术趋向。
粗略统计《清实录》使用“经学”一词的频率,乾隆朝位居各朝之首,约37次。其次则是康熙朝,约7次。这虽与历朝《清实录》的篇幅大小相关,但根本上缘于学术风气。清廷所谓经学,并非独尊汉学,而是笼统地提倡研究儒经,无分汉、宋,但在凸显实证研究,摒弃空谈性理,注重考据学方法等方面与民间汉学不谋而合。乾隆中期以后,朝廷不再独尊朱子,看起来与民间汉学十分契合。但细加分辨,乾隆朝的官方经学与民间汉学反差鲜明。
首先,清廷并不像民间学者那样青睐汉学。《清高宗实录》中儒学、经学一词明显增多,汉学一词则从未出现。乾隆《起居注》也未提到汉学一词。可知乾隆帝倡导经学,却不认同民间尊崇汉学的取向。《清儒学案》曾谓:“有清一代经学,以汉学为盛,而康、乾两朝御纂诸经,汉、宋兼采。乾隆中,荐举经学,为一时旷典,被擢者皆宋学也。”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五六《震沧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95页。质言之,乾隆帝提倡经学,却不独尊汉学;质疑朱子,却未打压宋学人物。乾隆晚期,朝内外出现了几位汉学官僚,但绝大多数汉学家仕途困蹇。
嘉庆朝没有放宽乾隆后期以经取士的严格标准。嘉庆十一年(1806),有御史奏请科考改为五经轮试,嘉庆帝谕云:“士子读书应试,自当通习诸经,敦尚实学”,“且现值经学倡明之会,应试诸生读五经者日多”,所奏“直为荒经者开一自便之途”,不可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1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7、488页。同时,嘉庆朝的经筵讲学也有严格定制。查《清实录》,除嘉庆四年(1799)、嘉庆五年(1800)因守制停止经筵外,其他年份均在二月(少数年份一月)或八月(嘉庆六年,1801)举行经筵,嘉庆十九年(1814)则春、秋两季皆有经筵,嘉庆朝共计举行了24次。《清仁宗实录》罕见理学、宋学等词,但经筵和殿试策问对其主题比较重视。嘉庆经筵所讲多为四书五经的常见文句,御论简白无华,而不像乾隆帝御论那样获得大量颂词。此时,汉学已经风行民间,但该词在《清仁宗实录》也仅出现一次,即嘉庆十四年(1809)殿试策问“言《易》首称汉学,其授受源流,皆有可考”。《清仁宗实录》卷二一○,嘉庆十四年四月庚戌条,《清实录》第30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1页。这表明嘉庆帝一方面对民间学术已略有注意,另一方面仍未将汉学作为庙堂儒学的资源。
再则,一些民间汉学家,包括后起的今文家重释儒学主题,有的还在批判理学中重建思想体系。在朝经学家中虽然也有类似学者,但却不能久居朝堂。乾隆帝欣赏朱筠、王引之、阮元那样偏重考据而缺少思想的能臣,而不能容忍有思想的经学家,如钱大昕、戴震等人。嘉庆年间,今文经学正在江南蓬勃兴起,但常州庄氏之学也未受到朝廷注意。故在乾嘉时期,官方经学对民间汉学的思想主题缺少认同。因此,在乾隆帝崇奖经学的同时,毁禁书籍和文字狱都达到高潮。据研究者不完全统计,清代大的文字狱始于顺治朝,康熙朝61年中不超过10起,雍正朝13年里共有20多起,而在乾隆朝的60年中,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在130起以上。郭成康:《乾隆帝——盛世光环下的多面人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第393页。乾隆朝毁销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从近年北京出版社编印的《四库禁毁书丛刊》亦可见一斑,而这不过是其中的极少部分。
乾隆帝垄断了作为经学灵魂的道统及儒学话语权,也不断从政治上打压儒家有思想或标志性人物。比如,清廷虽然在礼制上尊孔,但因衍圣公孔昭焕“袒庇庙户”“不知安分自爱”,部议革去公爵。乾隆帝一再降旨训斥后,开恩免革公爵,令其闭户读书,并表示:“倘仍怙终不悛,再敢干预公事,则是自取罪戾,毋望倖邀格外恩也。”《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己酉条,《清实录》第1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页。乾隆帝对“孔继汾案”的处理更为严厉。孔继汾为乾隆朝进士,以衍圣公叔父身份主持孔府事,所撰《孔氏家儀》一书被人告发增减了《大清会典》的仪节。孔继汾以纯属“家庭仪节”、不关朝廷礼制辩解,但仍被革职问罪,充军边疆,卒后不能归葬孔林。由此可知,乾隆帝始终将儒学、衍圣公、祭孔这些文治工具严格控制在手中,不像康熙帝那样显示对儒学、道统的信仰和尊崇。在乾隆帝的谕旨中,对汉族士人的训斥之词,如“腐儒”“习气”之类比比皆是。
综上,乾隆年间,朝野经学在形式上虽有相似,但朝廷对民间学术缺少关注和汲取,二者精神实质多异其趣,也可谓貌合神离。
二、庙堂儒学虚应故事
康熙帝重用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理学名儒,切磋学术,采纳计策,建立了庙堂理学,也以理学教化士民。乾隆帝早年受蔡世远、朱轼等理学官僚的熏陶,故延续了康、雍两朝尊崇理学的策略。乾隆三年二月重开经筵,同年八月的经筵御论亦谓《书经》“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一语“是言人君主敬之学也”,讲臣赞颂乾隆帝“治崇宽大,学本主敬”,《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乾隆三年八月癸未条,《清实录》第10册,第174、175页。这表明乾隆帝承续理学主题的姿态。乾隆初年沿袭前朝的儒学政策,谕告臣子们究心理学:“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条,《清实录》第10册,第875-876页。然而,乾隆元年佥都御史李徽请定《孝经》入《四书》之列, 以及请程颢入祀孔庙大成殿的奏疏均被否定,被指增祀之举会使无知效尤,“或穿凿经义,或托名理学,自便其私,大为世道人心之害”。《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乾隆元年二月戊辰条,《清实录》第9册,第364页。这种表态不无道理,旨在抑制尊崇宋学势头的发展。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谕云:“宋、元以来辨析朱、陆异同,初因讲学,而其后遂成门户,标榜攻击,甚为世道人心之害。嗣后有似此者,必治其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13册,第149页。这表明朝廷对理学各派不存门户之见,实则已经疏离了独尊程、朱的轨道。乾隆帝前期也讲“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类主题,但“惟以主敬存诚,孜孜自勉,以求保泰之道”。《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乾隆二年五月戊子条,《清实录》第9册,第747页。 “保泰”之策在无形之中限制了庙堂理学的发展。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乾隆帝已不再独尊朱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经筵,儒臣讲《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御论曰:“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诚之外无性,明之外无教……朱子谓与天命谓性,修道谓教,二字不同。予以为政无不同耳。”《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甲辰条,《清实录》第15册,第385页。此类情形,不一而足。乾隆五十六年(1791),经筵讲官讲《论语》“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和《尚书》“允执厥中”;《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二,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上庚戌条,《清实录》第26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页。 乾隆五十七年(1792)经筵讲《易经》“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六,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甲辰条,《清实录》第26册,第743-744页。乾隆五十八年(1793)经筵讲《中庸》“至诚无息,不息则久”。《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二,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上己巳条,《清实录》第27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针对这些经筵讲章,乾隆帝“御论”均立异于朱子注解,与康熙、雍正二帝尊崇朱子形成鲜明反差。有论者统计,在乾隆帝60年中,经筵讲学凡举51次。其间,自乾隆二十一年迄康熙六十年(1795)的32次经筵讲学中,乾隆帝均明显地向朱子学提出质疑,竟达17次之多。 陈祖武:《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乾隆帝立异于朱子经注,而不自觉地走向董仲舒的谶纬儒学。乾隆十九年殿试策论虽讲“天即理也”,但尤重董氏天人之学:“朕宵衣旰食,于天人感应之际,理道制治之原,整躬以率物,劝学以兴贤……董仲舒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又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已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遂借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一,乾隆十九年四月乙巳条,《清实录》第1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8-989页。《论语》中“仁者先难而后获”一句,朱注为孔子告诫樊迟,“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卷三,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5页。乾隆三十九年(1774)经筵御论认为:此语非就樊迟惑于鬼神而言,而表明了孔子论仁之旨,与回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意同。乾隆帝排斥朱子所述儒家“不惑于鬼神”的思想,却青睐“复礼”主题,赞赏董仲舒的儒学。正如乾隆帝后来所云:“人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兢兢业业,以绵亿万载之丕基。”《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条,《清实录》第2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6页。这种认识导致其主观上想超越宋学,实际上难开生面,只能重复董仲舒的“大一统”、天人感应之类旧题。
乾隆帝重视纲常伦理,有时很有己见。乾隆五十年(1785)经筵讲《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兹,与国人交止于信”一章,御论肯定此“实训万古五伦之要道”,且推而广之:“为君者,匪惟博施济众以为仁,即瘅恶弼教之义,亦必当本于仁而出之,所谓止也。人臣之敬,讵其夙夜匪懈、恪躬承旨之谓?即绳愆纠谬、陈善闭邪,亦必当本于敬而出之,所谓止也。”对“与国人交止于信”一句,御论解释为“兄友弟恭”“夫唱妇随”“朋友之信”,但于原文所言文王“与国人交止于信”只字未提。《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四,乾隆五十年二月丁亥条,《清实录》第2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408页。显然,乾隆帝较之朱注凸显了君主教民、臣子改过的蕴含,而于君主道德规范略而不谈。乾隆四十五年(1780)殿试策问又云:“孟子述道统之传,自尧、舜以至于孔子,盖谓心法治法同条共贯也。然帝王之学,与儒者终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30册,第93页。朝廷对儒学的教化和治平功能有所区分,淡化了理学的社会价值。
乾隆帝并未着意从儒学中汲取文治资源,而始终凌驾于道统之上,也不像其父、祖那样容忍朝野理学的发展。比如,雍正朝的谏臣谢济世生性耿直,而于理学不乏己见。他既指責陆、王背离孔孟而废学问,又反感独尊程、朱,认为宋儒于“孔孟名宗之而实畔之”。朱子讲“气质之性”亦有悖孔孟,因为“孔孟言性有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大相剌谬,实为获罪于圣门也”。(清)谢济世:《谢梅庄先生遗集》卷二《原性》,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雍正年间,谢氏注疏《大学》《中庸》,结果被劾“诽谤程、朱”,幸得雍正帝宽宥免究。谢氏将《学庸注疏》稍加修订后,又于乾隆元年正月再呈朝廷,提出经学“但当发挥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张、朱”。(清)谢济世:《谢梅庄先生遗集》卷一《进学庸注疏疏》,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66册,第119页。奏疏被乾隆帝斥为“肆口诋毁,狂悖已极”,“亦不自量之甚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1册,第58页。朝廷下令销毁其《学庸注疏》。乾隆七年(1742),谢氏再被人参劾“托名理学”“踰闲荡检”而遭革职。《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九,乾隆七年十一月甲戌条,《清实录》第1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7页。谢济世的理学驳杂肤浅,虽不乏新意,但在乾隆朝却不可能生长起来。谢氏被惩处后,标榜理学者销声匿迹。大小儒臣学而不思,甚至不学不思,广大士子则如乾隆帝谕云:“今学校遍天下,山陬海澨之人,无不挟诗书而游庠序,顾学徒以文艺弋科名,官司以课试为职业,于学问根本、切实用功所在,概未暇及。”《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乾隆五年十一月辛未条,《清实录》第10册,第895页。终乾隆一朝,此类谕令时有,大体流于官样文章。理学仍有正统门面,却只是虚应故事。
乾隆帝喜好书法、绘画、文学,着迷于写诗和艺术收藏。“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清)昭梿:《纯庙博雅》,《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页。这些雅好表明其热爱、熏染于汉文化,但与文治思想关系不大。乾隆帝虽讲“十六字心传”,但对如何贯通心法和治法却缺少心得。质言之,他受汉文化的熏陶偏重于文学、艺术,而疏于思想、学术,不能从儒学中汲取文治思想。因此,乾隆帝之于科技,既不像江南汉学家那样重视天文历算,又不像嗜好理学的康熙帝那样留心历算学,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兴味盎然。康熙帝的科技兴趣成为兼作君师的践履途径之一,多少对构建治道合统有所裨益。乾隆帝肯定“朱子具格致诚正之功,明治乱兴衰之故”,《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三,乾隆十一年闰三月丁巳条,《清实录》第12册,第408页。却对天文历算及西学没有兴趣。如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带来了代表西方科技水平的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船只模型等礼物。然而,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却不屑于了解“夷人”的仪器、机械,亦未令人研究。显然,清廷最高统治者对近代科技麻木无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嘉庆帝不像其父那样贬抑朱子,经筵时较为平实地阐明宋学主题。如嘉庆三年(1798)经筵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句,御论认为此句“为道统之渊源,而内圣外王之纲领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3册,第36页。嘉庆十三年(1808)经筵御论强调“存诚去私”,谓《中庸》一书“大本在诚”,当不受“气禀”“物欲”所限,“必用克己之功力,复夫天理之纯常”。《清仁宗实录》卷一九二,嘉庆十三年二月庚午条,《清实录》第30册,第534页。翌年经筵讲《中庸》“修道之谓教”,御论云:“天之生人,各正性命。性有善有不善之分,则在道有修有不修之故耳。”“道由性而出,由教而明”。《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嘉庆十四年二月壬辰条,《清实录》第30册,第763-764页。这些御论缺乏新意,但较之乾隆帝,嘉庆帝更重视道学,并且对其主旨有贯通表述。
嘉庆帝反复阐述程、朱主敬说,认为“君子之学,莫大乎主敬。圣人之道,莫要于执中”。《清仁宗实录》卷二二五,嘉庆十五年二月乙丑条,《清实录》第3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故其重视阐述“十六字心传”,以期融通心法和治法。嘉庆元年(1796),殿试策问首先指出:“人心道心,肇阐虞廷。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心也……心之用,主乎敬。”《清仁宗实录》卷四,嘉庆元年四月丙申条,《清实录》第2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6页。嘉庆四年殿试策问,首题也是“溯圣学之源者,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然允执厥中,实为治世之枢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4册,第246页。嘉庆十六年(1811)殿试策问重申“危微精一之旨,为帝王道统所开”,“朱子谓《大学》之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一敬”。 《清仁宗实录》卷二四二,嘉庆十六年四月戊辰条,《清实录》第31册,第265页。在嘉庆朝,“十六字心传”“主敬”说一直是经筵、殿试的主题。其主敬之旨不囿于内圣功夫,而较切近世事。嘉庆七年(1802)殿试策问提出:“程子赈济之论,曾巩救荒之议,朱子画一事件之状,有可行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7册,第176页。可见,朝廷此时也注意到道学家的治平之策。嘉庆十年(1805)经筵,嘉庆帝就“居敬而行简”指出:“行政必归于简易,则民知所从矣”。如何“简易”?“居心于敬,兢业求安。存诚于内,而勿自纷烦。惕厉于中,而无敢肆慢……孔门论古帝王之心法治法,胥在于是”。《清仁宗实录》卷一四○,嘉庆十年二月己未条,《清实录》第29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1页。这种治国思想不仅有裨于朝政,而且有助于朝野士大夫转向调和或兼采汉、宋之学。
“主敬”“执中”落实于治平之策的表现之一,是嘉庆帝的文治政策较为宽容。“为政以德”是儒家治国的根本理念,嘉庆七年经筵御论云:“平时克谨常宪,渐仁摩义,动静皆循礼法,则临民莅政,各得其真情实事,风化可臻淳朴矣……君心正,天下莫不归于正。诚为治本,道德齐礼,化民之要,以一人之心德,感天下人之心。可期兴起孚应,鲜有犯法之民,则政简刑清,庶几无为而治。”《清仁宗实录》卷九三,嘉庆七年正月庚子条,《清实录》第29册,第248页。在重复以德治国主题时,嘉庆帝注意“君心正”,向慕“政简刑清”“无为而治”。嘉庆十一年,江苏巡抚汪志伊奏请颁发“御制诗文集”于江南各书院,嘉庆帝谕云:“朕之政治即文章,何必以文字炫长,所请不必。”《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三,嘉庆十一年六月甲辰条,《清实录》第30册,第121页。这与乾隆帝好自显才学的风格形成鲜明反差。
因朱珪等大臣的疏请,嘉庆帝渐弛书禁,基本上停止了文字狱。这虽然基于汉族士人的反清意识趋于淡化,但与理学对清廷的潜移默化影响具有很大关系。嘉庆朝似乎重回以理学治国的轨道。尽管如此,嘉庆朝的庙堂理学没有新意,理学的文治功能没有彰显出来,也远未达到康熙朝的效果。此时,民间的学术大家转趋汉学,而缺少理学名家。在庙堂之上,嘉庆帝“皆循礼法”,重在“守成”,没有擢拔有创见的理学儒臣。同时,嘉庆帝也像其父祖一样痴迷于天人感应,他反复强调:“理本于天,人君代天赞化,敷言纯乎天理,非人君所自为训,即上帝之训也。” 《清仁宗实录》卷一四,嘉庆二年二月癸酉条,《清实录》第28册,第200页。 他所谓人心也是天人交感的落实途径:“天人交感之理,无时不在人心,范围曲成,造次颠沛,不可须臾暂舍。久道化成,成己成物之功,胥于是系。”《清仁宗实录》卷一○七,嘉庆八年正月甲午条,《清实录》第29册,第440页。因此,庙堂儒学仍笼罩在天人之学中,没有彰明治平之学的理论和价值。整个乾嘉时期,民间理学暗淡无光,庙堂儒学无所作为。
三、信仰世界多歧亡羊
士民信仰是一代文治的基石。乾嘉时期,庙堂理学既已停滞不前,那么何以教化万民,有效地践履文治举措?礼制无疑是其重要依赖。“清初定制,祭凡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天子祀天地、宗庙、社稷。有故,遣官告祭。中祀,或亲祭,或遣官。群祀,则皆遣官”。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八二《礼一·吉礼》,第2485页。清朝皇帝的祭祀活动未必完全受礼制约束。乾隆朝政治稳定,道统完全纳入治统的控制之下,象征传承儒学和道统的祭孔礼已不如清初那样重要。乾隆帝和嘉庆帝经常不亲自参与“中祀”祭孔,却有时亲祭“群祀”诸神,这就真实地反映了他们信仰世界的本质特征和实用取向。
查“实录”“起居注”可知,敬祖祀神是乾隆帝和嘉庆帝的日常事务。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亲祀神佛的活动日益频繁。清代皇家的御园内均建有不少佛寺,如北海的阐福寺、小西天、萬佛楼,圆明园内的安佑宫,长春园内的法慧寺、保香寺,清漪园内的大报恩寺、须弥灵境,香山的永安寺、实胜寺、宝相寺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由雍亲王府改建的雍和宫。那时京师内外,大刹林立,傍晚钟声相应,也便于君主、宗室随时祭祀。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第396页。登基五年之后,乾隆帝便频繁巡游。一生五巡五台山,六次南巡江浙,五到曲阜。乾隆十六年以后,承德山庄避暑、秋狝木兰也是乾隆帝每年的必备项目,出巡途中常有很多祭祀活动。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乾隆帝起居注》为例,可见其南巡之年的祭祀情形。
综上粗略统计,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共有87天祭祀活动,其间可能兼理政务,但祭祀是主要日程。皇帝没有外出时,参与京城及附近的祭祀仍然不少,每年总有数十次之多,这在乾嘉时期成为惯例。综观之,乾隆帝祭拜的神祇包括(1)祖宗、帝王类,如太庙、奉先殿、寿皇殿等;(2)佛教类,如雍和宫、永济寺、永安寺、开福寺、观音寺、觉生寺、弘仁寺、天宁寺、定慧寺、大佛寺、阐福寺等;(3)道教类,如大高玄殿、白云观、无为观、玄妙观、斗母宫、宗阳宫等;(4)天地山川类,如圜丘祭天、天泽祭地、城隍、龙王、禹王、河神、江神、海神、风神等;(5)古代圣贤类,如文庙、关帝庙、少昊陵等;(6)其他民间诸神,如药王庙、花神庙、火神庙、医神、蚕神及时令节日神等。
“万乘之尊”的乾隆帝几乎逢庙必拜,这似乎令人费解。这些祭祀虽然偏重仪式,但却与乾隆帝的信仰观念分不开。如果说,乾隆帝不是虔诚的佛、道信徒,那么其多神信仰的特色则是鲜明可见的。当然,正如民间祀神礼佛一样,其中包含了实用主义取向。比如,水旱灾频繁会被视为上苍示警,一旦祭祀“显灵”,清廷也会发谕谢恩。如乾隆三年祭龙神之后,乾隆帝鉴于黑龙潭龙神“祈祷必应”,特加“昭灵沛泽”神号四字。《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乾隆三年五月丁卯条,《清实录》第10册,第103页。同时,乾隆帝改“常雩”(祈雨)为大祀。据说乾隆帝作太上皇时,一日早朝后召和珅入对:
(和珅)至,则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杌。珅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久之,忽启目曰:“其人姓名为何?”珅应声答曰:“高天德、荀文明。”上皇忽闭目诵不辍。移时,挥出,不更问。仁宗大愕。越日,密召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云何,汝所对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诵之,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对也。” 易宗夔:《新世说·术解第二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8年,第180册第393-394页。
这则传闻无疑与乾隆帝的信仰观念完全吻合。嘉庆帝如同其父,每年也有数十天往京内外的佛寺、道观拜祭,对龙王、河神、雨神的祈拜也随着天灾频繁而增多。比如,《清实录》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乙亥,京城忽起风沙,嘉庆帝“心中震惧”,“惕思上苍警示之因”,随即谕云:“内外大小臣工,各当自省咎愆,殚心竭力,共勤职业,以副朕修德弥灾之意。”《清仁宗实录》卷三四一,嘉庆二十三年四月丙子条,《清实录》第3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1页。
同年四月,京师一带久旱不雨,嘉庆帝再命于黑龙潭、觉生寺设坛祈雨。“庚辰,上诣黑龙潭神祠拈香”。又命诸皇子分赴天坛、地坛、太岁坛祈雨。《清仁宗实录》卷三四一,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庚辰条,《清实录》第32册,第506页。次日, 京畿等地下雨。四月丁亥,嘉庆帝“以祈雨三坛斋戒一日”,次日亲“诣天神坛,命仪亲王永璇诣地祇坛,成亲王永瑆诣太岁坛祈雨”。并命皇次子旻宁诣黑龙潭、皇四子绵忻诣觉生寺祈雨。此外派内阁学士赴密云白龙潭等处祈雨。《清仁宗实录》卷三四一,嘉庆二十三年四月戊子条,《清实录》第32册,第511-512页。几天后,因得雨报,嘉庆帝“谢三坛,斋戒一日”。次日嘉庆帝“诣天神坛”,诸亲王分赴各坛“谢雨”。《清仁宗实录》卷三四一,嘉庆二十三年四月甲午条,《清实录》第32册,第513页。从清廷是年四月的祈雨活动,可见其信仰及祭祀之一斑。乾嘉年间,中原地区没有大规模战争,而自然灾害时有。遇有水旱蝗灾,朝廷照例会放赈蠲租,但祈求神灵也是乾嘉二帝的日常事务。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照例赴热河秋狝木兰,途中有中暑症状。七月二十四日至热河,“仍办事如常,诣城隍庙拈香,永佑寺行礼”。二十五日,症状未见好转,仍赴“溥仁寺、普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拈香”。当晚病情加重,遽然而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22册,第275-276页。嘉庆帝虔诚地信仰诸神,却因此错过了治疗时机。
其时最高统治者的知识水平没有超越前人,甚至不及同时的有识之士,而广大士民的信仰世界更加混乱不堪,成为滋生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沃土。乾嘉年间,士人的结社、讲学低落,而民间秘密宗教迅速膨胀,反清事件接踵发生。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70余名天理教徒在首领林清率领下攻入紫禁城,虽然事件很快被平息,但其产生的震动经久不息。心有余悸的嘉庆帝下了“罪己诏”,采取措施根除邪教,包括查禁邪教书籍,强化法律和保甲制度等。
此后,嘉庆帝在经筵时尖锐地指出:“人心不正之故,总由邪说横行也。其咎在上而不在下,盖有故焉!为人上者,不能彰明教化,宣扬礼义。司牧之官,惟知尸禄保位,视民如草芥。德不修,学不讲,乃有奸徒煽惑,假邪说以诬民,愚顽自趋陷阱而不觉。”《清仁宗实录》卷二八四,嘉庆十九年二月甲午条,《清实录》第31册,第875页。这番议论表达了嘉庆帝的关切,可谓切中肯綮。事实上,他不像康、雍、乾三帝那样注重开疆拓土,但关注于平息邪教,曾谕令臣僚云:“若惩一儆百,使乡曲愚氓,皆知邪教为必不可习之事,渐染日少,所保全者众矣。诸臣当明于大义,为国家除邪去慝,不可存妇孺之仁,而忘弭患于未形也。”《清仁宗实录》卷三一二,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己亥条,《清实录》第32册,第148页。较为典型的事例是,林清事件后,嘉庆帝召见近臣王引之,对答良久,具体内容旁人不知。次年,王引之受命视学教民丛生的山东,作《阐训化愚论》《见利思害说》等文,以教化士民,整饬风俗。这似乎在地方教化中凸显了儒学价值,但王引之那样有为的儒臣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官吏“日视其民之陷于匪僻,罹于饥寒,而莫之省。肆行邪教,而不能禁”。《清仁宗实录》卷三五四,嘉庆二十四年二月乙酉条,《清实录》第32册,第677页。
面对重重积弊,虽然嘉庆帝经常发布谕令,但收效甚微,“彰明教化”也落得为而不能。事实上,清廷祭拜神祇的情形一直延续到同光时期,大体没有变化。当清廷指責愚昧草民为邪教所惑,掉进大逆不道的陷阱时,其自身的信仰世界并未显示更高境界。这种精神状态的统治者自然不易驾驭一个庞大复杂的帝国,一遇突发事件,势必手足无措,危机四起。
余 论
乾隆后期,清王朝虽然仍是巍巍大厦,但其梁柱已经迅速腐朽。就其主要外在表现而言,首先是贪腐风气不可扭转。乾隆中期,贪腐仕风趋于严重,乾隆帝虽有认识,却“不肯令人告讦,惟俟其自败,即行按法惩治”。《清高宗实录》卷七七六,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丁卯条,《清实录》第1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0页。他惩治了一些贪污官吏,却没有触动更多的贪赃枉法者,尤其是和珅一类狡诈宠臣。乾隆一生好巡游,讲排场,多庆典,其八十寿辰的庆典,奢华隆重为史所未有,总计花费114万多两白银,由各省臣民分摊输供。乾隆帝己身不正,又无健全制度,自然不能制约庞大的官僚集团。嘉庆帝继位后,强调“俭为美德,贵乎有节。天地有节,则四时流行。王者有节,则庶民藏富……节者,中也,无过不及之谓也。若矫情拂理为苦节,穷奢极欲为不节,皆失中道,不得节制之宜矣”。《清仁宗实录》卷一二六,嘉庆九年二月壬戌条,《清实录》第29册,第694页。这对官场奢靡风气不无告诫、约束之效,但乾隆后期形成的腐朽仕风已经不可挽回。事实上,嘉庆帝六十寿辰也是“自都城至圆明园数十里中,棚坊楼阁,华丽炜煌,与乾隆时相埒”。(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1页。统治集团的奢华风气并无根本改变。
其次,“因循怠玩”的仕风弥漫官场。嘉庆帝勤于理政,并于嘉庆十二年(1807)发谕申明“求治以勤政为本”,指出各省“督抚养尊处优,不思勤以率属……以致属员等罔知儆惕,任意弛废,于地方事件毫不介意”。《清仁宗实录》卷一七四,嘉庆十二年二月甲申条,《清实录》第30册,第287页。然而,几年后即惊现林清案,嘉庆帝再斥仕风:“今之大弊在因循,大病在怠玩。因循则庶政不勤,怠玩则视民如草。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并无实惠,慢易居心,悠忽度日。此等具臣,即尧、舜、汤、武遇之,亦难图治,况中才之主乎?”《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二十年六月戊辰条,《清实录》第32册,第78页。所谓“因循怠玩”,既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又是敷衍塞则,欺上瞒下。嘉庆帝认识到官场积弊,却又无可奈何。
其三,更严重的是最高统治者不通下情,大小官吏为了自身利益,有意、无意地阻隔了信息传播。这似乎便于控制民众,粉饰太平,而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则朝廷难免发生误判和做出错误决策。嘉庆二十一年(1816),当英使阿美士德来华时,清朝君臣恼怒英使“不遵仪注”,命令英国以后不必遣使来朝,遑论中外正常商贸了。在中西隔绝中,英商最终采取卑劣手段,通过贿赂、勾结地方官吏,向中国输入鸦片,悄无声息地腐蚀着清帝国。
这些积弊固然与社会制度相关,而就朝政来看,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清廷文治的偏失。文治武功是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想,所谓文求其治,武显其功。清代乾嘉时期被视为文治武功的高峰。此时疆域辽阔,国力强盛,俨然追踪汉、唐盛世。乾隆帝被尊谥“敷文奋武”,嘉庆帝也有“崇文经武”的尊号,表现了兼重文武的姿态。清朝对孔庙和关帝庙的祭礼都相当隆重,象征着礼制上文武并重。然而,清廷崇尚武功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帝谕礼部:“今八旗人等专尚读书,有子弟几人,专令读书,不肯习武,殊违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 (清)席裕福、(清)沈师徐辑:《皇朝政典类纂·学校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第894册第3853页。清朝建国数代之后,八旗子弟的教育出现了重文轻武趋向,故乾隆帝指出:“我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废武?”他要求满族子弟“凡乡、会试,必须先试弓马合格,然后许入场屋,故一时勋旧子弟莫不熟悉弓马”。 (清)昭梿:《不忘本》,《啸亭杂录》卷一,第16页。清廷的八旗教育方针恰恰是治国理念的表征。事实上,乾隆帝自称一生有“十全武功”,以此张扬其治国功业。乾隆三十三年(1768),鉴于关公“尤昭灵贶”,朝廷加封其“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称号,《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己丑条,《清实录》第18册,第890页。
即是清朝尚武的表现。清朝以马上得天下,乾隆帝骨子里仍是重武轻文。
武功高低取决于战争胜负,这显而易见。文治立基于潜心教化,幽微难明,也难以准确地把握施行。乾隆帝的一些文治举措,如编纂图书、荐举经学人才、举办经筵等项,都暗含赶超其祖之意,但他不像康熙帝那样虔诚地崇信、究心儒学,故除了强化文字狱一类的高压政策外,尚缺少积极、精准的文治措施,不仅显得文治乏力,而且实效甚微。嘉庆帝主观上想作有为之君,却只是守成而已。因此,清中叶不可避免地形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历史上的武功文治往往产生令人目眩的光环,导致后人对历史全貌认识不清。清王朝之所以在道光以后一遇西方列强就不堪一击,固然在于东西方历史的阶段性差异。但就清廷的治国方略来看,文治偏失亦可谓其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责任编辑:孙久龙
Changing from Prosperity to Decadence of the Qing Dynasty: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during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LUO Jian-qiu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Many latent crises embedded in the Qing history during the flourishing Qianlong period. The imperial cour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whereas it would not recognize Han Learnings ideology transmitted unofficially. Although it inherited the official Neo-Confucianism, the court made no progress in either theory or practice, and suppressed the booming of Neo-Confucianism developed by both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scholars. At the same time, the faith world of the court was very confused and superstitious. Thereafter, Emperor Jiaqing adjusted his policy of Classics studies,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Neo-Confucianism again. He also advocated diligence and frugality in administration. However, it is almost of no help. Even though the court had acquired outstanding military achievement, it lost in cultural governance, which is one of the critical reasons why the Qing declined.
Key words:cultural governance during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imperial court Confucianism; faith world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2.0015
收稿日期:2021-06-12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苏联核计划档案文献资料翻译整理研究”(15ZDB064)
作者简介: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俄国经济史和社会史;高腾,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参见Рябев Л.Д.(общ.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Ⅱ,Кн.1.Саров.:РФЯЦ-ВНИИЭФ,1999.С.11-14.
② 全称荷电粒子加速器,它是使带电粒子在高真空场中受磁场力控制、电场力加速而达到高能量的特种电磁、高真空装置。参见桂伟燮编:《荷电粒子加速器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③ Рябев Л.Д.,Кудинова Л.И.,Работнов Н.С.К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1938—1945).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40-е—50-е годы).Т.1.М.:ИздАТ,1997; Paul R.Josephson,“Early Years of Soviet Nuclear Physic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43,No.10 (1987),pp.36-39 ; 刘玉宝:《早期苏联核计划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
2322501186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