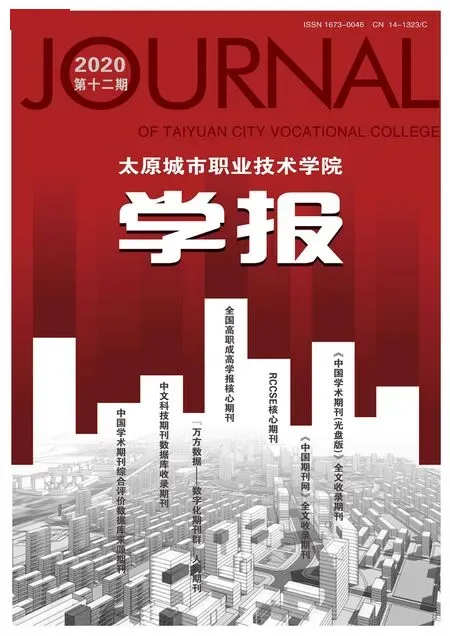试论江总文学思想形成的时代原因
■张慧芳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7)
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生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年),幼时聪敏、好学而有辞采。所作诗为梁武帝所嗟赏,任侍郎。张缵、王筠和刘之遴都很器重他。历仕梁、陈、隋三朝,卒于江都。初因得后主爱幸,常与后主饮宴赋诗,写有为数不少的艳体诗。后主荒于政务,陈朝快速灭亡,作为后主辅政权宰的江总,入隋后又官至上开府。所以,江总也历来被史家和一些文人所诟病。然而政治上的失误并不能抹杀其文学上的造诣,江总是当时文坛比较活跃和重要的文学家,五言七言均有佳篇。其文学思想不仅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而且影响了隋唐以后的文学思潮。
一、南朝的文学思潮
梁代文学思想十分活跃,诗坛上回响着不同的声音,有以“裴子野”为首的复古派,萧统一系的通变派,还有萧纲等人的新变派,然而随着裴子野、萧统等人的相继辞世,再加上“新变派”的文学理论更符合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于是萧纲携皇储之势,在一批追随者的积极拥护下,最终赢得文坛盟主地位。其文学思想也在诗坛大行其道。
新变派的文学思想体现在萧纲及其同时代人的一些书信和文学评论中,如: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说:
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
在此,萧纲要求诗歌表现“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簿”的感受,甚至提倡边塞生活,总的要求是“寓目写心,因事而作”,要写亲眼所见的内容,表达自己内心的切身感受。可见,他所提倡的“情性”内容是很宽泛的。而且萧纲这里的“情性”已背离了《毛诗大序》里所谓的“止乎礼义”“以讽其上”的“情性”说。自齐梁以来,诗人大量写作吟风弄月、抒发个人情感而无关乎政教的作品,到了萧纲这里,虽然难免有失偏颇,但却喊出了人性要解放,诗歌要畅所欲言的最强音。
在另外一篇文章《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萧纲的这种思想有更为彻底的表述: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这里的“放荡”一词,已如众多学者所考证的那样,并非是指生活不检点之意,而是指诗文表现的范围尽可以无所拘忌,作者在想象构思中尽可以纵横驰骋,出入诸种境界。也就是说,在内容上,任何材料都可以入诗,任何感情都可以抒发,不必畏首畏尾,多所顾忌,在这种文艺思潮引导下,人们内心深处长久以来被儒学所压抑的性情彻底迸发出来,对女性美的观照,以及由此连类而及的对服饰美和周围器物的歌咏都说明了,诗人在无限地扩大诗歌的审美观照。在艺术形式上,萧纲也呼吁不必为传统的形式和法则所拘束,可以大胆突破和创新,新体诗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于六朝。
萧纲还主张诗歌语言要明朗、精美,正如谢眺所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反对“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的“京师文体”(萧纲《与湘东王书》),这一点从他批评谢灵运诗“时有不拘,是其糟粕”也可以看出来,也就是反对象谢诗那样爱用典故玄言,不尚含蓄,失之板拙的语言风格。
二、江总的文学思想及作品
萧纲主持文坛时期,江总正值青壮年,处于人生世界观和价值观成形的时期,在与萧纲、徐陵等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以新变为主的文学思想:那就是不受约束地描写任何美的事物,抒发心中的所感所想,同时要琢磨锻炼诗歌的语言、辞采、声律等形式美,以达到声调流丽、语言华美、韵律和谐的效果。江总在梁代中后期写作了大量的艳情诗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其七言艳诗华美哀婉,音节流荡,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成就,如其中的名篇《闺怨篇》《宛转歌》等。
所谓闺怨诗(怨诗)体裁古老而常见,江总有怨诗十三首,多以“怨”为题,如《怨诗》《赋得空闺怨》《闺怨篇》《姬人怨》《姬人怨服散》等。这些艳诗中最得历代诗论家盛赞的是《闺怨篇》:
寂寂青楼大道边,纷纷白雪绮窗前。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合还空然。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辽西水冻春应少,蓟北鸿来路几千。愿君关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时妍。
此诗描写的是年轻貌美的少妇思念远征在外的夫君,是典型的思妇题材,全诗哀感顽艳,充满了对青春易逝,良辰不再的惋惜和流连。皑皑白雪映照着寂寥的青楼,看着池上双宿双飞的鸳鸯,女主人公心生羡慕,百无聊赖地望着空荡荡的房间,禁不住深深叹息:时光飞逝中红颜逐渐老去,心爱的人儿却滞留在天寒地冻的辽西、蓟北,多么希望夫君早日回还,莫辜负我们的青春韶华。在美人绵绵不尽的愁绪中,似乎绣花锦帐、空燃的苏合香、琉璃屏风、摇曳的灯火都沾染了美人的哀怨伤感。此诗对仗工稳,音节流荡,其诗歌形式的成熟与七律已相去不远,诗的情调更和晚唐温、韦、韩一派颇有相通之处[1]。沈德潜在《古诗源》中也说江总《闺怨篇》“竟似唐律”。可见江总在诗歌创作中较为擅长这种诗体。
随着梁末动乱的到来,许多诗人都流离失所,江总也不例外,当时为避乱曾经流寓岭南积岁。这段漂泊在外的生活让诗人感受到了很多沧桑、悲凉,诗风也逐渐变得清丽凄凉。天嘉四年,江总以中书侍郎征还朝,之后与陈后主过从甚密,频繁地参与后主文学集团组织的各类文会,在创作的同时又更加完善了他的文学思想。这时江总的文学思想表现在他和后主等人的一些书信中,如陈后主给江总的一封信《与詹事江总书》,这封信是后主为悼念早夭的陆瑜而写的,《陈书·陆瑜传》载:“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钞撰,未就而卒,时年四十四。太子为之流涕,手令举哀,官给丧事,并亲制祭文,遣使者吊祭。”其时,陆瑜与兄陆琰并侍东宫,因文学而为后主所重。后主在这封信中不仅表达了哀痛之情,还表明了对文学的看法。《与詹事江总书》曰:
管记陆瑜,奄然殂化,悲伤悼惜,此情何已。……每清风朗月,美景良辰,对群山之参差,望巨波之。或玩新花,时观落叶;既听春鸟,又聆秋雁。未尝不促膝举觞,连情发藻。且代琢磨,间以嘲谑。俱怡耳目,并留情致。自谓百年为速,朝露可伤;岂谓玉折兰摧,遽从短运。为悲为恨,当复何言!遗迹余文,触目增泫。绝弦投笔,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复叙怀。涕之无从,言不写意。
这封信不仅表达了陈后主和江总等人基本的文学观念,而且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一种风格和趋向,那就是情感上直抒胸臆,毫不雕琢;诗风则清华流丽,全无滞涩之感。这与萧纲等人提倡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一脉相传。诗人在创作时少用典故,减少了诗歌滞重拖沓的负累,而此时诗歌声律虽有所发展但还未达到唐诗的纯熟,这一特点使诗歌形式单调重复,却意外取得了音节流荡的艺术美感。江总的一些诗就具有这种特色。如他的一些赠别诗和悼亡诗感情真挚、写景诗和咏物诗则清新流丽,只是由于时代的影响,江总的诗歌可能更多了一层纤细柔靡的末世衰音,尤其入隋后作品,更显凄清悲凉。
江总的几首咏禽鸟诗写得清丽生动,如《雉子斑》:
麦垄新秋来,泽雉屡徘徊。依花似协妒,拂草乍惊媒。三春桃照李,二月柳争梅。暂住如皋路,当令巧笑开。
“协妒”“惊媒”“暂住”“巧笑”用拟人化的手法使这只可爱的禽鸟呼之欲出,如邻家女子般俏皮。“三春桃照李,二月柳争梅”更是将美妙的春光铺展在人的眼前,一种轻快、喜悦的情绪油然而生,似乎要随着那鸟儿迎风飞去。
另外一首《赋得泛泛水中凫》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出没时衔藻,飞鸣忽扬风”亦将禽鸟之可爱描绘得清新动人,句末嘲笑囚在笼中的春鹦不懂得自由的可贵。
三、江总文学思想形成的时代原因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征战频繁的乱世,到了南北朝时期,经过一段双方均无所获的战争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这期间经济、文化也循着自身的轨道向前发展。再加之南朝历代帝王都爱好文学,喜欢招纳接引文士,这种来自上层的提倡也极大的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虽然南朝社会相对安定,但内部的权力之争却是此起彼伏,始终不断,有趣的是,在这种篡乱中,士族却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为他们的利益不完全依赖同一姓氏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地位可以安然无恙。因此士族文人大多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所谓的君臣之义也不甚看重。再加上江南富庶的经济也为他们提供了优游卒岁的生活,于是刚健、俊爽的建安风骨离他们越来越远,文字也再难体现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既然无力改变现状,就将精力放在吟风弄月上,于是,南朝诗人更多的将视线转向日常生活、周围事物、男女之情和女性题材上来。
然而,对偏安一隅的南朝社会来说,稳定只是暂时的,前途依然是一片黑暗,战争还在继续,国运也日见衰颓,人们对生命与人生的意义产生了迷惑甚至是幻灭之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们无力扭转乾坤,唯有逃到自己喜欢的诗文里,或者干脆谈玄佞佛,及时行乐。在这样一种脆弱敏感的末世心态下,文人的生命必然已失去蓬勃的活力,其生命情调也只能表现为一种纤柔靡弱的特征。在诗中,人们既不可能激发出撼人心魄的强烈感情,也不敢直接揭示末世穷途的时代本质,唯能以娇羞扭捏的矫情与敛黛啼红的愁怨来折射出脆弱敏感的社会心态;以艳丽相高、绮靡相竞的风貌来掩饰穷途绝境的末世苍凉;同时也企图以此摆脱严酷现实的困扰,在唯美的创作中寻求某种心灵上的慰藉。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产生了大量的以描摹女性为主、形式上追求新变的诗歌。江总作为陈后主身边的文学臣,其诗歌创作自然更为显著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
———评郭庆财博士《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