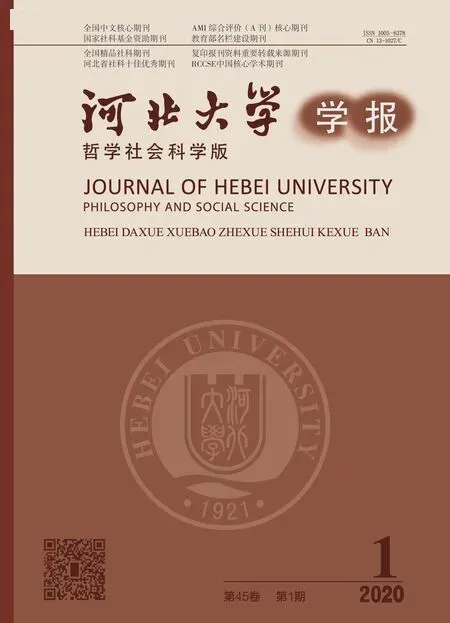历代周敦颐文集的版本源流与文献价值
粟品孝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610064)
宋儒周敦颐(1017—1073,下或简称为周子),道州(今湖南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被誉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对宋以来的中国乃至东亚各国的社会文化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文集编纂始于南宋,明代衍生出《濂溪志》和《周子全书》。别集、专志和全书三大系列相互影响,主体内容非常相近,可统称为周敦颐文集①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书末所附“周敦颐全集版本”、刘小琴《周敦颐文集版本考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均如此处理,本文也依此而行。。周子文集版本众多,情况复杂,目前关注和研究者不算多。祝尚书先生最早论其版本源流,他在《宋人别集叙录》中对由宋迄清的部分周子文集(含一种《周子全书》)做了梳理介绍,有开创之功[1]。之后研究生刘小琴著成《周敦颐文集版本考略》,对周子文集的别集、专志和全书三大系列的版本情况做了进一步梳理,并构拟有版本源流系统的图示。近些年王晚霞博士致力于《濂溪志》的整理和研究,对明以来多种《濂溪志》的版本情况和学术价值有专门论析,最近发表的《历代〈濂溪志〉的编纂与濂溪学的传播》一文更是分别从集系统、志系统、全书系统和遗芳集系统对历代二十多种周子文集做了梳理和图示②王晚霞《〈濂溪志〉版本述略》,《中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濂溪志〉修撰的学术价值及启示》,《南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日藏两种〈濂溪志〉考论》,《南昌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历代〈濂溪志〉的编纂与濂溪学的传播》,《船山学刊》2019年第5期。王博士还先后编纂出版《濂溪志(八种汇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濂溪志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二书。。寻霖先生在周子诞辰千年之际,也发表《周敦颐著述及版本述录》,对周子文集各系统、各版本情况有简要论述[2]。笔者搜集整理周子文集的版本多年,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深感已有研究既有重要推进,也存在诸多不足,尚有明显遗漏和失察之处。鉴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所知所见的三十多种周子文集的版本源流及其文献价值做一综合性论述,期能对周敦颐及其代表的理学文化的研究有切实推进。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周敦颐文集的由来及其在宋代的多次编刻
周敦颐著作,据其好友潘兴嗣撰《濂溪先生墓志铭》所述,主要有“《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①潘兴嗣《先生墓志铭》,见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八,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135页。一些学者认为《太极图》《易说》实际是一本书,应该标点为《太极图·易说》,见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上册,第46页。。而且由于周子在当时地位不高,这些论著最初只是“藏于家”,没有刊布流传。南宋初期以来随着理学和周子地位的上扬,其著作开始以《通书》或《太极通书》等形式在各地刻印流传。这些版本以周子本人作品为主,核心是其《太极图说》《通书》,另外还附有关于周子生平的“铭、碣、诗、文”,或者朱熹所写的周子《事状》[3]。
真正从文集的观念出发,并大量采录周子本人作品之外的内容,来汇编成周子文集者,开始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道州州学教授叶重开所编的《濂溪集》七卷(已佚)。据其自序,此本内容较之前所有的《通书》或《太极通书》版本都要丰富,编者不但注意“参以善本,补正讹阙”,还注意“采诸集录,访诸远近”,把“诸本所不登载,四方士友或未尽见”的内容汇集起来,比如重新收录朱熹过去编刻《太极通书》时删减的部分“铭、碣、诗、文”,把朱熹、张栻两位理学大儒注解周子《太极图说》的著作也补充进来,最后“以类相从,分为七卷”[4]。整体来说,此本突破了过去《通书》或《太极通书》时以周子本人作品为主的情况,“遗文才数篇,为一卷,余皆附录也”[5],主要内容已经是他人赠答、纪述、褒崇周子和诠释周子著作的有关文献。
叶氏编纂周子文集的原则、观念和规模,长期为后人所继承。在叶氏之后,用心搜求周子遗文遗事最勤者,是朱熹晚年弟子度正(1167—1235)。度正出生和成长于周子为官之地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周子曾任签书合州判官事五年)和周子为代表的理学快速发展的南宋中期,很早就确立了理学的信仰,并注意搜求周子的遗文遗事。科举入官特别是在问学朱熹之后,度正更是加快了这一步伐,并最终在积累近三十年之功的基础上于嘉定十四年(1221)编纂出周子文集。据其《书文集目录后》,度正“遍求周子之姻族,与夫当时从游于其门者之子孙”,获得大量有关周子的文献,或“列之《遗文》之末”,或“收之《附录》之后”,或对“遗事”“复增之”②度正《书文集目录后》,见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八,第142页。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卷六八六九据《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六亦收载,题名《书濂溪目录后》,见该书第301册,第14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这里引录的个别文字已据《全宋文》订正。。从这些用词来看,他在编定周子文集时必定有一个底本,极有可能就是上述叶重开编刻的《濂溪集》七卷本。其文集内容除了《太极图说》和《通书》外,还包括遗文、遗事和附录等卷目。值得注意的是,度正在编纂周子文集的同时,还编有周子《年谱》(或称《年表》),但是否附在周子《文集》中,不得而知。
度正所编文集久佚,是否直接刊印,也不清楚。但萧一致在嘉定十六年至宝庆二年(1223—1226)知道州期间刻印的《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正好是度正编定周子文集两年后不久的一段时间,故笔者怀疑此本是依据度正编定的文集来刻印的。此本已佚①清初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粤雅堂丛书本)卷三“宋文集类”曾著录此书:“宋板《濂溪先生大成集》,二册,七卷”,说明此本明清更替之际尚存世间。,但其目录则附在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周木编刻的《濂溪周元公全集》后面保存了下来。据目录可知,《大成集》七卷的内容依次是太极图说、通书、遗文、遗事和附录(三卷),应该是叶氏七卷本《濂溪集》奠定的基本结构和顺序。而且,上述度正《书文集目录后》提到的周子诗文,正好都在《大成集》目录中,这就进一步说明《大成集》很可能是根据度正所编文集而来。
在萧一致刊《濂溪先生大成集》后十余年,连州(时属广南东路,今广东连县)州学教授、周子族人周梅叟曾将其翻刻于州学,时间约在淳祐元年(1241)、二年(1242)间,时人称其“取《太极图》《通书》《大成集》刊于学宫”[6]卷四《举连州教授周梅叟乞旌擢奏状》。此《大成集》当是周梅叟从道州赴任连州时将萧一致主持刻印的道州本带来翻刻的。据时知广州府的方大琮所见,“其遗文视舂陵本稍增”[6]卷二十一《与周连教书一》,也就是内容较道州本(道州古为舂陵郡)略有增加。笔者推测,增加的很可能就是附在周木编刻的《濂溪周元公全集》后面的《濂溪先生大成集拾遗》所收的两方面内容:一是周子在合州与人游龙多山时唱和的八首诗,二是所谓“家集”的七篇遗诗。据方氏所见,道州和连州在刊印周子文集时,曾刊印周子年谱,即所谓“道本年谱”“连谱”,两者或许就是依据度正所编的周子年谱,只是后者较前者略有变化而已[6]卷二十二《与田堂宾(灏)书》,第13页。但周木《濂溪周元公全集》后面所附《濂溪先生大成集目录》及其《拾遗》都不见有周子年谱,说明当时的周子年谱或许是单独刻印的。
在萧一致刊《濂溪先生大成集》稍后,江西进士易统在萍乡(今属江西省)又刻成《濂溪先生大全集》七卷(已佚)。南宋晚期的目录学著作《郡斋读书附志·别集类三》中曾记载二书道:
《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濂溪先生大全集》七卷。右周元公颐字茂叔之文也。……始,道守萧一致刻先生遗文并附录七卷,名曰《大成集》。进士易统又刻于萍乡,名曰《大全集》。然两本俱有差误,今并参校而藏之。[7]
从这段文字的表述语气来看,《大成集》与《大全集》两者不但卷数一致,内容可能也相当接近。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大全集》必定吸收了度正所编文集的内容,因为此本就有度正所写《书萍乡大全集后》这一跋文[8]。
宋理宗宝祐四年至景定五年间(1256—1264),又有学者编刻《濂溪先生集》(已残,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此集虽然没有分卷,但仍像萧一致七卷本那样,内容依次是太极图说、通书、遗文、遗事和附录,因此可以肯定此本是承袭之前的七卷本而来。不过与之前的文集不同,此本在卷前列有周子的《家谱》和《年谱》,这大约是对之前周子文集编纂的一个增补。
至宋度宗咸淳末(约1271—1274),又有学者在江州(今江西九江)编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下称江州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江州本虽然增至十二卷,但在结构顺序上仍像之前的七卷本一样,依次是太极图说、通书、遗文、遗事和附录,前后承继关系十分清晰。不过,江州本与之前的不分卷本《濂溪先生集》可能渊源于不同的底本。如不分卷本的卷前为《家谱》《年谱》,江州本卷前则名《世家》《年表》,两本著录的一些人名也有明显不同,内容亦繁简不一。不分卷本和江州本所收周子著作的题名,也多有差别,如前者的《香林寺饯赵虔州》一诗,后者则题为《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诗》(此与《濂溪先生大成集》的著录同),并有注文道:“别本云:清献自虔州赴召,舟至造口,同游香林寺,石刻可考。《大成集》以为万安香城,非也。”另外就是江州本的相关内容明显比不分卷本要丰富得多。这些说明,江州本固然可能参考了不分卷本,但必定也参考了其他版本,并做了新的搜罗和整理。
二、明代以来周敦颐文集的主要版本及其源流
继宋之后的元代是否编辑和刊刻过周子文集?目前所见资料非常有限,仅知清末江苏省常熟县“小藏家”赵宗建的《旧山楼书目》有著录:“元刊《周濂溪集》,八本。”[9]明初纂修的《永乐大典》卷八二六九曾两次提到一种《周濂溪集》:“《宋周濂溪集》附录篇载《南安书院主静铭》”“《周濂溪集》附录篇载《谨动铭》”[10]。从现存的宋刻周子文集目录来看,附录部分都不见这两篇铭文,因此笔者怀疑此《周濂溪集》就是赵氏所见的元刊《周濂溪集》。
从明代开始,周子文集则有大量新的编刻,且形式更为丰富,不但延续了宋本的别集体,还新出现了《濂溪志》和《周子全书》。它们虽然在我国传统书目中分属集、史、子三个部类,但实际上交互影响,编排格局和主体内容也大同小异,因此一般把它们同视为周敦颐文集。明代以来这样的周子文集版本繁复,梳理下来,主要有三个系统。
(一)开始于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周木重辑的《濂溪周元公全集》十三卷本
此本几乎是在全部照录宋末江州本十二卷内容并在结构顺序上有所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若干内容而成,大体可称其为江州本的扩展版。其扩展的依据,有稍前周子十二世孙周冕编的《濂溪遗芳集》。比如在卷六《遗文》部分载录有周子《书窗夜雨诗》《石塘桥晚钓》,其中在《石塘桥晚钓》诗题下有小字注文:“旧无此五字,而此诗又连上共作一首,今从《遗芳集》改正。”在卷九《附录》中载录朱熹《爱莲诗》,诗后注道:“此诗近见《遗芳集》录之。”《濂溪遗芳集》久佚,今存时人方琼弘治四年(1491)的序言一篇。据方序,此集收录的是周子《太极图说》《通书》(誉为“芳”)之外的作品(誉为“遗芳”),包括周子本人的诗文,他人的赞咏、赠答、褒崇、记序[11]38a,与之后家集性质的《世系遗芳集》不同,是目前所见明代第一个周子文集版本。
三十余年后的嘉靖五年(1526),关中大儒吕柟编成《周子抄释》。其自序说他“得(周子)全书于宁州吕道甫氏”[12]7a。此“全书”当指周木《濂溪周元公全集》,因为:第一,笔者比对二书,发现《周子抄释》的内容没有超出周木本,其中卷二恰有周木从《濂溪遗芳集》过录而来的周子《书窗夜雨》和《石塘桥晚钓》二诗;第二,《周子抄释》在“附录”中既载朱熹《先生事状》,又载其《濂溪先生行录》,这种载录情况之前只见有周木本如此。不过,《周子抄释》仅有内外两篇(两卷),卷首卷末文字都不多,属于特别简略的类型,因此此本虽然一直受到重视,多次重印,甚至收入《四库全书》,但它在周子文集版本源流史上并无多大地位,后来都没有得到任何版本的依仿。
周木本在明清时期似流传不广,很长时间不见有人提及。直到清朝康熙中期,大儒张伯行才在北京一座寺庙得见其书,他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编成的《周濂溪先生全集》十三卷的序言中写道:“甲戌岁(康熙三十三年,1694),余馆中垣,居京师,乃于报国寺中偶得《濂溪全集》,如获至宝”[13]1b。过去我们一直不知道张氏这里所谓的《濂溪全集》为何,最近笔者将张、周二本比对,才发现张氏所谓的《濂溪全集》就是周木编的《濂溪周元公全集》,张氏所编《全集》是对周本《全集》的改编[14]。
张伯行是康熙时名儒,其《周濂溪先生全集》十三卷问世后影响极大。乾隆二十一年(1756)任江西分巡吉南赣宁道的董榕编辑《周子全书》二十二卷,光绪十三年(1887)关中大儒贺瑞麟辑《周子全书》三卷,一繁一简,主要依据的就是张本《全集》。其中贺本简明,是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克明点校本《周敦颐集》的“基础”本。
(二)以万历三年(1575)王俸、崔惟植编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为核心
此本主要参考之前的三种周子文集而来:嘉靖十四年(1535)周伦编、黄敏才刻于江州的《濂溪集》六卷,嘉靖十九年(1540)鲁承恩的《濂溪志》和嘉靖二十二年(1543)王会的《濂溪集》三卷。受命参与编纂此本的蒋春生在序言中说:“志(按指鲁承恩本)则博而泛,其失也杂;集(按指王会本)则简而朴,其失也疏,皆弗称。乃参取江州集,荟萃诠次类分焉。”[15]2b三本各有优劣,相对说来,两部《濂溪集》比较简明,而《濂溪志》则相当庞杂。此本虽兼取三本,但更多还是渊源于内容丰富的《濂溪志》。只是此本综合了之前三部周子文集的优长,在编排和书名上均作了新的处理,结构谨严,内容丰实,是后世周子文集编撰者非常重视的版本。
从发展源流来看,继承万历三年本的周子文集主要存在两个子系统:一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润州大族刘汝章在万历三年本基础上改编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刘本变化很小,几乎是对万历三年本的重刻;天启三年(1623)永州府知府黄克俭所编《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又主要是依据刘汝章本而来;黄本问世不久又为天启四年(1624)李嵊慈编《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三卷参考借鉴。二是开始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苏州周与爵父子所辑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世系遗芳集》五卷。前面十卷从书名到内容都承袭自万历三年本,仅有少量诗文的补充;后面五卷则是新增的,实际属周氏家族文集性质。之后康熙三十年(1691)苏州周沈珂父子以“重辑”为名,对周与爵本进行重印,并将各卷所题“吴郡守祠奉祠孙与爵编辑”或“吴郡十七世孙与爵重辑”挖改为“裔孙周沈珂同男之翰重辑”或“裔孙周沈珂同男之屏、之翰、之桢重辑”,并删去原本的周与爵辑刻书凡例;雍正六年(1728)周有士父子(当与周沈珂同族)再度以“重辑”为名,重印周沈珂本,各卷卷首又改题“裔孙周有士炳文甫重辑”。至乾隆时,朝廷编修《四库全书》,收入周沈珂本,并做若干处理,一是删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中的前两卷,二是剔除后面的五卷《遗芳集》,三是将书名省称为《周元公集》。其中周与爵、周沈珂、周有士三本跨越明清两朝,朝代已经更换,但版刻一直延续,足见其家族传承力量的强大。
这里要特别补充说明嘉靖十四年(1535)周伦编、黄敏才刻于江州的《濂溪集》六卷本(下称江州本)。江州本前有宋萍乡本《濂溪先生大全集》的胡安之序和署名度正的《年表》,似乎渊源于宋萍乡本。但据笔者比勘,其底本应是宋末江州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其收录中有些值得注意:第一,在卷首载录元末明初大儒宋濂的周子像记,开启了后来各种形式的周子文集收载此记的先河;第二,在卷二周子著作部分,将之前版本中的《思归旧隐》改题为《静思篇》,《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诗》改题为《香林别赵清献》,误收朱熹的《天池》诗。江州此本在二十多年后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为在江州为官的丁永成重刻,其中在卷六增多15篇诗文。江州本在周敦颐文集发展史上还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表现在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万历三年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就借鉴吸收过此本部分内容,比如最明显的就是卷四《元公杂著》部分,收录了题名《静思篇》《香林别赵清献》和《天池》的诗文。其次,同样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胥从化、谢贶编《濂溪志》十卷本,在卷二《元公杂著》部分也如同万历三年本一样收录,在卷七《古今纪述》部分还收录有江州本的王汝宾和林山的跋语。第三,江州本在《周子全书》系列的发展史上也起过重要作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山东按察司副使、管直隶淮安府事张国玺所编《周子全书》六卷就是依据江州本而来,是《周子全书》系列发展史上的第一部。笔者比对发现,这个《周子全书》六卷实际是江州本的翻刻,只是书名作了更改,序跋文字也全部换掉,而其他内容则一仍其旧。
江州本最大的特点是简要,但似乎有些过分,比如周子的诗文很不全,书信也未收,附录的内容也不多,因此难以独立构成一个发展系统中的一环,只能为其他有关版本提供部分内容而已。这种情况在所有过于简要的周子文集中都存在,比如上面提及的嘉靖二十二年(1543)王会编的《濂溪集》。它只有遗书(含事状)、年谱和历代褒崇三卷,而且《太极图说》和《通书》均无注解和相关论释,附录也仅仅九篇记文而已,因此也很难独立构成一个发展系统中的一环,只能为其他有关版本提供参考而已。不过王会本在卷首著录有濂溪故里图、月岩图、书院图,并有图说文字,卷二的年谱后有度正、度蕃兄弟的跋语,均为后来众多周子文集版本所继承。
(三)以万历二十一年(1593)胥从化、谢贶编《濂溪志》十卷本为核心
此本上承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永州府同知鲁承恩编的《濂溪志》。鲁本是周子文集编纂史上第一部名实相符的《濂溪志》,“首之图像,以正其始;次之序例、目录,以明其义;次之御制,以致其尊;次之遗书,以昭其则;次之著述、践履,以纪其迹;次之事状、事证,以详其实;次之谱系、谱传、谱稽,以衍其裔;次之奏疏、公移,以取其征;次之表、说、辨、赋、诗、记、序、跋,以备其考;次之祭文、附录,以稽其终”[16]43a,内容极为丰富,甚至有些庞杂。万历三年(1575)永州府知府王俸、道州知州崔惟植编《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曾参考鲁本,比如卷五的书信部分,就完全是照抄鲁本而来。当然,从书名和内容上,依仿鲁本更多的则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胥从化、谢贶编的《濂溪志》十卷。
胥从化本《濂溪志》在明清两代有很大影响。之后万历三十七年(1609)知道州林学闵编《濂溪志》四卷,就是依据胥本改编的,版刻多数照旧,结构则作了很大调整,内容也有一些变化,尤其增多了数十篇诗文;万历末又有人挖改林学闵本,形成旧题“李桢辑”的《濂溪志》四卷(旧题“九卷”),版刻和内容基本上还是林学闵本,只是凡有“林学闵”字样处,均作了剜改。这三部万历时期的《濂溪志》在版刻上前后相续,内容大同小异,可以相互补充。其中林学闵本卷首收载的周子画像,为后来众多版本所承袭,流传广泛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周敦颐集》也如此,几成周子标准像①参见粟品孝《万历〈濂溪志〉三种及其承继关系》,未刊稿。。
胥从化本《濂溪志》及其改编本后来很受重视。如明末天启四年(1624)知道州李嵊慈编《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三卷,主要就是依据胥从化本及其改编本《濂溪志》,并参考了天启三年(1623)永州府知府黄克俭所编《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李本虽以“集”为名,但版心题“濂溪志”,其序言名为《濂溪周元公志序》,其卷目安排也是志书形式,因此明显更多的是参照胥从化本《濂溪志》而来。至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道州吴大镕修《道国元公濂溪周夫子志》十五卷,也主要是参照胥从化本《濂溪志》及其改编本。之后道光十九年(1839)周子后裔周诰编《濂溪志》七卷,又主要是在康熙《道国元公濂溪周夫子志》的基础上新编的,并参考了康熙三十年(1691)苏州周沈珂父子“重辑”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其中附录的《濂溪遗芳集》一卷内容基本同于康熙《道国元公濂溪周夫子志》卷十五的《古今艺文志》,只是标题、作者和顺序有些变化。道光二十七年(1847)湖南大儒邓显鹤编《周子全书》九卷,尽管书名已无“志”,但实际上其底本就是道光《濂溪志》,该书卷首下尚有“道州濂溪志原本”字样。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徐必达校正《周子全书》七卷,也主要是参考胥从化本《濂溪志》,以及嘉靖二十二年(1543)知道州王会编的《濂溪集》三卷。此本最初是与记述张载的《张子全书》合刻的,称《周张全书》,后传至日本,有延宝三年(1675)重刻本。万历四十年(1612),巡按江西监察御史顾造在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也编有《周子全书》七卷,主要是依据徐必达本而来,只是编排顺序略有变化而已。
三、周敦颐文集诸版本的文献价值
周敦颐文集从最初的版本开始,就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周子本人的作品很少,主体内容是其他人撰述的有关周子的文献。而周子本人的作品主要是《太极图说》和《通书》,二者单行本易得,因此过去学界似乎不太重视周子文集的版本问题。笔者多年致力于此,深感过去的一些认识有偏差,周子文集的各个版本多具有很高的价值。下面仅从文献学的角度略做举列。
(一)可以对周子生平事迹有更准确的认识
周子文集各本一般都收录了关于周子生平事迹的年谱,但不同版本的著录往往有所差别。过去我们一般倚重清代张伯行的《周濂溪集》(丛书集成本),后来又常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周敦颐集》,二者均有署名南宋度正所编的周子《年谱》。其实,这两本《年谱》完全相同,都是经过删改的,只有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所收度正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才是原貌(至少更加接近)。从中我们对周子的生平事迹有一些新的认识。
比如在天禧元年丁巳条叙述周敦颐出生情况时,《年谱》载:“(周敦颐父亲)先娶唐氏……唐卒,[继娶]侍禁成都郑灿女,是生先生。”《年表》则载:“(周敦颐父亲谏议公)先娶唐氏……唐卒。左侍禁郑灿,其先成都人,随孟氏入朝,因留于京师。有女先适卢郎中,卢卒,为谏议公继室,是生先生。”很明显,《年表》显示周敦颐的父母均是再婚之人,他的母亲是再嫁之妇。可是《年谱》却把这一重要事实抹去了,这肯定与清代以妇女再嫁为耻有关。
在南水北调工程通水之后,优先保证深层和浅层地下水超采量的置换,充分利用当地水利基础设施,以地表水地下水联合利用为水资源利用的基本模式,实现受水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再比如嘉祐二年丁酉条关于周敦颐在合州的教学情况,《年谱》载:“九月,回谒乡士,牒称为‘解元才郎’,今不详为谁氏子。盖当时乡贡之士,闻先生学问,多来求见耳。”《年表》则载:“九月,回谒乡士,牒称为‘解元才郎’,今不详其为谁氏子。当是去年乡贡,今年南省下第而归者,闻先生学问,故来求见耳。”两相对比,《年谱》美化周敦颐形象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
另外,周敦颐出生的具体月日和地点,南宋度正编的《年表》不载,并在小字注文中写道:“先生之生,所系甚大,当书其月、日、地,而史失其传,今存其目而阙之,以俟博考”。之后的周子文集和年谱也长期未记,但清朝道光十九年(1839)周诰编的《濂溪志》,在《年谱》中则明确写道:“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五月五日,先生生于道州营道县之营乐里楼田保”。这一记载现在为很多人接受,但依据为何?并未说明,让人不免生疑。
(二)可以大体梳理出周子本人诗文的汇集过程,并对一些误收误题现象进行辨正
诚如前述,周子本人的诗文在其死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整理刊印,散佚严重,南宋以来才逐渐为人汇集。笔者在梳理历代周子文集版本的著录情况后发现,南宋末期周子文集的诗文已形成赋1篇、文5篇、书6篇、诗24篇、行记5篇总计41篇的规模,明朝时新增《任所寄乡关故旧》《春晚》《牧童》3首诗,误收《宿大林寺》(或题《宿崇圣》)、《天池》两首诗,清朝时新增行记5则,误收《暮春即事》《观易象》两首诗。在此基础上,我们来观察中华书局点校本《周敦颐集》,就会发现,其收录的《宿大林寺》《暮春即事》《观易象》3首诗均非周子作品,应当剔除[17]。
而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所收《书窗夜雨》和《石塘桥晚钓》二诗的著录也存在不足。此二诗实际是一首诗,应题作《夜雨书窗》。这在已知的多种宋刻本周敦颐文集中是很清楚的。南宋后期的《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虽然久已失传,但其目录还完整地保存在明代周木重编的《濂溪周元公全集》卷十三后的附录中,其中有《元公家集中诗七篇》,内有《夜雨书窗》诗,而无《石塘桥晚钓》诗。较《濂溪先生大成集》稍后刊刻的《濂溪先生集》不分卷本,其目录同样有《家集中七首》,也只有《夜雨书窗》诗,而无《石塘桥晚钓》诗。以上二本所收《夜雨书窗》诗虽然仅存目录,但明言出自“家集”,是很有说服力的。宋亡前夕刊刻的《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无有《石塘桥晚钓》诗,但有《夜雨书窗》诗。该诗共12句,其中前6句与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所收《书窗夜雨》诗完全相同;后6句与《石塘桥晚钓》诗也基本相同(仅有个别字微异)。这就说明,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所收《书窗夜雨》和《石塘桥晚钓》二诗,本为一诗,题名是《夜雨书窗》;《周敦颐集》将其析为两首著录,并将《夜雨书窗》改为《书窗夜雨》,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然,这并非点校者的臆改,他的失误渊源有自。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的底本是清朝光绪年间贺瑞麟所编《周子全书》,而贺瑞麟又主要是依据康熙年间张伯行所编《周濂溪先生全集》。张本卷八有《夜雨书窗》和《石塘桥晚钓》二诗,在《石塘桥晚钓》诗的标题后有小字一段:“旧无此五字,而此诗又连上共作一首,今从《遗芳集》改正。”这一情况包括注文恰好在张本所依据的明朝周木编的《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六中就有。这就说明,《夜雨书窗》和《石塘桥晚钓》二诗最初是联为一首著录的,题名就是《夜雨书窗》。将此诗析为《夜雨书窗》和《石塘桥晚钓》两首来著录,源于明朝弘治四年(1491)周敦颐十二代孙周冕编刻的《濂溪遗芳集》,后来明朝周木编《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加以承袭,张伯行本出自周本,贺瑞麟踵而继之,中华书局点校本又沿而不改,及至后来的《全宋诗》卷四一一也延续了这一失误。
(三)可以从中发掘大量新的文献,有些文献往往是独有而重要的
周子文集的文献量很大(而且越是后来的版本新增的内容越多),不少文献往往是其独有的,或是最原始的。
另外,周子文集还保留了不少其他传世文献失收的宋人诗文。据统计,在现存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有13人共19首诗为《全宋诗》失收,其中王子修、周刚、鲍昭、薛祓、文仲琏和周以雅等6人未入《全宋诗》作者之列;有37人共47篇文章为《全宋文》失收,包括周子的蜀籍门人傅耆所写的《与周敦颐书》和《答卢次山书》这两通对了解周子诗文之学有重要帮助的书信。何士先、徐邦宪、胡安之、陈纬、刘元龙、蔡念成、余宋杰、冯去疾、卢方春、曾迪和傅伯崧共11人甚至未入《全宋文》作者之列。另外还有11篇文章为《全宋文》收录不全或有明显差异者。如游九言《书太极图解后》,《全宋文》卷六三一〇依据嘉靖《建阳县志》,题为《太极图序》,但内容止于“先识吾心”,而缺“澄神端虑”以下的大段内容;林时英《德安县三先生祠记》,《全宋文》卷七二一一依据《永乐大典》卷七二三七,题为《德安县学尊贤堂记》,文字与此处差异较大[20]。
以上只是说周子文集对宋人诗文的补充。我们知道,周子文集在明清还有很多刻印,其中又陆续新增了大量明清人的诗文,我相信也有不少珍贵的文献资料有待发掘。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周子文集的一些重刻本、改编本、挖改本也不能忽视,内中往往也有一些新的文献。比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丁永成在江州为官时据嘉靖十四年周伦编、黄敏才刻《濂溪集》六卷本重刻的《濂溪集》。虽是重刻本,但在卷六增刻了15篇诗文,绝大多数不见于后来的周子文集。再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知道州林学闵依据万历二十一年(1593)胥从化本《濂溪志》十卷改编而成《濂溪志》四卷,版刻多数照旧,结构则作了很大调整,内容也有一些变化,尤其增多了数十篇诗文。更重要的是,林本卷首的周子像,区别于之前所有的版本,而为后来众多版本继承;而挖改自林学闵本的万历末旧题“李桢辑”的《濂溪志》四卷(旧题“九卷”),也有一些新的诗文收录。
总之,周子文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果超越文献学的视角,从思想史、教育史、社会史、经济史等方面着力,其价值自然会更加凸显。目前我们已经注意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吴大镕修《道国元公濂溪周夫子志》十五卷的影印本收入《中国哲学思想要籍丛编》(台北:广文书局1974年版),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周与爵父子重辑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世系遗芳集》五卷(哈佛大学藏本)被选入《中国古代思想史珍本丛刊》影印出版(北京:海豚出版社201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料编委会编《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料》二编第二十八册(北京:蝠池书院2013年版)还专门辑录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的众多“祭文”。这些都说明,周敦颐文集的价值,文献学之外的天空或更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