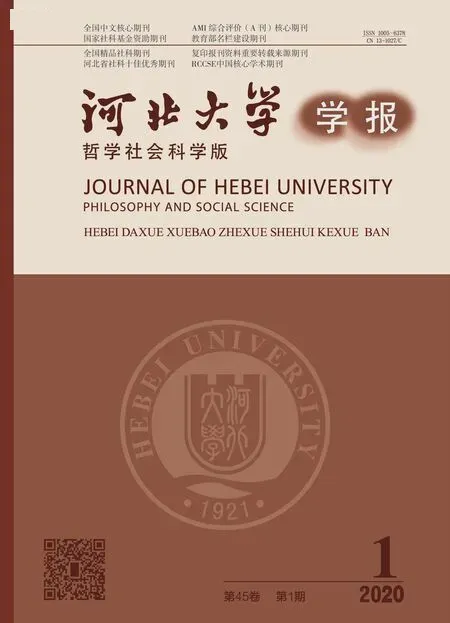论中国美学的“中和”智慧
袁济喜,刘 睿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国美学是中华文化的精粹,不仅有内在的精神理念,而且有思想智慧作为其津梁。中国美学的中和智慧,乃是基于天地之道的精神智慧。它的显著特征,既有形而上的本体支持,又不止于器用的范畴。一般认为,中和的审美概念诞生于秦汉时期,儒家典籍《礼记·中庸》论及“中和”时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798它强调“中”为情思隐而未发时的状态,而“和”则是发生以后的产物,是应接天地之道后达到的理想形态与境界,于是“中和”被赋予了精神蕴涵。在这一阐释过程中,“中”强调的是允执其中、不偏不倚,而“和”则注重由不同事物所构成的和谐理想的形态。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美学的融会贯通,不仅需要汲取精神价值,还需要借鉴古人的审美智慧。审美智慧和审美精神有所不同:审美精神是指审美主体所具备的精神价值体系;审美智慧虽然与审美精神有所联系,却是具有具体方法论的一种范畴,是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有机结合。自古以来,这种精神理念与方法相融合的特征与功能,催生出中国美学的理论批评,形成了丰富的范畴与概念,是我们尤其需要继承的精神瑰宝。
在长期的农业劳动中,先民们接触到天地自然的形态,他们直觉地感受到外在世界的丰富性蕴含在和而不同的形态之中。总体而言,他们采用两种认知模式来把握外部世界:一是《周易》的八卦模式,将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归纳为八种符号与图式,用来指称与概括天地人三者的生成与变化,其基本特征是“和而不同”。“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2]576。阴阳发散、变动相和是《周易》中的生命精神,也是中国美学的精神价值观念与智慧根基。二是阴阳五行模式,这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有着生动的论述,表现出古人的思想智慧,如“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3]4576-4577。后来衍生出春秋前史伯、晏婴、子产等人“以和为美”的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和之美的思想智慧基础。
区别“和”与“同”、凸显二者的“貌合神离”,是春秋时期思想家对“中和”范畴最有价值的贡献。从表面而言,“和”与“同”有相似之处,二者都讲究事物的和谐而反对杂乱无序,但是“和”追求的是和而不同,表面多样化的事物存在着内在的契合,可以通过外在的杂越达到内在的和谐;而“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处事方式,则是硬性强调外在的同一,实际上破坏了事物的内在和谐,扼杀了事物的生命力。将这一道理讲得最为透彻的是《国语·郑语》,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即周朝将要灭亡的问题时指出:“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4]史伯比对自然与人事,指出周王偏听偏信、党同伐异的做法势必走向自我毁灭。自然界中事物互相补充、“以他平他”,即把相异的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故能丰长而物归之”。相反地,只是机械地将相同的要素相加,就不可能产生新的事物。所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美产生于宇宙间多样事物的和谐相生之中。《老子》:“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5]6相辅相成是观察包括美在内的宇宙间事物的法则,人的思想智慧也受到这种原理的支配。《淮南子·精神训》指出:“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背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6]人的精神智慧来自于自然界的转化,作为精神智慧之一的审美智慧,也受到中和之美的启发,人文之美的丰富多彩来自于自然界的赋予。《文心雕龙·原道》强调:“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7]1刘勰描述了自然界的多姿多彩,强调文章之美是这种自然和谐之美的转化,旨在唤起同时代作者对这一美感的尊重,从过度雕饰的美学趣味回归自然之美——最高的和谐之美。中国美学的中和智慧缘于这种深刻的思想理念,继而通过诸多方法途径达到“中和”之境。
一、阴阳发散,变动相和
中国美学意图调和对立的两极,形成新的和谐,而不是简单地两相抵消,从而加剧矛盾的对立与冲突。其中《周易》认为和谐就是兼容对立的两端,如“乾”卦《文言》指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2]217又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2]216“乾”是阳爻之名,作为创生天地万物的始基,以自身创造力带给世界“美”和“利”,即审美与功用的效益,又不自我矜夸。
审美活动是人类个体性的彰显与表现,在讨论人性问题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赞美中和,推崇它既是人伦之要,又是一种行事的智慧与能力。汉魏以来,以阴阳五行论人性是一种基本观念,其中在刘邵《人物志》与嵇康《明胆论》中有着明确的论述。嵇康的儿子嵇绍在《赠石季伦诗》中写到:“人生禀五常,中和为至德。嗜欲虽不同,伐生所不识。仁者安其身,不为外物惑。”[8]北齐刘昼《刘子·和性》指出:“西门豹性急,佩韦皮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带丝弦以自急。彼各能以一物所长,攻其所短也。故阴阳调,天地和也;刚柔均,人之和也。”[9]370-371刘昼认为西门豹与董安能够调适自己的性格,各以一物所长攻其所短,所以能成就大事业。在工艺制作中也是如此,高明的工匠善于在刚柔之中找到均衡,从而制造出优良的器具。他说:“夫欧冶铸剑,太刚则折,太柔则卷。欲剑无逝,必加其锡;欲剑无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刚而锡质柔。刚柔均平,则为善矣。良工涂漆,缓则难晞,急则弗牢。均其缓急,使之调和,则为美也。人之含性,有似于兹。刚者伤于严猛,柔者失于软懦,缓者悔于后机,急者败于懁促。故铸剑者,使金不至折,锡不及卷;制器者,使缓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刚而不猛,柔而不懦,缓而不后机,急而不懁促。故能剑器兼善而性气淳和也。”[9]370刘昼强调人的秉性刚柔有偏,而制作器具也要寻找不同质地的材料、调和不同的制作要素。
诗赋创作亦注重中和之美。古代文人认为,赋乃是天地阴阳相交的产物,是对立两极的和谐所致。《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10]司马相如认为,赋的创作由经纬、宫商等因素互补而成,有机地统合对立的两极,得以摹写天地宇宙与社会人物。清代文论家刘熙载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艺概·赋概》:“司马长卿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成公绥《天地赋序》云:‘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意与长卿宛合。”[11]明代诗论家谢榛《四溟诗话》指出:“诗忌粗俗字,然用之在人,饰以颜色,不失为佳句。譬诸富家厨中,或得野蔬,以五味调和,而味自别,大异贫家矣。绍易君曰:‘凡诗有鼠字而无猫字,用则俗矣,子可成一句否?’予应声曰:‘猫蹲花砌午。’绍易君曰:‘此便脱俗。’”[12]67-68谢榛认为诗中的俗字未可一概否定,关键要看用在何处,如果符合诗的总体意境也可以自成佳句。他还列举了诗句来证明这一观点,读之令人解颐。
二、违而不犯,和而不同
中国美学的中和智慧,还表现在它善于从相反相成的维度去创造艺术的最高境界,讲究从不同中求取匀称、从均衡中带来变化。古人往往将美的和谐用“文”来表示,而“文”的蕴涵极为丰富,由诸多因素所构成。《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文。”[13]说明“文”是由不同的线条交错而形成的一种美的视觉形象。《易传·系辞》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2]550《楚辞·橘颂》曰:“青黄杂糅,文章烂兮。”[14]《礼记·乐记》曰:“五色成文而不乱。”[1]561王充《论衡》曰:“学士有文章之学,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15]由此可见,从均衡中求取杂错之美能够获得中和之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把杂多因素的组合视为和谐之美的根源,作为艺术创作的准则与方法。“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7]537。他所说的“神理之数”,也就是自然之道。
诗歌声律之美同样体现着“和而不同”的创造原则,有助于讽诵诗篇、吟咏情志、抒写性灵。明李东阳在《沧州诗集序》中说:“诗之体与文异……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风韵,能使人反覆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16]那么声律之美的特点是什么呢?西晋陆机《文赋》谈到:“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鲜。”[17]766-767他认为音声变化更迭、逝止无常,作文要掌握音韵的自然变化,采取有机的组织和安排。李善注“若五色之相宣”云:“言音声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为绣也。”[17]766陆机在《鼓吹赋》中还描写道:“饰声成文,雕音作蔚。响以形分,曲以和缀。放嘉乐于会通,宣万变于触类。适清响以定奏,期要妙于丰杀。”[18]4027在审美过程中,陆机对音乐与文学的会通十分重视,而在论述文艺各个门类时,以和为美是其基本观念。
陆机五色相宣、音声相和的观念,对齐梁声律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侃认为南朝齐梁时代的声律之论,实由陆机导路[19]。声律论由范晔、沈约、周颙等人相沿而创立,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声”与“病”两个部分。所谓“声”即四声,“病”即八病。《文心雕龙·声律》说:“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7]553刘勰所言“同声相应”指向的是“四声”的特质,而所谓“异音相从”则指向的是“八病”的内容。“韵”与“和”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追求重复呼应,后者重视参差变化,避免病犯,从不同中求和谐,是一种更高形态的美。文章(主要指骈文)的对偶之美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刘勰又言:“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7]588同自然界的造化一样,文章的对称骈俪也是自然形成的。从句式来说,骈文一般是四六相对,然而通篇骈俪会显得沉闷呆滞。为了避免这样同质化的审美感受,必须要酌以变化,达到“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故曰:“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7]571刘勰认为,四六句式虽为骈文通行的对偶句式,但亦须杂以三五句式,疏宕文气,骈散结合。六朝骈文大家庾信、徐陵就擅长这一技巧,于是很少有沉滞重复的弊病。
在中国古代的书法美学领域,唐孙过庭在《书谱》中从书法间架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和谐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20]2046-2047汉字的书法整体美要求“和”,“和”的特点是“违”,即同中求异,通过各有不同、神采荦异的笔画,组成书法的结构之美。又如,一个“多”字,有四撇再加两点,这四撇若写得不好,就容易雷同呆板变成“犯”,即互相一致。所以唐太宗《笔法诀》有所谓“多法”:“多字四撇,一缩,二少缩,三亦缩,四须出锋。”[21]145这就是力求不“犯”,而求“和而不同”。高明的书法家善于做到“违而不犯”。如赵孟頫《胆巴碑》中的“州”字,三个直笔变化参差,或回锋、或收锋,最后的一竖还带出一钩,显得别具一格。《芥子园画传》论树木的“三株画法”也说到类似的意思:“虽属雁行,最忌根顶俱齐,状如束薪,必须左右互让,穿插自然。”[22]作者认为“三株画法”最忌讳的是上下长短一般齐整,就像捆在一起的干柴,应该和而不同、自然变化。再如,“三”字最易变成三横雷同,缺少生动,但是在书圣王羲之的笔下,它们却被赋予不同的神韵。王羲之在《姨母帖》《奉橘帖》《三月帖》中,把相同的“三”字写得各具风韵。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强调:“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18]3220即令是方正严整的楷书,也要求尽量做到随字转变、和而不同。汤临初《书楷》说:“真书点画,笔笔皆须著意,所贵修短合度,意态完足。盖字形本有长短广狭,小大繁简,不可概齐。但能各就本体,尽其形势,虽复字字异形,行行殊致,乃能极其自然,令人有意外之想。”[21]71-72像清代取士专用的“馆阁体”,片面地追求乌光方正,缺少变化、呆板雷同、气韵全无,便走向了“同”而非“和”。
三、以一总万,统观全局
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范畴对达到“和”的途径,还提出了“以一总万、统观全局”的原则与方法。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一”指统率全体事物的本根,“万”是“一”的具体表现形态,即纷呈于宇宙、社会和精神界的事物。《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5]117在老子哲学中,“一”也就是“道”,即万物的始基与本体。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何晏、王弼真正从本体论角度对“一”与“多(万)”的关系作出系统论述,并推衍为处理矛盾、达到和谐的方法。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这是由自身的内在规律“道”所决定的。要达到和谐必须善于处理各种矛盾、认识本体,这是实现“和”的根本途径。
如前所述,从春秋时期开始,古人就意识到美是由杂多的事物所组合而成,并且主张“济其不及,以泄其过”[3]4546,将互相对立的两极互补互济,最终达到矛盾的统一与平衡,暗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蕴。然而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和观念,极少涉及在结构上如何将头绪纷繁的作品删繁就简、梳理脉络,使艺术作品成为有机整体的问题,它缺乏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那样的系统论述与理论创见。尤其是在两汉时期,文人的思维方式受到宇宙构成论的影响,习惯于对外部世界的经验性描述,所用概念与范畴也极其烦琐。曾有人批评扬雄的著作,“历览者兹年矣,而殊不寤。亶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23]。王充《论衡》考辨事物真伪,洋洋数十万言,方法却不免苛碎。又如《周易》的爻卦变化多端、纷纭复杂,而汉人说《易》方法繁复而不胜其烦,甚至杂以神秘的象数之学。王弼看到了汉人的这一缺陷,他在解释《周易》时创造性地运用了“以一总多”的方法。
王弼认为《周易》的解说必须明纲领、总其要,彖辞则是“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2]591。抓住一卦之主,就能够在纷纭万状的卦象变化中寻绎出头绪。他进一步阐发道:“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2]591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必然之理发挥作用。认识事物、处理矛盾,必须抓住这个根本,才能“繁而不乱,众而不惑”[2]591。
王弼在论《周易》大衍之义时也说:“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2]547-548《周易》的占卦采用五十根蓍草,但每次只用四十九根,剩余一根不用,与后人加之许多推测和想象不同的是,王弼借此阐明“以一总万”的原则。他认为以唯独不用的“一”作为本体,统率其他四十九根蓍草,共同发挥作用,完成大衍之数五十的妙用。推而广之,万事万物只有在“一”(本体)的统率下才能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王弼的这一思想对于审美和艺术创造的系统方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是对先秦两汉“中和”范畴的发展与创新。
三国时期,这种“以一总万”的思想也体现在政治哲学领域。曹魏刘劭在《人物志》中指明:“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24]33刘劭的“中庸”属于兼容众材的智慧,因为常人不免偏向某一具体的德行才干,唯有具备中庸之德的君主才能超越偏执、任用群臣。刘劭《人物志》强调:“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24]108刘昞注云:“水以无味,故五味得其和。犹君体平淡,则百官施其用。”[24]108这一中庸之德同样启发了审美智慧。曹魏谋士和洽就对曹操说:“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25]《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论为政时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26]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是从探明各类文体的性质、作用、写作规范入手来总结创作规律,其中《诠赋》《明诗》篇提出的一些原则,具有指导文学创作的普遍意义。而创作论则是刘勰从“横”的方面,探讨文学的构思、风格和发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属于全书的精粹。全书的《序志》一篇,具有交代背景、点明主旨的意义。刘勰特别指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7]727也就是说,《序志》篇是《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不用而以之用”的纲领,而这一理论体系是自觉借用了王弼易学的结果。这种“以一总万”、力求和谐的方法也体现在刘勰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例如他在《序志》篇中论述辨析文体时指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7]727所谓“原始以表末”,就是考察每一文体的源流演变;“释名以章义”,就是用正名来说明文体的特质;“选文以定篇”,就是列举每一种文体的代表作品加以评论臧否;通过历史的考察、具体作品的分析以及名号的辨析,最后归结到写作原则和要领,这就是“敷理以举统”。又如《论说》篇最后总结道:“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7]328因此刘勰的文体论纲目明晰、体系谨严,避免了“巧而碎乱”[7]726、杂而不和的毛病。
四、大化无迹,超越中和
中国美学的中和智慧的最高境界,便是超越具体法式,达到大化无迹、自然天工的“大和”境界。《庄子》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27]160成玄英疏曰:“不得已者,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养中和之心,斯真理之造极,应物之至妙者乎!”[27]163在庄子看来,所谓“中和”之心就是虚静荡然、无偏无倚、任从自然、涤除自我。晚唐诗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28]38司空图提出,只有超越具体物象方能得其“环中”。“环中”也就是以虚无恬淡为特征的“道”,它源源不断地衍生出各种诗歌之美的意象。作为艺术创作的境界,中和的审美智慧更多受到道家哲学与美学的启迪,六朝时期的许多文士喜欢用自然之道来阐释自己的创作体会。
南朝梁代文士萧子显自述其创作经验:“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29]因而主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30]。唐代李德裕《文章论》亦言:“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珍不足贵。”[20]7280古人非常推崇“无意”或“不经意”,以为诗文佳作多为无意中得之。这里的无意便是顺从自然之道,反对刻意雕琢。宋代的姜夔列举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28]682毫无疑问,他认为“自然高妙”的品级最高。胡应麟称赞斛律金《敕勒歌》之胜处,“正在不能文者,以无意发之,所以浑朴莽苍,暗合前古”[31]。这种大化无迹、自然天工的审美思想是对传统中和之美的发展。
在文论之外,画论、书论都崇尚无意之作。苏轼诗曰:“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32]黄庭坚《题李汉举墨竹》云:“如虫蚀木,偶尔成文。吾观古人绘事,妙处类多如此。”[33]3151清画家戴熙亦云:“有意于画,笔墨每去寻画;无意于画,画自来寻笔墨:有意盖不如无意之妙耳。”[34]清代著名的画家石涛论画,与前人多重笔墨技巧、经营位置不同,他自觉地以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来探讨绘画美学问题。《一画》:“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体,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35]1这段话指出,太古一片混沌,没有具体的物象;太朴始散,于是具体的法度产生了。而“一画”是统率万法的根本大法,具有本体与规律的涵义。“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它来自万物,是对万物的总括,“且山水之大,广土千里,结云万里,罗峰列嶂,以一管窥之,即飞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35]54。所以把握万物之美就要由“万”至“一”,即由具体事象进入到抽象领域。他说:“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絪缊,天下之能事毕矣。”[35]49石涛认为,绘画神韵的获得,不仅在于技法,而且在于掌握绘画的根本大法“一画”,通过心手交融的高超技艺,创造出神妙之作。
在书法评论中,古人也以自然之作为佳。如《宣和书谱》评晋王浑:“其作草字,盖是平日偶尔纪事,初非经心,然如风吹水自然成文者。”[36]562评晋王衍:“作行草尤妙,初非经意,而洒然痛快见于笔下。”[36]426评王安石:“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初未尝略经意。”[36]523苏轼《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33]3025董其昌说:“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37]越是无意、不经意就越有助于文艺创作的成功,这就是艺术创作的辩证法,也是一种审美的智慧。
诚然,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文人严格遵守前人的法度,不敢越雷池一步,反而落入创作的樊篱之中。最典型的便是江西诗派和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观念,在他们的理论阐释中,“中和”变成了固定的模式,阻碍了作家个体创作自由。崇尚个性的作家大都批评这种理论与做法,呼吁作家葆有灵活运用、突破常规的创作精神。明李贽指明:“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38]李贽强调真正的好文章,决非“首尾相应,虚实相生”之类的作品,而是天工自然的产物,反对因袭前人之法而不知有我。以李贽为代表的崇尚个性的文人承认艺术创作需要一定的法度,但是这种法度应该遵守自然之道,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个性与才华,这样才能产出真正和谐完美的作品。
五、中和智慧与胸襟人格
中和智慧不仅是一种方式与技巧,更彰显出一种胸怀与人格精神,在审美活动中涵育审美人格与文艺创作鉴赏。事实证明,任何智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聪明才智,总是与个体的胸怀人格相联系,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9]140《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1]819孔颖达疏曰:“‘极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谓天也,言贤人由学极尽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达于中庸之理也。”[40]所谓中庸,就是效法天之高明而通于人事,能够将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施行于人事。如上文所述,曹魏刘劭《人物志》对汉魏时期的美学思想的转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诗论领域中,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进一步诠释刘劭《人物志》“中庸”的观念。他指出:“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蕴乎内,著乎外,其隐见异同,人莫之辨也。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学者能集众长,合而为一,若易牙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矣。”[12]69谢榛强调古人养气,列举了阅读初唐、盛唐诸家之作的感受,认为学诗之人要对诸家之气兼容并包,如同调和五味一样。
在文艺创作与批评领域,中和智慧往往体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气度与包容。古人往往以对话与讨论的形式来领会作品的精神实质,实现精神的升华,其中《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切磋《诗经》的情形。《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39]9可见,“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然是一种好品德,但是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更符合君子的品德。子贡由此想到了《诗经》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句,意为君子要达到最高的道德境地,还必须不断切磋磨炼自己,为此孔子对能与子贡谈论《诗》感到欣慰。这种以对话与讨论的形式来鉴赏作品、切磋艺术、臻于中和之境的智慧,显然是通过作者的胸襟人格而获得实现的。两汉时代,经学一统天下的思想环境往往导致文士们对作品的评论简单化,班固对屈原《离骚》的批评就是如此。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士们喜欢通过讨论与辩论的方式来品评文章。《世说新语》便记载了许多名士以此进行文艺批评,达到一种兼收并蓄、宽容待之的境界。这一传统延续到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该书记载了作者与好友梅尧臣切磋诗艺的轶事。清代性灵派文士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八中指出:“蒋苕生与余互相推许,惟论诗不合者:余不喜黄山谷而喜杨诚斋;蒋不喜杨而喜黄:可谓和而不同。”[41]这将文艺评论者“和而不同”的胸怀人格表达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论,中国古代美学不仅体现出一种精神价值,更蕴含了一种审美智慧。这种道器合一的体系彰显出人格襟怀,塑造出审美精神。《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2]555器是道的外化,而道是器的统率。推而言之,“中和”的思想智慧与人格精神,让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获得实现与变通,呈现出游刃有余的创作境致,成为了中国美学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