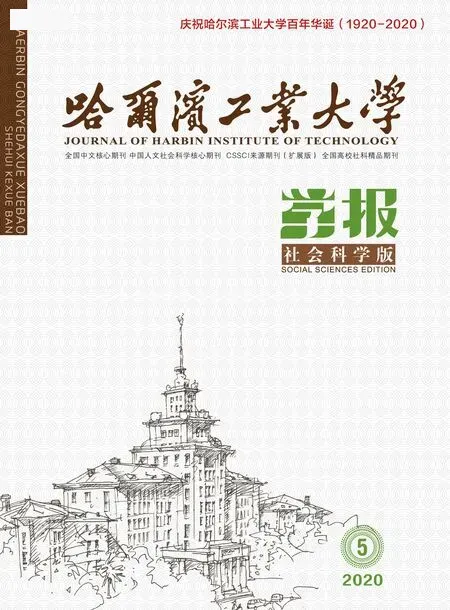中国现代作家的小城镇体验与河流书写
孙 胜 杰
(1.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150080;2.哈尔滨学院 文法学院,哈尔滨150086)
“镇”作为一种区域建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直被作为缩小城乡差距的重点建设区域,具有与乡村和城市都相关的中介性,所以被称为“乡镇”亦或“城镇”①费孝通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对小城镇的定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用一个普通的名字概括,称之为‘小城镇’”。参见费孝通《小城镇四记》,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小城镇与大都市的显著区别是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从地理位置来看,和城市相比,城镇在地理环境上与自然更亲近,已经有很多地理学者对河流与城镇体系结构形成演进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研究,城镇一般“沿河流相对集中分布”,“依河而建、依水而兴”,而且“沿河城镇一般具有河流属性职能”[1]。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批著名的小城作家,他们童年在小城镇生活,成年后离开小城镇来到大城市,需要提及的是这些小城作家在“成长—出走—归返”的人生过程中,河流都参与其中,并且作为文化之河、精神之河、家园之河、记忆之河等承载了小城作家诸多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比如沈从文之于沅水、辰河,萧红之于呼兰河,沙汀之于汶江,汪曾祺之于苏北里下河,孙犁之于滹沱河以及鲁迅、周作人之于浙江水乡……小城镇与河流的天然联系,在现代作家审美意识的观照下,文本中呈现的河流既是创作主体思想意识、情绪情感的指涉,也是临河而居的民众的生存状态、国民性呈现的重要表征,河流与城镇的关系见证了历经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形态。
一、现代小城作家的“水象”与童年经验
关于作家成长与地域的关系,现代作家的小城镇体验与情绪记忆有关,情绪记忆是“以体验过的情绪、情感为内容的记忆”[2],大多数小城作家都会以对童年时代的情绪记忆进行艺术创造想象。小城镇作家由小城孕育,而后出走来到都市,通过“身体的位移”唤起对故乡小城的观照,文学作品中具有明显的“可辨的地域意识、时空意识以及人事环境意识”[3]。临水古镇所蕴含的地域文化是小城作家讲述小城故事的追忆诱因,河流作为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文化精神”,河流成为小城作家情绪记忆的核心“诱因”与载体,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自觉地频繁出现在作品中。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将水的物质形态分为清澈的水、春水和流动的水;深邃的水、沉睡的水和死水;还有狂暴的水三种类型,其中狂暴的水是勇气的显示图,狂暴的水惊涛拍岸,对应的是弄潮儿独立河岸的尚武精神,狂暴的水的情感体验是预感;静水流深、小桥流水对应的是柔情似水的优雅品格,对其的情感体验是回忆。小城镇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重复出现的河流是情绪记忆的审美对象化,是小城镇作家情绪记忆的回溯。对于小城作家来说,他们的生命体验正如这时而沉滞时而奔涌的河流,河边的凝思是沉重的,河里的嬉戏是自由的。当“河流”融入小城作家的文学叙事,河流在文本中就不仅仅是自然地理意象,而是构成了小城作家对生命的理解与体验。生命体验是作家独特的生命沉潜,现实生活经过内心的提炼升华成为作家创作的审美对象,是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心理感受。
作家接受地域文化的濡染从童年开始,儿童时期形成文化结构心理图式,之后人格模式的形成便是同类文化印迹在此心理图式中不断被加深的过程。从原生家庭看现代小城作家的童年时代,他们大都有着丧父的经历,即使没有丧父,父亲在成长过程中也是缺席的,童年的苦难体验使生命之河陷入了沉滞期,家道中落,世态炎凉过早侵袭了小城作家的无邪童年,旧家衰败的心酸和尽遭嫌弃的内心痛苦成为小城作家共同的生命体验,也使他们从小养成了忧郁感伤的性格,“破落户”一般于“顾影自怜”[4]中体验孤独寂寞。童年体验是作家文学创作重要的文学创作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河流凝聚了小城作家所有的生命体验。沈从文童年时代父亲流亡关外,经历了从逃学河中嬉戏的“少爷”到辰河流域讨生活的“丘八”的身份位移,沈从文说自己的生活、思想、教育皆从孤独体验中获得,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最为得意之作是写了一条绵延千里的沅江边上的人与事。河流伴随着沈从文各种人生体验的生成,童年时期河流是释放天性、自由遐想的乐园;少年时期,河流是从军谋生,寂寞惆怅的安放地。沈从文孤独寂寞的情感在文学创作中以河流为载体,“孤独”也是其作品中人物的生命体验与情感表现,《龙朱》里的龙朱是美到极致的孤独寂寞,《边城》里的茶峒人善到极致的孤独寂寞。河流也是吸收悲切苦难之地,《边城》的世界即使再至善、美好都掩盖不了萦绕其中的寂寞、忧郁的情绪,翠翠、翠翠的母亲以及那些河上的妓女因为简单而执着的爱情信仰陷入命运的悲剧。小说结尾翠选择留在河上等待二佬傩送,而傩送的归期充满不确定性。可以想象一幅画面,河上的孤女,撑一支孤舟,孤独地等待归期不定的心上人,这种叙述张力所呈现的绝望与憧憬让孤独与忧伤情绪的表现达到了极致,沈从文将“孤独”与“河流”赋予了诗意的调配,这也正是《边城》的独特魅力所在。
小城作家群体大多具有“家道中落”的经历,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孤独寂寞中逆境成才的功劳多半归功于母亲。传统家庭中的母亲由幕后走到前台,一身兼双职,“以身示范,以情感动,以利诱导,以超强的意志力、拳拳的慈母心和家庭的道义感,去战胜抚孤成人生命旅途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同时在子女心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5]122。德国著名教育家福禄培尔曾经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中国文化“贵柔”,柔中有韧。自然界物质中水最为柔弱,但也最具坚韧性,“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在小城作家心目中,母亲如水一般至坚至柔,是人生成长中的启蒙者,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周作人、沈从文、冯沅君等作家的传记中都有启蒙老师是母亲的表述,这种影响恰如水的穿透力,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所以,小城作家的水象是柔和、明澈、鲜活之水,河流之于小城作家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既孤独感伤又温柔浪漫的集体记忆,而这种体验浸透了灵魂,奠定了品格。现代小城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承载着对故乡的记忆,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文学河流。
二、小城作家的现代性体验与民族河流梦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入侵的强烈撞击下,中国传统小城镇社会现代化进程被迫开始拉开了帷幕,河流也由此成为现代性的“符号象征”,而现代性体验是与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体验融合在一起的。小城作家的出生正逢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期,小城镇虽然还在宗法体制内,但现代文明已经触及,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自觉意识,所以,小城文学从诞生时起就伴随着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小城作家“以自己的全部的生命和热血去体验现代性的痛感或快感、忧郁或希望、灾祸或幸福”[6]。小城镇为那些处在中西、新旧交替时代,或持激进或持保守主义的小城作家提供了一个可以暂停缓冲、冷静思考的空间,但小城镇也因其封闭、单调容易滋生那种安于现状而又可以永久躲避的惰力。这种新旧重叠纠结的小城镇体验不能归结为简单的过渡性,而是一种现代性体验表现方式。
“流动是河的出路和前途”,对于追求现代性的小城作家来说,“出走”是新的人生选择,带着对远方的憧憬进行自我放逐,故乡的河流成为流浪、逃离的象征。小城镇是封闭的,绕城河是小城的屏障,但也阻碍了小城与外界的有效沟通,生命的和谐要通过交流与合作来实现,小城镇中的多数优秀者选择“逃离”,逃离的原因既关涉现实生存的物质贫困、包办婚姻、封闭保守、外出求学等问题,也有单调寂寞、憧憬远方、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等原因,这些因素恰好也是对小城镇沉滞、麻木、迂腐的人文精神生态的揭示。对于小城作家来说,“逃离”小城意味着生命漂泊的开始,而“漂泊”是精神上的自由,是对命运的违拗、文化规定的抗拒。突破旧的躯壳,汹涌的生命能量喷薄而出,冲动的生命意志、创造的生命目的、狂欢的生命自我律动,化作“激流”与“死水微澜”。1910年,郭沫若从家乡沙湾乘船到嘉定,心存高远志,怀抱救国心,作《泛舟谣》:“泛泛水中流,迢迢江上舟。长风鼓波澜,助之万里游”。1913年,乘船从重庆东出夔门,经朝鲜赴日本,抛却“休作异邦游”的母训,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就如涅槃再生,“被家规禁止涉入一尺深水的我,一跃而扑向海中,真是有再生般的快感”。《初出夔门》中描写了金沙江与岷江相互搏击的刚猛姿态,郭沫若的现代性体验是对自由的无限追求,“水一样奔流,狮子般奋迅”,最后成为“一个不忧的仁者和不惧的勇者”[7]。“流落在大渡河里,/流落在扬子江里,/流过巫山,/流过武汉,/流过江南,/一路滔滔不尽的浊潮/把我冲荡到海里来了。”[8]1927年,青年巴金在去伦敦留学的英国邮船上写下《海上的日出》,在文章中描绘了一幅海上日出景象,“太阳慢慢透出重围,出现在天空,把一片片云染成紫色或者红色。这时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这不是伟大的奇观么?”[9]巴金热情地把海上日出礼赞为“奇观”,而“奇”字正是青年巴金向往光明、冲破阻碍的亲身感受,是他作为时代青年对现代中国未来的期待。可以看到小城作家出走的现代性体验呈现在文本中多倾向于对河流的壮观场面的叙述。
按照加斯东·巴什拉对水的物质想象观点,河流所唤起情感体验是“梦与幻想”;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狭窄的艺术之桥》一文中也提倡,文学所表现探讨的是人、自然、命运、想象与梦幻之间的关系。整个20世纪的文化想象中,河流在民族复兴大业中不可或缺,河流形象始终与中国“现代性”进程(即民族国家产生与民族身份的建构)相伴随,代表着“民族复兴的集体渴望”。鲁迅、周作人、郭沫若、何其芳、徐志摩、沈从文等小城作家反复运用充满幻想和理想主义的“河流与梦”的叙事形式力图重燃一个古老民族的自信、自尊、自强。小城作家“关于民族身份与主体性的书写关联着民族河流梦的乌托邦地形学”[10],河流想象中将差异与对立话语相融合,在对故乡小城的回望与现实城市生存的焦灼、互动中完成对故乡小城的想象,并且透过小城的想象叙事完成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整体叙述。河流在激发小城之子们的社会想象、民族国家想象以及文化理想中扮演了动态的、开放的媒介角色。《故乡》结尾展现出河流梦的图景,我在目睹的故乡的衰败,带着气闷、悲哀的情绪离开故乡,漂流在河上,听着船底潺潺的河水声,睡意朦胧中逐渐“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鲁迅的河流梦境寄寓着一种自然空间的理想(金黄的圆月海边当空挂)和希望空间的美好(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未来的理想生活是人与人之间“没有隔膜”;劳苦大众不再“辛苦辗转”;生命状态不再“辛苦麻木”;生活状态不再“辛苦恣睢”。《故乡》中叙事者梦中的河流所唤起的理想生活渴望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的宏大集体理想:民主、平等、自由以及幸福地生活、尊严地做人。小城镇的封闭性、河流的流动性都会使生存其中的人们产生奔赴远方的幻想,在《太阳下的风景》中,黄永玉回忆表叔沈从文和自己都是在少年走出小城,“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体现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11],而对其代表作《边城》的读者期待是那些“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12]。《呜咽的扬子江》中,何其芳旅途中体验到交通领域的腐败,为故乡四川这样“狭的笼”所要肩负起的民族复兴的重任深感忧虑,“狭隘的峡间的急流,我听见了一只呜咽的歌,不平的歌,生存与死亡的歌”,这是目睹故乡现实后的愤懑,但对未来仍有着幻梦,又“期待着自由与幸福的歌”[13]。
三、小城作家的寻根体验与河流地理
文学作品对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的呈现一般与作家的思乡情感联系在一起,由小城镇进入大都市,因为“身体的位移”而唤起的故土乡情,大多数人会选择回归自然,通过对自然的回归寻求生命的价值意义,“河流”因为与小城作家的这份天然不解之缘而被选取作为“精神家园”的象征。所以,在小城作家这里,河流既是“家园”的象征,也是“根”的存在形式,“家园”情结在小城作家寻“根”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小城既是都市与乡村的连接点,又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自成体系,是独特的‘第三种社会’”[14]。所以,小城镇在空间地域具有独立的自足性,即小城镇自身的“地理隔离性”。小城作家“身体的位移”使这种“地理隔离”感在现实生活和精神心理上都得到凸显,同时也使“地理隔离”的价值意义得到发现与唤醒。小城作家对这种由于空间突破和“身体位移”而产生的情感体验表现得最为深刻且广泛,文学创作中呈现出由都市之“隔阂感”到对于“故乡小镇”之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的重新发现,如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如果说“地理隔离”构成了艺术家漫游的端点,而“返乡首先是从漫游者过渡到对家乡河流的诗意道说的地方开始”[15]。所以,对于小城作家来说,河之归返才彰显其诗意性与丰富性。走出小城家园的作家们在都市身心疲惫时就会顺流而归,返回最初的“家园”,不管是具体的现实家园还是想象中的精神家园。“漂泊”是小城作家的主动选择,“归返”亦是小城作家的主动选择。乡愁的诱导让小城镇最终成为小城作家的(精神)归宿。郁达夫归隐杭州,沙汀归返川西,郭沫若用“沫若”的笔名表达对故乡的眷念,沈从文梦断“边城”,萧红魂牵呼兰河……“对传统原乡空间的想象性回归表征着地缘民俗和民族情感认同的精神需求”[16]。
小城是小城作家一生最为魂牵梦萦之地,在文学创作中以物化形态对其呈现时,河流是小城作家家园情结最理想的具体情感载体,作家在对河流的形象生命进行叙述时会把形象的主体归结到故乡小城的河流,河川溪流纵横的乡土才能使自己的遐想(此岸走、彼岸来和河边思)物质化,通过故乡,梦才有适当的实体,进而形成一种恋乡的社会文化心理。小城作家对河流的书写不似黄河那样咆哮,也不像长江那般汹涌,只是小桥流水,平和安静。汪曾祺在散文《我的家乡》中畅谈自己与河流的渊源,在小说《逝水》中,把“河流”作为确定的故园意象反观自己生命过程,对人生作诗意总结时最重要的参照物。受吴文化滋养的苏北里下河流域是汪曾祺阴柔的文格与人格的诞生地,运河的柔波漫洇过秦邮故地,运河玩耍、看船打鱼、沿河上学,耳目之所接都是河水,水成了灌注他生命的永恒力量。虽然他辗转无数地方,但最终高邮永远是他的精神家园,人生的源头与归宿都是河水给予的生命润泽,正是精神上对河流的皈依,让他的一生“‘寂’而不枯、‘静’而不晦”[17]。
小城作家对童年生活的小城镇与自然环境的艺术感悟具有天然的优势,这种艺术感悟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并且常在与现实生存境遇相对照中被唤醒。小城作家从小城镇来到大都市,空间转换后的情绪敏感与历经迁徙变故后的矛盾冲击,“客居异乡”的现实处境让小城作家更加体验深刻。
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对故乡河流的欣赏正是出于“它同都市相隔绝”的原因,与都市隔绝,所以“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18],对于作家来说这是最好的教训。“而一旦故土渐渐远去,由河流之出口反观故土,他们此时则又多了一份作为艺术创造条件的内省体验、人生的自我审查。”现代小城镇文学凝聚了小城镇作家“‘活在昨天’的小城与人的觉醒的悲哀”[5]211的深切人生体验,陈旧、封闭、愚昧、保守的小城虽然得风气之先的天然机遇,但旧大于新、多数的不觉醒与少数的觉醒之间产生的悲哀与痛苦更为巨大,这成为多数现代小城作家们的集体经验。小城生活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日常性与重复性,普通人、日常事,绝大多数人凭着经验、习俗、传统等在凡俗、无聊中自为自在地度过光阴。而小城生活的重复性也使小城人的思维特征极具惰性与保守性,而缺乏创造性与进取性,这也使得多数从小城出走、以现代民族国家为理想的小城之子们感到小城死水般的存在状态,阻碍社会的发展,扼杀人的生命活力,这不仅是小城的悲哀,而是国家、民族的悲哀,所以小城作家选取最真切面对普通人、最直接反映小城地域特征的空间意象来折射小城群体的文化心态,表现其批判意识,“促使传统生活样式向现代转型”,所以,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小城作家面对故乡小城如此的重压与停滞都会被刺痛,当他们掀开记忆的闸门,心灵的重压也会随着流水倾泻而出,而承载这份心灵重压的将不再是自由、肆意流淌的河流,而是涡旋、停滞的河流形成的“大泥坑”与“洄水沱”的空间意象。
萧红在《呼兰河传》的开篇介绍呼兰小城的结构布局时,突出详尽地描写了小城东二道街上的一个“大泥坑”,它可以被看作呼兰小城特征的具象化,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符号。呼兰小城人们的生存状态与呼兰河地理环境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虽然人可以改变、创造环境,但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会更多影响生存在这一环境中人的性格,从而使人具有地域性格与环境特征。可见,呼兰小城人的生命力弱化与萎缩与生存环境以及生存方式有紧密的联系。呼兰小城自然地理与人文社会环境是闭塞、落后的,呼兰小城里的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生死是麻木、随意的,他们没有能力也未曾想过要好好保护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权利,由此而渐渐形成了对生命绝望而又漠视的态度。“大泥坑”是小城镇人生存状态的象征,它是陷阱、生灵吞噬者……但这里的人不但把因翻车、掉人而要抬车、抬马、救人等看成是非常热闹的事,而且还当作人与人之间可以说长道短的消遣;更讽刺的是,人们还把“大泥坑”里的淹鸡、淹猪、淹鸭等当作瘟鸡肉、瘟猪肉、瘟鸭肉来吃,以求得心理平衡。直到一位老绅士也掉进大泥坑,他才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拆掉两岸的院墙;两岸的人又不同意,又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在墙根种树,让人们爬着树过去。现实生活中的障碍,人们可以铤而走险,或绕坑而行,可是就不愿意改变现状,没有人愿意让这个“大泥坑”消失。这种对人生生命的绝望与漠视使得小城人们对生存环境没有任何改变的热情,麻木不仁、自欺欺人的凝滞、腐朽意识已经化作小城人的集体无意识,也造成小城人生命形式的荒芜。“大泥坑”象征了呼兰河人的那种安于现状、调和折中,对任何变动都害怕或者说不愿意的心理状态。
与呼兰小城“大泥坑”式的停滞相似的还有四川的“洄水沱”。“沱”的命名就来源于江水进入和流走洄水时由冲击力和离散力共同形成的深不可测的“漩涡”。“洄水沱”这种水域从表面看水流平稳,近于凝滞,由于流水在此处回旋,携带的泥沙污物等也汇聚于此,成为藏污纳垢、自我腐化与霉化的场所。“洄水沱”式人生景象经常会出现在四川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那是一种沉闷、压抑、毫无生机的僵化、停滞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特征用学者李怡的概述是“社会文化的停滞,生活模式的单调,以及个人理想的浑”[19]。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虽然是激流,但知识分子只能是出走后才能实现抱负,而浊在故乡只能是被不同程度的腐蚀、沉落在一片泥淖中,剩下的只能是高觉新(《家》)一样的“洄水沱”式人物。同时,“洄水沱”底部的暗流螺旋式运动,暗涛汹涌,随时会把身陷其中者吞噬,所以“洄水沱”也象征着自我损耗与毁灭的“窝里斗”。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小城作家痛感于故乡的停止与压抑,“洄水沱”磨蚀了知识分子的理想,满怀教育理想的汪文宣、曾树生(《寒夜》巴金),有着顽强生命力的苏幼旃(《古老的故事》陈翔鹤)等都被“洄水沱”吞噬了生命灵魂,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反省自身的参照体。
结 语
小城作家的“河流地理”有着对“故土诗意的遮蔽与呈现”[20]。四川的“洄水沱”与呼兰的“大泥坑”,其实质都是一种象征,代表了传统文化中愚昧、腐朽的意识对人的灵魂的腐蚀,病态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心理又造成生命的悲剧。而生命的悲剧与小城地域的封闭性所形成的一种顽固惯性机制相关,因为拒绝一切新鲜的异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入,呼兰河与洄水沱也只能是一河停滞的“死水”,一切都会沿着旧有的轨道缓缓陈腐地运转下去,从恬静到残酷、从残酷到麻木的老调子永远唱不完,而这些似乎也正是近现代中国形象的整体象征。但所幸的是,这样的地域还出现了萧红、李劼人等一批在漩流中有着清醒意识的作家,对这种状态能够提出警示、反思。赵园曾在《回归与漂泊》一文中指出,这种对于地域、环境的认同是人的宿命的悲哀的同时,又认为这种悲哀的意义决不仅是负面的,而是那种“折磨着因而也丰富着人的生存的诸种‘甜蜜的痛楚之一’”[21]。现代小城文学的河流书写其实远远超出了小城的范围,而是对国民性改造与启蒙、中国文化重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建构等宏大主题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