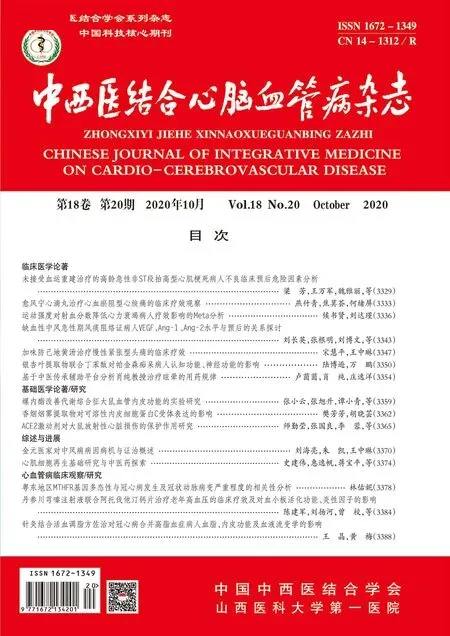金元医家对中风病病因病机与证治概述
刘海亮,朱 凯,王中琳
中风病是以突然昏仆、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不利等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病证,中风病包括现代医学的脑梗死、脑出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血管痉挛等疾病。近年来中风病发病率逐年升高,且该病具有致残率高、复发率高及死亡率高的特点[1],现系统回顾中风病的中医文献记载,为丰富临床治疗方法及提高病人生存质量等提供一定的临床参考。
1 金元之前中风病文献记载
金元之前多认为中风与“外风”密切相关,医家对于中风病研究肇始于《黄帝内经·素问》,其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提出“偏枯”“煎厥”“薄厥”等病名,认为本病与情志内伤、外感风邪关系密切[2]。《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提出邪气“在脏”“在腑”“在经”“在络”区别,张仲景创制风引汤、侯氏黑散等方剂用于中风治疗。
隋唐时期巢元方提出“风邪入脑”,认为气血亏虚,内有卫气不固、外感风邪气从而致病。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分别从“外中”与“内中”两个方向进行论述,认为“凡中风多由热起”“所患风人多热”,主张“内伤主热”学说[3],其论述对金元医家刘完素阐发火热学说产生较大影响。孙思邈将四时所中之风结合脏腑加以命名,如“肝风”“心风”“肺风”“肾风”“脾风”等,大小续命汤被历代医家广泛应用治疗中风。孙思邈提倡中风病人“当须绝于思虑,省于言语,为于无事”,通过调摄心神预防中风病,对精气亏虚、外邪引动发病之中风,提倡病初涤痰清热以治标,继以养阴清热、平肝息风以治本,临床针、灸、药等并用,首推灸治,并活用各种剂型。
唐宋之前代表医家的中风病学说不同程度推动了金元医家对中风病的认知,唐宋之后特别是金元时期中医学术思想争鸣,医家不断完善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多从“内风”立论,此外对中风病的临床治法与预后进行发挥与完善。
2 金元主要医家对中风病的认识与影响
2.1 刘完素“热极生风”学说 刘完素在《黄帝内经·至真要大论》“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等理论指导下,提出五志化火、六气皆能化火等学说,并受到孙思邈中风病内伤主热思想的影响,首创热极生风学说,认为中风病本质在热。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指出:“凡肝木风疾者,以热为本,以风为标”,概括性地指出中风病病机在于内风,从而开创了内风致病理论的先河[4]。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云:“凡人风病,多因热甚”,认为中风是由于火热生风、热扰神明、气血逆乱[5],关于中风病病机阐述突出“内风”观点;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中言“中风有瘫痪者,多因喜怒思悲恐之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由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也”,进一步指出情志为中风病的重要致病因素[6]。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载:“所以中风瘫痪者……由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7],首次提出肾水亏虚也是发病的重要因素,刘完素热极生风论对后世缪希雍等医家诊治中风病产生深刻影响。
刘完素将中风病分为中脏和中腑两大类,临证治疗区分寒热温凉,强调补肾滋阴、清降心火,重视气血流通法的应用;倡导分经论治,《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提出:“凡觉中风,必先审六经之候”[8],创制大秦艽汤以治疗中风外无六经形证,创制三化汤等方剂以疏风养血,其治疗中风病临证组方不离风药,开创性应用辛温风性药物以通腑泄热法治疗中风病中腑先例。关于中风病的先兆与预后,刘完素进行了详细论述,“诸筋挛虽势恶而易愈也,诸筋缓者难以平复”“若缓者但僵仆,气血流通,筋脉不挛”,即从筋脉抽搐和风病轻重程度判断预后;刘完素认为中风病具备先兆症状,若症见肌肉瞤动,或为手足不用,或为拇指次指麻木不仁则三年必有大风,提倡应用天麻丸、愈风汤、八风散等药物,为中风病的防治提供了借鉴。
清代著名医家叶桂受刘完素“热极生风”“心火暴盛”学说影响,认为中风病病机肝风内动为“身中阳气之变动”,提出“阳化内风”学说[9]。因心血失养、肾水亏虚、肺金失平、脾土不培以致肝阴不足,血虚生热化风,凤阳扰动,九窍不利而头目不清,症见抽搐瘛疭跌扑眩晕等,由此叶桂提出“养血息风”“缓肝息风”“镇阳息风”“介类潜阳”等多种治则,先用养血、缓肝、滋阴等方法顾护正气,再用镇阳、潜阳、和阳等方法以息风。
现代医家重视中风病的预防并取得丰富的经验。陆永昌教授提出镇肝潜阳等防治中风四法[10],并指出“治莫胜于防”,张学文教授提出“可逆性中风”[11],临证多采用活血化瘀等治疗中风先兆。随着中医体质学说发展,探讨中风病致病的综合危险因素与易发体质,辨体辨证用药,降低中风病高危体质人群发病率,对今后中风病的防治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2.2 张元素倡导六经辨证施治 张元素《洁古家珍》言:“大抵中风者多着四肢、中脏着多滞九窍”,明确指出中风病中脏病位在里,临床表现以“即不识人”的偏瘫、神昏等症状为主;中风病中腑病位在表,临床表现以“肌肤不仁”的肢体挛急不舒为主,其中“病在里用下法,病在表用汗法”,中风病中脏当用下法,中腑当用汗法。张元素《洁古家珍》云:“风中腑者,先以加减续命汤,随证发其表”“中脏则大便多秘涩,宜三化汤通其滞”,临床灵活使用通补治法,倡导六经辨证施治,重视中风病的预后及临床调护,提出调阴阳、补肝肾、和营卫的具体治法。
针灸配穴上,张元素重视大接经针法,即“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之意”[12],皆取自十二正经井穴,“从阳引阴”法是从足太阳膀胱经井穴至阴穴开始,顺次取肾、心包、三焦、胆、肝、肺、大肠、胃、脾、心、小肠十一经井穴;“从阴引阳”法是从手太阴心经井穴少商穴开始,顺次取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十一经井穴[7]。
明代杨继洲[13]总结前人关于中风病的针灸经验,《针灸大成》列中风病专章,针对不同症状采取针刺不同穴位,并指出火灸在中风病的适应与禁忌情况,该书涉及30余处穴位为目前多为临床首选。邓铁涛教授辨治中风病昏迷病人采用针药结合[14],阴闭以苏合香丸配太冲、丰隆、人中,阳闭以至宝丹或安宫牛黄丸配十二井穴、人中、太冲等。注重分部取穴、循经取穴为现代临床治疗中风病的重要取穴原则。
2.3 张从正“厥郁生风”学说 张从正在中风病诊治上受刘完素用药寒凉学术思想启发,根据《黄帝内经》“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的风邪致病特点,认识到中风病昏不知人、口眼歪斜、顿僵暴仆系列症状与风邪相关,力主中风病病机为肝风内动、风火相煽、上冲犯脑。发病节气上,张从正认为中风病“多发于每年十二月,大寒中气之后,及三月四月之交,九月十月之交”[15],已认识到发病与时间节律的关系。
张从正认为中风病因“以风为本,以痰为标”。临证分析口僻病因属性不同,认为“然而不愈者何也?盖知窍而不知经,知经而不知气故也”,即在当时已认识到口角歪斜的临床表现可由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和脑卒中两种疾病引起。张从正倡导“邪去正安”,临证多采用汗、吐、下三法合用,“风病之作,仓卒之变生,屡用汗吐下三法,随治随愈”[16],用药多采用凉膈散、防风通圣散、三圣散等,疗效显著,并进一步提出三法禁忌,强调临证根据不同病情选择相应剂型。
2.4 李东垣“气虚生风”理论 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的枢纽。李东垣所处时代,社会动乱,百姓饮食不节,加之寒温起居不适等因素,认为中风病的发生多与正气亏虚相关。中风病病因病机根源于“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指出非外感风邪,病因归纳于正气亏虚;“凡人年逾四旬,多有此疾”,李东垣认为中风病发病与脾胃虚损及年龄有关,老年脾胃功能虚弱,脾失健运失于统摄,脏腑经络失于濡养,中风病在老年群体中多发,并进一步指出中风病的发生常与痰浊闭阻气血相关。
李东垣创新性地将中风病分为中脏、中腑、中血脉3类[17]。用药经验上,对中腑、中血脉病人提出“和脏腑,通经络”的治法,起初不宜用龙脑、牛黄、麝香等辛香通行之品,为麝香治脾入肉,牛黄入肝治筋,龙脑入肾治骨[17],恐用药引邪深入;另外不可多用大戟、芫花、甘遂导泻大便,恐损阴津,愈发损耗正气。临证施治中,李东垣承袭刘完素及张元素的学术理论,临证多用加减大秦艽汤及加减续命汤等方剂。中风病中脏者,表现痰涎壅盛、神智昏冒者,应用至宝丹等重镇之品;中风病中血脉,在外表现有六经证者,应用小续命汤加减及疏风汤治疗;中风病中腑者,表现为腑实阻滞者,应用三化汤或麻仁丸以通利肠腑。
清代医家王清任受李东垣“气虚生风”理论影响,重视气血流通在机体中的作用,将元气作为生命之本,“人行作动转,全仗元气”[18],将中风病专以“半身不遂”代述,病机以“气虚”立论。“或左或右半身无气,无气则不能动”“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王清任将中风病病因病机阐述为气虚为本、血瘀为标。根据中风病气虚不能鼓动血行而致血瘀病机,创制补阳还五汤以重用黄芪大补元气,加之配伍川芎、桃仁、地龙等活血通络化瘀之品。王清任的补气活血证治思路,对后世应用推广活血补气治法提供了有益借鉴。李东垣“气虚生风”学说在后世逐渐发展,由此而形成中风病内伤致病的病机理论,现代临床多将正气亏虚以致脏腑功能失调作为中风病的主要发病机制,肝肾亏虚、气血虚少作为发病根本,相关研究证实,部分地区中风病病人年龄以(59.95±13.87)岁为多发区间[19]。
2.5 朱丹溪“痰湿生风”理论 朱丹溪进一步发展了刘完素正气亏虚、内风致病的理论,进而独辟蹊径认为本病乃“痰”所致,认为中风病病机为“痰湿生风”。《丹溪心法》中载“半身不遂,大率多痰”,东南之人,脾气失健,水津不化困脾,聚痰生湿,脾气亏虚进一步加重,湿郁日久化热,热极生风,风火冲脑为中风的主要病机,由此认为“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20];并指出“风之伤人,在肺脏为多”,考虑到地域与体质的发病因素。
“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21],朱丹溪将化痰开瘀作为治疗大法,主张根据气虚、血虚、挟湿、挟水分别使用补法与吐法,另外考虑到地理环境、体质、气候等因素差异,“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论”。治则上,朱丹溪提出“以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或作血虚挟火与湿,大法去痰为主”[20],重视化瘀法的应用,临证多血虚用四物汤加竹沥,气虚用独参汤加竹沥、姜汁等益气开窍豁痰,此外常用天麻、牛膝、地龙、半夏以行瘀祛风化痰通络。中风病初期如见昏倒,急掐人中,苏醒后应用四君子汤、二陈汤等祛湿化痰方药治之。
王永炎教授多以化痰通腑法辨治痰瘀互结、中焦腑气不通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22],通腑化痰类药物如瓜蒌、大黄、天南星应用广泛。王新陆教授从血浊论阐述脑动脉硬化的发病机制[23],清化血浊法在临床诊治痰瘀互结脑血管疾病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2.6 王履划分“真中风”“类中风” 王履将中风病分为“真中风”“类中风”。王履尊经致用,其学术思想源于朱丹溪,系统总结朱丹溪关于中风的学术思想,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加之自己的学术见解,阐释中风病的病机,《医经溯洄集》中提出:“河间主乎热,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24]王履从病因角度直接阐释真中风和类中风的区别,并进一步提出“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王履将朱丹溪、李东垣、刘完素及前人中风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归纳与总结,丰富了中风病机及证治的认识。
王履关于中风病“真中风”“类中风”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清代医家沈金鳌提出将痹证、痿证、厥证等归纳于类中风范围,扩大了内风致病的证治理论,对后世中风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支持。
受金元主要代表性医家病因病机证治理论的影响,明代缪希雍认为中风病发病为“内虚暗风”,即阴虚内风立论,南北气候各异,体质差异,治法上顺气化痰清热以治标,养阴固本以治本,以脱离前人温散外风和同时代温补肾元的常法。治疗中风病多使用单方、验方,除用汤药配合丸剂,注重中药炮制以增效减毒,提倡配合手法,风格独树一帜,影响颇为深远。
3 小 结
中风病作为中医内科的常见疾病,临床发病急骤,自《黄帝内经》开始,对中风病的具体病因病机进行详细论述,如“偏枯”“风痱”“大厥”等;在《黄帝内经》理论指导下,历代医家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及临证治法不断阐述发挥,唐宋之前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医家提出中风病的“外风”学说,以感受外部风邪,“风人多热”等具体特殊体质因素等展开。
金元时期,时代动乱,学术碰撞,金元医家百家争鸣,刘完素提出五志化火理论,首创热极生风学说,将中风病分为中脏和中腑两大类,创制大秦艽汤等首开应用辛温风性药物以通腑泄热法治疗中风病中腑的先河;张元素在针灸治疗上,重视大接经针法,皆取自十二正经井穴;张从正多采用汗、吐、下三法合用剂型灵活多变治疗中风病;李东垣提出“气虚生风”理论并将中风病分为中脏、中腑、中血脉三类;朱丹溪根据自身“痰生热,热生风”观点,重视行气化痰开瘀治则的应用;元著名医家王履将中风病分为“真中风”“类中风”两类。金元医家学说交相辉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医家借鉴前人理论学说,结合自身临证经验,创造性提出中风病的不同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理论。金元以后,受金元医家学说影响,明代赵献提出中风病病机痰涎壅盛,本在脾肾,标在痰涎,将补肾健脾化痰作为中风病主要治法,治中风病之痰;陈自明提出“医风先医血,血行风自灭”[25],以活血祛风法作为中风病治法;叶天士提出“阳化内风”的致病理论;王清任的半身不遂气虚血瘀学说,以补气活血化瘀通络的临证思路对应用活血化瘀法具有深远意义。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时期关于中风病学说流派纷呈,在唐宋之前“外风”学说的理论上,进一步拓展了中医学对中风病病因病机与治法方药的理论体系。现代临床中风病辨证多元化,治则治法多样化,诊断标准化,活血化瘀、通腑化痰、滋补肝肾类治则治法在中风病各分期中应用居多,且受金元以来针药结合,配合药洗、外敷等治法,常取得理想的临床疗效。受金元以来重视内因致病病机学说的影响,刘完素与李东垣对中风病中脏、中腑、中血脉的划分为重要的辨证要点,现代中医临床以肝肾亏虚、风火痰气瘀虚病理因素与产物交互作用作为中风病的主要发病机制,并将刘完素、朱丹溪、李东垣等医家祛风通络、健脾化痰、补益肝肾、活血化瘀等治法进行有效发挥,地黄饮子等名方在脑血管疾病后遗症期辨证基础上得到广泛应用。关于祛散外风药物的安全用药剂量及使用配伍问题,仍需进行科学分析。合理应用金元医家关于中风病的临证有益经验,遵循个体差异,掌握不同证候群体的病机与病理因素特点,以求“古为今用”,提高中风病病人治愈率与生存质量,需不断进行科学有益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