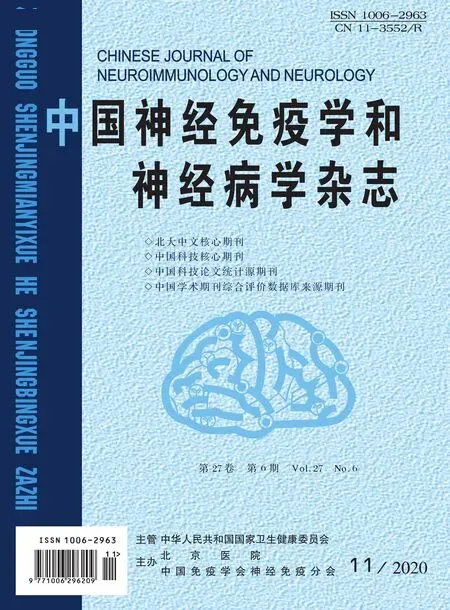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研究进展
石冰心 武雷 黄德晖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NMOSD)是以视神经和脊髓同时或相继受累为主要表现的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近年来针对NMOSD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无论是2015年诊断标准的更新,还是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antibody,MOG-Ab)的发现,抑或新药的研发等,均拓展了人们对该疾病谱的认识。现就近年来有关NMOSD领域研究的热点及新进展进行综述。
1 流行病学
不同种族、地区间NMOSD的发病率存在差异。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非白种人的NMOSD发病率较高,以育龄期女性为主。在亚洲范围内,以东亚人群(中国人和日本人)患病率似乎更高,而在世界范围内黑种人患病率似乎最高。日本北部地区NMOSD的原始患病率为4.1/10万,平均发病年龄为45.2岁,女性(86%)明显多于男性[1]。多种族人群聚居的马来西亚槟榔屿地区其患病率为1.99/10万,其中华裔人群患病率最高[2]。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NMOSD的估计发病率为每年0.037/10万,估计患病率为0.70/10万[3]。Mori等[4]研究结果显示,除马提尼克岛(10/10万),全球大多国家地区发病率约为5/10万或更低,且与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不同的是,尚未发现NMOSD的患病率与纬度具有相关性。目前尚无确切的全球流行病学数据。
2 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改变
NMOSD的确切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其是在遗传易感基础上,由环境因素作用下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所致。
水通道蛋白抗体(AQP4-Ab)阳性患者病理生理机制已有较多阐述,其靶抗原为星形胶质细胞;在AQP4-Ab阴性患者中,约20%患者可检测到MOG-Ab,其靶抗原为少突胶质细胞,两者存在不同的病理生理基础[5]。
对于合并肿瘤的NMOSD,既往多被认为其是一种罕见病和一种常见病的共病,但近年来研究发现癌细胞可表达AQP4,两者间可能存在直接的病理学联系[6]。AQP4-Ab可能由抗肿瘤的免疫反应产生,但不一定会出现NMOSD相关临床表现,其发病需其他因素参与。
约30%的NMOSD患者在疾病首发或复发前经历过感染,感染可能是NMOSD自身免疫反应的触发因素,机制可能与分子模拟、AQP4的免疫耐受性被打破或全身细胞因子反应引起免疫紊乱有关[7]。
虽然典型的病例呈散发性,但也有报道显示约3%左右为家族型[8],且不同种族间发病率存在差异,提示NMOSD发病与基因多态性有关。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基因被发现对NMOSD的发病具有保护或易感作用,但两者间确切的关系仍需进一步验证。
维生素D对细胞因子的产生、免疫细胞的发育和分化以及抗体的产生均有调节作用,其水平降低与NMOSD的疾病活动有关,可能参与了NMOSD的发病过程[9]。肠道菌群结构的改变也被认为是诱发NMOSD的可能环境因素之一[10]。此外,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头部外伤史和流产等亦与NMOSD的发生存在相关性[11]。
3 临床和影像学特征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检查发现,AQP4-Ab阳性者“未受影响的眼睛”也可存在中心凹厚度变薄[12],提示中央凹富含表达AQP4的Müller细胞或视网膜星形胶质细胞已出现了自身免疫炎症性损害。另外,弥散张量成像亦也观察到临床“未发生过视神经炎(optic neuritis,ON)”患者的眼睛亦存在视网膜内部结构和视觉通路的损伤[13]。
NMOSD患者脊髓炎多为长节段,轴位上病灶易累及中央管,颈、胸髓多见;也可表现为短节段,在AQP4-Ab阳性者中,首发表现为短节段脊髓炎的比例甚至高达14%[14]。少见临床和影像表现还包括脊髓空洞样表现、周围神经损害表现、自主神经系统症状(心血管系统、颈髓病变导致Horner综合征等)以及高颈髓病变导致的颈源性头痛、瘙痒等。有研究认为,合并结缔组织病者的脊髓病灶节段一般更长[15]。
以极后区综合征起病者常被误诊为消化系统疾病。顽固性咳嗽可能是延髓背侧受累的少见表现。
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组织器官也可表达AQP4并出现相应损害,如肌肉[16]、肾脏[17]、肺[18]等,但可能由于补体调节因子对外周的保护作用[19],NMOSD仍以中枢神经系统受累为主。
NMOSD易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20],近年来报道的少见共病包括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特发性肥厚性硬脑膜炎、皮肌炎、重症肌无力等。
功能影像技术如弥散张量成像、髓鞘水成像、脑多频磁共振弹性成像等有助于发现脑白质区域的隐性损害和组织变性[21]、评估皮质脊髓束完整性等[22]。还有关于皮层厚度与认知损害关系、病灶区域髓鞘含水量、皮质脊髓束髓鞘水分改变[22]、铁稳态[23]等方面的研究。
4 MOG-Ab相关疾病
MOG-Ab相关疾病研究是近年来热点之一。AQP4-Ab阴性NMOSD患者中约近1/3存在MOG-Ab,后者中有少部分同时合并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抗体阳性。关于MOG-Ab阳性疾病的分类,部分学者认为其是NMOSD的亚型。但由于二者免疫病理不同,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及预后均有一定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们是不同的疾病实体,将其称为MOG-Ab相关疾病(MOG-antibody-associated disease)。
总体来说,与AQP4-Ab阳性者相比,MOG-Ab相关疾病发病更早(前者平均发病年龄约为40岁,后者约为30岁)[5],女性构成比例较低〔前者女∶男约为(3~10)∶1,后者约为2.8∶1〕,44%~83%者呈复发缓解病程,总体复发风险较AQP4-Ab阳性者低,约50%~80%的患者遗留残疾。此外,与AQP4-Ab阳性患者相比,只有约9%的MOG-Ab阳性者存在相关共病,而前者此比例约占1/3。
ON是MOG-Ab相关疾病最常见的表型,且ON发生率或同时发生双侧ON的比例均较AQP4-Ab阳性者高,炎症好发于视神经前段,视交叉和视束通常保留,视神经严重肿胀和扭曲,70%~80%可见眶内神经鞘膜和脂肪组织强化。AQP4-ON虽然也多见纵向广泛受累,但视神经后段受累更多见,肿胀较轻且很少扭转。
约50%的MOG-Ab相关疾病患者存在脊髓病灶,多为长节段,腰骶髓病变是其相对特异的表现,而AQP4相关脊髓炎病灶以颈、胸段居多。
约45%的MOG-Ab相关疾病患者发病时颅脑存在病灶[5],且随病程进展这一比例会增加。大多发病时为双侧病灶,1/3有幕下病灶(主要位于脑干)。与AQP4-Ab阳性者相比,MOG-Ab阳性者丘脑和脑桥病灶更多见,极后区病灶较少见,颅内病灶多呈斑片弥漫分布,较大者可表现为假瘤样病灶,且易累及灰质[24],甚至可有软脑膜强化。动物实验表明,通过给予经MOG免疫的大鼠皮质注射促炎细胞因子,可诱导大鼠发生广泛的皮质脱髓鞘[25]。尽管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但伴和不伴癫痫的脑病被认为是MOG-Ab相关疾病较常见的表现[26]。部分患者以头痛、发热、脑膜刺激征起病,初期易被误诊而延误治疗。目前大多研究认为这种无菌性脑膜炎表现可能是该疾病谱中的一种特殊表型[27]。
MOG-Ab相关疾病患者的视力及运动功能预后一般较AQP4-Ab阳性者好[28],患者对糖皮质激素(后文简称“激素”)的使用和戒断敏感,部分患者减量过程中出现病情加重,激素减量过程宜缓,有复发倾向者建议小剂量激素维持或加用其他免疫抑制药物。但有研究发现,部分接受利妥昔单抗(rituximab,RTX)治疗的MOG-Ab相关疾病患者在B细胞有效耗竭状态下仍有复发,提示其存在非B细胞依赖的病理基础。
5 诊断
2015年更新的诊断标准中取消了对NMO的单独定义,统一命名为NMOSD。对于抗体阳性者,有六大主征之一即可诊断;对于抗体阴性或未检测者,需具备2个主征(其中必须要有三核心主征之一),并同时满足附加MRI条件。Hamid等[29]研究显示,2015年标准将NMOSD的诊断率提高了76%,其中AQP4-Ab阳性组提高了62%,AQP4-Ab阴性组提高了14%。Hyun等[30]对252例符合2015年诊断标准的NMOSD患者研究发现,仅136 (54%) 例满足2006年诊断标准。新标准允许更多抗体阴性者被纳入诊断,而抗体阴性患者中(部分MOG-Ab阳性)男性比例较抗体阳性组高,故新标准可能会对NMOSD男女患病比例产生一定影响。
6 治疗
激素冲击、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仍是NMOSD急性期治疗的选择。临床研究显示,RTX在预防复发方面具有优势,甚至在复杂难治性及NMOSD与MS不能很好区分者中亦显示出确切效果。RTX输注后几周内的疾病活动可能与B细胞活化因子和自身抗体水平的暂时增加有关。其不良反应包括输注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和后期可能发生的间质性肺病等。建议监测B细胞比例来指导给药和重复给药[31]。此外,已有针对发病机制中不同环节的新药被批准进入临床或试验阶段[32],如C5补体抑制剂(eculizumab)、白细胞介素-6受体阻滞剂(SA237,tocilizumab)、抗CD19B细胞耗竭剂(inebelizumab)等;还有一些靶点治疗药物,如CD59、葡萄糖调节蛋白78、水通道蛋白、Th17细胞等正处于研究阶段。
7 特殊人群的NMOSD
7.1 儿童型NMOSD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约4%在儿童时期起病,有限的研究结果显示[33],儿童型亦以非白色人种更多,AQP4-Ab阳性率约65%,抗体阳性与阴性患者在人口统计学、临床及实验室特征方面无统计学差异。儿童型中MOG-Ab阳性率较高(约20%),发病年龄呈双峰分布,发病年龄较小者(4~8岁)脑病发生率高,小脑脚病灶发生多,极后区综合征较少,可能具有一定特异性;发病年龄较大者(13~18岁)ON发生率高。MOG-Ab阳性儿童复发间隔相对较长,预后相对较好。目前缺乏基于临床试验证据的儿童用药指南,可选择的药物包括激素、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硫唑嘌呤、RTX等[34]。
7.2 晚发型晚发(首发年龄≥50岁)NMOSD并不少见,占30%左右,还有部分极晚发病例的报道。晚发者脊髓受累比例较高,发病年龄与扩展残疾状态量表评分(EDSS)间存在正相关,视神经和颅内病变较少,提示可能存在基于年龄的解剖易感性[35]。还有研究认为,晚发型患者临床表现与早发者类似,但预后一般较早发者差,尤其在AQP4-Ab阳性或AQP4-Ab与MOG-Ab均阴性时[36]。
7.3 妊娠患者NMOSD对妊娠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大多研究认为NMOSD不增加死胎或流产风险[37],但也有研究认为妊娠会增加流产、先兆子痫风险,尤其是在抗体阳性者,且高活动期受孕风险更高[38],其机制可能是AQP4-Ab可通过与胎盘AQP4结合,激活补体和引起炎性细胞浸润进而导致流产。因此建议病情平稳半年以上再考虑妊娠。AQP4-IgG在妊娠中晚期可穿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但目前尚未发现这些孩子出现NMOSD的临床征象,且抗体在1~3月龄时可自动转阴,与IgG半衰期相符。
有关围产期发病率,一般认为产后3个月内可增加复发风险,而针对妊娠期间复发率的报道结果尚不一致。妊娠期维持合理有效的免疫抑制治疗有利于控制疾病活动。激素、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被认为相对安全。针对免疫抑制剂的疗效,研究证据相对较多的是硫唑嘌呤,对于妊娠期复发风险高的患者获益可能大于风险。越来越多的临床个案报道妊娠期患者使用RTX治疗可获得良好妊娠和新生儿结局[39]。
生产方式、麻醉方式、喂养方式不影响疾病病程[40],服用非氟化激素者进行母乳喂养相对安全,尚未检索到有关婴儿不良事件的报道,建议在服药1~4 h后哺乳。服用吗替麦考酚酯、甲氨蝶呤、米托蒽醌的患者应避免母乳喂养,关于使用硫唑嘌呤、单克隆抗体母亲的母乳喂养是否安全,目前尚无定论。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有关NMOSD在全球流行病学和确切发病机制等方面尚不十分明确,但随着对其在临床、影像学以及MOG-Ab相关病和特殊人群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对NMOSD的认识不断清晰;此外,新靶点治疗药物研究的不断开展,将会对其治疗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