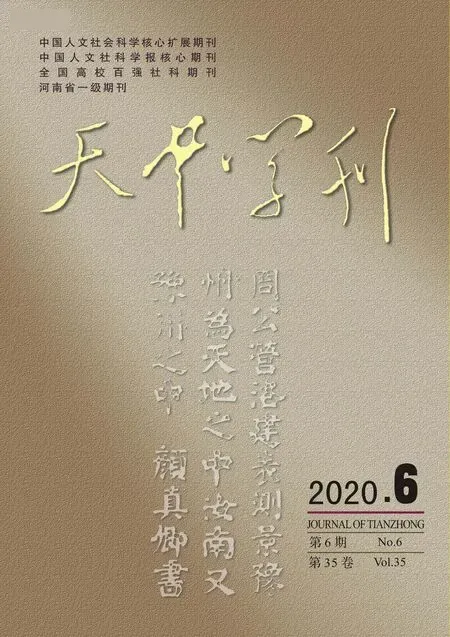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诗话中的“共鸣”及其诗学特征
洪树华
论中国古代诗话中的“共鸣”及其诗学特征
洪树华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共鸣”是阅读者在阅读鉴赏作品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情感现象。在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诗话中,存在着大量的“共鸣”资源。这些“共鸣”资源,或是简单涉及,或是上升至理论的阐发。探讨“共鸣”的不同心理层次,分析古代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把握,体会古代诗论家对文学接受者共同心理现象的高度关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共鸣;称赏;堕泪;诗话;诗学特征
“共鸣”是阅读者在阅读鉴赏文学作品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情感现象。“文学鉴赏中的共鸣,是鉴赏者对艺术形象进行审美观照时的感同身受,主要指鉴赏主体和鉴赏对象在思想感情方面的一种共通感。”[1]462在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诗话中,存在着大量的“共鸣”资源,或是简要涉及,或是上升至理论阐发。笔者以诗话为中心,试图对“共鸣”的不同心理层次进行探讨,分析古代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把握,体会古代诗论家对文学接受者心理现象的高度关注,进而把握“共鸣”现象的诗学特征。
一
从现存典籍看,“共鸣”现象的记载,可以追溯至《易经·乾·文言》:“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2]“同声相应”就是指声音的共鸣。另外,《庄子·徐无鬼》:“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鲁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鲁遽曰:“是直以阳召阳,以阴召阴,非吾所谓道也。吾示子乎吾道。”于是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3]鲁遽对瑟的声音的调试,“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其实就是指共鸣。然而这些与笔者要谈的“共鸣”并非一回事。笔者所谈的“共鸣”是指在诗话中涉及的接受主体在阅读作品过程中的情感反应,即作品中的思想内容、艺术形象感染了接受者,引起接受者情感一致的效应。
或许有人会认为,涉及艺术的“共鸣”仅存于西方文论之中,如黑格尔说:“因此人们常说,艺术总要感动人;但是如果承认这个原则,我们也必须提出一个问题:艺术应该通过什么来感动人呢?一般地说,感动就是在情感上的共鸣……但是在艺术里感动的应该只是本身真实的情致。”[4]黑格尔在谈到“情致”时,对“感动”做出了简单明了的解释,认为感动就是在情感上的共鸣。还有西方学者在提及欣赏建筑艺术时,指出了欣赏者的“共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曾说:“一根神庙中的立柱,只所以看上去挺拔向上,似乎是承担着屋顶的压力,并不在于观看者设身处地的站在了立柱的位置上,而是因为那精心设计出来的立柱的位置、比例和形状中就已经包含了这种表现性。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与立柱发生共鸣(如果我们期望这样做的话)。而一座设计拙劣的建筑,无论如何也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5]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了古希腊神庙建筑艺术的欣赏者有可能与精心设计出来的立柱发生共鸣。总之,上述所引西方学者的言论,都涉及艺术欣赏中的“共鸣”话题。
二
“共鸣”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诗话中并没有直接出现,但是不能说中国古代诗话没有相关的语言表述。
(一)中国古代诗话中的“共鸣”资源
在中国古代诗话中,“共鸣”资源最早可追溯至《诗品》,如《诗品》卷下“宋监典事区惠恭”条:“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干。颜为诗笔,辄偷定之。后造《独乐赋》,语侵给主,被斥。及大将军修北第,差充作长。时谢惠连兼记室参军,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调。末作《双枕诗》以示谢。谢曰:‘君诚能,恐人未重,且可以为谢法曹造。’遗大将军,见之赏叹,以锦二端赐谢。”[6]20又《诗品》卷下“梁常侍虞义梁建阳令江洪”条:“子阳诗奇句清拔,谢朓常嗟颂之。洪虽无多,亦能自迥出。”[6]24上述引文中的“赏叹”“嗟颂”带有赞叹之义,这是“共鸣”的最初迹象。后来,诗话中出现了涉及接受主体的“涕泣”现象,如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老杜《衡州诗》云:‘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此语甚悲。昔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后之人亦当有味此而泣者也。”[6]400“涕泣”一词表明接受主体在阅读作品之后具有了“共鸣”的心理现象。又如元代蒋正子的《山房随笔》记载了鉴赏者“堕泪”的情形:“一户曹之妻,与太守有私,府学一士子知其事。户曹任满将去,守招其夫妇饮,士子作《祝英台近》付妓,令歌之:‘抱琵琶,临别语,把酒泪如洗。似恁春时,仓卒去何意。牡丹恰则开园,荼䕷厮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无谓,复道明日行呵,如何恋得你。一叶船儿,休要更沉醉。后梅子青时,杨花飞絮侧耳听,喜鹊哩。’守与此妇俱堕泪,其夫不悟。”[6]719太守与掌管农桑、民户的官员之妻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婚外情,他们作为鉴赏者听到歌妓演唱《祝英台近》时,被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和浓郁的情感所感动,情不自禁,一起“堕泪”,进入了“共鸣”的状态。
(二)鉴赏主体“共鸣”的心理层次
中国古代诗话蕴藏了丰富的“共鸣”资源,主要涉及鉴赏主体在阅读或欣赏作品过程中,与作品中的思想感情、艺术形象达到同频共振的地步。这些鉴赏主体身份不一,有上至皇帝,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云:“唐时伶官伎女所歌,多采名人五七言绝句……大历中,卖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价至数十万,云:‘此女子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安可他比?’李峤汾水之作,歌之,明皇至为泫然曰:‘李峤真才子。’”[7]1972此则记载了唐明皇听到歌伎唱李峤《汾阴行》而感动流泪。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下第四十四条也有类似记载:“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李峤《汾阴行》,能使明皇感动流涕,真绝唱也。”[8]211还有下至普通读者,如都穆《南濠诗话》卷上云:“王孟端舍人作诗清丽。尝有人久客京师,乃别娶妇,孟端作诗寄之云:‘新花枝胜旧花枝,从此无心念别离。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对数归期。’其人得诗感泣,不日遂归。”[9]511孟端,是明人王绂的号,客居京师者被王绂的诗所感动而流泪。无论是皇帝,还是一般读者以及诗论家,他们都是文学接受者或鉴赏主体。从这些鉴赏主体的鉴赏活动来看,“共鸣”包含了不同的心理层次:
1.初级层次——称赏与叹息
众所周知,欢喜与悲伤属于人的基本情感。在鉴赏活动中,由于受到作品中艺术形象或内容的感染,鉴赏主体对诗歌的鉴赏也会表现出欢喜与悲伤的情感。
一方面,鉴赏主体会表现出“称赏”之类的积极情感。在明、清诗话里,有多处记载了鉴赏主体鉴赏诗歌时表现出“称赏”,有时也用“赏服”“叹绝”“激赏”“叹赏”“吟赏”等词语来表达鉴赏主体的心理。清人查为仁《莲坡诗话》第三条云:“杨无补年才弱冠,为人题扇云:‘闲鱼食叶如游树,高柳眠阴半在池。’某宗伯见之,吟赏不置。”[8]475“吟赏”是某宗伯对年龄才二十岁的杨无补的诗句吟诵赞赏。又《莲坡诗话》第五十九条云:“曾有僧假余诗谒王阮亭先生,中有‘乱松残雪寺,孤磬夕阳山’句,先生叹赏不已。”[8]488阮亭是王士祯的号,其诗论的核心是“神韵”,能对查为仁的诗句怀有“叹赏”的心情,说明该诗句的精妙。在明、清诗论家中,清代王士祯(禛)较多关注鉴赏者因鉴赏诗歌而引起的心理反应,他在《渔洋诗话》中多处涉及鉴赏主体对诗歌的赞赏,如卷上第二条:“东亭与宋荔裳、严武伯、叶元礼诸名士,游吴兴道场山,共赋五言诗。兄诗先成,群公叹绝,以为‘微云淡河汉’之比。”[8]165王士祜(东亭)即兴赋诗五言赢得了在场诸名士的赞叹。又如第六十七条:“予所居小圃石帆亭南,有池曰春草。一日集子弟群从赋诗。弟士骊幔亭有‘天际星河倒入池’之句,予甚激赏之。”[8]177“激赏”说明王士祯十分赞赏王士骊的诗句“天际星河倒入池”,这是王士祯作为鉴赏者的审美鉴赏心理的直接体现。在诗歌鉴赏活动过程中,“赏服”“叹绝”“激赏”“称赏”“叹赏”“吟赏”等都是鉴赏主体受到作品中的思想内容或者艺术形象的感染而触动了情绪的表现,是内在心理的外在显现。有时在诗话中,还可见用“击节”来表达鉴赏主体的积极审美心理。“击节”,本指打击乐器以控制乐曲的节奏,也表示十分赞赏。明、清诗论家多次运用“击节”来表达鉴赏者的赞赏心理,如蒋冕《琼台诗话》云:“先生尝与友人冯元吉夜宿江馆。元吉诵宋人周明老《题龟山》回文诗,属先生两和其韵。先生和之,元吉击节叹赏,以为非明老所及。”[9]649琼台先生的和诗,得到了冯元吉的赞赏。查为仁《莲坡诗话》云:“横塘居士文钦明,其先高丽人,国初入京师,两传而富峙陶、顿。居士赋性脱略,任意挥霍。……一夕招余,出歌姬数人佐酒,中有双鬟歌一绝云:‘含烟浥露一枝枝,半拂阑干半映池。最恨年年飘作絮,不知何处系相思?’为之击节不置。”[8]494横塘居士文钦明对其中一名歌姬的歌曲十分赞赏。上述涉击“击节”的例子,说明了鉴赏主体在鉴赏诗歌时表现出赞赏的心理。可以说,“共鸣”得以形成,往往是从对诗歌的赞赏开始的。
另一方面,鉴赏主体会表现出“叹息”的情感反应。鉴赏者在鉴赏诗歌作品时,除了有赞赏的审美心理,还有“叹息”的情感反应,如王士祯《居易录》:“欧阳永叔致仕,乞居颖,终其身不归庐陵,前人议者不一,洪文敏《二笔》驳之尤详,略云:欧公吉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泷冈,公自为阡表。而公中年乃欲居颖,其《思颖诗》序云云,逍遥于颖,盖无几时。惜无一语及松楸之思。崇公唯一子,公生四子皆为颖人,泷冈之土,遂无复有子孙临之,是因一代贵显,而坟墓乃隔为他壤。予每读之,辄为太息。”[10]王士祯摘引了洪迈的笔记,每次阅读欧阳修的《思颖诗》序,联想到欧阳修的家世背景,发出长叹。可见,“太息”含有悲伤的情感成分。在明、清诗话中,对阅读者因阅读诗歌而引起悲伤心情的情况也多有记载。有的是诗论家以自己的阅读实践,谈及阅读带来的伤感,如陈第《读诗拙言》云:“愚读《离骚》,爱其才情濬发,托兴高远,诚辞赋之宗也。至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则窃叹曰:是其谤之招乎。至‘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葅醢’,则又叹曰:夫其自知之矣。盖其嫉谣诼,怨灵修,回望故都深缱缱焉,直令人恻然伤心。”[7]2190陈第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谈到阅读《离骚》触发的叹息与伤心。郭子章《豫章诗话》卷六云:“予故友杨寅弼,字君良,通政载鸣公子,文贞公孙也。能诗,早卒。予为铭其墓,略曰:‘嗟嗟!君良已矣,所可不朽腐者,独文与诗。’予尝次第其诗,读之,益又足悲矣……‘从军苦最苦,啼寒在故乡。’读之令人气沮畅回,山欲堕而海欲枯。”[7]2350郭子章阅读故友生前所写的诗歌,愈加悲痛与伤感。明代瞿佑在《归田诗话》中也多次提及读者因阅读诗歌而叹息、悲伤,读者或因诗歌表达的“愁”感而不乐,如:“柳子厚诗:‘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作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或谓子厚南迁,不得为无罪,盖虽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语虽过,然造作险诨,读之令人惨然不乐。”[9]15或因诵读诗歌,触景生情,而发出感慨,如“渔家傲”条:“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渔家傲》词曰:‘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予久羁关外,每诵此词,风景宛然在目,未尝不为之慨叹也。”[9]21或因读者见到以先人的言语作为挽诗而悲伤,如“温公挽词”条:“及温公薨,献可之子由庚作挽诗云:‘地下相逢中执法,为言今日再升平。’盖记其先人之言也。读者悲之。”[9]23或因诗歌表述诗人被贬远荒而使人读之感到伤感,如“东坡傲世”条:“韩文公上《佛骨表》,宪宗怒,远谪,行次蓝关,示侄孙湘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又《题临泷寺》云:‘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读之令人悽然伤感。”[9]25瞿佑指出诗人韩愈的不幸遭遇触发了阅读者的伤感情怀。清代诗论家贺赏谈到耿湋的《沙雁篇》中联能引起读者的“凄凉”之感,其《载酒园诗话》云:“耿湋诗善传荒寂之景,写细碎之事,故钟、谭表章皆当,无失入者。至其所遗,如‘暮雪余春冷,寒灯续昼明’,深肖山寺。‘几度曾相梦,何时定得书’,酷似怀人之绪。《沙雁篇》尤有寄托,中联云‘还塞知何日,惊弦乱此心。夜阴前侣还,秋冷后湖深’,读之令人凄凉。”[11]339
总之,无论是称赏,还是叹息,都是鉴赏者阅读诗歌时与作品中的内容、艺术形象及作者产生了共通感,即“共鸣”。可以说,这是“共鸣”的初始阶段。
2.高级层次——涕泪(堕泪)
鉴赏主体在阅读诗歌时,受到诗歌中的艺术形象、作者的情绪感染而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就会出现涕泪的现象,这种心理现象是“共鸣”的高级层次。为何阅读鉴赏主体会被感动而落泪呢?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就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2]667严羽说的“感动激发人意”,就是指诗歌能感动读者,或者说能使读者激动。这种“感动激发”,是鉴赏主体在阅读鉴赏的过程中受诗歌内容的影响而形成的,有时甚至会出现“涕泪”(堕泪)的现象。这种情感效应其实就是“共鸣”。
在诗话中,古代诗论家注意到鉴赏主体出现“涕泪”的心理现象,是因为鉴赏对象的题材、内容、情感与悲伤、凄凉、不幸有关。诗话中的相关记载很多,如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彭民望始见予诗,虽时有赏叹,似未犁然当其意。及失志归湘,得予所寄诗曰:‘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黯然不乐。至‘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乃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谓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论文耳。’”[9]494彭民望见到李东阳所寄的诗时表现出的情感是“潸然泪下”,随后的动作是“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其实这与诗中悲伤、凄凉的情感以及鉴赏者的个人失志有关。又如毛先舒《诗辩坻》卷二:“子建黄初以后,颇搆嫌忌,数遭徙国,故作《吁嗟篇》,又作《怨歌行》,俱极悲怆。谢太傅闻之而泣下沾襟,有以也。”[12]27曹植的《吁嗟篇》以“转蓬”自喻,表达了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和痛苦的心情,《怨歌行》抒发了对曹丕迫害自己的悲愤之情。谢安被这两篇作品的“悲怆”情调感染而“泣下沾襟”。诗论家毛先舒在此评价为“有以也”,已经意识到谢安流泪的原因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有的诗论家注意到作品柔缓的情调也能引起人们落泪,如清代赵执信《谈龙录》第二十四条云:“然歌行杂言中,优柔舒缓之调,读之可歌可泣,感人弥深。如白氏及张、王乐府具在也。”[8]315
(三)产生“共鸣”的原因
古代诗论家注意到诗歌作品表达的强烈悲愤情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如明代都穆《南濠诗话》云:“元杜清碧本集亡宋节士之诗,为《谷音》二卷,惜世罕传。予近得其本,如程自脩《痛哭》云:‘匆匆古今成传舍,人生有情泪如把。乾坤误落腐儒手,但遣空言当汗马。’……柯茂谦《鲁港》云:‘可惜使船如使马,不闻声鼓但声金。’皆悲愤激烈,读之可为流涕。”[9]513–514又如江盈科《雪涛诗评》云:“唐人题沙场诗,愈思愈深,愈形容愈凄惨。其初但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已自可悲。至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则愈悲矣,然其情犹显。若晚唐诗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则悲惨之甚,令人一字一泪,几不能读。”[13]2754实际上,由于人们对悲苦、伤痛等情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审美感受,换而言之,鉴赏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人性具有共同点,因此,描写悲苦、伤痛等题材的作品往往更能拨动读者的心弦,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如果作品叙写的内容、表达的情感是矫揉造作的,鉴赏者不可能被打动,更不可能产生“涕泪”般的强烈情感。古代诗论家注意到作品只有表达真实的情感才能拨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弦,如明代江盈科《雪涛小书诗评》云:“李陵《答苏武书》,情真语真,悲壮激悲,千古而下,令人一读一泪。”[13]2769李陵在《答苏武书》中,讲述了自己迫不得已投降匈奴,全家因而受到牵连被诛灭,并通过与苏武持节归国的对比,抒发了自己身处异域、怀念故土的强烈情感。在江盈科看来,《答苏武书》所述的一切都“情真语真,悲壮激怨”,千古而下的读者都会产生“一读一泪”的强烈的艺术效果。明代茅一相《欣赏诗法》云:“《答卢中郎》五言,磊块一时,涕泪千古。”[7]2126《答卢中郎》即《答卢谌》,是刘琨的一首五言诗,被清人沈德潜收录在《古诗源》中,同录的还有刘琨的《重赠卢谌》《扶风歌》,这三首五言诗,皆“以慷慨激越之声,抒感怀浩宕之情”。茅一相认为,《答卢中郎》抒写诗人一时心中的郁结,却能使千古以来的读者感动流泪。再如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云:“皇甫子安之东览,古《选》颇胜;子循之禅棲,近体为佳。子安卒,蔡子木以诗哭之云:‘五字沉吟诗品绝,一官憔悴世途难。’可谓实录。蔡每对余读,辄哽咽泪。”[7]1967蔡子木写诗哀悼皇甫子安,其中的诗句是逝者生平的事实,作为阅读者的蔡子木“每对余读,辄哽咽泪”,表现出强烈的情感。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诗论家还提及了阅读某些文学作品时,鉴赏主体需要长久或多次阅读体会,才能更好理解作品,达到共鸣的状态。如针对楚辞,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拟《骚》赋,勿令不读书人便竟。《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歔欷。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7]1887这段话被茅一相《欣赏诗法》所引,文字略有不同[7]2143。王世贞指出阅读《离骚》,要反复多次仔细体会,才能感动流泪。又如郝敬《艺圃伧谈》卷二云:“初学读《楚辞》不知味,只缘意思躁率。凡诗赋须优游讽味,始能动人,泛滥涉猎,不领其情兴,犹之文字而已。读《楚辞》,须舂容三复,乃得其沉痛悲婉之致。”[13]2894在此,郝敬指出,阅读《楚辞》,要多次反复玩味,才能达到“沉痛悲婉”的效果。关于对诗歌的反复吟咏,其实前人也说过,如《梁书·何逊传》:“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14]南朝沈约道出了反复阅读何逊的诗歌,表明对何逊诗歌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严羽也重视诗歌的情感共鸣效应,要求读者长时间阅读作品,了解诗歌的真味。《沧浪诗话·诗评》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如戞釜撞甕耳。”[11]622一般来说,读者在阅读、鉴赏作品之后,其心情不可戛然而止,“还会有一个持续的玩味过程。这一过程也许会持续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是醒时还是梦中,留在我们脑中的印象羁留不去,想摆脱也摆不掉。只觉得作品那动人的艺术形象时时在眼前浮现,那深刻的哲理、旨趣和醇美的情味似乎含藏不尽,迫使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咀嚼品尝,欲罢不能。当然,玩味这一状态不是直到最后才出现的,在整个阅读鉴赏过程中都间或有之,不过程度不同而已”[1]471。读者在阅读欣赏时出现“涕洟满襟”的情感现象,其实就是读者与作品、作者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南宋朱熹也提及反复阅读的重要性,明人释怀悦在《诗家一指》中转引了他的观点:“晦庵论诗,所谓读诗须沉潜,讽咏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须是先将那诗来吟咏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看了注,又吟咏三四十遍,便意思自然融液浃洽,方有是处。诗全在讽咏之功。”[9]117可以说,明、清诗论家承接了前人论诗反复吟咏的真知灼见。除了楚辞外,明、清诗论家还针对其他作品谈到多次阅读品味,能够引起阅读者的情感变化,如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马柳泉《卖子叹》曰:‘贫家有子贫亦娇,骨肉恩重那能抛?饥寒生死不相保,割肠卖儿为奴曹。此时一别何时见?遍抚儿身砥(应为:舐)儿面:有命丰年来赎儿,无命九泉抱长怨。嘱儿“切莫忧爷娘,忧思成病谁汝将?”抱头顿足哭声绝,悲风飒飒天茫茫。’此作一读则改容,再读则下泪,三读则断肠矣。”[15]谢榛指出,每次阅读鉴赏明人马柳泉的《卖子叹》,能够带来鉴赏主体的情感变化。清代乔亿《剑溪说诗》卷上云:“《古诗十九首》最近《国风》、《小雅》,读之久,令人感叹流连,泣下沾衣。”[12]1075乔亿认为,长久阅读鉴赏能使人达到“感叹流连,泣下沾衣”的强烈“共鸣”效果。
三
“共鸣”资源在古代诗话中大量出现,这是不应被忽视的一种现象。虽然“共鸣”论在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中都存在,但是中国古代诗话中的“共鸣”资源与西方文论中的“共鸣”论却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正如邓新华概括说:“中西文论存在方式上的差异:西方文论具有较强的理论分析,中国文论则显示出感性经验的特征。”[16]因此,中国古代诗话中的“共鸣”论的诗学特征体现如下两方面:
其一,形象性。西方文论中,涉及“共鸣”的表述并不使用形象化的语言,而是使用抽象化的词语。如弗洛伊德说:“如果《俄狄浦斯王》感动一位现代观众不亚于感动当时的一位希腊观众,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样:它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题材的特性。在我们内心一定有某种能引起震动的东西,与《俄狄浦斯王》中的命运——那使人确信的力量,是一拍即合的……实际上,一个这类的因素包含在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中:他的命运打动了我们,只是由于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命运。”[17]弗洛伊德说的“感动”“震动”“打动”“一拍即合”等抽象化的词语,其实就是“共鸣”。另外,从上文所引黑格尔关于“情致”和鲁道夫·阿恩海姆关于欣赏建筑艺术的话语看,西方学者在表述“共鸣”时,不做具体形象化的描述,而仅仅用词语做抽象概括的表述。然而,在中国古代诗话中,涉及“共鸣”的论述大多是以直观的方式出现,也就是通过具体的叙述,以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将人内在的强烈心理活动外化显现,从而使读者获得具体的感性印象。如陆深《俨山诗话》云:“尝闻故老云:会稽杨维桢廉夫以诗豪东南,赋《白燕》,其警句云:‘珠帘十二中间卷,玉剪一双高下飞。’时海叟在座,意若不满,遂赋一首云:‘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浸衣。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廉夫击节叹赏,遂废己作。手书数纸,尽散座客,一时声名振起,人称为‘袁白燕’。”[9]711这就是以具体叙述的方式来说明“共鸣”现象。袁海燕所赋的一首七言诗受到了杨维桢的赞赏,“击节叹赏”就是鉴赏主体内在强烈的心理活动的外化表现,其形象性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情感性。西方文论重论辩,由于使用抽象的语言,“共鸣”论不明显带有情感性。相比而言,中国古代诗话是独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其理论、范畴等均与西方文论具有很大差异。在中国古代诗话中,“共鸣”论大多是通过具体而形象的语言描述来呈现的,其情感性的呈现是非常明显的。从“共鸣”的一般层次来说,称赏(叹赏)与叹息(太息)都能表现欣赏主体的情感,如《莲坡诗话》云:“曾有僧假余诗谒王阮亭先生,中有‘乱松残雪寺,孤磬夕阳山’句,先生叹赏不已。”[8]488又如上文引王士祯《居易录》中的一段话语“予每读之,辄为太息”。无论是“叹赏”,还是“太息”,都是鉴赏主体内在情感外现的表达,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从“共鸣”的较高层次来说,“涕泪(堕泪)”是鉴赏者比较强烈的情绪反应。一般来说,鉴赏者受到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感染较深,就会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甚至出现涕泪(堕泪)的现象,如薛雪《一瓢诗话》第二二一条:“李山甫《寒食诗》,真画出清明二月天也,就此一斑,可窥全豹。《公子家》二首,尤为绝伦,读之令人想到‘伶伦吹裂孤生竹’、‘侍臣最有相如渴’、‘当关莫报侵晨客’等诗,不觉泪涔涔沾袖矣。”[8]714上述所引描述了阅读促使读者流泪的现象,这是内在强烈情感的鲜明呈现。毫无疑问,中国古代诗话中的“共鸣”论通过使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述,因而具有或深或浅、或重或轻的情感程度。“共鸣”的情感的强烈程度就是涕泪(堕泪)。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尤其是明、清诗话中,存在着大量的“共鸣”资源。这些“共鸣”资源,包含了不同的心理层次:初级层次——称赏与叹息;高级层次——涕泪(堕泪)。从中可见,古代诗论家认识到诗歌(歌曲)的内容、形象与情感感染了鉴赏主体,导致“共鸣”这种强烈的情感效应的产生。因此,探讨“共鸣”的不同心理层次,分析古代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把握,体会古代诗论家对文学接受者的心理现象的高度关注,对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共鸣”现象及其诗学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孙子威.文学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 黄征.易经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5–6.
[3] 陈庆惠.老子庄子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300.
[4] 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8–289.
[5] 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24.
[6]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 周维德.全明诗话:三[M].济南:齐鲁书社,2005.
[8] 王夫之,等.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9] 周维德.全明诗话:一[M].济南:齐鲁书社,2005.
[10]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下册[M].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689.
[11]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富寿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 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3] 周维德.全明诗话:四[M].济南:齐鲁书社,2005.
[14] 姚思廉.梁书: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693.
[15] 周维德.全明诗话:二[M].济南:齐鲁书社,2005:1312.
[16] 邓新华.古代文论的多维透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17]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张唤民,陈伟奇,译.裘小龙,校.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15.
I206.09
A
1006–5261(2020)06–0097–07
2020-04-24
山东大学(威海)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Y2019004)
洪树华(1966―),男,江西上饶人,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