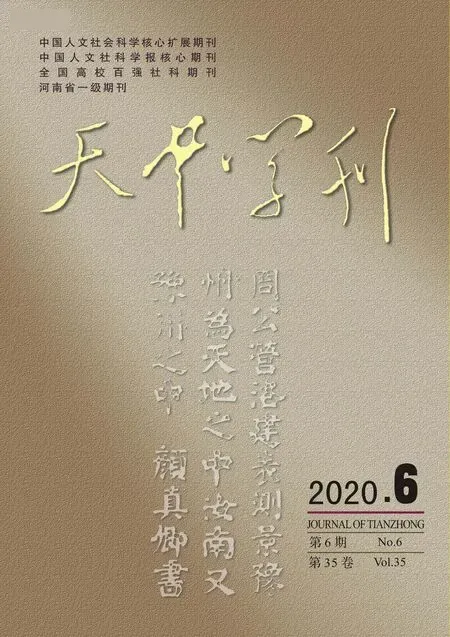战国时代“天下之中”概念的生成
崔建华
战国时代“天下之中”概念的生成
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周人受商代疆域五方、四土认知架构的影响,称洛邑为“土中”。与商代疆域认知架构相比,周代的“天下”概念具有更强的政治色彩。相应地,“天下之中”的概念不仅强调地理中心,还内在地要求地理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一致性。西周、春秋时代均不满足这一要求,不具备形成“天下之中”概念的基本条件。战国时代走向统一,正是在争夺统一天下之主导权的历史进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诞生了。
战国;天下;天下之中;土中;疆域认知
“天下之中”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概念。多年来,学者们围绕这一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探讨,相关成果①对深入理解“天下之中”的概念助益良多,但仍然存在一些有待继续探索的基本问题,如“天下之中”概念何时形成、“天下之中”与“土中”的关系等,皆未得到深入考察。有鉴于此,笔者拟将考察焦点再次锁定于“天下之中”概念,探讨其在先秦时期的生成过程。
一、“天下之中”概念形成于战国晚期
在西汉史家的记录中,“天下之中”是周公在营建东都时对洛邑的定位。《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1]133对于这个记载,李久昌说:“从周公的话中,可以看出,周公是以‘天下’为空间视域来确定都城位置,重点从中央王朝对所辖政治疆域的空间地理控制角度选择适中的地理位置确定统治中心,包含了天下中心观和国都中心观,这就出现了最初的区域中心地思想。”[2]龚胜生也以此记载为依据,认为周公营建洛邑的真正原因“正如周公所一语道破的,无非是因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罢了”[3]。从二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他们都相信,洛邑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话语是出自周公之口的。然而,在现存《尚书·周书》的《召诰》和《洛诰》中并没有这样的话语。与《尚书》的缺失恰相反,不但《史记·周本纪》当中出现了这句话,而且《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也记载刘敬说道:“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1]2716
既然《史记》的两处文字均记载周公已具有洛邑为天下之中的认知,那么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史记》在两处同记一事,我们似乎也应当如以往学者一样,相信《史记》的记载为真,司马迁对周公言语的记录应当有所本。然而,仔细对比不难发现,虽然两处记载的基本意思并无不同,但文字的细微差异处有二:其一,发表观点的主体及方式,由“周公”亲自“曰”,变成了“周公之属”内心“以为”;其二,“四方入贡”变为“诸侯四方纳贡职”,表述方式稍繁复了些。由这两点差异可以感知,对于周公是否真的说过洛邑“为天下之中”的话,在史家心中其实并不十分重要,因此史家行文比较随意,在表述上时而用外化的“曰”,时而用内向的“以为”;时而用单一、确切的“周公”,时而用群体、含混的“周公之属”。
实际上,如果辨析的内容仅止于周公说过什么或没说过什么,那么意义很有限。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应当意识到出自后世史家笔下的周公形象或许是存在问题的,也就是说,对于经由附丽于这一形象的心理、言语、行为描写而推知的周初概念体系,应当心存警惕。具体到“天下之中”概念,由于周公所言或所想是夹杂在一段随意性较强的文字中被表述的,因此,推论周初已经形成“天下之中”的概念,便显得颇为草率。
实际上,《史记》在叙史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因后世观念而影响其行文的现象。比如传世《战国策·赵策一》有“燕尽韩之河南”的记载[4]901,而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献书赵王章”中,这句话写作“燕尽齐之河南”[5]。考虑到燕、韩之间相距遥远,燕国夺得“韩之河南”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可以判定,《战国纵横家书》的“燕尽齐之河南”更接近《战国策》原本。当司马迁截取《战国策》文以编《史记》时,这句话却被改写为“燕尽齐之北地”[1]1817。司马迁为何要将《战国策》的“齐之河南”改为“齐之北地”呢?“可能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西汉人已对原文中的‘齐之河南’感到突兀,因为汉代的‘河南’长久以来都是一个郡的名字,其地域指向十分明确。”[6]因汉代人感到费解而涂改前人的文字遗存,《史记》将“天下之中”的版权冠于周公名下,亦可作如是观,只不过“天下之中”的使用不是因为前人的概念已使汉代人费解,而是因为“天下之中”更贴合汉代社会的语言习惯,更便于汉代人的理解。明乎此,我们对“天下之中”概念集中出现于《史记》也就不难理解了。
《史记》所谓“天下之中”,除了见于《周本纪》及《刘敬叔孙通列传》,还可在《货殖列传》中两见。其一曰:“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其二与范蠡事迹有关,范氏佐勾践灭吴后,“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1]3257,遂于陶“治产积居”[1]3262,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此说又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1]1752。尽管司马迁在叙述先秦历史的过程中屡次提及“天下之中”,但范蠡“以为”陶为“天下之中”,当属史家对前人内心世界的想当然。而“三河在天下之中”则是史家看到“王者所更居”这一历史实情后,对三河地区特殊地位的总结。两者均不能直接作为先秦已有“天下之中”概念的证据,而应将之视为司马迁以汉代习用语描述先秦历史的表现。
当然就文献所见而言,“天下之中”概念亦非创自汉代。《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7]《荀子·大略》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8]可见,战国末年就已出现“天下之中”的概念。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迄于战国末年的更多文献所能见到的不是“天下之中”概念本身,而是各式各样含有“天下之中”色彩的其他词汇。
西周时期有“土中”②。《尚书·周书·召诰》载周公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9]212《逸周书·作雒》也记载:“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10]524西周亦用“中国”之概念。作于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有铭文曰:“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11]这里的“中或”即中国。战国时期,“宅兹中国”的主角变成了韩国。《韩非子·存韩》记载:“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同篇又载荆令尹之言:“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12]18战国时代还有“中央之国”的说法。《韩非子·初见秦》记载:“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民轻而难用也。”[12]8从字面上来说,“中央之国”似乎有“土中”“中国”的味道,但具体所指为赵国,地域指向大不同于二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天下之中身”的提法。《战国策·魏策四》记载,有策士为劝阻秦国攻魏,对秦执政者说:
梁者,山东之要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山东见亡,必恐,恐必大合,山东尚强,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4]1297
所谓“梁王天下之中身也”,即将魏国视为“天下之中身”,与“天下之中”概念仅是一字之差,但毕竟还无法等同,它是一个取譬于蛇的形象比喻。
如果说在《战国策》《韩非子》中我们还只是看到多种在语义上具有“天下之中”味道的词汇,那么《荀子》《吕氏春秋》则直接出现了“天下之中”的概念。考虑到这几种文献的写作年代相距甚近,我们或可推断“天下之中”概念的生成与战国晚期以来大一统局面即将实现的政治大变局存在某种关联。也就是说,描述疆域中心的概念从“土中”向“天下之中”的演变,当与西周初年至战国晚期的政治变迁密切相关。
二、商周革命与“土中”概念的运用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概念”的生成往往是由朦胧认知逐步走向清晰、理性的结果。“天下之中”的概念虽形成于战国晚期,但在此之前人们对“天下之中”的追寻实际上已有长久的历史。先秦“土中”“中国”“中央之国”“天下之中身”等概念的出现,皆是其表征。简单扫视这几个概念,不难发现,对方位意义上“中”的强调是它们的共同点③。除此之外,还有明确提出天子处中理念的内容。《管子·度地》说:“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同书《轻重乙》篇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国之四面,面万有余里,民之入正籍者亦万有余里……天子中立,地方千里。”[13]《孟子·尽心上》说:“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④那么,先秦社会对疆域之“中”的执着究竟有着怎样的政治文化内涵呢?《尚书·周书·召诰》在讲“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之后,紧接着又叙述周公之言:“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9]212对这番话,孔安国做出如是解读:“周公言其为大邑于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为治。为治当慎祀于天地,则其用是土中大致治。是用土中致治,则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获太平之美。”曹魏经学家王肃对周公之言第一句的理解是:“天子设法,其理合于天道,是谓‘配皇天’也。天子将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称周公之言其为大邑于土之中,其当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为治也。”[9]212–213揣摩孔、王之说,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周公之言的核心在于天人关系的建构,即“用是大邑配上天而为治”,“用是土中”方为“慎祀于天地”,“土中致治”方获“天之成命”,“将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诸如此类的说法皆贯穿着一个理念——“土中”是维系上天与人间和谐秩序的关键。
周公以天地秩序为旨归而寻求“土中”,或许是继承了周武王遗志。《逸周书·度邑》记载,商周交替之际,武王已有“定天保,依天室”的设想:
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今,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10]479–481
周武王反复强调“依天室”“无远天室”,反映了天在周人信仰体系中无与伦比的地位。正是基于对天的信仰,周人创造了“天下”的概念。《尚书·周书》多见“天下”之称,如“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等⑤。但是,周人定鼎之初既然要通过确定一个中心点以达成天人秩序的和谐,为何他们的话语体系使用的是“土中”,而非能够充分反映周人政治语言特色的“天下之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关注商周观念继承性的一面。甲骨卜辞中有如下一条: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
除了东西南北四土之外,卜辞中还可见到有关“中商”的内容: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
□巳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
依据上引卜辞文例,胡厚宣断言:“中商即商也。中商而与东南西北并贞,则殷代已有中东南西北五方之观念明矣。”[14]
由史料出发,此论固然成立。然而,我们若细加分辨,就会看到,在同一条卜辞中,东西南北四土与中商不并见,前一条有四土而无中商,后一条有中商却无四土。对此,庞朴分析道:“既然说到‘四方’,即使不提‘中商’或‘商’,实已隐含中方于其中了。当然,如能把这个隐含者表达出来,把‘中’与‘东南西北’并列而为五方,那便意味着达到了自我认识,意味着跳出自我而把我当作对象,与客观对象同等对待,而这是需要时间的。”[15]他认为商部族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尚未达到“跳出自我”的阶段,在商人心目中,中就是商,商天然便居中,商部族实际上的“中土”定位,既无须论证,也不必对居于东西南北四土的人们刻意宣传。这种无须论证、不必宣传的心理,意味着商部族对自身的群体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尚处于混沌状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商部族的个体成员深陷于一个天然居中的群体,在东西南北四土并没有对他们的地位形成压力的情形下,他们便缺少明确主张“中土”地位的动机。
处在商人的认知水平上,“中”是无待他求的,商部族在哪里,哪里便是中,这其实暗含着一个逻辑,即“中”的认定与商部族是否真正处在商王朝控制区的地理中心并无必然的关联,商人所谓“中”,实质上只是政治中心,尽管在五方结构里,中商看起来确实居中。但是,到了周初,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明显的政治之“中”与地理之“中”的两分。周人的龙兴之地在关中,关中自然就是周人的政治中心。不过,长期以来,周人接纳了商朝构建的“中商+四土”的政治地理架构,其自我认同是“西土”。这在《尚书·周书》中是常见的,如《泰誓》中的“西土有众”“西土君子”,《牧誓》中的“以役西土”,《酒诰》中的“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等。先前业已形成的这一自我定位,势必导致克商之初的周人难以拥有自居于中的自信。由于既有的政治中心在疆域版图中偏居一隅,在此情境下,探求“土中”便成为增强自信、弥补缺憾的重要途径。这也就意味着,对作为地理中心的“土中”孜孜以求,实际上是因新的政治中心在既有疆域地理格局中的先天劣势而引发的。
立足于西土而寻觅“土中”,无论是立足点抑或寻觅的对象,总体上均未脱离商人“中商 + 四土”的政治地理思维,只不过是思维主体由商人变换为周人,相关的具体操作也须与周人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对于周人而言,“天下”的概念虽已形成,天下亦已属周,但天下的政治中心与天下的地理中心却并不一致,两个中心相互分离。面对这样的既定现实,提出“天下之中”概念并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关键词,岂非自扬家丑、自寻烦恼?而且,天子明明在西边,怎么能自称在天下之中呢?
看到周天子在确立自身“天下之中”地位时,因面临两个中心相分离的困境,不得不选择“土中”概念⑥。回头再琢磨前引《吕氏春秋》“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以及《荀子》所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作为“天下之中”概念的最早例证,二者皆要求政治中心与地理中心的同一性,至此我们便不难明白这样一个关节,即“天下之中”概念在形成之初便隐含了政治中心与地理中心合一的特定要求。
三、春秋战国时代“天下”之失“中”与再造
有学者指出:“随着灭商战争的胜利,以及在东土封建诸侯的陆续完成,周人所面对的统治范围不再只是西土,眼光所及已是普天之下。”[16]32在此情形下,周人逐步淡化自身的“西土”色彩。西周中期以后,原先局限于周部族内部的“西土”地域认同,变成了天下领域内“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宗法制下的亲缘认同”[16]32。淡化区域色彩,扩大认同范围,周王朝长期以来致力于此。照此说来,周王既称“天子”,那么,对“天下之中”的迷恋必定是周天子的心理常态。因为若能获得“天下之中”的地位,则周部族的地域色彩将不复存在,并且对周政权的认同范围也将达于极致。然而,纵观整个西周时代,周天子一直无法摆脱这样的境地:一方面,洛邑既已营建,土中在焉;另一方面,关中是周人立国之本,作为传统的政治中心,又绝不能放弃⑦。政治中心与地理中心两分的现实困局使“天下之中”概念无法在西周时代流行开来。只不过这样的困局在两周之际终于有所改观。
周平王东迁洛邑,天子所象征的政治中心与地理意义上的“土中”合二为一,这是不是意味着“天下之中”的概念呼之欲出了呢?答案仍是否定的。众所周知,两周之际的都城迁移是在被动状态下发生的,申戎联合犬戎、西戎攻周,关中不保,这才导致平王不得不移都洛邑。迁都的这一具体情境决定着,东迁之后的周天子已很难再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核心地位,与此直接相关,洛邑也不可能在实际上成为天下的政治中心。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一直在下降,直至战国晚期被秦国废黜。伴随着政治一统的逐渐消解,谁才是天下的主宰?春秋争霸、战国兼并的五百多年历史即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天下既然已失去固定的政治中心,那么在此客观形势下,图霸的各个政治体便会有意无意地回避虚位周天子所居的地理中心,而着意强调自身在列国政治交往中的中心地位。此种心理的外在表现当中,策士游说诸侯时的一番说辞堪称典型代表。比如苏秦说秦惠王“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郡,北有代马,此天府也”,说燕文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说赵肃侯“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1]2242–2247。尽管苏秦所言是各国区位特征的实况,但其背后隐藏着一种特定时代的普遍心态,即战国是一个没有固定中心的时代,同时也是人人皆可想象自己为中心的时代。所谓“韩居中国”“赵氏,中央之国也”“梁王天下之中身也”,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
不过,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然有自居于中的普遍心态,但在现实中并没有哪一个曾公然宣称自己是“天下之中”,原因应当就在于这是一个霸权迭兴的时代,就整个华夏版图而言,各诸侯国并没有处在地理上的天下之中,它们即便夺得霸权,也是暂时的,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没有哪个诸侯国具备自称“天下之中”的那份政治自信。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天下分裂、中心缺失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却兴起重塑中心的思潮。《尚书·禹贡》记述禹别九州后,有天下五服的规划:“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9]153。《周礼》亦有多处言及服制。其一是见于《秋官·大行人》的“六服”说:“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9]890–893。其二是见于《夏官·职方氏》的“九服”说:“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9]863其三是见于《夏官·大司马》的“九畿”说,其文字大体同于《职方氏》,只是将其中的多个“服”字改为了“畿”[9]835。诸说尽管在区域划分的数量上有五六九之差,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采用了同心圆或“回”字型天下格局。在这种天下格局里,天子所在的政治中心与天下疆域的地理中心实现了合二为一,只不过这种重合与中心缺失的社会现实恰恰相悖,反映了先秦知识阶层对政治乱局的一种理想型、理论性思考。在他们心目中,天下只能有一个中心。这个理想并非哪个时代某一流派的知识专利,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从诸子的叙事中人们不难读出,在他们的政治观念中,有一个几乎是不能研究的自明前提,那就是‘一统’。无论是道家的‘王者’还是儒家的‘王道’,也不管是墨家的‘上同’还是法家的‘一律’,都殊途同归,概莫能外”,而思想界之所以普遍有“一统”的强烈期待,“当源始于‘三代’有过的‘天下’概念”[17]。
的确,作为一个概念,“天下”指代的是政治体所控制的地域,然而在语词结构上却是以“天”说地、以“天”统地,天然地具有强调“一统”的政治意蕴,这与商代五方并立、无待于天的格局大异其趣⑧。政治共同体的表述方式由商代五方变化为周代的“天下”,应当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即商代方国联盟的国家形态,经过周人的大封同姓,方国更替为封国,血缘纽带的充分利用使得国家形态中的同质性、集权性因素显著增长[18]。那么,当战国以来具有“专制”色彩的集权君主制逐步代替分权意味较重的等级分封制,“天下”概念自然便成为诸侯兼并过程中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
在传统上,秦王朝往往被定性为“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大一统”概念当然具有悠久的历史,说秦王朝用铁血战争践行了“大一统”理念,并无不妥。然而,有学者注意到,《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六《秦始皇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在叙及秦统一时,均书作“初并天下”。论者认为,“并天下”是秦人在描述自身的统一功业时所精心选择的用语,与通常所讲的“大一统”相比,这个描述能更好地传达出秦人之功“超迈前代”的自我评价。换句话说,“‘并天下’而非‘大一统’,更能凸显秦统一的军事成就与帝国建立的政治伟绩”[19]。这是因为先秦“大一统”要旨在于尊王,主张天下应该有一个权力中心。如果仍以“大一统”来描述秦统一,则只是突出了秦始皇接续夏商诸帝、周天子这一权力传承脉络,使天下再一次有了一个政治中心。而秦统一的成就并不止于此,它实际上是再造“一统”。所谓“再造”,即指秦始皇“突破了所谓五帝以来的‘帝-诸侯’政治秩序”,他不再如周天子那样,是“帝-诸侯”这一旧的“天下”政治模式的中心,而是“皇帝-郡县”这一“新的‘天下’政治模式”的中心。他以自己的中心地位促成“君主与地方政治联结层面的‘郡县制’全面彻底推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整个华夏版图内“君主对所统地域较为单一而有效的直接控制”[19]27–36。
秦人对自身统一功业的“并天下”表述,蕴含着政治模式的重大转折。此项认知传达着这样的历史信息:在春秋战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漫长进程中,“天下”已不再是之前的“天下”,它的具体成分由诸侯变成了郡县。当统一的王朝在帝国版图内找寻“天下之中”的时候,其表述方式或许会在不知不觉中体现出郡县体制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所谓“三河在天下之中”,将“天下之中”定义为河南、河东、河内三郡所组成的区域,便是明证。
先秦时代中国中心的称谓由“土中”而演变为“天下之中”,反映了国家组织形式由方国联盟向分封体制的转变。中国中心所指的具体区域由单一的洛邑转变为组合式的三河,这体现了相对松散的国家组织形式向高度集权的郡县体制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中心由城市洛邑而转变为郡级行政区组合而成的三河,这是先秦以来中国核心区由点而面的扩展。中心的扩展意味着区域融合的深化,也预示着中国认同在深度与广度上的上升态势。
① 主要有龚胜生《试论我国“天下之中”的历史源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光明日报》2004年9月21日)、李久昌《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张新斌《“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初论》(《中州学刊》2018年第4期)等。
② 《史记》所谓“四方入贡道里均”“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应当是史家从周人的“土中”一词推衍出来的。
③ 邓国军认为:“终殷周二代,‘中’观念内涵传承者有三:一是‘中央—四方’的统治模式;二是‘居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三是‘中轴对称’的建筑原则。”他所揭“中”观念的三个面向,实际上都是方位意义上的“中”,足见“中”之方位意义的根深蒂固。详见邓国军著《殷周时期“中”观念的生成演变——兼论殷周制度文化的沿革》(《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
④ 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66页。“俾中天下”见《逸周书·作雒》,不过清代治《逸周书》甚勤的朱右曾在引“俾中天下”时写作“以为天下宗”。黄怀信等学者以为“盖所见本异”。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著《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页。也就是说,“俾中天下”未必是《逸周书》原本的文字。黄怀信认为,《作雒》记录的事件“当属可信”,但“文字不甚古”,“其文字,亦必出西周,或据西周旧文加工整理而成,要必不晚于春秋早期”(参见黄怀信著《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55页)。其所谓“文字不甚古”,通过比较《作雒》“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与《尚书·周书·召诰》“自服于土中”的表述,便可真切地感受到。看来,《逸周书·作雒》虽然说的是周初之事,但其中的“中天下”,很可能不是周初的文字。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周初之人已有“天下之中”心理追求的推论。
⑤ 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认为“天下”这一概念“是在战国时代登场的”,理由在于“天下在观念上基于天圆地方的盖天说世界观,即为天穹所覆盖的正方形大地。这一天圆地方的天下观念,缘于前四世纪初发生的宇宙观的转换,自仰视天穹的视角变换为向下俯视的视角”(参见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79页)。但有天文史研究者认为,“盖天思想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穴“南部边缘呈圆形,北部边缘呈方形”,此形制“正是古老的盖天宇宙说的完整体现”,古人对天圆地方的认知来源于“他们对于天地的直接感受,因此这种观念最为质朴,也最根深蒂固”。参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390、463页。笔者以为,立足大地以“仰视天穹”的视觉感受已足以引发天圆地方的盖天之思,日本学者认为天圆地方的认知必赖于“向下俯视的视角”,将盖天说的形成定于战国时代,恐难信从。错误断代所推导出的“天下”概念登场于战国时代,亦不能接受。
⑥ 参见黄晖著《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19―1020页。“土中”概念显然袭自《尚书》,但“土中”具体所指由“雒”改为“三河”则反映了汉代历史背景。
⑦ 参见周振鹤著《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9页。周振鹤指出,“虽然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有时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位置。因为除了理想以外,政治军事经济因素要起着实际的作用。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在这种考量下,首都就可能设在有所偏向的位置而不是地理中心”;“王朝时代称为龙兴之地”的“政治根据地”是“另一个与地理中心有矛盾的因素”,“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
⑧ 参见晁福林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在殷人的意识中,天帝固然神威巨大,但兴云作雨乃天帝自为,世间王者只能通过占卜预知,而无法干涉。因此,殷人格外重视和自己关系直接而密切的祖先神,对天帝则“一毛不拔,不奉献任何祭品”。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李久昌.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J].史学月刊,2007(9):22–29.
[3] 龚胜生.试论我国“天下之中”的历史源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93–97.
[4]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91.
[6] 崔建华.先秦秦汉时期的“河南”地域称谓[J].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3(2):28–39.
[7]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460.
[8]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485.
[9]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4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275.
[12]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051,1443.
[14]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79–280.
[15] 冯建国.庞朴学术思想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18.
[16]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7] 韩东育.法家的发生逻辑与理解方法[J].哲学研究,2009(12):32–40.
[18] 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M].北京:中华书局,2010:127–128.
[19] 孙闻博.“并天下”:秦统一的历史定位与政治表:以上古大一统帝王世系为背景[J].史学月刊,2018(9):27–36.
K231
A
1006–5261(2020)06–0126–08
2020-01-3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ZS031)
崔建华(1981―),男,河南渑池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