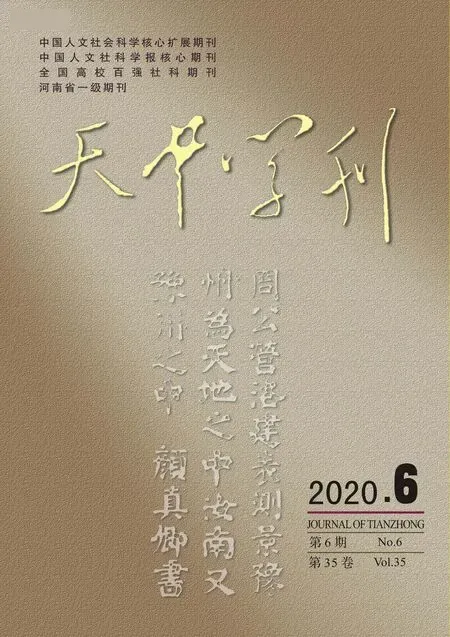《文心雕龙·比兴》篇发微
魏伯河
《文心雕龙·比兴》篇发微
魏伯河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国学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031)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称“比显而兴隐”,只是就其外部表征所做的区别。在《比兴》篇的论述中,存在着“比多而兴少”的轻重失调现象。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兴”重视不够,事实上他更推重的是“兴”而不是“比”,在他的观念中,存在着一个“比小而兴大”的价值判断,而这一判断是就其内在特质和社会功用而言的。至于论述中出现的轻重失调现象,则是由于“兴”在后代用例甚少且论证困难所致。对作为表现手法的“赋、比、兴”,我们今天应该有综合的考量和总体的把握。
《文心雕龙》;比兴;刘勰;童庆炳
“比兴”是中国文论中最古老的话题之一,古往今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至今仍然是研究的热点。刘勰《文心雕龙》专设《比兴》篇,是文论史上“比兴”研究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有承先启后之功。在这篇专论中,刘勰明确提出“比显而兴隐”,童庆炳据此提炼出了“比显兴隐”说,有很详尽的论述[1]。然而,“显”与“隐”是否刘勰判断“比兴”区别的唯一标准呢?其实不然。因为刘勰对“比兴”,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除了“显隐”之别以外,还有“理与情”“小和大”等种种不同的考量。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下面从《比兴》篇的篇章结构入手,就这一问题略做探讨。
一、《比兴》的论述轻重失调
《比兴》全文仅592字(不含标点),在《文心雕龙》中属于短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短文中,就文字篇幅而言,刘勰谈“比”者多,而说“兴”者少。按照通常的段落划分,除第一段(从“诗文宏奥”至“诗人之志有二也”,共98字)讲“比兴”的意义及其关系,属比兴并论外,第二段(从“观夫兴之托喻”至“信旧章矣”,共201字)讲“比、兴”的艺术表现特点,其中论“兴”占三分之一,论“比”则占三分之二;第三段(从“夫比之为义”至“则无所取焉”,共259字)专论“比”的类别及用“比”的基本原则,未正面涉及“兴”。最后到了“赞”(“赞曰”至“如川之涣”,34字)里才又把“比、兴”合起来说。严格讲来,全篇专论“兴”的文字只有下面几句,区区65字而已:
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2]213
这番解说,大抵不出经传范畴。“兴”与“比”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直接的比喻,而是“托喻”,即借他物寄托要表明的意思。“婉而成章”,语出《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婉而成章。”杜预注:“婉,曲也。谓曲屈成辞,有所避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则化用《易·系辞下》语句:“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韩康伯注:“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其所举的两个例子《关雎》和《鸤鸠》也都出自《诗经·国风》。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刘勰的组合是很成功的。他仅撷取五经中三部经典及其传注中的几个词句,就总结了此前关于“兴”的传统观点,抓住并突出了“兴”这种表现形式的主要特征。
但《比兴》篇对“比、兴”的论述如此详略悬殊,轻重失调,看似不无偏枯之病,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文心雕龙》中以并列词素为标题者多有,有关论述虽非完全平分秋色,但如此畸轻畸重、轻重失调者却仅此一例。精通文章写作之道的刘勰,对此何以顾此失彼呢?难道他认为“比”比“兴”更重要,所以才多用笔墨的吗?
二、刘勰实际上更推崇“兴”
笔者认为,尽管刘勰在这篇《比兴》专论中以大量笔墨论“比”,而对“兴”着墨不多,但他对“兴”绝非轻视,恰恰相反,两者之间,他更重视和推崇的其实是“兴”而不是“比”。他对“比”“兴”之间联系与区别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在《比兴》的“赞”中,他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指出二者都有把距离遥远、本不相干的两种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功能。但他对二者的区别更有着清晰的认识,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比”和“兴”的外部表征不同。刘勰云:“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兴”在“诗之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中为毛公(西汉“毛诗”整理者毛亨、毛苌)所“独标”。至于其原因,刘勰认为是由于“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就是说,与“风”的“通”(通于美刺)、“赋”的“同”(同于铺陈)和“比”的“显”(含义显明)相比,“兴”具有“隐”即含义比较隐晦的特点。由于其“明而未融”,如不特别标明,一般读者就会意识不到,所以必须“发注而后见”,尤需加以重视。显然,这只是依据外部表征立论,并非“比兴”之间的全部差异。
其次,“比”和“兴”的应用范围不同。诗文通篇用比者间或有之,如《诗经·魏风·硕鼠》,但更多见于语句和片段。而“兴”呢?尽管关于“兴”的语句未必很多,且其与正文的关系亦若即若离,却大多笼罩全篇,决定着全篇的“基调、氛围、韵味、色泽”[3]。一篇兴体的诗文,如果去掉了起兴的句子,整个作品就不再是兴体,而且艺术效果也会大为失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比”大多应用于赋颂类作品,在汉赋中甚至达到了“比体云构,纷纭杂遝”的程度;而“兴”则更多应用于讽喻类作品。在刘勰看来,《诗经》是比、兴并用的,屈原也能“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如司马迁所说“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4]。汉代以来的辞赋作品,则主要描写都市园林之宏伟壮丽、奇珍异宝之美不胜收,迎合了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心理需求,意在歌功颂德,虽然最后也有几句讽喻的话,但其结果是“劝百讽一”,起不到顺美匡恶的作用,以致“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诠赋》)。这样一来,文学作品“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序》)的功能便丧失了,从而导致“兴义消亡”,完全背离了《诗经》的“旧章”即传统。
再次,“比”和“兴”的生成原理不同。刘勰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指出“比”是“附理”的,主要和“理”有关,“兴”是“起情”的,主要和“情”有关。这一区别很有意义。正因为“比”主要和“理”有关,所以不仅适用于诗歌等文学抒情类作品,也适用于论证说理类的文章;因为“兴”主要和“情”有关,所以只适用于诗歌等文学抒情类作品,而很难应用于其他文章。这一区别还决定了二者在表达上的不同追求:“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2]213就是说,“比”贵在明理,愈直接、明白愈好;而“兴”贵在意会,越婉曲、隐晦越好。
最后,“比”和“兴”的社会功用不同。刘勰通过大量例证指出,汉代赋颂类作品之所以不如《诗经》,即“文谢于周人”的原因是“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他把这种现象称作“习小而弃大”。“习”与“日用乎比”对应,“弃”则与“月忘乎兴”对应。很明显,在刘勰心目中,“比”属于“小”者,而“兴”属于“大”者。对这种现象,刘勰明显表露出不满。“比、兴”何以会有“小、大”之分?所谓“小、大”指的是“比、兴”的哪个方面?显然,主要不是指外在的形体或篇幅的差异,而是就其内在特质和社会功用而言。当然,这里的“小”和“大”,与作为兴体艺术特征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所指兴体作品中的起兴之物与讽喻之义是不同的。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相对于“比”,刘勰对“兴”其实是高度重视并特别推崇的。在他的“比兴”观念中,有一个“比小而兴大”的基本价值判断。与“比显而兴隐”就外部表征立论不同,“比小而兴大”是就二者的内在特质与社会功用而言的。在《比兴》篇的论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刘勰对“比体云构”持批评态度,而对“兴义消亡”则有痛惜之情,其原因即在于此。由此也可看出,刘勰恪守《诗经》传统的意识是何等强烈,他的宗经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论文叙笔”如此,“剖情析采”亦然。笔者认为,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刘勰的“比兴”观念。
三、《比兴》轻重失调的原因
刘勰认为“比小而兴大”,对“兴”高度重视并特别推崇,而在论述的篇幅上却如此轻重失调,似乎不合逻辑。考察这一微妙的现象,可以体察到刘勰写作中的某种难言之隐。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两个因素制约了刘勰的表达:
(一)例证多寡
在存世文献中,“比”的用例俯拾即是,可以信手拈来,而“兴”的例子在《诗经》之后的文人作品中却如凤毛麟角,难得一见,无法像讨论“比”那样,通过分类列举正反例证加以展开。所以,除了《诗经》中的例子之外,刘勰只提到了屈原作品“讽兼比兴”,且并未涉及具体篇目,汉代以后则一无所举。或许有人会说,产生于东汉后期、被后世誉为“古今第一首长诗”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不是兴体吗?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七步诗》等不是“讽兼比兴”的吗?为什么不能作为例证呢?对此,笔者认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虽为兴体,但该诗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5],在徐陵将其收入《玉台新咏》之前,很有可能还未最后定稿,也没有进入文人视野,故而《文心雕龙》全书从未提及,也自然无法作为本篇例证。刘勰对曹植的作品应该十分熟悉,但正因为其“讽兼比兴”,所以拿来单独作为“兴”的例证并不典型,甚至可能引起争议,所以刘勰没有将其揽入,应该是其立论严谨的表现。
有趣的是,童庆炳在《〈文心雕龙〉“比显兴隐”说》中论“兴”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是王昌龄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一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他认为这两首诗的末句都是“兴”。但在笔者看来,两例都很难说是标准的“兴”,而更大可能还是写实,因为“高高秋月照长城”和“唯见长江天际流”均属当时可见之景,不过是景物描写中由小到大、由近及远拓展开去而已,仍属“所咏之辞”,并非与眼前实景若即若离的“他物”。刘勰云“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所以“兴”又称“起兴”“起情”。“兴”的本义,决定了兴句用在篇首或段首才是其常态。童先生自己也承认,这两个例子并“不典型”[1]10。看来,童先生在写作中也曾面临与刘勰相同的难题:典型的“兴”体例证,在《诗经》之后的文人作品中,颇不容易找到。对此,笔者认为,童先生和刘勰也受到了同样的局限。须知,《诗经》中的兴体作品大多出于国风,而国风是搜集保存的各地民间歌谣,后世的民间歌谣还普遍保持了“兴”这一传统。如果不是局限于正统文人的作品,而把眼光放宽到各种民间歌谣如“汉乐府”“信天游”“竹枝词”之类,要选取兴体的例证或许就不至于如此为难了。
(二)论证难易
我们知道,相对于“赋”和“比”而言,“兴”要难把握得多。朱熹论“兴”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6]“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7]2067许多人将他的话视作定论。其实他的解说是比较含混的,因为“先言”的“他物”与“所咏之辞”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前者是怎样“引起”后者的,“虚用”的“两句”是怎样“钓起”下文的,并未能说清。对此,他自己也曾感到困惑。因为他还说过:“诗之兴,全无巴鼻……振录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7]2070“巴”即“把儿”、柄,“鼻”即“鼻儿”,二者均为物体上便于人抓取的部分,俗称“抓手”。“巴鼻”即抓手①。所谓“无巴鼻”者,即没有抓手,不好把握,不易捉摸也。至于“全不取其义”,亦不尽然,两者的意义联系更多介于取与不取、若有若无之间。比朱熹早了600多年的刘勰肯定也曾面临这样的难题。如果尝试还原刘勰的写作过程,可以推测,他并非不想对“兴”展开讨论,可惜由于“兴”不易捉摸,实在不容易措辞,所需例证又不充足,无奈之下,只能点到为止,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指出其表现形式为“托喻”,为“婉而成章”,可以以小见大,如斯而已。至于由此造成的结构失衡,便难以顾及了。对此,后人似不宜苛责。
四、对赋比兴关系的总体认识
众所周知,按照历史上早已流行的说法,在“诗之六义”中,“风、雅、颂”三义指诗歌形式,“赋、比、兴”三义指表现手法。近年亦有将“六义”均认作诗歌体裁者,如郑志强《〈诗经〉兴体诗综考》就认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8]但这一新说尚未得到普遍认可,笔者这里仍按传统说法展开论述。在笔者看来,“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形式,并非指诗歌的形式或体裁②,而是指诗歌类型,其分类的依据是作品的来源和用途,如郑樵《通志序》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9]朱熹也有类似的说法:“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宗庙之诗。”[7]2067然而,从战国后期的屈原、荀况、宋玉开始,特别是到了汉代,本是“六义”之一、作为表现手法的“赋”却由“附庸蔚成大国”,以至于“与诗画境”,成为一种流行的体裁。魏晋之后,赋的题材或写法虽有发展变化,却长期保持着与诗比肩的地位。曹丕《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有《明诗》篇,又有《诠赋》篇,《文选》则将赋体作品列于卷首,均是其明证。
不过,赋成为独立的文章体裁之后,其作为表现手法的功能并未丧失。刘勰《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固然可以认作赋体作品的特点,但也同时是赋这种表现手法的特点。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赋”作为表现手法,就是直陈其事,直抒胸臆,以叙述描写为主,是绝大多数作品中最基本的表现方式。童庆炳说:“我们千万不可把‘赋’看成是‘赋比兴’中似乎是最没有价值的方式。实际上,赋的抒情方式,只要运用得好,也可以写出非常出色的作品。”[1]7这是很有道理的,只不过他把“赋”仅视作一种“抒情方式”,未免有些偏狭,因为“赋”还是一种重要的叙述、描写方式。而“比”和“兴”虽然在后世有时也被称为“体”,如刘勰“比体云构”云云,但并没有能像“赋”那样,获得与其他体裁并列的地位,仍然被作为表现手法、修辞艺术来对待。这也就是刘勰之所以将“赋”作为文类置入“文体论”来加以论述,而将“比、兴”作为写作艺术放在“创作论”来加以研究的原因。直到现在,“比、兴”仍然主要被视为表现方式或修辞艺术,绝非偶然。
怎样把握赋、比、兴三种表现方式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就它们对作品的重要性而言,其实赋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离开了比、兴,赋仍可以成文;而离开了赋,仅靠比、兴则很难成文。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人类在认识事物或审美过程中对普遍存在、须臾难离的对象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现象本来就屡见不鲜,正像许多最基本的东西(例如空气、阳光、水和父母养育之恩等)却往往被人忽略一样,赋作为表现方式在很长时间里不被重视,甚至被认为无甚奥义、不值得研究。至于作为文章体裁的赋,因与议题无关,此处姑且存而不论。
“比、兴”相对于“赋”,从语言修辞的角度来说,则因其相对稀少和更具艺术性显得更高级一些。在赋的基础上增加比、兴,犹如锦上添花,正像人们欣赏一幅锦缎,往往首先被上面的花纹所吸引一样,相对于作为底色的“赋”,“比、兴”的研究更能形成热点。而“比兴”由于显隐、理情、小大等不同,在释读和应用上又有着难易之别。尤其是“兴”,因只能意会而很难言传,其解释历来是一个难题。童庆炳在《〈文心雕龙〉“比显兴隐”说》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他说:
由于诗人的情感是朦胧的,不确定的,没有明确的方向性,不能明确地比喻。诗人只就这种朦胧的、深微的情感,偶然触景而发,这种景可能是他眼前偶然遇见的,也可能是心中突然浮现的。当这种朦胧深微之情和偶然浮现之景,互相触发,互相吸引,于是朦胧的未定型的情,即刻凝结为一种形象,这种情景相触而将情感定型的方式就是“兴”。……兴句的作用不是标明诗歌主旨,也非概念性说明,兴句所关联的只是诗歌的“气氛、情调、韵味、色泽”,重在加强诗歌的诗情画意。[1]8
这样的解读基本是合理的,可以使人对“兴”有比较可靠的把握。因为他是综合了前人经学的、语言学的、文学的各种说法,也比过去各种解说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一种后起的新说。但能否成为定论,尚难断言,因为至今仍有若干不同的解读出现。
“比、兴”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它们在应用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篇兴体的诗文,里面可以包含若干个“比”;而“比”中却很难包含着“兴”(“讽兼比兴”者除外)。例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开头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为起兴,它是笼罩全篇的,故全诗可以确定为兴体,但其中可以有“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等大量比喻。仅就这一点而言,刘勰称“比小而兴大”,也是很有道理的。
总之,作为表现方式的赋、比、兴,就应用范围来说,赋是最基本的,相对来说也是较易掌握的;比的应用也很普遍,掌握起来难度也不大;兴只在特定的文学体裁中应用。由此可知,赋、比、兴三者之间,并非仅是并列关系。就其应用范围或重要性来说,三者之间是由主到次的排列,而从艺术性来说,则呈现为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层级。刘勰《附会》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2]243,青少年作文对表现方式的学习掌握,也宜从最基本的赋即记叙、描写开始。
① 童庆炳将“无巴鼻”解作“全无意义”,明显有误。见《〈文心雕龙〉三十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293页。
② 因为三者在形式或体裁上并无多大区别,若以形式或体裁论,都是以四言为主的诗歌。
[1] 童庆炳.《文心雕龙》“比显兴隐”说[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5–11.
[2] 刘勰.文心雕龙[M].戚良德,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88.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82.
[5] 魏伯河.《孔雀东南飞》文本演变考略[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7(4):52–57.
[6]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1.
[7] 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郑志强.《诗经》兴体诗综考[J].浙江社会科学,2008(10):99–105.
[9] 郑樵.通志二十略[M].影印四库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
On Bi Xing in The Literary Mind
WEI Bohe
(Shando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Foreign Affairs, Jinan 250031, China)
LIU Xie says in his book The Literary Mind (Wen Xin Diao Long) that Bi is apparent and Xing is hidden, which is only the outside differences. In his essay on Bi & Xing, it seems that Bi is mentioned much more than Xing. In fact, he thinks that X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i in terms of social functions. As for the disproportion in the discussion, i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Xing has few cases afterwards to demonstrate. As the wayss of expression, we sh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and overall grasp of Fu, Bi and Xing.
The Literay Mind (Wen Xin Diao Long); Bi & Xing; LIU Xie; TONG Qingbing
I206
A
1006–5261(2020)06–0091–06
2020-04-02
魏伯河(1953―),男,山东宁阳人,教授。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