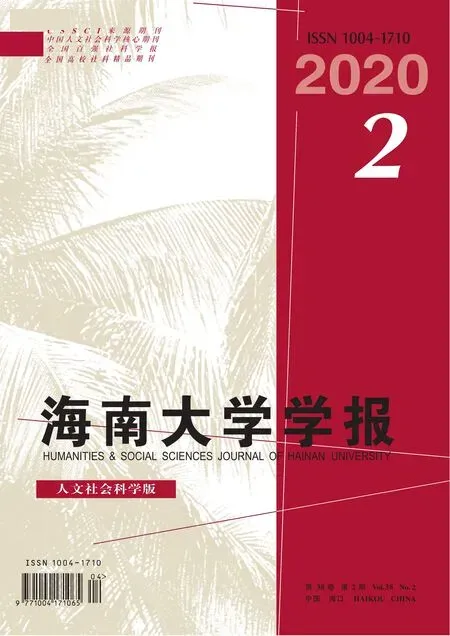“网络祈愿”亚文化的深层透视
罗红杰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2018年网络十大流行语排行榜显示,“锦鲤”名列前茅,备受关注。至今为止,依然盛行于网络空间之中,成为一种独特的网络亚文化景观。“锦鲤”原意指涉好运、幸运,加之现代信息技术的赋权和青年群体对视觉图像的钟爱,逐渐演化成一种独特的青年亚文化现象。锦鲤祈愿衍生出一系列的网络祈愿图景,由传统认知的正式的求神拜佛仪式转向符号化的幸运游戏,隐喻着当代青年群体的情感需求和精神世界。“网络祈愿”亚文化是指以网络祈愿标识物为文化符号、以青年群体为忠实拥趸,并对“祈愿物”诉诸一定的情感依托,以期实现祈福者对于考试、升学、就业等各方面“幸运表达”的文化样态,是一种新兴的小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网络祈愿”亚文化意涵着青年群体对个人压力和身份焦虑的一种另类释放,同时也是对价值虚无和意义追寻的一种真实反映,并具有鲜明的弱抵抗性和风格化的特点。深度剖析“网络祈愿”亚文化的文化风格和意义实践,对科学引领网络祈愿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祈愿”:一种青年亚文化景观
“锦鲤”自古以来就被人们当作“圣物”来崇拜,寓意着美好未来、无限前途、升官发财等幸运意义。“锦鲤”是鲤鱼的一种,“鲤”意指“利”,“鱼”指涉“余”,传统风俗有“年年有余”“鱼跃龙门”之说。“锦鲤”被人们奉为幸运的图腾信仰,用以寄托美好愿景。传统的幸运图腾融合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衍生出以“信小呆”“杨超越”“魏璎珞”等具有“锦鲤”意味的新的网络祈愿图景。网络祈愿文本消解了祭神拜佛的传统仪式,并以符号化的幸运游戏得到不断传播和扩散。锦鲤祈愿是一种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青年亚文化风格。“风格是某种特定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使该种文化区别于任何其他文化。风格是表征一种文化的构成原则”①鲍列夫:《美学》,乔修业,常谢枫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83页。。网络祈愿成为时下一种独特的青年亚文化景观,其文化风格具有独特的生成逻辑和表征意义。
(一)风格生成:网络祈愿的亚文化图腾
风格是凸显与其他文化类型区别和差异的标志,也是其最吸引人的文化符号。网络祈愿作为一种独特的网络亚文化,由“文字图像”构成独特的风格。从其风格来看,重要的不是这些符号,而是这些符号如何被使用。“青年亚文化的风格是一种社会符号式的隐喻,它不是凭空创造或想象出来的,它要借助于已有的物品体系和意义系统,通过对这些物品的挪用和对意义的篡改来实现”①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网络祈愿就是在传统祈愿仪式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拼贴与同构,加之网络信息技术的赋权,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网络祈愿的亚文化风格。
首先,盛行于网络的“祈愿景观”。其一,“信小呆保佑”。2018年9月29日,支付宝赶在国庆节之前发起了一场具有超级大礼的抽奖活动,被选中的幸运儿将得到全球160个品牌赞助的各种优惠和免单福利。该抽奖活动参与人数达300万余人次,中奖率300万分之一。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信小呆”从300万人中脱颖而出,幸运中奖,成为当前最大的“锦鲤”。从此“信小呆”被赋予幸运的象征,随之网络粉丝暴涨将近百万人。网络空间中开始出现转发“信小呆”,下一个“锦鲤”就是你的祈愿文本。其二,“杨超越祈福”。2018年一档选秀娱乐节目《创造101》,让杨超越从众多选手之中脱颖而出,如今成为家喻户晓的流量明星。杨超越一个出身普通、才艺一般、唱歌偶尔跑调的小姑娘通过选秀强势出道,成为青年群体中幸运之子的真实存在。杨超越可谓“一夜成名”,虽然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但是她真实地存在于我们普通人之中,极易引起青年人的认同和共鸣。“杨超越祈福”的祈愿现象成为网络空间中一道亮丽的风格化图景。其三,“魏璎珞守护”。魏璎珞是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的一个角色,底层宫女出身,一路逆袭成为皇权贵族,走向人生巅峰。魏璎珞在剧情中每次遇到艰难困苦之事总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魏璎珞一时成为庇佑、逆袭的祈愿符号,被赋予驱除霉运、转危为安的象征。通过转发魏璎珞等祈福行为,以期消灾避难、祈求平安。通过这种虚拟的仪式来谋求一时心理的安慰。除以上祈愿图景之外,还有在网络空间中通过佛祖、菩萨、财神等传统的佛像神像等形式来祈愿转运。抑或通过四叶草、流行语、彩虹等美好的事物来寄托自身的心愿。在特定的语境下,青年群体特别是在校学生会通过转发、点赞马克思、恩格斯、孔子、牛顿等对每个领域具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图像,以期得到他们的天赋和能力来满足自己的美好愿景。
“网络祈愿”独特的文化风格是通过不断拼贴、同构而逐渐生成的。拼贴是网络祈愿亚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一环。正如菲斯克所说:“拼贴是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者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②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网络祈愿把传统习俗中表征幸运符号的神佛、圣物、自然物等进行重新的意义排序和语境更新,以此来产生新的象征意义。在校青年群体每逢考试就会转发“考试锦鲤”“佛光普照”等,这就是通过拼贴的方式赋予“锦鲤”“佛光”新的意义,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保佑自己顺利通过考试。不同的语境和场景挪用不同的文化符号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象征。另外,拼贴还赋予网络祈愿以抵抗的力量。青年群体之所以热衷于网络祈愿,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景,希望能够实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身存在的压力和焦虑,表达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抗,希望借助超自然的力量解决自身的困境。
“同构”(homology,也译作“异质同形”)即“在群体价值和社会风格之间存在着象征性的相符一致”③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第121页。。同构就是某种结构的复制与再现。网络祈愿就是传统求神拜佛仪式的网络复制和翻版。网络祈愿亚文化内含的青年群体的核心关切、符号形象、群体心理构成了一种“同构性”。在这种网络亚文化风格中保持和反映了祈愿的形象、青年的心理,也是这些相似“碎片”被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文化风格。“四叶草”“佛像”等祈愿景观契合了青年群体的某种价值诉求和生活方式,这种风格与主体之间存在着象征性的吻合。“杨超越”“信小呆”等符号形象与传统神佛、圣物“异质同形”,也存在着某种结构上的复制和翻版。
(二)意义实践:网络祈愿的“异化”与收编
传统神圣、庄严的祈愿仪式逐渐转向具有符号化的日常游戏。网络图像化时代,青年群体把传统意义上的祈愿行为移植、挪用到网络空间之上,形成了符号化、图像化的祈愿文本,并通过戏谑性、娱乐化的方式出场和扩散。这种符号化的幸运游戏弱化了青年亚文化抵抗的意义,消解了传统神圣化的祈愿仪式,呈现出一定的“异化”之态。最终,“网络祈愿”亚文化难以逃脱被收编的命运。
1.祈愿文本:符号的狂欢
庵上湖村,七百多口人,八百多亩地,原是一个典型的无资源、无产业、无区位优势的“三无村”。如今,庵上湖村产业兴旺,村民人均年收入逾3万元,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山东省旅游特色村、山东省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农业旅游示范点、山东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等称号。
网络祈愿文化景观的出现并受青年群体的热捧,与网络信息技术和“图像化时代”密切相关。祈愿行为契合青年群体寻求释放压力、情感寄托的精神需求,加之网络技术赋权与青年群体对视觉图像的崇拜和狂欢,以“锦鲤祈愿”为代表的网络祈愿景观盛行于世。网络祈愿景观中的祈愿文本以“语言图像”的形式完成。文字符号用来表征青年群体现实生活中直观的美好期望和愿景;图像符号就是祈愿者挪用各种具有幸运意味的“锦鲤图像”(信小呆、杨超越、魏璎珞等);“语言图像”的符号就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祈愿文本,象征着青年群体的文化人格。
图像化的祈愿文本增添了趣味性和娱乐性,使原本庄严、神圣的祈愿仪式变得生动活泼,甚至被不断地篡改、拼贴形成各式各样的符号集合体。“网络锦鲤”被赋予成超自然能力的幸运物,通过各种赋意、改写,在网络空间中被肆意地转发、把玩。“在图像永不停歇的传播中,速度取代了深思,分心取代了专注,情感模糊了意义,一瞥取代了凝视,重复取代了原始(图像),公共屏幕取代了公共领域。”①郭小安,杨邵婷《: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第70页。网络祈愿逐渐成为一种日常化的游戏、符号化的狂欢。随着祈愿符号沦落为日常游戏时,它蕴含的抵抗意味也大大弱化了。
2.日常游戏:仪式的消解
“冒渎不敬,是降低格调的狂欢式体系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模拟、讽刺。”②北岗城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传统祈愿实践是一种神圣、严肃的宗教仪式,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风习俗。传统祈愿仪式有着正式正规的流程和规格,以彰显圣物的权威及祈愿者的虔诚。祈愿者以仰视的姿态供奉圣灵,并通过舞龙狮、烧头香、迎财神等方式企图获取神灵的关照。日常祈愿仪式还着重强调祈愿者“主体在场”,必须在特定的空间,构建“人神共在”的关系,祈愿者顶礼膜拜、心怀虔诚之心接受神灵赐福。
以“锦鲤祈愿”为代表的网络祈愿消解了传统祈愿仪式的神圣感,并逐渐演化成随手转发的日常游戏。首先,网络祈愿打破了日常祈愿仪式的时空界限,不再局限于顶礼膜拜的隆重场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祈愿活动的神圣感和仪式感;其次,网络祈愿仅保留了日常祈愿仪式的信仰符号,抹去了传统宗教的“规训与戒条”。在网络空间中人人即可参与、随手就可转发完成祈愿动作,无需“主体在场”,也不用朝圣叩拜、供奉香火。传统祈愿仪式被不断消解,网络祈愿被赋予“神圣、幸运”的意义被当代青年群体进行消费和娱乐。除此之外,网络祈愿逐渐被商业市场收编,赋予祈愿符号商品特性。网络中衍生出各种祈愿抽奖活动,“一些转发祈愿抽奖活动,已逐渐演变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的象征符号”③蒋建国,杨盼盼《:网络祈愿:幸运游戏、精神走私与认同困境》,《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第73页。。
3.收编方式:常规的宿命
解码网络祈愿亚文化的风格,深刻体悟网络祈愿所表征的意义,它隐藏着对现实困境和“主流霸权”温柔的抵抗。青年群体试图通过网络祈愿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同时也积极寻求一种认同、存在的意义。只不过这种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象的、没有意义的,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种意义上的抵抗难以摆脱失败的宿命,最终滑入被某种方式收编的窠臼。
二、精神症候:“网络祈愿”下的精神异化之域
青年亚文化现象是了解青年群体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观景窗⑤李伟《: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亚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基于社会心态的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9期,第107页。。网络祈愿折射出当代青年群体身份焦虑和理性袪魅的精神之域。青年群体通过网络祈愿这种方式缓解自身的精神焦虑以及寻求一种意义支持。在这种自我麻痹的符号游戏中凸显出青年群体价值的虚无和理性的袪魅。
(一)情感需求与身份焦虑
“我焦虑,我祈愿”是典型的网络祈愿的亚文化风格。网络祈愿的动作满足青年群体情感需求的同时,也彰显出青年群体当前身份焦虑的精神现状。网络祈愿之所以能够成为风行一时的亚文化景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网络祈愿契合了青年群体共同的情感需要和身份认同。尽管不同的青年群体面临不同的现实窘境,但是他们所企及达到的初衷和愿景都基本相同,大致关涉生活、学习、工作等诸多方面。青年群体通过网络祈愿来满足情感上的某种需求,缓解生活中矛盾、焦虑的情绪和心态。“转发此条锦鲤,你将收获一筐好运”“转发杨超越,你将高分通过四六级考试”等,形成了网络祈愿标示性的风格,青年群体通过这种网络祈愿动作获取积极的心理暗示与情感的慰藉。他们本身也清楚这种方式并不能实际性地解决现实的问题,只是渴望从未知的超能力中寻求意义的支持。网络祈愿试图营造出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在这种理想世界中自己被赋予“幸运之子”的能力,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渴望完成的心愿,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这就契合了青年群体的情感需求,为其提供了一个暂时逃避现实、憧憬理想实现的渠道。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地位的担忧……现今,身份的焦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要想觉得自己不是个‘失败者’,我们必须期望更多。”①阿兰·波特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当代青年群体存在着普遍的身份焦虑。身份焦虑呈现出一种扩散的状态,普遍蔓延,同时使人产生出一种焦躁与不安。当代青年群体面临着现实巨大的压力,在校学生考试、升学、就业;在职青年加班、升职;社会青年结婚、生子等一系列的压力,他们惧怕失败的苦楚、竞争的压力、愿景不能实现的痛苦,焦虑与不安相伴而生。随之“我焦虑、我祈愿”就应然而生。这种焦虑体现出青年群体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质疑与否定,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不如通过网络祈愿,渴求能像“杨超越”“信小呆”一样轻而易举实现梦想。他们锲而不舍地转发“锦鲤图腾”,特别是在某种特定的时刻,如考试来临之前、升学之际、升职之时,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通过这种网络仪式祈求从“他者”身上汲取神力,强化对结局的掌控能力。也是通过这种网络祈愿的方式转移自身的焦虑与不安,试图想象性地抵制外部风险、制造美好结局。
(二)价值虚无与理性祛魅
“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他根本的存在。”②罗洛·梅:《焦虑的意义》,朱侃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青年群体通过网络祈愿的动作来遮蔽内心的焦虑,更是价值虚无的体现。他们不清楚自己的价值目标是什么、真实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怎样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只能通过想象性的网络祈愿逃避现实。网络祈愿还折射出青年群体信仰危机和理性袪魅的精神之域,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他者”的关照和青睐,自己的精神家园逐渐坍塌、理性认知日益萎靡。
价值虚无是精神危机的突出展现。“得以躲避那些长久以来困扰自己的危险。最后,人们无法形成或保持对自身正直品行的信任。”③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青年群体通过网络祈愿试图想象性地解决问题,长期以往会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怪圈,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精神危机。当青年群体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习得性无助感”,这种无助感会迫使他们求助于“幸运锦鲤”等符号圣物来缓解压力、调节心理平衡。自身内在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不足以填补他们内心的空虚、排解身份的焦虑。“杨超越”“信小呆”等网络幸运符号超越了他们的价值信念,从中获取想象中的力量。“于是人便焦灼地从所有这些具体的内容中抽身而去,转而寻求一种最终的意义,这才发现从精神生活的特殊内容中取消意义的,正是精神中心的丧失。”④何光沪:《蒂里希选集》(上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页。内心构筑的价值体系逐步沦落成为虚拟符号的附庸。
网络祈愿隐喻着青年群体理性袪魅的精神之域。这场盛行于网络的祈愿狂欢,一方面助长了青年人懒惰之风,另一方面也消解了青年群体的理性认知。现实的窘境和矛盾下,青年群体往往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积极寻求外部的力量,通过网络祈愿的方式渴望谋求理想的结局。此时青年人的理性屈服于符号神性,理性认知在逐渐丧失。“我转发、我幸运”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方式,更是带有唯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大多数祈愿者通过网络祈愿都期望天降大运、不劳而获,侥幸的心理压制了内心的理性,这也使得青年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日益萎缩。风格化的网络祈愿景观是青年“独白式狂欢”的产物,是没有意义的建构物。美好生活不是靠祈愿仪式赋予能量所得,而是需要青年自身努力奋斗才能实现。
三、社会动因与文化心理:外在性社会压力与内生性文化心态
青年亚文化既是了解青年群体精神之域的观景窗,也是透视社会现实和文化心理的仪表器。通过网络祈愿亚文化现象隐喻的意义表达和情感体验,我们能够深层透视青年群体面临的外在性社会压力和潜藏的内生性文化心态。
(一)外在性社会压力
“亚文化是人们试图解决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矛盾产生的,这些矛盾是人们共同经历的,能导致一个集体认同形式。”①迈克尔·布雷克:《越轨青年文化比较》,岳西,张谦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网络祈愿亚文化是青年群体面临社会矛盾和社会压力展现出的一种表达动作和价值判断。当代青年群体通过转发、点赞、编辑“锦鲤”“信小呆”等虚拟幸运符号以期缓解自身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等外在性社会压力。
其一,生活压力。一方面社会转型压力增大、社会结构优化升级、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青年群体的生活压力随之增大;另一方面青年群体生活经验不足、经济能力较弱,他们可能要面临结婚、生子以及赡养父母的生活状况。在社会大环境和自身生活的压力加持下以及网络信息技术方便、快捷、碎片化的特性赋权,青年群体试图通过“网络祈愿一线牵”来谋求幸福婚姻,通过“网络拜佛祈子求女”来保佑多子多福等。青年群体通过这些网络祈愿的方式想象性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尝试性地缓解自身面临的生活压力。
其二,学习压力。在校青年学生是网络祈愿亚文化景观生成的主体力量,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青年学生也面临着一定的学习压力。他们在校期间要面临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四六级考试,还有考研、考博的升学考试等,这些考试以及日常的专业课学习给予青年学生巨大的学习压力。每当考试来临抑或考试成绩即将公布时,“压力”和“焦虑”集聚成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本时,青年学生就会通过“临时抱佛脚”“转发四叶草”等网络祈愿的形式祈求“他者”保佑自己顺利通过,取得良好成绩。
其三,工作压力。工作压力是当代青年群体产生身份焦虑和精神异化的重要因素。一些青年人离开学校步入职场,突然的身份转换、人际关系的处理、工作负荷的加大等造成青年群体压力剧增。青年群体通过网络祈愿的方式谋求“摆脱困境的可能性方案”,他们在网络上通过“转发杨超越,今年升职有望”“点赞魏璎珞、工作顺利、事事顺心”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纾解内心的压力。网络祈愿成为青年群体符号化的“心灵鸡汤”和戏谑性的日常游戏,他们不断地复制、转发,制造出一种群体式的“喜感”,来逃避现实的困境和工作的压力。
(二)内生性文化心态
文化心态是社会多种面相的文化心理表征,也是青年群体内心最敏感部分的真实显现。而青年亚文化是展现青年群体文化心态的透视镜和观景窗。通过网络祈愿亚文化景观能直观感受到青年群体内生性文化心态的弥散和情绪的意义表达。网络祈愿潜藏着典型的犬儒主义心态和泛娱乐化心态。
其一,犬儒主义心态。犬儒主义心态是人们面对困境和压力时所呈现出来的心理表征。“有意识虚幻”和“想象性解决”是犬儒主义心态突出的表现。青年群体热衷于网络祈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够通过各种“锦鲤祈愿”有意识地虚幻现实生活、逃避压力;想象性地解决问题、纾解焦虑。首先,有意识地虚幻现实生活,使自己沉浸在异托邦的世界里。当青年群体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时,他们试图通过网络赋予的虚拟空间加之祈愿仪式加持的神灵护佑,青年们乐此不疲地沉浸在福柯所描绘的“异托邦”的世界里。其次,想象性地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困境,以缓解内心的压力和焦虑。网络祈愿图景中,无论是“杨超越”“信小呆”,还是一些圣物、佛像,它们都具有超越一般意义上具体的人的能力。青年群体试图通过它们超自然的能力来化解自身遇到的现实困境,想象性地解决问题、缓解心理压力。无论是“有意识虚幻”还是“想象性解决”都折射出青年群体的犬儒主义心态。
其二,泛娱乐化心态。泛娱乐主义心态是网络信息技术耦合青年娱乐需求而呈现的一种心理状态。网络祈愿的文化图景逐渐消解传统祈愿仪式的功能,逐步演化成一种符号化的日常游戏。网络祈愿亚文化的生成逻辑展现出青年娱乐方式的更新和精神需求的泛化,青年群体通过疯狂转发、点赞符号化的祈愿图景来满足自己的某种精神需求。集体式的符号狂欢是泛娱乐化心态的主要表征。网络祈愿在网络空间中盛行一时,受到青年群体的喜爱和追捧,并逐步演化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娱乐游戏。青年群体从“我焦虑、我祈愿”的文化心态转向“谁祈愿、谁幸运”的娱乐心态,随手转发、随机点赞“网络祈愿”甚至戏虐性地转发任课老师的照片作为祈愿“圣物”,其目的仅仅是追求所谓的点击率、点赞数和关注度来满足自己一时的娱乐需求。网络祈愿不断地经过改写、同构甚至颠覆带有娱乐、戏谑的游戏风格,这也正契合了青年群体娱乐化的情感需求。
四、恰切之道:“网络祈愿”的正向发展
网络空间是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域,同时也是汇集青年群体价值诉求的聚集地。网络祈愿亚文化就是在网络空间中滋生的一种新兴的青年亚文化景观。网络祈愿亚文化既是青年群体逃避现实困境而不断追寻栖息之地的文化反映,同时也是折射当代青年文化心理的“观景窗”。对待“网络祈愿”的亚文化现象,我们应该以奋斗幸福观引领青年健康向上、努力奋斗的价值观念,积极提升青年精神境界,化解精神异化之域,同时优化文化治理,探索主流文化与网络祈愿亚文化的和谐发展之路。
(一)强化价值引领,以奋斗幸福观培育青年正确的价值观
“网络祈愿”隐喻着当代青年消极的文化心态、异化的价值观念。青年群体在面临生活、学习、工作等困境和压力时,往往试图能够通过各种“锦鲤祈愿”来逃避问题、舒缓压力。他们借助流行的祈愿文本加持想象性的情感愿望来逃避问题,他们乐此不疲地沉浸在虚幻的“异托邦”世界里。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异化的价值观。为此,迫切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用奋斗幸福观破除“不劳而获”“想象性解决”问题的错误理念。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等重要思想,这是新时代的“奋斗幸福观”,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最新表达。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奋斗幸福观”归根结底要落实在青年人那里。青年要树立起“奋斗幸福观”,不能沉迷于“网络祈愿”来面对现实的困境和压力。首先,要把奋斗幸福观内化于心。奋斗是青年最鲜亮的底色。人生长路困境和挫折时常发生,青年要树立起面对挫折和困境的正确价值观,更不能沉陷于“神灵佛像”的唯心主义。一方面,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苗孕穗期”,这就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对其进行积极引领,使其在面对问题和压力时树立正确奋斗观;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服务青年的能力,在青年出现实际困难的时候及时地给予帮助,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青年的氛围,同向同行,群策群力,青年的“奋斗幸福观”就会真正地生根发芽。其次,要把奋斗幸福观外化于行。“网络祈愿”是错误生活观的典型叙事。正确的价值理念重在认同、贵在践行。通过示范引领、实践养成、教育引导把奋斗幸福观融入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促进自我建构,提升青年精神境界化解精神异化之域
网络祈愿亚文化隐喻着当代青年群体身份焦虑、理性袪魅、价值虚无等精神异化的症候。“网络祈愿”现象的生成既源于现实生活的困境和压力,也有青年群体精神走私的因素。诺贝尔奖得主鲁道夫·奥伊肯曾言:“一种精神个性的获得形成一个崇高的目标,只有通过相当大的努力,并且往往要有相当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约束,才能实现。”①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为此,要促进青年群体精神个性的自我建构,不断提升青年自身的精神境界。首先,引导和督促青年群体投入时间和精力,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的充盈不会不学自得,这就需要青年关注价值体验、浸润红色基因、提升精神境界。一方面要加强科学知识的学习。知识的累加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精神发展的过程。知识丰富的人精神世界也会更加充盈、眼界更加广阔。另一方面要在日常生活中提升精神素养。要从身边优秀、成功的人身上汲取营养,养成努力拼搏、不迷信、“不信佛”的精神品格。其次,教育和引导青年充分利用和开发精神资源、培育理性思维。精神资源意指那些以人的知识、情感、观念、信仰、能力、品质以及各种文化等形式存在的精神性因素②廖小琴:《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青年要在日常生活中自主开发和利用这些精神资源,将其吸收转化为自身的精神食粮。自身精神世界的充盈自然会破除身份焦虑的精神异化之域。除此之外,要培育青年的理性思维。青年人是被标注为“叛逆、充满怀疑、富有激情、容易激动”的一代人,他们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网络祈愿”的风行在一定程度上是青年群体无意识跟风从众的结果。为此,我们要注重青年群体理性思维的锻造,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文化资源引导青年理性启蒙、培育青年理性思维。
(三)优化文化治理,探索主流文化与亚文化融合发展之道
“网络祈愿”本质上是一种亚文化景观,既具有微弱的抵抗意义,也具有积极的建构功能。从文化治理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一味地打压和否定网络祈愿亚文化的客观存在,应以差异的视角、包容的态度探索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和谐发展之路。首先,要转换思维:从冲突管理到协调治理。冲突管理思维强调青年亚文化是一种从属文化,是处于文化生态系统末端和权力中心边缘的文化形态,并具有强烈的抵抗性和冲突性,进而以“管控”为最直接和最必要的手段进行收编与治理①平章起,魏晓冉:《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社会冲突、传播及治理》,《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第39页。。冲突管理思维的本质是维护支配文化的根本利益。网络祈愿亚文化的抵抗意义不断式微,认同和建构的力量不断加强。冲突管理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整体性的文化生态,损害青年亚文化的运行机能。我们应转换思维方式,转变视青年亚文化为“麻烦制造者”的观念,转向协调治理的思维模式。协调治理强调协商互动、均衡发展,主张青年亚文化在合理的规制内包容性发展。我们对待网络祈愿亚文化应采取分级治理、分类治理、协商治理、转化治理等方式,促使网络祈愿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和谐共处。其次,要变革范式:从社会本位到关系本位。社会本位的治疗范式是在病症化、问题性的青年亚文化价值预设基础上,以一种狭隘视野对待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引领方式②闫翠娟:《从社会本位的治疗范式到关系本位的建构范式:新时代青年亚文化引领的范式革新》,《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16页。。社会本位的治疗范式延续了伯明翰学派阶级对抗的研究范式,强调社会的主体价值,主张社会利益高于一切,忽视了个体的需求和利益。社会本位的治疗范式在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用在网络祈愿亚文化上显然不合时宜。关系本位的治疗范式是一种调和、中庸的治理方式,既强调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又注重边缘文化的存在价值。对待网络祈愿亚文化,我们应转向关系本位的治疗范式,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重发挥网络祈愿亚文化的建构功能、凝聚功能和映照功能,探索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和谐共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