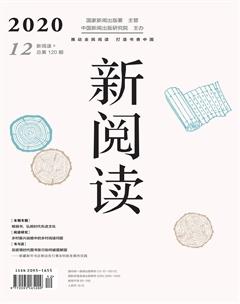数字媒介时代城市阅读空间的融合实践
关灵姝
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阅读从以私人阅读为主的时期走向了如今的公共阅读时期,各种公共阅读文化实践也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层出不穷。在数字媒介时代,城市阅读空间的性质具有了延展性的变化,公共性也越为凸显。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人们自由发表公共意见的一种场所或空间,这个空间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在城市生活中,阅读空间不仅是人们阅读的场所,还是沟通城市的“媒介”。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实现了城市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交织着建筑、街道、空间、地理、信息、历史、文化、集体记忆等多重城市象征网络系统,创造了新型社会交往关系与公共价值”。本文立足于数字媒介的传播特性,探讨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在数字媒介时代有了怎样的新实践。
边界拓展:重塑城市阅读的空间体验
数字媒介时代,新的传播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一方面它们通过技术对场景进行塑造,重构了人们对于空间的感知;另一方面它们“模糊了物理和数字空间之间的传统边界,为公众参与创造了新的时间与空间”,并使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发生重叠。阅读空间在新媒介技术的中介下得到了发展,为城市阅读创造新的可能。
受到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传统的实体书店和图书馆由原来单一的购买、借阅空间,拓展为融合阅读、社交、文化、消费的“第三空间”。欧登伯格将除居住空间和职场空间以外的自由、宽松、便利的空间称为第三空间,这些空间为信息交流和公共交往提供了平台,体现了城市的多样性和活力。建于广州的方所书店是集书店、设计和展览为一体的新型阅读空间,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书店模式,将物感体验与知识阅读相结合,打造了复合的阅读空间。此外,实体书店与图书馆将城市历史文化特色與空间相融合,重构了人与阅读场所之间的连接。作为老北京地标之一的东城区角楼图书馆,将雕梁画栋、朱红色的古式木质装修风格融入整个空间,使整个空间都充满了老北京的历史文化元素。这种新型阅读空间将文化创意与实体空间相融合,通过复合的经营模式拓展了传统书店与图书馆的边界。
在现代互联技术的中介下,实体书店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其实体与虚拟的界限也在逐渐被延伸。2016年9月,我国大型图书电商“当当网”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第一家实体书店梅溪书院在长沙开业。移动知识付费社群樊登读书会为满足会员线下的学习需求,成立了实体的樊登书店,构建了线下阅读场景。此外,实体书店也举办各种主题的读书会和文化沙龙,让公众参与、分享与讨论,将单一的图书阅读空间拓展为知识传播空间。南京先锋书店开展各种主题的分享会、读者见面会,为社会各个阶层、民众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场所,丰富了城市的社群生活;同时建立了线上的读者群,实现了线上数字交往与线下实体场所的结合。新媒介技术的出现,让城市阅读跳出了原有的格局,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得到勾连,书店从消费场所转变为可供阅读、知识交流与精神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间。
交往空间:线上线下融合的社交化阅读实践
在传统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中,公众的阅读行为都是孤立的,缺乏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文化场域。受到数字化生活的影响,阅读空间在实体的基础上叠加了虚拟空间,以阅读为媒介为公众提供了平等对话的文化交往空间,形成社交化阅读的新实践。
新媒体手段的介入,使原本私人的阅读行为向公共领域拓展,孤立的个体得以相遇。新媒体社交平台新世相曾策划了“丢书大作战”活动,将一万本书丢在北上广的地铁、航班、顺风车上,将这些书分享给读者,在阅读结束后,读者可将这些书留在新的地点,让书流动起来。同时,读者也可以将自己的书分享出去,通过书内的二维码可以看到每本书的漂流轨迹和读者留言。这种以书为媒介的阅读分享活动,促进了知识的分享,也为陌生人之间的社交提供了可能。实体书店也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线上线下贯通,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2018年建立的实体书店网易蜗牛图书馆,不仅定期发起文化活动、展览演出、文化沙龙,为读者提供文化交流空间,还依托“网易蜗牛阅读”APP的社交功能,引流读者到线下的实体书店参加活动。
传统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中,公众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缺乏平等的交流空间。而大众媒介和新媒体融合下的“读书会”与“读书社群”,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隐匿了公众的真实身份,使得平等交流得以展开;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参加文化交往活动,形成兴趣、观点相符合的文化共同体,获取了自我身份的认同。网络知识社群“罗辑思维”通过线上线下的交互网络,将不同价值认同的人群进行细分,建立起观点、兴趣、目标较为一致的子社群。读书会成员因某一领域的“兴趣爱好”聚合在一起,这个领域越聚焦,人们对社群与自己身份的认同感越强,而社群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
打破区隔:以阅读空间为媒连接人与城市
城市传播聚焦于“可沟通性”这一核心概念,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而传播则是编织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城市中的实体空间为这种关系传播提供了平台,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实体书店与图书馆作为城市文化空间,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下打破了原有的一些阅读区隔,不论是从地理、时间与群体方面,都为人与城市的“对话”提供了交流交往的平台。
随着城市阅读空间在形式与功能上的转变,各种形式的阅读空间正在渗入城市的大动脉,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而使阅读变得更为便利与自由。如今,微型图书馆、流动书车、便民读书站等社区阅读空间遍布城市。温州市建成开放了几十家城市书房,让公众切身感受到了阅读的便利性。书房内配置自助借阅机、高清投影仪、音响等,旨在打造一个书籍、影音、咖啡共存的多元文化空间,市民也可以在书房中参加读书会、讲座,进行文化知识的交流与分享。移动智能设备也进一步拓展了城市阅读空间,原本固定的借阅时间得到扩展。东莞设置了24小时自助图书馆和图书ATM机,弥补了基层图书馆数量和服务的不足,使图书馆的服务时间、空间得到延伸。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正在成为城市公共文化体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实体书店还是图书馆,都面向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知识的获取与交流。深圳龙城街道五联社区图书馆在农民工活动区域内创办企业图书借阅点,不仅为外来农民工群体提供免费书籍,还在电子阅览室里设置了电视、投影仪,开办专题讲座与各类知识文化活动,不但满足了农民工群体工作之余的精神需求,也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公共阅读空间不仅给不同人群的阅读行为提供了充足的场所,给予他们自由阅读权利以充分的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弱势群体的权利。如合肥市三孝口24小时新华书店,不仅是读者的阅读场所,在深夜时也成为城市书香的风景。
结语
数字媒介时代,阅读空间作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得到进一步拓展。新传播技术的介入,一方面使阅读由私人场景转移到公共空间,其公共性得到进一步扩展,阅读空间也由传统的单一借阅、购买空间,转变为融合阅读、社交、文化的“第三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得到贯通,打造了新的复合空间,由此创造了新的阅读场景与社群连接方式。这种阅读空间性质与功能的拓展,为公众在复合空间中平等、自由地进行文化共享、交流提供了可能性,不仅打破了由于阶级、身份的不同所造成的阅读区隔,还构建了新型的城市共同体,为人与城市的“沟通”创造了新的内涵。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
[2]孙玮,褚传弘.移动阅读:新媒体时代的城市公共文化实践[J].探索与争鸣,2019(3):118-126+144.
[3]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孙玮.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7):5-15+126.
[4]何映霏.社群化阅读视域下读书会转型探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1):9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