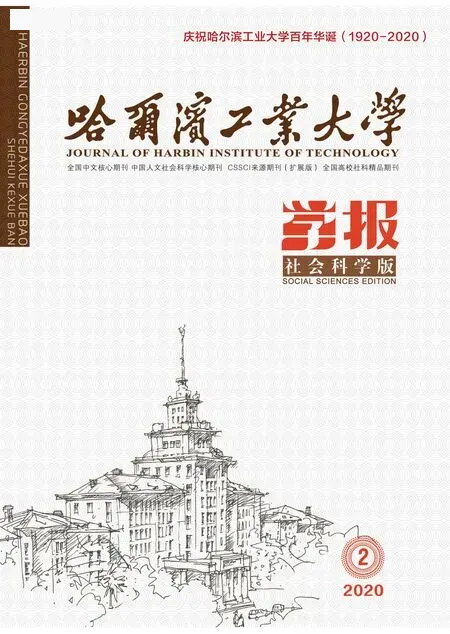论国际传播学的去西方化
——一个对西方化传播观的批判
赖祥蔚
(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中国台北)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更成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在宣传思想工作上的重要理论创新。针对怎么“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已有许多阐述,要致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良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也给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优化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赋予新的使命,向世界说明“中国梦”是惠及各方的发展机遇。
“讲好中国故事”,不只涉及国际传播的工作推展,也牵涉国际传播的学术理论,因为当前的国际传播学具有高度的西方色彩,有重新检视的必要。中共中央2016年12月30日通过《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在这当中,当然就包括了对国际传播学等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构建。
国际传播的滥觞,从中国历史来看,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传说时期;如果从西方当代主权国家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可以从17世纪近代民族国家的登场算起,尤其是1648年签订、奠定民族国家基础的“西发里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国际传播是国际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受到了国际关系现实的诸多影响。早先的国际传播是国际政治中现实权力的反映,国际强权挟其优势国力之助,不免会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将其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世界观向其他区域推广或散播。中国在封建时期的朝贡体系必然有其伴随的旧时代国际传播模式,而当代的现代化理论则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际传播传统上被视为外交的延伸,一个常被引用的定义,就是借助传播科技来进行跨国传播,透过接触其他国家的人民与决策者,希望影响他国的舆情与立场。传统的国际传播是国家对外的单向宣传,是外交政策的工具之一;如果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定,这类宣传被称为“伤害性宣传活动”,包括意图性的错误宣传与选择性的错误宣传,前者是负面资讯或假资讯,后者则是曲解或不平衡的资讯。
国际传播虽然存在已久,不过国际传播学的受重视,迟至20世纪中期才开始。国际通讯社与国际广播是20世纪前期与中期最重要的国际传播方式,过去许多国家的国际新闻超过八成都是倚赖美国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与合众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英国的路透社(Reuters)与法国的法新社(AFP)这四大国际通讯社提供。如今随着新的传播科技一再兴起,情况已有改变。20世纪末,卫星电视与网路电视快速取代传统国际广播的功能,卫星电视一度引领国际传播的新风潮,英国的 BBC、美国的CNN、日本的NHK、中国的央视都发挥了强大的穿透力。卫星电视的角色很快又遇到了网络媒体的挑战,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的界线被打破,也加进了更多非政府的因素,这是国际传播的新局面。
最传统、最简明、最常获得引述的国际传播定义是:跨越国境的传播。然而,网络传播经常穿越国境,传统以国界为分界基础的国际传播现实已经产生重大改变,公民团体与个人都扮演了前所未见的重大角色。例如成立于2006年的非营利组织“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布了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外交、军事等机密文件,立刻就对相关国家的外交作为造成了冲击;2010—2011年发生在北非国家突尼西亚的革命,透过推特等社群媒体发挥了国际传播的影响;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的史诺登(Snowden)在2013年揭露美国国安局以“稜镜计划”(PRISM)进行广泛的秘密电子监听,消息一出立即影响国际外交,更成为当年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三名;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一直盛传有境外势力介入,透过网络传播假讯息、假新闻,影响选举结果,引发全世界高度关注,相关调查与探讨持续许久。
由此可见,国际传播的行为者与实际运作场域,都已经产生了许多巨大变化,国际传播学当然有必要重新检视。现有的国际传播学反映出强烈的美国色彩,欠缺更广阔的国际化以及多元的立场与观点。本研究将针对国际传播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主张国际传播学应该致力于去西方化,进而立足在地化即地方化或本土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学。
二、文献回顾
(一)国际传播学的发展
现代的国际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界,在此之前,第一代研究者包括拉斯威尔(Lasswell)、李普曼(Lippmann)、柏纳斯(Bernays)等人,主要是从宣传面向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本来是政治学者、后来被传播学界奉为开山宗师的拉斯威尔,以其国际宣传研究开启了国际传播学的先河。拉斯威尔(1927)以“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为题出版专著,应该是当代学界针对国际传播的第一本专著。
具有理论意义的现代国际传播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诞生,第二代的国际传播研究者冷纳(Lerner)、宣韦伯(Schramm)等,关注的是冷战期间的宣传,包括国家如何使用其宣传资源,以加强内部共识并且瓦解敌人的战力,同时也开始了理论的建构。
在冷战时期,国际传播学进入了理论建构阶段,现代化理论与创新传播等论述,主宰了其后数十年的国际传播学发展,至今未歇。早先的国际传播学反映出浓烈的美国价值,美国学者冷纳就直言认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以线性的进程去追赶美国的现代化模式。20世纪70年代之后,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依赖理论给国际传播学的内涵带来不少挑战,而英国与美国相继致力于国际的新自由主义,也影响了国际传播学;到了21世纪,网际网路与社群媒体的兴起,更使国际传播出现了全新的面貌。
由回顾来看,国际传播学已经有了可观的进展,不少学者已经试着提出国际传播模式的归纳与分类。有学者根据传播技术进行划分,也有学者从国际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来进行划分。依照科技发展可以把国际传播分成三个不同时期:国际会议时期(1835—1932),电报、电话以及国际广播为此时期的主要工具;国际宣传时期(1933—1969),英国、德国与美国陆续成立了国际宣传部门,透过国际广播等传播方式进行国际宣传;传播新科技时期(1970—),各国纷纷开办国际电视频道。
英国学者斯巴克(Sparks)从国际关系的局势来划分不同时期,他指出:国际传播理念的发展演变有三个关键时期[1]:1947年冷战开始,国际传播论述以发展传播理论为主,为的是借此围堵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结合国际传播与行为主义研究途径,进行公共外交的研究[2];1968年开始的激进主义也使得国际传播与帝国主义及反帝国主义结合;1989年苏联瓦解,使国际传播进入了全球化理论的盛行年代,彷彿意识形态的国际斗争已经终结。
这三个时期的国际传播学特色,可谓发展传播、媒体帝国主义以及全球化理论。这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迄今,就传播媒体全球化对于国际关系影响的解释来看的三大典范(paradigm)。第一个是“传播与国家发展”,第二个是“媒体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第三个是“全球化”。这三个典范大致代表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乐观主义,媒体被看成“神奇的触发器”,可以带动社会发展;第二个阶段是殖民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全球化[3]。上述三个阶段的国际传播学,都反映了强烈的美国色彩与西方利益。这种西方本位的传播学观点,已经开始引起检讨[4]。同时,全球化的进展也激起了非主流的观点,例如从马克思主义来反思,因而产生出依赖理论,依赖理论又可以分成“依赖不发展”与“依赖发展”两种观点。除此之外还有强调全球化之下的在地化[5]。质疑西方本位的论述,已经引发了不少关注,但是还没有撼动国际传播学的主流地位。
有学者不只考量传播技术,还参考实际的行动主体而将国际传播另外分成了三个与前述分界不同的发展时期:国际化(internal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国际化阶段大致对应冷战时期,民族国家为行动主体,正逢东西方对抗、南北球对立,国际传播的技术以中短波广播为主、卫星电视为辅,公民的身份认同为民族国家之公民,此阶段的主要理论特色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全球化阶段处于后冷战时期,在各国解禁的风潮之下,全球企业与全球媒体兴起,扮演了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区域性遭到减弱,公民的身份认同陷入全球与在地的拉扯,此阶段的理论特色是“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跨国化阶段则进入多极化的国际关系格局,网络的高速时代来临,促成网路社会与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得国际传播的行动主体从国家扩散到了社会乃至于个人,公民的身份认同具有创设性与流动性,此阶段的主要理论特色则是“文化混同”(cultural hybridity)。问题是,在美国的强势文化霸权之下,如何透过正确认知以找回认同?葡萄牙学者Santos从认识论出发提出“南方认识论”,倡导“全球认知正义”[6]。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传播学的研究重点除了应该迎向网络所带来的新冲击,更应该对国际传播学的西方化本质进行深层检视。
(二)国际传播学的两种美国传承
国际传播学提供了审视国际传播的视角与理论,当然,任何理论都不免会反映特定的价值与观点。现代化理论等主流国际传播学的诞生,有其源自美国的学术传承。当时美国学术界有两个主要的传播研究学派:一是芝加哥学派,一是哥伦比亚学派。其演变刚好反映了美国当时的社会情境。两个学派关切的核心议题与研究方法颇不相同。芝加哥学派渐渐体认传播对个人的影响力其实非常有局限,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学派却大谈传播可以促进现代化。这两大主要理论尽管共存,深入探讨却会发现两者之间未必相容的现象[7]。
相较于芝加哥学派重视社会诠释,哥伦比亚学派则强调行为科学。前者以人类学研究途径探讨都市变迁与人际沟通,后者则试图在微观层面探讨媒体的短期效果,想探讨媒体如何改变个人或团体的态度与行为,结果却不乐观,大幅修正了过去认为媒体具有明显且立即效果的“魔弹理论”。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代表的麻工学派却以无比的信心断言媒体具有宏观的长期效果,从此开启在国际传播领域引领数十年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是美国政府积极鼓励的产物,哥伦比亚学派发现媒体的效果相当有限,麻省理工学派的政治社会学者却刚好相反,积极主张媒体在促进第三国家能够发挥神奇的效果。冷纳在1958年以“传统社会的消逝”为名出版专著,该书副标题则是“中东的现代化”,这本书被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作,奠定了国际发展传播的主要基线;宣韦伯(即施拉姆)写成专著《大众媒体与国家发展》,一度被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者看成是迈向发展的指南,这本书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意义非凡。与此同时,罗杰斯(Rogers)结合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扩散与爱荷华大学的农业传播扩散之说,在1962年提出“创新传播理论”。这些论述让第三世界误以为简单方案可以解决困难问题[8]1-28。除了前述的主要美国学派之外,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陶(Rostow)在1960年发表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详细描述了从传统到发展之间的五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具体特征,也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论述基础。
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成果,其实与麻省理工学派所倡议现代化理论的假设颇有冲突,前者发现媒体对于受众可以发挥的作用有限,后者却强调媒体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这就显示当代现代化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科学假设或许不无问题。尤有甚者,与现代化理论具有近亲关系的创新传播理论,至今在发展中国家仍然被许多学者奉为圭臬,但是深入检视之后却会发现其研究方法其实颇有问题。
(三)主流国际传播学的反思
由美国主导而发展的国际传播学,一开始就牵涉了冷战冲突,因此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质疑,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混合了南北紧张,这时候出现的依赖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获得启发,把剥削的概念引入国际互动之中,从理论上把现代化变成了剥削化,对于现代化理论形成了全新的挑战,但是美国仍在第三世界传播现代化理论,想要以此来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
由于传播媒体没有发挥预期中的发展功效,传播与国家发展典范不禁陷入了困境。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个替代性的典范出现,亦即媒体帝国主义。学者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由来已久,主要是师承马克思学说。就传播的角色而论,直到美国传播学者席勒(Schiller)在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媒体帝国主义才俨然成为了一家之言。媒体帝国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媒体的所有权、结构或内容,受制于其他国家媒体的利益,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力极不平等。其他用语包括了文化帝国主义(强调文化侵略)或是资讯帝国主义(强调资讯控制),有学者更以电子殖民主义来形容,相较于过去的重商殖民主义,电子殖民主义寻求的是透过受众的耳目来影响其态度、欲望、信念、生活型态或购买形式。媒体帝国主义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这让一些学者不以为然,认为应该改以传媒内容的商业化来分析,尤其是美国式的商业化传媒内容。晚近由于国际媒体之间的交叉控股,因此提及美国传媒帝国主义已经不再适当,而应改称带着浓厚美国口音的跨国公司传媒帝国主义[9]40。西方媒体势力的强大存在,确实让许多非西方国家感到忧心。
不平衡的国际资讯流通是一个事实,也构成了媒体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学者认为,本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除了单纯地加以吸收之外,还有融入与抗拒等策略[10]。
20世纪末期最受关注的国际传播学理论是全球化理论,有学者倡议全球化应该促成“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11],不过在实际上,全球化更多地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展现出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因此在政治经济上催生了全球化媒体霸权的登场;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媒体霸权是以美国为首的英语文化为主,不免引起了其他语言文化的在地化抗衡,例如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在1989年通过“欧洲无国界”诉求,呼吁成员国尽量播放彼此的广播电视节目。这些主张试图对抗美国的压力,以免高举全球化旗帜的国际传播在实际上变成了单向的美国传播。直到最近,欧盟仍然试图透过强调要购买或制作在地节目等政策,来减缓美国影视产业借助OTT TV等网际网路便利而扼杀欧洲的在地影视文化。
关于资讯流通不平衡的问题,许多研究都已经证实了不平衡的存在。尽管若干研究显示,观众喜欢收看自己国家或文化的节目,但是进口节目的现象仍大行其道。其原因除了进口节目的成本低廉,只占自制节目的1/10之外,主要还是自制节目不足。全球资讯的不平衡流通不只存在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阵营,美国则是全世界最大的节目输出国。其中原因除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私有化的传播媒体在市场中比较具有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媒体市场的经济规模可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分别进行了电视节目在国际上的传播分析,两次分析都发现了单向流通与以娱乐节目为主等特征。美国与西欧国家为输出大国,但西欧国家本身又是美国节目的输入国。传播媒体全球化与资讯流通不平衡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价值、尤其是商业化价值对于消费、个体主义、个人选择的强调;第二,公共领域被娱乐取代;第三,保守政治力量的强化,例如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跨国企业,却不利于劳工;第四,地方文化的侵蚀,甚至是各国多元观点的不平衡发展[9]153-155。非美国的欧洲等国家,一方面需要美国传播产业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国传播产业的压迫,这些发展刚好体现了依赖理论的“依赖发展”与“依赖不发展”等辩证关系。
三、国际传播学的更新
21世纪的国际传播在理论与实际上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实务上,网络与社群媒体已经改变了国际传播的运作,各种资讯在网际网路上快速传递,使得国际传播的行为者、传播渠道、受众以及效果,都与过去迥然不同。不只各国元首等重要人物纷纷在社群网路上发表重要宣言,第一时间就可以同步传播到全世界,这就打破了过去国际传播主要都被掌握在重要国际通讯社或是国家广播与电视等媒体的局面,很多国家“借此宣传”其主张,甚至还有越来越多民众也自行扮演起“公民记者”的角色,只要所挖掘出来的报导内容具有足够的感染力,一样可以立刻向全世界广为传播,发挥重大影响力。
面对国际传播的巨变,华人传播学者早有反思,也提出若干学术探讨与具体主张,其中以李金铨教授与赵月枝教授的分析最为深刻,两人不约而同地揭露了国际传播学的西方本质,并且主张应该重新回到在地化,才能以正确的认识论来建构这门社会科学。国际级华人传播学者对于国际传播学必须去西方化所显示出的共识,更可见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目前在中国台北的政治大学担任玉山学者的李金铨教授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且编辑了一本国际传播的理论专著,全面检视国际传播理论与学术典范。这几篇论文的阐述论点以中、英文相互呼应,试图更新国际传播理论。李金铨在2015年以《国际传播的国际化》为名编著的专著,更结合多位青年传播学者的著作,广泛批评传统的美国中心学术传承太过偏颇,扭曲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发展,进而主张国际传播研究必须真正国际化,新的起点应该是“世界主义”的精神,由各国学者各自从其在地的文化出发,据以提出对于国际传播的新诠释与新观点,这样才能为国际传播提供新的研究动力与发展契机[8]1-28。
李金铨首先针对国际传播学的美国化现象进行批判,他直言:既有的国际传播学其实存有内在矛盾与瑕疵,“哥大学派在微观层面寻求媒介的短期效果,也就是媒介能否改变个人或团体的态度与行为。而麻省理工学派却以无比的信心揣测媒介宏观的长期效果”,至于Rogers汇聚哥大的新闻扩散与爱荷华大学的农业传播扩散之说,提出了享誉数十年的“创新传播理论”。李金铨也批评不仅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是一种目的论的循环逻辑论述,先有结论再找证据,而且证据也有瑕疵;此一理论让第三世界精英误以为简单方案将可解决困难问题[5]212-215。
李金铨指出:“如果把美国发展出来的传播学当成科学,则依照此一宇宙论与知识论,世界就变成美国的放大版。”他认为国际传播学存在“内卷化”(involution)的情况,欠缺更宽广的视野。李金铨认为,国际传播学想要跳脱美国的框架,各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们更需要文化自信以及在知识论方面展现自主性,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才能够迈向真正的“国际化”[8]15,至于具体的理论建构途径则是以多元文化世界主义为新起点,建立复杂、多元而整合的架构。就此而论,国际传播应该提倡“以区域为基础的研究,以世界主义不断进行对话,一方面拒绝美国的宇宙观,另一方面也反对谨守狭隘的特定族群观点,因为前者将造成美国化的学术殖民,后者则因为欠缺普遍意义而难以理论化”[12]3-30,具体的研究途径则是应该舍弃极端的实证方法,因为这样的途径忽略了文化性,因此应该以韦伯式的现象学路径为基础,也就是研究者应该从自己的生命世界出发思考国际传播的意义,然后从更大的脉络去重新加以诠释。这就是把主观解释加以客观化,也就是重建国际传播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在2019年荣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获聘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的赵月枝教授就主张,有必要从认识论出发对现代西方霸权知识/权力体系进行颠覆[12]3-30。即使挑战西方主导知识/权力霸权,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地一概排斥“西方”知识,但是必须承认,“美国中心论”在理论层面的影响非常严重[13],她强调如果用本土的案例去证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这依然是“西方理论,本土经验”的套路,在本质上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一定要将文化多样性的想象,跳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框架。
对于国际传播学的重新建构,不只涉及知识论,还与本体论相关。赵月枝教授强调,在认识论上一旦要对西方知识霸权提出挑战,必然呼唤“本体论和价值论变革,激发有关生存的意义、生活共同体(community)与政治文化共同价值的新想象”[12]3-30。 赵月枝教授 2017 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强调:“中国传播研究不但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中国社会和历史知识基础上,而且不能随意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14]
就此而论,各国学者在致力于国际传播学去西方化之后的发展,正是基于各国自己的本地化或本土化特色去深化国际传播学的论述。对于中国传播学者来讲,当然就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学。
结 语
在网络时代,不只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的界线逐渐被打破,连传播与非传播的界线也开始模糊。哈佛大学教授奈伊(Nye)在1990年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意指在军事与经济之外,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也具有重要影响力。以当代的情况来看,包括影视节目、文化创意产业等,都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环,也都能发挥国际传播的效果,值得更深入研究。
有研究早已指出,美国影视内容永远以美国为中心,不只英雄与正义总是由美国提供,而且对于非白人、其他国家往往充满负面的刻板印象,例如女性、黑人等少数族群的形象常常受到扭曲,许多国家也都被描绘为丑陋的反派。一个知名的经典争议是美国迪士尼公司在其“全球思维、在地行为”(Think global,act local.)的全球化行销策略之下,在1998年推出了动画电影作品《花木兰》,这部电影改编自中国民间故事,为了加强剧情的冲突性与趣味性,不仅更改原本故事的情节,更把花木兰的对手“突厥”加以丑化,引来了突厥后裔国家土耳其的严重抗议。尽管如此,美国迪士尼公司无动于衷,继续全球放映,而土耳其则是在国内予以禁演。结果是全球影迷只看到电影中突厥的恶形恶状,浑然不知土耳其人的抗议与不满。
由此可见,软实力的影响力确实重要,这鲜明体现出了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学的重要性。就此而论,“讲好中国故事”可以说是当前中国深化与强化软实力的具体战略。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要让国际传播学去西方化,才能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学基础上,更加“讲好中国故事”。
李金铨指出:传统的国际传播学存有不少瑕疵,尤其反映的是美国特色。提倡“文化多元主义”的学者,对于全球化情境中的异质发展与互动交流发展表示乐观,相信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两股力量的撞击下,传播科技的变革与多元价值的争鸣,可望打破资本垄断与殖民神话,并促成文化的混杂化(hybridization)。这种论述,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理论的观察角度,可以弥补传统理论之不足,也呼应了李金铨教授的主张。然而,相较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一味乐观,毋宁也需要加强对国际传播学的检视与重构。李金铨教授与赵月枝教授都从知识论与方法论出发,呼吁重新建构国际传播的理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起点,值得相关学者思考并且提出研究论述,从而丰富国际传播的研究与理论。尤其当深入到本体论,美国中心的国际传播学至今仍以西方为文明的终点,也把西方化看成国际传播的方向,至于传统的主流国际传播学更是充满西方价值偏差。国际传播学在去西方化的同时,中国学者应从本土化出发,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内涵,再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思考当前国际社会的扭曲与不足,以及国际社会国际传播的应有面貌,从而以之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想象,发展出全新的国际传播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