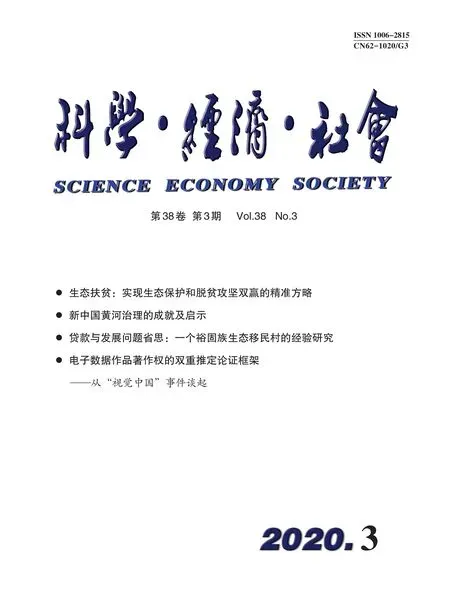《无尽的玩笑》对新型后人文主义主体的构建
黄 贺,陈世丹
(1.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2.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外语教学部,北京 100048)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 1962-2008)是美国“X一代”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也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当代文坛中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华莱士青年时便以天才新锐的形象进入文坛,之后更是以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巨著《无尽的玩笑》(InifiniteJest, 1996)赢得巨大的声誉,成为美国八九十年代走入文坛的新一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中的代表性人物。虽然作家因抑郁症盛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但他在美国文学乃至文化界中的影响力却长盛不衰,其作品不仅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也得到了批评界的持续关注和解读。作为华莱士的代表作,《无尽的玩笑》更是如此。小说对于光怪陆离的美国后现代社会景观的描绘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厚重的思想内涵吸引着人们不断对其重读和阐释,以期从中发掘出能够给人以智慧启迪的文学营养。诸多华莱士研究者都注意到,《无尽的玩笑》体现出清晰、深刻的后人文主义思想。后人文主义理论家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也曾专门撰文解析这部小说,认为其展现了人文主义主体在后人类时代的溃败并昭示出后人文主义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新型认知。不过海尔斯并未进一步分析小说是怎样建构起能够在新的人类生存境况下牢固树立的新型后人文主义主体的,而只是简略地评析了小说中的部分人物“抛弃了自主性主体的幻象”,“极为艰难地完成了主体性的彻底重建”[1]。以后人文主义主体观剖析《无尽的玩笑》,可以发现小说塑造了一批拥有后人文主义主体特质的人物,并描绘了具备新型主体性的人们是如何在后人类境况下发现自我、成功生存的。
一、后人文主义对构建新型人类主体的主张
后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其对人文主义所建构的人类主体的颠覆及其对后人类境况下新型人类主体的重塑。在后人文主义看来,人文主义把人之主体性建立在理性、智识等超验品质之上,从而把人类主体看做超越于世界万物之上的特殊存在,这成为了人类中心论及其带来的人类不断膨胀的控制欲和征服欲的思想源头。后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所推崇的主体性并非根深蒂固的哲学现实”[2],一切所谓的人性和人之本质都不过是历史性的建构。这就彻底解构了人作为万物灵长和世界中心的神话,把人拉回到同世界万物同等的平面之上,为还原人类主体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后人文主义对人类主体性提出了全新的认知,为理解后人类境况中人的地位、价值和行为准则提供了思想基础。
首先,后人文主义认为人类主体具有内在杂糅性,人的身体和意识是由有机物、无机物、信息、数据等多种跨越物种、边界和功能的异质成分混杂交融的产物。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哈拉维(Donna J. Haraway)提出了著名的赛博格(Cyborg)来描述这种混合主体。哈拉维认为,赛博格的成分混杂性使其能够打破人与其他物种、机器与有机体乃至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界限,跨越种族、性别和阶级身份的束缚,因而被权力意识形态视为怪异且非法的,但却拥有冲破各种二元对立和威权体制的巨大潜能。而随着人类对自己身心理解的加深,人们发现所有人都是赛博格式的存在。正如哈拉维所言:“就目前我们在正式话语和日常实践中对自己的认识而言,我们发现自己就是赛博格、杂交种、拼凑物和嵌合体。”[3]也就是说,赛博格式的多元混杂主体是人类主体的普遍存在范式。人类主体的杂糅性不仅指人类内在由多元异质成分构成的本质,同时也意味着人与外在边界的消融,这就内含着一种尊重差异、包容开放的伦理意旨。
其次,后人文主义反对人文主义认为人类主体是自足、自生和自主的看法,主张人类同外界环境之间互联共通、互依共存,因而人类主体是一种同外在共生的主体。后人文主义对于人之存在的认知主旨是“人类生命镶嵌在具有极大复杂性的物质世界之中,而我们的持续生存要依赖于这个世界”[4]290。这是因为后人文主义戳穿了人文主义所建构的人类具有自主性和自由意志的幻象,指出人在本质上是同动物乃至机器等其他存在物别无二致的信息—物质实体,人的生存和活动无不是在同外界一起构成的分布式功能系统中进行的,比如人驾驶汽车行驶,通过读书学习,用电话通话,等等。人与汽车、图书和电话共同构成了一个个分布式系统,是这些系统完成了人的行动、认知和交流等功能,而非人类自身。这样看来,人类就不再被认为拥有利用、控制和改造外在环境的主体意志,而是人与非人类介质共同组成了完成思考和行动的分布式系统,人类的主体性便从这些系统中生发出来,是一种与其他非人类介质互依共生的主体。
再次,后人文主义认为人的主体性永远在流变生成,人拥有与外在共同演化的主体。后人文主义指出,人文主义把人类主体视做僵化、固定的存在,这不仅扭曲了人之存在的真实面貌,也带来了种种边界、等级和秩序。人并没有固定的存在实在,而是始终处于与同环境中的他物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共同演进的过程中。后人文主义理论家沃尔夫(Cary Wolf)就把人的存在看做一种虚拟态,这种虚拟态并不是指虚幻的存在,而是说存在具有永不固定的动态性和永不封闭的开放性,处于永不完结的演化进程中。这一认知打破了人之超验性存在的神话,把人重置于世界万物不断演化的历史网格中,恢复了人“作为一种跟技术和物质的各类形式共同演化的合成性物种”的本来面目,“而正是这些本质上非人类的技术和物质让人变成了今天的样子”[5]。
内在杂糅性以及同外在的共生性和共同演化性是后人文主义对于人类主体特点的全新认知,这些特点重新界定了人类存在的本质,重构了后人类境况下的人类主体。借此,后人文主义“在物种之间界限日益模糊并开始混合交融的”后人类时期“倡导一种对于生命更加包容的定义,呼吁一个更加有力的道德伦理回应,并主张对非人类生命形式承担责任”[6]19。
二、悦纳他者,构建杂糅异质的主体
后人文主义把人的身心存在视为不同种类的物质与信息的聚集体和交互作用界面,人类不再是自足、封闭的存在实体,而是多元异质成分的混杂物。因而,后人文主义主体并不排斥他者或异物的存在,反而视其为自身的必要构成部分。在构建自我时,那些被传统人文主义所贬斥的物性、兽性、畸形、残疾等成分都被充分尊重甚至被糅合到主体里,和自我一起构成了新型的赛博格式主体,在这种主体中“他者构建了自我,他者被吸纳到自我之中”[6]105。这样的能够包容异质、悦纳他者的主体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不会在人与非人之间界线日益松动的后人类时代陷入存在焦虑或是走向消亡,反而能够更加牢固地确立自我。
在《无尽的玩笑》中,不能悦纳他者,反而单向度地追求纯粹的人之存在的人物都难以逃脱主体性沦丧的命运。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显示出两种病症——洁癖和对思考上瘾。前者的代表是主人公之一哈尔·因肯登扎的母亲艾薇尔。艾薇尔有着极端的洁净焦虑症,恐惧任何不洁的事物。小说中反复提及的一个事件是哈尔小时候无意中吞食了一块肮脏的霉菌,发现了此事的艾薇尔顿时变得歇斯底里,“用手指夹住满是霉斑的菌块,高高扬起,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救命,沿着方形花园反复跑圈”[7]11。在其洁净焦虑背后是艾薇尔的人格洁癖,是她对于纯粹自我的固守和对外界异质性他物的敌意。而后一种病症则典型地体现在哈尔的父亲吉姆身上。吉姆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到了摆脱情感、用理性控制一切的世界观并在自己的人生中将其付诸实践:在网球场上他全力摆脱情感波动,只冷静地用力学知识分析网球的落点和走向,成为一名顶尖运动员;他还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学者,提出的光学理论影响了世界格局;他甚至在转型成为导演后所拍的电影都以高度自我反思性为特征。可以说,吉姆是一位思考成瘾,有着思考强迫症的人。他就像小说里指出的那样患上了“分析瘫痪症”(Analysis-Paralysis)[7]203,极为善于思考,却情感瘫痪,无力同外界交流,内心空虚痛苦,最终把头放进微波炉中爆头而死。吉姆的死同小说里的多个人物一样都见证了“我思故我亡”的道理,是过度地沉迷于思考使他们迈向存在危机,这无疑是对人文主义所推崇的“我思故我在”的格言莫大的嘲讽。他们的故事说明,把主体性建立在理性等超验品质之上只能使人沉溺于自我中难以自拔,把自我封闭在思想的外壳里不同外界沟通,最终只能走向精神瘫痪。
而哈尔无疑继承了母亲的洁癖和父亲的聪慧,因此也同其双亲一样陷入了自闭和痛苦之中。在整部小说里他始终躲在学校的各个隐秘角落不断地思索,而无力行动。讽刺性的是,他依赖于服食一种名为DMZ的强力毒品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动力,这种毒品却是从“一种只生长于其他霉菌之上的隐蔽的霉菌”[7]170中提取出来的。而当他试图戒掉这种毒品时,就沦入了小说开头就交代了的结局:他在大学入学面试时突然瘫倒在地、无法言语,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表情,面目扭曲地发出“连动物叫声都算不上的噪声和呻吟”[7]14。这正暗示着在缺少了象征异质性他物的霉菌的摄入下,哈尔彻底丧失了主体性,沦为连动物都不如的存在。评论者指出,“让哈尔瘫痪的是一种极端内在性”[8]201,这种内在性将一切异质性他者隔绝于外,只关注自我意识,追求纯粹理性自我的建构,最终使哈尔走向内在情感缺失和同外界的绝对孤立,并吞噬了他的自我。
在小说中能够彻底摆脱这种内在性,勇于接纳他者,并拥有多元成分杂糅而成的强力主体的代表性人物是哈尔的哥哥马里奥。马里奥是因肯登扎家庭中的异类,他不像其家人那样拥有矫健的躯体,而是一位羸弱的畸形人。因为出生缺陷,他四肢发育不良、肌肉萎缩,经历了数次矫正手术,他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肉体和各种复合化学材料的混合体。然而就是这样的畸形躯体却能够最好地跟其他人相处和沟通:畸形前凸的脊柱使他体态微微前曲,始终处于半鞠躬的姿态,这让同他交往的人感到被尊重和认真倾听,因而非常乐于同他谈话;面容矫正手术和人工移植的眼睑让他的表情一直呈微笑状,给人天然的亲切感。更重要的是,马里奥绝没有其家人的身体和思想洁癖,而是乐观坦然地生活在网球学院里,真诚大方地同他人交流,因而成为所有人的朋友,收获了家人的信任、师生的尊重和友谊,知晓最多的秘密。他跟父亲学会了电影拍摄,但拍出来的作品却跟父亲拍的那些自我意识浓厚的实验电影迥异,而是利用自己畸形弯曲的手臂适合操作玩偶的优势拍摄了玩偶剧,并大受欢迎。他的玩偶剧的内容是戏仿当政的清洁美国党发起的清洁美国运动等政治运作,犀利地讽刺了清洁美国党以追求国家洁净为借口而大肆排斥异己、玩弄政治强权的政治伎俩。可以说,马里奥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睿智地认识到以清洁为名排斥他物的荒诞性,因而坦然拥抱异质性存在,并在多元成分的杂糅中把自己的残疾转化为一种优势,从而建立了强大的主体自我。
同马里奥一样能够积极拥抱他者并将其化为自我一部分的还有网球学院的学生阿尔特·斯蒂斯。斯蒂斯因为注意到自己的床会神秘地自行移动而向网球学院的学生精神导师莱尔求教。莱尔对他说:“不要低估物体。切勿不把物体考虑在内。毕竟这个十分古老的世界主要是由物体组成的。”[7]14斯蒂斯从中大获启发,开始吸纳物性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在打网球时不把自己视做打网球的主体,而是同球、球拍和场地一起配合运动的物质存在。小说中指出:“如果打开斯蒂斯的头,你会看到轮子嵌套轮子,齿轮和轮齿装配井然”[7]395。他的头脑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台机器。然而正是成为赛博格式存在的斯蒂斯球技大增,甚至差点击败了哈尔这样的顶尖球员。斯蒂斯之所以能够在网球场上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他拥抱了物质性”,显示出“反内在性的积极潜能”[8]205。在小说中,斯蒂斯成为网球学院的新星同哈尔在球场上的不断沦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正说明了人文主义建构的“我思故我在”式的自足主体的溃败以及后人文主义所设想的“我物故我在”式的杂糅性主体的成功。
三、平等互依,构建与外在同生共荣的主体
后人文主义揭示出人之自主性是人文主义在不可靠的基础上建构起的神话,认为人同其他物种乃至非生命物质在本质上是同源共生、相互构成的,因而具有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后人文主义反对在人文主义思想范式之下孽生出的物种歧视等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张人与其他物种之间是一种平等伴生关系,人类对于非生命物质也非单纯的开发利用,而是同其进行了共生性结合并由此形成一种彼此合作的关系。人类主体正是在与外在的伴生和合作关系中生发出的共生性主体,这种共生性主体同世界中其他生命和非生命存在一道构成“相互之间以一种彼此受益、非剥削性的方式互动的后人类共同体”[9]。
在《无尽的玩笑》中活跃着一群包括马里奥在内的残疾人,他们的存在正是对后人文主义所设想的共生性主体的绝佳注脚,因为残障式存在更加突显了人对外在的依赖性,而后人文主义对于人类主体共生性的认知则揭示出人具有普遍的外在依存性。这就意味着残障式存在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残疾或是无能,而是正常、普遍的存在范式。甚至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残障研究把残障式存在看做更为健康和良性的存在范式,因为只有承认“人在本质上不可避免的依赖性、人类之间不可抽拖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我们同动物、环境等非人类世界之间的相互依赖性”[10],把人的存在理解为外物协助下和资源网络中的存在,人们才能真正做到自由、踏实和可持续的存在。在小说中,拥有健康的人格和良性的人际交往并成功赢得所有人尊重和信任的马里奥正说明了残障式存在更易于生成一种人与外在互依共生的主体。
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唐·盖特利的成功戒毒和重寻自我同样典型地体现了人类主体的共生性。盖特利曾是一位重度毒瘾患者,同时也是毒贩的帮凶和打手,靠给毒贩卖命讨生活。毒品成瘾令他身心都遭受巨大侵蚀,几乎将他拖下死亡的深渊。出于对生命的一丝信念,他进入恩耐特疗养院接受戒毒治疗。在那里他加入了戒毒互助小组,互助小组要求他采用例行的十二步戒毒法进行戒毒,而其中的关键步骤是履行向上帝祈祷的仪式。然而盖特利却并不相信上帝,当他质疑不信上帝的自己如何能够通过向上帝祈祷实现戒毒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管你信还不是不信根本不重要,你只要这样做就行了”[7]635。同样,他也不相信互助小组组织的戒毒经历分享会是有用的,认为那是“一群底层潦倒人士仓促无序地聚在一起,喊着陈腐的口号,带着虚假的微笑,喝着令人反胃的咖啡,整个活动是那么地蹩脚,让人确信这绝不会有什么效果,除非是对最傻的傻瓜”[7]395。但祈祷和聚会却诡异地在盖特利身上奏效,甚至连他自己也吃惊于自己能够通过这样简单的仪式和粗陋的活动慢慢脱离了毒品对他的强力控制。他虽然自始至终也没有相信上帝,并坚持认为戒毒小组聚会是无聊的集体发泄,但他能够认真地遵循戒毒法的要求,定期参加小组聚会,同时“每日早间跪下来祈祷,让主帮助他,晚间再跪下来跟主感恩,不管他相不相信自己在跟什么事或什么人讲话,他却能真的度过那一天毫不沾毒”[7]350。盖特利对互助小组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将信将疑渐渐转变为机械地坚持参与,并意识到互助小组的十二步戒毒法“就是奏效,没有其他的。根本无法解释”[7]443。
盖特利的这一段似乎确实“无法解释的”离奇戒毒经历却吸引了评论者的较多关注和阐释,海尔斯也对其做了解读,认为盖特利能够通过十二步戒毒法成功戒毒恰恰是因为他不理解为什么这种戒毒法能够奏效,他的这种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让他得以放弃个人意志对戒毒行为本身的思考和掌控,从而成功“摆脱自主性自我的幻象,接受万物相互关联、自我行动的影响终将回归自我的世界,认识到自己是这样的世界里的一份子”[1]。也就是说,他摆脱了人文主义所建构的自主性主体,不自大地试图去评判和控制外物,而是把自我重新定位为和外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主体,从而能够以一种更加谦卑、审慎、自律和负责的态度行事,这让他重新建立了自我同外在的关系,并重构了主体自我,因而得以成功戒毒。
结合海尔斯在别处对“中文房间”思想实验的讨论来理解盖特利的戒毒经历可以更加清楚地阐发海尔斯在此处的观点。“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是美国哲学家塞尔(John Searle)提出的著名命题,塞尔假设不会说中文的自己在一个孤立的房间里借助中文符码和规则书就可以破译从门口塞进来的中文纸条并用中文进行回复,产生他能够用中文同别人交流的假象。塞尔提出这一思想实验的本意是反对机器能够思考,拥有同人一样的智能的观点,然而海尔斯却指出,在实验中懂中文的不是塞尔,而是整个房间,即包括人、中文符码、规则书和纸片在内的整个房间构成了一个分布式认知系统,在其中“生发出的人类主体的认知同整个分布式认知系统联为一体,‘思考’这一活动由人和非人介质共同完成”[4]290。海尔斯进一步指出,当代人类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类似于“中文房间”的分布式情境,在这些场景中人类无法独立完成认知和行动,只有依赖其他非人类介质才能够共同维持分布式系统的运转,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
以此观之,小说中盖特利的戒毒正是在一个“中文房间”式的分布式系统中完成的,帮助他戒除毒瘾的并非他个人的理性和意志力,而是他同互助小组和疗养院的环境共同组成的分布式功能系统。这个系统的良性运转支撑着他走上无毒的道路,而他也借此重新发现了一个同外部环境共生的新型主体。这也就是为什么成功戒毒的盖特利逐渐把互助小组看做自己的老朋友,把疗养院视为自己的家。在小说末尾,他为了保护疗养院的同伴挺身而出,被歹徒重伤,但他借此完成了自我救赎,因为他终于走出了唯我主义的藩篱,把自我的主体性建立在同外在的联结和共生中,成为了后人类社会中行动的英雄。
四、相互作用,构建同环境协同演化的主体
后人文主义认为人的主体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实在,而是在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生成和演化。人之“存在”(Being)实质上是一种“生成”(Becoming),而且是同环境中的他物一起经历的“共同生成”(Becoming-with)[11]。后人文主义所理解的人类主体性并非生发于人的内部,而是生发于人类同环境之间的关联、交换、相互调谐和适应中。因此,后人文主义主体不仅同外在环境共同生成,也同其一直处于协同演化的过程中。
在《无尽的玩笑》中可以发现诸多人类同外在环境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和共同演化的生动案例,其中最为精彩的要数小说对视频通话技术在美国社会中兴衰的描绘。令人叹服的是,在小说创作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今天业已普及的视频通话技术尚未问世,但华莱士以惊人的想象力精准地预测了这种技术的兴起和演变。在小说的详实描述中,视频通话技术同人类主体之间正是经历了一种相互调谐、共同演变的发展过程。视频通话电话在推出伊始就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并得到迅速普及,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语音通话,允许人们在聊天时看到对方的面容,让通话显得直接、真实。因而电信公司不断升级高清视频技术,让视频画质越来越清晰,人们在通话时能够越来越真切地看到对方的形象。然而,人们的人格心理却渐渐地被视频通话所改变:一方面,人们开始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这是因为视频通话时的人们再也无法像单纯语音通话时那样开小差或是干别的事情,而是迫于社交压力必须伪装出全神贯注的倾听者和交谈者的形象;另一反面,人们对于自己形象的虚荣心越来越强,开始对自己出现在视频中的长相感到焦虑,而高清视频能够定格和放大人们面容中的瑕疵,所以很多人患上了“视频面容不悦症”,讨厌自己的长相,认为自己长得不招人喜欢。为了缓解这一普遍的心理病症,电信产业开发出了一种“高清图像塑形技术”,这种技术能够“运用化妆品产业和执法部门业已开发成熟的形象塑造设备,在给定电话消费者的多角度图像中选出令其满意的多张图片,并从中挑出最为美观的元素,然后结合起来,形成一张高保真、可传输的非常漂亮的面部合成图像,图像中的人脸带着真诚且因为全神贯注而微微紧张的表情。”[7]148这其实就是运用图像处理和合成技术给人带上了一张面具,这既能缓解人的社交压力,也减少了人们对自己面容缺点的焦虑。
可是这种图像塑形技术又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虚荣,他们不满足于仅是还原和再现自己最美的一面,还渴望让自己在视频通话时显得更美。这种需求又催生了能够对人的面容进行美学优化的“美颜技术”,比如“让下巴更挺,眼袋更小,疤痕和皱纹更淡”[7]148。这种美颜技术在让人显得更加漂亮动人的同时却给人带来了自我形象认知偏差,使人内心觉得自己的真实形象过于丑陋,因而感到焦虑、自卑,无法接受真实的自己。于是通信企业吃惊地发现“大量的视频电话用户突然变得不愿出门,不肯同别人面对面交谈,因为他们害怕别人已经习惯于见到他们在电话中的远远更为漂亮的自己,在见到真人时会感到幻灭和失望,就像跟总是化妆的女性第一次素颜见面时给人的感觉那样。而且他们自己也害怕见到别人的真实面容。”[7]149在小说的描述中,随着美颜技术的不断优化,人们普遍患上的这种“面容美化焦虑症”愈发严重,也变得对美颜技术更加依赖。小说不无讽刺性地指出,随着人们对自己真实形象的美化越来越多,视频通话实际上又变回到了音频通话,因为人们和音频通话时代一样再也见不到通话者的真实容颜了。
通观小说对视频通话技术发展历程的描述,可以发现其核心特质是“用户被视频通话所改变,而他们对该技术的使用也转过来改变了视频通话”[12]。在技术和使用者、市场和消费者共同构成的环境中,人同视频通话技术相互影响、相互调适、共同演化,技术和市场塑造了人,人的需要也反过来推动了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而人也在这种相互塑造、协同演化的关系中不断生成新的主体性,发现新的存在状态。
在小说展现的世界中,不仅人与技术相互影响,人与自然环境更是密切相关、相互塑造,这集中体现在小说想象出的“大凹陷”中。“大凹陷”本是美国东北部的一大片宜居的地区,但因为人类向其中排放了过多的化学废料和工业污染物而变得无法居住,被政府隔离起来,变成了一片无人区。根据小说的描述,在这片区域内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异,巨型仓鼠和昆虫成群泛滥,植物可以食人。然而即使将这片区域隔离起来也未能阻止毒化了的自然给人类自身带来的巨大毒害,自然中的毒物通过大气和水循环进入到人们体内,使人的身体出现了变异,甚至精神都变得失常,小说的众多人物身上都有着明显的症状。“大凹陷”的存在不仅表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整体性和内在关联性,同时也深刻地说明人同自然相互影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同演化关系。
在后人文主义思想范式下,人类主体是多元成分杂糅交融的产物,与外在互依共生且共同进化,以杂糅性、共生性和共同演化性为特质。后人文主义持一种开放包容的伦理姿态,在人与外在相互关联的坚实基础上重新定义了人之主体性,为后人类时代中人的生存提供了建设性洞见。华莱士的小说《无尽的玩笑》精彩地刻画了后人文主义所设想的人类主体形象,生动演绎了后人文主义主体是如何在危机重重的后人类境况下踏实生存的。借此,小说充分体现了后人文主义关于建构人类新型主体的主张:悦纳他者,构建杂糅异质的主体;平等互依,构建与外在同生共荣的主体;相互作用,构建同环境协同演化的主体。解读小说对后人文主义思想范式下人类新型主体性的构建,可以对理解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存在本质、树立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伦理准则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