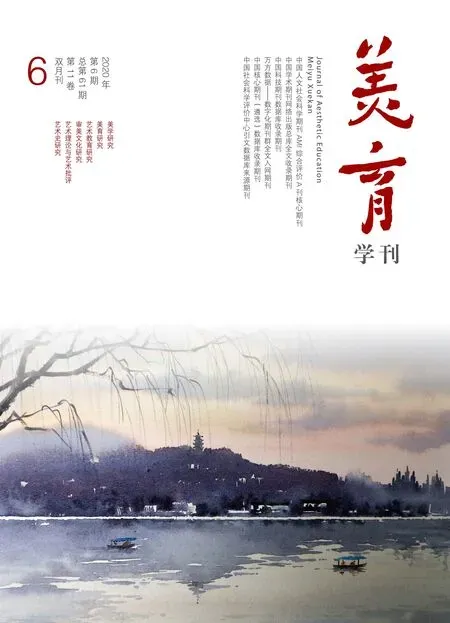他山之石:美国儿童剧作家夏洛特·乔普宁的艺术创作及实践
范煜辉,肖珏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夏洛特·乔普宁(Charlotte B. Chorpenning,1873—1955)是美国儿童剧文学领域的先驱。她在1931年之后,开始为芝加哥的古德曼儿童剧院(The Goodman Children’s Theatre)创作儿童剧,她的作品绝大多数改编自“普遍流传”且“熟悉”的童话故事、民间故事和知名的儿童作品,强调清晰的价值观。[1]晚年,乔普宁总结她儿童剧艺术经验的论著《与儿童剧的二十一年》(Twenty-OneYearswithChildren’sTheatre)被相关从业人员奉为圭臬。美国儿童戏剧史权威内莉·麦卡斯琳评价说:“乔普宁在儿童戏剧文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她领导了四十年代这场运动,使儿童剧院成为美国社群生活具有活力和重要的机构。”[2]126乔普宁去世后的第二年1956年,美国儿童剧文学领域的最高奖开始颁奖,每年颁给一位杰出的美国儿童戏剧家,冠以“夏洛特·乔普宁剧作家奖”。[3]鉴于国内未有研究涉猎这位重要的美国儿童戏剧家,本文力图勾勒乔普宁的儿童剧实践,通过分析其代表作,阐释乔普宁的儿童剧创作理念,希望能对国内的儿童剧改编有所助益。
一、乔普宁与古德曼儿童剧院
美国儿童剧经常与美国成人戏剧的发展不同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成人戏剧受到了经济大萧条的波及,但儿童剧却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美国儿童剧始于1903年,但到30年代,美国儿童剧市场化远比成人剧要低,这也使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儿童剧没有像成人剧那样受到经济大萧条的重击。“在1930年到1940年代,是美国戏剧史上忧伤岁月。经济衰退给了这个国家百老汇的生意以沉重的一击。”但美国儿童剧却依旧繁荣。“因为商业化剧院,没有在这个国家儿童剧的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2]76儿童剧发展更多依靠社区剧院,剧院不追求经济收益,却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儿童戏剧表演帮助小演员们塑造更完善的人格,乔普宁的名字就与芝加哥的一家社区剧院——古德曼儿童剧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古德曼儿童剧院成立于1925年。30年代它成为芝加哥地区的文化机构。这家社区剧院注重给当地儿童上演有价值的剧作,有些像戏剧学校。这家艺术机构以收取的学生学费、票房收入维持运营,演员是剧团里的三年制的学生。1931年,乔普宁接受了这家剧院的导演职位(1931—1951)。在这之前,她任教于威诺纳州立教师学院和西北大学等校。乔普宁接手剧院时,剧院每季演出6部戏剧,乔普宁将其减为4部,并推出额外的周末表演。虽然演出的场次增加,但仍是一票难求,票会提前6周就售罄。乔普宁主持的古德曼儿童剧院,在1938年到1952年共上演了35部儿童剧,其中,确证的有19部儿童剧是乔普宁创作的,乔普宁的剧作占剧院演出一半以上。[4]乔普宁在这些剧作中基本上身兼三职,既是剧作者,也是导演和制作人。1968年,104位美国国内儿童剧从业人员从148个剧作家的241部儿童剧中选择最佳剧作,乔普宁入选剧作三部,为最多,其中《皇帝的新装》《侏儒怪》《睡美人》分列第五、六、八位。[5]乔普宁在古德曼儿童剧院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考察乔普宁的古德曼儿童剧院上演的剧作,基本是当时深受儿童喜爱的作品或故事改编的。改编是美国二战前所沿袭的儿童剧创作的主导策略。美国儿童剧始于艾莉丝·赫特(Alice Hert)创办的儿童教育剧院(Children’s Educational Theatre,1903—1908),该剧院上演了第一部美国儿童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挖掘适合儿童剧改编的素材而非原创”,这一创作策略也被之后的美国儿童剧从业人员所沿袭。像切尔·梅吉(Chare Major,1881—1954)的巡回儿童剧团,演出事先进行问卷调查,选择孩子们已经知道了的故事进行改编。乔普宁在选择剧目时与梅吉有着相似的观念:“孩子们跑来看剧作时,应该对剧中的人物烂熟于胸。”[6]对乔普宁来说,儿童剧创作第一步是学习,然后是教的过程。分析乔普宁领导的儿童剧院演出的这些儿童剧,其所选取的改编素材来源多样,丰富了儿童剧的资源库。
关于美国戏剧对神话资源、原型、民间故事等的改编,不少人以常识推断美利坚合众国建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的文明史太短暂,美国缺乏丰厚神话、民间故事等资源。像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揶揄美国剧作家谢泼德、古厄尔和威尔逊等成人剧作家“浅薄”:相比欧洲剧作家,萨特运用希腊神话,许多戏剧运用贞德的主题,欧洲戏剧家倾向于现有的原型和神话;美国剧作家就“只能用早期的美国电影,流行音乐的世界和滑稽的脱衣舞表演了”。[7]很多人把美国视作文化荒漠,嘲笑这群缺乏经典滋润的扬基佬心灵的贫瘠,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戏剧文化与厚重感绝缘,美国的民族性格也沾染上了这种快餐文化的浅薄。然而,以史为证,古德曼儿童剧院的儿童剧并不像艾斯林所言的“浅薄”,剧作家们选材的视域广阔,古今国内外,为其所用。
乔普宁的改编理念是要将前人的故事一代代传递下来,这是先辈留下的丰厚馈赠,也是儿童剧改编的“最好的选择”。这些故事“来自久远过去的智慧,它应和着我们当下的渴求”[8]36。古德曼儿童剧院的素材并非像艾斯林所鄙夷的拘囿于美国本土浅薄的流行文化,她们的不少剧作素材来自于其他民族的神话或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经常会有多个版本,乔普宁会“竭泽而渔”,搜集多个版本的故事,综合比较、汇融之后进行再创作,如希腊神话点石成金的迈达斯国王的故事,法兰西最伟大的骑士罗兰与查理曼大帝的传奇,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神灯的故事,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角主神毗湿奴的化身罗摩的神话,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轶事。也有根据国外脍炙人口的童话和小说改编的,其来源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还有一些儿童小说经典,如《爱丽丝漫游奇境》和《鲁滨逊漂流记》等。
特别需关注的剧作是剧院根据美国本土文化资源挖掘与整理的。取自美国作家适宜儿童剧改编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有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王子与贫民》,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等;诗歌有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有关美国拓荒者丹尼尔·布恩的传奇《发现,肯塔基的开拓和现状》等。不少儿童剧的素材不是来自文本,如根据历史轶事改编的《阿布·林肯-新萨勒姆节》和《林肯的秘密信使》,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的《印第安俘虏》,根据美国口传民间故事改编的《鲍尔·班扬》。这类剧作要求真实性。为了创作有关林肯的剧作,乔普宁深入查阅国会图书馆和美国档案馆的资料,通读林肯及其同时代人的著作和演讲;写作《印第安俘虏》时,乔普宁研究主人公埃莉诺·莱特尔(Eleanor Lytell)的背景,又去美国民族学局研究塞尼卡的印第安人的报道,调查他们的仪式、习俗、食物、舞蹈、歌谣和颂歌等,尽力还原历史细节的真实。
乔普宁主导的古德曼儿童剧院有着自由宽松的氛围,乔普宁管理剧院并非一手包办,她鼓励、协助其他人大胆实践,这使得剧院推出的剧目选题更具包容力。从现有掌握的材料来看,乔普宁的创作未超越美国主流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传统,她的《印第安人俘虏》展示了塞尼卡印第安人捕获白人小女孩之后将其抚养成人,铭刻了印第安人野蛮的刻板印象。乔普宁在儿童剧里表现出来对少数族裔的敌视和排斥,而她同事的剧作在少数族裔问题上比她更具开放性,也补充丰富了古特曼儿童剧院剧作的价值观取向。像《小李波》上演的是一个关于中国侦探的故事,主角是一位12岁的华裔美国姑娘,她帮助一个小偷在唐人街的华人社群里得到人们的谅解,剧作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中国文化和华裔美国社群。关于美国非裔主题,剧院改编自马克·吐温的儿童剧《哈克贝利·芬恩》,观众对该剧上演的故事耳熟能详,剧作延续了原著的反种族歧视主题。儿童剧《小黑人桑波》改编自苏格兰作家海伦·班纳曼(Helen Bannerman)的《小黑人桑波的故事》(TheStoryofLittleBlackSambo,1899)。剧作中的小黑人桑波一改同时期黑人单纯、未开化的负面形象。虽然时过境迁,“桑波”一词在20世纪中叶成为对黑人的蔑称,这部作品现已禁演,但在当时原著深受孩子们喜爱。
麦卡斯琳评价说:“乔普宁长期杰出地为古德曼儿童剧院服务,可能她誉满全国是因为她的剧作和对儿童故事的改编。她对儿童戏剧文学的贡献是杰出的。无论是从在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2]92乔普宁领导的古特曼剧院在选择剧目素材时视野广博,已不仅限于她之前的儿童文学名篇,还有涉及具有奇幻色彩的神话、民间故事等。古特曼剧院对美国本土资源的保护性挖掘,进一步扩展了美国儿童剧的主题空间,使其具有了博大的文化包容力,从儿童剧的素材选择上来看,这也是乔普宁对艾斯林等人偏见的最好回击。
二、展示它,不要讲述:乔普宁编剧的核心原则
麦卡斯琳在《儿童与戏剧》中曾说:“每个优秀的儿童剧作家都需要用哲学观念或美学原则来驾驭他的实践。”[9]乔普宁的戏剧创作哲学也是她的生活哲学。她相信宇宙是美的,她努力用人物塑造和行动来表达这种美,这些都是她为小观众创作的。美的时刻能够抓住儿童的注意力。乔普宁创作最为核心的原则是“展示它,不要讲述”[8]55-58。这是她所有儿童剧成功的秘诀。下面将根据乔普宁创作的《侏儒怪》等,探讨乔普宁儿童剧改编的核心原则及其编剧策略。
“展示它,不是讲述”,乔普宁的儿童戏剧并不回避对孩子们价值观的教育,但这种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宣教,而是要让儿童快乐地对角色产生情感认同。“娱乐(Entertain)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tenere,意思是‘去抓住’。好的儿童剧会能提供让儿童去认同人物的机会,这人物需是在儿童能够理解的——有趣的,有价值的,引人入胜的场景中展现的。”[10]而儿童要对戏剧人物产生情感认同,人物的内心情感必须是充盈丰富的,能让孩子们从角色身上发现自己的性格,触发儿童产生代入感,进入角色所面临的价值选择困惑之中。但乔普宁的剧作基本都是改编剧,有些底本的人物会受到民间故事叙述范式的限制,人物内心着墨不多,这也就是说,乔普宁的创作名义上说是改编剧,她的底本大多只是提供基本故事框架与人物关系,人物形象则需要乔普宁通过想象力加以充实丰满,以展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其中乔普宁最值得借鉴的改编经验是营造出情境展示核心人物的价值选择困惑。
乔普宁的《侏儒怪》根据德国民间故事改编,这个故事也收录在《格林童话》里。底本的民间故事采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只概述故事,并没有关注人物的内心情感。乔普宁要将其扩展成儿童剧,就需充盈磨坊主女儿的内心。但当读者透过民间故事的表层,按照逻辑推导人物的内心活动时,却发现磨坊主的女儿在价值观上是畸形的,这个人物并不“有趣”和“有价值”。格林童话中,国王与磨坊主女儿之间没有纯洁的爱情。国王听说磨坊主女儿有神奇的本领,能把麦秸纺成金子,于是他三次下令把她领进了装满麦秸的屋子里,两次以生死相要挟,“这一通宵你得把麦秸全给我纺成金子,不然天一亮你就必须死去”。他说:“如果今夜里你能给我纺好的话,我就娶你做我的妻子。”故事里,磨坊主女儿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人。男人只要有足够的权势,就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威胁要杀死你,不断压榨、虐待你,第二天他幡然醒悟,跑过来说现在你有资格配跟他分享权力,女人可以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坦然接纳。在道德品质上,磨坊主女儿也并不高尚。她贪图权势,胆小怕死,言而无信,背弃承诺。反而是故事里的反面人物侏儒怪不贪恋金钱,他把生命看得比金钱更重要。当王后提出送给他王国的所有财产时,侏儒怪拒绝了:“我宁要一点有生命的东西,不要全世界的所有财富!”他有着骑士风范,有怜悯心,三番两次帮助磨坊主女儿:先是把麦秸纺成黄金,后又是当她大声痛哭,哭得他可怜她了,“如果在三天之内你知道了我的名字,我就把孩子留给你”。最后,当王后说出他的名字之后,他没有毁约,而是“自个儿把自个儿撕成了两半”。[11]
格林童话里的正面角色磨坊主女儿性格顺从,成为男权的玩物。在儿童剧《侏儒怪》中,乔普宁改编了原有的民间故事,增设了人物,大幅扩充人物内心活动,弥补了原来故事的败笔。儿童戏剧开场,伴随着音乐,侏儒怪围着一口怪锅在诡异地跳舞,吟唱着:
今日我酿造,明日我烘烤。
我用力踩踏,世界不安摇晃。
无人知晓,我来自何方,
无人知晓,我名为侏儒怪。
啊,我要走遍东西,
直至找到最合适的孩童。
我要走遍南北——
侏儒怪的母亲赫尔达问儿子,你在干什么?侏儒怪回答:“我在寻找东西放进我的锅里。”面对母亲的逼问,侏儒怪透露了他阴暗的秘密,他想要偷一个国王的儿子放进他的锅,这样他就可以统治人们的思想,进而终结人类的命运。邪恶的赫尔达给儿子出谋划策说,想要人类毁灭,变得贪婪,就必须达成一个交易,要有一个王后心甘情愿地拿自己的儿子换取黄金。面对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交易,邪恶的侏儒怪藏在阴暗的世界边缘等待着时机。剧作增设的序曲,使得民间故事里只有一维的现实世界,拓展为儿童剧中幻想与现实二维世界并存交融,扩展了《侏儒怪》的宇宙观。侏儒怪只要在锅旁倒转三圈就有小门打开,可以通向现实世界里的任何地方,他犹如罪就伏在门前。侏儒怪母子的邪恶的赌注,寻找到最贪婪的人性,一个会拿自己的儿子去作交易换取金钱的皇后,这场来自地狱边缘的赌注是《约伯记》中,天堂里上帝和魔鬼赌注的逆转。如果说,无辜的约伯代表着人类受难,那么,儿童剧磨坊主米勒之女受的诱惑,接受的考验,也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因为她的价值抉择关乎人类是否会灭亡。
乔普宁在《与儿童剧的二十一年》中着重强调,儿童剧里要有让儿童来认同的角色。这个角色应该是圆形人物,有着丰富的心灵,这样才能触发儿童的代入机制,进而引发情感认同。阿林顿也说:“好的儿童剧是有好的故事,许多张力和行动,丰富的圆形人物。”[12]为此乔普宁在剧中增设了王子这一角色,增添了王子和米勒之女感情这条线索。王子爱上了平民磨坊主的女儿,因为她具有他心目中王后的品格,他让米勒之女选藏宝室里的珍贵珠宝还是他登高采集来的鲜花,米勒之女选择了鲜花。王子说:“我幻想着我的皇后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王子送给米勒之女项链和戒指作为交换订婚的信物。米勒之女拿起野花变成的项链,草编成的戒指,王子说:“它们比黄金、珠宝更让我满意。我会像你保存我的戒指一样长久地保存你的戒指。”当国王要求米勒之女在太阳的影子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就必须把麦秸织成黄金。王子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不惜违抗父命,被父亲投入了监牢。在这危急时刻,米勒之女在暗室里看着满屋的麦秸一筹莫展时,侏儒怪出现了。当侏儒怪提出要项链,要王子送给她的花时。米勒之女经历了痛苦的煎熬:
米勒之女:但这对我来说是别人给我的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侏儒怪:很好。(她哭了。他看着她,徘徊着。)
米勒之女:我该怎么办?
侏儒怪:给我项链!给我花!稻草眨眼间就能成为黄金。
米勒之女:我不能给你这些。(侏儒怪跳脚,挥动拳头,怒气冲冲地跳来跳去,吱吱作响。)
侏儒怪:别让我发脾气。
米勒之女:我只是说我不能。
侏儒怪:我受不了……再见!
米勒之女:别走。[13]
米勒之女内心经历焦灼和痛苦,她的犹豫徘徊展现在了舞台上。为了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她最后做出让步,割舍了心爱之物。最后一次是米勒之女的至暗时刻,侏儒怪露出獠牙,向米勒之女索取她的头生子。有了前两次对米勒之女内心苦痛展示的铺垫,第三次剧作家做了巧妙的回避,没有展现这一场戏,此处无声胜有声,就交给观众的想象去完成。儿童剧里米勒之女性格纯真善良,不贪婪,她三次与侏儒怪的交易,是她心爱的人身处危境需要她去担当,爱情比金钱更重要。她放弃了外在财富戒指、项链,换取了自己爱人的平安,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乔普宁赋予米勒之女丰富充盈的内心,通过将故事展示在舞台上,在童话的幻想结构之中,让孩子们去探索善恶的概念,走进人物内心,代入自己的经验去处理这些生活问题,进而帮助儿童找到实现自我的经验与意义。
营造情境展示人物价值选择的艰难,这是乔普宁儿童戏剧改编的核心要素,这不仅体现在乔普宁的《侏儒怪》中,在她的其他剧作中也有运用。乔普宁根据美国1779年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成《印第安俘虏》。埃莉诺·莱特尔(Eleanor Lytell)年幼时被塞内卡部落的印第安人种粟者(Cornplanter)首领俘虏,被带到塞内卡部落,替代首领去年被人杀死的弟弟。勇敢的埃莉诺得到了塞内卡全族人的爱戴,融入了塞内卡社群。“她已经是种粟者首领的妹妹。她的母亲老皇后的女儿。罐子里最好的肉,种粟者首领会挑出来给她。”当埃莉诺的母亲在外苦苦寻觅女儿八个月,找到了塞内卡部落时,种粟者首领害怕失去妹妹,“她会偷偷地潜入我们村子。你会看到她的脸,你会听到她的声音。你会有奇怪的感觉。你现在不知道你将来会做什么事。对她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死”。当埃莉诺听到自己的母亲生命危在旦夕之时,她不得不压抑自己对母亲的思念,“考验我!哦,我的哥哥,试一试和看一看吧!把我的白人母亲带到我在的地方。我会向你展示你能相信我。我会像你手中的一支箭。我会按照你的意志走或者留”。[14]同样痛苦的抉择最后也摆在了种粟者首领的面前,他的妻子千方百计地设计陷害要毒杀埃莉诺,并不惜玉石俱焚,将埃莉诺的身份暴露在了埃莉诺的白人母亲面前,种粟者首领是铁石心肠地强留下心爱的妹妹,还是放她和她的母亲离开部落,这是乔普宁为剧作人物设置的两难境地。
乔普宁希望儿童剧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浸入式情境,体察人物内心世界,这是乔普宁儿童剧偏静的一维:沉浸,体悟,认同;但乔普宁充分考虑到孩子们心理接受时间的长度,儿童剧也要有动的一维,孩子们坐太久时间而没有运动是不好的,她聪明地意识到剧作里要包含一些“活动点”。在创作《杰克与豌豆》一剧中,乔普宁说:“孩子们帮助杰克从困局中走出来的努力,给了他们剧烈活动的机会,而且还没有中断故事。在结尾杰克打巨人的时候,绊倒了他,巨人陷在了椅子里。杰克把他绑了起来。这个场景点大致就是被征服的巨人和胜利的杰克。”[8]17
乔普宁的儿童剧注重故事人物与小观众们的互动,不仅仅依靠台词,更多的是去展示。在展示过程中,乔普宁充分考虑到戏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舞蹈、音乐,甚至喜剧场面都应该成为戏剧动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综合这些问题,乔普宁尊重观众,回应观众,她会安排学生在表演的时候和小观众们坐在一起,观察他们的反应,并根据小观众的反应及时对剧作做出相应调整。乔普宁一直践行着她自己的信念:在改编时要有对儿童剧的有神圣使命感,信守创作儿童剧不应只关注票房,而更应关心儿童剧对人类共有价值观的守护。
三、余论:乔普宁对中国儿童剧事业的启示
根据《2016中国儿童剧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儿童剧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观众人数最多的戏剧类别。2016年国内演出儿童剧12928场,票房收入超过3.8亿元,超过了成人话剧市场。(1)转引自张燕:《今天,我们如何创作和演出儿童剧?》,载《上海戏剧》,2017年第6期。但国内儿童剧市场却有着诸多乱象,正如《剧本》主编温大勇指出:现在儿童剧在表面上很繁荣,实际情况则不然,奢华的包装下难掩内容的贫乏。[15]笔者对国内儿童剧的观感体验与温先生的评价大致相仿。近年在杭州陪孩子观看了不少儿童剧,然而,除了像《小贝的书柜》等少量精品剧外,绝大多数儿童剧都不尽如人意。国内儿童剧剧本创作滞后,剧作家改编过分追求时髦IP,舞台被大量诸如小猪佩奇、汪汪队、海底小纵队这些热门的动画片IP改编剧所充斥。儿童剧创作追求快餐化,文学性和艺术性堪忧。很多剧目枉顾儿童剧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沦为了拉长版的动画片,剧本乏善可陈,舞台的喧哗与骚动背后,没多少给孩子去探索回味的价值意义。
作为一个美国儿童剧研究者,纵观美国百年的儿童剧发展史,美国儿童剧自1903年诞生,排演的第一部儿童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确立了美国儿童剧创作的主导倾向是注重改编。以乔普宁为代表的古德曼儿童剧院为例,美国儿童剧改编的素材来源多,有神话、民间故事、文学经典、童话、历史伟人事迹等。相比较而言,中国当前儿童剧的改编素材就过于狭窄了。另外,国内的儿童剧在价值观塑造上,不少过于简单粗暴,未考虑儿童剧体裁的特点和孩子们的观剧感受,相信乔普宁的儿童剧创作和艺术实践会对我国相关从业人员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