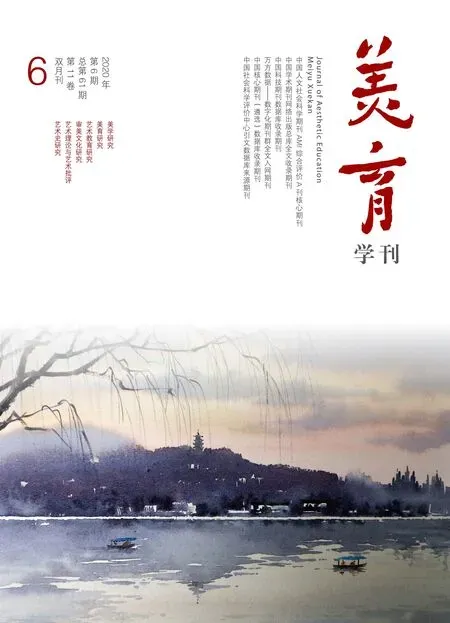从“原作”到“原境”
——西方艺术史课程实地教学的重心转变
李 晨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一、引言
意大利拥有丰厚的文化与艺术遗产,尤以永恒之城罗马、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东西方文化的汇聚地威尼斯等城市为典型代表。因此,意大利无疑是学习西方艺术史的最佳目的地。[1]近年来,同济大学开始实施“佛罗伦萨海外校区艺术教育基地交流项目”,旨在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探索独特的艺术教学模式。在此背景下,人文学院启动暑期短期海外课程,组织师生赴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三城展开实地教学。依托于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海外校区,人文学院的课程项目内容包括中意教师共同设计的主题讲座、专题研讨及实地调研。在极佳教学效果的基础上,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还从艺术史、博物馆学、艺术设计等角度完成了各自的分组研究项目。
更重要的是,西方艺术史中最有分量的古典艺术与文艺复兴艺术均与意大利密切相关。因此,该海外课程项目对人文学院的西方艺术史课程教学尤其有启发意义。师生在意大利为期两周的学习和考察,不仅改进了人文学院西方艺术史的课程教学,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对西方艺术史教法的范式转变产生推动作用。多年来被倡导的西方艺术史实地教学,重心应当从“原作”转移到“原境”。
二、“原作”与西方艺术史教学
近年来,随着艺术史学科的成熟,艺术史的研究和教学日趋概念化和理论化。一个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艺术史相关课程大部分在教室内进行,出发点为图像,即原作的不同形态的复制品。这种模式的缺点显而易见,毋庸赘述。因此,许多学者和教师呼吁艺术史教学不应脱离实物。教学的重心,至少在一定比例上,应从“图像”转移到“原作”。结合博物馆尤其是美术馆的实地教学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常见手段。[2]
在博物馆展开实地教学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原作,对作品产生从图像得不到的直观理解。一方面,作品的尺寸不再是课本上的数据,而是直观的感受。如参观梵蒂冈博物馆的《雅典学派》时,学生无不感叹其铺满墙面与穹顶的篇幅,以及超乎想象的震撼程度。另一方面,绘画作品尤其是油画作品的细节,往往由于印刷术或多媒体设备的限制,在书本或幻灯片上都无法得到完全展示。在博物馆内的原作前,学生可以超近距离观察,注意到其笔触的变化,画面的凹凸不平感,甚至作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一块看似多余的颜料。另外,学生还可以学以致用,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学习并评价场馆规划和作品的展陈设计,为将来从事策展或相关职业打下基础。例如,在佛罗伦萨皮蒂宫,多数学生都注意到该博物馆的布展方式决定于其家族收藏兴趣,并非按照作品时代或门类展开,这种方式其实没有顾及观众,尤其是西方艺术史知识较薄弱的观众的感受。
由此可见,目前这种强调“原作”的博物馆实地教学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很大的提升空间。博物馆的展陈既是一种创作,也是一种破坏。作品原有的存在状态常常被改变,这不利于观者对艺术品的理解。例如,罗马时期的石棺经常被当作雕塑作品摆放在展厅内。这些石棺当然是罗马时期的实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不是原物了。它们的外观也许并没有大的变化,但在博物馆这一新的环境中,其原有组合和被观看方式发生变化。这时的石棺不再是丧葬用品,而是变成了雕塑作品,并和其他雕塑,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真正意义上用来观赏的雕塑作品,放在一起,以展示雕塑艺术的发展史。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原境”这一概念并将其运用到艺术史的教学中非常有必要。西方艺术史的教学更是如此。
三、“原境”与西方艺术史教学
艺术史中的“原境”概念最初由以巫鸿为代表的艺术史家们提出,该词实为英文context的中文翻译。Context在艺术史中的含义与文学中的“语境”或“上下文”截然不同,因此被译为“原境”,主要指历史环境。[3]这一理念迅速被国内学者接受与推广,中国艺术史教学与教材编写中的“原境”缺失问题也渐渐受到重视与反思。[4]其实,国内的西方艺术史教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教材来讲,无论中国学者编写的较有代表性的教材[5],还是西方人撰写的西方艺术史经典教材[6],多数也是按雕塑、绘画等艺术分类方式展开叙述。这除了观念原因之外,文本叙述方式的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实地教学对原境的强调就显得尤为关键。艺术史,尤其是西方艺术史教学中对“原境”的强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使用的原境
在西方艺术史的教学中,学生最常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件作品是用来干什么的?”诚然,文艺复兴以来,相当比例的艺术品确实是用来欣赏的。在学生们参观皮蒂宫等由私人收藏和私人府邸改造而来的博物馆时尤其能感受到这一点。不过,包括皮蒂宫在内的博物馆藏品也有相当比例是前主人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当它们被放置在自己家中时,已经过了二次改造,其最早的“原境”已不复存在。基督教艺术是最典型的例子。
好在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多有教堂,其中往往有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雕塑、祭坛等原作,很多教堂建筑本身也是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原作。这些原作很好地保存了艺术品的原境。因此,同济师生参观了佛罗伦萨的Orsanmichele教堂博物馆,并请佛罗伦萨大学Raffaele Valesi博士结合宗教背景展开实地教学。该建筑一层为仍在使用的教堂,二层以上为空间改造后的博物馆。在一层教堂看到壁画、祭坛等作品的同时,学生们对于这些艺术品功能的疑问也就基本解决了。然而在二楼,基督教题材的雕塑被从原境剥离,并被按主题分类重新安置在博物馆中,其本意便消失了。观者学习的难度也立刻增加了很多,需要借助更多的讲解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解。
(二)创作的原境
西方艺术史教材中往往将艺术品按照绘画、雕塑、建筑等门类分别展开叙述,受此影响,西方艺术史的教学也往往按艺术分类进行,这其实也不利于学生对艺术品内涵的理解。
多数艺术品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博物馆或教材中看到的那样一件件孤立的作品,它们往往是跨界的,绘画、雕塑、建筑多种门类的艺术品常常彼此包含、融为一体。他们之间甚至经常没有明晰的界限。以建筑为例,在一座西方古典建筑中,建筑与装饰几乎无法完全区分开来。不同风格的柱础、柱头、三角楣、拱顶等,既是建筑构件也是装饰元素。虽然西方装饰艺术后来渐渐独立出来,但其中仍保留着大量来自建筑的母题。即使是绘画、人像雕塑等看似与建筑截然二分的艺术形式,也往往用于装饰建筑的内部空间,从而与建筑艺术本身融为一体。
这些艺术品的创作过程本身也能很好地体现艺术的多门类融合,当然这也是这种融合最根本的原因。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大师们通常多才多艺。例如巴洛克艺术大师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既是建筑师、雕塑家,也是画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为圣伯多禄大教堂设计的正面柱廊与圣伯多禄广场。中央穹顶下,覆盖教皇祭坛的青铜华盖也是贝尼尼的作品。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按照建筑或雕塑艺术的门类分别来看这两件作品,显然无法真正理解贝尼尼。不仅如此,青铜华盖正上方的教堂中央穹顶是米开朗琪罗设计的,这些建筑构件与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拉斐尔的壁画以及其他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艺术大师们的作品一起,将圣伯多禄大教堂变成了一件极为震撼人心的综合艺术作品。
另一方面,很多常被忽略的细节也能展现这种多门类艺术的融合甚至互相借鉴。例如,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收藏了大量哥特式绘画,传统教材或课堂往往从画面出发分析其主题、构图、笔法、色彩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哥特风格。这种分析固然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但常被忽略的一个细节是,艺术史教材插图中往往只展示画面、略去画框,其实这些画框也是非常典型的哥特式,且整体设计类似于一座哥特式建筑,无论是左右两侧类似于建筑柱式的边框,还是画面上方的尖拱,都是典型的哥特式元素。这些哥特式画框无疑是专门为哥特绘画设计与创作出来的。
在一些建筑与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同时保存至今的场所,创作的原境则能够被直观感受到。例如,学生在参观Orsanmichele教堂时,身处教堂的建筑空间之中,注意到教堂内部略显昏暗的光线情况,以及可用于创作壁画的狭窄墙面。这种环境显然给湿壁画的创作增加了很大难度。Orsanmichele教堂内的壁画均为湿壁画,这种壁画需要趁灰泥还新鲜(fresco)时进行绘制,创作过程在灰泥变干燥变硬之前必须完成。也就是说,这些湿壁画的作者通常需要在数小时内快速完成自己的作品。在了解湿壁画的这一特性并感受到创作原境之后,学生在评判艺术家水准时就能很自然地将时间和光线因素考虑进来,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壁画创作。
(三)历史的原境
历史的(尤其是经济的)原境之重要性,最直接的表现为大环境对艺术的影响。例如,经济中心的转移往往带动艺术家与艺术中心的转移,赞助人的经济实力与个人喜好通常会直接影响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作品数量,外界经济条件对艺术创作材料等细节也有直接的影响——油画、蛋彩画的转变与混用就与经济条件的变化直接相关。
最典型的例子无疑是威尼斯经济的崛起与威尼斯画派的兴起之间的联系。虽然从教材中、在课堂上学生都会学到这一知识点,但是,只有在他们漫步在威尼斯街头、斜倚在贡多拉之上,观察宏伟的教堂建筑、穿梭于精美的民居建筑的时候,才能直接感受到当年威尼斯的富庶及其直至今日的影响。这种体验在任何课本和课堂上都是得不来的。
另一方面,有时候艺术的繁荣程度看起来却与经济实力不匹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锡耶纳画派为代表的锡耶纳哥特艺术。当时的锡耶纳是和佛罗伦萨类似的城邦共和国,不过其经济和政治势力远不及佛罗伦萨。然而,锡耶纳的哥特艺术却能够和佛罗伦萨分庭抗礼,风格也与之完全不同,两者一起使十三四世纪的意大利艺术显得十分多彩。如果只分析艺术家或作品,甚至仅看经济与政治因素,都无法理解锡耶纳哥特的繁荣。这时,历史的原境,即历史地理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锡耶纳的地理位置刚好处于法国教徒至罗马朝圣的交通要道上:锡耶纳哥特受到多方艺术因素的影响,因而风格独特;受到教徒实际需求的推动,因而一片繁荣。历史地理的原境对艺术的影响,只有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才能真切感受到。即使学生们只是坐火车旅行,他们在旅途中也能感受到各重要城市(大致相当于昔日的城邦)之间大致的方位关系与距离,以及这种空间关系对艺术的影响。
(四)自然的原境
波提切利的名作《春》,虽然主题是神话,但其中很写实地描绘了500多朵花,这些花分属100多个品种,并且绝大多数都能在佛罗伦萨春天的郊外找到。如果说这种自然的原境受季节与植物学知识的限制较难领悟,那么茛苕与古典艺术之间的关系就直白得多了。
茛苕(Acanthus)纹样在西方装饰艺术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其优美的曲线因被科林斯式柱头采用而影响深远。茛苕纹样甚至还深刻影响了中古中国的装饰艺术,这种装饰纹样在8世纪以后的中国相当常见。[7]不过,茛苕这种植物原产地中海沿岸,甚至“茛苕”这个看起来很有中国特色的名字也只是英文“Acanthus”的音译而已。中古中国的工匠们并未见过茛苕的样子,他们所创作的茛苕纹样也与古典艺术中的原型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学生们显然幸运得多,当他们来到亚平宁半岛的土地上,看到茛苕的叶片,在博物馆或建筑遗址中看到科林斯式柱头时,就能很好地理解茛苕纹样与植物形态之间的关系,也能更好理解其设计灵感来源传说(茛苕包裹篮子)。在此基础上,学生们观察茛苕纹传入中国之后的变体,并与古典艺术中的茛苕纹样作比较,就能比较容易地还原茛苕纹的流变以及工匠的创作过程。
另外,学生们在意大利的旅行与生活过程,看似与艺术关系不大,其实当他们身处意大利艺术自然的原境并用心观察时,也能领悟到许多艺术载体与题材背后的深层原因。当飞机即将降落在罗马的机场时,学生们俯瞰罗马周边较少高大乔木的丘陵地形,以及郊外零星分布的大理石采石场,就能明白为什么意大利建筑与雕塑最主要的材质是大理石而非木材。当学生们在意大利餐馆享用美食时,会很容易发现橄榄无论在小食、前菜、调味料还是主食辅料中出现的频率都非常高,这一食材的地位也能帮助学生们理解意大利艺术中橄榄或橄榄树相关题材的流行。当学生们辗转于各大城市之间,在火车窗外看到大片的葡萄园与分布其中的葡萄酒庄,便能感受到人们对葡萄酒的传统热爱,进而理解葡萄藤纹样在古典艺术中的流行,以及酒神题材绘画雕塑等作品在不同时期都很常见的原因。这种自然的原境对理解西方艺术尤其是意大利艺术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四、结论
西方艺术史的教学和研究有其特殊性,师生都必须在理论与图像学习的基础上,接触大量原作并展开实地考察,这样才能深入理解西方艺术的本质,及其背后的历史、政治、经济等文化驱动力。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依托于佛罗伦萨海外校区展开的西方艺术史实地教学活动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学生们不仅拓宽了艺术视野,还培养了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的能力。茛苕纹由西到东的传播、中西木建筑与石建筑的差异等具体问题带来的对比视角,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西方艺术,同时也更好地理解中国艺术,认识到两者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互相联系,进而将两者纳入世界艺术史的范畴内重新考量。
另外,同济师生在意大利为期两周的考察和学习,不仅改进了人文学院西方艺术史的课程教学,还能对西方艺术史教法的范式转变产生推动作用。多年来被倡导的西方艺术史实地教学,强调从“图像”转移到“原作”。然而,目前这种强调“原作”的博物馆实地教学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很大的提升空间。西方艺术史的教学中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从“原作”转移到“原境”。
——《艺术史导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