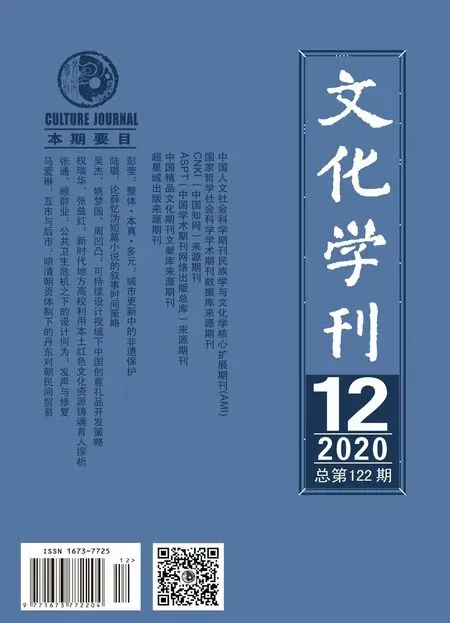蓝鼎元海盗治理措施析论
王华锋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福建漳浦人,年少丧父,家境贫寒,后随族兄蓝廷珍赴台平定朱一贵之乱,对沿海地区社会情况有着深刻理解,“其志存乎世道人心,其心系乎生民社稷”[1]序文6,张伯行曾赞其“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1]行述4。蓝鼎元认为,海盗“非有所谓巨贼,不过一二无赖,饥寒逼身,犯法潜逃,寄口腹于烟波浩荡之际……升平小丑,有何难治!”[2]289-290。因此,蓝鼎元尝试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以图彻底解决海洋不靖的问题。治标是指“练兵丁,选死士,精器械,慎机密,搜丑类而歼之”,治本是指“课农桑,修学校,以养以教,自然不为盗贼”[2]289-290。
一、镇守战略要地
福建沿海“凡二千余里,港澳凡三百六十余处,要口凡二十余处”[3]4111,自古多海盗。清王朝为维护福建的地方安靖,设置福建水师,额定官兵二万七千七百余人,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艘[3]4111,清政府的海防兵力主要集中在海盗多发的泉州、漳州地方。泉州海防重在金门、厦门两地。金门、厦门两地远控台湾、澎湖列岛,近卫泉州、漳州,为海防重地。漳州沿海地区,自九龙江口折向西南,经六鳌港、漳江口,循铜山向南为诏安港口。其南隔海为南澳镇,由于地处闽粤交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漳州海防重地。南澳的重要性,历代多有论述。陈伦炯曾在《天下沿海形势录》中指出:“南澳,东悬海岛,捍卫漳之诏安、潮之黄冈、澄海,乃闽粤海洋适中之要隘。”对此,蓝鼎元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沿海地区的驻防必须选择战略要地守之。蓝鼎元多次论及南澳镇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南澳为闽、广要冲,贼艘上下所必经之地。三四月东风盛,粤中奸民,啸聚驾驶,从南澳入闽。纵横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屿、料罗、乌纱而上,出烽火流江而入于浙。八九月西北风起,则卷帆顺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粤。”[2]289-290南澳岛“厄塞险阻,外洋番舶必经之途,内洋盗贼必争之地”[2]257-258,作为海盗南来北往必经之路,加强对闽、粤两省之门户的南澳岛的防范,对于缉捕海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废除商船军器禁令
1717年2月,清政府实施南洋禁航令,主要措施有五项:第一是控制商船航行南洋,第二是查禁米粮出口,第三是加强对民船的控制,第四是严禁移民海外,第五是严禁携带军器、炮位。其中,第五项的规定渐趋严厉。1719年,清政府规定一切出海船只不许携带军器。1720年,清政府再次规定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其原有炮械、军器具令地方官查收。远洋商船一般都携带大小不等武器,以备不测,如今,禁止海商携带武器,无疑是剥夺商船的防卫能力,遇到海盗袭击,船上人员只能束手就擒,别无他策。蓝鼎元指出,海盗“出遇商船,则乱流以截之,稍近则大呼落帆。商自度无炮火军械,不能御敌,又船身重滞,难以走脱,闻声落帆,惟恐稍缓,相顾屏息”[2]289-290。面对此种情况,蓝鼎元认为,海盗“此等小辈,无他伎俩。但使商船勿即惶恐下帆,又有炮械可以御敌”[2]289-290,即可解决这一难题,因此要求“驰商船军器之禁,则不出数月,洋盗尽为饥,未有不散伙回家者也”[2]289-290。
三、严格巡洋会哨制度,严惩官兵贪腐行为
《防海备览》一书称:“夫防海者,须防之于海,非俟其近岸而防也,盖陆路之窥伺易觉,而海面之跋扈无常,哨船之设,诚为至计。”[4]哨船即为巡洋会哨制度,按照规定,会哨的时间和地点是不能随便变更的,巡洋官员设置方面也有严格规定,总兵为统巡官,副将、游击为总巡司,都司、守备为分巡官。然而,随着海疆平靖日久,将卒疲玩,出现了各种滥行代巡的行为,统巡官或以参将、游击代之,或以千总、把总代之,总巡官或以外委及兵丁头目递相代巡。蓝鼎元指出:“向来各省巡哨,实心者少……每欲出巡,必预张声势,扬旆徐行,一二月未离江干。又于周中旦暮鼓乐,举炮作威。”[2]289-290同时,蓝鼎元还废除陋规流弊:“邑故有渔船四百,每船例四金,新令至,必输金以易新照。”[1]行述13还有部分官兵并不实力擒拿海盗,且以“他邑之盗也”[1]行述15-16互相推诿。由此可见,官兵缉拿海盗并不实心。针对巡哨以及官兵贪污腐败行为,蓝鼎元认为要严加整饬:第一,严查哨船接济海盗事件;第二,及时更换老弱兵丁;第三,选取合适的军器;第四,巡哨以采取秘密行动,不事张扬,或把兵船改装商船,以出其不意之法擒贼;第五,对士兵要恩威并济,使“三军之士,怀德畏威”[2]289-290,提高作战力。
四、开海贸易以纾缓民生
唐宋以来,我国的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就十分发达。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力下降,明政府由此强化了海禁政策。但是,海禁并未起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走私贸易、海盗贸易的盛行,尤其是嘉靖时期的倭寇之患以及明清之际的海盗之患。对于沿海居民而言,海洋经济在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当中央政府实行“禁海”或“开海”政策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就会发生利益冲突,沿海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就随之而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矛盾,封建社会固有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航路被禁,对福建沿海民众影响至深。蓝鼎元指出:“闽广人稠地稀,田园不足以耕,望海谋生者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2]263-264闽浙总督高其倬也指出:“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余利归赡其家属。”[3]10303蓝鼎元认为“弭盗之源,抚民为本”[2]289-290,开海以缓解民生问题是多数地方官的共识。蓝鼎元不仅要求开海贸易,而且要求关注民生问题:“米价腾贵,运载平粜。雨旸不节,斋戒祷祈。又以春秋巡行阡陌,课农桑,择其勤者奖励之……经理海疆之要务,使民无盗之原也。”[2]289-290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地方官兵与地方民众的关系,约束兵丁的不法行为,以顺应民情民心。如此一来,海疆自然平靖。
五、兴学重教改善民风
福建地区民风素来彪悍,轻生死重财利,海盗频出的漳、泉地区更是如此。泉州地区自“正嘉以后,家尚客气,武勇为杰,狂躁为能,负山滨海顽梗险健之夫动务终极,甚则甘心。骈胁多力之雄,如彪如虎,十百为群,依窟负隅,一啸蜂聚”[5],漳州地区游手惰民“凶悍喜斗,睥睨杀人”[6],此种民风已造成闽南地区严重的社会问题。雍正曾下谕旨曰:“朕闻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众盛,欺压单寒。偶因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复逃匿抗拒,目无国宪。两郡之劣习相同,而所属之平和南胜一带尤甚……耳闻目见,皆剽悍桀骜之风,而无礼让逊顺之气。”[7]蓝鼎元认为,福建地区“民风刁悍”是民众下海为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海盗问题,除了施以严刑峻法之外,还应重视民众教化、改造民风,此为治理海盗的根本。“法当知弭盗之源,在乎民风。课农桑,修学校,以养以教,自然不为盗贼,治其本也。”[2]289-290
六、严防接济切断海盗物资来源
蓝鼎元认为,海盗常在海上行走,粮米食物、火药军器等必须依靠接济,接济者多为沿海地区的商贩、渔户等群体。海盗“出没无时,贼与小旗为号,瞭见即为接应”[2]262。沿海民众与海盗的这种“亲密”关系由来已久。宋代,福建地区有这样的风俗:“二广及泉、福州,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8]明代的漳州地区,“一村约有万家,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又聚数千,其冬夏至柘林,今春又满载仍回漳州去矣”[9]。清代的福建安溪人李光坡也曾指出:“舰船必资料粮,伺掠米商能得几何?所恃渔舟,阴载内米,与之交通。”[2]256陈庚焕亦指出:“接济之弊不尽在商船之透漏。窃闻贼船所在,必诱附近村落,负米运水,倍偿其值。愚民趋之若鹜。汛地稍加禁止,贼辄蜂拥戕害,否即抢去汛台炮位,俾以失炮伏法。官弁禁不敢呵,亦势不能阻也。”[2]292-293蓝鼎元进一步指出,官兵哨船是海盗的最大接济来源,此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海盗屡禁不止的根源。“向来南澳地方,皆守港哨船接济,如东陇港、南洋港、樟林港、澄海港、沙汕头、海山、柘林、井洲,各处哨船,无一不接济者。而东陇、海山、南洋三处为尤甚。”[2]289-290他发出感慨:“民船犯禁,官兵可缉;官船作弊,孰敢撄锋?”因此要求“镇将留心稽察,无使敢蹈前辙”[2]289-290。
七、结语
蓝鼎元的海盗治理思想是其长期海疆社会生活和沿海从政工作的经验总结,其能够从沿海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蓝鼎元作为一个普通官员,难以对中央政策产生影响,其提到的巡洋会哨中海防官兵的腐败行为一直无法得以解决,也使得巡洋会哨流于形式,海防形同虚设,乾嘉之际海盗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至鸦片战争爆发之时,清朝海防在英国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也已是注定之事。回看蓝鼎元的治理海盗思想,虽然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是其强烈的海洋意识和现实意义仍值得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