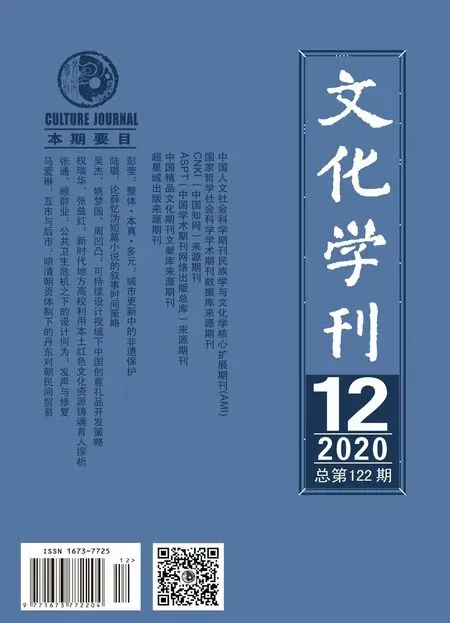略论顾大典戏剧艺术风貌
冯 军
自魏良辅等人拉开昆山腔戏剧改革的序幕之后,戏剧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顾大典即是其中一位。徐朔方评价顾大典戏剧作品说:“他的思想和作品,如同他的为人一样,无论放浪诗酒,或者着重道德教训,都是境界不高,而近于平庸。”[1]264在明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戏剧界,他既没有像汤显祖那样狂飙突进,为至情狂呼呐喊,也没有走向沈璟对格律声调亦步亦趋的境地,而是以自己的戏剧才能中规中矩地进行创作,“无误可顾”(梅鼎祚《与顾道行学使》)地表现戏剧的特征与本质,使自己的戏剧作品呈现出雅俗共赏,既彰显个人特质又凸显时代精神的艺术面貌来。
一、教化与主情并举
莎士比亚曾说:“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2]作为“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实的反映”(西塞罗语)的戏剧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即惩恶扬善,教化人心,抨击、揭露人性的假恶丑,突显、表彰时代的真善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伦理教化功能是中国传统戏剧的规范思维,“风化论”“风教说”经久不衰。吕天成论戏曲“皆主风世”(《义侠记序》),“作劝人群”(《埋剑记》第一出)。王骥德在《曲律》里更指出,戏曲作品“奏之场上,令观者藉为劝惩兴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为有关世教文字”[3]213。高明《琵琶记》“持大头脑处”,讴歌有忠有孝蔡伯喈、有贞有烈赵五娘,明确的创作主旨令其大受统治阶级以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重视,纷纷肯定其作品“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荆钗记》塑造了忠孝节义俱全的王十朋典型形象。丘浚《五伦全备记》更是戏曲教化史上的典范之作。在传统戏曲教化审美规范的熏陶与影响下,顾大典戏曲创作也积极向教化功能靠拢。顾大典戏曲作品有《清音阁传奇》四种,《青衫记》《葛衣记》今存全本,《义乳记》残存佚曲、《风教编》已佚。《青衫记》叙写白居易与裴兴奴的爱情故事,肯定裴兴奴情有独钟,白居易此情不渝。《葛衣记》谴责到溉忘恩负义,赞扬刘孝标义干云天、慧娘忠贞守节、任西华忠孝节义。《义乳记》褒奖义仆李善忠心耿耿,抚养幼主。《教化编》虽佚,但从篇名仍能明显感觉到顾大典宣扬教化的创作意图。
顾大典(1540—1596)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明史·世宗纪》卷末记载:“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4]在激荡的社会氛围中,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既有积极主张复古以求改变世道人心的复古主义思潮,也有主张性灵彰显个性解放的思想。顾大典一方面同复古领袖王世贞多有交往,在文学创作上倾向复古。他的传奇作品皆以历史人物事件为素材,思想上强化传统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顾大典也尊重个性与情绪的表达,在风化的外衣下主张性灵,体现了他个人的主体价值与生命体验,展现了时代的精神与风貌。顾大典本身就是一位较为张扬自我个性的文人。万历十五年(1587),顾大典因放荡风流,遭人弹劾被贬禹州,不赴任而退职还乡,建谐赏园优游生活,也常组织家乐演出自己创作的戏曲作品。在顾大典的传奇中我们看不到明初如丘浚《五伦全备记》等作品的酸腐气、伦理教化的僵化教条,同时也感受不到汤显祖《牡丹亭》那样为情至上的“异端”思想,而是以包容中正的态度来对待爱情婚姻与人情世态。在《葛衣记》中,顾大典对忘恩负义者的态度不是鞭挞,而是理解宽容;在《青衫记》中,顾大典以理性态度对待爱情婚姻,以团圆为结局。顾大典善于优化传统美德,消解人生悲剧,体现了内方外圆、内圣外王的生活之道。
二、音韵宽严适中
亚里士多德说过,戏剧包括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其中“唱段是最重要的装饰”[5]。不仅西方的戏剧重视唱段,我国的戏剧也是以音乐为本位。戏剧家必须按韵依谱进行写作,以达到“合律依腔,便于歌唱”,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均为古代度曲的圭臬。昆山腔改革奠基者、实践者魏良辅、沈璟更是严格格律曲调的积极提倡者与施行者。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论及昆山腔演唱时说:“五音以四声为主,但四声不得其宜,则五音废矣。平、上、去、入,务要端正。有上声字扭入平声,去声唱作入声,皆做腔之故,宜速改之。”[6]沈璟对曲谱要求更加严格,他说:“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怎得词人当行,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7]。
顾大典出生成长在讲究韵律与腔调的昆山腔发源地——吴江,与“纵使词出绣肠,歌称绕梁,倘不谐音律,也难褒奖。耳边厢,讹音俗调,羞问短和长”的沈璟年龄差12岁,是同乡,平时交往也较为密切。“兼有顾曲之嗜”的顾大典也是非常看重戏曲音律这一传统的,并付诸行动。恪守吴江派家法的沈璟之侄沈自晋在其《南词新谱》中选录了顾大典《风教编》中的曲子,如《朱奴剔银灯》《园林沉醉》。同时代其他记载音乐声谱的书籍如《群音类选》等也摘录节选了顾大典诸多曲子作为创作的范本。由此不难看出顾大典对音律的重视与讲究,并得到了同时代音律家的肯定。
但他并没有走向魏良辅、沈璟等人对格律声调孜孜追求的境地。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说:“顾道行先生亦美风仪,登第甚少。曾一就教吾越,以闽中督学使者弃官归田。工书画,侈姬侍,兼有顾曲之嗜。所畜家乐,皆自教之。所著有《青衫》、《葛衣》、《义乳》三记,略尚标韵,第伤文弱。”[3]225“如《青衫记》第五出鱼模、齐微、支思混用,第八出用先天韵而《破阵子》弹字是寒山韵,《六犯清音》掩字是廉纤韵。”[1]265张凤翼也说过:“(《青衫记》)中间有数字未协,僭为改定。……君即欣然诺之。”[1]265上述事例说明顾大典讲究格律,又不太注重格律的绝对工整严密,但不像汤显祖那样只注重内容而忽视形式,而是持中庸的态度,在内容与形式的重视与不重视两极之间,过犹不及在他这里并不存在。
三、风格雅俗共赏
“昆曲的曲子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歌舞等综合伎艺中,特别注重歌唱和曲子。二是它不仅以‘剧’的面目出现,而且还以‘曲’的形式生存,即既有‘演戏’的形式,也有‘唱歌’的类型。”[8]用于歌唱的唱词是戏剧的关键与灵魂所在,每一位戏剧作家都注重对唱词的精益求精。
顾大典在传奇唱词中也倾注了他的努力与追求,雅俗共赏的审美范式是其具体体现。如《青衫记》书写白居易与琵琶女的故事。白居易文人气质浓郁,唱词典雅清丽。如【坐湿青衫·北新水令】“鲲弦铁拨紫檀槽,断送了许多年少,空林惊宿鸟,幽壑舞潜蛟,切切嘈嘈,写不尽相思调。”而裴兴奴琵琶女的身份决定了顾大典对她唱词的设计则是通俗浅显,明白晓畅。如【裴兴私叹·普天乐】:“我性儿焦,心儿躁,怪得我家生得俏,家生俏忒恁妆乔,把歌和舞镇日轻抛,教咱怨着,竟不顾我凄凉门户发萧骚。”王骥德《曲律》卷二《论家数第十四》说:“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3]118顾大典戏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浓淡相宜、雅俗相间的审美风格。
“传奇,非奇不传。”传奇作品的核心内容是传写奇事,最重要的是情节离奇,关目好。在戏剧内容与情节上,顾大典也在深与浅、媚俗与文人教化方面做到了相得益彰。他在戏剧创作中积极继承、发扬了传写奇人奇事的传统,注重戏剧关目的新鲜离奇,情节的迂回曲折,人情物态的变化移转。如《青衫记》人物际遇的千回百转,《义乳记》人物遭遇的大起大落。再如《葛衣记》中任西华得神仙之法,开天门,裂地府,召天兵天将;刘敬恭剪纸成兵。不过,新奇热闹形式包孕的题材内容却是老生常谈,缺乏创意。
顾大典戏剧雅得细致,俗得热闹。雅俗相间的风格特色既没有使戏剧走向案头孤芳自赏,也没有脱离群众与舞台,而是在中和之道中使两者达到平衡。
总之,顾大典传奇作品不同于元杂剧对时代的揭露与批判,也不同于南戏有关风化体的极端张扬,而是主体自由平和甚至带有些许文人优越感、责任感地去抒写。提倡传统美德,消解人生悲剧,体现内方外圆、内圣外王的生活之道。顾大典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与创作实践影响了李渔的热闹与商业化倾向,启迪了《桃花扇》理智情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