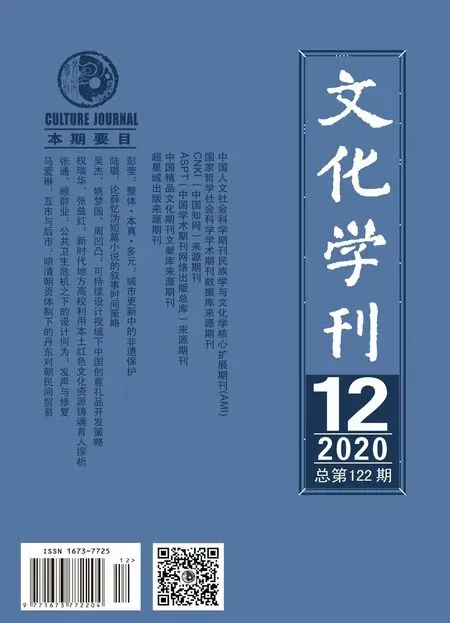信仰内核的嬗变与民俗文化的传承
——以晋东南“二仙、成汤、三嵕信仰”为例
白美云 赵振焕 路 恒
晋东南即山西省东南部,古曰“上党”。该词初见《国语》,秦统一后始设上党郡,至两汉与今天的地域大体相当,隋唐改置为泽潞二州,后随历代发展,范围名称几经变化,现包括长治、晋城二市。这里群山环绕,地势险要,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神话传说,留存了众多的明清乃至宋金以前的古寺庙,积淀了淳朴厚重的民风民俗,可谓山西民间信仰的核心地带。
“民间信仰”亦称“民俗宗教”,1897年由日本学者姊崎正治提出,指潜伏栖生于地域社会底部与正统的组织宗教相对立的信仰习惯,它无教祖教义,不成体系,受共同体生活限制,具有很强的地域性[1]。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2]。民间信仰作为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与中国乡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互生互长,呈现为祖宗崇拜与地方性神灵信仰两大系统[3]。由于本文以祠庙为载体,探讨民间信仰与民俗传承,故采用“祠神信仰”一词,“祠神信仰”可以说是狭义的“民间信仰”。说到这个词,更多人想到的是“迷信”,但这种信仰中亦包含有“合理的习惯”[4]。其信仰形态以“小庵小庙”为载体,根植于地域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既包括民众对超自然力及其精神体的崇拜,也包括由此产生的原生态民俗[5]。
一、祠庙分布与信仰的产生
作为地域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综合,祠神信仰物化为一座座庙宇,晋东南地区古祠庙遍及城邑乡里,几乎“村村有庙,户户敬神”,不少村庄有四五座庙,其中一村中气势宏大的庙称为“大庙”。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众多祠庙,彰显出泽、潞二州祠神信仰的地域性、兼容性、多样性与广泛性,也反映出当地民众朴素的生活愿景。
(一)二仙信仰
二仙庙以陵川、高平、壶关为中心,遍布晋东南地域。二仙信仰历史悠久,作为地域性俗神,二仙传说丰富多彩,当地流传较多的二仙本为唐末潞州壶关普通农家乐氏二女,天资聪颖,后母虐待刁难,但二女纯孝不渝,因“至孝感天”幻化成仙,自此兴云布雨、圣迹频现,每逢大旱,乡民祈祷,必降甘霖。宋徽宗崇宁年间,曾显灵于边戍,助宋抗夏,鬻饭救度军将,被朝廷加封为冲惠、冲淑真人,庙号真泽,始派官员祭祀[6]。明清时期二仙被赋予更强的神力,擢升为以布雨为主,集医药、生育、守护等多种神职于一体的全能神[7],形成了以孝德为核心,壶关紫团山真泽二仙庙为祖庭,遍布晋东南的民俗信仰文化体系。
(二)三嵕信仰
三嵕信仰发源于屯留,后主要向南流布,以长子、高平为盛。三嵕,本山名,“数峰并峙曰嵕”,《新唐书》卷43《地理志》载:“屯留,上有三嵕山。”碑载:“逮宋崇宁间,缘屯留县申请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郡守敷奏于朝,敕赐三嵕山,以‘灵贶’为额。”说明在宋崇宁年间,原始的山神三嵕受朝廷敕封,成为正祀之神。在其后的传播过程中,逐附会上古英雄——羿神,有关羿的身份界定有三,当地人普遍认为三嵕主祭之神为射日羿神[8]。明洪武间改号“三嵕山之神”,有司岁祭,复以山名为神名。清代长治三嵕庙“在城西街,祷雨多应,俗以为神司冰雹,故农民祀之最诚,乡村建庙甚多”[9]。可见,三嵕神在历代发展过程中已由射日之神变为致雨司雹之神,行祠遍布各州县。
(三)成汤信仰
成汤神庙群落众多,相对集中于阳城、泽州、高平,汤帝行宫以阳城为最,达76处。汤本为商开国君主,但民间流传的此信仰并无政治因素,而是源于古老的雩祭。雩祭即祈雨,《尚书》《论语》等典籍记载:为救困于七年大旱之黎民,汤以己为祭品,祈雨于桑林,燔柴焚身之际,至诚之心感动上苍,终普降甘霖。祈雨圣地——桑林,被认为是阳城境内的析城山[10]。至宋,汤帝祷雨的具体地点首载史册:“析城山,在县西南七十五里。应劭注《汉书》云‘析山在阳城西南’,即此也。山领有汤王池,俗传旱祈雨于此。”[11]建汤庙祈雨,可溯至唐[12]。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赐“广渊庙”敕额,封析城山神为“嘉润公”。之后开始大规模营建汤帝庙祈雨。汤帝历代都以赐雨润民为主要职能。
以上传说故事,或为行孝之女,或为上古英雄,或为古之帝王,因能“御大灾、捍大患”,徽宗时,这些人格化祠神被国家封祀,开始纳入皇权支配的国家信仰体系中。之后,其信仰形态随陆路、水路向周边扩布,受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影响,同时受各地已有神灵的牵制,形成了一个个既相对封闭又开放的祭祀文化圈。各祠庙以主神为中心,神神共存、各司其职,福佑一方。宋末,晋东南地区乡村神庙系统已初具轮廓[12]。
二、信仰成因与民俗表征
(一)祠神信仰的缘起
二仙、成汤、三嵕信仰在唐末北宋就已盛行。作为覆盖晋东南广泛地域的地方文化事象,深深根植于该地域社会的生活土壤,是特殊社会环境、文化生态下民众的自然选择。
“上党,……以其地极高,与天同党”而名。因其地高燥,掘地三千尺犹不及泉,山多地少,灌溉不易,故农事艰难。据史书、碑刻资料载,该地干旱连年不断、大旱隔三岔五,“开元十二年(724),泽、潞大旱,帝设坛宫中,亲祷暴立三日”[13]7。“土地干燥,不能下种,四月至十月无雨,河干井涸,颗粒无收”[14]。清代更是大旱连年,在1401—1900年,共发生旱灾117次[15]。
位于今晋城高平市河西镇西李门村二仙庙内的《记荒警世碑》记载了光绪三年(1877)当地人民生活的惨象:“丙子春亢旱,夏无麦,秋禾半。丁丑春徂夏。旱既太甚。……而高邑亦成灾之区也。”“且又有杀子女以省米食,更有父食子,兄食弟,夫食妻,妇食夫……饥饿频死之人,遂窃抱而煮食,诚不乏矣。”碑中所言“高邑”,即现高平市,因干旱导致人食人现象发生。
农业文明的先天不足,古代科学技术的落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困惑,只能将自身的生活需要祈求于超自然力的神灵。严重的旱情使得晋东南“雨神”信仰极为发达,二仙、成汤、三嵕神均被赋予司雨功能,反映了民众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朴素的生活愿景,也体现了祠神信仰现实功利的特点。
(二)信仰的民俗表征
留存至今的大量庙宇既是民众对地域神灵信仰的积累与体现,也是进行春祈秋报的重要场所,更是信仰持久传播的有力载体。至迟在唐末,晋东南已经开始筑庙祷雨;宋代至清,每逢大旱,地方官员亲自虔诚祈雨,以求普降甘霖。出于对神灵的敬畏,形成了诸多的年年轮转、代代传承的祭神、娱神仪式,催生出当地悠久繁杂的迎神赛社民俗,成为古老祭祀中鲜活的生命形态。
1.迎神赛社
上党地区的赛社很多。“赛社”,泛指报谢神明的祭祀活动。神庙中集乐户歌舞神前曰“赛”[16];“社”字的本意为“地祇”,即土地神,祭祀土地神的场所也被称为“社”。传统的赛社活动都依托庙宇进行。“赛社”一词晚至南宋出现,上党地区的赛社亦渊于宋,盛极明清,衍及民初[12]。
作为北方迎神赛会的缩影,2006年贾村赛社入选首批国家非遗名录,因其保存较为完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民间赛社抄本。光绪本《排神簿》中所迎请的各类神祇,大唐冲淑真人、冲惠真人(二仙)、护国灵贶王(三嵕)各出现6次[17],足见民间祠神在当时的影响力。
传统的赛社活动大都在春夏,为期6天,一般要举行下请、迎神、享赛、送神等仪式程序。享赛分头赛、正赛和末赛,主要表现仪式为在正殿神前供盏,即向神上香供馔。头赛一般在献殿举行,之后转移到神殿对面的舞楼。供盏次数为“前七后八中十二”,最后一盏朝太阳,共二十八盏。每供一盏都是礼节繁杂,音乐不绝。祭祀奏乐体系承袭了唐宋乐曲[18],庙内乐户上演的祭祀酬神戏剧的演出形态有宋金遗存的队戏(如《过五关》《斩华雄》《鸿门宴》《长坂坡》等历史故事)、院本(如《土地堂》《三人齐》《错立身》《闹五更》等),元明杂剧(如《虎牢关》)等。服装原始粗犷,道具极为粗糙,赛社成为了解宋元以来晋东南社会的活史料。
可见,赛社滋养丰富了信仰,它们深深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成为该地域重要的文化标识。
2.众多的庙会
古代中国有神就有庙,有庙就有会。晋东南庙宇星罗棋布,成就了大大小小的庙会。鼎盛时期,该地一年内的庙会多达千余,现仍留存大半。庙会是以庙宇为依托,以民间信仰为核心,在特定时空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民俗活动[19]。陵川小会岭二仙庙内碑文记载了当时庙会的盛况:“每四月十五日,演戏成会,百剧并陈,一时车马辐辏,士女缤纷,亦可谓极盛云。”时至今日小会村、黑土门、神眼岭等6村村民或独办或联办庙会,在庙前搭台唱戏以祭祀二仙。荫城镇的村民们也在这天手持灯笼、沿途供香,将二仙神像抬出来巡游再送到邻村,称为“十转赛”。《潞城县志》载:“祀三嵕,仲春仲秋上戊日,县官具鸡豕致祭,仪如明宦。五月朔日、六月六日,民间献荐馨以祀,有司□□拜如常仪。”[20]六月初六是三嵕神的生日,这一天各地三嵕庙大都会举办祭祀和庙会,上香供馔,隆重有序。汤帝庙会更是传承久远,大致固定为每年的春祈秋报时,农历二月二或五月十二迎神献供,七月十五或九月初九秋报感恩[21]。在阳城析城山,人们会将南峪村的木质“汤王走像”抬入各村汤帝庙祭拜供奉,等庙会结束后送还,整个场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祭祀是歌、舞、乐的自然结合,只有通过音乐、演剧才能达到酬神、娱神的目的,完成礼的传播。演剧丰富了庙会,庙会传承发展了演剧。在目前我国的348个剧种中,山西省现有剧种38个,排名第一[22],八音会、上党梆子、上党落子、潞安大鼓、上党二簧、眉户等都被选入国家非遗名录,不能不说这与庙会祭祀仪式有很大关系。
庙会还为耍铙钹、高跷、抬阁、旱船、扛桩、打铁花、舞龙、舞狮、竹马、打鞭等形式活泼、精彩纷呈的传统民间社火表演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空间,长治市潞城县的民间社火更是闻名全国,入选国家非遗名录。庙会还孕育了彰显地方文化色彩的风味美食,以及皮影、面塑(阳城)、布艺(黎侯虎)等传统手工工艺。可以说,庙会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民俗,民俗滋养了信仰,信仰为庙会之魂。
三、新时代的祠神信仰与民俗传承
如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而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应该是文化。民俗文化作为乡村重要的传统文化,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民众长期积累、创造、形成、传承的风俗习惯[23]。信仰作为民俗文化之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融为一体,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要想发挥民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就有必要辩证地认识祠神信仰,兴利革弊,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合理的文化重构,革故鼎新,以期被良性地长久传承。
(一)传故育新,服务乡村振兴
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祠神信仰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与不足,因此,需要去伪存真,仔细甄别。二仙、成汤、三嵕信仰自唐始传承千年,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积淀最深的文化类型之一,不可否认亦包含着丰富的可为今用的伦理价值[24]。嘉庆五年(1800)《重修真泽宫碑记》载:“二仙真人,其忠孝之精诚。”长子县阳鲁乡成汤庙康熙七年(1668)《重修商汤圣帝庙记》载“商汤圣帝神……祷雨以苏百姓……本村立庙祀之,岁以报赛相祀也。”二仙的仁爱孝悌、谦和好礼,三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成汤的为社稷献身、体恤民情、惩恶扬善精神,具有催生个体向善、推动社会向善,形成“善村善乡”的社会作用[25]。
在传统民俗文化与我们渐行渐远的今天,不少年轻人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总体上反应迟钝、情绪淡漠,甚至对传统民俗活动存在排斥心理。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因此有必要让他们认识到民间信仰在规范世俗人心与民众价值取向方面的积极作用,克服自鄙心理,树立自珍意识。同时还要树立“俗因时变”的理念,在讲好地域故事的同时融入中国梦,使民俗活动常过常新。
目前,贾村正在打造“上党赛社第一村”的文化品牌,在全国的影响日渐广泛,如何利用这一文化名片,串联更多的文化因子,营造地域民族文化氛围,并赋予信仰新内涵,注入民俗新活力,构建富有时代特点的新民俗,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文化群体,使他们自觉内生文化诉求,形成新的群体效应,是民俗传承时应该思考的。同时,还要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积极宣传,让民俗走出地域、走出国门,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让古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软实力。
(二)时空、人际错位,融洽、秩序乡井
历史上,民间信仰与民俗活动杂糅互构,曾作为古代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力量,成为乡土文明的关键部分[26]。自古以来,晋东南的迎神赛社都以村落为单位,通过敬神娱人的民俗活动,将不同社会身份、不同经济利益的人聚集起来,实现了神与人的对话,人与人的互动。既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又凝聚了人心,达到了增强地域认同感与归依感的社会效应。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祠神信仰受地缘关系影响显著,在安土重迁的社会环境下,多采用家庭或村落“世袭”方式不断传承。例如:清末民初,长子县著名的迎神赛社主礼——东大关村牛振国,祖上五辈人均担任过大赛主礼[27]。
今天中国正进行着亘古未有的大变革,乡土中国逐渐转型为城镇中国,农地关系松弛,年轻人逐渐从乡村流向城镇,聚集于附近都市圈,由务农转变为务工,作为民俗传承的主体,参加祭祀活动、表演的时间受到限制,而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农村,空心化严重,参加、主持民俗传统节目者日益衰老,传承人力资源缺失,承载民俗文化存续的基石岌岌可危。
再者,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中关注精神文化的群体逐年递增,国民文化意识不断高涨,文化素养日益提高。因此,可以考虑将民俗活动的日期错位,由固定日期调整为节假日,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便于都市居民爱好者参与村落民俗文化传承的仪式,通过祭拜获得精神的慰藉、心理的安宁;在狂欢中释放平日生活之压力,感受神圣,忘掉俗世烦忧,增加生活的动力与信心。同时,建议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允许有兴趣的周边、外地人员参与民俗活动项目,完成超人际的转变。乡村振兴换言之就是让乡村充满活力,因此需要让这些传承久远的民俗活动继续焕发凝聚人心、缔结乡井情结的功能。
目前,赛社庙会活动少则三五天,多则半个月,从本研究小组采访壶关县真泽宫信众来看,二仙庙会盛况空前,自农历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近半个月的庙会,加上前期准备工作,耗时耗财,减少庙会日期,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使新时代的民众乐于传承。
四、结语
地域民俗文化是农村传统文化的底色,是该地域社会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长期以来该地域伦理价值与道德情操的体现。目前,国家、地方政府将民俗文化视为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如何挖掘民俗文化之魂——民间信仰中的隐性积极因素,传旧立新,服务于乡村文明建设,还需要不断尝试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