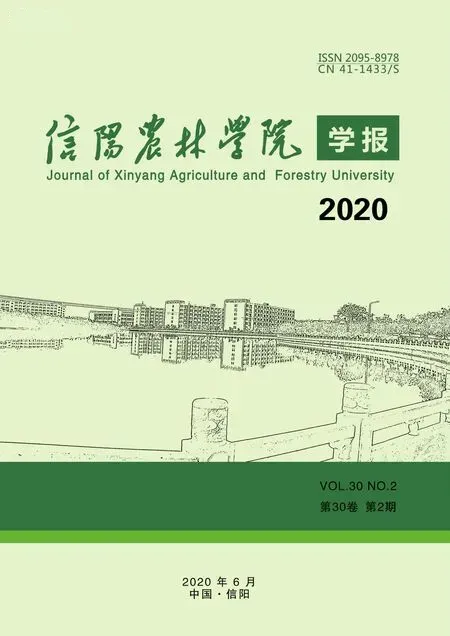科拉快跑:《地下铁道》之魅探析
李忠
(信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科尔森· 怀特黑德创作的《地下铁道》于2016年8月出版并迅速风靡欧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于2016年获得美国图书小说奖与亚瑟· C·克拉克科幻文学奖,2017年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同年还获得英国曼布克奖。小说并未从传统黑人小说“殖民身份”建构出发,而是运用一种“妄想式”架构,给广大读者展现出一段快跑“美国历史”的穿越幻想,展现出科拉追求生命自由、打破自身宿命的勇气,用一种逃离与反抗来自愈内心创伤,迎接生命成长之魅。
1 逃离种族极权黑暗
1.1 逃离种族极权之恶
怀特黑德在小说中追忆了女主角科拉外祖母阿加莉悲惨的一生,用一种电影快镜式手法呈现了美国黑奴的囚笼处境。阿加莉在西非村落被抓捕,送上黑奴船,甚至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到达美国之后,种植园恶劣的条件与不断的奴役买卖让她失去了自己的历任丈夫与全部子女。在奴役制度下,阿加莉一生无法逃脱颠沛流离的命运,最终死在那片铺满黑奴鲜血的棉花田。怀特黑德描写种植园中的科拉,并没有用浓墨重彩去正面展现黑奴被虐场景,而是用冷静文笔写下读者无法忍受的黑奴悲惨遭际。一群女黑奴如同牛羊一样被圈养起来,根据奴隶主实际需要进行繁殖,用所谓战略节育来控制黑人的数量,从而消灭那些低劣的基因。科拉承受着在棉花地里的繁重劳动,时常要遭受恶毒的鞭刑和轮奸,奴隶主在血腥的棉花地里释放着最为原始与野蛮的欲望[1]。种族极权之恶还体现在黑奴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保证。美国1850年颁布《奴隶逃亡法》并规定:黑奴一旦逃亡北方,南方的奴隶主可以把奴隶抓捕回来,逃奴一旦被抓通常会受到非人的对待。小说中的逃奴安东尼被抓回,被全身涂满油脂架在一个支架上,就像圣诞节烤火鸡一样放在火上慢慢烘烤,为了警醒,让其他黑奴一旁观看。怀特黑德这部小说从多个方面揭示了美国黑奴的生存困境以及种族极权之恶在美国南方社会的具体表现。
1.2 逃离种族极权之平庸
1.2.1 平庸之罪 人的平庸之恶正如《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描述:“人之极权之根本恶来自于人性动机的起源,平庸之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2]《地下铁道》中所体现的极权的平庸之恶在于奴隶制下美国白人的无思辨、无判断、盲从性而产生的犯罪。平庸是当代人生活的一种常态,平庸的盲从会做出违背社会正义与道德之事[3]。《地下铁道》中黑奴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白人至上”成为众多白人的至理名言,任何白人碰见逃亡的黑奴都有举报与缉拿的义务,提倡废奴的白人无疑违背当时的社会意志。科拉与西泽逃亡途中,偶遇一群打猎的白人,这群白人蜂拥而上,最终导致流血惨剧。这群白人猎人与科拉的主人毫无交集,却做出如此“正义之举”,就是把种族极权专制看成社会正义性存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白人蓄奴主也会对自己同胞痛下杀手。如蓄奴者里奇韦得知一对白人夫妇帮助逃奴,带人包围白人夫妇的房子并一把火烧了,黑奴与白人夫妇都死于那场罪恶之火。在种族极权下,里奇韦只是工具人,他机械、盲目、服从,他的作恶无思辨与主观、独立价值,本质上是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奴仆。文中一个白人小女孩深受“白人血统最为高贵”的思想侵扰,对逃奴充满各种敌意假想,学校从小就教育她“看见逃奴就要报告,不然不是乖孩子”,当她发现父母藏匿黑人逃奴时,主动向上级告发,导致父母被捕,黑奴惨死[4]。小女孩盲目接受种族极权教育从而树立起种族主义世界观,应有的善良与童真被打破,犯下平庸之罪。
1.2.2 被规训的灵魂与肉体 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福柯提出两种人被规训的意象:一种建立在暴力刑法基础上的规训—封锁,另一种建立在全景敞视主义下的规训—机制。与暴力刑法规训—囚牢比起来,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让权力施压承担起责任,让权力的操作变成高速又经济的规训机制,从而实现“人的精神对精神的权力”[5]。美国南方社会奴隶主把持话语权,建立一种全景敞视主义规训,《地下铁道》中科拉搭乘地铁路过不同的蓄奴州,向读者展现种族主义用多种形式规训黑人的身体、精神与认知行为。《地下铁道》中科拉出生在佐治亚州,在这里黑人背负沉重的劳动作业,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监工与奴隶主的虐待。蓄奴主宣布对黑奴的绝对占有权,被规训的黑人无法反抗,心生畏惧,从而由内到外地进行自我劝诫,就像科拉外祖母在充满血的棉花田中学会“服从”才能苟延残喘一样,想逃脱这里几乎不可能。除开肉体上的规训,还有对黑人精神的阉割与认知的扭曲。完全剥夺黑人的受教育权,不断从认知上告知黑人是白人的私有财产。如黑人男孩霍顿对蓄奴者里奇韦非常信任与依赖,被里奇韦花五元买回,第二天里奇韦给他自由证书,他不但没有享受自由反将自己打扮成车夫,一旦里奇韦抓回逃奴便协助运输,对黑人同胞毫无怜悯之情。霍顿每天睡前用小手铐把自己锁在车倌位置,钥匙放入口袋,才敢睡觉,正是白人至上理念对黑人自由追求的欲望阉割殆尽的体现[6]。
2 穿越时空隧道的抗争与疗伤
2.1 强权下的抗争者
《地下铁道》故事中,科拉要守护外婆与母亲留下的遗产,被阿娃与工头摩西达成交易将她赶到伶仃屋。同时年轻黑奴布莱克看中科拉的小木屋与菜地,发生狗屋事件,充分反映出在美国种族时代的强权暴政,不仅仅是蓄奴主的强权,还有同族的互相欺压。《地下铁道》中佐治亚与北卡罗纳都实行的是“残酷生命掠夺政治”:一方面奴隶主通过极端的压迫剥夺奴隶人身自由,将他们作为私人财产占为己有;另一方面蓄奴州政府通过煽动性言论发动平庸群众不断摧毁黑人力量,用一种规范化原则对黑奴进行“生命管理”。在佐治亚棉花田与种植园中,黑奴的死亡就像捏死一只蚂蚁般寻常。通过科拉视角呈现给读者一个人间炼狱:“一个男黑奴被打死吊在树上,任凭乌鸦与秃鹰啃食,女黑奴被鞭笞露出森森白骨,无论是她死或者生都通通被架在柴火堆上灼烧。为了防止黑奴逃跑,给他们脚镣与手链,更严重砍断双手与双脚。”[4]科拉自身也被特伦斯用狼牙棒击打,第二天按“老规矩”用辣椒水清洗伤口,科拉深深明白在这白人世界迟早要被折磨致死。当科拉逃到北卡罗莱纳时,蓄奴主不分老幼与男女,将奴隶折磨致死之后,如胜利猎物一样挂满名为“自由小道”两侧的树桠上。死者中甚至还包括支持废奴的白人、帮助奴隶者与奴隶同情者。在这样的强权暴政下,科拉“三码见方”的领地被抢夺时,她拿起斧头自我捍卫,当切斯特遭受来自奴隶主的鞭打时,她见义勇为护住男孩。她为自己的生命抗争,一路从北卡罗莱纳、印第安纳到达象征自由的北方。
2.2 苦难历史疗伤者
创伤在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指成人在儿童期的生活经历对其以后的成长与生活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个体所受到的刺激超过自身控制力时就形成一种创伤感。科拉的精神创伤开始于十岁时母亲梅布尔不告而别,接下来是佐治亚州棉花种植园被限制自由与狗屋事件,以及在逃离期间遭遇各种不公平待遇。尽管科拉在19世纪残酷奴隶制度压迫下经历种种伤痛,身心饱受摧残,但她没有就此消沉,而是踏上了一条自我拯救之路。黑奴泽西与科拉一起逃跑时,在他眼里科拉是力量与自信、优雅的化身,当看见黑人小奴仆遭受鞭笞,其他黑奴冷眼旁观,“只有科拉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孱弱的身体做了小黑奴肉盾,承受来自主人的重击”,泽西相信科拉不但不会成为他逃亡过程中的累赘,还能成为最好的伙伴[7]。泽西与科拉逃亡过程中,科拉是泽西在地下铁道逃亡的“火车头”,如果没有科拉,二人的逃亡不会成功。从泽西的视角来看,“只要是科拉认准方向,要定的事物,不管多么微小,她都懂得它珍贵之处”[4]。
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打破了白人至上文学作品中黑人女性愚钝的刻板印象。科拉这位黑人新女性具有正能量且乐观积极,面对命运的磨难与创伤,她丝毫不乱,积极应对一切。当科拉逃亡到北部并且在“自然奇观博物馆”谋求到一份工作,她不满博物馆展演的白人发迹史,要求表现从“种植园”到“运奴船”再到“非洲大陆”,只有这样展演才能让科拉产生一丝慰藉:“非洲腹地是所有黑人的生存之根,她为自己是黑人无比骄傲。”[7]科拉通过抗争命运束缚来舒缓自己的精神创伤,实现内在心灵的复原。
3 生命乌托邦空间构建
3.1 生命安全驿站
《地下铁道》将科拉对生命自由的追求浓缩在她的逃亡过程中,同时每遇一州怀特黑德就给她建构一个真实而奇幻的空间。这种虚拟物理空间无疑与福柯的幻觉异邦理论相契合。异托邦是在当前社会机制真实存在的局部化空间场所,用边缘视角去窥探当前整个社会全局,深挖隐藏的隐蔽权力关系与文化理念[8]。《地下铁道》对福柯理论的实践体现在以白人为主流的文化中黑人族群彻底丧失生存权利,白人掌握主流话语权,小说从棉花田、博物馆、监狱等局部空间展现黑人族群被排斥与压迫的绝望,怀特黑德给科拉制造幻觉异托邦无疑是这个群体向往的生命安全驿站。福柯认为幻觉异托邦来自于一个最完美的空间,但这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乌托邦,只是对现实社会的合理补充[9]。怀特黑德在小说中为科拉建构了三个生命安全驿站,每个生命安全驿站都是一个短暂美梦。
科拉搭乘地下铁道从佐治亚到南卡罗来纳时,她重获新生并在这里获得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在安德森家中做保姆。虽然南卡罗来纳也是蓄奴州,却比佐治亚环境宽松很多。科拉下班之后,可以去商店观赏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用工资买一条蓝色裙子,有休息日,甚至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软床。这是她以前在佐治亚不敢妄想的。怀特黑德用大量对比手法,从科拉视角将南卡罗来纳塑造成黑人作为自由人的生活模式并能接受教育、参加聚会,这与佐治亚奴隶制种植园模式形成巨大反差,无疑是怀特黑德给她打造的幻觉[10]。
科拉逃到北卡罗来纳后,白人马丁·维尔斯让“她躲在屋顶上狭小密室里,这里从地板向上逐渐变窄,高不足一米,长也仅有四米五”,“墙上仅有的小孔是光和空气的唯一来源”。此地对于黑人极端排斥,甚至维护黑人的白人也会遭受杀害。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仇视黑人,因黑人想摆脱束缚,追求自由,同时黑人数量迅速增加逐渐威胁白人的生存空间。读者从科拉视角借助狭小气孔窥探公园每周五上演的抓捕黑人戏剧,同时此处也是处决黑人之地。狭小空间挤压着科拉的行动空间与精神空间,怀特黑德替她建构了一个温馨梦幻空间:“她到达北方,有一个明亮的家,房屋设计漂亮,围绕她的是温柔的丈夫与可爱的孩子。”这种平凡温馨的家庭生活对于身处奴隶制的科拉无疑是幻想,反衬现实中科拉的悲凉处境[11]。
科拉在田纳西州被里奇抓住,后面巧遇自由人罗亚尔。罗亚尔救出科拉,随后两人一起搭乘地下铁道前往印第安纳州瓦伦丁农场。印第安纳州瓦伦丁农场的黑人都是自由民,生活条件优渥,有着较高文化涵养,科拉在这里开始学习文字,住属于自我的单独房间。瓦伦丁的黑人原本一直过着幸福生活,但是他们冒着生命风险为被压迫的黑奴到处奔走。科拉与他们结交越深,越能体会来自灵魂层面的启迪,让她明白:“只有不断追求自由与解放,才是生而为人的一种权利。”这是她第一次体悟“人”的权利,黑人崛起只能靠自身。
3.2 异托邦精神空间
福柯所撰述危机异托邦理论是指弱势群体在身处危机状态下提供给他们特定边缘性空间的安全庇护所。怀特黑德笔下为科拉建立起三个异托邦精神空间。
在南方佐治亚州种植园遭遇无数鞭打,只有伶仃小屋与小菜园是她身体与精神的安全庇护所。伶仃屋是保护科拉的危机庇护所,而科拉的精神世界则寄存在小菜园。小菜园不足三平方,它是科拉一点点开垦出来的,打理小菜园时的科拉精神状态异常放松。科拉逃亡中的地下铁道非常隐秘,专门庇护黑奴逃出种植园,去往北方自由州。怀特黑德四次用科拉逃亡时乘坐地下铁道的空间秩序构成危机乌托邦空间,地下铁道由无数人用鲜血与汗水铺排出来,专门为黑奴而建立,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它虽然深藏于污浊地下,却是光明与自由的象征,给无数黑奴带来新生的希望。在《地下铁道》北方被多次提及,科拉最初逃亡的终点就是北方自由州。怀特黑德小说最后的描写不多,但是足够建立一个宏大层面的危机乌托邦,让人们看到善良的光芒从未熄灭,以黑人为代表的边缘人终于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4 成长生命之魅
4.1 追寻自由
主人公科拉从佐治亚出发,路经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印第安纳,最终跑到象征自由的北方。科拉在这场充满艰险的逃亡之旅中经历人性的险恶、不公的法律,以及随时被抓捕的风险与社会暴力,但从未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她穿越了整个美国,最终到达象征和平的北方。当她到达北方时,用尽生命之力大声喊出:“我是佐治亚的,我跑出来了。”对自由的决心与追求正是黑奴解放运动的能量来源。怀特黑德借助科拉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美国追求自由的决心与勇气[12]。
当科拉逃到南卡罗来纳后,虽然获取了自由,黑人可以读书识字,衣食无忧,周围人们待黑人也十分亲厚,过着舒适的日子。原本打算一路向北的科拉也沉溺于短暂的自由和平生活中。但这里的白人只是给他们有限的自由,尤其是经历博物馆展演一事,科拉领悟到真正生命自由不仅是获得生命(生理)权利,除掉身上镣铐,而是主宰自我。
4.2 女性生命观照
《地下铁道》中充满对女性群体的生命观照。小说中写道:“白色的男人和棕色的男人狂暴地利用这些女人的身体……不断地殴打,打得她们脑子里没了理智。”[4]在南方蓄奴州的“人间炼狱”中,男女不平等让黑人女奴生存更为悲惨,从限制生育、被黑人男奴夺取财产到不断被白人追击抓捕,科拉在男权世界中一直孤独前进,当她获得自由时,也是向世界宣布作为女性的自己拥有了平等的权利[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