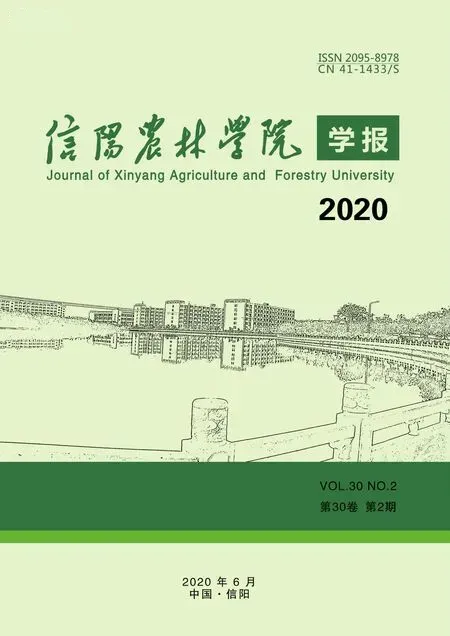田野札记、录音笔与情感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现代性记忆书写方式
李柯霓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1100)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一位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白俄罗斯作家,虽然没有亲历战争,却诞生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家庭之中,因此,拥有属于苏联那一代人的“二手时间”。经历过《普里皮亚季真理报》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写作训练以及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训练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拥有不同于一般文学创作者的“非虚构写作”视角,也奠定了她其后所有写作的基础。她通过直接个人记忆与搜集而来的后记忆(postmemory),修筑起属于苏联—俄罗斯一代人的“乌托邦”,再现了苏联卫国战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等一系列苏联历史上的关键时间。作者在其中完成了他者与自我的记忆书写,呈现了一本不同于官方文献的田野纪念册。
记忆书写作为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着眼点,其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也具有较强的文学特征。近年来研究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从宏大书写转向个体化书写,从追求唯一“真实性”到“增补”(supplement),从理性书写转向感性化书写,从结构化转向碎片、零散化。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文学书写之中,展现了记忆的现代性转向,从文学的层面展现了现代性的记忆应当如何书写。
1 田野空间:话语体系的解构与建构
阿列克谢耶维奇构建了一个有别于上层政治空间的民众空间,并且赋予被压抑的群体以表达的话语权利。她解构了传统的权力话语体系,在田野空间中找到了现代性记忆重塑的方法。
福柯在就任演说中提到,“在任何社会中,任何说话和论述规则,实际上就是强加于社会的某种‘禁令’。也就是说,通过语言表达形式所表现的各种说话和论述规则,实际上就是对于说话和做事的某种‘限制’,即向人们发出某种‘禁令’,在教导人们怎样说话的时候,实际上禁止人们说某些话和做某些事”[1]132-133。社会中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历史讲述话语机制,纵使是看上去被小人物讲述的历史,由于他们选取的语言本身已经制定了一套逻辑与论证系统,他们无法跳脱出这套体系进行记忆书写。社会上层的话语体系是一种悬浮在社会整体之上的“幽灵”,它制造了一种政治真实。在《锌皮娃娃兵》中,它既成为欺骗娃娃兵们走上阿富汗战场的工具,也成为欺骗他们家人的理由。娃娃兵回忆“可是我两次受骗,没有告诉我真相,没有说明那是一场什么战争”[2]31,他们的妻子得到的官方回答是“他自愿申请去的”[2]31,而实则他们却是在酒醉之后被投入铁皮舱之中。上层话语体系将阿富汗战争包装成为一场正义之战,为保存阿富汗革命成果,并在现实生活中隐瞒锌皮娃娃兵们的死因,也禁止幸存者回国言说自身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经历,使得处于“田野”之中的小人物们的话语被阉割,成为潜藏在海洋之下的巨大冰山。
然而阿列克谢耶维奇仍试图去打破这种既定的话语机制,她运用录音笔作为记录工具,几乎记录了对于受访者采访的全过程,在整个话语记录之中,她企图寻找到话语本身的裂隙。每个人的讲述本身就存在大量的矛盾点,作者的工作便是在大量庞杂繁复的口述之中找寻二元对立的冲突点,不是抹平,而是呈现,并用这种冲突的并置,凸显记录文学的独特的“戏剧冲突”。她曾发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强行掩藏于地下的个人真实,还有一种是充满时代精神的整体精神”[3]100-101。《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一位上等兵拒绝去回忆这段可怖的历史,她说“我能记住的就是那种阴森恐怖的孤独感”,在杀死第一个人之后“心里害怕极了”,这与官方话语中宣传的“英勇善战的女战士”形成强烈的落差。《锌皮娃娃兵》写到:“您千万不要写我们在阿富汗的兄弟情义。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们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因为是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我们同样想回家。”[2]21官方宣称阿富汗战场上的军人们同仇敌忾,而实际回忆之中,战士们不过是因为过于恐惧而抱成团。作品中的每个个体身上都存在着有悖于表层话语的部分,正是这种呈现引发了历史观察者们的深度思考。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独特话语处理方式,是将多种声音并置,形成一种复调色彩。但这种“复调”并非先前研究者所分析的,是作品内不同的叙事者的“复调命运交响曲”[4]489。先前研究者大多忽视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调”之中的另一层指涉——上层空间与田野空间的两重性。田野的声音与上层的声音并非简单的交织关系,而是具有多重性。其中的小部分,是交织的关系,即讲述主人公既认同主流话语,又对其保持一定的怀疑。而大部分,两者对于同一事件的阐释是相互对立的,即主人公认为主流话语具有欺骗性,他们对于事件本身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主流话语。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种类型,即上层空间与田野空间仿佛处于完全异质的时空之中,他们互不干扰,几乎没有交集。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一书中摘录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的采访。这个生活在偏远农村的老人仿佛是整个国家的“局外人”。对她来说,世界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样,在巨大的时代震荡中,她什么都没有失去,也似乎什么也未得到。她只等待春天,那时候又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播种,而春天总是会来的——不像某些别的希望。这些小人物处于一种闭锁的状态,几十年来都只关心那些生活必需品。普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
2 录音笔:从唯一“真实性”到“增补”(supplement)
历史学研究转向后,出现了具有现代性的新的历史研究方法,人们开始关注历史本身的真实性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历史研究不再追求唯一的“真实性”,而是找寻到了一种历史真实的建构方式——“增补”(supplement)。不再强调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而是通过不断增加他者,产生无限趋近于历史真实的效果。就如同阿列克谢耶维奇手中的录音笔,它客观地、无选择性地记录下众声喧哗,不主观制造二元对立。它通过不断记录下碎片式的记忆,使其共同拼接成为一面完整的记忆墙,使历史的玻璃去雾、祛魅(Disenchantment)。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言“正是事件突现和主体介入构成了真理生成机制”,多重主体的引入促成真理浮现。
《二手时间》对于传统的单一“真实性”的质疑最为强烈,因为在苏联解体这段剧变时刻,没有“高高在上”的国家意志占统治地位,只有纷繁、混杂、失落与找寻。大众传媒已经不能再提供所谓“真相”,或者哪怕只是一种官方宣传的“真相”。人们说:“我买了三份报纸,每份报纸都在说自己写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5]正如同作者在一次采访中写道,“她们两人的故事中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名字。不过她们两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她们自己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5]33。处于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每个人的故事都不相同,但也并非对立,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否定他者,而是为读者提供一种跟随口述者进入历史本身的入口。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所有作品都在试图寻找一些边缘的“增补者”。从二战中只出现在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中的女兵、被无辜卷入战争的儿童与一些下等士兵,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中消防员的妻子、流离失所的难民;从经历苏联解体政治信仰失落的普通人,到成为阿富汗战争牺牲品的娃娃兵。他们无一例外都站在官方核心历史的边缘。
这些“增补”看似是破碎、随机与零散的,但实则他们形成了新的“容贯的平面”。这个平面与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自我盘绕的莫比乌斯环”[6]24有相似性,它们虽然彼此之间并没有衔接,但永远在同一个单侧曲面上,是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描绘,拥有共同的历史任务。这个新生成的“容贯的平面”,是一种“没有开端与终结”、“体系中的任意两点之间皆可连接,体系内部保持内在的开放性、动态性与多维关联性”的新场域。从某种程度看,文本中的不同讲述者之间也存在对话关系,他们之间是开放互动的。《二手时间》中每一位后苏联社会中的普通人,仿佛都在针对“无产阶级生活与资产阶级生活的选择”这一命题进行研讨与对话。《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每一位被迫纳入“切尔诺贝利人”身份的普通人,开始共同思索这次惨绝人寰的、空前的灾难。他们的生活被这次灾难联系在一起,共同书写了一部边缘的灾难史。不同的讲述者可能持有类似的观点,抑或完全相反的观点,而这也是历史本身的开放性造就的,也使历史有多重的入口,即德勒兹所言:“一个根茎可以在其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断,但它会沿着自身的某条线或其他的线而重新开始。”[7]10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故事进入,向前或者向后阅读,选择自己希望跟随的讲述者进入历史之中,以新的视角观看历史。读者仿佛掌握了一种“上帝视角”的权利,跟随着作者的增补去还原历史,淡化早期历史研究的中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乌托邦”,而这也许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何称其作品为“乌托邦之声五部曲”的原因,纵使通过不断的“增补”与解构,逐渐接近历史本身的面目,但终究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绝对真实,但正是类似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们不断的努力,才使得我们更加趋近历史。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一切都不可靠。今天被认作是真理的东西,明天就不是了。一切都处于变化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迷信。”
3 情感史编撰者——“情感文献”与“创伤修复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仿佛一位人类情感宫殿的塑造者,她不拘泥于单纯的口述记忆或者历史记忆的单纯讲述,而是融入“多汁而丰沛”的情感,使得其笔下的作品都化为一卷卷情感史文献。正如其自身谈到,“我不只是干巴巴的历史,一个个事件,一个个事实,而是在写一部人类情感的历史。人在事件发生期间想了什么、理解了什么,又记住了什么”。萨拉·邓尼斯说:“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她所写的不是单纯的历史,也不是仅仅叙述事件,而是写下了一部部情感史为我们描述了人们的情感世界。”[4]489
现代性的记忆书写更加强调“个体化”“解构”以及“口述历史”,而这些关键词都与情感密不可分,感性对于理性的超越促成了不同于传统的记忆书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本同时具有两种特征:一方面,她的作品可被认为是一种情感创伤的揭露与反映,是一部“情感文献”;另一方面,它们也起到情感修复的功能,被认为是一种创伤的愈疗手段,是一部“创伤修复史”。
作为“情感文献”,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存在较多“刺点”,促使讲述者与读者一同走进那些铅字背后的“创伤记忆”。“情感文献”的一种“刺点”是依靠感官知觉激发的,作者常常运用的感官是视觉与嗅觉。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还是想你,妈妈》中,儿童对战争的回忆大多与色彩、味道紧密相连。他们对战争的记忆是印象画派式的。他们会关注到夏日盛开的缤纷花朵,“丁香花就这样盛开了……绸李花也这样盛开了……”[8]15。绚烂盛开的鲜花与记忆之中最血腥、残酷的战争并置,使记忆中的残忍更加凸显,激发潜藏的创伤;作品中一位心理学家回忆“我从小就记得宰杀野猪时家里的气味”[9]42,一位钳工回忆幼年经历战争时说:“我记住了什么?新鲜的树木的气息……活生生的气息……”[8]28,这种看似与战争、灾难无关联的碎片嗅觉感知,却成为讲述者每次回忆的触发点。类似事件的触发也是创伤记忆被揭露的一种途径。一位口述者在深夜中听到采石场中的巨响,会立即回想起战场。另一层面来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忆讲述,本身也是一部“创伤修复史”。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谈到“被压抑的公共记忆被公开、被言说、被感知时,社会集体的创伤才有被疗愈的可能性”。阿列克谢耶维奇为被压抑的小人物们提供了一个言说途径,他们的记忆由历史底层被翻出,重见日光,从而使这部分记忆有疏解与愈疗的可能。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文本之中展现的愈疗手法有多种,如生物愈疗、信仰愈疗与文学愈疗。
生物,包括动物与植物,预示着生命力与活力。在灾难与战争之中,人表现得脆弱不堪,生命随时会消逝,而有时候在此种孤独境遇中,生物的存在状态为人自身的生活提供了希望。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作品中大量描述生物。《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疏散区居民巴达耶娃在讲述的最后说:“庄稼发芽了……长得真壮实……”[9]75;一位受灾的语文老师说:“墙上、房门、天花板、屋顶,我都插满了柳条”[10]204;一位讲述者说:“现在我的镭(讲述者的狗的名字)跑出去了……我担心,它跑到村外会被狼吃掉,那样的话,就只剩我一个人了”[10]60。这些生物是讲述者们的情感寄托,也是带其走出黑暗创伤的治愈之物。信仰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是另一种治疗的方式,能够带给苦难中的人以存活的希冀。俄罗斯民族性格一直以来受到宗教影响较大。在早期多神教之后,东正教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系统,这种宗教观念也融注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信仰愈疗来源于宗教教义,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经历者开始阅读“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一定是完美的”[9]90等教义;一位火箭燃料专家与人们一起“建立一个教堂……切尔诺贝利教堂”[9]210;《二手时间》中马利克娃讲述在苏联解体之后,“每个人都去教堂,外婆也跟着去,开始画十字、吃斋”[5]379。苏联解体之后,据统计数据显示,宗教教会大规模增长,1991年俄罗斯联邦的宗教群体数目5502个,到1997年已经达到14688个。在经历了一系列难以言说的苦难之后,宗教信仰在情感上的支撑作用远远超过科技本身,人们企图在宗教信仰中获得救赎,“人们又开始相信上帝了”[5]81。文学愈疗也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常用的方法。一位受难者回忆,“前些时候,我找到了一大本普希金的集子……‘死亡在我看来十分可亲’”[9]90-91,文学触发人们思考,也使人们更加平静地面对人生、死亡等事件。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确在书写一部情感史,但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呈现,她更希望提供一种疏解方式,使经历者与阅读者能通过文字的途径得以净化。
4 结语
阿列克谢耶维奇开拓出独具一格的记忆书写方式,她将文学领域的记忆书写无意识地带入现代书写场域,赋予其现代风格。在她笔下,记忆已经远远超越个人范畴,成为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档案,甚至成为历史类影视作品拍摄的参考背景之一。近期HBO(Home Box Office)电视网新出了一部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电视剧,故事大多取材于《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已经实现了合法化的历程,同时,更进一步,她也为边缘记忆的疏导与愈疗提供了方法,让那些拥有还未被挖掘出的记忆与难以言说的记忆的承担者看到了希望。“非虚构文学”与“文献文学”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性得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