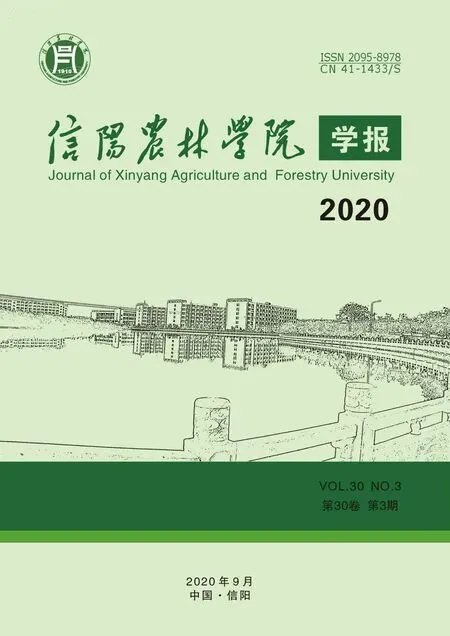毛姆笔下的海外中国人形象
——以《阿金》《叶之震颤》两部短篇小说集为例
王梦潇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英国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对中国的想象和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形象在英国作家的笔下不断变化,这种形象的复杂变化在20世纪的英国文学中尤其明显。19世纪末,黄祸论兴起,英国作家对中国的否定性描写占据主流。但一战爆发后,许多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前途生出忧虑之情,想要去往遥远的东方国度寻找出路。毛姆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东方,踏上了中国以及周边的许多国家的土地,想要在这里找到他理想中的东方国度。
毛姆在很多作品中都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但其被研究较多的几部作品,如《彩色面纱》《在中国的屏风上》等的故事背景都是中国。这种设定虽然能更加详尽地展现中国人的在地形象,但或多或少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而《阿金》和《叶之震颤》两部集子中的短篇小说都不是以中国为故事展开的背景,《阿金》的故事背景是马来西亚及周边地区,《叶之震颤》的故事背景是太平洋地区。这就让我们有了另外一个研究角度,即在毛姆笔下,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此外,在这两部作品中,中国人都不是最主要的角色,大多数是毫不起眼的配角。在文学作品中,配角往往只是功能性的人物,但正是这样的特性,使得毛姆减少了对这些中国人的人性共同层面的挖掘。这样的角色设定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像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这就更能显示出,中国人在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区的处境。我们可以以此探究,在毛姆眼中,中国人在异国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形象、姿态存在的。
1 毛姆笔下的海外中国人形象
1.1 身份
在这两本短篇小说集中,中国人大多以下等人的身份出场,其中,仆人和厨子是出场频率最高的中国人形象。在《阿金》的序言中,作者告诉我们,阿金是毛姆在游览马来半岛及周边地区时的中国仆人,这部短篇小说集也以这位中国仆人的名字命名;而在《麦金托什》和《火奴鲁鲁》中,毛姆都塑造了中国厨子的形象。在《阿金》和《叶之震颤》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中,仆人、厨子前几乎都要加上“中国”两个字,仿佛在毛姆笔下,这两个职位是中国人专属的。
中国仆人和中国厨子的设定显示出了毛姆眼中的海外中国人的地位,即白人的附属品。一方面,这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异国都难以找到理想的位置,而只能处于下等阶层。另一方面,这也显现出中国人在他者眼中的形象。虽然毛姆反对殖民,但他毕竟是英国人,流淌在他血液中的种族优越感是无法磨灭的。在他看来,在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区域,处于主导地位的还是白人,而中国人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当然,从毛姆对厨子的中国人身份的定位,我们也可以推测出毛姆对中国食物是比较喜爱的。
再者,中国商人也有在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中频繁出场,但毛姆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多的刻画,我们只能看出,在毛姆眼中,商人是中国人形象的典型代表。在《阿金》一集的《丛林中的脚印》中,毛姆写到中国商人的房屋体量之大和中国海外商人之多;在《穷荒绝域》和《尼尔·麦克亚当》中,他都有对中国商铺的描写。在《遭天谴的人》中,中国商店只是作为金格·台德事件的爆发地点出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叙述用途,而这个“中国佬”也只是作为功能性的人物出场。但毛姆下意识地会将商店设定为中国人开办的,可见,中国人与商人常常联系在一起讲,中国海外商人在毛姆笔下的典型形象便可想而知了。毛姆偶尔也会写到中国商人的狡猾,写年轻人受到中国人的哄骗,买了一些没有用处的东西。这大概是源于西方人对中国商人的固有印象。
除此之外,海外中国人还以妓女和中国医生的形象出现在这两部短篇小说中。毛姆对中国妓女的描写并不友好,相比较他笔下日本妓女的体贴周到,中国妓女骨子里仿佛透着一股冷漠感,有种排他的傲气。
1.2 体貌
关于中国人的外形,毛姆在《阿金》和《叶之震颤》中有几个典型的描写,这些描写也体现了毛姆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首先,毛姆笔下的中国人个头矮小。他描述阿金个子很矮,《丛林中的脚印》中捡到怀表的中国人身材矮小,还有着罗圈腿。这些都表现了毛姆内心的种族优越感,他对中国人身材矮小的刻画来自于潜意识中对中国人的矮化。再者,中国下等人民在毛姆眼中是落后的、未开化的。他在《麦金托什》中描写中国仆人是“光着脚板”的。从某种层面上讲,衣着完整其实是一个人文明的表现,而这里对中国仆人光着脚的形象的刻画,表现了毛姆眼中的海外下层中国人文明程度是很低的、较为原始的。
而对于注重打扮的中国人,毛姆的叙述口吻也是颇为贬斥的。在《火奴鲁鲁》中,他写道:“再就是中国人,男人一个个肥胖阔绰,穿着古里古怪的美国式衣服。”或许在毛姆眼中,中国人就应该维持他们的朴素、未开化的原始形象,当他们学习“文明”的西方人的穿着,或是化上妆的时候,就丢掉了他们本身最为纯粹的东西,变得面目全非了。这也许与毛姆对中国古老、神秘的想象有关。他不希望现代化的东西污染了纯净的中国人,因此,当看到中国人的现代化装扮的时候,便会心生厌恶。
1.3 性情
首先,在毛姆笔下,海外中国人,尤其是底层的劳动人民,是不爱多嘴、默默埋头做事的。他在《阿金》的序言中写阿金“做事干净利落,不爱多嘴说话”。在《叶之震颤》中的《麦金托什》写中国厨子总是一言不发地在做事情。在《火奴鲁鲁》中他又写道:“爱吃苦的中国人和狡猾的日本人便从他们手上夺走了生意。”毛姆对海外底层中国劳动人民性情的评价比较高——他们不爱说话,但很能吃苦,默默地为主人完成所有的事。
其次,毛姆常常把中国人与犯罪联系在一起。在《丛林中的脚印》中,布朗森的死亡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人”干的。“中国人”在这里被怀疑为杀人犯,不是因为布朗森与中国人有什么瓜葛,而是在当地人眼中,“中国人”经常干出抢劫杀人的事情。然而,这一案件真正的杀人凶手并非中国人,那么我们可以猜测,这或许是毛姆为了让西方人反思自己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而作出的设定。
再次,毛姆还认为中国人是类型化的,缺乏变化的。他们没有西方人性中复杂的一面。在《阿金》的序言中,毛姆写道:“他们多少都缺乏变化……他们的古怪表现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以说,在他眼中,中国人的人性是较为单薄的。这表现了毛姆对中国人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对中国人未受污染的淳朴性情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种族优越感。
当然,毛姆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他与中国人接触的深入而有所转变。最初他认为,中国人是神秘的东方人,是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生物,他们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感,并认为阿金除了把自己当作雇主之外,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别的感情。彼时,在他眼中,中国仆人不过是用以交易的物品、为己所用的服务者。但他没有想到,阿金在离开他的时候,竟因为不舍而流下了泪水。这时,他才意识到,中国人也是像西方人一样有感情的生物,他们的感情比西方人更纯粹、更真诚。
在这两本短篇小说集中,毛姆经常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预设和中国人的实际表现之间的落差,来表现自己对中国人印象的转变。同时,他也以此纠正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2 毛姆笔下复杂的海外中国人形象产生的原因
2.1 集体想象的无意识
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集体想象下的中国,但“集体想象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英国人视野中的中国人形象是游移不定的,这与不同历史时期英国的处境、中国的地位、两国的关系以及交流的方式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英国集体想象下的中国是相当复杂的。毛姆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其对中国的想象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2.1.1 西方优越论 虽然毛姆对中国是充满兴趣的,对殖民文化也是厌恶的,但是,从小在西方长大的他,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早已产生了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印象,难以避免受到集体想象的影响。“当我们掀起遮在毛姆中国形象上的那块彩色面纱,源自于西方优越论的自负心理也就展现无疑了。确实,无论如何,毛姆都难以逃过那傲慢与偏见的文化心态。”[1]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地位都大不如前,西方列强在侵略、压榨、控制中国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他们认为自己是比中国人高一等的民族。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毛姆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因此,他会不自觉地用一种俯视视角观照中国人。或许他对自己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是不自知的,但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的确能读出微妙的种族优越感。
2.1.2 黄祸论 1893年,英国历史学家皮尔逊(Charles H. Pearson, 1830—1894)发表了《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NationalLife and中racter,A Forecast)一书,在书中,他反复强调以中国人为首的有色人种的“可怕”之处。这使得“黄祸论”席卷西方,西方人对中国人产生了普遍恐惧的心理。此后,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 1883-1959)在13部傅满楚系列小说中塑造了险恶的中国佬形象,加剧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恐惧心理和厌恶情绪。
处于同一时期、同一国度,毛姆不可能不受到这两位英国人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也会不时地流露出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恐惧,将中国人与犯罪联系在一起。但毛姆并没有陷入到“黄祸论”带来的恐慌中,他在与中国人接触后,认识到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因此,在他笔下,中国人不是真正的凶手,中国苦力的暴动轻易就被镇压了。毛姆的这些叙述都表现了他对中国人印象的转变,也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固有认知,纠正了西方人因为“黄祸论”对中国人产生的不必要的恐惧。
2.2 个人经历的影响
2.2.1 童年的不幸遭遇 毛姆的童年是不幸的。在他8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两年后,父亲也过世了。此后,他寄居在叔父家,叔父对他很冷漠,家境又很是贫寒,这使他的童年过得非常凄惨。11岁的时候,他被送去学校读书,身材的矮小和口吃的毛病让毛姆在学校受尽了嘲讽,他倍感孤独,也变得异常敏感。
童年的不幸让毛姆更能体会到不幸之人的情感,从小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也更能理解底层民众的处境。因此,他在观察生活在苦难中的海外中国人时,常常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欣赏中国仆人与厨子不爱多嘴、能吃苦的品性,用人文主义悲悯着无休止劳动着的中国人,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有着深沉的同情和敬意。因此,在毛姆的笔下,生活在最底层的海外中国劳动人民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他们不屈不挠地与艰苦的生活和自然环境相抗争。
2.2.2 哲学思想的影响 毛姆的叔父是一名牧师,而这是一位极其自私的牧师,让毛姆在童年时期就对基督教产生了质疑。随着年岁增长,苦难与不幸让毛姆用一种更为悲观的态度审视生活,无数次祈祷未果后,他不再相信基督教,甚至对基督教嗤之以鼻。在毛姆不断求索的过程中,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使毛姆产生了共鸣,而叔本华对东方哲学的推崇则让毛姆对东方充满了向往。于是,东方就成了毛姆寻求智慧的方向。
2.3 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被完全暴露出来,一部分西方人对自身的文化产生了质疑,毛姆也因此感到不安,他想从东方文明中寻找出路。
毛姆来到中国之前,已经在心里有了对于中国的想象,虽然中国不像他想象得那般古老、神秘、辉煌,但他还是会带着这种眼光去审视中国。他在一定程度上无视了东方的现代化,认为中国人是落后、原始但又淳朴、真挚的人,这种颇具选择性的描述与毛姆塑造中国人形象的目的之一有关,即与西方人形成对照,用中国文化弥补西方文明的缺失。
他在《阿金》的序言中写阿金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做事,写阿金总是在最后一刻登船,写阿金被骂还笑嘻嘻的,并将阿金的这种慢节奏和自己的急性子进行了对照;他又在许多篇目中都写了中国仆人安安静静、勤勤恳恳地工作。他用中国人的安静、平和、舒缓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浮躁进行对比,进而否定西方文明。在他看来,工业文明压抑和扭曲了人性,西方人的自然本心在不断膨胀的物欲之中逐渐丧失,而东方文明是没有受到工业文明污染的一片净土。在毛姆笔下,中国人在没有被工业文明玷污的东方文明的庇护下,身上有着那种最为淳朴的、未开化的情感。这在毛姆看来,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了西方文化的‘自我’”[2],毛姆塑造的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就是对西方“自我”残缺部分的补充,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人形象是毛姆的心灵投射。
3 结语
毛姆对中国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毛姆与中国人接触的深入,他对中国人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有所转变。在来到中国之前,毛姆可能会受到西方身份的影响,以俯视的视角观看中国人;可能会受到英国传统文学对中国浪漫、辉煌、神秘想象的影响,对中国人有乌托邦式的想象;可能会受到19世纪黄祸论对中国丑化的影响,将中国人与犯罪相连。但经过对中国人的近距离观察,他有了新的理解。他看到,中国人也是和西方人一样具有人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虽然毛姆无法避免地受到集体想象的影响,但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