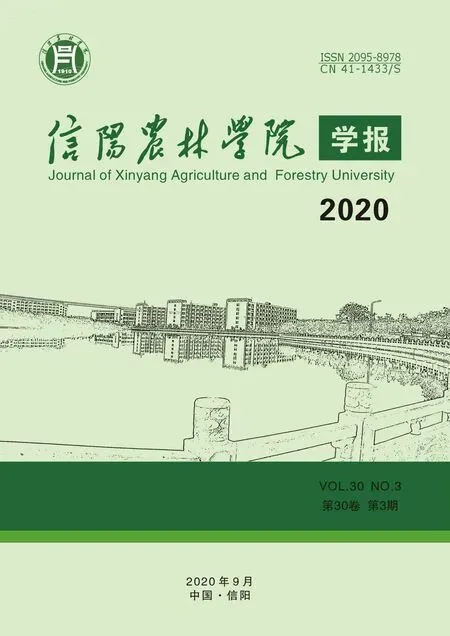双重目光暴力下的自我形塑
——从汤亭亭《女勇士》看华裔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马哈力麦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凝视理论从萨特的哲学、拉康的心理学和福柯的社会学等众多理论汲取了营养,自此凝视成为剖析和解构男权的有力切入点。在现代视觉文化中,可以发现“凝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性别化的观看权力”[1]53,凝视可以说是携带着权力运作的观看方式。观者被赋予某种看的特权,通过看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即权力主体,而被观看者在沦为看的对象时,往往感知到观者目光带来的权力的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进而被客体化,沦为他者。来自于权力主体的种种凝视——因性别、种族、阶级权力分化而对沦为观看对象的女性群体或个体的身体、自我意识、人格进行控制、驯服、改造和编码。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提出“他人的注视”命题,认为他人的注视是塑造我们主体性的决定性力量。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个体通常会以丧失自我、背叛自我意愿来取悦他人而沦为被观者权力意志内化了的客体。拉康也从心理学角度提出镜像凝视理论,同样指出“他者的注视”对自我意识建构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凝视是主体向他者欲望陷阱的一种迷入,是他者的目光对主体欲望的捕捉。福柯的全景监狱理论进一步探讨了凝视与主体建构的关系。全景监狱通过观看者视点永恒的可视性让权力自动产生作用。
《女勇士》中置身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和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两种文化之间的双重目光“轻视”下的女性,在被凝视而沦为客体对象的同时也不乏反抗意识,其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对凝视主体将其客体化的反抗,以女性反凝视和自我言说的力量冲破男性凝视和白人群体凝视的覆盖,向权力主体发起挑战,为女性自我言说,寻求自我身份认同。
1 双重失语:主体性的缺席
《女勇士》中几位女性人物无一不生活在男性话语权力主体和白人群体话语权力主体的凝视之下,她们作为被“凝视”的对象,或被监视,或被轻视,或被有意无视而沦为“隐形人”,往往成为话语权力运作的客体,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的话语权力,只是由外在的规训权力支配、改造和形塑。这种“失语”恰恰说明了她们沦为客体的自我意识主体性的缺失。
中国传统女性在男性话语权力主体凝视下的主体性缺失主要体现在话语权的丧失上,这一点在叙述者“我”的姑妈身上尤为明显。她始终以我的“无名姑妈”,“无名女子”,“她”,父亲的“妹妹”等处于从属性地位的“他者”的形象出现,没有自己的姓名和独立的身份,可以说她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沦为男性目光支配的客体而丧失女性自我的典型。约翰·伯格在《视觉艺术鉴赏》中指出男性凝视于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关键性作用,“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作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2]。在男权社会尤为如此,女性往往成为男性权威凝视的对象,以消极被动的方式迎合男性的目光,并依此进行自我形塑,将男性的凝视内化为自我的意识,于是,女性在一味的迎合中成为男性目光裹挟的对象。女性透过男性凝视认识自己的形象,并将男性凝视内化,由内在的男性视角来审视此被审视的女性自我。小说中“我”的“无名姑妈”就是典型的男权凝视下的传统悲剧女性。她与当时逆来顺受、被动迎合男性目光的大部分女性不同,敢于大胆挑战男性凝视的特权,质疑传统两性关系中男性主导的看与被看模式,以异于传统男性社会的审美标准美化个人身体外观,试图作为凝视主体去观察并主动吸引男性目光的注视,却受到了男权社会过度的凝视——监视。
“凝视是监视的权力,它通过可见的或是隐匿的目光投射控制被凝视对象”[1]57,形成一种统摄性的、无所不在的注视网络,由此就产生了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3]226。这种被迫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被凝视对象的统治,使其总是处于受支配的地位[3]211。小说中的无名姑妈与奉父母之命成婚的丈夫分离两年后,却怀了孕,众目睽睽之下挺起了大肚子。村民们以“夫有二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在分娩的当夜,狂怒的村民们冲进家里,“停下来凝视着我们,他们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4]2将一切置于眼下,对每一寸试图逃匿的“暗角”进行审判,她被充当“家长”的村民们抄了家,被视为“妖魔”驱逐,被迫流落到荒郊野外,随后抱着刚出生的婴儿投井自杀。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极少被正视,不是被拔高为“天使”,就是被贬低为“妖魔”。中国父权文化极力将她们规训为“天使”,即孝女、贤妻、良母,要求对父亲、丈夫甚至儿子绝对的服从、忠诚和归顺,剥夺了她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进行自主选择的话语权,沦为女性主义批评家口中彻底的“他者”,即“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5]。《女勇士》中“我”的奶奶便是一位将男性凝视彻底内化了的传统女性,一个“他者”,她完全丧失了女性自我,取而代之的是臣服于男性目光下的男性化了的自我,不但“轻视”同为男性凝视客体的女性,更是成为极力捍卫男权主体的“主力军”,“无视”自己不守传统男权话语规训的女儿,试图抹去一切与之相关的家族历史印记,作为其反抗男权规训的惩罚。
内化了男性凝视的女性,视男性的目光注视为自我存在的身份价值准则,毫无主体性人格可言。“我”的月兰姨妈被男性目光“轻视”甚至“无视”时,以内化了的男性视角审视自我,“轻视”自我。月兰姨妈体态娇小柔弱,是传统男性目光中的温婉贤淑、三从四德的女性,从父母之命嫁给了比她小的丈夫,婚后20多年来一直靠远在美国的丈夫寄钱服侍公婆,养育子女。离开丈夫视线多年而被“无视”的她,将丈夫的“无视”等同为“自我”的卑微。在“我”的母亲勇兰的帮助下移居美国后竟幻想只要丈夫同意,她愿意去做女仆伺候丈夫在美国的妻儿。月兰见到丈夫的那一刻,在丈夫粗鲁的美国式眼神的逼视下,缩作一团,双手捂脸,被离婚都不敢言语,只感到自己来到了“鬼”的世界,“迷路了,把魂丢了,支离破碎地丢得满世界都是”[4]142。她最终精神崩溃,在加州一家疯人院死去。离开丈夫、子女、公婆注视的姨妈,剥离了贤妻、良母、孝女角色的掩护,只剩“轻飘飘”的“自我”,既无法承受被剥离客体身份也寻求不到自我存在的主体性而至疯癫。
另一重的失语,即在白人为主流的种族话语权力主体凝视下,华人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在美国白人眼里,她们始终是不入流的“他者”。“我”和母亲勇兰身在美国没少受到“目光的暴力”,走到哪里似乎都能感受到被有形或者无形的目光盯着,因此美国在“我们”眼里是个到处是“鬼”的国家,令人无处遁形,所有人都处在一定的凝视尤其是心理凝视空间,参与着主体与客体的心理游戏。“我”在美国亦被人称作“黄鬼”,这种行为“将目光的暴力加之于他者身上,使之成为主体化与客体化的一个粘合区”[6],而“我”在这无处不在的“目光暴力”之下,童年时期在美国的学校里有着极其不愉快的经历,曾像是得了失语症一样,终日沉默,回答课堂提问时只能发出难听的“呃呃”声,回到家后又恢复正常。母亲勇兰在中国时如“女勇士”般无畏无惧,所向披靡,作为一名知识女性——一名乡村医生救死扶伤,“驱鬼逐魔”,生活起居亦是有佣人照料,衣食无忧;可到了美国却成了“神力”尽失、为生活奔波劳碌的洗衣妇,正是种族话语权力凝视将她们边缘化,沦为白人目光支配的他者,或被过度关注而引起“心理不适”,或被视而不见而成隐形人。
2 自我言说:主体性的建构
小说《女勇士》中,在双重权力主体凝视下的女性并不总是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她们也进行反凝视,反抗“他人的目光”对“自我”的捕捉和控制,以冲破男权凝视和白人凝视下的客体地位。“我”和母亲勇兰的主体性建构正是通过反抗男性凝视和白人凝视来实现的。萨特认为“只有当我意识到他人对我的意识时,我才成为我自己意识的客体,否则我便无法成为自己意识的客体……因此,作为客体的我究竟是什么,这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他人。这就是‘他人即地狱’的原因:我的身份,甚至我本身,最终都要依赖于他人。因此,只有通过支配他人,我才能实现自己的主体性。”[7]由此来看,实现自我主体性的过程,首先必然是意识到他人对我的意识,其次成为自我意识的客体,即受他人意识支配,最后通过支配他人来打破自我的客体性而确立主体性。小说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字眼——“鬼”,可以解读为叙述者“我”和周围华裔女性意识到的来自于中西方文化无形的凝视力量,一种从他人眼光里感知到的自我的他者性,作用于“我”的主体性构建。
在福柯看来,“造就主体的模式分为他律模式和主动模式,前者是由权力和知识构造主体的方式,而后者则是自我的主动选择,按照个体的意志创造自我。”[1]58“我”的母亲勇兰的主体性建构可以从这两方面来分析。其一是他律模式的主体塑造。在中国她是一名乡村医生,以医者的科学知识和权力武装自己,进而以“医学凝视”主体去观察“病人”,直视“压身鬼”而最终以“言语”逼退它。“压身鬼”骑在勇兰的身上,想把勇兰压死或使她窒息而死,而勇兰无畏地独自与它作战。她大喊道:“我不会妥协的,你什么样的折磨我都能忍受。如果你们以为我怕你,那你就错了。你对我来说并不神秘……你们这些胆小鬼,可是你们斗不过强壮的女人。”勇兰正是靠着“不停地言说”击退了“压身鬼”。这里,“压身鬼”可以被理解为女性“自我意识的客体”承受的双重压迫力量——中国传统社会父权制的压迫和美国白人社会种族主义的压迫。勇兰战胜“鬼”的关键不仅是反客为主的医学凝视,还有不停地说话,进一步显示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性,即拥有话语权就意味着拥有自我身份和自我言说的权利。其二是主动模式的主体性建构,自我的主动选择,个体意志创造自我。勇兰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即摆脱男性凝视的客体地位而争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基本主体性,在这一点上,她和月兰的被动性承受完全不同。在意识到自己男权凝视下的客体地位时,她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从一定的“高度”主动去观察、凝视,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及属于自己的身份,如小说里提到“她也从未改过名字——勇兰。有一技之长的女人有权不用夫姓,就用自己婚前的名字,如果她们高兴的话。到美国之后,她还叫勇兰,从未用过美国名字,也不曾取上一个应酬必要场合的名字”。因而,女性凭着自我意志达到世俗眼光中一定的“高度”而去主动凝视,争得话语权,才更有可能进行自我主体性建构。
“我”的主体性建构主要体现在对中西方文化隐形的双重权力压迫的反抗中,主要有三个层面,自我隐匿,自我否定,自我书写。从第一层面来说,就如小说副标题“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所示,“我”的童年在各种“鬼”的笼罩中度过。这里的鬼亦可理解为一种他者性,叙述者从他人的注视中感知到的客体的自我。当然,其中包括母亲给“我”讲的无名姑妈的“鬼魂”,“我的姑姑缠着我。她的鬼魂附在我身上”,叙述者的母亲反复告诫她不要重蹈姑姑的覆辙,然而姑姑在男权凝视下的悲剧在其意识中挥之不去,从而衍生出她对自我身份的怀疑和思考。在《白虎山》一节中,看似是讲述花木兰的故事,实则以第一人称融入了隐匿的自我,想象自己获得某种强大的神力,能够“俯视”中西方文化的压迫力量以获得主体地位。而现实中自己却是暴露在各种“鬼”的目光暴力下,为此焦虑不已。她拒绝被凝视,也拒绝去注视那些凝视她的目光,将自己的存在减到最低,在白人的学校里终日沉默进行自我隐匿,将自己的画作全部涂黑,企图躲避“鬼”的目光。在第二个层面,叙述者开始主动捕捉他人意识中自我的客体形象,打破、否定、质疑他人眼光凝视下的“客体自我”,作出了一系列的反抗行为。“我”从另一个失语的华裔女孩身上感知到在白人群体沦为他者的自我意识的“镜像投射”,对她施暴,逼迫其说话,而实际上是逼自己发声。“我”对贬低女性的言语极其敏感,每听到“养女就好比养牛鹂鸟”,“养女没有好处,宁养呆头鹅不养女”,“费力教养女孩不值当,终是嫁为别人妇”[8]46,“女孩不行!”[8]47,“女孩儿好比米粒里的蛆虫”[8]43诸如此类的话语,“我”便气得重重的跺脚,摔盘子拒绝洗碗做饭,不刻意打扮自己取悦他人,而使自己看起来邋里邋遢,说话故意粗声粗气,模仿男孩走路,这些行为都极力去挑战男性眼光中的传统女性自我。“牛鹂鸟”,“鹅”,“蛆虫”都被认为是没有自我意识、低人一等的存在,女性被等同于这类存在,无疑是否定了女性主体性的存在,“我”的反其道行之都是否定男性目光对女性自我的否定。第三个层面便是女性自我的书写。母亲反复说“你不能把我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而叙述者将其写下来公之于众,她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笔如同花木兰的剑一样锋利,可以“斩妖除鬼”,揭示他们的一切“罪行”和不公,是建构女性话语权以获得自我主体性强有力的武器。她以叙述主体的目光使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压迫性力量、可说的或不可说的成为被审视、被观察、被言说的对象,作为一种终极的“复仇”。
3 自我认同: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消解
华裔女性的主体性的建构实质上也伴随着其自我意识置于主客体地位时二者间的转化与平衡,即对自我身份的怀疑、否定后的寻求和认同,因为移民并不只是空间上的,更是一种文化意识上的。《女勇士》中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白人文化边缘挣扎的“我”,就面临了双重的身份认同危机,而“我”的身份危机影射出的是整个华裔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查尔斯·泰勒认为,“认同问题关系到一个个体或族群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确定自身身份的尺度。‘认同危机’的最重要表征就是失去了这种方向定位,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9]。叙述者的主体性建构过程遭遇了两个方面的认同危机,性别身份认同危机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生在华人圈,“我”免不了被父母和其他第一代美籍华人灌输中国传统男权文化里女性的从属性,即他者性。如上文中所言,将女孩视为“鹅”“牛鹂”“蛆”等,以及无名姑妈和月兰姨妈的悲剧事实,母亲也说“我”终有一日会长大成为一位妻子,一个奴隶,但是她也将花木兰的故事讲给“我”听。从古自称“奴家”的女性形象和花木兰“女勇士”的形象对叙述者来讲是一种冲击,她感知到了其中巨大的张力,开始对自我的性别身份感到困惑,质疑并否定来自传统目光的对女性身份的期求。拒绝做饭洗碗,摔盘子被骂“坏女孩”时,反而甚感欣慰,因为她认为“坏”既是对男性目光里女性标准的突破,也是女勇士般的无畏,因此她反问道,“坏女孩不是跟男孩相差无几了吗”[8]43。她从模仿女勇士身上的男性气质到真正形成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可以在《白虎山学道》这一部分中发现,表层是花木兰故事的叙述,实则是以第一人称进行“隐匿自我”的潜叙述,将花木兰的形象杂糅,结合了花木兰作为“女勇士”的本身和岳飞刺字精忠报国的“男性特质”,形成一种“双性同体”的自我,寻求对立中的平衡,也预示着对父权制的消解和对两性二元对立的否定,实现一种去男权中心,两性和谐互通的愿景。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所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10]
在美国白人为主流的社会里,叙述者的民族身份也同样遭遇了认同危机。以白人的眼光,她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黄鬼”,在父母和长辈口中她也算不上是像出生在中国不幸夭折的两位兄姊那样真正的中国孩子,于是陷入对自我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中,而导致童年时期在白人群体中的失语症。初入学时,“我”也时常对“I”和“here”两个英文词感到困惑,因为遭到双向挤压的“我”从未切身体会过身在“此处”的归属感。她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也诉诸于“中西合璧”,去欧美中心化,这种意识也可见于《白虎山学道》,以想象的形式实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国花木兰的故事里也夹杂了爱丽丝梦游的奇遇,她没有固守一种本质主义的自我观念,而是通过弱化两种文化间的界限,消解二者间的对立关系,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自此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趋于平衡的包容性的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