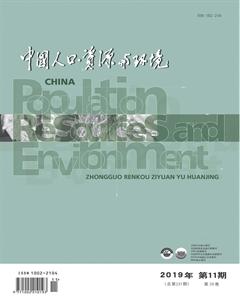论美国第四代环境法中“一体化多模式”的治理方式
蔡守秋 王萌
摘要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给环境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其需要有多种环境保护治理模式。美国四代环境法均是在原有的环境法律体系不足以应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时而产生和发展的。与前三代环境法相比较,美国第四代环境法提倡的“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将摒弃碎片化和单一化(或一刀切)的治理模式,通过关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来增强人类对生态系統的修复能力,试图以整体的、综合的或协调的方式将多模式治理相连接,具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多元化管理模式的特征,并成为美国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已经开始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主要有环境治理实施者、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信息与决策的相关性、创新性与治理能力相结合四方面内涵,符合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目前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存在“部门分散、地方分割”等诸多“碎片化”现象,借鉴美国第四代环境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需要在政策实施方面要积极贯彻落实“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在环境理论方面要强调整体主义新生态观;在环境实践方面要注重基于综合生态系统的治理方式。美国第四代环境法倡导的“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模式与我国学者提倡的综合生态系统的管理模式都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可持续性的特点,是一种跨部门、跨区域、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但由于相关环境决策和执行的依据缺乏严格明确的强制性标准,导致美国第四代环境法仍然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不足。
关键词环境问题;美国第四代环境法;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9)11-0082-08DOI:10.12062/cpre.20190623
目前,许多学者用“代际”隐喻来描述环境法的演变。在美国,环境法“代际”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从1970年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简称CFR)开始,实际晚于美国环境法的颁布。在此之后,随着美国环境法的发展,相继确立了三代环境法[1]。但是,据我们所知,美国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环境法在调整范围和监管模式上仍然存在争议。例如,环境监管模式随着一些企业的重点业务的改变而改变,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2]。而环境法作为调整“人—自然—人”关系的规则,目的在于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3],在不断地协调过程中发现,它不是在某种最优平衡点上建立的,而是在适应形成这种平衡点的各种条件。通常我们会用“整体性、综合性、相互关联性”等词汇来描述环境法的特征,就像环境法的许多理想目标一样,这些天衣无缝的表述并不能准确地指导实践,大多数是因为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不连续性和不可兼容性。
几十年来,美国环境法一直试图保护环境免受人类行为的破坏。理查德·拉撒路(Richard Lazarus)曾辩称,“环境法已步入中年,已是灰头土脸,需要更新。”[4]然而,随着环境法地不断发展,新一代环境保护制度的出现,解决了前人未解决或未充分解决的问题。美国环境法的最新版本是本文所提到的“第四代”环境法,它所关注的是一体化多模式(Integrationist and Multimodal)治理方式。
1美国四代环境法的概况与比较
1.1四代环境法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第一代环境法,内容主要包括“命令与控制监管、基于技术标准和法律诉讼规则”,以及其他污染预防技术—统称之为“硬”方式或“国家干预”的方式,其作用是要求我们遵守规则[5]。美国第一代环境法具有“命令和控制”的监管特点,也就是丹·塔洛克所说的法治诉讼(包括执行环境法规的公民诉讼)和基于技术标准的污染控制。这一代环境法试图通过主要由中央联邦机构制定和控制的管制手段来治理污染,以防止对环境的损害。
第二代环境法是对以“命令和控制”监管方式导致的监管僵化和经济效率低下的第一代环境法作出的回应。这一代环境法寻求引入监管灵活性,提高效率,并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合规激励、市场工具以及灵活协商的规则来利用市场激励机制。第二代环境法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以激励行为,有效提高企业、个人和政府机构的环境绩效,因此,市场和公私伙伴关系主导了第二代环境法,为治理环境提供了便利。第二代环境法试图摆脱僵化和高成本的监管方式,转而注重成本和经济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所谓的“软干预”监管方式。
第三代环境法的特征不同于第一代环境法即基于“命令—控制”的监管模式,也不像第二代环境法即关注“经济效率和市场机制”。相反,第三代环境法强调在分散管理和集中管理过程中的社会政治利益。第三代环境法综合了以监管主导的第一代环境法和以市场主导的第二代环境法,具有可持续性,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环境正义、反身法(reflexive law)、协商解决机制、公众参与、适应生态系统管理等特征[5]。不过,这些看似大杂烩的元素集合有一些包罗万象的主题。第三代环境法主要关注整个环境系统,以过程为导向,从对具体环境结果的追求中抽身出来,致力于为环境保护提供某种法律框架和结构为前提[6],使其在环境、社会和经济上具有可持续性。其次由公众参与或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来实现的,这种参与旨在为环境保护提供合法依据,通过个人和组织的参与来改变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或社会不公平的行为,并改善环境管理中的社会反馈循环机制。因此,在第三代环境法中,权力下放的合作机制是制定新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新规则将指导人类和社会行为走向环境保护、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第三代环境法关注新的领域,扩大了环境问题的范围和我们对环境敏感度的理解,即扩大了可允许的干预范围和更广泛地看待环境法问题的角度。
第四代环境法是美国环境法的“最新一代”。也是本文的写作重点,该部分主要讨论阿诺德(Arnold)和冈德森(Gunderson)教授对最新环境法现状的实质分析及对未来环境法发展的预测。第四代环境法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是对前三代环境法的不足做出的回应,即否定前三代环境法所认为的,环境是一种静态的物质,可以保护、维持,也可以像商品买卖那样用于交易的观点。在第四代环境法的研究中,阿诺德和冈德森教授更关注的是环境系统的弹性,他们认识到社会、法律和生态系统的演变是一个复杂、动态、相互适应、相互关联的过程。支持第四代环境法的学者认为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是高度动态的,是由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法律制度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所形成的。它的目标是通过关注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治理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来增强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同时,还具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多元化管理模式特征。例如在美国建立不同类型的联邦—州伙伴关系、多方利益相关者协作、以协商为主的激励机制等。在第四代环境法中,主张法律是用来刺激和支持“适应性”治理的,尽管在此之前法律实际上是作为适应性治理的障碍。
1.2第四代环境法与前三代环境法的对比分析
每一代环境法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没有哪代环境法能取代上一代环境法,新一代的环境法都是在原有的环境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尽管有时只在方法上或法律调整的优先顺序上做了修改,甚至这些方法会被取代、抛弃,但至少从之前的成功或失败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尽管如此,这四代环境法的发展对当今及未来环境问题的保护都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表1显示了四代环境法之间的比较。
与前三代环境法不同,第四代环境法将有效地利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并通过各种连接点将它们结合起来。因此,它不仅仅提高环境治理的能力,更是一股力量,促进和变革环境法的发展。此外,第四代环境法中的一体化多模式治理的演变将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联系,包括《水法》、《能源法律和政策》等。当然,一体化多模式管理将是新一代环境法和环境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的阻碍,使得前三代环境法难以有效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适应性”治理模式是一种需求,因而成为第四代环境法中的一个关键特征。目前对环境法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法如何适应环境现状的问题上,而不是着眼于环境法是否会适应环境。为了真正响应对新的适应办法的需求,即将实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灵活性。美国第四代环境法最突出的特征是,它将摒弃碎片化和单一化(或一刀切)的治理模式,支持“一体化多元模式”。就像阿诺德(Arnold)教授所描述的“在环境治理中使用的多元治理模式或方法是指至少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5]多元化治理模式会涉及使用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例如命令和控制监管、侵权责任、公共教育和市场激励等。在美国,多元化治理模式也可以描述为使用多个特定的机构或机制来治理环境,如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机构、美国森林服务机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国家自然资源机构、木材行业组织机构、特定的木材公司、地方政府、环保团体、当地的民间团体、学校、非正式的多方参与团体、联邦法院、州法院等。简而言之,即利用多个机构、组织、团体或权威机构从事环境治理工作。关键是如何在最佳时机通过“协调或协作”的方式使多元化治理工具达到一种最好的治理模式。例如,改变濒危物种或受威胁物种的主要栖息地的联邦法规与保护敏感栖息地的地方区域法规尽管都符合“命令和控制”治理模式,但两者的法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在对这个新兴治理环境体系的构建中,新模式将不仅仅是“附加的或具有竞争性的”,而是“将其成为一种促进和变革环境治理的力量”。正如阿诺德教授所言“这种多模式治理方式,使得新一代具有适应性的环境法在本质上是多中心化的,利用各种不同的环境治理工具,从多种解决环境问题方案中寻找最佳结果。”[7]
2“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的具体内容
2.1“一体化多模式”的内涵
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促使环境法体系变得更加一体化[8]。“一体化多模式”治理试图以整体的、综合的或协调的方式将多模式治理连接或者是连接一个系统的多个方面的过程[9]。之所以使用“一体化多模式”这个词,是因为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及子系统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几乎不可能只使用同一种治理方式就能解决整个环境问题。复杂的环境系统特征是多样的、不连续的、甚至是混乱的,这种混乱迷惑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导致其无法真正掌握和实现完整而纯粹的环境治理结果[10]。
理论上,“一体化多模式”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在问题框架层面上,环境法和环境政策渐渐开始关注生态系统内的关联性、社会系统内的关联性以及这两种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以综合或相互联系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例如有些环境问题跨越了不同领域或学科,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上产生了不连续性的影响或不同类型的问题。其次,在对这些问题的应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上,法律、政策、计划、行动等,将越来越需要社会上多个机构、组织、社团和个人的相互联系、相互协作、共同行动。最后,在反映或解决方案本身的层面上,环境法面临着挑战,需要对不同的治理工具和方法做出调整。
在环境法中,依据相关理论得出,“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正在兴起,并将作为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给环境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其需要有多种保护治理模式。此外,“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已经开始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以下是对环境法律“一体化多模式”治理结构中的四个连接点的具体分析。
连接点一,环境治理实施者
在一个复杂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一个行动者、团体或机构能够有效地解决大规模、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没有哪一个行动者、团体或机构能够不受其他行动者、团体或机构的影响而单方面采取行动。关于多方环境治理实施者相互协作的一个难点是,“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合作行为者或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共识。许多“新治理”理论的一个中心特征是,借助第三方污染治理企业的专业优势和规模效应,以及在完成污染治理目标上的成本和效果优势,来实现降低企业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之目标[11]。然而在美国,为了避免在价值取向和结果取向中做出权衡,并没有建立严格的法律或制度,容易导致环境治理实行者实施无效的、含糊的或无法执行的计划。
连接点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的第二个連接节点集中于复杂的环境问题具有多样性等特征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社会反应。例如,环保部门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负责监管的生态系统保护被认为比传统的按政治区域划分管辖的环境问题治理方式更可取[12]。关于环境治理目标的多功能性问题,我国郭武教授提出的环境法所蕴含的增益性功能据以产生的主动性、“计划性”制度和机制,对法治实践具有预测功能。这一功能一方面改变环境法律制度生成的内在逻辑,使超越“回应型法”进而形成超前性、预断性环境立法的制度生成方式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将直接对环境法治的运行过程产生重大影响[13]。例如,美国地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在联系地方活动、外部条件方面的影响更大、更具有灵活性,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此外,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考虑了不同规模的系统功能范围,并试图寻找适当的连接节点。
连接点三,环境信息与决策的相关性
随着环境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如何通过一体化多模式的治理方式产生和传播环境信息是目前需要讨论的话题之一,这些信息通常由许多不同的环境行为者、环保机构、环保组织以及环保团体搜集,可为环境决策者在做出相关环境决策时提供真实数据依据。例如,在美国绿色建筑协会驱动下的LEED认证项目中提供的环保信息和建议有效地减少住户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美国部分州和一些国家已经被列为当地“绿色建筑”的法定强制标准。又如,在流域规划过程中产生和收集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为流域内的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说明对流域潜在的影响因素,同时这些信息也被用在联邦和州的监管项目、土地开发设计和其他流域的管理中。尽管如此,一体化多模式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行为和环境条件之间复杂关系的信息,无论是通过法规、标准规范还是通过实践,均应当被考虑和用在决策当中。同样,一体化多模式治理要求及时反馈,通过反馈信息,针对不同环境计划进行修改、调整或做出新决策,这样才能更好地采取措施或有效考虑决策的结果。否则,“一体化多模式”的使用只有外观,而没有实质的内容,无法有效治理环境。
连接点四,创新性与治理能力相结合
一体化多模式治理的第四个连接节点是将创新与环保机构或环保组织的治理能力联系起来。尽管目前的环境制度会带来短期的环境收益,但随着环境系统的完善及人们的环保意识提高,需要环保机构或环保组织在不断发展的外在条件和压力下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及应对能力。例如,提高各种不同的环境治理模式或治理方法的可适用性,加快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可适用性的提高可能与环境体系结构的完善有关,也可能与通过网络或共享平台生成并传播的创新理念有关,或者与改进的信息生成技术、监视结果、评估(循环反馈)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有关[14]。同样,如果多种环境治理模式分散但又充分地联系在一起,以避免各治理模式相互破坏或相互冲突,那么利用多种模式治理是一种存在风险且效果显著的战略。例如,我们看到各级环保机构、多方参与者、甚至环保团体在选择使用不同的环境治理工具以应对土地使用对河流、水质、居民供水情况的影响时,都需要考虑各种治理模式的适用程度。然而,这种适用度是双向的,环保机构和组织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和相关资源来进行治理模式的创新。传统的单一化和高度碎片化的环境治理模式阻碍了环保机构和环保组织提高其创新能力,从而影响治理环境的效果。
然而,如果我们要想改善环境或促进环境法的发展,首先需要了解环境法产生的背景和发展历程。我们必须从环境法特有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结合法律多元化特点来看,环境法的体系是复杂的,而且具有自适性,这表明我们在学习环境法律过程中应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好的、坏的还是中立的[15]。通过对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的理论和实证考察,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估其在实现环境治理、应对我们当前和未来环境问题以及协调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有效性。此外,一体化多模式的环境治理仍需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继续改进与发展,一体化多模式治理如果要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就需要不断地与环境发展相适应。
2.2“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的目的和意义
如上所述,一体化具有整体性,具体指把部分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预期结果也是完整的。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主要是指环境的完整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人类发展的同时也要维持着植物、动物与人类生命的平衡发展,并且必须允许这种发展持续下去。目的是想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的弹性、多样性和完整性,确保包括空气、水和土壤在内的基本自然生命系统的持续稳定发展。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生态功能的存在是持久的,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理念。环保专家也使用“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服务”一词来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维持并满足人类生活条件的过程[16]。“一体化多模式”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相对其他环境治理模式,它具有优先性和不可替代性[17]。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一体化多模式”治理,需要明确生态阈值以确保达到生态完整性的目标。生态阈值界限的规定,限制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的破坏,此外,还需要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将对生态阈值的界定纳入法律框架,作为全面、可审查、可执行的法律法规。例如对空气、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阈值界定。只有将其作为法律规定的实质内容,才能更好的实施环境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也可以被看作是新一代国际环境治理的种子,这种治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改善环境[5]。然而,在现实中,未能真正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特定物种的目标,因此,必须构想出一种新的理论,以产生一种新型的、更有效的环境治理模式,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模式就是其中的一种创新治理模式[18]。但是,我们不能只从理论上探讨治理模式本身的利与弊,还要看实际的执行情况。在环境法实施层面上,效率是关键,实际落实推动环境改善的进度。
从执行的角度重构环境法时,“一体化多模式”的环境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执行的难度。治理模式的落实必须根据环境问题的变化进行调整,比如在气候变化时期的物种保护问题,日益复杂且存在多方利害关系。因此,需要用“一体化多模式”的治理方法解決。如果新一代环境治理是多模式的,并且具有一体化的性质,那么从根本上说,利于获取协同效应。当今,环境治理问题已经涉及到国际层面、国家层面以及国家以下各级监管机构之间的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的出现将更加注重把多元管理模式融合一体并纳入环境治理体系中。美国“一体化多模式”的环境治理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与全球环境治理紧密相连,从而认识到类似的发展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从特殊视角为理解美国国内环境政策提供重要信息,特别是当它涉及到全球重大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等,可以提出改进方案。“一体化多模式”治理的实施证实了之前分散式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甚至证明了分散式治理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实现“一体化多模式”治理对于应对全球复杂的环境问题至关重要。
正如阿诺德(Arnold)教授所说,“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的出现,大部分是因为由复杂的、潜在变化、多样化、多重集合的环境问题导致,且在现行环境法代际交替中并没有重视解决方案甚至在回避解决的办法。他列举了美国水资源、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等交叉的环境问题来说明这一类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是导致多种治理模式融合为一体的驱动因素。例如,为了保证水源的充足性和可用性,不仅需要考虑《清洁水法》对允许工厂直接排放的规定,还需要考虑州和地方政府颁布的《土地利用政策》,同时,还需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阿诺德教授以鲁尔和萨尔茨曼的研究为基础,将这种环境治理模式描述为“政策丛林中的超级政策丛林”,因为许多相互作用的组合为实现环境治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法律体系[19]。在美国第四代环境法发展的背景下,“适应性法”(Adaptive law)的概念随着阿诺德等教授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体化多模式”的特点[20]。其核心观点是,法律本身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生态条件而改变,并以促进社会和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方式来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目前的运作,似乎正在展示其适应能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谈判的具体轨迹表明,它的适应是朝着更大程度上的“一体化多模式”治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像《京都议定书》那样自上而下、结构相对僵化,而且只关注单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2.3对美国第四代环境法治理模式的利弊分析
美国第四代环境法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复杂的环境问题,进而也开始迎接全球环境和严峻地区的环境问题的挑战,如生态系统、水文系统和全球气候系统等[21]。因此,在对庞大的环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来应对复杂的环境问题的背景下,能够更好地理解环境治理模式向“一体化多元模式”的转变过程。
首先,美国第四代环境法提倡的环境治理理念与环境治理模式本质上是渐进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环境治理系统能力方面的提高不仅仅是渐进式或小范围内的提高,而是巨大的、甚至是转型的提高。第二,美国第四代环境法对弹性科学的运用允许开发和适用严格的标准,这些标准更符合社会—生态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而不仅是静态严格的规则,旨在维持或治理现有环境使其完全恢复到某种扰动前的状态[22]。例如,根据相互联系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作为主要驱动力量来制定标准。这样的标准起到预先警告的作用,即不能试图接近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生态阈值。同时还要考虑社会系统的复原力、环保机构的复原力以及生态系统的复原力,统称为多元复原力[23]。第三,社会—生态复杂性是社会系统无法单一“解决”或简化的问题。因此,承认并围绕社会—生态系统复杂性构建的环境法律框架比之前忽视或逃避这一现实的环境法律框架更具有可行性,可见,美国第四代环境法试图解决社会—生态系统复杂性的问题。最后,美国第四代环境法的特点主要以非正式或紧急反馈循环路径的方式达到“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的目的[24]。
我们在看到美国第四代环境法对环境治理问题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不足。首先,美国第四代环境法中提倡的“一体化多模式”的治理方式目前只是一个美好的發展趋势,而并没有真正的转变。这将意味着暂且只能在小范围内渐进式的提高生态环境系统的弹性和适应性,而不足以改善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不足。第二,美国第四代环境法仍然会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的保护力度不足,因为相关环境决策和执行的依据缺乏严格明确的强制性标准。没有任何规则、标准或问责机制来限制这种灵活性,而这种灵活的执行方式会助长对环境的开发和破坏行为。第三,生态环境系统的复杂性依然存在,美国第四代环境法可能会考虑相互关联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但这种认识本身并不足以建立有弹性的环保机构并对这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回应。美国社会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未来将面临的环境问题,无论采用哪一代环境法,都将难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无论是适应性环境管理、环境规划、环境法还是环境治理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未能将循环反馈的理论转化为循环反馈的路径。在大多数环境案例中,很少建立正规的监管体系和严格的评判标准,此外,根据相关环境监测和评估的结果,我们也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评估与改进,同时强调环境治理过程如果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流程来评估,那么就无法基于这些评估结果进行治理决策上的调整。
3“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对中国的启示
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广泛性和长远性,决定了环境治理必须是系统化、规范化的统一管理。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形成了“国务院统一领导、环保部门统一监管、地方政府分级负责”[25]的环境治理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新的环境、经济、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发展,这种环境治理模式存在的“部门分散、地方分割”等诸多“碎片化”现象也逐一暴露出来[26]。通过对美国第四代环境法“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的具体了解及利弊分析,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在政策实施、环境理论以及环境实践方面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启发。
3.1积极贯彻落实“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不仅表明中国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同时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对人类法律重新塑造以使人的行为同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相协调”[27]。由于美国第四代环境法才刚刚开始发展,我们还不能准确地描述构成它的主要框架与影响要素。但是,我们可以对其核心内容进行一个相对有根据的描述,即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现状以及所产生的环境政策要求,将推动新一代环境法走向“一体化多模式”治理的方式,它摒弃传统的碎片化和单一化(或一刀切)的治理模式,用以解决复杂化、多样化、动态化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治理的“一体化多模式”概念的提出也反映了人们对环境治理对象和治理过程的复杂性的理解以及在开发新的治理方式时对这种理解的应用。在传统的环境法理念无法有效应对今天的环境问题时,必然面临着在原有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对环境治理方式继续进行革新与发展。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首先受到环境法理念的影响,只有对传统环境法理念重新进行定义,积极贯彻落实“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才会真正的实现环境保护,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局面。
3.2强调整体主义新生态观
美国第四代环境法提倡的“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体现了环境法理论中的整体主义。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看,“环境法作为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如何生存的法律规范体系”[28]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在环境法中关于整体主义共有三种学说:第一,生物中心整体主义,其中所有生物被认为是与自然环境共存的整体;第二,生态中心整体主义或环境整体主义,即它将自然系统视为一个整体;第三,人类中心整体主义,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整体实体。目前许多学者对整体主义进行分类概括,主要有:实体整体论、人类中心整体论、等级制整体论和普遍的宇宙整体主义。
实体整体论认为每一类实体都具有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其组成部分不同,并将其统一定义为一个整体。人类中心整体主义将人类视为整体,突出了人类身体和灵魂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本质。而环境不一定被认为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整体主义中,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视为互补关系。分层整体主义将宇宙的整体视为一个完整系统,他们之间具有子系统和超系统的关系,形成一个等级。普遍的宇宙整体主义通过整合宇宙中的所有元素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在这个模型中,人类是宇宙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以及所有独立的实体,无论是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都必须在整个宇宙中以整体形式来理解。罗杰斯认为单一的人类和单一的环境是开放系统领域中的独特领域,这表明宇宙是整体的领域,作为整体的领域被视为不可分割的,这些观点符合实际整体主义的原则。强调整体主义新生态观,重新肯定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和谐关系,有利于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完善。
3.3注重基于综合生态系统理论的调整方式
美国第四代环境法所采取的、基于一体化多模式的调整方式,其实就是目前中国环境法学者强调的、基于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包括综合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调整方式。所谓综合生态系统管理(Integrated Ecosystem Management,简称IEM)是指管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一种综合管理战略和方法,它要求综合对待生态系统的各组成成分,综合考虑社会、经济、自然(包括环境、资源和生物等)的需要和价值,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行政的、市场的和社会的调整机制,来解决资源利用、生态保护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以达到创造和实现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多元惠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29]。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要求采用合理的管理方法来处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问题,并要求试图解决生态系统功能认识上的不足。因生态系统进程是非线性的,且进程的结果具有滞后性、不连续性、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必须能处理这样的不确定因素,而且应该及时反馈在实践和研究中探索的内容。即使在因果关系还没有完全被科学确定的情况下,也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以免对环境造成严重后果。
综上可知,美国第四代环境法倡导的“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模式与我国学者提倡的综合生态系统的管理模式都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可持續性的特点,是一种跨部门、跨区域、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系统,不仅着眼于短期的环境治理,而且还要考虑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两者均属于适应性管理,即因地制宜,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及时作出管理策略上的调整,以便灵活应对。但目前我国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还不够明确,缺乏具体的生态系统管理制度,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4结语
阿诺德教授所描述的美国第四代环境法中的“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似乎反映了比美国任何时期环境法提出的治理模式都可靠有效。通过近期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趋势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体化多模式”的环境治理方式即基于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的环境治理方式,这种管理模式与美国第四代环境法所讨论的环境治理模式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治理模式相关联。同时也表明,“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将在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中得到关注,此外,还要考虑参与全球环境政策的工具以及权力的范围等因素。从这个视角来看,主张“一体化多模式”环境治理方式,有可能对大规模复杂的全球环境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如果还按照过去几十年来单一化、碎片化和规模化的模式来理解,那么这些问题似乎难以解决。尽管如此,仍需要强调这一观点对今后研究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多模式”治理方式的实施不仅促进环境政策的发展,同时还可能大大提高人类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能力。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的环境状况比之前有所改善,我们所采用的环境治理模式也在逐渐改进。在美国,仍会以国家干预的方式来引导人们加强对环境的关注与治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关注环境问题,但并不能作为一种最佳方式为国家实现环境治理提供基础。仅凭所谓的干预主义成功案例,并不应成为在制定未来环境政策时的依据。当然,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采取严厉的监管手段是减轻或防止环境损害的最佳选择,或者,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所有治理手段中的最佳选择。事实上,当颁布新一代的环境法和环境政策时,环境政策制定者应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目前制定的环境法规,以及它在政府监管中的位置,是否会阻碍人们实现环境治理的最佳途径。
(编辑:于杰)
参考文献
[1]MILLEF J G. A generational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its grand themes: a near decade of garrison lectures[J]. Pace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002,19(2-3):501-514.
[2]BINDER D. Looking back to the future: the curmudgeons guide to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law[J]. Akron law review, 2013,46:993.
[3]吕忠梅.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28.
[4]LAZARUS R J.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and the graying of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law: reflections on environmental laws first three decad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Virginia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2001,20:104.
[5]ARNOLD C A. Fourth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law: integrationist and multimodal[J]. William & 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review, 2011,35:771-791.
[6]谭冰霖.论第三代环境规制[J].现代法学,2018(1):124.
[7]ARNOLD C A. Working out an environmental ethic: anniversary lessons from mono lake[J]. Wyoming law review, 2004(4):1.
[8]FISHMAN R L. The divides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problem of harm in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J]. Indiana law journal, 2008,83:661-663.
[9]FOLKE C, PRITCHARD L, BERKES F, et al. The problem of fit between eco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ten years later[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7(12):30.
[10]BROWN K. Hum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reality check[R]//Governing sustainability, 2009:32.
[11]刘长兴.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法律责任基础与合理界分[J].法学,2018(6):182.
[12]LORD C P, STRAUSS E G. Natural cities: urban ecolog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urban ecosystems[J]. Virginia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2003,21:317-325.
[13]郭武.论中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形成和发展趋势[J].法商研究,2017(1):91.
[14]DOREMUS H. Precaution, science, and learning while doing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J]. Washington law review, 2007,82:547-568.
[15]NOURSE V, SHAFFER G. Varieties of new legal realism: can a new world order prompt a new legal theory [J]. Cornell law review, 2009,95:61.
[16]DAILY G D. 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 [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65.
[17]CONSTANZA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 Nature, 1997(15):253.
[18]LONG A. Global integrationist multimodal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fourth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law[J].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law, 2015,21:170.
[19]RUHL J B, SALZMAN J. Climate change, dead zones, and massive problems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 guide for whittling away[J].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10,59:80.
[20]ARNOLD C A, GUNDERSON L. Adaptive law and resilience[J].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013,43:10426-10428.
[21]YANG T, PERCIVAL R.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law[J]. Ecology law quarterly, 2009,36:615.
[22]CRAI G R, BENSON M H. Replacing sustainability[J]. Akron law review, 2013,46:841-862.
[23]KARVONEN A. Politics of urban runoff: nature, technology, and the sustainable city[M]. MIT Press, 2011:156.
[24]FELDMAN D, INGRAM H. Making science useful to decision makers: climate forecasts, water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networks[J]. Weather, climate & society, 2009(9):1.
[25]周建鵬.区域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湘黔渝“锰三角”为例[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2.
[26]蔡立辉,谭海波.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J].社会科学,2010(8):12-19.
[27]ROBINSON N A.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law perspectives on legal regim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Widener Law Symposium Journal, 1998(3):247.
[28]吕忠梅.环境法的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
[29]蔡守秋.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与法(下)[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