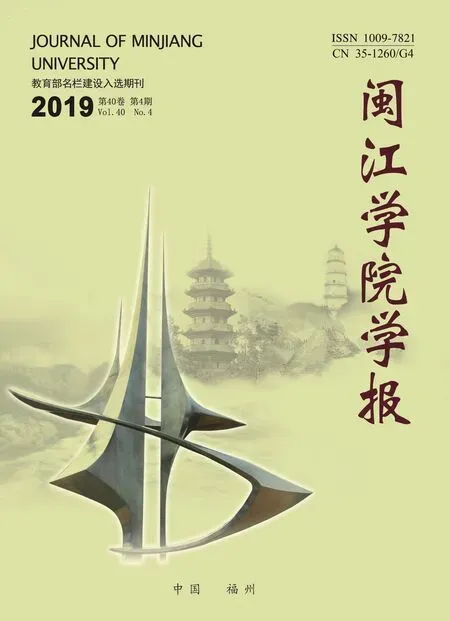从“三时论门”看唐代近体诗文本结构的时间轴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引言
佛教在分析诸法缘起及有情众生的生命流程时,从时间序列看,无论小乘大乘经典,都好用“三时”作为观测点或切入点。后秦鸠摩罗什译《成实论》卷二《论门品》即云:
有“三时论门”,若于此事中说名为色,若色曾有、当有、今有,皆名为色。识亦如是,若识曾知、当知、今知,皆名为识。如此等,名“三时论门”。[1]第32册,278
此“曾”“当”“今”三时,通俗地讲,就是指过去、未来和现在,并且,用它可以解释任一名相,如色、受、想、行、识之“五蕴”,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之“十二因缘”等。
什译《十二门论》中,第十一门叫作“观三时门”[1]第30册,166-167。不过,大乘中观学派主张缘起性空,认为“三时”仅在俗谛层面成立,隋吉藏《十二门论疏》卷下《观三时门第十一》就明确指出:
问:大小内外,一切因果,不出三时,论主并破,即应无因果耶?
答:三种因果,皆出佛经,并是如来适化之说。一切诸法,无决定性,佛有无量方便,而为利人显道。但学人封执定性,故论主并须破之,然后无方可适时而用。[1]第42册,211
虽然吉藏法师更重视“三时”的空性本质,却依然承认其为方便之说,不可或缺,同样具有弘法教化之用。
《成实论》《十二门论》之“三时”观,与其他佛典所说的“三际”“三生”“三世”含义相同(1)参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台北:佛光出版社,1988年)“三世”条(第536页下栏-537页上栏)、“三生”条(第543页下栏)、“三时”条(第596页中栏)等。。概言之,从有情众生的生命进程看,过去世也叫前生、前世、宿世、前际、前身(过去身),现在世又作现世、现生、今生、中际、今身(现在身),未来世也称来世、来生、当来、后生、后世、后际、后身(未来身)。而三时、三际、三生、三世与三身(2)三身,一般指佛的三种身,又称三佛身,包括法身、报身和应身。但其他人也可以有“三身”之别,只是含义迥异,如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十七就说佛与象首舍利弗讨论过过去身、现在身、未来身“一时有不”的问题(《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12页中栏)。本文所说三身,即指与三时、三世同义者。的时间序列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三种,即线性式、循环式、线性和循环交互式(3)此分类法,是参照周利群《循环与线性交互的佛教时间观》(《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第124-130页)而来。又,周氏论据主要取自佛教譬喻经。。
佛教三世流转、三生(身)相续的观念东传后,它借着因果报应的思想要义,对中土各阶层人士的世界观都有所影响,并在中古以降的各种古典文学作品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小说类文体最受关注,成果亦丰,并涉及题材、情节、叙事母题、叙事结构、叙事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4)如孙逊《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第69-77页)、白化文《三生石上旧精魂──汉文学对通过佛教经典传来的古代南亚次大陆文学素材的使用与扬弃》(《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第1-8页)、熊明《论〈圆观〉与三生石意象》(《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第232-236页)、刘惠卿《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母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李小荣《晋唐佛教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而对古典诗歌之佛教时间观的检讨,尚缺少系统性(5)于此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性论著还是较为常见的,如萧驰《中国古代诗人的时间意识及其它》(《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第16-23页)、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史成芳《诗学中的时间观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丁威仁《三国时期魏地文士“惜时生命观”研究──以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之诗歌为研究对象》(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许迪《先秦至魏晋诗歌中的时间意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若就唐诗时间意识方面的研究论著而言,给笔者启发较多者有谭绍芬《论唐诗中表现时间意识的几种典型句式》(《湖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第64-69页转第73页)、王钟陵《唐诗中的时空观》(《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第131-142页)、李浩《论唐诗中的时空观念》(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四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38页)、李晖《论唐诗的时间描写》(《北方论丛》1994年第2期,第44-49页)等,但它们的重点基本上不在或较少涉及佛教的时间观。。兹仅以唐人近体诗(6)目前对唐代近体诗的研究,或关注其源流(如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或检讨格律之正、变(如霍松林《简论近体诗格律的正与变》,《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第104-117页),或论律句类型与表现(如张培阳《近体律句考——以唐五律为中心》,《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第49-60页),或比较诗人古体今体之变异(如尚永亮《柳宗元古近体诗与表述类型之关联及其创作动因》,《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第52-59页),诸如此类,虽给后人诸多启示,却鲜见专论近体诗文本结构之时间轴者。为例,从“三时论门”的角度分析其文本结构之时间轴的表现形态及其蕴含的佛教思想(7)目前虽有几篇论文涉及了唐人近体诗尤其是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时间观问题,如陈允吉《王维〈辋川集〉之〈孟城坳〉佛理发微》(《佛教与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2-282页)、王志清《审美时间中的生命体验——王维的时间意识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6-20页)、初娇娇《“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论佛教时间观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中国美学研究》第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9-104页)等,然诸人研究的重点是佛教(或禅宗)时间观与王维诗作的互动关系,而不是诗歌文本结构所呈现的佛教时间序列。。
二、文本结构之时间轴的三大类型
笔者对唐人近体诗文本结构的分析,是以诗人当时的创作语境为前提,即强调作品生成的历史场景或现场性。因为对后世读者而言,所有唐代诗人,其作品都已成为过去,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诗人创作的时间原点,并把它想象成凝固的现场,并以此来释读相关作品的文本结构的时间轴,当有更广阔的操作空间。而其时间主轴的基本形态,主要有三大类型。
(一)线性式
线性式可分成完整型和简略型。
1.完整型
其时间轴,一般只涉及三个时间点——去、今、来(当然,有时诗人也会省去相关的时间名词或时间副词),排列顺序既可按照自然之先后法则,也可以自由变动。
(1)按“去·今·来”之自然顺序者
此类形式最为常见,兹举4例:
1)孟浩然《过故人庄》曰: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2]
此五律,是孟浩然田园诗的代表作之一。从时间结构看,首联说的是过去,即故人为了诗人的到来,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食物;中间两联,叙述诗人到访现场时的所见所闻,属于当下;尾联则展望重阳日的再相聚,显然是将来要做的事情。
2)灵一《雨后欲寻天目山,问元、骆二公溪路》曰:
昨夜云生天井东,春山一雨一回风。林花并逐溪流下,欲上龙池通不通。[3]卷809,1 987
此七绝的时间轴,诗僧是以眼前所见的雨后景物为基点(第二、三两句),第一句回溯过去(昨夜),末句属于设想之辞,即问元、骆二人由此地能否到达目的地——龙池,因其在天目山的主峰龙王山上,而“欲”字的时间指向,毫无疑问是将来。可见,本诗的时间轴,与前述《过故人庄》完全一样,都用“去·今·来”的自然顺序。当然,两者也有小小的不同,即孟浩然结尾期盼的将来,是较远的将来,而灵一所问是较近的将来。
3)郑谷《忍公小轩二首》(其二)曰:
旧游前事半埃尘,多向林中结净因。一念一炉香火里,后身唯愿似师身。
严寿澂等人认为该组诗属于《西蜀净众寺五题》之一,大概作于郑谷入蜀六年之间(从广明元年十二月至光启元年春),尤以中和二、三年间(882—883)为最近是[4]。细绎其内容,是作者向忍公所作的倾述:首句叙说了诗人过去的交游状况;第二句承前而来,是诉说自己当下的一般状况,其内容与第一句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之所以要结缘佛教,是因为旧游凋零、前事难再;第三句依然叙当下之事,拈出礼忏之细节描写;第四句是发愿,诉说来世,希望能成为像忍公一样的出家人。同样,三、四两句也存在因果关系,即诗人当前的修行之因,必将成就“似师身”的果报。
4)司空图《丑年冬》曰:
醉日昔闻都下酒,何如今喜折新茶?不堪病渴仍多虑,好向灉湖便出家。
此七绝作于天祐二年(905)冬[5]。因诗人当年八月曾应宰相柳璨之召赴洛阳,故首句之“醉日昔闻”云云,当指与此有关的事情;第二、三两句,转向描述当下的生活细节,即诗人归山之后,好以新茶来消除其渴病(暗用“长卿病渴”之典,长卿,即司马相如);末句之“出家”,则在表述诗人今后的人生志向。本诗与前述郑谷诗的文本结构一样,首句写过去,二、三句写现在,末句讲将来。
(2)“去·今·来”顺序有所变动者
这种情况,主要包括下列几种变形:
1)“今·去·来”
如韦应物《咏露珠》曰:
秋荷一滴露,清夜坠玄天。将来玉盘上,不定始知圆。[6]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首句写眼前所见,交待露珠当前的属性,它是秋天荷叶上的朝露;次句溯源,指向过去,认为它来自清夜的玄天;结尾两句,则属于设想之辞,作者要是将它置于玉盘,可能就改变了露珠原来的圆形。
再如刘禹锡《答张侍御贾喜再登科后自洛赴上都赠别》曰:
又被时人写姓名,春风引路入京城。知君忆得前身事,分付莺花与后生。[7]
贞元十年(794)春,因作者二次登科成功并准备参加次年的吏部试,途经洛阳时遇到侍御史张贾,后者写诗向他祝贺(但张氏原诗已佚),此则为刘禹锡的答谢诗。其中,前两句自叙述的是二次登科之事,属于当下的场景;第三句“前身”云云,则是转述张贾追忆其科考历程(张贾,贞元二年中进士科),时间上属于过去;第四句“分付”的内容,当指张贾对诗人良好的祝愿,即预祝他到长安后同样春风得意,捷报频传,时间指向是未来。不过,由于刘禹锡此诗具有明显的叙述性,涉及他和张贾相识相知的过程,故在结构与前述韦应物之作稍有不同,并非聚焦于一事一物,特别是第三句的重心,实际上转向了张贾。当然,结句为“合”,兼叙自己和张贾之事(8)曹逢甫主张绝句的结构也有“起承转合”(参《从语言学看文学——唐宋近体诗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2页),笔者认为,刘禹锡此诗就很有代表性。。
2)“去·来·今”
如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曰: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3]卷515,1 307
该诗题目又作《闺意献张水部》,它是朱氏临近考试献给水部郎中张籍之作,作者巧妙地以新娘妆饰适宜与否作比喻。在其叙事的时间轴中,第一、二句分别写“去”“来”,三、四两句转写“现在”,通过新娘之问,刻画了朱庆馀忐忑不安的心理。
3)“今·来·去”
按,此后三种形态,相对说来,虽然不如前三种常见,但是,也能找到相关的代表作,如欧阳詹《出蜀门》曰:
北客今朝出蜀门,翛然领得入时魂。游人莫道归来易,三不曾闻古老言。[3]卷349,864
本诗第一句“今朝”,点明了北客离开蜀门的时间,第二句“入时”,表面上叙述的是过去之事,但是,“领得”的心情却发生在离开之时,所以,整体说来,前两句的叙述时间仍然着眼于当下。第三句“归来”(回归到家乡)的时间点,显然转向了遥远的将来。第四句为倒装,正常语序当作“曾闻古老三不言”,古老,即故老,其时间节点陡然折回到过去。“三不”,即“三不归”(典出《管子·轻重丁》),指三种乐而忘归的情景(意谓蜀地容易使人流连忘返)。而且,三、四句之间,还存在因果关系,但其顺序是先说结果再追溯原因。
4)“来·今·去”
如储光羲《寄孙山人》曰:
新林二月孤舟还,水满清江花满山。借问故园隐君子,时时来往住人间。[3]卷139,325
此诗前两句着眼点在将来,设想孙山人下山后乘舟还回江宁的场景(9)按《御选唐诗》卷三十二所注,新林即新林浦,一名新林港,在江宁府西南二十里。;第三句点题,储光羲向孙山人发问的时间,应在寄诗的瞬间,而“住人间”的“时时”,则属于孙山人过去的行为。当然,末句和前两句也存在照应关系,正因为孙山人过往常住人间,所以,他将来再回江宁城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
5)“来·去·今”
如段成式《送僧二首》(其二)云:
想到头陀最上方,桂阴犹认惠宗房。因行恋烧归来晚,窗下犹残一字香。[3]卷584,1 489
要准确理解本诗的时间轴,必须结合组诗第一首七绝之“《形神不灭论》初成,爱马乘闲入帝京。四十三年虚过了,方知僧里有唐生”[3]卷584,1 489。从两首诗的前后语境及结构特点(第一首在文本结构上,前两句重在叙事,后两句重在议论)看,可知第二首是先从将来着笔,前两句虚拟了僧人回归寺院之后的场景,三、四两句陡然转向诗人的自述,既有点题之用(第三句交待送别僧人的时空是在夕照下的长安),又说明了诗人回家的过程,因为与僧人感情之深,依依不舍,所以才回家甚迟(回家行为已经完成,时间上属于过去),而回家之后,见到的是燃烧殆尽的一字香(香火依旧,观察的时间点应为现在)。
2.简略型
此类型是指时间轴只涉及“去”“今”“来”中的任意两个时间节点,如“去·今”“今·来”“去·来”等表现方式者。其实,它们在中国早期诗歌如《诗经》、楚辞中就有广泛运用,唐诗亦然,此不细论(后文于此,略有分析)。
(二)循环式
循环式的时间轴,可有多种类型。但据笔者对近体诗的观察,最常见是双循环和轴对称循环,而且,在“去·今·来”三个时间节点中,往往只出现两个。
1.双循环
本类型是指时间节点重复出现两次者,较常见的是五种表现形式。
(1)“去·今”循环
如顾非熊《关试后嘉会里闻蝉感怀呈主司》曰:
昔闻惊节换,常抱异乡愁。今听当名遂,方欢上国游。吟才依树午,风已报庭秋。并觉声声好,怀恩忽泪流。[3]卷509,1 286
会昌五年(845),在唐武宗的亲自干预下,“举场角艺三十年”的顾非熊,终于进士及第,扬眉吐气[8]。据题目及上下文,故知该五律作于该年秋天长安西市的嘉会里。其文本结构,可分成上下两篇。上篇“去·今”的时间跨度较大:首联“愁”字,概括了诗人数十年落第之后听闻秋蝉的感受;颔联“欢”字,概述的是及第当年的心理状态,并且前后持续了大半年,因为进士放榜时在春天。下篇“去·今”的时间跨度极短(应是会昌五年秋日某个中午的前后):颈联的虚词“才”“已”,表明作者虽然一闻蝉鸣就感受到秋风的凉意,但是,由于心境不同,往岁的忧愁早已烟消云散;尾联虚词“并”“忽”,则说明不论“好”的感觉,还是感恩的行为,都是现在进行时(其中,“并”字具有总括蝉吟、秋风之用)。换言之,两个“去·今”循环的时间轴中,有前大后小之别。
(2)“今·去”循环
如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其三)曰: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9]1 211
是诗作年及“尚书”所指是张建封还是其子张愔,目前争议较大(10)相关论文之介绍,参[日]福本雅一著,李寅生译《燕子楼与张尚书》,《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15-22页。,因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故暂且搁置不论。红粉,一语双关,一指女性使用的脂粉,一指张家的舞妓盼盼。若从叙事的时间轴看,作者采用的是“今·去”循环式,一、三两句“今春”“见说”及第二句“曾到”,时间分别指向现在、过去,当无疑义。末句使用反诘修辞格,意指盼盼长期弃用脂粉,早已心灰意冷,所以,其时间指向应为过去[10]。
(3)“今·来”循环
如刘商《送王永二首》(其一)曰:
君去春山谁共游?鸟啼花落水空流。如今送别临溪水,他日相思来水头。[3]卷304,766
是组诗题名又作《合溪送王永归东郭》。第一首以设问开头,问是当下之问(实写),答的内容却指向将来。“啼鸟”“落花”“流水”等,是诗人想象王永回到东郭之后的所见所思(虚写),虚实相生,颇有意趣。三、四两句,“如今”与“他日”对举,写法与一、三两句相同,并有一一照应之用。
(4)“来·今”循环
如贾至《送王道士还京》曰:
一片仙云入帝乡,数声秋雁至衡阳。借问清都旧花月,岂知迁客泣潇湘?[3]卷235,586
本诗作于贾至乾元二年(759)八月至宝应元年(762)冬被贬岳州司马期间(11)有关贾至贬谪岳州之作品名目,参肖献军《贾至年谱》(《唐代湖湘客籍文人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7-59页)。。其文本结构的时空主轴都颇有特色,皆用双循环,即“帝京(将来)→贬所(现在)→帝京(将来)→贬所(现在)”(帝乡、清都,同义。用衡阳不用岳阳,一方面是受“衡阳雁回”之典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是自身平仄的需要,即第二句第六字需用平声字,而“岳阳”之“岳”为仄声字(12)又,贾至此七绝,总体说来是失粘,但一、二句与三、四句各自的平仄关系又合律。。当然,衡阳在岳阳之南,北雁南飞是要经过岳阳。若以接近联想视之,衡阳也可指代贾至的贬所岳阳)。从时间轴言,第一句是设想之辞,即想象王道士已经入京;第二句则回归送别现场,并点明送别王道士时在深秋;第三句承第二句而来,因为北雁南飞过冬之后必回北方,诗人触目伤怀,进而产生了自己在不远的将来被召回长安的希望,所以才借秋雁之口来问候帝乡旧时的风物,但第四句诗人的自答,其主旨又回归当下的客观事实,即自己依然是潇湘迁客,正过着以泪洗面的贬谪生活。
(5)“去·来”循环
如卢纶《寄郑七纲》曰:
小来落托复迍邅,一辱君知二十年。舍去形骸容傲慢,引随兄弟共团圆。羁游不定同云聚,薄宦相萦若网牵。他日吴公如记问,愿将黄绶比青毡。[3]卷278,703
此七律是卢纶向老友郑纲的感恩述怀之作。首联、颈联重点追忆自己过去与郑七的交往缘由,虽说诗人自小命运多舛,却承蒙对方知遇,前后竟达二十年之久,期间,两人即便聚散不定,对方仍然像蛛网一般牵挂自己;颔联、尾联所述内容,同为想象,不过,颔联指向较近的将来,尾联则是较远的将来。
本来,从理论上讲,“来·去”双循环也有存在的可能,然目前在作品中尚未发现完全合乎规范的具体实例。究其原因,似与其第二次使用“去”这一时间节点易使人太过伤感有关,因为这不太符合中国传统的大团圆审美结局的读者期待。就唐诗文本结构的时间轴而言,虽无“来·去”双循环式,却可以把“来·去·来·今”视作其变形。如戴叔伦《广陵送赵主簿自蜀归绛州宁觐》谓:
将归汾水上,远省锦城来。已泛西江尽,仍随北雁回。暮云征马速,晓月故关开。渐向庭闱近,留君醉一杯。[11]
此诗叙述的空间较为复杂,即诗人当时送别赵主簿的地方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而赵氏实际上先去成都省亲,后来才沿长江乘船来到广陵,其最后目标是再北返故里绛州(今山西绛县)省亲。从时间轴看,第一句从“将来”着笔,二、三两句追叙赵氏从成都到扬州的行程(过去时),第四至七句,再次着眼于将来(虚拟赵氏从扬州出发以后的行程,并设想他很快就要和亲人见面),但最后一句直接折回当下,交待诗人欲设酒筵相送的盛情。
2.轴对称循环
这是指以“去”“今”“来”中的任一节点为中心,再以另一节点为前后对称的文本结构形式,常见的有五小类:
(1)“今·去·今”
如白居易《勤政楼西老柳》曰:
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9]1 549
此五绝作于长庆二年(822),构思颇具艺术性。前两句触景生情,人、树并举,时间节点是当下;第三句追溯老柳的历史,它虽已枯萎近半,却有辉煌的前世,是植于开元盛世,百年沧桑之后,依然葆有坚强的生命力;末句又回归当下,诗人在强烈的对比中,意在讽刺穆宗皇帝的惰政,即长庆之治远远不能跟开元盛世相比。
(2)“来·去·来”
如吴融《送僧上峡归东蜀》曰:
巴字江流一棹回,紫袈裟是禁中裁。如从十二峰前过,莫赋佳人殊未来。[3]卷686,1 730
此七绝,诗人首句设想了僧人乘船返回东蜀的行程,第二句折回叙述僧人过去在长安所得到的优渥待遇,即他曾经获得御赐的袈裟,三、四两句又预想僧人经过巫山十二峰的场景,并提醒对方不要惊扰其中的神女(盖用巫山神女、巫山云雨之典故)。
(3)“去·今·去”
如杜甫《戏赠阌乡秦少公短歌》曰:
去年行宫当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觉人情好。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12]505
此诗的时间轴相当清楚,前四句都统括于所叙“去年”之事,五、六两句叙述“今日”之事,七、八两句又回忆过去之事,但其时间跨度(一天)远短于第一个“过去”(一年)。
(4)“来·今·来”
如刘长卿《瓜洲驿重送梁郎中赴吉州》
渺渺云山去几重,依依独听广陵钟。明朝借问南来客,五马双旌何处逢?[13] 499
储仲君指出,是诗作于贞元五年(789)春的扬州[13]498-499。是诗用第一称叙事,首句设问,虚拟了梁郎中前往吉州(今江西吉安)的路程,表达的是作者对梁郎中的关切之情;次句转向当下,意即梁郎中离开瓜州驿之后,只有自己还孤独地听着远逝的钟声;三、四两句,再次呼应开头,又用问句,但问的对象是从南方回来的客人,关注他是否曾和梁郎中相逢。
(5)“今·来·今”
如韩翃《赠张五諲归濠州别业》曰:
常知罢官意,果与世人疏。复此凉风起,仍闻濠上居。故山期采菊,秋水忆观鱼。一去蓬蒿径,羡君闲有余。[3]618
此诗作者,又作郎士元[3]卷248,626,未知孰是,暂系于韩的名下(但两者文字完全相同)。它和前举刘长卿诗一样,也用第一人称叙事。在文本结构上,可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包括首联、颔联,总体说来,时间节点属于现在。首联“常”字,表明张諲一生都喜好隐居(事实上也是如此,其人初隐少室山,中第后官至刑部员外郎,天宝中却辞官再隐);次联“此”字,说明时间指向更直接的当下(即韩、张告别之时,相对首联而言,其时间长度要短得多)。后半部分的时间节点,则包括将来和现在。颈联表面上用了陶潜东篱采菊、庄子濠上观鱼两个典故(分别出自陶渊明《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庄子·秋水篇》),其实诗人是借此来虚拟张諲回到濠上别业之后悠然自得的生活场景;尾联上句“蓬蒿”,也是用典,说的是西汉张仲蔚归隐之事(皇甫谧《高士传》谓其隐居之处,蓬蒿没人),但末句诗人的“羡君”之举,其实和张諲“一去蓬蒿径”的归隐行为是同步的,其时间节点又回到了送别的现场,并且和颔联有所照应。
此外,从理论上讲,以“来”为轴心的“去·来·去”类型也有存在的可能,但它和“去·来”双循环模式一样,目前也未发现完全符合其范式的具体作品,故暂时存而不论。
(三)线性与循环交互式
交互式的具体情况极其复杂,目前暂不能作穷尽式的分门别类,所以,只能择要举例略作分析。大体说来,它是线性式和循环式的混合体,较常见的有两种:要么线性中包括循环(有的还是无穷循环),要么循环中涵盖线性。
1.线性中包括循环
(1)宋之问《寒食江州满塘驿》曰:
去年上巳洛桥边,今年寒食庐山曲。遥怜巩树花应满,复见吴洲草新绿。吴洲春草兰杜芳,感物思归怀故乡。驿骑明朝宿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14]380
武周证圣元年(695)春,宋之问曾使江西,故诗作于此时[14]786。其时间轴的总体结构十分明显,是按“去”(第一句)、“今”(第二至六句)、“来”(第七、八两句)的自然顺序排列。但是,若只看第二至八句的时间轴,它又呈现为“今·来·今”的轴对称形式,特别是末句回答“明朝宿何处”之问时,答语是“来”中寓“今”,它是用时间的空间化来回答上句空间的时间化之问。除了线性时间轴串联了循环时间轴以外,本诗的空间轴也在故乡(洛阳及相邻地区)、他乡(江州及相邻地区)之间往复循环,故在形式上颇有讲究。
(2)王维《辋川集》之首篇《孟城坳》云:
新家孟城口,古木馀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15]413
王维的辋川别业得自前代诗人宋之问的蓝田别墅,其与道友裴迪等人于此往来唱和,所得即聚为《辋川集》,它是王维精心结撰的山水田园组诗。而《孟城坳》置于首篇,当有特殊的含义,其揭示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佛教思想,奠定了整组诗的感情基调。首句之“新家”,其时间指向是当下;次句之“古木”“衰柳”,强调了历史的沧桑巨变,时间指向更偏重于过去,同时寄寓了旧中可以生新的辩证法;三、四两句,当为诗人的告诫之语,即警醒将来此宅的主人,无论他是谁,都无须悲伤,因为悲伤本身也是空的。总之,旧主宋之问、新主王维以及未来的主人,他们都只是历史的过客。换言之,物也好,人也罢,皆非永恒的存在,本质上都是缘起性空的表现。因此,全诗从时间轴的整体结构言,属于“今(首句)·去(次句)·来(三、四句)”之线性式,但第四句的“昔人”一词,蕴含丰富,他既可以指王维眼中的宋之问,也可以指未来主人眼中的王维,甚至在未来主人心目中,还可以兼指王维和宋之问。同样,第三句的“来者”也是无穷无尽的,如此往复,“来·去”就可以无限循环下去了。
(3)李白《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曰: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16]
此诗思想较为复杂,有佛、道并重之意,尤其是与《维摩诘经》关系密切(13)详细分析,可参李小荣《酒肆与淫舍:李白维摩信仰中的取舍问题》(《唐代文学研究》第1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2-424页)。。从诗人答语中的时间轴言,其总体框架也是“今·去·来”式。前两句讲当下的一般状况,重点是诗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青莲居士出自佛教,与“酒肆藏名”所隐喻的维摩居士同义,谪仙人出自道教。第三句所说的迦叶之问,显然已经完成,故在时间点上可视为过去。末句“后身”云云,则属于将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回答,虽然仙、佛并置(第一句),然而仙、佛呈现的时空意识却迥然有别:从仙的层面看,李白认为自己是谪降,即前身(太白星精、酒仙,天上)→今世(酒肆藏名者,凡尘);从佛的层面看,他要追求涅槃境界,即今世(青莲居士、维摩居士)→后身(金粟如来)。当然,后一层面与佛典本义相反(14)按隋吉藏《净名玄论》卷二所引《发迹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866页中栏),维摩诘居士的前身就是金粟如来。,这是李白活用佛典之故吧。总之,本诗显示了三生观对李白的深刻影响,其自认的流转过程是:前身(天仙)→今身(青莲居士、谪仙)→后身(金粟如来),所以,“今·去·来”是全诗显在的时间轴。此外,它又隐含了两个循环的时间轴:一是大的三身流转;二是前两句体现的“今·去·今”的轴对称循环,即青莲居士(今)→谪仙人(去)→酒肆藏名(今),换言之,“谪仙人”同时兼具“今”“去”两种时间指向,这是本诗的特殊之处吧。
(4)元稹《岁日》曰:
一日今年始,一年前事空。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17]
此诗议论与抒情相结合。由于岁日(新年第一天)时间的特殊性,故诗人感慨良多。从时间轴看,总体结构是“今·去·来”式。第一句直指当下,第二句回到过去,三、四句展望将来。但是第四句的“一年”,因与第二句有重复关系,所以,二、三、四句又形成“去·来·去”的轴对称循环结构。换言之,本诗是在线性轴的大结构中,还套用了一个循环结构。此外,一日与一年,一年与百年之间,又是循环式的结构,虽往复轮回多次,然其本质属性是空,这显然浸染了浓重的佛教思想色彩。
2.循环中涵盖线性
(1)崔护《题都城南庄》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3]卷368,919
此诗第三句“不知”,又作“只今”,则时间节点更加清晰。其总体结构是“去·今”双循环式,即第一句有一组“去·今”,第二至四有一组“去·今”(第三句为“去”,三、四句又是“今”)。但从诗人的心理时间言,其实他在今昔对比中对未来是有所期待的,只是没有明白说出来而已。所以,从某种意义看来,本诗还潜藏了一条线性的时间轴“去·今·来”。顺便说一句,像本诗循环(显性)线性(隐性)之交互模式者,唐诗中极常用。
(2)李商隐《夜雨寄北》曰:
君问归期末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18]1 230
对于此诗的文本结构,清人朱彝尊指出,首句有问有答,次句写“今夜”,三句指“他日”,四句又是“今夜”[18]1 231,可见早就有人注意从时间轴来分析其特色所在。
从整体结构看,有人把它归入“今日想他日之思此日”[19]的时空模式中,其时间轴是“今·来·今”,即属于本文所说的轴对称循环式之一。其一、二两句叙说诗人异乡怀人的过程,总体上表现的是回信时的当下情境,第三句转写将来见面的场景,第四句叙述的内容又回归当下,“巴山夜雨”四字重复出现,性质却已大变,即眼前的实景已变成了虚拟之景。另外,第一句,细想开来,其实“君问归期”的时间节点肯定是在过去,然受限于当时的通讯手段,义山自然不可能立马回复妻子的关切,故“君问”与“未有期”的答语之间,其实还包括了一个线性时间轴,即过去→现在。三、四两句又是问答,答句所述内容,虽是当夜的场景,但夫妻果真要团聚的时间点依然是将来。换句话说,三、四两句“来·今”之“今”的时间感受,主要是属于心理时间而非客观时间。
(3)朱元《迎孙刺史》曰:
昔日郎君今刺史,朱元依旧守朱门。今朝竹马诸童子,尽是当时竹马孙。[3]卷732,1 834
孙刺史,指孙愿,朱元与他是儿时好友。全诗总体结构是“去·今·去”之轴对称循环式,但第一句自身含有“去·今”之对比,第二句自身是“今·去”对比,二句各自有一个线性的时间轴。此外,从全诗叙述自己与孙愿的人生经过看,诗中又潜藏了“去·今·来”这一完整的线性时间轴,因为二人已经步入子孙满堂的老年生活,如果孙愿现在还不关照自己,将来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三、成因略析:《诗》《骚》传统的继承与佛教观念的加持
上文主要就唐人近体诗文本结构所呈现的时间轴的三大类型及其类型的一般表现形式作了简单的介绍。但笔者要补充说明的是,多数时间轴的使用,并非唐人独创,而是渊源有自,单就中国早期诗歌《诗》《骚》所用时间轴说来,唐人是有所继承与发展的(15)韩高年在《论“诗骚传统”》(《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第113-120页)主要展示了《诗》《骚》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国历代诗歌创作及诗人人格、品位批评等方面的影响。其实,《诗》《骚》文本结构中的时间轴,后世诗人也有所继承。不过,本文举例,主要以《诗经》为主,毕竟其时代要早于楚辞。。
(一)对《诗》《骚》传统的继承
1.循环时间轴
最能表现这一模式的是《诗经·豳风·七月》。其文本结构中的时间轴,体现的是观象授时的循环历法,展现了自然时序(时令或节令)的周而复始,其性质是口头流传的农时歌谣(16)参高艳艳《〈诗经·豳风·七月〉诗性观照下的时间意识》(《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66-70页)、许迪《〈诗经〉中的时间意识探析》(《云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55-61页)等。。唐人近体诗中,除前述元稹的《岁日》以外,与此手法相近或同一机杼的作品极多,如李世民《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张说《钦州守岁》、杜甫《立春》、韦应物《九日》等,真是不胜枚举。但在唐人的生命体验中,除了岁时悠悠循环无尽以外,还多了三生相续的观念。
2.线性时间轴
《诗》《骚》中文本结构的线性时间轴,其常见形式主要有三种。
(1)今昔对比
其表现方式本来有二:一是由去至今,二是由今溯去。但《诗经》文本结构较常用的是前者,尤其是《小雅》的某些乐章,如《采薇》第六章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20]414;《出车》第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第五章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20]416。唐代诗人,既把“去→今”时间轴用于全篇,如骆宾王《于易水送人》、王维《崔兴宗写真》、杜甫《登岳阳楼》、孟郊《登科后》、韦庄《焦崖阁》等,又广泛使用“今→去”时间轴,如王昌龄《客广陵》、刘禹锡《赠刘景擢第》、尚颜《匡山居》等。
(2)今来对比
今、来对比者,如《唐风·葛生》曰:“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20]366全诗五章,每章时间轴相同,都是从女性当前的所见所想写起,然后再抒发她对亡夫的思念之情,只不过描述将来时间节点的方法是由近及远,并渐次推到遥远的百年之后。这种“今·来”的线性时间轴,唐人近体诗的文本结构中同样十分常用,如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王昌龄《送吴十九往沅陵》、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吴融《送许校书》等。《邶风·简兮》第一章曰“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20]308,从“方将”一词可知,前两句是女性观舞者对舞师表演的心理期待,时间指向是将来;“日之方中”等四句,转向现场,时间节点就在当下,故其时间轴大致为“来·今”。唐人从预想将来着笔后再转向当下的近体诗文本也时有所见,如李白《赠汪伦》、李端《重送郑宥归蜀因寄何兆》等。
(3)贯通“今”“去”“来”
这种文本结构中的时间轴,一般使用三个时间节点。如《魏风·硕鼠》有三章,每章结构完全相同。其第一章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20]359从其时间节点看,头两句是农民对统治者(硕鼠)的现场指斥;三、四两句,农民重在回顾自己多年的辛苦耕作,并倾诉而得不到对方任何回报的愤怒;最后四句,抒发农民誓愿寻找乐土的理想,时间指向无疑是将来。其时间轴是“今·去·来”。
再如《小雅·信南山》第一章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20]470其时间轴大体可以两句为一单元进行判别,头两句重点指向过去,中间两句指向将来,最后两句则转向当下,故属于“去·来·今”式。
贯通“今”“去”“来”之时间轴者,唐人近体诗中十分常见,前文已有说明(且类型更加多样),不再重复举例。
3.线性与循环交互式
这种形式展示的是《诗经》各章或部分章节之间的关系。如《秦风·车邻》第一章曰“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第二章曰“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耄”,第三章曰“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20]368-369。从“未见”“既见”“今者”“逝者”等语词判别,三章之间的总体结构是较为清楚的(其中,第三章同于第二章,可称为循环式),即“今·去”(第一章)+“今·来”双循环(二、三章叙述“今”的场景占主体,仅用“逝者”一句表示将来)。
再如《卫风·氓》[20]324-325共有六章,其文本结构虽然较为特殊,叙事之中夹有大量的议论(三、四两章,议论发生的时间可视作当下),总体时间轴却是“去(一、二两章)·今(三、四两章)·去(第五章)·今(第六章)”的双循环式(17)不过,有学人指出《氓》的空间轴也有很大的叙事功用,因为“淇水”是诗的中心意象,第一章“送子涉淇,至于顿丘”,第四章“淇水汤汤,渐车帷裳”,第六章“淇则有岸,隰则有畔”,它们“依次构成昔日的欢爱——今日的悲凉——后日的悲酸这样一种三部曲式的发展历程”。而“淇水汤汤”两句,“正出现在诗的中心段落,出现在今与昔的交汇点上,以此为中心轴线,前后呈现出强烈的映照和对比”。参李从让《〈卫风·氓〉结构艺术新探》,《阜阳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56页。。不过,在双循环的总体框架中,又夹杂使用了线性时间轴:如第一章弃妇回忆自己与氓相识相恋乃至商定婚期之全过程时,就把这一特定的“过去时”再分成“去”(一至四句)、“今”(五至八句)、“来”(九、十句)之自然时段,第六章叙述当下的回忆时,其所忆内容又可分成两个线性时间轴,即“去”(第一句)、“今”(二至四句)+“去”(五、六句)、“今”(七、八句)、“来”(九、十句)。
至于《离骚》文本结构中的时间轴,情况相当复杂,既重视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的时间诗学[21],也高度关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22],又充分体现了神话色彩浓重的“圆环性质的时间”与历史性质的“直线性质的时间”[23]的交互。总之,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中的时间轴,基本上呈现的是线性、循环交互的时间轴。
线性与循环交互式的时间轴,唐人近体诗也很常用(且表现方式更加丰富),前文同样有说明,也就不重复了。
(二)佛教影响的时间节点及唐人接受的主要表现
1.时间点
佛教“三时”时间观影响中国古典诗歌的时间节点,当在晋宋之际。据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文学篇》第85条“简文称许掾云”下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评述许询、孙绰玄言诗时所说:“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至过江,佛理尤盛……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18)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不过,“至过江佛理尤盛”,余校本作“至江左李充尤盛”,此不取。另外,标点笔者也有所改动,特此说明。过往学人,十分注意“三世之辞”的含义,一般认为它代表的是汉译佛典(19)在此,尚可补充中古时期的一则史料,如北齐樊逊对“问释道两教”上书时曰“二班勒史,两马制书,未见三世之辞,无闻一乘之旨”(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12页)。“三世之辞”与“一乘之旨”尚有互文关系,因为汉译佛典主要是大乘经典。,并由此论证佛教思想对东晋玄言诗所产生的具体影响(20)参张伯伟《玄言诗与佛教》(《禅与诗学·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69-194页)、陈允吉《东晋玄言诗与佛偈》(《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第77-93页)等。,此诚然不误。不过,笔者以为,东晋玄言诗所受的佛教思想影响,自然也应该包括佛教的“三时/世”时间观。可惜的是,由于玄言诗存世作品太少,并且其中确实没有以佛教“三时”时间轴为中心的作品。然而深受佛教化玄学影响的谢灵运,他既直接引佛教“三世”一语入诗,如作于景平元年(423)冬末或次年初春的《石壁立招提精舍》,开篇便说“四城有顿踬,三世无极已”(21)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0页。因“四城”指释迦牟尼为太子时出东南西北四城门游观之事,故“三世”也属于佛教语境,指去、今、来。,元嘉十年(433)于广州临刑前又赋有《临终诗》曰:
龚胜无遗生,李业有穷尽。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殒。凄凄后霜柏,纳纳冲风菌。邂逅竟既时,修短非所慜。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上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22)《广弘明集》卷三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356页上栏。“李业”之“李”,本作“季”,此据《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本传改。另,本诗版本复杂,字句多有不同,相关情况,参郑伟《谢灵运〈临终诗〉佚文注文辨正》(《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9期,第47-50页)。
是诗思想较为复杂,有人认为它体现了谢灵运三教圆融的临终关怀[24],可备一说。笔者更关注其文本结构中的时间主轴。前四句用典,所叙西汉末龚胜、李业,曹魏末嵇康,西晋末霍原等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易代之际不肯与新王朝合作的有节气之士,时间节点是“过去”(当然,谢客以此自比,似暗指四人是自己的前世);第五至十句,则重在概述其一生的遭遇,空有高远志向,竟然一事无成,从时间节点看,显然属于“现在”;最后四句,述说死后之事,他誓愿再到人世间,要平等地救度有情众生,甚至是自己的冤仇之人,时间节点为将来。所以,全诗采用的是佛教典型的“去·今·来”三世流转的时间轴。嗣后,北周释亡名《五盛阴》云“先去非长别,后来非久亲。新坟将旧冢,相次似鱼鳞……定知今世土,还是昔时人。焉能取他骨,复持埋我身”[1]第52册,358,则从无常的角度论证了三世流转。
2.唐人接受的主要表现
唐人接受佛教“三世”观的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把个体生命的三世流转直接入诗。有的自述,如王维《题辋川图》“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15]477;白居易《爱咏诗》“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9]1 838,《香山寺二绝》(其二)“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9]2 391。有的述他,如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12]656,窦巩《题任处士幽居》“客来唯劝酒,蝴蜨是前身”[3]卷271,681,陆畅《题悟公禅堂》“芸阁少年应不识,南山钞主是前身”[3]卷478,1 213。有的自述与述他相结合,如皎然《送胜云小师》“昨日雪山记尔名,吾今坐石已三生”[3]卷819,2 009,前句用雪山授记的佛典,是讲胜云小师将来的果位,后句是皎然的自述;白居易《山下留别佛光和尚》“我已七旬师九十,当知后会在他生”[9]2 679,则把自己和佛光和尚的相见寄托于来世。
二是用三生观念来评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同时寄予诗人的自我人生体验,其题材多集中于咏史、怀古类。如李涉《题涧饮寺》云“百年如梦竟何成,白发重来此地行。还似萧郎许玄度,再看庭石悟前生”[3]卷477,1 211,其第三句讲述的是东晋玄言诗人许询三生造塔的佛教故事(许询后身→后梁萧詧→中唐裴肃。裴肃则是裴休之父)(23)参《景德传灯录》卷12“裴休”条之夹注(《大正藏》第51册,第293页中-下栏)、《佛祖统纪》卷37“大同三年”条(《大正藏》第49册,第351页上栏)等。,第四句呼应首句,诗人感慨即便自己有三生相续,也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二)开篇即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18]307,该联贯通“三世”,并就马嵬之变做了定性评价,指出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才是发生事变的根本原因。温庭筠《蔡中郎坟》则说“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25],第二句的本事,典出《语林》所说蔡邕为张衡后身的传闻(24)此据《白氏六帖事类集》卷7、《太平御览》卷360所引,《太平广记》卷164谓事出殷芸《小说》,北宋晁载之辑《续谈助》卷4则谓出《世说》,可见相关传说在中古时期相当流行。。当然,温庭筠暗以张衡、蔡邕后身自比,诉说怀才不遇的悲凉之情。
三是进一步强化了“三时”时间轴在近体诗歌文本结构中的作用。比如,前文举出的多种表现方式,它们大多虽不是唐人独创,但相对于前人说来,运用时更加自觉和规范,且有规律可寻,也可以作为“唐代规范诗学”(25)张伯伟《论唐代的规范诗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67-177页)一文,主要讨论了唐代近体诗的“诗学语言学”问题,但笔者认为,其文本结构中时间轴的类型学研究,也是规范诗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