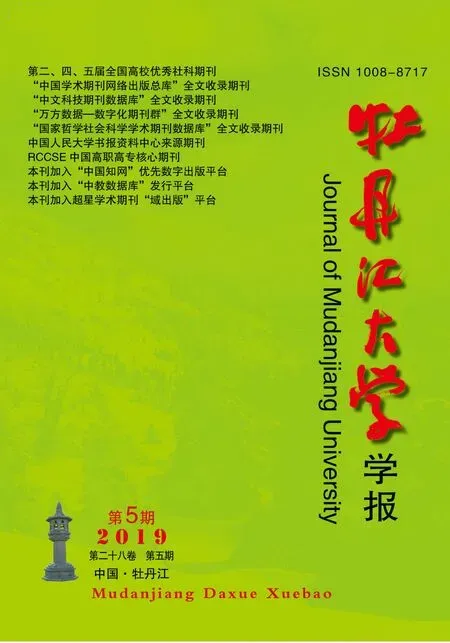纳西族作家和晓梅小说集《呼喊到达的距离》之探究
魏 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和晓梅是纳西族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作为一个地处边隅的少数民族作家,和晓梅以其女性的温柔与舒缓书写着自身的民族文化,丽江的纳西村落成为她笔下独特的书写场域。其于2016年获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集《呼喊到达的距离》更是凝聚了和晓梅创作的精华。在一个个故事中,无论是丽江地域风情下纳西民族多彩民俗的呈现,边地人物群像的塑造,还是坚忍的文化心理透视,都展示着一个女性作家视角下对本土民族文化的呈现与探寻。本文旨在通过对和晓梅小说集《呼喊到达的距离》中的民俗呈现、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文化心理的揭示这三方面的探究走进和晓梅笔下的纳西文化,试图探寻和晓梅作为女性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书写。
一、多彩的民俗文化
在滇西北的美丽丽江,北有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高原阳光的热情与雪山的高洁相融合养育了一代代纳西民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和晓梅同样汲取了本土的滋养,使这片地域融为自己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丽江纳西村落成为其书写的一个场域,一辈辈纳西人流传至今的民俗生活在其作品中得到呈现。
《呼喊到达的距离》中多篇小说以纳西民族为背景构建了一个个故事。讲诉着摩梭少年泽措成长命运惶惑与特殊性的《未完成的成丁礼》,木与吉决然为爱殉情的《飞跃玉龙第三国》;奶奶的故事《有牌出错》,其中都充斥着丰富的纳西民俗文化。泸沽湖,火塘,花楼等一系列意象的选取,展示了纳西民族生活的环境,构建了一幅幅民族风情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民族,有对爱情的执着也有独特的走婚制度与成年仪礼。
《未完成的成丁礼》中,泽措在成丁礼到来之际改变了命运,由泸沽湖畔的泽措转变为城市里的威廉。泽措是摩梭阿夏婚的孕育结晶,是母亲与外乡人一夜结下的情缘。居住在滇川边境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较长时期以来一直实行独特的阿夏婚姻。阿夏婚姻是一种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男子于夜晚到女子家中访宿,第二天清晨又返回到自己家中从事生产劳动,偶居双方不组织共同的家庭。[1]在《未完成的成丁礼》中,花楼是摩梭少女用来接待男方的地方。母亲为妹妹准备的花楼,泽措对迪测姐姐花楼的闯入,都是走婚的小小缩影。
成丁礼是一个特殊的仪式,标志着少年少女的成长。按照摩梭人的传统习俗,女孩和男孩长到十三岁时便要分别举行“穿裙子”和“穿裤子”仪式,标示着成人,可以开始参加一些劳动和社交活动。少年泽措在心里对成丁礼充满期待,他渴望与所有的摩梭少年一样在成丁礼那天变得强大又健壮,不愿瘦弱而被嘲笑与众不同。然母亲费尽心思为泽措准备的成丁礼牛仔裤却是短小轻薄的,这打破了泽措想要长大的梦,破碎了他内心长成和落水村人一样高大的梦。重要的成丁礼仪式给泽措带来的是对成长的沮丧。最终,泽措的命运没有在成丁礼仪式上通过一条花裤子得到改变,而是被“外地人”带离泸沽湖畔。母亲在花楼与外地人的一夜情缘孕育下泽措,外地人如溺水一般幸运地抓住了泽措这根救命稻草,得到了巨额财产。泽措在成丁礼上渴求的强大与健硕,终于在远离落水村后得到实现。在走婚与成丁礼民俗文化的构建背后,和晓梅用悠扬又哀伤的挽歌笔调讲诉了少年泽措的命运与成长:成丁礼结束了,泽措成了威廉,那遥远的泸沽湖也在城市的呼啸中成为记忆。
纳西民族是一个有着自己丰富绚丽文化的民族,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它具有一般宗教文化的共同品质,又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性。[2]东巴文化贯穿在纳西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无论是仪式还是民俗,都留有东巴文化的影子。《飞跃玉龙第三国》中,玉龙第三国,是殉情人的天堂。在一段凄美的爱情中,我们认识到纳西特有的婚嫁社会民俗文化:纳西族最庄严的婚礼——行“素礼”,是将象征着“素”的红绳绑在两人紧握的手上。正常情况下由东巴主持,但凡行过素礼的男女,灵魂将永远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会分离。在这样仪式的庄严中,殉情的人们往往会在男方或女方强行的婚礼之前出逃,因为他们深信那段诵过经文的象征灵魂的细线会将他们永远地束缚住。玉龙雪山下的凄美爱情,是纳西婚俗文化的展示,也是一曲曲爱恋挽歌的书写。
和晓梅笔下呈现的民俗,不是对其的批判与否定,而是旨在通过对民俗的诗意书写表明一个民族特有的生命意识与文化内蕴。成丁礼对少年的影响,智者大东巴超度亡灵对纳西人民的意义,殉情背后少年少女对爱情的执着追寻,都体现了在时间的长河中一个民族永恒的执着与坚守。
二、边地人物形象的塑造
小说集《呼喊到达的距离》中,和晓梅塑造了一群边地人物形象。《连长的耳朵》中坚忍善良的连长;《未完成的成丁礼》中独立坚强守护着家族的母亲与祖母;《有牌出错》中乐观豁达、言出必行的奶奶;《飞跃玉龙第三国》中为爱殉情的吉与五姨。纵观这些边地人物群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连长为代表的边地男性形象:顽强隐忍,体现着人性的光辉。一类是以母亲为代表的边地女性形象:坚强独立,蕴含着纳西女性的执着与明媚。
《连长的耳朵》讲述了一个连长的故事,战争中失去听力的连长经历九死一生,运用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与智慧带领连队取得一次次胜利,战功显赫。然而在一次巡逻中,连长惨遭女敌人的暗算,在陷阱里昏迷,独自面对赤身裸体的女敌人。失去记忆的连长无法解释为何女敌人赤身裸体,也无法想起为何女敌人的内裤在自己的手上。这未解的谜团随着时间慢慢沉淀,连长默默背负着流言蜚语。最终等连长的韶华逝去,在一场瞌睡醒来,在耳朵的碰撞声中,连长想起了那天的一切:女敌人中毒后吞下地形图,怀着巨大的仇恨而选择同归于尽陷害连长,将自己的衣物脱光艰难地伪造犯罪现场。连长纵然负伤严重,依然在等待女敌人做完这一切,朝她爬去,替她将裤子穿好,企图将周围的一切整理好,还原他们的清白。连长的重伤来不及等他将一切收拾好就使他昏迷,由此才有了他手上的那条内裤。连长对逆境的顽强隐忍,对女敌自尊的维护显示出了巨大的人性光辉,更是一个民族忍辱负重的坚韧呈现。
与连长的形象类似,在和晓梅的笔下,纳西女性同样是顽强隐忍又独立的存在。和晓梅的小说采用了女性的审美视点,“这一视点以女性的自审意识为基础,用自觉的女性眼光,以女性的立场和姿态,……通过刻画真实生动的女性形象,来高扬女性的审美理想。”[3]和晓梅以自己的女性视野,讲述纳西女性的故事,表现纳西女性的独立与执着顽强。
在《呼喊到达的距离》中,纳西女性以“母亲”“奶奶”“五姨”为代表。她们既刚烈又柔韧。《未完成的成丁礼》中,母亲与祖母用爱与独立顽强守护着家族。她们为家族甘愿奉献一生,母亲在临盆前将生死屋让给即将去世的老祖母,女性在生命抉择面前的无私与顽强,或许正是纳西族历千年苦难之后仍能繁荣的缘由。《有牌出错》中的奶奶,年轻时眼睛孕育着温和,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是大东巴的长孙女,有着显赫的身份,却是一个“叛逆者”。逃婚与“二流子”的爷爷结婚并以赌博为生计,背离了东巴家的传统。奶奶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善于发现和总结人生哲理的内涵累积了一定的财富,开了茶庄与驿站。在与来往的马帮赌钱中,一个小个子男子与奶奶的赌局,改变了奶奶的人生。奶奶由此放弃了自己日渐安定的生活与创造的家,为了遵循赌局的游戏规则,做到言出必行,追随一个马锅头开始极其艰苦的流浪生涯。纵然在马锅头死后,奶奶仍然凑足了赌约上的十年才辗转返回达瓦村。这从东巴家族中出走的叛逆形象,敢爱敢恨,凝结着纳西女性乐观豁达的生活哲理及智慧。纳西族自古以来就有殉情的传统,青年男女得不到家长的同意便奔向玉龙第三国,《飞跃玉龙第三国》中,和晓梅塑造了殉情女性的形象,她们对爱情执着勇敢,有着少女的纯真与善良。五姨与吉佩儿是殉情文化下相异的两个女性形象。五姨在年轻的时候拒绝家人安排好的婚事,决心与爱人共同奔赴玉龙第三国,在喝毒酒的一瞬间,感受到肚子里孩子的生命力,由此企图放弃寻死,然而心爱的人却早已喝下毒酒留下她一人。由此五姨在世人的眼光中独自冷漠孤傲地生活,内心充斥着想念与愧疚。与五姨的放弃不同,吉是一个纯真果敢的形象。因为订婚对象拓对小动物的残忍,吉对他全然无好感,爱上了普通的短工木。这超越世俗与家庭的爱,让两个年轻的少男少女偷偷奔向玉龙第三国。吉对玉龙第三国的向往是对爱情的执着追寻,最后替木挡的一枪,也表现了在爱情中的决绝。纳西年轻的少女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的世俗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民族对爱坚守的缩影。
不同于纳西女性的独立顽强、敢爱敢恨,和晓梅在《呼喊到达的距离》中塑造了一系列城市中迷茫的青年女性形象。诚如和晓梅自己所言“我在现代社会里寄存着躯体,却在东巴文化的世界里寄存念想。”[4]在现代社会里寄存躯体的作家,探寻着现代社会的脚步,在作品中弱化了民族身份而构建一个个城市中的女性形象,引人深思。
《来自一条街的破碎》中,田红是孤寂高傲的,她怀揣着少女的压抑。田红将家庭的破裂原因归结于母亲,并不惜出卖少女的色相与钟逸民做交易报复母亲,而隐忍的母亲选择置之不理。父母的冷漠与忽视加剧了田红的孤立与不合群,这一性格的不断强化使田红的心理愈加激进陷入与小伙伴交往的困境,如同破碎的街一样,田红的心灵也是破碎的,难以愈合。与田红类似,在《春节,落雪的昆明》中,沈纤惠也是孤独不合群的形象。《春季,落雪的昆明》以女大学生为题材,以日记为线索,讲述了大学生沈纤惠与周围室友格格不入,通过不断更换男友寻找爱情,企图获得温暖,最终沦为杀人犯的故事。沈纤惠的孤独与寂寞是不合群造成的,她对未来的迷茫与孤独的体验,使她最终走向生命的滑落。《我与我的病人》中,“我”作为一个都市的女心理医生,却被生活所困,企图多赚钱达到物质上的丰富,我的患者小敏有着幸福的家庭,却在对丈夫的怀疑中生活得心力交瘁。和晓梅通过一系列都市女性形象的塑造,使得我们对生活产生思考,这背后的生存哲学引人思考。
纵观《呼喊到达的距离》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各异,却聚集着共同点:她们都拥有活泼顽强的生命力,对美好的事物总是执着追寻。和晓梅对纳西女性的塑造,更是融入了纳西民族精神的书写,与其说作家在书写纳西女性形象,不如说作家是在为纳西族立传,将女性的刚毅顽强独立融于纳西的血液,用自己的审美体验呈现这个不朽的民族的坚韧。
三、坚忍的文化心理
纳西族是一个自强不息、进取向上、勤劳智慧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晓梅笔下的纳西人民有着顽强坚忍、重情重义的民族文化心理,他们代表着纳西人的美好,坚守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腹地。
《有牌出错》中奶奶的故事,是遵守约定的人生的改变。有着棕褐色温和气息眼睛的奶奶是大东巴的长孙女,大东巴是东巴中的长者和导师,奶奶的忤逆与东巴家族的智慧背道而驰,她决然的逃婚与同东巴经文中为纳西先人不齿的赌博赢取家产的行为,使奶奶与东巴家族彻底决裂。在一场场的赌博中,奶奶在游戏的法度中一次次获胜。奶奶的名气成为无数马锅头们反复咀嚼回味的内容,然而,在和一个达瓦村人记不住相貌的小个子男人赌博中,奶奶输掉了唯一的一张牌,这张牌是悬念亦是奶奶生活与人生的转折点。奶奶为此押上了十年的时光,开始了极其艰苦的流浪生涯。敢爱敢恨乐观豁达的奶奶是一个言出必行的纳西女性,她的承诺必行是一个民族敢于承担的宣言,昭示着乐观豁达,敢爱敢恨,言出必行的文化心理。
《连长的耳朵》中,连长在无法洗清自己的冤名的情况下,仍然为暗算自己的女敌维护着最后的尊严,这表现出的人性光辉是一个民族跨越国界的人性大美。连长逆境中的顽强隐忍,是一个民族忍辱负重的坚韧文化心理。同样的,纳西青年也表现出重情重义、不畏死亡的文化心理。《飞跃玉龙第三国》中,木与吉的殉情正体现了这种文化心理。“不自由,毋宁死”是木与吉准备殉情时的心态,他们以死来抗争,以死来殉自由和爱情的理想。他们是纳西青年的一个小小缩影,是纳西青年情感至上、爱情至上的文化心理追求。和晓梅是为纳西民族书写,她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尊严感塑造了她笔下纳西民族坚忍、言出必行、重情重义的民族文化心理,也让我们读懂一个民族的坚忍与自豪。
《呼喊到达的距离》是和晓梅为自己民族立的传。多彩的民俗,淳朴的民风,在沪沽湖畔,在一代代纳西人中。通过和晓梅的书写,我们认识了一个有着自身灿烂文化的民族,他们敢爱敢恨,他们顽强坚忍,他们重情重义。和晓梅笔下的一个个人物是无数纳西人的缩影,是有着自身文化心理的骄傲的纳西人。她用自己的文字构建了一个属于她的纳西世界,也让读者了解到一个有着丰富文化的纳西王国。
——雁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