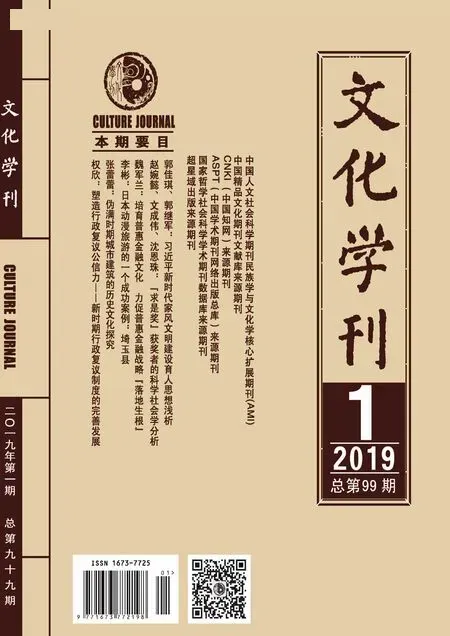中国古诗英译过程中背景信息的介入对目的语受众审美体验的影响
何慧珍 郑 婷
中国古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似简单的文字,短小的篇章,却描写了优美的自然风光、表达了诗人的情感、记录了时政局势等。中国古诗的独特之处在于简单文字下面隽永的内涵,而诗歌内部的深刻内涵正是诗歌翻译学习和翻译的最大难题。中国诗歌的优美和深邃早已引起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的兴趣,但碍于其晦涩难懂,许多外国友人在诵读中国古诗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仅是外国学者,本国许多诗歌爱好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本国学者在学习中国古诗的时候,除了需要了解古诗中字词的发音和词义,还需要了解诗歌创作的背景文化知识,进而了解诗人创作的环境和心境,尽量拥有与诗人相类似的审美体验,与诗人产生精神层面的共鸣,从而更快地掌握原诗的深刻内涵。
一、审美体验的理论概述
根据伽达默尔的考证,审美体验所说的“体验”一词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后开始出现在一些作家和理论家的著作中,但是体验概念的真正成形,是在狄尔泰出版《体验与诗》等著作之后。狄尔泰、歌德、马斯洛、王一川等众多中外学者都对审美体验作过详尽研究,将审美体验与美学、心理学、认识论等领域相联系,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审美体验研究体系。中国古代美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体验”一词,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大家已然提出了审美体验这一重要观点,并在他们的相关著作(《老子》《大宗师》《孟子》)中提及审美体验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美学认为,审美体验活动是“心与物、情与景、神与形、意与象的融合,它强调个体对生存环境的独特感悟,是一种心灵的、总体的生命体验”。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范畴大都没有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它注重“体验”,读者不能从著述中得到清晰认识,只能去感受、体验。所以,在中国古诗的学习中,审美体验的感悟十分重要。
著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提出语言是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并坚持认为文字存在的目的是再现语言,一个文字就是一个有声的意象。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瑟夫·房德里耶斯也提出人们对语言所能下的最一般的定义是一种符号系统。“文学作品中的字、词不是一个单一的名称,一个单独的名称不能展示一件事实的复杂变化过程,也不能把一件事物产生的前因后果和它存在的可能性和非可能性表述清楚,更不能把作者对它的看法表示出来。”[1]所以,文学语言并非一种单一的、一对一的简单符号系统,它具有一个动态的、一对多的意义系统。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所思所想的语言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并非某一种具体的事物。无论创作者的想法多么深刻,构思如何精巧,作者在创作时需要运用文学语言,将抽象的意义或抽象的情感转换成读者熟悉的一系列符号[2]。按照这一道理,对不同人来说,同一个字、词就既可以理解为具象的物件,又可以理解为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事物,甚至抽象的概念。
浙江大学文学博士王苏君曾在《审美体验的层次》一文中提到:“审美体验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体验,或称为知觉体验。第二层次是认同体验。第三层次是反思体验。”[3]同时,她在文章中指出:“所谓认同体验是指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发生情感上的共鸣,审美主体在想象中把自己当作审美对象,或者由审美对象联想到与自己有关或曾使自己感动过的别的事物。”[4]这正如汉斯·罗伯特·耀斯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所提到的:“审美经验不仅仅是视觉的领悟和领悟的视觉:观看者的感情可能会受到所描绘的东西的影响,他会把自己认同于那些角色,放纵他自己的被激发起来的情感,并为这种激情的宣泄而感到愉快,就好像他经历了一次净化。”[5]
二、背景信息的介入
诗人在进行创作时,无论是对大自然的歌颂,还是对时事的评述,或者对个人经历的描绘,往往都是有感而发。所以,要想让目的语读者拥有相同的感受,首先要让受众清晰地了解诗歌创作的背景及诗人的经历,从而与审美主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下面笔者就杜甫《兵车行》的英译为例,浅析中国古诗英译过程中背景信息介入对目的语受众审美体验的影响。
《兵车行》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大多诗歌都记录了当时社会真实模样,所以杜甫的诗被誉为“史诗”。杜甫纪实的诗歌创作手法,给人们呈现了一个朝代由兴到衰的真实过程,其诗歌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等。《兵车行》这首诗大抵创作于天宝十载(751),在这之后唐朝的战争就越发频繁,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诗人站在“记录者”的角度,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同时讽刺了唐玄宗穷兵黩武的行为。下面,笔者结合实例,就Witter Bynner、Rewi Alley、Florence Ayscough三者的翻译展开论述。
例1:
原文: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译文1:
Farther, mother, son, wife, stare at yougoing.
Clogging up the road, their rising dust obscuring the great bridge at Xianyang.
——Witter Bynner
译文2:
Besides them stumbling, running
The mass of parents, wives and children clogging up the road, their rising dust obscuring the great bridge at Xianyang.
——Rewi Alley
译文3:
Fathers, mothers, wives, children, all come out to say farewell;
Dust in clouds: they cannot see the near-by Hsien Yang Bridge.
——Florence Ayscough
在没有背景介绍的情况下,Witter Bynner和Rewi Alley的翻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均是对离别场景的描述。然而,原诗虽然也是描述道别的场景,但是此时是送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奔赴凶险异常的战场,此次道别可能是永别。这些深层的含义并未在原诗的字面意思上表达出来,但是根据诗歌创作的时代和时间背景,这一场道别实则是生离死别。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能将深层的含义翻译出来,读者将很难有准确的审美体验;而若逐一翻译,便不能穷尽诗歌中各个意象的深层含义,还会失去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独特的美。Florence Ayscough在译本中选择了“farewell”这个具有“永别”含义的单词,将原诗中“诀别”这一隐藏的感情直接翻译了出来,同时用“cannot see”再一次强调“永别”。Florence Ayscough在其他地方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例2:
原文: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译文:They drag at men's coats, fall beneath their feet, obstruct the road, weeping;
Sounding of weeping rises straight divides the soft white clouds.
有了前文“永别”作为背景知识铺垫,此句的翻译中,目的语读者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译者所描述的抓住亲人哭的场景,以及哭声凄惨和响亮的画面。正是由于前文背景知识的介入,使得读者将自身置身于诗人和译者的语境中,产生了类似的情感共鸣,让诗歌中描述的抽象画面变得形象。
浙江大学文学博士王焱在《庄子审美体验研究》中指出:“对于音乐欣赏的首要目标是,使欣赏者能够调动内心的情感,通过聆听音乐得到美的体验,获得丰富的想象与情感反应。这样才有利于欣赏者从多角度、深层次地感受音乐。”[6]笔者认为,诗歌的学习也是如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首先调动目的语读者内心的情感,使之尽量站在相似的精神层面,获得类似的情感反应,这样才有助于读者了解诗歌更深层的含义。通过译者向目的语读者介绍原诗的背景文化,让受众融入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空间中,达到更加深入地了解原诗的目的。详细的背景文化介绍可以让目的语读者不再单纯地停留字面理解的层次,而是对整个诗歌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
古诗的英译看起来是一个客观的翻译过程,实则是一个主观创造的过程。诗歌背景的介入,对受众而言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能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人在创作中和译者在翻译中融入的个人审美体验。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知识储备,去体验和感悟诗歌。但是,由于时间、空间和个人经历的融入,差异性是必然存在的,译者在翻译诗歌的时候、目的语读者在欣赏译本的时候,都难免带入一些“新的意义”[7]。这种个人审美体验的介入,不但说明了诗歌本身的开放性,又可以让不同译者和读者从不同角度对诗歌进行理解,从而逐步实现对原诗真正的、立体的理解。
三、结语
诗歌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文学形式,原本就带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包含了许多内涵和外延。所以,译者在翻译实践活动中,仅仅是对原诗逐字翻译,反而丢失了原诗的美,故而译者在翻译时也需要对原诗中无法用言语表达以及隐藏起来的情感进行完善,而不是对原诗的简单呈现。诗歌的许多美产生于读者体验的过程,译者在翻译中必然会先对原诗进行解读,在这个解读过程中,译者也是读者,也会融入个人审美体验,“这种的解读方式难以避免带有解读者自身的主体烙印”[8]。背景信息的介入,能让读者更加真切地了解原诗创作的时间和空间,能更好地与诗人对话,从而达到更为近似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