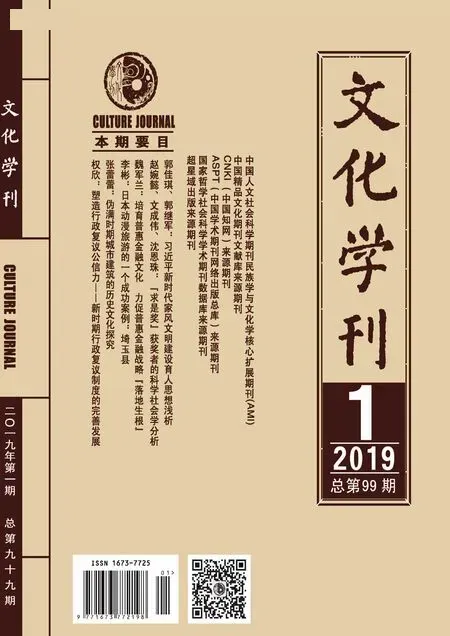陆机生命意识研究
岳 磊
一、乐生哀死
陆机生命意识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乐生哀死。生命无常,人生有限,这也是人之常情。
陆机《饮酒乐》云:“蒲萄四时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1]从这首诗描述的画面可以看出这是贵族享乐的场景,可是里面却有一句不搭调的“朝醒弦促催人”,让整首诗无端地流出了一种愁绪,不禁让人想问诗人在愁什么。关于此,陆机的其他诗文里隐藏着答案,如《董桃行》:“世道多故万端,忧虑纷错交颜,老行及之长叹。”[2]《拟今日良宴会》唱“人生无几何”,《顺东西门行》中“感朝露,悲人生”。正所谓诗言志,这是陆机自己在感慨时光易逝,老之将至,但是又无可奈何,无法阻挡,就只能是“桑枢戒,蟋蟀鸣”,和他人一起“激朗笛,弹哀筝,取乐今日尽欢情”,及时行乐。
人生在世七情六欲,烦恼诸多,人生难再少,时光如流水,不若及时行乐,这也是人之常情。享乐是人的本性,可以说是贪图享乐,也可以说是趋利避害。诗经《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幸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3]其后,汉乐府《西门行》云:“为乐当及时。”有趣的是,在社会动乱的汉末也有这样的说法。无名氏写的《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就有“为乐当及时”一句。汉末一直到魏晋时期都是一个乱世,这是当时社会流行及时行乐思想的现实基础,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的生命大都是朝不保夕。朝不保夕的生活让人们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体悟,既然长寿不可期,那么及时行乐追求生命的厚度,也就自然而然了,陆机有及时行乐的想法也就无可厚非。不过,陆机祖辈、父辈都是东吴重臣,可以说家学渊源,本人又是“伏膺儒术,非礼不动”[4],“清厉有风格”[5]。这样看来,陆机所歌的及时行乐应该会有自己独特的印记,与《诗经》中的《唐风·蟋蟀》、汉乐府《西门行》及《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所说的及时行乐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无奈与感伤在陆机的诗歌里随处可见,如《饮酒乐》有“朝醒弦促催人”,《董桃行》有“忧虑纷错交颜,老行及之长叹”,《顺东西门行》有“感朝露,悲人生”。人生易老古今同叹,若说陆机有哪些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有很强烈的功名意识。《秋胡行》云:“生亦何惜,功名所勤。”因此,可以说,陆机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及时行乐思想是在不能实现人生理想之时的自我发泄。时光易逝,功业难建,重振家风无望,怕是无论是谁都不能轻易释怀的。
陆机在《梁甫吟》中通过“年命时相逝,庆云鲜克乘”[6]一句,感年命流逝;在《百年歌》《感丘赋》道尽了年华逝去的无可奈何,只“愿灵根之晚坠,指岁暮而为期”[7]。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就产生了,既然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希望能长寿,能够终享天年。然而,人生七十古来稀,长寿谈何容易,更何况是在乱世,痛苦也就不可避免了。既然死亡不可避免,就希望能早日建功立业,陆机感时叹逝也是其功名意识的流露。于是在《日重光行》中感伤“身没之后无遗名”,在《长歌行》中感叹“寸阴无停晷……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8]。
陆机追求功名的路上并不顺畅,甚至动不动就会有性命之忧。如九锡文及禅诏事件,“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9]。陆机仕途不顺,政局不稳定社会动乱固然是其主要原因,但他的出身也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重要。陆机身处“亡国之余”,虽“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10],并“以荐之诸公。”但是,张华的重视与举荐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陆机在事实上依然不为北方士人所重。这从《世说新语·方正》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书中记载:“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11]甚至陆机贵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之时,竟有一小都督“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12]地位之尴尬可想而知。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陆机对功名的渴望。
陆机的功名意识一方面与陆机“伏膺儒术”有很大的关系。儒家主张入世,主张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与齐家是为治国平天下作准备。另一方面,与陆机家世有关系。如上文所说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重臣,身份显赫。然而,随着东吴的灭亡,陆氏一门也随之没落了。陆机一直想建功立业,重振家风,这种渴望也浸在了他的诗歌里。孙明君认为陆机是一个进取的人,但进取之士并不等于就是儒学之士,陆机诗歌中的功名意识实际上来源于他的士族意识、门第观念[13]。然而,不管他的功名意识是来自“伏膺儒术”,还是“源于士族意识、门第观念”,陆机功名意识的表现与他的生命意识是结合在一起的,“与生命短暂的感伤情绪结合在一起”[14]。也就是说,陆机的功名意识与他的哀死之叹是联系在一起的。
二、生死如一
陆机生命意识表现出生死如一的观念。生之有苦,然死亦有悲。生与死俱是一悲剧。既然皆是一悲剧,生与死也就如一了。这与乐生哀死是截然相反的。乐生哀死与生死如一看似矛盾,然联系陆机的人生经历来看,这也是历经世事后的一种体悟。
其一,生之有苦。于陆机来说,爱别离苦为最,求不得苦其次。求不得苦体现在陆机渴望建功立业,重振家风,然事不尽如人意。陆机的世界充满了死亡,爱别离苦在陆机诗文里随处可见,《叹逝赋》云:“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15]。陆抗于吴凤皇二年(273)秋死于任上;吴天纪四年(280),陆机兄长陆晏、陆景先后去世[16]。《与弟清河云诗》《吴贞献处士陆君诔》《愍思赋》《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记述了他亲人的亡多存寡。《门有车马客行》中“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17]一句,读之深觉凄惨;《拟青青陵上柏》《悲哉行》感叹人生短暂与飘零;《东宫作诗》《于承明作兴士龙》的欲归不能的无奈;《赠弟士龙》《豫章行》的兄弟别情;《答张士然诗》《赠冯文羆》的思乡怀人。悠悠念思悲情难禁,此间种种,情何以堪。
其二,生之有苦,然死亦有悲。陆机通过《王侯挽歌辞》中“操心玄芒内。注血治鬼区”[18],忧死后之事;在《吊魏武帝文》里叹息“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19],感慨在面对死亡之时无论是什么人、无论生前有多么强大都不能阻止死亡的来临与发生,这实在是人生之大悲。《挽歌三首》:“反复铺陈渲染,将死亡之悲表现到了极致,从一方面折射了陆机晚期的心态。”[20]不过,在《大暮赋》序中,陆机却说:“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21]体现出了道家齐生死、一荣辱的达观,一反诸多文中的感伤、哀愁、无奈与叹息,竟流露出生不足恋、死不足悲的意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陆机真的看破生死了,如陆机《挽歌辞》:“在昔良可悲,魂往一何戚。念我平生时,人道多拘役。”[22]乐生恶死,这是人之常情,恐惧与无奈是每个人都很难消除的。可是,有生之年里“人道多拘役”,活着又有何意味?
陆机的思想,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过除了儒家,陆机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君子行》:“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23]这首诗歌里思想杂陈儒道,在体裁的划分上可以说是属于玄言了。不过,道家思想体现得并不是那么明显。在刘运好教授校注的文集里有一首《失题诗》,在这首诗歌里陆机的道家思想倒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失题诗》其一:“澄神玄漠流,棲心太素域,弭节欣高视,俟我大梦觉。”[24]其中,“澄神”就是使心神澄澈,也就是庄子所谓的心斋。这一首《失题诗》讲述的都是道家之事,陆机彻悟生死如大梦之初觉,所言是道家齐生死、一荣辱之哲学[25]。在《大暮赋》里,陆机有生不足恋、死不足悲之意,《君子行》“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一句也是杂糅儒道的玄言,在《失题诗》说大梦觉的道家之言也就不出奇了,可以说这是陆机对生命有了生死如一的感悟,也是陆机对道家思想的接纳。表面看来,陆机的生死如一之悟与乐生哀死表面看是有矛盾的,其实不然。这是陆机在经历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惨淡黯然的人生之后,在精神上穷极思变回归道家思想之时必然会有的一种体悟,也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三、生与死的超越
陆机有了生死如一的感悟之后,生命意识体现出超越生与死也就自然而然了。乐生哀死的背后是对现实的无力与无奈。陆机有感生之有苦死亦有悲,生死如一的背后,同样是对现实的无奈与无力。对生的超越就是希望像仙人一样永生,或者像隐士一样自在与洒脱地生活在山林之中。对死的超越就是能留名世间,流芳百世。超越生与死,无论哪一种都是挣脱现实的一个方式,也是陆机生命意识的一种升华。
(一)对生的超越
对有永恒生命仙人的艳羡,大都有感于人生百年转眼即逝的苦恼与无奈,如曹植、郭璞等的游仙诗,陆机也不例外。《列仙赋》:“夫何列仙之玄妙,超摄生乎世表。”[26]陆机想求仙,实现对现实生命不永久的超越,可是仙踪缥缈。《王子乔赞》中仙人“遗形灵岳,顾景忘归。乘云倏忽,飘摇紫微”[27],但那只是一种遐想,一种虚幻。陆机自己也很明白长生不可经营而得,如《齐讴行》中“长存非所营”一句,道尽了陆机心中的苦涩。
求仙是虚幻的,陆机就想着换一种方式,以求实现对生的超越,或同隐士那样隐于山林,超脱于世俗,让自己从残酷的争斗中脱身出来,从自己建功立业的渴望中超脱出来,从重振家风的理想中超脱出来。例如,《幽人赋》云:“超沈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隐士,超然物外,不为外物所动,因为超越了尘世功业,所以世俗的罗网也就不能加在自己身上了。可实际上,陆机并不是真想做一个隐士,超脱世俗,如《招隐诗》其二“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这两句诗可以说是陆机对归隐的真实心态。归隐不是陆机自愿的,而是对现实感到无奈之后的选择,归隐之意是在苦苦求索富贵不可得之后才有的。孙拯作《嘉遁赋》劝其归隐,顾荣等同乡劝其回吴,陆机最后都没有听从,在变幻莫测的斗争中越陷越深。最终,叹息华亭鹤唳之不可得闻,也就是陆机身处那个时代的必然结局了。他追求对生的超越是矛盾的,想求仙却又明白仙踪缥缈,不想归隐却又不得不去想归隐,羡慕归隐之人。这是儒家入世思想与道家出世思想的矛盾在陆机身上的体现。在这个矛盾的背后,是陆机对现实的无奈,这种无奈导致陆机对生的超越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二)对死的超越
儒家有三不朽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28]魏晋之人重视文章,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9]据姜剑云考证,陆机的著作有十一种之多,如《陆机集》《连珠》[30]等,著述颇丰。
陆机生前就著名于世,“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31]。其后,对陆机虽有贬抑,然更多的是褒扬。唐太宗在其本传后赞“百代文宗”;梁钟嵘亦不吝溢美之辞;《诗品序》称“陆机为太康之英”;刘勰《文心雕龙》多处论及陆机及其作品;萧统《昭明文选》中所收录的作品中,陆机是最多的。
陆机的诸多著作中《文赋》影响最大。《文赋》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创作论,文中提出了“诗缘情说”,与“诗言志”并称中国诗学两大范畴。陈良运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从先秦至两汉的核心是“言志”,在这个时期的诗与应用的文学没有明显的本质区别。直到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诗歌才真正能对情感进行审美。“诗缘情而绮靡”是诗歌之美的首次张扬,也是创作思维方式的一次转型。诗人创作从“有指向思维”转至“我向思维”,从功利取向思维转到了审美取向思维[32]。可以说,陆机真正实现了“寄身于翰墨”“而声名自传于后”。
无论陆机是想通过求仙追求永久,或隐于山林享受自在的生命,来实现对生的超越,还是追求“立言”实现“不朽”,都是陆机超越现实生命的一个方式,是他生命意识的升华。当然,陆机对生超越以失败告终,在对死的超越上,陆机凭借文章实现了“不朽”。提起陆机,我们总能记得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这是陆机的不幸,不过却是文学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