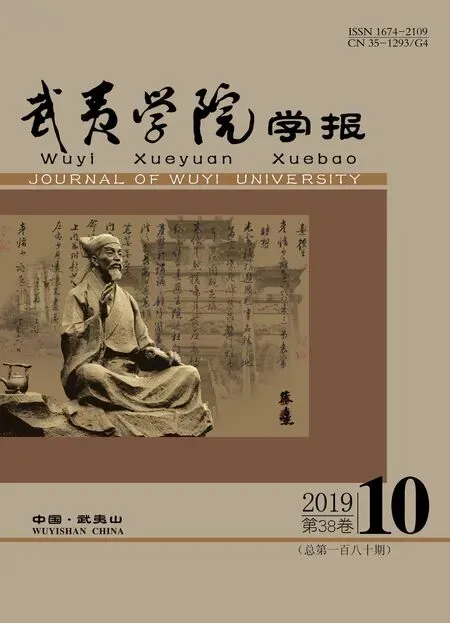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形成历史脉络研究
汪杨燕
(1.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1;2.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 福州 350001)
“生命共同体”概念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对其理论来源以及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阐释,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解,而且对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看法的基础上,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中华传统文化“和合”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习近平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曾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1]儒道“和合”观念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着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首要价值和思想精髓。
儒家思想历来主张“和”,这里的“和”不仅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它还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论语》思想的精髓,就在于以仁心善待万物,将天、地、人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对自然作过多的干预。在孔子看来,天就是自然,他认为四季周而复始,万物生生不息是自然固有的规律,任凭神灵也无法干预。此外,不论是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还是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等都体现着丰富的“和合”思想,这种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价值观成为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自然”概念的哲学家,他的学说主张“道法自然”。“道”在老子那里可以化生出关于宇宙自然、世间万物的一切规律和秩序,“法自然”作为老子“道”的最高准则,要求对自然必须采取一种无为顺应的态度,而不应当人为干预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和运行规律。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同样也体现出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从“齐物”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过程是庄子化“有待”为“无待”以“游”于“逍遥”的必要前提。强调“天人合一”,去除物我之别,将天地宇宙、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庄子学说的旨趣所在。习近平对道家生态思想也有独到的理解,他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人合一,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2]由此可见,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实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而从根本上说“生命共同体”思想也是对中华传统道家生态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曾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4]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曾多次深刻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5]恩格斯也曾深刻警醒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于我们。”[6]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依赖于自然界,离开了自然界,人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人类社会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学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如果违背了自然,必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习近平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就曾援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提到的关于人类破坏自然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事实来警醒人类,可见,习近平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始终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当今社会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他提出“生命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精髓,同时也体现着习近平深刻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二、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生命共同体”思想的萌芽与酝酿
1969年年初,年仅十五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川县,在当地的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开启了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在梁家河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四川农村置办沼气的报道,就自费亲自前往四川绵阳学习如何利用沼气。回来以后,他将所学经验付诸实践,不遗余力地在生活条件落后的梁家河办成了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沼气池的建设,解决了困扰当地农民的燃料供应问题,有力地保护了林草资源,减少了对山场的破坏,在陕北高原植被稀少地区开辟了一条保护生态环境的崭新发展模式。在这里,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思想虽未形成,但是其对生态环境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初显端倪。
1982年3月,习近平前往河北省正定县任职。在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的三年多时间里,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开始萌芽。习近平指出,正定县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必须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进行统筹规划。就正定县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一战略思想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习近平指出:“自然界为人类造就了日光、空气、土地、河流、森林、矿藏各种资源,供人类享用。过去,人类以无限制地开发以求生产的发展,这是那个时代的战略。现在,以合理开发、节制使用以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平衡,这是现代、当代的战略。”[7]由此可见,习近平已经深刻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类必须从自然中获取自身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但是,自然界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很多都是有限的。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而应该给自然界以“返还”。对于自然资源,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从而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平衡体现了习近平对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关系的深刻把握。由此,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得以萌芽,这种思想也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渐走向成熟。
(二)“环境就是生产力”:“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初步形成
1985年至2002年,习近平怀着热烈的山海情怀和赤子初心,在山川秀美的福建省经历了长达十七年的工作生涯。在福建任职期间,习近平提出了“生态福建”的生态战略构想。针对厦门的发展,习近平指出,厦门有着山海相通、陆岛相望的自然地理条件,要想充分利用好这些自然条件,就必须保护好海湾生态,重点建设以水为中心的生态型亚热带海滨特色景观城市。建设资源节约、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且独具特色的生态城市。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一场自然资源保卫战在厦门全市席卷开来。生态环境的改善、特色景观的开发、旅游事业的发展,不仅为厦门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为市民制造了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习近平注重生态保护的做法充分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而且能够带来持久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之后,习近平又先后带领宁德人民和福州人民走上了生态发展之路,为农村地区摆脱贫困以及城市建设指明了发展前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习近平逐渐意识到,自然本身对人类有着独特的价值。福建省既然拥有了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就更应加倍珍惜。而在福建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习近平始终秉承“滴水穿石,功成不必在我”的赤子初心,坚持“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对历史有交代”的崇高使命,在全国率先谋划建设绿色、循环、低碳的“生态省”,让“绿色”成了福建最明亮的一道底色。
2002年,习近平开始前往沿海发达省份浙江省任职,在浙江5年的探索使习近平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渐成体系。习近平指出:“像所有的认知过程一样,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人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8]因此,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全体人民自觉自为的行动,打造“绿色浙江”必须加大生态教育宣传力度,提升社会群体的环保意识,创设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氛围,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使全体人民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齐心协力呵护共同的生态家园。针对浙江发展面临的“两座山”困扰,习近平提出,“两座山”关系的实质就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正确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采用辩证统一的观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辩证统一关系。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针对安吉县余村的发展状况,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这是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的重要战略思想。针对当时存在的很多疑问,习近平指出,浙江省具有良好的生态优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来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和生态观光等,这样,生态优势就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绿水青山”就能带来源源不断的“金山银山”,不仅如此,浙江人民在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能享受优美的生态环境带来的惬意与舒适。因此,“生态立县”“生态省”建设对于浙江乃至全国地区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项高明之举。在浙江任职五年,习近平始终将“生态省”建设作为浙江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为了消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他进一步提出“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GDP”[2]这一生态生产力的发展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面整治环境问题,给广大人民群众指明了发展前景。2007年习近平前往上海任职,他进一步将“生态省”建设的治理思想深入贯彻到上海市的发展中,坚持以绿色生态为导向,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且取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推动了上海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总之,在这些地方的领导实践促使习近平对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愈加深刻,从而为“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2008年,习近平前往中央任职。在此期间,他将几十年来所积累的地方工作经验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初步提出了“生命共同体”概念,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探索,进一步强化了“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构建与制度转化,逐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伟大构想。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9]自然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能量循环是自然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处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人的发展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好运作,如果这一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人的发展,甚至是人的生命必然也会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与内生动力机制,加快制度体系构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从源头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在论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时,习近平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10]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并将其作为指导我国“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远发展的科学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宗旨,它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强调以人为本,善待自然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准则,不仅是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将“生命共同体”思想进一步深化到国家战略层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建设放在国家发展的突出地位,纳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并就此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方针政策,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1]由此,“生命共同体”思想正式纳入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框架。
三、“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旨归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其本身包含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生命共同体”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前提。“生命共同体”强调的是实践基础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是有一个有机整体,这就要求人类在审视自然的时候必须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最终都要人类付出代价。“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终极价值追求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美丽中国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我们自身的力量。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建设是从外部力量和制度层面来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话,那么,十九大提出我们必须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则更加强调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形成生态价值观,从思想层面来保障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重要体现。因此,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终极价值追求的“生命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前提与基础。
其次,“生命共同体”思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生命共同体”概念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它既包含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准则,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生态实践导向。“生命共同体”始终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一方面离不开对人与自然整体性关系的考察,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态实践基础,只有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才能从根本上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此外,“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实践特性还要求我们不仅要增强生态意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意识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建设美丽中国也将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因此,“生命共同体”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方法论基础。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就是在汲取前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长期的地方工作实践中,在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趋紧、人与自然矛盾凸显的时代课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刻的生态哲学底蕴,它既包含着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辩证思路,还体现着“环境民生论”这一现实主题,“生命共同体”之终极价值追求就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被提上了日程,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最终在实践转向和制度建构方面得到了新的历史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