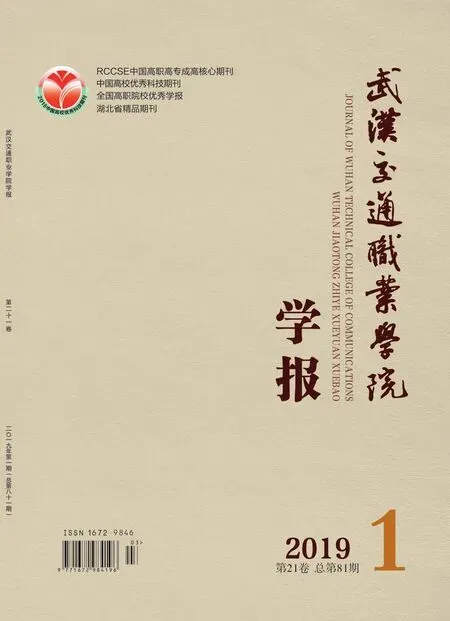针对妨碍安全驾驶案件的刑法规制路径研究*
宋莉莉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近年来,“车闹”事件此起彼伏,成为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现行法律对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惩罚还不到位,亟待完善相关法律,也说明了我国刑事刑法对立法的适时性体现的还不够充分,对于一些反映时代特点的犯罪行为,如妨碍驾驶行为并没有及时得到体现。为此,笔者建议增设“妨碍安全驾驶罪”,及时补充具有时代特点、符合时代要求的罪行规范。
一、目前我国妨碍安全驾驶事件多发
目前我国车辆数目激增,车辆事故频发,其中因妨碍公交车司机安全驾驶所导致的交通事故近年来更是频频发生。
2018年10月28日,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悲剧的发生,让整个社会痛心不已,发人警醒。11月2日,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官方宣布了此次事件的原因系“乘客刘某错过下车地点,与正在驾驶中的驾驶员发生争执,刘某持手机攻击驾驶员,驾驶员冉某将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格挡刘某,并与刘某抓扯,造成车辆失控,致使车辆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击后坠入江中”。十五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
无独有偶,2017年4月28日17时许,沈阳男子郭某乘坐刘某驾驶的282路公交车,郭某因没有及时下车,与公交车司机刘某发生厮打。过程中,不仅刘某被打伤,还导致公交车失控撞上行驶中的车辆,造成对方车中一人受伤,郭某赔偿被害人损失后,被认定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17年11月26日下午,福州市某公交车在行驶至一桥上时突然失控,撞上桥边的护栏,车头探出桥面,险些坠桥,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原因为一名车上乘客想要在非站点地下车,被司机拒绝后,伸手拉扯司机,导致公交失控,随后该乘客被警方行政处罚。
2017年11月27号上午9点多,在青岛市34路公交车上,车厢中一名女乘客因玩手机坐过站。在要求下车遭到驾驶员拒绝后,与驾驶员发生争执,司机随即报警,最后对徐某依法采取行政拘留五天的处罚。
2018年10月29日上午,北京市丰台区某公交车乘客邓某错过目的站,要求司机停车被司机拒绝,随后用整箱牛奶猛砸司机手部,严重影响驾驶员正常驾驶,致使公交车与一辆正常行驶中的小轿车发生剐蹭。最后,邓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丰台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车闹”事件时有发生,记者报道此类事件常用“险酿大祸”一词一语带过。但此次造成十五人死亡的悲剧,教训之惨重,让人不敢直视。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敲响的安全警钟振聋发聩,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为化解此类公共交通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应尽快采取措施,或从立法根本上增设“妨碍安全驾驶罪”,以指导法官更规范、更精准、更公平地裁判。
二、刑法中增设“妨碍安全驾驶罪”的必要性
对于增设“妨碍安全驾驶罪”的提议,我国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有观点认为动辄增加刑法罪名,将导致刑法过度化,国民对刑法的认同感减弱,而且不得不考虑其治理的方向及配套措施的建立。对于“车闹”事件,可以在交通管理措施方面找到应对之法,也可依靠行政制度来预防[1]。也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体系足够评价这一行为,刑法增设“妨碍安全驾驶罪”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如刑法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中的危险方法可以进行扩张解释,没有必要再去增设新的罪名。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注重刑法理念的时代更新,坚持刑法改革的国际化,并深化新型犯罪的刑法治理[2]。在现行刑法条文不足以评价一些反应时代特点的犯罪行为时,应当适时的在具体内容、刑罚任务和目的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改变。这不仅体现出我国刑法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印证了我国刑法内容所具有的前瞻性的特点。
(一)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的不足
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律评价此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并不适用。在前文列举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车闹”事件最后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处罚,此举有诸多不妥之处,理由如下。
第一,从量刑程度上讲,若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刑罚过重,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前者是危险犯,即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有可能会造成多数人人身伤亡和大量的公私财产损失的危险,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安全,即使该行为所引发的危害结果尚不严重,行为人也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判处法定幅度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对于妨碍安全驾驶行为,若行为人暴力殴打的行为不足以导致驾驶人员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且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该充分考虑到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低,社会危害性不大,并不能等同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主体。此时再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就会导致刑罚过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应当承担的责任不相适应,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二,从危险程度上讲,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不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若将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不乏有任意扩大此罪中“以其他危险方法”的适用范围的嫌疑,对此应务必做严格解释[3]。只有行为人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采用的危险方法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的危险性相当,且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能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4]。反观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其本质不过是乘客与驾驶人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将其上升到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相当的危险性程度,是不恰当的。
第三,从危害结果的可控性上讲,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害结果是不可控的,而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危害结果是可控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行为人一旦实施了防火、决水、爆炸、投毒的行为,对可能侵犯的对象和造成的危害结果都无法预见,既无法预料也不可控制。然而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人却能够控制其危害结果。例如,谩骂侮辱驾驶人员,向驾驶人员吐口水等行为。其行为的危害结果和范围不可能随时扩大或增加。
第四,从主观方面上讲,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主观上具有“加害性”,主观恶性大。而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不具有“加害性”,主观恶性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行为人往往是为了追求损害他人生命健康安全的结果,希望或放任损害公共安全的结果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加害性”,主观恶性大。而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一般不具有这种“加害性”,它的危险性来自行为本身,主观恶性小。
(二)以危险驾驶罪或交通肇事罪处罚的不足
也有人建议以危险驾驶罪或交通肇事罪处罚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危险驾驶罪指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其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秩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秩序,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且危险驾驶罪犯罪主体主要是机动车驾驶人员,虽然与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同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无论是从犯罪形式还是犯罪主体来讲,都不能将妨碍安全驾驶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行为。再者,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预防性立法模式,目的是防患于未然[5]。所以,危险驾驶罪刑罚相对较轻,最高刑罚也仅仅为六个月拘役,不足以有效抑制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发生。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同“妨碍安全驾驶罪”相比,二者相同之处在于二者所侵犯的客体皆为公共安全,并且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共通性,即必须发生在整个交通运输活动过程中。但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决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进行处罚。首先,交通肇事罪主体主要是直接从事交通运输业务和保证交通运输的人员;而实施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主体,主要是乘客。其次,必须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则未必引起严重后果,如仅是谩骂、侮辱行为。最后,严重后果必须由违章行为引起,即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所引起[6];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主体是乘客,违章行为也就无从谈起。很显然,以交通肇事罪处罚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也是不合理的。
(三)现行行政法规难以有效规制
我国现行调整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行政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规定:“乘车人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不得向车外抛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为。”本条是对乘车人的要求。乘车人不得有在车内大声喧哗、吵闹、与司机闲聊、将头手伸出窗外等干扰驾驶员正常驾驶、影响行车安全的行为。此条只是包含了对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行为的处罚规定,难以有效规制日趋复杂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不能作为对妨碍安全驾驶行为进行处罚的依据。且处罚结果较轻,不能起到威慑作用,也很难有效减少因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笔者认为,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不应简单的定义为“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因其所侵犯的客体为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关乎社会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都应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仅以罚金或行政拘留进行处罚,其惩戒力、震慑力较轻,不足以有效打击犯罪、教育公众,不足以维护公共安全的底线[7]。
三、国外在妨碍安全驾驶行为方面的经验
在国外一些国家,攻击公交车驾驶员之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国家对此种行为进行准确定性,并兼顾此行为的危险性,往往以严格而明确的立法去界定,并实施惩罚措施。这不仅有效减少了因妨碍安全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而且对妨碍驾驶行为起到了良好的预防效果,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是美国在此方面所做的相关规定。美国各州均将“以暴力手段危害公交车驾驶员等公共交通营运人员”这一行为视为威胁全车乘客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并明确立法,对此行为给予严重的惩处措施。纽约州相关立法将袭击公交车驾驶员等公共交通营运人员的行为,从“轻罪”直升到了“D级重罪”,危害程度相当于袭击警察,最高可能会被处以七年监禁的惩罚。新泽西州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袭击公交车驾驶员,将处以7000美元罚款并处以五年监禁的刑罚。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各州不仅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审理“以暴力手段攻击公交车驾驶员”案件时,对于情节轻微,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案件,行为人都将定为重罪,并以重罪的处罚方式进行处罚。例如,辱骂公交车司机,向公交车司机吐口水等行为,看似轻微,却发生频率极高,将导致驾驶员分散注意力,威胁行车安全,应当同样以重罪处罚。
美国相关立法将公共生命财产安全作为第一考量,而不是仅看案件后果的轻重。这种量刑考虑,将很大程度地抑制此类事件发生,有效地预防犯罪。两相对比,我国对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处罚则过于轻微了,有时仅以批评教育作为处罚结果。导致此类事件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不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很大程度上存在侥幸心理,这无疑对一些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加拿大在2015年通过法案,认为对袭击包括公交车、出租车、渡轮、地铁等所有公共交通驾驶人员的行为绝对不能等同于普通的人身、财产犯罪的量刑,应该处以比普通袭击行为更严厉的法律惩罚。
在英国,立法者认为,对于攻击公交车驾驶员等公共交通营运人员的行为,考虑该犯罪行为的危险性,后果的严重性和现实性,应归属于一种反社会行为,无论是警方还是伦敦交通局都可执行反社会行为令(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来保护公众免受公共交通中反社会行为的侵害。被执行该令的犯罪人员在至少两年内不可以进入指定公共区域。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法律中详细规定了公交车驾驶人员在与乘客发生冲突时的做法:“当乘客做出暴力、喧闹、侵犯性行为,或者严重醉酒的情况下,驾驶人员有权让乘客下车。公交安全工作人员(包括驾驶员)有责任采取行动,确保公共人身财产安全。”
四、“妨碍安全驾驶罪”的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妨碍安全驾驶罪”可以这样设定:指行为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采取暴力手段侵害驾驶人员人身权,妨碍驾驶员安全驾驶,危及正在行驶中的车辆安全的行为。
(一)“妨碍安全驾驶罪”构成要件
本罪中所侵犯的客体应是双重客体,即不仅侵犯了公共安全,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但是,它的最终结果是危害了公共交通工具行驶的公共安全,使用暴力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应当将其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中。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交通工具上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危及交通安全的行为。犯罪对象是驾驶人员即实际控制交通工具的人员,行为人必须是对正在行驶中的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危及交通安全的,才构成犯罪。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使正在行驶中的交通工具的安全处于危险状态即构成犯罪(危险犯),并不要求有实际的严重后果发生,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时,则应适用结果加重的刑罚处罚。
本罪的主体应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既可以由中国人构成,也可以由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构成。
对于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人主观方面而言,行为人需有双重的故意,以暴力手段攻击正在驾驶的驾驶员行为,侵犯了驾驶员的人身权,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而放任公共交通工具发生危险,严重危害了公共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后果主观上具有间接故意。
(二)量刑
妨碍安全驾驶行为造成的一般后果,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加以如下从重处罚的情形:
1.在人员、车辆密集区域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
2.在雨天、雾天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
3.在桥梁、隧道、陡坡、急弯等危险路段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
4.经他人劝告、阻拦后仍然继续实施的;
5.其他严重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如此量刑,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迎合了社会预期。
五、结语
“车闹”事件频繁发生,说明了我国社会民众对于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性和风险意识淡薄。建议单独设立“妨碍安全驾驶罪”,不仅是因为现行法律条文不足以评价妨碍安全驾驶行为,重要的是能够更加明确,更具有针对性地精准打击这种妨碍安全驾驶、危及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单列“妨碍安全驾驶罪”以更清楚明了的刑法罪名规定维护公共安全,使民众对公共交通领域公共安全秩序的法律遵守意识得到加强,让广大乘客都懂得打骂正在驾驶中的驾驶人员实则是在危害公共安全,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对“车闹”行为形成震慑。
维护公共交通安全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对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严惩,如同一道法制枷锁,将“车闹”行为束缚其中。除此之外,还需要多管齐下,如强化公交车上的安全装置、加装隔离装置、实时监控车内情况、增加报警装置、完善驾驶室功能等措施保障行驶安全;媒体各界要增强法制宣传力度,呼吁社会公众自觉遵守乘车规范;加强公交车司机的岗前培训教育;倡导尊重司机、宽容平和的社会气氛,并保护和激发公众尤其是乘客见义勇为的美德,营造安全有序、公正和谐的社会空间,将公共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率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