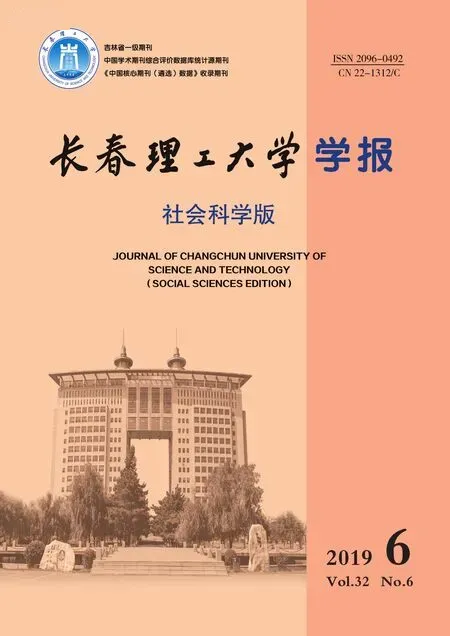蒋彝对中国书法的译介研究
蒋玲燕,顾 毅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222)
一、引言
中国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的艺术,中国书法文化的介绍往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书法教材作为课堂重要的载体,是书法对外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汉语热”的出现,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英文的或者是中英对照的中国书法教材。以英文编写的中国书法教材,写作语言虽然是英语,但是其指向却是中国文化,其中自然涉及翻译,尤其是中国书法术语的翻译。教材中对翻译成分的处理失当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传播与接受度。谢天振承认,“60多年来尽管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外译,希望以此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然而却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6。”他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因为在两千年来的译入翻译实践(从古代的佛经翻译到清末明初以来的文学名著、社科经典翻译)中形成的译学理念——奉‘忠实原文’为翻译的唯一标准、拜‘原文至上’为圭臬等——已经深深地扎根在这些领导和翻译工作者的脑海之中,他们以建立在译入翻译实践基础上的这些翻译理念、标准、方法论来看待和指导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译出行为,继续只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而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诸种因素,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出行为的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等……[1]7。”此说虽针对汉语典籍外译,但对以书法教学为目的的书法教材中翻译问题的处理亦有启示。
蒋彝(Chiang Yee)为作家、书画家,生于1903年,江西九江县人,字仲雅,笔名“哑行者”。蒋彝自20世纪30年代初旅居西方,用英文创作了多部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谈到2 0世纪70年代前以英文写作并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华裔作家,人们常常会想到林语堂。其实,就贡献而言,与他齐名的还有旅美华裔游记作家蒋彝[2]。”
蒋彝1938年于伦敦出版了Chinese Calligraphy:An Introduction to Its Aesthetic and Technique(《中国书法——美学与技艺方面的介绍》),下文简称《中国书法》①文中所引用的蒋彝原文,其翻译皆来自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书法》译本。,其中包括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构成、书体、书法的抽象美、技巧、笔画、结构、练习、书法与绘画等章节。书中序言说明:本书的部分正文,最初于1935—1936年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时,以讲课形式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以及伦敦的中国社会团体中发表[3]17。该书一版再版,成为英语国家许多大学里中国书法的经典教科书。
CNKI检索显示,目前有关蒋彝的44篇论文大多集中于他以英语写作的域外游记文学,以及他的写作效果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及中国对外出版的启示。以蒋彝《中国书法》为个案的翻译研究较少且多为文本内的微观层面研究。顾毅、俄倩[4]探讨了“永字八法”的翻译,其中引用并评价了蒋彝的翻译,并将其与其他的翻译做了对比。周玉芳[5]把蒋彝的《中国书法》和陈廷祐的Chinese Calligraphy:The Art of Handwriting(《中国书法:书写的艺术》)进行对比,就书法出版物的传播策略进行研究。任一鸣[6]在后殖民文化批评中的文化翻译视角下对蒋彝的作品进行了研究。本文将结合接受美学的理论,将其放在《中国书法》这一具体的文本中,结合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期待视野”、“审美距离”以及“隐含读者”等,以观察蒋彝是如何处理《中国书法》中所牵涉的中国书法翻译问题的。
二、接受美学相关理论概述
“接受美学”概念由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Robert·Jauss)于1967年首次提出。尧斯指出[7]:“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尧斯认为传统文学理论长期忽视了读者这一重要因素,而只将注意力集中于作家、作品和研究理论等。他肯定读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主张将作家、作品以及读者接受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面的研究视角。同时,他认为读者的接受不仅仅影响到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甚至会影响作家的构思。
(一)期待视野
所谓“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活动接受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8]61。“期待视野”决定了读者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判断标准,以及对作品的基本态度和评价[9]33。由于期待视野不同以及期待视野自身的发展变化,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的动机是不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读者动机包括:审美动机、求知动机、受教动机、批评动机、借鉴动机[10]326。接受动机不同,必然导致读者不同范围的阅读选择;即使面对同一部作品,读者的着眼点也会不同[10]328。可见,期待视野是影响读者阅读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审美距离
在审美距离原理的相关问题上,罗悌伦认为,“理解过程和反应过程一道产生接受过程,接受过程的积累形成审美经验。而审美经验会使人产生一种潜反射审美态度……倘作品符合接受者的审美经验,则他的审美期望得到加强,于是接受十分顺利。可见,审美经验对接受具有制导作用。审美经验的这一制导作用需要一个‘美学距离’或‘角色距离’。就是说,接受者不能将自己等同于某一角色,而要取旁观态度,从一定的‘美学距离’出发,这样才能进行审美欣赏,并且一边欣赏一边领悟。审美经验的制导作用随这一‘美学距离’而变化[11]。”罗悌伦在原文中给出了审美距离和审美作用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

图1 审美距离和审美作用的关系
由图可见,距离为0时,失控,接受者完全进入角色;距离增大时,作用趋近0,接受者默然[11]。隋荣谊、郭黎阳[12]将其引入归化异化的翻译研究之中,认为“原点对应读者的直接期待,抛物线最高点对应读者的创新期待。当文本的审美距离与读者的直接期待重合时,译者全部采用归化策略,文本在读者中的审美效果为0;随着文本与读者直接期待的审美距离逐渐增大,翻译时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文本在读者中的审美效果递增:如果审美距离过大,超越读者的创新期待,译作中异化多于归化,作者在读者的审美效果会逐渐减小趋于零。”基于前人的研究结果,本文试图在翻译策略上进行一些扩充。本文涉及的译介大致有:如英译、释译、给出中文、音译等。在蒋彝的中译英的翻译实践中,给出中文和音译所达到的效果更类似于“异化”所达到的翻译效果(使读者靠近作者),同样,“英译”和“释译”更类似于“归化”的翻译效果(使作者靠近读者)。图示的原点,对于国外读者来说,英语是母语,此时译文是以“归化”效果的翻译为主(如英译和释译),不涉及到读者既定视野以外的内容,与读者的直接期待融合,文章的可读性为最强。从原点往后,虽然“归化”所占比随着审美距离增大而逐渐变低,但“归化”效果的翻译策略仍处于主要地位。此时,对读者而言,文章可读性慢慢降低,读者与异语(中文)逐渐亲近,看到既定了视野以外的东西,创新期待变高,使得审美效果上升。随着审美距离不断增大,过了一定“度”之后,文章以“异化”效果的翻译成分为主。此时,虽然读者与异语较为亲近,创新期待较高,但文章的可读性变差,造成阅读障碍,审美效果降低。由此可得,单一的翻译策略则不能够保证翻译效果。
(三)隐含读者
“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的概念是由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Iser)提出,与现实读者相对。由于译名的差异,有时也被称为“隐形读者”、“隐性读者”、“暗隐读者”等。朱立元认为,“‘隐含的读者’既非现实的读者,也非理想的读者,而只是一种可能出现的读者,一种根植于本文结构中、与本文结构暗示的方向吻合的读者;同时,这个‘读者’又不只受制于本文结构,而是有其能动性与创造性的,‘他’能把本文结构提供的可能性加以具体化和实现。实际上,这个‘隐含的读者’乃是被赋予人格化名称的文学本文潜在意义在阅读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8]268。”
三、《中国书法》译者受众接受意识及译介策略方法分析
《中国书法》调动了蒋彝的编者、译者、教师多重身份。编者即作者身份起统摄作用。其中的翻译是为了完成写作的目的,而在选择翻译材料、制定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过程中又体现了他的师者身份。师者身份需要他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学生的汉语、中国文化及中国书法的认知水平。因此,蒋彝的译介模式则更倾向于读者接受。学生在书法课上的主要目的是接触、学习外域文化。译介内容过多贴近母语,则无助于学生接近异国文化,过多贴近异语,则会对本来就没有中文功底的学生造成理解阻碍。
(一)译者受众接受意识分析
蒋彝在书的绪论部分写道:“这本书不是为已经具备这方面知识的西方人,也不是为中国公众而写的。我打算使它成为那些有意探究书法基本原理的人的简易指南……我写本书的动机之一,是希望帮助这些人不需学习中文就能欣赏书法。倘使他们能够懂得那些词的文字意义,当然更好[3]20。”由此可见,蒋彝的读者定位是懂点中文的读者,当然,不懂的话也没有关系。
在接受活动开始之前,任何读者已有自己特定的“期待视界”,即“对每部作品的独特的意向(一种高于心理反应、也高于个别读者主观理解的意向)[8]63。”朱立元认为,这种阅读前的意向和视界,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中的选择与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8]63。蒋彝充分地考虑了受众的“期待视野”。蒋彝在作者序中写道[3]17:“教授英文书法的教师维·伊·霍克丝小姐,向我提供了许多有关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欢迎的知识。”英国著名评论家Herbert Read在给本书的序中写道:“第一次拜读蒋先生的著作时,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一美学与现代抽象艺术的美学之间的相似之处[3]7。”蒋彝充分把握住了外国读者对中国艺术的期待视野以及阅读意向,在书中用大量篇幅解释中国艺术和美学,如第四章中的抽象美和中国书法,第十章的美学原则等。
“读者对作品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释,其接受是‘阐释性的接受’,这就必然带来‘阐释的主观性问题,不同读者的鉴赏趣味或读者的水平问题’,造成一千个观众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8]63。”蒋彝在介绍中国文字时提到:到目前,中国文字已达50万。同时,蒋彝充分考虑了读者对大量汉字的“畏难”心理,特别附上脚注说明:读者不必因此而不敢学习汉语。为容易读和讲起见,只要记住4000字左右或甚至再少一些[3]24。这一附注避免了多数没有中文基础的读者可能会产生的“阐释的主观性问题”,即误以为只有学会所有汉字才能达到汉语学习的要求。陈廷佑在Chinese Calligraphy一书中写到“据统计,现在常用的字为3500个,而汉字字库中的总数约有9万个[13]。”蒋彝“中国文字已达50万”之说不知依据为何,但不管怎么说,其初衷是为了打消读者的畏难心理。
蒋彝不仅对读者有明确的定位,并且也照顾到读者的潜在要求,因此在翻译上给予适当的考虑。在《中国书法》的第三部分的参考目录上[3]240,蒋彝对所有参考书目统一采用“中文+音译”的形式,如:许慎Hsu Shen:说文解字Shuo-Wen-Chui-Tzu,不进行英文翻译甚至解释。对于没有中文基础的国外读者来说,这一部分完全是晦涩难懂的。蒋彝在参考文献的开头写道,“针对那些了解中文,并渴望进一步学习中文,不仅限于此书的人,下列书推荐一读[3]240。”(中文译本中并未翻译,此句为笔者译)。虽然蒋彝在最开头给读者的定位为不具备中国书法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没有学习过中国汉字的外国人。但是,可以看到蒋彝在写参考目录时,结合了读者的客观情况,再次对读者进行划分。蒋彝提供的参考文献书籍大都是中文古籍,类似许慎的《说文解字》,华石斧的《国文探索一斑》等,几乎都没有正式出版的英译本,甚至有的为古文文献。对于没有中文基础的外国读者,这些书目对他们的参考价值不大。因此,蒋彝只标注参考书的中文名称和读音,便于有中文功底的读者借助这些译介找到中文书。
潜在的读者不是谁捏造出来的,而是作家创作心理上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它对激发作家创作的冲动、欲望、指导作家确定创作的方法、原则和观察、概括生活的视角、方向,帮助作家进行符合读者需求的艺术构思和写作,都有重要意义[8]280。
(二)术语的深度翻译
中国书法一般被定义为汉字书写的艺术,所以,一般的对外书法教材会包括汉字的起源、汉字造字法、各种书体的演变、基本笔画、间架结构、审美、书法的练习方法等章节,而每个章节都会有突出内容的核心概念或者术语。这些概念及书法术语往往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在古代书论等文献中经常出现的纯粹的中国文化负载词,在教材中被翻译成英语。本文摘取了蒋彝[3]25-32、王晓钧[14]、李文丹[15]书法在各自撰写的对外教材中的“六书”翻译来进行对比。
蒋彝采取的是英译、释译、音译、中文等译介非单一模式。首先,此策略优势在于其“精准”。因为,此书致力于为那些没有中文基础的外国读者能顺利学习书法而编写,因此多种不同的译介能够辅助读者多方位了解教材中的学习内容。拿“指事字”来说,王晓钧将其译为Indicative(or Diagrammatic),李文丹译为Indicatives。仅以某个英语词来对应可能会带来误导。李文丹将转注和假借字都译成了Borrowing。Borrowing在英语语言学中其实有固定含义。《语言学教程》对此进行的解释是:Borrowing:A word is taken from another language and it may be adapted to the borrowing language’s phonological system[16]。由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中文里的假借字或者转注字是从别国语言里借过来的。其次,单一译介不利于学习者在其他参考书目中定位学习内容。因为对外书法教材的接受者是很多中文水平不佳甚至欠缺的外国人,阅读中文的书法书籍有一定困难。而目前很多书法术语都没有统一的翻译,不同的教材有不同的译名。很多书法参考书目之间在译名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互相也没有一定的交集。比如,郦青和杨晓波[17]列举了不同译者和字典关于“指事”的英译,有的单译成Self-explanatory Characters,或者是Zhishi,或者是Chih Shih,还有的译成Indicatethings等,对于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来说,很难把三个词联想到一个事物上去。而蒋彝尽可能地将译介都列了出来,使得读者能够通过这些不同的译介去别的参考书上进行查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读者接受的信息没有因为翻译的不同而造成误解。

表1 蒋彝、王晓钧、李文丹的“六书”翻译
在对外书法教材的编纂问题上,采用单一的“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折损接受效果。他的译介策略并非单一,包括音译和汉字以及插图说明。可以看出,蒋彝并非将其仅作为一个翻译工作来做,而是将其放在教材文本的视角之下,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以及客观认知来进行译介的选择。此译介策略将文本信息的保真度最大化。
基于阿皮亚等人的深度翻译主张,穆哈维(Muhawi)提出,为了尽可能展现原文丰富的多层含义,要包括这几个层面:它必须包括原作中的原文本(或文字)、罗马字母音译、语素形态上的翻译(字面上)以及意译[18]。从中可知,深度翻译的文本可以展示文本不同层次的信息。蒋彝在此书中的多种不同翻译策略则暗合穆哈维的翻译主张。蒋彝给出中文的译法,则暗合穆哈维的“原作中的原文本”,音译则是“罗马字母音译”,英译则是“词素形态上的翻译”,“释译”则是“意译”。
毫无疑问,读者的审美效果是受到文本内容以及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影响而不断变化的。美学距离并不是越近越好,或者越远越好。一成不变的译介,往往不能收到很好的接受效果。获得审美需求的最大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需要译者不断地在翻译的过程中权衡客观条件,充分结合读者的接受性,预设隐含读者的需求,不断地调节归化异化和直译异译等各种翻译策略。蒋彝的《中国书法》一书译介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