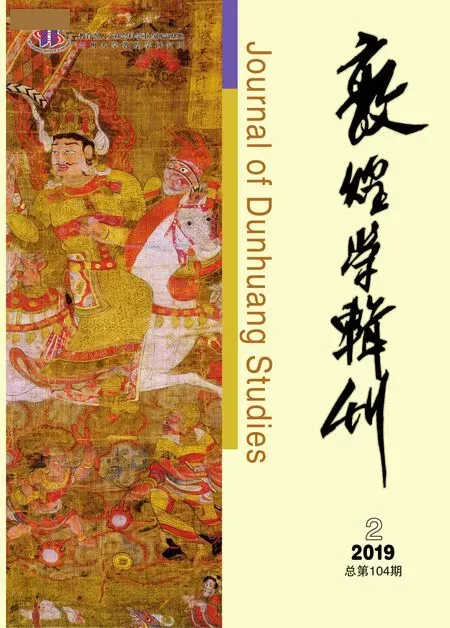敦煌吐蕃文书军事问题研究综述
华锐吉
(1.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2.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甘肃 夏河 747100)
吐蕃军事问题是学界学者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但其缺乏直接的研究材料,除了在藏汉两文的历史古籍中有零星记录之外,就只能从敦煌文献中窥视一般。尽管相关资料不多,但是广大学者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料,做出了非常伟大的研究。本人就目前所获而知,敦煌古藏文写本中直述吐蕃军事问题的文书只有1份,为 《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①巴桑旺堆分两部分发表了这一新发现的关于吐蕃军事的文书,前118行发表在 《中国藏学》2014年3期上,论文题目为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书残卷解读》,后389行发表在 《中国藏学》2015年增刊上,论文题目为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书 (下卷)初步解读》。下文中用 《敦煌古藏文兵律》代替该文书名。。另外还有文书间接涉及了吐蕃时期的军事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有2份,分别为法藏P.T.1185号写卷和英藏ch,73,xv,10号写卷。
P.T.1185号写卷,最先由王尧、陈践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成汉文,并为写卷定名为 “军需调拨文书”。②此写卷的译文另外还收录在2008年出版的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中。王尧、陈践 《军需调拨文书》,《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之后,陆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该文书中出现的论悉达古(blon-stu-gu)并非吐蕃大相噶尔之子悉多干 (mgar-sta-gu);认为文书大约抄写于9世纪前期吐蕃统治河陇地区之时,此文书对该时期,吐蕃与吐谷浑、党项等民族之间的军用物资征集、抚恤费用发放等军政事务管理以及与这些民族的关系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①陆离 《敦煌藏文P.T.1185号 〈军需调拨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西藏研究》2016年第4期。ch,73,xv,10号写卷,由托马斯首先翻译出版在其著作 《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中,后由匈牙利藏学家乌瑞作了进一步考释,改正了托马斯著作中的错漏。他认为这份写卷的内容主要涉及吐蕃统治下的基层军事组织,有助于了解吐蕃占领下的河陇西域基层组织体系,进而推断出吐蕃的区域组织的权限。②[匈]乌瑞著,赵晓意译,杨铭校 《关于敦煌一份军事文献的注释》, 《国外敦煌学、藏学研究翻译与评述》,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7页。又载于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20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5页。《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最先由巴桑旺堆先生发表出来,这份文书的发布为吐蕃军事研究提供了一份新材料。他完整抄录了藏文原文508行③此文书应为508行,但是巴桑旺堆先生发表的行数为507行,是在抄录时把第424行抄在了第423行之后,故而序号少了一行。,并对文书进行了初步的汉文翻译,文章最后附影印图版。④巴桑旺堆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书残卷解读》,《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书 (下卷)初步解读》,《中国藏学》2015年第S0期。西藏大学的西热桑布教授也在 《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上发表了这份写卷的藏文原文,另对写卷作了题解分析。⑤西绕桑布 《新近发现的吐番时期军事律法文献评介》,《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15年第4期。达琼依据该写卷中出现的赞普名号、大臣名字、亲属称谓,结合藏文典籍中的相关记载,考证了这份新发现的兵书律例的颁布年代和书写年代,分别为都松芒波杰和赤松德赞时期。⑥达琼 《新发现的吐蕃兵律年代初考》,《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16年第2期。
一 关于吐蕃军事问题的著述
王忠的 《新唐书吐蕃笺证》(1958)是国内较早时期出版的以吐蕃军事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该书根据藏汉文有关史料,主要以 《新唐书·吐蕃传》为蓝本对吐蕃时期的史实进行了增补、考证,并对其讹误加以修正,研究了 《新唐书》所记载的吐蕃军事,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价值。根敦群佩的 《白史》依据敦煌藏文文献以及藏文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对吐蕃军队的组织构成、职官以及军队的英勇雄壮做出了精炼评介。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1965)通过对唐蕃之间一些战例的分析对吐蕃军事力量之优劣作了精辟的论述。英国学者托马斯在著作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依据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论述了吐蕃军事,主要涉及吐蕃在西域的军事组织、给养、铠甲、将领的等级和任命,军事指令等内容。次旦扎西、杨永红的 《西藏古近代军事史研究》(2010),是一部关于吐蕃军事史的专题研究著作,分上、下篇。上篇主要论述了吐蕃时期的军事问题,涉及包括吐蕃军事成就、吐蕃军事制度、吐蕃军事法规、吐蕃军事情报、吐蕃军队兵器、吐蕃军队作战的特点等等。在附录 《唐蕃军事事件年表》中统计了唐蕃之间发生的192次大小战争,并且详细地列出了唐蕃谁胜谁负。研究资料主要涉及了敦煌文献以及吐蕃碑铭石刻等。张云、林冠群主编的 《西藏通史吐蕃卷》(2017)则充分利用了敦煌藏文文献,专列一章探讨了吐蕃时期的军事,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吐蕃时期军事状况的大致面貌。朱悦梅的 《吐蕃王朝历史军事地理研究》(2017),利用历史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吐蕃军事制度、军事力量构成及其地理配置、军事给养特点、对外军事进程和军事地理方略等重要历史军事地理问题。
二 吐蕃军事问题研究方向
(一)军事制度研究
山口瑞凤对于吐蕃军队占领敦煌之后在当地的统治情况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他在讨论吐蕃在敦煌统治方式的变迁中,提到了吐蕃的军事组织,军政权下的官吏称谓以及名位顺序,尤其指出rgod-sar-kyi-sde①藤枝晃等人将rgod-sar-kyi-sde,翻译为阿骨萨部落。应为 “军部落”是相对于 “民部落”而言。②[日]山口瑞凤著,高然译 《吐蕃统治的敦煌》,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63页。王尧、陈践在 《吐蕃兵制考》一文中论述了吐蕃军队的名称来源、建制与定员、军队与氏族之关系、军事联盟等几个方面。指出吐蕃军队的组成、编制是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全民皆兵制”,分析了氏族与军队之间的关系,而此有利于吐蕃强大军事联盟的建立。③王尧、陈践 《吐蕃兵制考略——军事部落联盟剖析》,《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陆离分析ch,73,xv,10号写卷认为阿骨萨部落军队由 “射手”和 “护持”组成,前者是作战主力,后者负责杂务并参战。认为此种方式源于吐蕃军队的桂 (rgod)庸 (g.yung)制度。其基层兵制 (tshar)对于西夏、归义军军制产生了极大影响。④陆离 《吐蕃统治敦煌基层兵制新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杨铭、何宁生针对ch,73,xv,10号写卷和其他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tshar一词,对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基层兵制做了详考,认为tshar不应是于阗语,否认了乌瑞所作的“队”之解释,认为其应为汉语借词,与 “曹”相当。⑤杨铭、何宁生 《曹 (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杨铭《新刊西域古藏语写本所见的吐蕃官吏研究》,《中国藏学》2006年第3期。朱悦梅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的汉藏文文献,分析了吐蕃军队的构成,着重研究了吐蕃的军队给养制度,以及跟随自然地理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的给养方式。⑥朱悦梅 《吐蕃王朝军队给养方式探蠡》,《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任小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兵律》,结合新疆所出简牍,认为暗军 (mun-dmag)应系吐蕃军旅中的先锋军或奇袭军。⑦任小波 《暗军考——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中国藏学》2017年第2期。任树民认为吐蕃军队的作战兵种主要是骑兵,并且对军队装备、军功奖罚、战时体制等内容进行了探讨。⑧任树民 《吐蕃军事力量概述》,《西藏研究》1990年3期。另外还有一些论文是从宏观方面进行了分析。贺冬大约发表了6篇关于吐蕃军事的论文。在一篇文章中从宏观上对吐蕃军事制度形成原因做了分析和探讨,认为自然条件、政治制度、游牧经济和宗教文化等都对吐蕃军事制度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①贺冬 《试析吐蕃军事制度形成的原因》,《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在 《吐蕃军队兵役制度简论》这篇文章中对吐蕃军队的兵役制度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寓兵于民是吐蕃的兵役制度的重要形式。②贺冬 《吐蕃军队兵役制度简论》,《柴达木开发研究》2013年第1期。韩丹春对吐蕃军队的军事动员制度做了介绍和论述,认为吐蕃时期的军队拥有一套完整的、成熟的军事动员制度,为吐蕃军队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③韩丹春 《吐蕃军事动员制度研究》,《青藏高原论坛》2013年第3期。
(二)战略战术研究
在关于吐蕃军事战术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何峰。他根据藏文历史文献记载和敦煌文献记载,对吐蕃的军事战略与战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罗列出了吐蕃时期常用的6种战术,认为吐蕃对学习和运用战术非常重视。④何峰 《论吐蕃的军事战略与战术》,《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但介于资料的限制没能做更广泛和具体的论述。⑤此论文发表时间为2007年,在吐蕃军事方面最具权威的资料——敦煌古藏文写本,是在2014-2015年发布的,故此何峰在当时并没有看到第一手的吐蕃时期的军事资料。另外刘力钢借助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及汉文史籍在何峰老师的研究基础上分别对吐蕃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战术做了论述。⑥刘力钢 《吐蕃在唐蕃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初探》,《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张云对吐蕃时期的战略扩张进行了宏观上的分析和研究,尽量详细地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谈论了吐蕃战略扩张的实施情况。并且提出了吐蕃政权之所以强盛,以及逐渐走向衰落的原因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之设想。⑦张云 《吐蕃王朝扩张策略之分析》,《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齐德舜、洲塔根据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的各种征战史实,分析了吐蕃军队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军事思想,认为吐蕃军队以取胜为最终目的指导思想对其在战争中取得的骄人战绩是密不可分的。⑧齐德舜、洲塔 《吐蕃政权的传统军事思想初探》,《西藏研究》2008年第1期。杨永红认为吐蕃的军事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总结了吐蕃将领在征战过程中有充分的自主权、征战中充分利用被征服地的资源等一些作战特点。认为这些因素在吐蕃军事由弱至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⑨杨永红 《吐蕃军事发展的基本特点》,《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他的另一篇文章总结了吐蕃军队在作战方面形成的与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一套战略战术,包括以骑兵为主,善于远征和突然袭击,军事行动季节性明显等等。⑩杨永红 《吐蕃军队作战的特点》,《西藏研究》2010年第6期。但是在文中并没有运用直接的藏文文献资料,更多的是对汉文史书的利用,因此在分析上明显存在主观臆断之嫌,缺乏客观性判断。贺冬对吐蕃军事战争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阐述了军事战争对吐蕃王朝政权体制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⑪贺冬 《试析吐蕃军事战争》,《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三)军事情报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可看出吐蕃军队有着十分发达的驿传制度,重视军事情报的收集、有着非常发达的情报搜集网络。陈庆英、端智嘉在一份藏于敦煌文化馆的 《十万般若颂》经卷的空白处发现了一份简短的吐蕃驿传文书。他们对此文书进行了汉文翻译和解读,指出吐蕃时期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驿递制度,而且有效地推行到了吐蕃所管辖的所有地区。并且在战时还要负责巡查等任务,又具有军事性质。①陈庆英、端智嘉 《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甘肃社会科学》1981第3期。之后由张广达利用这件文书及国外所刊布的一些藏文文书、简牍,结合汉文史料,对吐蕃驿制名称、组织体系及其作用作了一番十分有益的研究。②张广达 《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7-178页。只是这些研究偏重于驿传制度本身,而对于吐蕃驿递的具体情况谈得不多。陈践践探讨了吐蕃为管理驿递人员而专门设置的机构 “笼馆”,以及为管理驿递人员、军需供应而设置的武官官衔。③陈践践 《笼馆与笼官初探》,《藏学研究》第7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74-179页。陆离认为吐蕃模仿唐朝驿传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驿传体系。④陆离 《吐蕃驿传制度新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杨永红和潘娜娜依据新疆出土的吐蕃藏文简牍,对吐蕃军事情报人员so-pa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详细的解释了so-pa的6种分类,分析了so-pa的生活掌控以及对其的管理办法等,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的文章。⑤杨永红、潘娜娜 《吐蕃军队的索巴》,《西藏研究》2009年第2期。
(四)军事建制研究
吐蕃军事建制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吐蕃本土军事建制,还有一种是在占领区的军事建制。在吐蕃本土军事建制方面,比较多的研究集中于茹 (ru)、千户 (stpngsde)等领域。岩尾一史在关于茹制在中亚的运作这一方面有非常好的研究,他在 《吐蕃的茹与千户》⑥[日]岩尾一史 《吐蕃のルと千戸》,《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3号,2000年,第573-605页;沈琛、陈丽芳译 《吐蕃的茹与千户》,朱玉麒主编 《西域文史》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9-64页。一文中,对后世的藏文文献和新疆米兰等地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和木犊进行了梳理,找出了这些资料中可见的茹制,并且对茹制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朱悦梅对吐蕃在西域占领区的军事建制很有研究,发表了4篇与此有关的论文。分别对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体系及西域绿洲地理环境对吐蕃军事建制的影响;⑦朱悦梅 《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军事建制及其特征》,《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对于 “吐蕃中节度”从源流、辖域及与制度的关系;另外对于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源流、辖域,以及五道节度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新见解。⑧朱悦梅 《吐蕃中节度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朱悦梅 《吐蕃东境 (鄙)五道节度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林冠群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唐代吐蕃占领区的建制情况进行了详细研究,尤其讨论了吐蕃在占领区设置的5个德论康钦莫 (bde-blon-khams-chen-mo)。⑨林冠群 《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黄维忠探讨了 “朵思甘”与雅末塘节度使。并认为 “朵甘思”mdo-khams实际是五道中的 “中道”,雅莫塘节度使即河州节度使。①黄维忠 《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关于 (khrom)有很多专门的研究。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对 “khrom”一词进行了专门研究和比较贴切史实的解释。他认为,“khrom”是公元7-9世纪期间吐蕃政权在边境区设置的带有军事性质的行政单位。②[匈]乌瑞著,沈卫荣译 《释khrom:七一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1-138页;荣新江译 《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第106-113页。马德 《KHROM词义考》认为 “khrom”不是吐蕃本土机构,是吐蕃在占领地区仿照唐制而设置的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其功能应该与唐朝的节度衙、都督府相似。③马德 《KHROM词义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五)吐蕃的军事职官研究
吐蕃统治敦煌与西域期间的职官问题,这一课题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有不少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王尧、陈践、F·W托玛斯等中外藏学家对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的刊布与释读,推动了对西域敦煌社会历史进行全方位讨论的热潮。P.T.1089号文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吐蕃在军事占领区规定职官等级最为详细的历史资料,其所记载的官员多为军事职务。所以P.T.1089号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关于吐蕃在军事占领区职官问题研究的历史资料。最早由拉露女士全文翻译、解读了P.T.1089,发表在1955年的 《亚细亚学报》上。王尧、陈践是国内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先驱者,他们依据原卷胶片,对原文进行了拉丁文转写和全文翻译。④王尧、陈践 《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汶江结合各种文献资料,按其理解基本勾画出了吐蕃时期官制的轮廓,但其某些观点值得商榷。⑤汶江 《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号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汶江在其文末附有该写卷的汉文译文,但只有81行,与王尧、陈践在 《吐蕃职官考信录》中的录文及译文84行有显著差别。王尧等认为汶江翻译的81行应有漏误。张云对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制度体系作了讨论,通过分析整理出44种吐蕃在统治敦煌时期的职官名称。⑥张云 《新疆出土简犊所见吐蕃职官考略》,《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陆离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军事职官扎论 (dgra-blon)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可能源于吐蕃本部,是吐蕃特有的职官。⑦陆离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军事、畜牧业职官二题》,《敦煌研究》2016年第4期。对于 “节儿”有很多国内外学者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⑧法国藏学家戴密微在 《吐蕃僧诤记》中提到 “节儿”可能是 “使持节”或 “持节”的简称,或者此词即“节度使”之省称。法国藏学家拉露把 “节儿”译为 “县长”。匈牙利藏学家乌瑞认为 “节儿”译为 “镇长”更为确切。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先生认为 “襄结波 (nang-rje-po)”与 “节儿”有密切的关系,“节儿”也许是一个通称。托玛斯、藤枝晃认为节儿是属于吐蕃自身的一种职官,在吐蕃统治河西后,吐蕃人又将其推行到瓜沙等地区。王尧通过对多种文献资料的考察、对堪,认为 “节儿”是藏文rtse-rje的对音,其词源与吐蕃人习惯将官府设置在山头的有关系,同时也截取了汉文节度使之音。⑨王尧 《敦煌吐蕃官号 “节儿”考》,《民族语文》1989年第4期。张云对认为 “节儿”之意为 “总管”或 “上官”系统称。①张云 《“节儿”考略》,《民族研究》1992年第6期。金滢坤、盛会莲探讨了沙州节儿的设置以及其拥有沙州军政大权等职能。②金滢坤、盛会莲 《吐蕃沙州节儿及其统治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陆离认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时设置的乞利本 (khri-dpon)一职与节儿论 (rtse-rje-blon)是一致的,也可简称为 “节儿”。③陆离 《吐蕃敦煌乞利本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林冠群通过辨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文献资料,认为乞利本和节儿是两种不同的官职。④林冠群 《沙州的节儿与乞利本》,《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
综上所述,敦煌吐蕃文书军事问题研究相对于吐蕃其他方面研究来说显得较为薄弱,但是也算成果颇丰,研究包括了吐蕃军事的各个方面。目前来看,具有以下一些不足之处。其一,研究资料运用方面,国内早期关于吐蕃军事问题的研究大多数主要是借助于汉文资料分析研究,有效利用藏文研究资料方面比较欠缺。其二,早期对于军事制度的研究大多数从宏观方面出发,缺乏具体制度研究,而且研究深度参差不齐,研究水平高低不同。后期随着研究深入,研究方向转往具体的、细微问题,如开始关注茹、千户、节儿、khrom等问题;其三,在战略战术研究方面,缺乏研究资料,大多都是泛泛而谈,鲜有文章能够涉及实例,文章所用资料屈指可数。巴桑旺堆将 《敦煌古藏文兵律》发表之后,才有了新资料运用的可能,期待更多的学者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