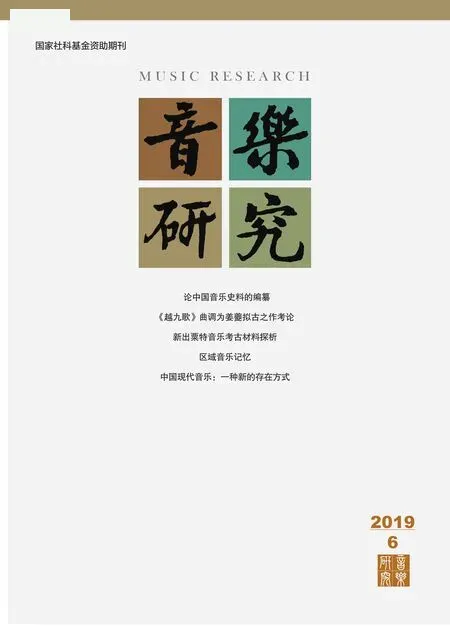论中国音乐史料的编纂
文◎王小盾、金 溪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处理资料。音乐史学的本质,则是处理主要以文本形式(兼及文物形式)呈现的关于音乐活动的史料。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人就进入了定居生活。至晚在甲骨文时代,书写成为记录历史的主要方式。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①公元前841 年,西周人推翻施行暴政的周厉王,推举周穆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政,称“共和”。从这一年起,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如君王在位,都以编年形式做了明确记载。)起,中国人逐年不断地记下了自己的历史,古代中国便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本文献。这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中国谈音乐史学,必定要谈史料编纂学。因为编纂音乐史料是进行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础。
编纂音乐史料的必要性,不仅同中国音乐史学的特性有关,而且同中国音乐文献的特性有关。同一般的典籍文献相比,中国古代音乐文献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它分为“乐”“音”“声”三部分,散落在古文献的不同部类,②参见王小盾《中国音乐学史上的“乐”“音”“声”三分》,《中国学术》2001 年第3 期;又载《隋唐音乐及其周边》,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年版。不集中。第二,它在文献整体中占比例小,比较隐蔽。第三,它通过各种记录方式保存下来,往往呈碎片化面貌,不易搜集与整理。第四,它过去只被少数人关心,难得刊印,比较完整的音乐古籍往往只有一两个版本;即使存在多个版本,也比较晚近,甚至出于同一个版本系统。由于早期的祖本往往佚失或残缺不全,所以很难进行版本对校。第五,古代只有“乐学”而没有“音乐学”。因此,经部以外的音乐文献很少得到校订与梳理,存有许多讹误和模糊之处。怎样来理解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这些特点呢?文献学研究者的理解是:整理音乐文献很难。而中国音乐研究者则认为:其实使用音乐文献更难。即使去寻找比较准确的古代音乐资料,也是一件难事。
很多音乐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音乐史料加以编纂和整理,从而推动音乐史学科的科学化和精密化。从已有成果来看,有四个方面比较突出:(1)整理出版音乐古籍。(2)分类汇编音乐史料。(3)对残存音乐古籍实施辑佚。(4)对藏于域外或采自民间的特殊文献加以搜集整理。这些工作值得表彰。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各类工作之间存在明显的性质差别,且尚未受到重视。因此,编不编音乐史料,诚然是一个问题;如何编纂中国音乐史料,同样是一个问题。为此,本文拟结合近年来音乐文献学的实践,对音乐史料的编纂方法问题加以讨论。其要点是:针对整理出版音乐古籍的工作,讨论如何运用文献学方法的问题;针对分类汇编音乐史料的工作,讨论体例类型及其演进关系的问题;针对辑编散佚乐书的工作,讨论如何复原乐书结构的问题;针对搜集整理特殊音乐文献的工作,讨论中国音乐史料学的新领域问题。
一、音乐古籍整理中的文献学方法
音乐古籍整理以“书”为对象,亦即针对独立成书的古代音乐文献。从方法角度看,主要有两种工作:第一是校注,即通过校勘来建立一个符合原貌的定本,通过注释来征引旁证资料以疏通文义;第二是汇编,也就是建立同类著作的集成。近年来,校注成果有王守伦等人的《律吕正声校注》,亓娟莉的《乐府杂录校注》。大型文献集成则有王耀华、方宝川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钱仁平主编的《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汇编》,刘崇德主编的《唐宋乐古谱集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组织编纂的《中国工尺谱集成》。这些成果意味着,音乐文献整理工作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显著的进展。
而若从印刷手段角度看,以上工作可分为影印、排印两类。前者用于大型音乐文献集成,后者则用于单部著作的校注。使用这两种手段,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关于如何校注专书,文献学家讨论较多。现在看来,容易被忽视的是音乐文献影印工作。
影印的主要优势在于简捷,可以迅速汇集材料并呈现古籍原貌,因此,较适合那些版本较少、藏地分散、不通行的音乐古籍珍本,以及符号形式的音乐文献。以上几种集成书,就注意了这两类音乐文献。比如《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所收录的《琴苑要录》,原藏于国家图书馆,为铁琴铜剑楼抄本,属珍本古籍。而《唐宋乐古谱集成》和《中国工尺谱集成》,则收录须以图像形式保存其原有面貌的乐谱文献。它们证明,对于音乐文献来说,影印是不可缺少的整理方式。
古籍影印有两项必要的技术:一是照相、扫描技术,二是文献学技术。近年来,照相、扫描技术有很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文献学技术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特别是以下三项技术。
(一)重视选择底本
底本意味着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平台,对于任何一种整理都很重要。而就影印古籍来说,底本选择则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因为底本好坏既可决定影印质量,也可影响影印的意义——我们知道,影印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播内容完备、文字准确、最具学术价值的版本。
比如《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其第一辑影印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乐志、律志,以及“十通”中的音乐部类,选目很好。但有一个问题:这些书的大部分都有现代人的校点本。因此,《集成》在选用版本时面临了三条路线:第一,为方便读者,尽量选用最佳版本,亦即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的点校排印本。第二,为了对点校本加以补充,尽量选用较稀见的早期刻本。第三,为便于操作,选用简便易得的版本,比如二十四史选用“百衲本”,《通典》等“九通”选用光绪浙江书局本。大家知道,《集成》一书走的是第三条路线,这是让人有点遗憾的。因为第三条路线是学术价值较低的路线。其实,即使第一条路线有体例方面的违碍,我们也应该参考各种点校本的版本说明,来实施第二条路线。比如《通典》,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版本,经长泽规矩也、尾崎康两位日本专家先后校订,已成为善本。相反,从武英殿本翻刻而来的浙江书局本,却是一个庸本。王文锦在校点本《通典》的前言中对此说得很清楚。他说:“明代以后的《通典》版本,多有误刻或擅改古本的地方,武英殿本所依据的明人王德溢、吴鹏校刻本于古本窜易尤多。”③(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7 页。由此可见,直接影印浙江书局本,而不加入今人依宋元善本而提出的校勘意见,便可能对学术产生误导。
(二)保留古籍的形式特征与版本信息
随着扫描技术的提高,近年来出现了两种处理古籍的方式:一是退底色反白,二是灰度影印。④参见南江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籍影印出版》,《中国出版史研究》2008 年第1 期,第89 页。有些古籍甚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式,将两种版本上下分栏并列排版,以便对照阅读。这种反白与灰度影印相搭配的情况,也出现在音乐古籍的影印工作中。比如《唐宋乐古谱集成》第一辑、第二辑,就基本上采用钞本、写本以灰度影印,刻本以反白影印的方式,较好地保存了原本纸面上的形式信息。
不过,在《唐宋乐古谱集成》第二辑《唐宋乐古谱类存》中,却留有一个瑕疵——所收录的两种《碣石调·幽兰》,均为反白影印。其中一本取自《古逸丛书》所收影旧钞卷子本《碣石调·幽兰》,属二次翻印,固然无法显示原本面貌;但另一本的原本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则应该考虑灰度影印。现在的做法,未实现本书“钞本写本以灰度影印”的体例要求。
(三)撰写提要,明确古籍的身份
撰写提要,可以把两种特殊信息——经编纂者目验的信息,从古籍内外提炼的信息——记录下来,是影印古籍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来说,完整的书籍提要,至少有书名、卷数、撰人、年代、内容要点和版本状况等六个要项。
音乐研究者在整理古籍的时候,向来比较注意撰写提要,例如《琴书集成》的每一册卷首,都有该册所收书目的《据本提要》。近年来,《唐宋乐古谱集成》和《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也都做得比较好。但如果要举出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永乐琴书集成》。此书于2016 年由西泠印社影印出版。书首有一篇《出版说明》,说此书“明成祖敕撰,为明内府写本,全书凡二十卷”,“收罗鸿博,语无不详”。又说因“查阜西先生编辑《琴书集成》时没有收录”,所以把台北藏本“影印面世”。这篇《出版说明》,其功能也就是提要。它是否合格呢?我们认为不合格。第一,它虽然说到了书名、卷数、内容、版本和收藏情况,但读者无法从中了解这部书的来历。比如,此书作者是谁?版本系统如何?这些基本信息是空缺的。第二,它的表述很含糊,关于原本馆藏地,只说了“原书现藏台北”六个字。不仅在原书影印本上看不到序言、跋语、牌记、印章,而且,读者即使想调查其版本流传情况,也无从着手。第三,它声称考虑到查阜西先生对《琴书集成》的整理,但査阜西先生所说以下一句话,它却未予回应。这话见于《琴书大全》提要,云:“《千顷堂书目》著录《永乐琴书集成》的子目与此书相同,但《永乐琴书集成》为写本,亦非永乐间的工料,疑是明季书商伪作。”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琴曲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1 页。《永乐琴书集成》是不是“明季书商伪作”?这个问题很尖锐,此书整理者有责任加以回答,至少应该提供必要的相关信息,但很可惜,《永乐琴书集成》的整理者没有这样做。
(四)进行必要的校勘
以上所说意味着,整理古书有一个基本要求,即首先要明确此书的文献学性质。《永乐琴书集成》的问题,就是因来历不明而性质不明。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此书和《琴书大全》作一对勘,考察这两部琴书之孰先孰后。我们做了这个对勘工作,发现两书在文字上大体相同,的确出自一源,但其差别却很微妙。首先一个情况是:根据上下文义,同时比较两书所引前代文献,可以判断,《永乐琴书集成》的书写往往比《琴书大全》正确。这意味着,《琴书大全》是摹刻《永乐琴书集成》而成的,在摹刻时因形近造成了错误。其次一个情况是:在《永乐琴书集成》第三卷突然出现了大量误字,误字之上有明显的加笔痕迹。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是有人在《永乐琴书集成》成书后,用加笔划的方式故意制造了错误。尽管我们不知故意刻划者是何人,其意图如何,但可以肯定,《永乐琴书集成》并不是晚明书商的伪造。也就是说,《永乐琴书集成》具有原创性,价值高于《琴书大全》。它早于《琴书大全》(略早于1521 年)而成书,应该产生在影印本所说的永乐年间(1402—1424)。
总之,影印音乐古籍,是一项赋有文献学意义的工作。既需要按版本学规则选择版本,尽力保存版本信息;又需要按目录学规则,撰写信息完整的提要;还需要采用校勘学方法,进行必要的考订工作,以明确古书的来历。只有做到这三条,所影印的音乐古籍才具有明确的学术身份,因而具有充分的史料价值。
二、音乐史料汇编的体例及其类型
“史料”和“文献”是两个略有异同的概念。“史料”指据以研究历史的资料,特别是编纂史书所用的资料,既包括书报和文件,也包括实物和口碑。“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文”指记录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传述相关掌故的人。⑥(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92 页。因此,“文献”指的是文化载体。但在现在,“文献”通常指记录知识的书面资料,特别是文字资料。两者相通的地方在于:文献可以用为史料,史料的主体是文献。但它们也有不同:“文献”概念强调知识的形式(是不是“文献”,看它是否具有文本形式),“史料”概念强调知识的内容(是不是“史料”,看它是否具有服务于史学的内容);“文献”概念是客观的,“史料”概念则包含由史学提出来的价值判断,有主 观性。
和以上两种概念相对应,音乐文献学中有专书整理与史料汇编的二分。专书整理可以说是“文献学”的工作,针对古书;史料汇编则应该说是“史学”工作的一部分,针对具有某种史学特征的文献——既包括古书,也包括文书、文物、口碑和古书中的片断。从研究方法角度看,音乐史料汇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文献整理。一般来说,两者都强调完备地占有资料,但音乐文献整理追求文本自身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音乐史料汇编则追求文本所记载的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后者服从于史学研究,要对文献内容加以选择,注重其应用性;因此,它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工作体例——确定选材范围、结构框架、书写方式。这是史料汇编工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目前,在文献史料汇编方面已有相当多的成果。从体例看,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选编类型。如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中国古代乐论选辑》(1962)、吉联抗的《孔子孟子荀子乐论》(1963)、《春秋战国音乐史料》(1980)、《秦汉音乐史料》(1980)、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2000),以及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历代乐论选》(2018)。这些作品采用一种比较常见的编排方式:以所引用的典籍为单元,按时间先后排序——也就是按照朝代与时间先后排列各种典籍,再按照卷次列出相关资料。这一类型的主要功能是依音乐史的顺序介绍资料,服务于教学。其学术含量主要取决于选材是否精当、注释是否准确。
第二种,类编类型。如2002 年初版、2014 年修订再版的《汉文佛经音乐史料类编》。这是一部典型的音乐史料汇编著作。它把近百万字音乐史料,分为音乐神话、佛国世界的音乐、音声中的哲学、早期佛教与俗乐、佛教音乐传入中土、中土佛教唱诵音乐、中土佛教歌舞杂戏和日本僧侣所记载的音乐等十四个部类,每一类下又各设小目,依照时间顺序排列资料。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分类,二是全面网罗相关资料,三是以《征引佛经目录》的方式考订书中全部资料的时间顺序。这些特点都表明了它的宗旨:服务于学术研究。因此,其学术含量不仅在于选材是否精当,典籍年代是否准确;而且在于分类是否恰当,是否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具有前沿意义的认识路线。
第三种,考编类型。例如《汉唐散佚乐书的整理与研究》的“辑佚编”部分。它有两个特点:一方面,遵循类编的编纂体例,将汉唐之间一千多年的散佚乐书,按其内容、性质,分为乐类、律类、琴类、歌辞类、录类和谱类等十类,每一类之下以朝代为序,同一朝代中又按作者生卒年或成书时间的先后排列资料。另一方面,它的目标是全面而准确地辑编佚书,因此,在“汇编”与“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考校”的内容。后者包括:(1)为每部佚书撰写解题,梳理其成书时代、撰人、内容、流传等信息。(2)尽力搜集同一条史料的不同版本,进行对勘。(3)对史料进行多角度考证,写为按语。(4)设置疑误辨析一类,列出在汇编史料过程中被剔除的条目,加以讨论。这一类型同样以服务于学术为宗旨。因此,其学术含量既体现在“编”的方面,也体现在“考”的方面——通过校勘和考证,一方面提供具有文本真实性的史料,另一方面揭露文本所反映的关于编纂者、编纂过程的关系,从而使散乱、零碎的史料方便地用于学术研究。
那么,有没有第四种类型的史料汇编呢?有的,不过它目前还存在于理想当中。2017 年10 月,在“中国音乐史学史专题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交了《中国古代的音乐史书写》一文⑦参见王小盾、金溪《中国古代的音乐史书写》,《音乐艺术》2018 年第3 期。。此文考察了汉代《史记·乐书》、南朝《古今乐录》、唐代《太乐令壁记》、五代《大周正乐》、宋代《玉海》和清代《律吕正义后编》等一系列音乐文献,同时考察了早期的乐录体文献。我们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史书写往往采用“两层一面”的体例。“两层”指的是两层结构:第一层纵向分类,第二层在“历代沿革”的名义下作时间维度的叙述。“一面”指的是一种表述法:陈述每一个事物,都按“长编”方式排列原始资料。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学著述有三大文体:一是纪传体,重分类;二是纲鉴体,重年代顺序;三是类书体,分类排列原始资料。“两层一面”实际上是这三种文体的结合,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书写实践的结晶。换句话说,中国古代音乐史书写经历了从断代史到通史、从分类史到综合史、从别录到总录这三条线索叠加的演进方式,才建立起了自己的形式传统。因此,它呈现了一个很紧凑的著述面貌:依照分类排列资料,在资料基础上进行考证与论述。这一体例既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史料汇编的体例,又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史著述的体例。显而易见,作为音乐史书写和音乐史料汇编两者的结合,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中国音乐史研究,值得引入未来的中国音乐史学。
总之,中国音乐史料汇编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基础工作,其价值取决于它的学术含量,其发展过程因而表现为学术含量逐渐增加的过程。实践表明,一个好的著述体例,是通过充分吸收各种史学方法(特别是文献考据之法)而形成的,这是编纂音乐史料汇编的关键。
三、音乐古籍辑佚中的结构复原
上文说到,中国古代音乐文献有“碎片化”的特征,其主要表现是早期音乐古籍往往散佚。早在南朝梁代,沈约就说过:其时汉代乐书已基本无存。⑧《隋书》卷13“音乐志”,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288 页。此后经历侯景之乱、隋末焚书以及安史之乱、黄巢之乱等种种书厄,官私文献同样很难保存。大量古书只留下了书名,或只有片断文献见于其他典籍的引用,引用时且往往被节略、删改。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音乐史学有一个重要责任:抢救那些已经散佚的音乐古籍,最大限度地恢复其原貌。
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从1990 年起,我们实施了一个名为“古乐书钩沉”的史料学项目。叶昶、张振涛、李玫、喻意志、朱旭强和余作胜等人先后参加了这一项目。到2016 年,它发展为金溪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唐散佚乐书整理与研究》,经多年努力,共辑出汉代至五代散佚乐书二百多种,其中有佚文留存的约一百种。我们从中得到一个认识:和史料汇编一样,音乐古籍辑佚也要有明确的体例作为指引。但它的体例意识有两重性,既要建立自己的工作体例,又要把握古籍原书的体例。如果说辑佚学的基本要求是对散佚古书进行复原,那么,我们首先要注意对原书体例加以复原。原书体例不易尽知,这时,就要按多闻阙疑的原则来求证。
从具体操作看,复原佚书的结构,有以下几条求证途径。
其一,借助后世典籍对原书卷次的记录来恢复卷次,借助后世典籍所采用的佚文排列方式来恢复排列顺序。前者如王应麟《玉海》,其中音乐部分保存了徐景安《历代乐仪》、刘贶《太乐令壁记》等数种乐书的卷目与卷内子目分类;后者如《初学记》等唐宋类书,各书所载《琴操》篇目,对每首琴曲标明了序号,且排序方式基本一致,可借以确定原书的排序。
其二,根据同时期的音乐文体分类观辨析原书的性质与结构。这一方法之所以可行,乃因为汉唐之间的乐学著作往往是官方记录,与仪式有关,因而有较严格的体裁观念——以不同体裁记录不同的音乐活动,并以书名表现书籍的性质。例如《乐社大义》《乐论》《乐义》均署为梁武帝所撰,书名且相似,但其性质却各有异同。根据《隋书·音乐志》所载沈约天监元年奏疏及相关记录,⑨同注⑧,第288 页。这三部书有共同的编纂背景,在梁武帝登基后不久编纂,目的是“定大梁之乐”,亦即为雅乐改制奠定理论基础。资料表明,《乐社大义》旨在为雅乐改革活动确立指导思想,并阐述相关理论和古代传统,由作为雅乐改革的组织者与最高领导者的梁武帝亲撰,即《隋书·音乐志》所谓“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所以《隋书·经籍志》将此书列于乐类之首。而《乐论》是对前代雅乐制度的讨论,带有驳论性质,通过批驳前人观点,来证明梁武帝雅乐理论的正确性与权威性。《乐义》一书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小字注文,为梁“武帝集朝臣撰”⑩《隋书》卷32“经籍志”,第926 页。,是朝臣对先代雅乐文献的汇编。从功能上说,这三种乐书代表了“自制定礼乐”的三个方面:(1)以《乐社大义》阐述改定礼乐的纲领。(2)以《乐义》汇编历史资料。(3)以《乐 论》辨析“旧事”,进而确立可采用的思想素材。这些分析,有助于判断佚文的归属。
其三,根据散佚乐书的体例和背景文献的体例辨认佚书之结构。比如我们收集到十条“乐书”佚文。为辨别其归属,考证了信都芳《乐书》、徐景安《乐书》(《历代乐仪》)和《太平御览》等文献,得出三个认识:第一,《魏书·术艺传》⑪原文云:“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又聚浑天、欹器、地动、铜鸟漏刻、候风诸巧事,并图画爲《器准》,并令芳算之。会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魏书》,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955 页。和《北史·信都芳传》记载说,信都芳曾饱览安丰王元延明的藏书,“得律管吹灰之术”。据知信氏《乐书》的编纂基础是元延明的藏书与信都芳的律学造诣。这在《乐书要录》的引文中可以得到印证。第二,《太平御览》的编纂体例是:卷首所列引书目录,与正文中的引书基本对应。据此判断,其引书目录中的《乐书》,对应的就是正文卷五六五《律吕》中的《乐书》“雅乐部器”条,以及卷五六六《历代乐》中的《乐书》“上古诸帝乐名”条。参考《玉海》等著作,我们判断这两条资料出自徐景安《乐书》。第三,徐景安《乐书》中有《八部乐器》一卷,是按八音顺序排列乐器的。综合这些认识,十条“乐书”佚文的归属与位置,是容易判断的。
其四,根据佚文内容判断其在原书中的位置。这是因为,处于不同位置的文献,在内容和书写方式上都会存在区别。比如在《古今乐录》的佚文中,有一些内容较宏观的文字,可以判断是“序文”的佚文。
以上所说,是进行音乐古籍辑佚的一项核心工作。围绕它有很多细致的事情可做。首先一件事是辨认引文正误。由于古人引书的方式比较随意,往往采用节引方式、转述方式,或根据主观意见改动文字,因此,要广罗资料来作比较,得出准确认识。这样做,有三种常用的方法:(1)注意内容是否符合书籍的年代。(2)看书名是否混淆。(3)考察引文是否有流传线索。比如《太平御览》卷五六五载牛弘对隋文帝问候气事,而署书名为《古今乐录》。鉴于《古今乐录》成书于陈代,早于隋文帝,故可取第一种方法,判断这是一条误引的文字。又如明清引文常常是从唐宋典籍中转引,而非直接引自早期音乐文献,因此要取第三种方法,留心前人未引而明清人新引的文字。其次是辨别辑本之误。由于乐书辑佚有很大难度,所以容易出现错误。从辑录《大周正乐》的经验看,容易犯五种错误⑫参见亓娟莉《〈大周正乐〉辑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6 期,第122 页。具体论证见另文。:(1)将不属于原书佚文的内容辑入,以至于文意不通;(2)忽略年代较早的文献,而袭用晚近文献中的错字;(3)不按可考的卷内结构罗列佚文; (4)漏辑;(5)误标句读。例如陈旸《乐书》卷一三六“编磬”条云:“大架所用二十四枚,应十二律倍声,唐李绅所传也。小架所用十四枚,通黄钟一均,上倍之,《大周正乐》所出也。”其中所记“大架”之事,乃出自唐李绅。所记“小架”之事,出自《大周正乐》。《〈大周正乐〉辑考》一文未细察,统辑为《大周正乐》之文。这就属于第一种错误。
乐书辑佚是常见的音乐史料工作,古已有之。近年来较具影响的成果是吉联抗的《古乐书佚文辑注》⑬吉联抗《古乐书佚文辑注》,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年版。。此书从中华书局点校本《乐府诗集》中抄辑乐书佚文,并用《四部丛刊》影汲古阁本对核,所辑文字概依《乐府诗集》排序。这种做法发人深思。积极地看,它反映了中国音乐史学的一项诉求,即中国学术的确需要音乐古籍辑佚之学。客观地看,它代表了中国音乐文献辑佚的早期规范,即采用选编的方式来辑佚,服务于教学而非学术。但从消极方面看,它并不符合中国文献学的传统,因为它不注意全面占有资料,也无复原古书的意识。借用孔子的说法,它不是“正色”的音乐史料学,而是“紫色”的音乐史料学。这提醒我们:中国音乐史学不仅需要辑佚之学,而且需要辑佚学的科学规范——需要建立竭泽而渔地搜集资料的自我要求,建立尽可能地复原原书架构的目标。这样做,有一个必要的步骤,即细致考察古代乐书的时代特征,考察其体例及其背景文献的体例。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音乐史料学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基础学科。近三十年来,它积累了很多经验。通过学术实践,相关研究者已经建立起对中国音乐史学之特性、中国音乐文献之特性的认识。文献史料的丰富性,决定了中国音乐编纂的重要地位。这种丰富性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音乐学的。而音乐文献强调伦理等级,因而从属于少数人的特性,也决定了中国音乐史料编纂的难度。尽管如此,中国音乐史料编纂学和整个中国音乐史料学,仍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其发展进步的主要方式是:一方面,越来越关注中国音乐学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越来越注意吸收中国史学的学术方法。这有三个突出表现:(1)在整理出版音乐古籍的工作中,充分运用文献学方法,即重视选择底本,注意底本的形式特征,按规范撰写提要,以必要的版本校勘作为整理音乐古籍的前提。(2)在汇编音乐史料的工作中,重视体例设计,因而出现了选编型、类编型、考编型等多种著述文体。(3)开始按规范的文献学方法辑编散佚乐书。这些进步,简单说来就是:资料领域扩大了,学术方法丰富了,学科结构也得到了改变。举个例子,以前编辑音乐史料,尽管也会注意设计体例,但由于以音乐史教学为目标,这种设计的标准较低,只注意编写方式的一贯性,以及音乐史教师的阅读预期。而现在的音乐史料编纂,却逐渐把文史各学科的学术预期作为对象了。这种中国音乐史料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般意义的中国文献学或中国史料学的重要分支。
中国音乐史料学,是在包括中国音乐史学在内的文史各学科的推动下进步的。由于这种推动,它还有一个重要动向,即开始关注一些特殊的音乐文献,比如藏于域外的汉文音乐文献、流传在民间的仪式文献和唱本文献。2012 年,接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我们启动了“域外汉文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重大项目。其主要内容是:以历史上的汉文化圈为范围,针对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等东亚国家,调查它们在历史上使用和保存的汉文文献,对其中的乐书、乐谱、乐图、日记、音乐仪轨、乐家文书等著作和相关史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到2018年,已实施以下工作:(1)以考订方式进行《高丽史乐志》研究,完成《高丽史乐志校释》《高丽史乐志研究》等专著。(2)以校点方式整理日本古乐书,编成七卷本《日本古乐书集成》。(3)以辑编方式、叙录方式整理日本各种音乐文献,编为《日本古记录中的音乐史料》和《大陆音乐在日本的流传:汉文史料叙录》。 (4)收集资料,着手编写《越南汉文音乐史料汇编》。除此之外,我们还与其他音乐史学研究者合作,开始进行民间仪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民间唱本的整理和研究。这些工作意味着,中国音乐史料学,其领域正在逐步扩大。而随着视野的扩大和学术规范的确立,中国音乐史料学也将建成自己的方法体系。老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以相信,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健康发展的中国音乐史料学,那么,未来的中国音乐史学便必定会有广阔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