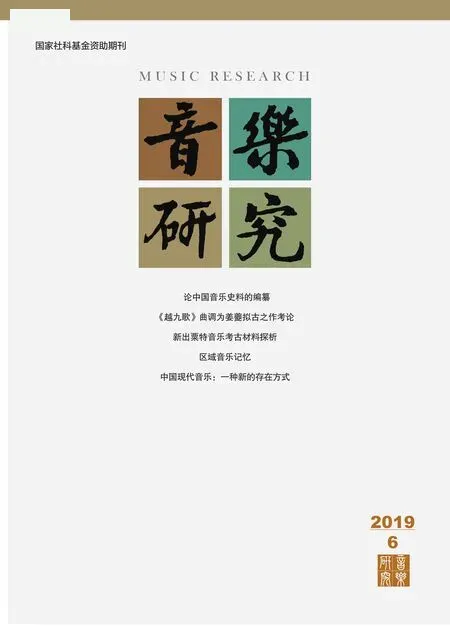区域音乐记忆—以冀中为例
文◎张振涛
一、记录书面和未记书面的记忆
音乐记忆是种神奇现象。演奏家站在台上,一口气演奏个把小时,双目若闭若睁,状态半醒半醉。一首奏鸣曲或协奏曲,几十分钟挤满上万个音符,节奏繁复,声部交错,诡数幻惑,处处玄机。然而,音乐家却能条理分明,连接有序,按照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把声音归置妥帖。这不禁使人惊叹: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把乐谱上数以万计的音符装进脑袋,不仅令外行匪夷所思,也令同行叹为观止。听到莫扎特等音乐家过耳不忘的故事,中国音乐家也会泛起相同联想,不识谱、不认字,一天学堂也没进过,更不像莫扎特一样穿戴体面的民间艺人,过耳不忘、过目成诵,数十出大戏的唱段、戏文、表演,完整呈现。这样的人,何止十个八个,漫山遍野都是。草根阶层,没有本本,没有谱子,却能演绎出连篇累牍的说书、戏曲、套曲的口头文本,只不过他们未像莫扎特那样被载入史册而已。
衡量记忆的标准是“长久的保鲜度和精确的复制力”。王世襄记述的昆曲笛师殷溎深背过全部《异同集》九百七十四出戏曲曲牌的事,①王世襄《〈异同集〉题记》,载《锦灰堆》(合编本)贰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版,第580 页。杨荫浏背过《天韵曲谱》九十多折昆曲曲牌的事,让我们知道,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大都具有这类本事。私塾教育的基本方式是死记硬背,戒尺手板,体罚厉骂,毫不容情。20 世纪50 年代,新疆维吾尔族杰出艺人吐尔迪阿洪(1881—1956)演唱十二套木卡姆的事,让人领教了什么叫“超强大脑”。这个记忆量可以用音乐学家万桐书、周吉等记录的一大册乐谱来衡量。1951 年,杨荫浏为天津单弦艺人程树堂(?—1951)录音,他端起三弦唱出一套23 分钟的单弦牌子套曲《霸王别姬》,时长与一首贝多芬奏鸣曲相当。数十套牌子曲也可用杨荫浏、曹安和、文彦记录的《单弦牌子曲集》来衡量。1994 年,中国音乐研究所邀请陕北榆林歌手王向荣到北京录音,从上午9 点录到下午4 点,共唱了44 首民歌。1990 年,邀请西北“花儿王”朱仲禄(1922—2007)到北京录音,从上午唱到下午,张君仁的博士论文《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记录了他唱的159 首花儿。分节歌是多段歌词,《四季歌》四段、《五更调》五段、《十绣》十段、《十二月》十二段;《珍珠倒卷帘》从一月唱到十二月,再从十二月唱到一月,共二十四段,这些口头文本没有哪位艺人是拿着本本唱的。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皮影戏班是中国音乐学院黄虎的研究对象。戏班一晚上演出近四小时,如果把戏文全部记下来,足足两万多字。戏班一般要在庙会演十来场,戏文全部记下来,约十几万字,印出来就是一本书!影戏人物,四五十个,各有各的影子,各有各的唱腔。班主操作自如,如同厨妇摆弄锅碗瓢勺。皮影一亮相,唱家一开腔,提起线头,接通储存,连接有序,无不清荡。“整体记忆”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老百姓形容:“一个影子艺人在影幕背后,长十个脑袋都不够用!”他们就是“长十个脑袋”的人。
京韵大鼓艺人骆玉笙的《丑末寅初》 《马嵬坡》《子期听琴》《击鼓骂曹》,西河大鼓艺人马增芬的《玲珑塔》,都是曲艺名篇。“小彩舞”(骆玉笙)在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第一句,唱得虎虎有生气,一口气铺排出的历史画卷,气势恢宏,风靡全国。暂时抛开艺术表现不谈,单看记忆力,最简单的办法是统计字数(因现场变化,略去个位数)。《丑末寅初》580 字、《马嵬坡》890 字、《子期听琴》2050 字、《和氏璧》1020 字、《击鼓骂曹》1520 字、马增芬《玲珑塔》1630 字。上述统计,仅是唱词,十倍于此的音符,难以用小节数量化。每次堂会,要一口气唱下来,一个晚上,总量惊人。白居易《长恨歌》960 字,背《长恨歌》的人,会被人视为“有文化”,而背唱京韵大鼓《马嵬坡》的人,不一定被人视为“有文化”。但从记忆量上看,后者毫不逊色。艺人记忆,深不可测。
有幸被记录的名篇,字数可计,而田头巷尾的薅草锣鼓、书场园子的弹词演述、陕北说书的连本长篇,大多未经统计,若整理印刷,都是一大本!殷溎深抄的五十册《异同集》,吴畹卿、杨荫浏抄录的《天韵社曲谱》;冀中音乐会抄写的“十三套大曲”、晋北鼓吹“八大套”、江南丝竹“八大名曲”,每套时长都在数十分钟以上。古时亦然,宫廷教坊、梨园弟子,“男记大曲四十,女记小令三千”,都不是小数。
20 世纪编辑的“十大集成”更是铁证。参加记谱的音乐家知道,哪首民歌是看着谱唱的?哪首乐曲是看着谱奏的?哪部戏是看着剧本演出的?哪个民间故事是看着本本念的?全部背诵!
老百姓的评价不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是“唱了一箩筐”“唱了一篷船”“肩挑背篓尽是歌”。如同电影《刘三姐》的“斗歌”桥段,酸秀才翻箱倒柜,接不上茬,民歌手张口即来,宛如天籁。这类故事,绝非虚构。我们在陕北庙会上听说书艺人唱《隋唐演义》,每晚数小时,连唱七天。“故事篓子”一筐一筐装不完!
被誉为“文化长城”的“音乐集成”,民歌、器乐、戏曲、曲艺,数以万计,没有一首是看着谱来的。艺人千千万万,每人都是记忆宝藏。印尼伽美兰、印度拉格、阿拉伯木卡姆、非洲木琴乐队、拉丁美洲音乐,哪个看谱?知道这些,才能理解印度古谚:“一个印度诗人的死亡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十大集成”摆在面前,是真正的图书馆,让人称得出此话分量。
二、记忆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社会分工论》一书提出“集体意识”概念,即社会成员相对一致的信仰与行为,因共同意识决定的理论。他的弟子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于1925 年 引 申出“集体记忆”概念,即人的记忆是在家庭、团体和社会影响下形成的。他指出,个体记忆必须使用人类共同的沟通工具——语言、概念及逻辑,理所当然受其制约。记忆是在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和民族认同中形成的。个体参与的“集体欢腾”仪式,令“集体记忆”存活于日常。“往事”是由社会集团建构、施加于个人的。他在《记忆的社会基础》阐述了“集体记忆”框架。《论集体记忆》则分析了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差别。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 《社会如何记忆》把记忆分为社会记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三个层面。参与礼仪、演奏乐器并舞蹈,形成身体记忆,这其中,乐舞是重要载体。他强调“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的操演而形塑,提出结构性遗忘,即记忆和遗忘是一体两面的观点。他探讨了“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论证“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大卫·格罗斯按照历史进程把记忆“社会图式”分为三种:宗教图式、政治图式、大众媒介,赋予记忆以纵向性。②参见杨凤岗《多元时代的宗教和世俗主义》:“法国宗教社会学家赫尔维尤·里格(Daniele Hervieu Leger)说宗教是记忆之链,宗教的礼拜仪式、读经祷告、拜山朝圣,目的都在于接续记忆。”《读书》2017 年第9 期,第54 页。
上述理论让我们了解到,所谓“记忆”,并不是个体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被精英阶层筛选出来并通过仪式固定下来,再通过教育和艺术方式由身体实践沉积于个体脑海中的。记忆绝非凭空而来,更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社会总体精神的产物。社会、团体、族群和家庭,通过不同介质(如书本媒体、宗教仪式、艺术实践等)植入个体。依靠这些介质,人们记住了大致相同的内容,并以此维系相互之间的关系。没有共同记忆的人,不会共处。赵世瑜说:
一方面正如哈尔布瓦赫所说,记忆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记忆的框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集体记忆影响、甚至取代个体记忆的过程——当然,或许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影响、取代的过程中个体记忆的残留物。③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外二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由此而论,一个地区的民间艺人掌握的曲目,绝不是他喜欢什么就记住什么那么简单了,而是在社团中通过习艺过程和实践空间——仪式行为,建构于他脑海中的。他必须记住这些内容,也只能记住这些内容。不相干的东西,不是被压缩到最小范围,就是被强制舍弃。所以,透视个体记忆,就是透视集体记忆,上可识集体,下可探个体。音乐学应该通过衔接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纽带,解读地方性知识。
三、四种记忆模式
近些年来的记忆理论突飞猛进,人文学科对记忆的研究不同于医学界的神经学或脑科学,而将其看作与文化、历史紧密相连的领域,以集体记忆以及为巩固集体记忆或“集体主体同一性”为目的的行为。本文借用记忆理论的“集体记忆”“个体记忆”分层,把冀中的情况归为四类:“官方记忆”“传统记忆”“社团记忆”和“个人记忆”。下面缘此分层,分而述之。
(一)官方记忆
记忆理论的核心是“集体记忆”,但细加分析就会知道,人们所处的环境不但有国家大背景,也有地方小背景。因此,所谓“集体记忆”也就不仅有大背景的“集体记忆”,还有小背景的“集体记忆”。若把前者称为“官方记忆”,则可把后者称为“传统记忆”,因为乡村文化往往保持了与大背景相对应的小背景。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与“官方记忆”不同的“传统记忆”,虽然两者都可称“集体记忆”。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乡民背后有两个强大的“集体”,两个“集体”灌输的内容,往往不同。官方记忆与传统记忆有时相同,有时相悖。这就是为何要把“集体记忆”分为“官方记忆”与“传统记忆”的原因。
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音乐会的部分会员,“文革”期间曾参加本村“剧团”,演出“样板戏”。这个经历使他们混杂了两种“集体记忆”:一是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现代唱腔(评戏移植京剧);二是传统的笙管套曲。他们的储蓄曲目大致如此:一种是传统的“集体记忆”,另一种是现代的“集体记忆”;前者是“传统记忆”,后者是“官方记忆”;前者是历史内容,后者是现代内容。两个“集体”规定了性质不同的两类音乐,因时因地,分而用之。两种音乐,也因不同场合而发挥着不同功用。
分析曲库,不能不使人看到“文革”影响。会员开口便能唱出广播喇叭天天灌输的唱腔,既非主动,也非被动,耳濡目染,刻骨铭心。这是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唯一认可的音乐,高密度和排他性,使每个人牢记不忘。半政治半娱乐仪式,把身体记忆转化为潜意识,在不自知状态下,获得了牢记效果。几十年过去,即使平日谁也不提,但只要凑到一起,你提一句,我跟一句,依然能把当年“磨出茧来”的唱腔“拽”回来。这属于典型的“官方记忆”。④历史上也存在过官方不断强调某些曲目的情况。“上初即位,不忍观《破阵乐》,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韦万石奏:‘久寝不作,惧成废缺。请自今大宴会复奏之。’上从之。”(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十四册),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6385 页。不搬演就遗忘,遗忘涉及统治集团历史记忆。一套大曲从一个典礼到另一个典礼,重复率从每年数次到因帝王故去而戛然而止,不需多久,就会淡忘,好比媒体时代一首歌曲的流行取决于聆听次数一样。宫廷不允许遗忘祖上传统,采用典礼方式巩固记忆。“由于记忆对集体主体同一性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存储和传播必然受到严格控制,对控制权的掌握一方面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权力。”
(二)传统记忆
南高洛音乐会会员最常参与的仪式是丧葬。葬礼每年平均十多次,这个密度有效巩固了会员们的“传统记忆”。乐师都会演奏大曲《普庵咒》,这高度的统一性,便来自一年中发生频率最高的葬礼。参与仪式是巩固记忆的最有效手段。乡村乐师只有在参与葬礼时才拿起乐器,而非城里人兴之所至而操弄乐器;乡村乐师在一个社团中需一起演奏乐器,也非城里人可“单打独斗”,不需从众。因此,城里人具有行为的个性化,因而在记忆内容上也具有个性化;笙管乐是合奏,没有集体记忆,无法实现,团队对个体的塑造,有决定性作用。
冀中大曲十几套,一般一个会社只能够演奏一两套,个别能演奏三套以上。大部分乐师常年应用的只有一套《普庵咒》(包括《孔子泣颜回》等),因为此套大曲的曲名与葬礼相关。《普庵咒》之所以声遍四野,多数人能够演奏,是因为丧礼是延续“集体主体同一性”的底盘。虽然老人鼓励弟子多背曲牌,但没有协作,再多曲目也因找不到合作者和实践机会,最终淡忘。可见,集体行动与合奏形式对记忆曲目是何等重要。
比之具有超强记忆的个别精英,我们更渴望了解大多数乐师的记忆为什么趋同。他们为什么只记住了《普庵咒》而不是其他?为什么多数人选择了仪式纳入“记忆”的内容,而非处于个人爱好的曲目?因为老百姓把孝道视为隆家之道,倍加 看护。
戏曲、说唱、秧歌和庙会、丧葬,是乡村仪式的主要载体。在乡村,看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看他认不认字,而看他有没有参与包罗万象(评戏、秧歌剧、舞狮、小车、幡会、武术等)的仪式。许多认字不多却能记住大量历史典故和戏曲故事的人,说道理的高度令人惊奇,对他们而言,看戏和参与仪式,比阅读重要。过去的冀中村民多不认字,受教育的方式就是看评戏、看秧歌剧、听说书和参与仪式。所以,20 世纪初,李景汉等社会学家在定县专门考察秧歌小戏时,希望以此作启蒙工具。这些活动的影响远远大于书本,它们是生动的社会课堂,村民们所熟知的传说典故、历史人物和道德观念,主要来自秧歌、评戏和佛道教仪式。许多名人的幼年教养,大多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这些人在乡村仪式上记住了大量戏曲故事和伦理典范,为孩子提供了健康的“养料”。
大部分人通过集体行为复制记忆,仪式减少,记忆便日趋淡化。乐师说,从“四清”到“文革”,政策收紧,曲目淡出,遗忘逼来。这不是个人记忆出了问题,而是体制性休克,即保罗·康纳顿所说的“结构性遗忘”。
“文革”时期,官方“集体”抑制社区“集体”,但小环境也有耐久力,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延续了“传统记忆”,甚至因为官方的不提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小环境刻意去强调“传统记忆”。“传统记忆”与百姓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即使不被官方提倡,也会因生存需求和历史遗风而坚持不懈。
北师大社会学系曾有个讲座题目叫《土地的记忆比人的记忆更久远》。“传统记忆”就是“土地记忆”。把一切归于“集体记忆”大范畴,可能使复杂问题平板化。所以,应该分清“官方记忆”与“传统记忆”,前者不能成为“集体记忆”的全部。
(三)社团记忆
屈家营音乐会的林中树,具有超强记忆,给大多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1986 年3 月28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初次采访的日子当作“明白日”,进而确定为该村“节日”。一个农民之所以能够把30 年间遇到的人名、单位名、报刊名和历历往事脱口而出,就在于一年一度、重复上演的“发明的节日”——哈布瓦赫所说有效巩固记忆的“集体欢腾”仪式。如果不是年年岁岁见到常来常往的同一批人,如果不是年年岁岁听到相同的价值认定,如果不是与学者、记者交往从而明白文化的价值,他怎会把与生计不相干的文化纳入自己的生命史?所以,与其说他的记忆非同一般,不如说持续近30 余年的“集体欢腾”仪式构成了鲜活的“情景记忆”。巴尔扎克描写过这种全息性“超强大脑”:
他的心,用一种能与他眼睛的敏捷相配合的速度,立刻把书里的意义抓住……他不但记得第一次曾涉猎过的书本上那些意念安排的情形,就连在很久以前,他自己心灵各个阶段上的状态,他都能记得。那就是说,他的记忆力在回想方面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用以回想他的心灵所曾通过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并且还能回想到曾经贡献给他的心灵以完整意念的那整个的活动……他的脑子,自早年就习惯于这种能够把人类力量集中的复杂机能,现在便从那个富庶的贮藏所里吸收了一大堆丰富的影像——它们是非常的明晰而新鲜——来构成他心灵正在活泼地深思的一种滋养品。⑤〔法〕司蒂芬·支魏格著,吴小如、高名凯译《巴尔扎克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19—20 页。
一年一度的相见,情景历历在目,记忆也在一次次的聚会中不断巩固。林中树不但记住了事件的细节,而且记住了场景(更因乔建中和黄虎的记录而呈现书面)。他的记忆不会出错,甚至经岁月打磨而更加清晰。试问屈家营下代人还会有如此记忆吗?林中树把生命中“不可能”出现的人物与事件刻骨铭心,盖因“无事件境”的乡村发生率非但不是百分之一,而是岁岁年年、周而复始的“集体欢腾”仪式。这个机遇,他赶上了,念念不忘。把生命史与乐社史联系起来,使“主事人”产生了难得一见的超强记忆——这样说当然不否定他个人的特殊禀赋。
这正是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采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理论框架,把记忆理论应用于事件(《战争框架》),从而提出事件构建记忆的范例。也如同中国学者王晓葵在《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一文追溯“唐山大地震”30 年间的封存、唤起和重构过程,用以探讨“灾害记忆”的情况一样。林中树的记忆来自社团,而非个人。“不同的结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时,往往会形成一种叠加和放大的效果。”⑥晋军《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读书》2016 年第8 期,第81 页。社团的重大事件,无疑是个人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
(四)个体记忆
儿童教育研究成果认为,一般人不记得童年的事,脑科学称为“童年失忆”。记忆起点始于三四岁,只有少数人记得此前发生的事。这样的刺激,来自家庭。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注重幼儿阶段。《颜氏家训》说: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己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⑦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173 页。
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⑧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127—128 页。
大量背诵和耳提面命,是巩固记忆的不二法门。唯有如此,记忆才能融入骨血。长辈的督促,使雄县韩庄音乐会会头谢永祥积累了大量曲目,因而获得了全社尊重。能演奏长时量曲目,是一家乐社享誉一方的标志。与饭碗相连的吹打班、戏班,曲目积累的多寡更是性命攸关。
1.谢永祥的故事
个体记忆与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记住多套大曲的人,大多是因为家庭传承。谢永祥就是突出个案,韩庄音乐会被誉为“谢半会”,盖因这个家族的传承。谢永祥回忆,开始学时,一伙人一冬只能学两三首曲牌,进展缓慢,第二冬就快多了,他成为这伙人的杰出代表,不仅因为他技艺精湛,还因为他背诵曲目最多。我们关心的就是“上伴”(当地方言意为“同伙”)的一群年轻人为什么只有谢永祥记住了多套大曲而其他人做不到。毫无疑问,他之所以能记住多套大曲,皆因父辈的天天念叨,世泽熏陶。
霍布斯鲍姆认为:“大多数的口述历史是个人的回忆,个人是一个不可靠的保存记忆的媒介。”⑨〔英〕霍布斯鲍姆著,刘北成译《下层历史》,载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 页。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不可靠只是一方面,如果把一个人放入家族环境,会看到个人记忆并非孤立现象,是以家族记忆为背景的,这样的个人记忆,值得信赖。
时间长了,谢永祥以及家族成员,发现了一股巨大使命感降临身上,这使命感当然不是冲着音乐会去的,而是冲着整个乡村文化去的。毫无疑问,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说,这个家族之所以千方百计成为乐社“骨头”(当地方言“脊梁”之意),乃是因为各种各样来自社区各个方面的激励话语刺激所致,那已然构成了一种不能推卸的责任。具有峰回路转意味的是,他遇到了前来采访的音乐学家,记录下了他们的功绩。
2.“过脑子的字”
另一个突出事例是韩庄乐师徐继新。他虽没有谢永祥的家族背景,却靠非同寻常的毅力,成为能韵唱大曲最多的人。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饶曦多次采访过他,记录了这则故事。
徐继新因常年在一家红木厂打工,出村干活,骑自行车,乡村土道,枯燥无寄,热爱音乐的徐继新,竟然充分利用一来一往的时间,默诵大曲。这段路途,刚好背默两套大曲。他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一路行一路背,持续了整整40 年!他把三套大曲,一天背两遍,一年下来,等于念了七百遍。40 年下来,等于念了约两万八千遍。如果把三套大曲均分为三,每套大曲,都念了约九千三百遍。
强烈的爱好和非凡的毅力,使他不但温故,而且知新,根据韵谱规律,他开始探索从未学过的大曲。冀中大曲的难点在于,谱面上没有的“字”,要靠师傅口传心授,补足实践中实际存在的“字”。为恢复大曲,我们千寻万觅,找不到能够把未学大曲,依靠“阿口”规律,补足所有“字”的人。常年在肚子里默默背诵大曲的徐继新,参透底蕴,渐入佳境,竟然挑战了这项无人敢碰的技术难关,做出了前人未敢也未能做出的壮举。改革开放四十余载,时逢太平,海内晏然。他反复琢磨,硬是把另外七八套大曲,全部顺了下来,成为唯一能把十几套大曲韵唱下来的人。徐继新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像白娘子非要盗仙草,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他未曾料到,饶曦的博士论文,以数十页记谱,还原了他默念的曲调。眼看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口中的大曲变成了活生生的乐谱,他不无骄傲地总结:“四十年前我住的是这个村,四十年后我住的还是这个村。可四十年间,我唱下了七八套大曲。虽不值一提,但师傅们九泉有知,一定觉得值。”
秦始皇时代的文人伏生,专攻《尚书》。秦亡后,他藏书壁中,依然不放心,干脆背下来。战乱过后,壁中书果然不存。伏生于90 岁高龄等到了收集典籍的汉朝官员。他口齿不清,由女儿翻译,《尚书》因此留传。如果没有他的记忆,文脉便断了。
徐继新做的,就是这种功在千秋的事。一趟趟外出又一趟趟返回的路,他因“过脑子的字”被载入音乐史册。这则案例充分说明了记忆中个性因素的复杂性,展示了一位有心人巩固记忆所采取的长年累月默诵的奇效!不能不说,十几套大曲的庞大记忆量,体现了徐继新的顽强个性。
当然,一流的“好脑子”毕竟是少数。我们在冀中发现过数位像莫扎特一样的“好脑子”。雄县张岗乡韩庄的谢永祥、徐继新,霸州市信安镇张庄的李都岐,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的蔡安,静海县子牙乡小黄庄的李宝砚,固安县礼让乡屈家营的冯月波,掰着指头,数得过来,凤毛麟角,万里挑一。这类奇才与散布的大多数艺人相比,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如果不是持续十年的“文革”和延续十年的“断层”(近20 年),还真难有机会把差不多跨越了大半生的“断层”作为一个量度,测验“超强大脑”的过硬程度。“鸿沟”让人看到相隔20 年依然记得初习曲谱者的天赋。正如人脑复制功能并非都善于精确复制一样,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具天赋,把大部分人忘记的知识延续到另一个时期。
20 世纪80 年代,大部分乐社面临着相同困境,有心复社,无力回天。没有录音机,难以把师傅传授的乐曲恢复如初,成为心病。努力恢复的行动,构成一件值得记录的抵抗“结构性失忆”事件。由此推知,历史上延续数十年的战乱给文化带来的灾难该是何等剧烈!持续上百年的“三国演义”“五胡乱华”“南北分立”“军阀混战”,需要放大多少倍才合适?“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多少美丽曲调,在一次次考验记忆、挑战记忆的动乱中遗失?冀中没有哪家乐社能够演奏十三套大曲!岁月偷走了并不牢靠的记忆。这就是我们对记忆这种奇特现象产生兴趣的原因。
(五)情景记忆、身体记忆、指法记忆
相对于“集体记忆”“个体记忆”,还有一组概念值得探讨——“情景记忆”“身体记忆”。这组概念主要用来归纳记忆的方式,而这一点对不靠书本记忆的艺术家来说更适用。许多戏曲演员不识谱,主要靠“情景记忆”“身体记忆”。他们不会把台词、唱腔、动作分开,哪句唱腔对应于哪个动作,哪个动作对应于哪个情景,哪个情景对应于哪句唱腔,整体记忆,相互依赖。身体记忆的好处是,动感性、具体性,不枯燥。艺术家体会最深的是身体记忆、音声记忆,这不但与艺术相关,还与个体经历相关。
山东省吕剧团的代表剧目是《李二嫂改嫁》,主角郎咸芬(二嫂)与杨瑞卿(六弟),通过演戏,结为夫妻。他们的记忆是以现实版的爱情为“底本”的。这类事例在戏班中具有普遍性。二人台、二人转演员,假戏真做,终成夫妻(内容若非夫妻也不方便),不在少数。台上记忆,台下生活,不分彼此;戏中夫妻,实际夫妻,不分彼此;从艺经历,个人经历,不分彼此。有什么能比真假莫辨、难分彼此更刻骨铭心?
对于不认字的演员来说,看本本是多余的事。“当地著名的秧歌艺人一般都有惊人的记忆力,宋文川对我们说,还是心记口授学的扎实,他问:‘本来心里能记下的戏,再认一遍字不是多费一遍事吗?’”⑩董晓萍、〔美〕殴达伟(R.David Arkush)著《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 页。
法国学者提出“身体记忆”的概念,萧梅引申为“指法记忆”,十分形象。这类概念非常适合于音乐家。音乐家喜欢“指法记忆”,没人愿意背谱子,与音响连在一起的指法,高度保鲜。音乐家在朱熹总结的“心到、眼到、口到”记忆方法之上,再加一个“手到”概念,强调身体作为记忆载体的重要性。音乐家是充分利用身体和指法记忆的群体。
五、正确认识私塾教育与活态传承
自然传承指有强烈爱好和浓厚兴趣的人,没有正式拜师,采取默习方式,听、看、背、唱,私下模仿,自学成材。蒲亨强称为“剽学”。⑪蒲亨强《“剽学”——值得注意的民间音乐传承方式》,《中国音乐》2002 年第3 期,第23—24 页。偷学、剽学是方法。民间流传的“杨露禅陈沟偷拳”故事,说的也是这事儿。学习动力源自兴趣,源自生存压力。师傅草台呈艺,口若悬河,徒弟若无过目不忘的本事,学不到真经。
北京四城吹鼓手的曲子张广山都会,四城最棒的吹鼓手都是他的朋友,过去的吹鼓手不像现在,师傅手把手地教曲牌,那样彼此之间就成不了朋友。只有吹一遍就能记下来、重复出来的才能是朋友。过去没文化,完全凭脑子,凭自己的聪慧。⑫姚慧《京西民间佛事音乐及其保护研究——以张广泉乐社为个案》,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
洛德将口头文化中荷马史诗歌手的学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个学歌的人通常要选择一位歌手,紧紧跟随着他听歌……学歌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模仿的过程,这包括学习乐器的弹奏和学习传统的程式和主题……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大量实践(练习)、模仿和融会贯通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歌手开始完整地学唱另外一些歌……直到他能够独自创作或再创作史诗歌为止……一个成熟歌手的标志是他在传统之中游刃有余。⑬〔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30—35 页。
戏班口头记忆与学院书本记忆,到底哪个合规律?戏班子与鼓乐班是民间的、土气的、没理论的,但训练有效。学堂教育与民间传承,孰优孰劣,不易回答。培养人才,民间沿袭着一套老方法,耳提面命、口授心传,从未被怀疑过。“正规教育”把没有课本、不读书写字,视为“业余”。学堂教育出来的是学士、硕士、博士,民间教育的是鼓匠、吹手、戏子。其实这种评价忽略了记忆规律。原本学术界说不出合理性在哪儿,“非遗”理论提炼的“活态传承”,为我们找到了理据。活态传承是文字难以表述的艺术教育中最重要、最“靠谱”的方式。音乐是种身体参与度极高的艺术,吹拉弹打,浑身上下,一齐参与,记忆载体就是身体,就是指法。新型教学法体现了先进理念,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让活态传承获得重新解读。当前院校,一反其旧,注重身体参与,与民间教育殊途同归。
结论:记住传统
历史上许多名人,因超强记忆而千古留名。“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博闻强记,过目不忘,有一次,别人不慎将棋盘搞乱,他只扫过一眼,便凭记忆恢复如初。魏明帝曹睿,“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薄性行,名迹所履,及其兄父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⑭(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五册),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2345 页。三国时蜀国尚书令费祎,“认悟过人,每省读文书,举目暂视,已究其旨意,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⑮同注⑭,第2360 页。南北朝时王琳,“体貌闲雅,喜怒不形于色;强记内敏,军府佐吏千数,皆能识其姓名。”⑯(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十二册),第5328 页。唐玄宗时名将张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张)巡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⑰(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十五册),第7039 页。
陆正伟《晚年巴金》道,他读康熙年间诗人顾贞观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写下的《金缕曲》时,“病床上巴老也跟着背诵起来”,“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诗词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下来”。⑱余秋雨《巴金百年》,载《门孔》,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60—61 页。那代文学大匠,四书五经,皆能背诵,大段散文,倒背如流,功夫便是成就基座。
历史名人,“聪敏强记”,“纤毫不差”,“心算口占,应时条理”。江苏电视台节目“超强大脑”,展示过这类人,几十年前某一天发生的事,一一道来,若非直播,直不敢信。这些超强大脑的故事,往往让人觉得记忆是极其特殊的个体的事,其实大部分人的记忆是在集体中确立的。根据上叙,归纳如下:
第一,冀中乐社对选择哪首大曲,取决于丧礼取向。《普庵咒》对于其他地区的乐班、乐师没有意义,不会列入记忆。所以,该地的集体记忆与“地方性知识”或“地方性仪式”相关。
第二,乐师习乐是集体行为,搭伴同行。笙管乐是合奏,是集体性行为,记忆也是集体性的,这与现代人学音乐根据自己喜好、自由选择曲目的方式完全不同。
第三,传统记忆呈衰减趋势,以仪式衰减为前提。
记忆研究在音乐学界尚未获得重视。本文以此寻找民间艺人之所以相互间保持内在联系的原因,以期解读区域文化相通性的内在联系。记忆并非是一种抓不住的“虚无”,我们把难于把握的“虚无”转化为可以把握的曲目,以现象为对象,以果寻因。所以,仪式就是一种可以凭靠的介质,民间艺人的记忆也由此可以获得“看读”理据。
民间精英干了什么功德无量的事需要后人记住?有人活了六十年,有人活了三四十年,但做了一件相同的事——记住曲目,使流传了几代人的大曲不至消失。学术界称之为“捍卫记忆”⑲〔苏联〕利季亚著,蓝英年译《捍卫记忆》,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 年版。的琐事,多少年后才让人看出不凡之处。战乱与动乱频仍的日子,艺人把最容易丢失的音乐,储存脑海,做出拯救区域文化的壮举。今天,有什么比保留曲目更简单?录音录像,记谱印刷。但20 世纪90 年代之前,全凭脑子。因此应该记住那些把难以记住的音乐印在脑海里的人。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一书扉页上写道:“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这大概是研究记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