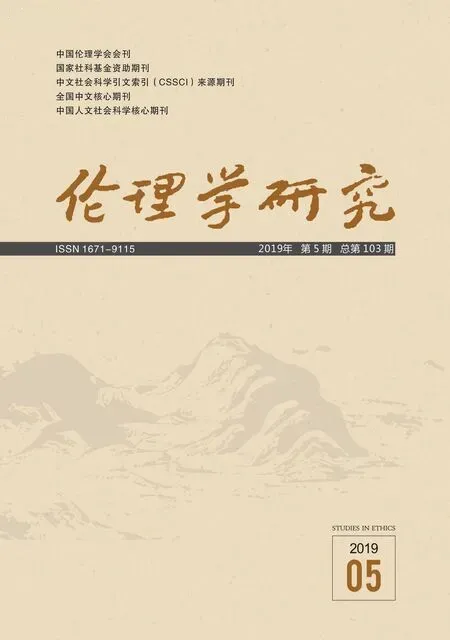戴震“仁”学考论
魏冰娥
“圣人之道,唯在仁恕”[1],仁是儒家为学的本旨要义。蒙培元先生曾总结儒家之“仁”到:“仁既有情感内容,又有理性形式,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在天为‘道’,在人为‘仁’,天道之‘授’于人者为命,但其核心是一个‘生’字。”[2](P57-58)也就是说,抛开仁的诸种诠释①,仁内在地包涵着三个维度:生、情(欲)、理。仁之“生”,自《易》“天地之大德曰生”[3](P530)始,孔子即以“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4](P493)含蓄表达仁得于天之生,程朱也以“天地以生物为心”[5](P366)“仁者,心之德,爱之理”[6](P187)明确仁属“生”物之德。仁之欲,孔孟以“我欲仁,斯仁至矣”[4](P196),“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4](P316、337)以及“可欲之为善”[7](P346),“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7](P268)等彰显仁所内含的可欲向度。仁之理,由孔子“忠恕”、孟子“寡欲”开启,直至程朱“天理说”达到极绝。合言之,仁合生、欲、理于一体。
然而,孔孟对仁之生、欲、理三维度的自觉是不够充分的。因此,《论语》《孟子》等并未对仁之生、欲、理三维度作出直接表述。程朱虽直述仁之生、仁之理,但囿于天理、人欲的二元对立,造成了理欲抽象化与割裂化[8](P37),这使得“仁”偏向以至等同“理”而逐渐远离甚至失去“欲”。换言之,程朱所持之仁偏离了孔孟仁合理欲之旨趣,并因此而被戴震称为“异趣”。所以,戴震追访孔孟,通过对仁的疏通与证明,自觉明晰仁之生、欲、理三维度及其逻辑关联,以“生生”“欲无私”及“遂欲通情”等规定“仁”,并基于生生与条理间的辩证关系,视欲与理为相互依存、互相成就且“由自然而必然”的合作关系。这在传承孔孟仁学传统、弥补程朱仁学不足的同时,实现了对原始儒家仁学的超越。
一、“生生”之仁
“生生”之仁起于《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及“一阳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显诸仁,藏诸用。”[3](P503)仁显现天地万物的生化不已,天地万物的生化不已是一阴一阳之道的结果。显然,“生生”之仁在《易传》这里,具有本体论建构意义。《易传》的这一本体论建构,牟宗三先生将其划分为两种进路:自然造化与儒家的道德形上学[9](P11)。换言之,“生生”之仁从一开始便是宇宙本体论与道德形上学的,既指向自然界,也面对人伦道德,合天道与人道于一。
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原因,何晏解释为:“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进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10](P61)。之后,朱熹和刘宝楠分别将其理解为:“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6](P77)以及“孔子五十学《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传是学。然则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易》是也”[11](P98)。从何、朱、刘三氏的说明可以肯定:(1)孔子较少谈论《易》之性与天道;(2)《易》之性与天道“深微”,难以用语言表达;(3)体证《易》之性与天道需要体证者具备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孔子多言“仁”。然而,《论语》论“仁”百余处,却多以如何达仁、怎样行仁为主,并不直接规定仁。换言之,孔子所言之仁实是仁之体证与践行。从这个意义上讲,言“仁”并不比言“性与天道”容易,仁与性、天道等一样无法仅用言语表达。因为如此,得于“天”的“生生”之仁在孔子这里的表达是极其隐晦的。
从自然造化看,“生生”之仁体现于“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的变化中;从道德形上学讲,生生之仁表现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P4)以及“爱人”践行里。显然,“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体证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孝弟之道”与“爱人”践行人伦社会的繁衍不止,二者虽未真抒“仁”意,但却共同展现并证成“生生”之仁及生生不已之道。
“生生”之仁在程朱这里,和孔子相比,显得直接明了得多。“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12](P32)万物生生意向是天道生生的表现,也即“生生”之仁的自然造化。“生生”之仁的道德成就即在于“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12](P33)。朱熹总结二程“生生”之仁:“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无而在”[13](P3280);“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以得之心为心者也”[14](P923);“别无所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15](P1756);“仁者,心之德,爱之理”[6](P187)。在程朱这里,“生生”之仁是生物之心、心之全德、爱人之理。它统贯人物之生生不穷,并归于“理”本体之内,仁与道、理合于一体。仁与道、理相合,加上“理”的绝对性和至上性,因此,仁与道难免不能充分展现《易》生生不已之道的生化性与流动性。可见,“生生”之仁在程朱这里,实际上偏离了《易》“生生”之仁的原初本旨。
针对孔子“生生”之仁的委婉含蓄,程朱“生生”之仁的有所偏离,出于训诂的戴震直接考证《易》“继善成性”,指明“道”是“生生”之仁的形上根据,“生生”之仁是合于“道”的结果: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条理之秩然,礼至著也;条理之截然,义之著也;是以见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懿德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继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则与天地继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道,言乎化之不已;……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16](P7-9)(《原善·三卷·上》)
道是一阴一阳的气化流行不已,它具有生生、条理两大功能,道之生生是仁的来源,道之条理之秩然有序是礼的来源,道之条理之截然有分是义的来源。善,也即仁礼义,是顺畅地实现“道”不已之生生与条理,一旦善(仁礼义)得以实现则天下懿德、人物有常。因此,“天地之大德曰生”实指气化之道的生生不已: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气化之于品物,可以一言尽也,生生之谓欤!观于生生,可以知仁;观于其条理,可以知礼;失条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是故可以知义。……是故生生之谓仁,元也;条理之谓礼,亨也;察条理之正而断决于事之谓义,利也;得条理之准而藏主于中之谓智,贞也。”[16](P9-10)(《原善·三卷·上》)
元、亨、利、贞分别对应仁、礼、义、智,“以仁、礼、义为名的道之形而上的德性,引生出并对应于仁、礼、义之道德的德性。”[17](P130)据此,仁即是生生:“生生者,仁乎!”[16](P8)“仁者,生生之德也;……在天为气化之生生,在人为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为德也。”[18](P203)
正因为气化流行之道“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18](P197)因此,与《易》及孔子一样,戴震的“生生”之仁同时面向宇宙自然与人伦道德,兼具自然造化与道德形上学之本体意蕴。就自然造化而言,“卉木之枝叶华实,可以观夫生”[16](P10);对人伦道德来说,“饮食男女,养生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16](P27)。作为本体的“生生”之仁,既体现于卉木枝叶的生长华实之中,也表现于饮食男女的生养之道里。由此,得“仁”即得天与人、自然与道德:“仁以生万物……仁得,则父子亲。”[16](P8)
从生生与条理的关系看,一方面,“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18](P203),另一方面,“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18](P204)。生生与条理的辩证关系表现为:生生是条理的来源,生生之中必定呈现条理,因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顺畅有序的;条理是实现生生的保障,因为有序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且和谐生长,二者相互依存、互相成就。换句话说,由生生而条理是气化之道的自然顺成,它不是条理对生生的强制约束;由条理而生生是气化之道的必然复归,是呈现条理之后的应有结果。由此,无论是自然造化,还是人伦道德都将归于“生生→条理→再生生”的大历程,并且这一历程是一个“由自然而必然”的圆融过程:“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天地人物之道于是乎尽。”[18](P199)简言之,生生与条理是相互关联、互相证成的关系,二者自然而然地呈现自身,共同体现着气化流行之道的生生不已。依此类推,“生生”之仁与条理秩然之礼、条理截然之义也秉持这一辩证关系,因而源于生生的仁自然而然地含赅源于条理之秩然的礼与条理之截然的义。一句话,仁统贯礼义,礼义实现仁,这与孔子对仁礼的最初设想不谋而合。
戴震以本体、兼人物诠释“生生”之仁的致思方式还完全合于《易》的原初规定,但超出《易》的是:其一,以饮食男女呈现人伦道德中的“生生”之仁,为其后肯定欲情确立合法根据。反言之,禁情绝欲的人伦之仁是无法彰显生生之道的。这一方面将戴震的道德哲学扎根于人及其生活,另一方面通过生生将仁,尤其是人伦道德之仁与欲、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孔孟所主张的仁欲关系本旨。但与孔孟相比,戴氏的“生生”之仁显然更加直白且缜密。其二,以“归于自然,适完其自然”诠释生生及其条理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为生生之欲与条理之理的合一确立合法根据,进而确证仁,尤其是人伦道德之仁内含理与欲;另一方面,“生生→条理→再生生”决定着“欲→理→欲”之间的转换是没有对立、自然圆融的,也即理、欲之间相关且整体,而这正是戴震批判程朱的核心所在。在他看来,理学家最大的错误还不在于置理于欲之上,而在于视理欲之间为二元对立且非整体关联,更别说相互成就的关系。因此,程朱的“生生”之仁难以衍生欲、仁间的相互依存与互相生成,更难内含欲与理。其三,以大历程诠释“继善成性”,从而视“生生→条理→再生生”与“欲→理→欲”均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生化不已过程,这正好彰显“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神髓。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仁学在内的戴震哲学旨在呈现生化不已之历程,因此它是灵动的、发展的、向上的,这符合儒家原初本旨。总之,戴震对“生生”之仁的这一考论,在恢复原初本旨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原初本旨的超越,纠正了程朱“生生”之仁的偏离。与此同时,戴震“生生”之仁也为其后“欲无私”之仁、“遂欲通情”之仁的提出与证实奠定形上根据。
二、“欲无私”之仁
“仁”离不了“欲”且内含“欲”在先秦儒家那里同样未被直接清晰地展现出来。孔子论仁与欲大致可归结为三种情形:其一,隐射仁不离欲,以“我欲仁,斯仁至矣”[4](P196)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4](P86)为代表。对于前一句,从字面看,欲作动词,表示想要,其对象是仁。因此,就表面看,似乎仁并不内含欲。但反过来看,本句还意指:我可以欲“仁”并由此“仁”至;我也可以欲“非仁”而由此“仁”不至。显然,无论所欲是“仁”,还是“非仁”,它们都是名词之欲的内容。由此推断在孔子在这里,欲不仅并不妨碍仁的实现,并且欲且欲于仁还是实现仁的必要前提。换言之,孔子以极其婉转的方式阐明仁不离欲。至于后一句,前儒多着力于阐释“能”而强调仁内含着智(知),比如刘宝楠“好恶咸当于理,斯惟仁者能之也”[11](P75)以及钱穆“惟仁者其心明道,乃始能好人恶人”[19](P80)等。无论是刘氏以“理”释“仁”,还是钱氏以“心明”释“仁”均表明:(1)“智”(知)是达“仁”的必备要素;(2)“仁”内含着“理”。的确,仁内含知是孔子一贯的主张,仁内含知有助于我们进行好人恶人判断,但仁内含理应是孔子留给后儒的无言指引。然而,如果以好人恶人来诠释“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话,好恶作为对欲望的情感表达,已经预设“仁”内在地包括着欲。
其二,仁潜含欲。这可从“樊迟问仁,曰‘爱人’”[4](P337)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4](P87)中得到说明。“爱人”之“爱”显然言明仁含欲情,而以道的方式欲求富贵则表明富贵之欲也可以是实现仁的有效前提。换言之,正是在肯定人人欲求富贵的基础上,才可谈论欲求富贵方式的得当(合于道)与否,进而实现仁。反之,没有富贵之欲,求富求贵之方式也无从谈起,更别说仁的践行了。
其三,忠恕之道推导仁合理欲。无论忠道,还是恕道,个体之欲既是取舍自身欲望的标准,也是满足他人欲望的准绳。“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20](P127)也就是说,个体之欲能够同欲,个体之欲走入同欲,也即达到“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践行爱人的忠恕之仁实是申明理欲合一且理出于欲的。
孔子论“仁”肯定欲但却未对欲作出分类,而孟子以“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7](P268)将欲分为:道德欲望(“义之欲”)与自然生理欲望(“生之欲”),并高扬道德欲望。但无论是“生之欲”,还是“义之欲”,孟子都认为“可欲之谓善。”可欲是善的前提,仁义礼智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情(欲)的扩充。与此同时,欲之可与不可依据何在?孟子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7](P352)寡欲促进养心,多欲或无欲(虽未言明)是无法养心的。寡欲是衡量“欲”可与不可的理性标准,“善”合“欲”与“理”。合起来看,在孔孟这里,欲是实现仁的前提,理是欲走向仁的保证,仁含欲与理。显然,孔孟的仁、欲、理阐释直指人伦,不再是“生生”之仁所面向的宇宙本体,无论是爱人、亲亲、忠恕还是恻隐都是“生生”之仁在人伦生活中的展开。
于孔孟言,仁隐含理欲合一,仁、欲、理三者不可分割且属于同一世界,仁是理欲顺成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仁统摄甚至高于理与欲。然而,在程朱那里,仁、理、欲的关系却展现出另外一番图景,“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18](P152),欲与理分属两个世界,仁是理居于心的结果。也就是说,理是仁的前提,仁、理地位置换,理欲二分割裂,欲不再是仁的基础,理、欲、仁之间不是同一本原的整体关联与相互证成,而是分属二本的强制结合。这显然是私淑孟子、正名儒学的戴震所不能忍受的。
戴震以“生生”之仁为本体,直言人伦道德之仁首先是“欲无私”:“无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绝情欲以为仁,去心知以为智也”[18](P209)。仁并非绝情禁欲,而是欲“不私,则其欲皆仁也。”[18](P195)欲“不私”即是达仁,仁不仁的关键不在欲不欲,而在私不私。私是什么?“私也者,生于其心为溺,发于政为党,成于行为慝,见于事为悖,为欺,其究为私己。”[16](P23)“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私生于欲之失。”[18](P158)私即是心沉溺于欲,在政治上表现为结党,在行为上表现为作恶,在事为上表现为欺诈,其根源于追求一己私欲。因此,私又称为“欲之失”。“失”即不合于中节:“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流;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为相生养之道,譬则水由地中行也。……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18](P160)所以,仁是中正之名:“曰仁,曰礼,曰义,称其纯粹中正之名。”[18](P198)不失即中节,也即理,仁是中正之理则。
欲是什么?欲是源于“生生”之仁的饮食男女等生养之事,属“血气之自然”:
“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16](P9-10)(《原善·三卷·上》)
“《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男女,养生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16](P27)(《原善·三卷·下》)
“欲者,血气之自然。”[18](P169)(《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合言之,仁是自然之欲合于中节之理的结果,内含欲与理。理即必然之则:“理非他,盖其必然也。”[21](P87)自然之欲与必然之理的关系表现为:“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礼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18](P169)“自然之欲→欲无私(必然之理)→仁”是一个“由自然而必然”的圆融且生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欲、理、仁两两之间并非二事,欲是仁的基础,理是由欲及仁的保证,仁是理与欲的合一。欲、理、仁不可分割,水乳交融,同属生化历程,共同证实并表现生生。
由此,面向人伦道德的“欲无私”之仁,在戴震这里以“人伦日用”与生养之道为根基:“道者,居处、饮食、言动,自身而周于身之所亲,无不该焉也。”[18](P200)“就人伦日用而语于仁,语于礼义,舍人伦日用,无所谓仁,所谓义,所谓礼也。”[18](P206)换言之,离开自然之欲与五伦日用,理失去根基,仁无从谈起。据此,伦理道德交还给人及其真实欲情与人伦生活。
从戴震“欲无私”之仁的这层阐释看,它在复归先秦儒家仁合理欲的基础上完成以下超越:首先就论证方式言,戴氏的证明是直白且缜密的。直白在于,和孔孟相比,戴震明确规定欲、理、仁、私、“由自然而必然”等概念的内涵而非意向性表达。缜密在于,无论是由本体的“生生”之仁推导人伦的“欲无私”之仁,还是由生生条理逻辑关系论证理欲合一,抑或以“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阐述“生生”之仁与“欲无私”之仁在生、欲、理、仁的相互转化中所展现出的生化历程都是整体如一,有分有合,前后贯通的。由此,戴氏对程朱理学在这一问题上的批判直击要害,十分有力。其次就思想旨趣而言,戴震强调理、欲非二事,理、欲、仁属同一世界,无非是为正名“理”只是必然的、由欲及仁的重要环节,不应成为“仁”之上的绝对主宰,更不应离“欲”而存在,离欲之理与绝欲之仁都是无根的空洞口号,必将成为压制人正常欲情的虚假工具,最终脱离人及其生活。与此同时,以欲为基础的仁也回到孔孟当初“为仁由己”的理想设定,毕竟一个脱离人及其生活的仁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最后,就其自身哲学体系来讲,“欲无私”之仁进一步实现并确证了“生生”之仁,并因此而倡导一种德福一致、事实与价值合一的伦理生活:一方面,生养之欲保证现实生活中的人应该首先拥有自然生命,这是“生生”之仁的底线,因为每一个人真实地活着是获得个人幸福与彰显宇宙生生的基础;另一方面,“欲无私”确保真实活着的每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彰显其道德生命,更为宇宙生生实现提供秩序保障,二者共同实现个体德福一致及宇宙生生不已。
三、“遂欲通情”之仁
“欲无私”之仁展现的是个体欲望满足,以及欲、理、仁之间的逻辑关联,这对于发扬先秦忠恕之仁的戴震来讲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看来,“生生”之仁既是个体之欲与群体之欲的共同满足,更是忠恕之道的切实践行:“圣人顺其血气之欲,则为相生养之道,于是视人犹己,则忠;以己推之,则恕。”[18](P169)因此,戴震扩充“欲无私”,提出“遂欲通情”:“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18](P209)“遂欲”即“遂人之欲”:
“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16](P27)(《原善·三卷·下》)
“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18](P157)(《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18](P201)(《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仁义礼智》)
“遂人之欲”要求“遂己之欲”的同时,推己及人地“遂人之欲”。实现“遂人之欲”以人、己同欲为前提,“遂人之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方面“己之欲”的遂通需要他人为其创造条件,而他人条件的创造其实是遂通“人之欲”的结果;另一方面人己之欲的共同通遂也即实现“生生”之仁。“遂欲”表明“己之欲”与“人之欲”同样重要,都是应当遂通的对象,“己之欲”的通遂不得妨害或无视“人之欲”的通遂,“人之欲”的通遂也不能伤害或忽视“己之欲”的通遂,也即人己之欲均应被充分地尊重且遂通,不应因人己身份差异而被剥夺或践踏。由此,己与人、个体与群体之欲均关照在“生生”之仁里:君不因遂己欲而不遂臣之欲,父不因遂己欲而不遂子之欲,兄不因遂己欲而不遂弟之欲,夫不因遂己欲而不遂妻之欲,上位者不因遂己欲而不遂下位者之欲,反之亦然,最终实现社会的五伦和谐与生生局面。
“通情”即“以情絜情”:“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18](P150)“以情絜情”的实质是“平所施”之恕道:“平所施谓之恕。”[16](P23)它要求我们平等地对待人我之情及其得达,强调得达“己之情”时,反躬静思“人之情”,进而得达“人之情”。“以情絜情”基于自我反思与情感体验,感通人我之情及其得达,尽力促成人我之情的得达,彰显人我之情的平等与得达必要性。可见,“以情絜情”与“遂人之欲”的实质均是“视人犹己”而“以己推之”,都以人我欲情的相同相通为前提,也即“遂欲通情”以欲情能同相通为基础。
对此,胡适指责“戴震假定‘一人之欲,天下之人同欲也’(《疏证》二)……但那个假定的前提是不很靠得住的。”[22](P48)胡氏认为,戴氏以“己之欲情”揣度人之欲情其实和程朱理学犯了同样错误——“一己臆断”。因为现实中的“人之欲情”各不相同,以同欲为前提,“遂欲通情”要么无法实现,要么造成专制,这和程朱“以理杀人”的本质相同。针对胡氏质疑,成中英提出“这项批评只有当我们未能领会此标准之开放结构时才或可成立。……只有在以至善之前景为归趋的学习历程中,天下一致与适用于天下的考验标准才可显现出其最可靠、最适当的方法,也足以确立价值之所在,即道德或德性之真实价值所在”[17](P118)。在成中英看来,任何欲情及其遂通均具有社会性,而非纯个体的独自遂通。因此,为更好实现欲情遂通,主体需要置“己之欲情”于“社会(人)之欲情”的共同标准与开放怀抱之中,以最大限度地遂通“已之欲情”,并在“己之欲情”的遂通中走向且实现“人(社会)之欲情”的遂通。也就是说,“人之欲情”及其标准既是遂通“己之欲情”的必要条件,也是遂通“己之欲情”的最终归宿。
胡、成争执的焦点在于“遂欲通情”何以可能。对此,戴震同样在理、欲、仁三者的逻辑联关中给予了回答。“生生”之仁是性之欲情的形上来源,因此,性之欲情虽各有差异但却共同呈现生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性之欲情可称得上异中有同,异在于成性的各欲情及其遂通有殊,例如上智之欲情与下愚之欲情有别;同在于成性的所有欲情均展现生生,比如君子问学与商人经商类同。简言之,千差万别之欲情及其遂通同归于生生,“生生”之仁为“遂欲通情”的实现确立前提与目标。然而,仅有前提与目标,还不能确保“遂欲通情”真正实现。因此,生生必具条理,条理之理既是心之同然,也是欲情之必然,它是性之知所具备的能力。换言之,性之知使得性之欲情(自然)及其遂通能够合于必然之条理(理),从而保障“遂欲通情”的实现。简言之,成于条理的性之知所具备的理性能力保证了成于生生且千差万别的性之欲情各得遂通并展现生生人伦,“遂欲通情”之仁合欲(情)、理于一。并且,和“欲无私”之仁一样,“遂欲通情”之仁由欲(情)及理同样是“自然而必然”的圆融合一。
但和“欲无私”之仁相比,“遂欲通情”之仁所呈现的是一个异彩纷呈而又殊途同归的理欲合一之仁。从多与异的角度看,它既充分尊重且肯定个体欲情而彰显自由与平等,又足够自觉欲情之多与异才是人伦生生的必要奠基。就同与一的视角言,它还为包括人及其伦理生活的杂乱安排了合理秩序,进而实现人伦礼仪与社会文雅以及他心中的王道社会:“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16](P159)也就是说,戴震的“遂欲通情”之仁所欲实现的是一个有欲有情、人人平等、和而不同、欲情理合一且勃勃生机的人伦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欲情均得到充分的彰显与遂通,并且基于“欲→理→生生”间的逻辑关联,上位之人的“以理杀人”既失去其存在基础(欲)也无法真正实施起来。
由此看来,胡氏的指责忽略了戴氏“遂欲通情”之仁中所隐含的欲情差异,更未关注到差异的欲情终将合于同(理)、归于生生的实质,从而简单地对立欲情之异与理(知)之同。成中英的辩护洞见到戴氏“遂欲通情”之仁中所内含的整体之同,但却未能对其所重视的欲情之异展开说明。异与同之间是相互辩证的,没有差异的同,不可能存在,也豪无意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才是可能实现的有价值的同。一句话,“遂欲通情”之仁力主基于欲情差异的普遍准则,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称“戴震的‘以情絜情’为‘合理的利己主义’原则”[23](P308)。显然,基于合理利己的伦理准则是面向人及其现实生活的,它通过欲情的合理满足,帮助人们过上有福合德、事实归于价值的伦理生活。
由此可见,“遂欲通情”之仁和孔孟之仁相比,它在延续孔子“爱人”之仁以及孟子“仁政”实施的基础上,将欲情、理融入忠恕之道,丰富并落实孔孟之仁的践行,并通过对欲情差异及其归于普遍之理的厘清与论证,十分清晰地展现了其对孔孟之仁的推进与发扬。与此同时,理学之仁在戴氏这里沦为既无欲情保障,更无欲情差异的空洞之理。总之,无论是本体意义的“生生”之仁,还是道德含义的“欲无私”之仁与“遂欲通情”之仁都力图恢复原始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所展现的欲、理、仁之间的张力与圆融。此外,除去“仁”属本体与准则之外,戴震“仁”学还指明,仁也是德性:“仁义礼之仁,以理言;智仁勇之仁,以德言,其实一也。”[21](P129)
[注 释]
①仁的含义可归结为:(一)仁是天地法;(二)作为天地法的表现为生生;(三)仁作为人间法表现为有利于生生的行为和情感、观念;(四)仁是人之本性;(五)仁是诸德之源;(六)在情与理之间,仁的本质是情。参见宋大琦.欲与仁[J].原道.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