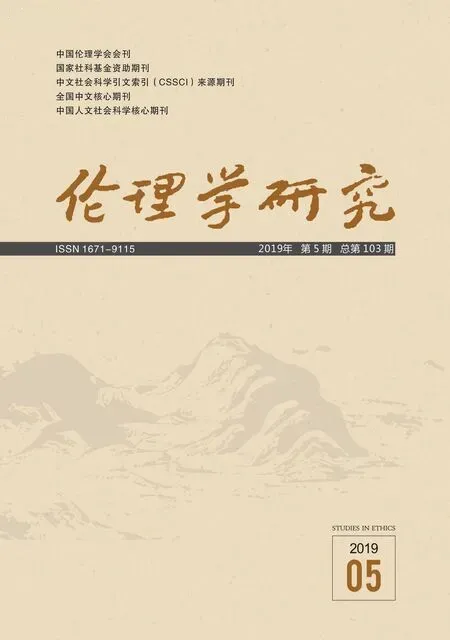康有为民主政治伦理观的意蕴与局限
张怀承,张 娟
任何政治制度以及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变化都是围绕一定的政治价值理念而进行的。如果说从封建专制政治过渡到近代民主政治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那么,对于近代民主政治价值观的接受与价值系统的构建则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秉轴持钧的一步。近代“天崩地解”般的社会大变革赋予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们面对中西文明的交锋与对撞,自觉理解并利用近代民主价值观念来重构政治规范与政治秩序的时代使命。出于对历史现实的回应,在炽热的爱国热情与忧民情怀下康有为自觉承担起了对政治价值规范破旧立新的艰巨使命,发起和领导戊戌变法运动从而启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新进程。康有为追索民主的努力代表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良药的艰苦探索,反映了近代国人在亡国亡种的社会危机中对腐败的专制统治的觉醒以及对民主价值观念的渴望与追求。
一、康有为民主政治伦理观的来源
“民主”这一词汇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价值观念对于中国来说是晚清西学东渐中的“舶来品”。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们在开启向西学习的潮流中把“民主”思想引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是民主最原始的内涵,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最迫切的需求,因此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最初是从政治民主这一向度来理解西方的民主思想,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也成为近代国人奋斗的主要目标。构建新的政治伦理必然包含对传统政治伦理的否定与摒弃,而对于有着深厚传统政治文化积淀的中国近代社会而言,遽然彻底告别适应了几千年的政治价值观不太可能。如何实现传统政治伦理与近代政治价值观的融汇贯通,促进专制政治伦理向民主政治伦理的过渡,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必须面对的问题[1]。
1.托古——采撷传统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
中国自古就有民本思想,以民为本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最早的民本意识源于四千余年前的《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统治阶级第一次认识到民是国之根本。到了西周,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政治纲领,认为天命即民意,只有以德治国、以德保民,才能配有天命,“敬德保民”成为夏商以来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重要转变,表征着政治伦理的价值判断依据由神变为人,人们开始从人事中寻找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伦理标准和依据。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的动荡、政权的频繁更替让哲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民”的重要作用。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是先秦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典型代表。民贵君轻思想始于孔子,而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思想的是孟子,孟子重民、贵民,在民本思想上深有建树,是先秦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王制》以舟水关系比作君民关系,“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突出表达了民对君的制约作用。春秋战国时期,民本主义政治伦理观逐步形成体系,成为儒学体系中的进步力量,并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成为贤君明臣们制定政策的理论指导。
通过对传统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实现新旧政治伦理的对接与互证,康有为试图减缓顽固势力对其“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舆论压力,论证自己的主张“合乎古训”,从而达到保护和宣扬自己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的目的[2]。康有为视孔子为完美的至圣先师,通过对传统文化源流的考证得出“六经”皆孔子所作的结论。他认为孔子作《春秋》,但没有将改制的思想写入书中,而是通过口传的方式将其中隐晦的改制思想传给孔门弟子。通过对孔子微言大义的阐释,康有为赋予孔子主张共和、民主、议院的思想,将孔子装扮成锐意改制的“素王”[3]。他甚至认为西方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和议会制度思想皆由孔子首创。他在《孟子微》中说“孔子之为洪范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是也;尧之师锡众曰:‘盤庚之命,众至庭’。皆是民权共政之体,孔子创立,而孟子述之。”[4](P421)而在《孔子改制考》中,他着重发挥孔子的“仁政”思想,认为“孔子之道,务民义为先”。由此,在康有为眼中,孔子是一位以民为本的民主政治家。康有为认为孟子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且先秦大哲中,孟子的民本政治伦理思想最为鲜明,故康有为对孟子民本思想的解读更为细致与深入,专著《孟子微》一书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重释。康有为将孟子的重民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直接对等起来,在书中多处用西方民主政治观念彰显孟子的民主精神。例如,他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揭示为“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4](P421)。孟子思想本无社会契约观念,康有为通过对孟子“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一句加以现代性诠释,使得孟子拥有用社会契约方法来解释国家起源的思想[5]。籍此,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价值观通过康有为对孟子民本学说的重释、改造与转介从而得以理解和传播。
2.仿洋——择取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伦理观
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是君上—民下框架内的政治价值观,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君主统治。跟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相比,不管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毫无关联。为了拉拢民心,扩大战斗的同盟军阵营,早期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民主政治理念在内涵上提倡人人平等、主权在民,号召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自由与权利,外延则要求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因此民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从内涵上来说可谓判若云泥。
民主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意为由民众进行政治统治,或为民众利益而进行统治,西方“民主”一词起初的含义就是政治上的“人民当家作主”。17—18 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摧毁了封建等级政治伦理和神学价值观,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政治。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催生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人人平等、主权在民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构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伦理观的主要组成部分。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通过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论建立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伦理价值观。他们认为,人天生地享有自由、平等、民主等权利,人身权利是最古老、最基本的社会正义,这一理论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要求,为西方世界所普遍接受。19 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思想随着西学东渐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一大波有识之士,并最终成为他们反抗封建专制的有力思想武器。
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对康有为的影响极为深刻,康有为正是通过借鉴天赋人权思想来论证人人生而平等从而对封建专制的统治工具——纲常伦理进行批判。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在《人类公理》和《实理公法全书》中,以人由天地原质而生为出发点构建了一条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路径。通过论证,他指出,平等、独立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正如他在《孟子微》一书中所说的,“盖天之生物人为最贵,天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4](P413),通过天赋人权的理论指引,康有为将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章句下》)引申为人人生而平等、自主,并将其上升至天之定理、人类公理的至高境界,从而为其兴民权、立宪法、设议院等民主政治主张奠定了理论依据和形上根基。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在论证人的平等、独立的应然性的同时,以釜底抽薪似的方式否定了封建等级政治依附的传统政治伦理价值观,为民主(自主、自立、自由)进行了完整的论证,促进了国人人权意识和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觉醒和体认。
二、康有为民主政治伦理观的内涵
出于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和推翻压抑人性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强烈愿望,康有为试图通过制度的变革,在中国开出一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道路。通过对中西政治伦理思想的杂糅与改造,康有为最终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康氏民主政治伦理思想大厦。
1.人人有自主之权
康有为“民主”思想的核心与根基为人人有自主之权,通过承认普通民众有人身独立、平等的权利,把民众从封建三纲伦理中解放出来。其民主思想的主要攻击对象为封建纲常礼教,而不是封建君主的地位。他的意图是利用民主价值观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平等关系,从而在意识形态上推翻封建政治人伦规范,建立一种新的基于人身独立与平等的资产阶级人伦规范。
康有为对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正当性论证以探究人最初的本源为起点,试图从源头来寻找理论依据。通过对人本原意义的研究,他发现“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6](P148),也就是说人都是由天地原质而生的。既然人人都由天而生,那“天地生人,本来平等”[6](P153)则是再自然不过的天之实理,正如他所说,“夫人类之生,皆本于天,同为兄弟,实为平等”[7](P40)。在这一实理的支撑下,他进一步推演出“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6](P148)的公法,正如他所说,“以天之公理言之,人各有自主独立之权,当为平等……以人之事势言之,平等则智乐而盛强,不平等则愚苦而衰弱”[7](P40)。这一推理逻辑的结果是,既然人人源出于天,人人生而平等,故人与人之间也就无所谓尊卑,每一个人都天然地享有上天赋予的自由、平等权利,那么现实生活中君父、子民、父子、夫妇之间的上下绝对从属的关系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康有为对人生而平等与独立的论证是对以三纲为支柱的封建宗法政治伦理的彻底否定,他从形上层面帮助人们摆脱了数千年来封建政治伦理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使人获得独立与自主的权利,对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2.君为民而立
康有为“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思想使得个人摆脱了封建人身依赖与思想束缚,实现了私领域的独立与自主。以此为基点,他将民主理论进一步向公领域扩展,通过重塑君民关系,构筑了一套以民为国家权力来源的政治建构理论,这套理论成为康有为政治变革运动的理论基础。
君权天授观以及天然而严厉的等级制度造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同时也成为封建君主获得政权正当性的依据以及维护政权稳定性的工具。按照君权天授下的君—臣—民的组织逻辑,君位于权利的最顶端,君权受命于天命,“受天所命作之君”。臣依附于君,官权授命于君权,以维护君权为目的。而民则处于权力链的底部,是受统治的群体,这一组织体系,尊卑有别,等级分明,人身依附关系紧密,在这套体系中个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彻底丧失[8]。康有为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国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而是“天下之人公共同有之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借鉴西方民主政治中的社会契约理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对国家的起源作了重新的论证。他认为之所以有国家,是因“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由于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人民遂“公举人任之”[4](P421)。而对君主存在的理由以及地位他如是说,“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6](P152)。意思是,君主是人民公选的,是人民的代理人,其作用是管理民众的公共事务,保卫公共安全,如果君主失职,则可以被剥夺管理职位。康有为对君民关系的颠覆性解释,彻底反转了传统民本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君上—民下框架,将民视为国家权力的来源。通过“民立君”“民为主”的论证,康有为为其政治变革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3.限君权扩民权
康有为政治变革主张的核心是实行“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现君与民对权力的共享,他认为对当前中国而言这是最理想的政治形式。康有为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深以为然,他认识到要实现君民共主必须限制君权,扩大民权。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他在逐步的政治实践中提出了由立宪法、设议院到开制度局的政治主张。在1895 年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首次提议设立“议郎”,他口中的“议郎”具有民主选举的意味,“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9](P44)。《上清帝第三书》显示了康有为议会思想的萌芽,“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10](P80),在这一时期,他对议院的职责以及选举方法都有所思考,其民主政治价值观进一步得以完善。而1898 年1 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的君主立宪思想最为成熟与全面,他明确向皇帝进言开设国会,制定宪法,“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11](P5)。康有为对议会的设计也作出了细致的思考,整体原则是效法俄日,建立民选下院和公推上院,其中“约十万户而举一人”的民选下院占据主导地位,至此,康有为的民主政治思想达到顶峰。1898 年1 月底,康有为获总理大臣召见,并随后受到光绪赏识。为获得了光绪的全力支持和缓解朝廷内部守旧势力的压力,康有为改变了以往的激进战略,在民选下院的路线上做出妥协,代之以自上而下的开明君主改革路线。康有为的民主政治思想由上下两院以民选下院为主修改为建立具有上院性质的制度局一院制。制度局是康有为在国情与时事下通过多方权衡与慎重考虑而做出的调整,在守旧势力强大的特殊背景下,制度局是实现民主的过渡机构,由维新派组成的制度局是在当时背景下能够曲折实现康有为“许天下人上书”心愿的折中办法。
4.民主是渐进的过程
早在1895 年,严复就意识到公民选举权与议院之间的张力,他认为国民“民智未开”,开议会为时尚早,并据此反对立即开议院,梁启超深受其影响[12]。康有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深有研究,未尝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在获得光绪的支持前,他更需要以民主、议院作为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旗帜来赢得改革派的支持。而被召见之后,康有为有了更强有力的靠山和变法保证,为了缓和守旧势力对变法的阻碍,康有为以“旧党盈塞”“民智未开”两大理由指出立即开议会在中国不可行。康有为认为开制度局在当时的形势下可行且稳妥,他视制度局为实现议会制君主立宪的过渡形式。对于自己政治思想的转变,康有为给出了两点解释。首先是敌我力量太过悬殊,当时维新势力十分孱弱,而守旧派却异常强大,同时维新内部也有人反对立即开议会。如若操之过急,很大可能会刺激到守旧势力,反而对变法不利。其次,民主选举对中国民众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不符合国人思维定势与处事方式的舶来品,且中国国民教育尚未普及,国民不具备民主的理性,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贸然大兴民权,实行民众选举,恐会生乱。国际上正反两面都有鲜明的实例,日本明治维新始于1868 年,可是直到1890 年才正式实行议会制度,日本因实行渐进的民主而变法成功。而波兰的改革则提供了对民主操之过急而遭反杀的反面教材。由此,他得出民主的进程需要循序渐进的结论,开立议会之前必须对民众进行教化和启蒙,只有通过逐步提高公民的政治素养与民主理性为君主立宪的实行打下良好的民众基础,才能真正实现“君民共主”。因此在新旧严重对立的背景下,康有为坚定地认为依靠开明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是切合中国国情的方案。
三、康有为民主政治伦理观的时代特质与理论局限
康有为的民主政治价值观是近代中西融合、新旧交替的综合结晶,因此其思想既具有近代西方启蒙运动所蕴含的独立、平等、理性的基本精神,又难以摆脱思想深处固有的中国本土文化中尊君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1.康有为民主政治伦理观的时代特质
(1)主体性
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文艺复兴促进了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启蒙思想和宗教改革在此基础上,以复归的理性精神为武器,颠覆了宗教禁欲主义的既有价值观,确定了具有理性的人的主体性地位,将道德价值的终极指向确定为鲜活的个人,由此开启中古和近代的分界[13](P205)。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自封建社会伊始便逐步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儒家宗法等级政治伦理思想为统治手段的君主专制政治。在儒家政治伦理主导下,人与人之间贵贱不同、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位,各守其礼,绝不逾矩,以实现儒家政治伦理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谐有序的政治局面。儒家政治伦理以封建纲常思想为核心,臣民的政治生活以忠君、无违、顺从为行为标准,臣民对于君具有单向度的义务观念。在这一价值观指导下,个人失去自由与独立,人与人之间处于具有明显封建等级烙印的依附关系之中,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合理欲望均遭排斥。由此可见,儒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抹灭人的主体意识来教化百姓安分守己,从而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目的。
于夹缝中生存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压制其发展的封建等级以及封建伦理思想具有强烈的不满。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康有为极度服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受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他认为若要使国家强大与独立,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人首先必须获得独立,独立的人格以及个人自主的地位是民主政治得以开展的前提,只有摆脱封建人身依附,人人具有能够自立、自主的主体性地位,才能以平等、独立的身份参与政治实践。正如他所指出的“天之生物人为最贵,天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康有为提倡个人的自立与自主、启发与弘扬主体权威与价值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是对中国数千年来轻视个人、抹杀个性与个人合理欲望的传统政治伦理观的彻底颠覆,它动摇了传统社会的理论根基,让传统观念变得不再牢不可摧。
(2)平等性
平等是中国先人自古就有的追求,然而古代平等的内涵不同于近代的平等,无论是儒家的成圣、道家的得道还是佛家的成佛,古代先哲们追求的都是一种形上层面的平等,平等并未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且始终缺乏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条件。随着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和中西严重不对等的国际关系面前,平等与独立成为近代中国人的精神期盼与奋斗目标,平等一跃成为普遍的价值理念与实际追求。近代平等的内涵不仅有要求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国际关系平等之义,更具有对封建纲常伦理,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男女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对抗之义。在康有为的理论体系中,平等与民主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康有为的民主思想以平等理念为铺垫,他在论证人人有自主之权时就是以“天地生人,本来平等”为立论依据。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国民的个人自主,他将平等视为不证自明的人类公理。而在《大同书》中,他又将民主与平等并重,“吾采得大同、太平、极乐、长生、不生、不灭、行游诸天、无量、无极之术,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痛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7](P164)在大同社会通往绝对的平等的设计路径上,康有为特别注重人人的自主之权,尤其是女子的自主与自立,甚至将“男女平等各自独立”视为通向至平社会的第一步。民主与平等在相互的理论支持中共同构成了康有为的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
(3)理性
中外封建君主专制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都曾使用“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作为其专制统治的正当性依据。在整个欧洲中世纪,神学政治伦理观主宰了社会政治生活全部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要求。上帝是唯一的真理来源,君主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君主的权威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欧洲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人们思想的启蒙,促进了人理性的觉醒,“君权神授”下的神权政治观坍塌。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虽不信奉“神”,但信奉“天命”,“天命”是最高的行为准则,是封建统治者获取政权合法化的最佳说辞[14]。在“天命”的影响下,封建纲常伦理也成为了统治阶级钳制民众的思想工具,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伦理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定海神针,被国人奉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圭臬以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唯一标准。在皇权至上的社会结构中,个人自主无从谈起。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在给中国带来坚船利炮攻击的同时也送来了理性之光。康有为对西学的狂热,其实更多的是对以自由、平等、独立为核心的理性思想的服膺。通过理性的指引,他将矛头直指封建三纲。通过对人人隶属于天、人人生而平等的论证,康有为帮助国人摆脱封建愚昧思想的束缚,获得个人的独立与自主,同时通过重塑君民关系冲击了传统“君权天授”观,让民众的政治参与有了理论的可能。而他的维新变法政治实践虽如昙花一现且没有成功撼动传统专制统治的根基,但是却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2.康有为民主政治价值观的理论局限
康有为不加辨别地把中国传统民本政治伦理思想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结合起来,使两种完全不相同的理论合二为一,虽然在形式上弥补了传统与近代的巨大鸿沟,促进了民主中国化的发展,但是这种“强史就我”方式的结合,恰恰也模糊和扭曲了中国民众刚刚启蒙的民主政治意识和民主政治观念,其结果反倒加强了封建君权,也导致了其民主思想与政治主张最终走向失败。
(1)理想与现实相悖
在正式变法之前,康有为大力主张立宪法以制君权、设议院以通下情,政治思想中削君权、兴民权的意蕴十分浓重。而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却以“民智未开”为由不再主张立即开民选议会,转而相信只有依靠皇帝才能实行变法实现中国的自救。同时,康有为虽然在理论上十分赞赏民主共和政体,他认为民主共和政体最有利于人道,民主共和也成为他最终的政治理想,但他却在辛亥革命后固执地沉迷于君主立宪的政治构想中,不顾君宪制度在中国实行的最佳时间窗口已错过、民主已成为中国势不可挡的思想潮流的实际情况,一意孤行地反对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甚至不惜被扣上“开历史倒车”的骂名参与张勋的封建复辟行动,希冀借助张勋的军事力量变民主共和为虚君共和。他的政治思想与实际政治举措明显不一致,出现了兴民权的政治理想与重君权的实际行动严重悖离的情况。
从康有为1901 年写给赵必振的书信中可以窥探康有为由兴民权到重君权思想转变的原因。他在信中写道“当时那拉揽政,圣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15](P400),因为无法得知圣上对变法的态度,更得不到朝廷对变法的支持,康有为此时不得不面临两个变法路径选择,一是如若通过多次上书,康有为“许天下人上书”的民主政治思想得到光绪认可,则可以依赖开明君主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康有为认为的最佳变法途径。其次是光绪根本不认同或者强烈反对维新派的主张,则选择以民选议院为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路线[16]。在得到光绪赏识前,维新派选择“不得于上,则欲争于下”[17](P314),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产阶级同盟者以及开明士大夫对变法的支持。1898 年6 月,光绪召见康有为,君臣一番深谈后,康有为确信光绪值得辅佐,旋即改变了政治斗争策略,公开放弃之前主张的立即开国会的主张,改而建议成立无损君主权力的制度局,依靠君权进行变革,将变法希望寄托于开明君主。虽然这一政治策略的转变是为了获得体制内的支持,制度局也是实现议会制君主立宪的过渡形式,但是康有为设计的民主政治实践路径中,君权不但没受到限制,反而在“民主”的过程中让皇帝有了“乾纲独断”的可能。制度局的组成成员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钦定,国家大事也必须由圣上“亲临折衷”,制度局成员虽具有进言、咨询甚至决策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力说到底还是皇帝所赐,其“民主”仍然禁锢在“君上—民下”的框架内,这样的“民主”与传统民本并无本质区别,与资产阶级民主更是背道而驰[18]。康有为理想与实际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他始终无法摆脱儒家尊君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决定了他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对君权的崇拜以及对封建势力的妥协,折射出资产阶级软弱性与妥协性的阶级局限,也说明这样的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
(2)民主与自由相离
民主、平等、自由是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固定组合,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观,其中任何一个价值理念要充分发挥作用,都离不开其他理念的支持与辅助。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以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平等与个人权利为目的,其思想被凝练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并在资本扩张中将这一价值观念波及全世界。近代民主思想在传入中国时,国人对其的理解更多的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对民主的内涵及其与平等、自由之间的关系存在理解上的偏差,甚至是有意为之的误读与转换。
仔细解读康有为的思想,会发现康有为极少提及“自由”。民主与自由虽经常联系在一起,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民主”意指人民的统治,落实到现实层面则包括全体成年人的投票权和竞选公职的资格。而“自由”的要义是指在人们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对私人领域的保护,人权是自由政治秩序的核心要素。在中国,封闭的小农经济、严厉的封建纲常以及高压的专制统治抹杀了人们的自由权利,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也有自由的因子,例如追求个人主义的杨朱学派,但是就算是在当代,杨朱学派也被当作是自私自利的典型。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天下为公”的认知基础之上,在古代谈自由会被视为与“公”相对以及离经叛道,连哲人先贤都很少言及自由,正如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所说“夫自由一言,为中国历代圣贤所深畏,而从立以为教也”,这一影响延及至今。康有为虽然承认人的合理欲望,并主张制度的建立要以去苦求乐,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标尺。但他同时也主张人的合理欲望应通过国家来实现,他并不主张人有实现自由的权利,他认为自由是由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恩赐,而不是天生就有的。他在变法中所争取的政治自由,也只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士大夫的自由,而没有普及到普通大众。所以,康有为在他的民主思想里剔除了自由的理念,他所追求的是缺乏自由的民主。虽服膺西学,但是康有为也深刻地了解国民性与中国的国情,所以他不敢明目张胆地谈自由与个性解放。他的《大同书》虽很早成书但迟迟藏而不发,很大原因就在于《大同书》触及到了儒家伦理的最核心部分,例如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思想,这无疑正是自由主义思想。
结论
康有为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利益,从建立伊始便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民主,它以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为目的,其民主价值观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与政治性意蕴,对普通百姓尤其是无产阶级而言,他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其光鲜的政治口号背后掩盖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虽然他的民主价值观具有难以弥补的理论缺陷和阶级局限,其理论对实际政治生活也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结合历史背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思想,并从历史中去寻求民主政治的经验与教训。康有为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通过对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内核的吸收,加速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使民主意识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对传统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汲取则拉进了中国人与民主这一新事物的距离,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康有为站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转型浪潮上,以不屈的毅力、坚韧的性格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殚精竭力地思索与探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开启了中国近代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