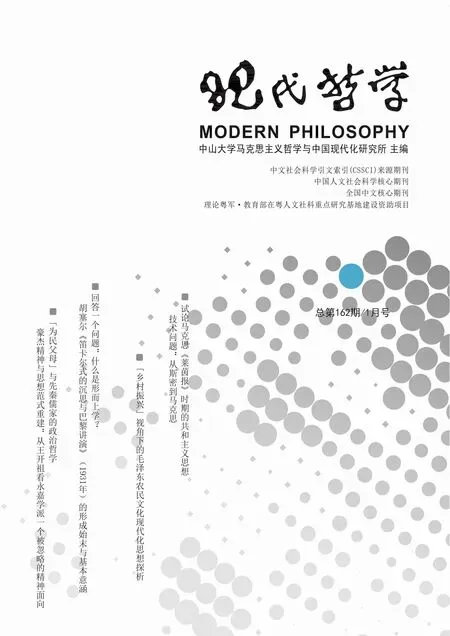豪杰精神与思想范式重建:从王开祖看永嘉学派一个被忽略的精神面向
刘梁剑
一、引言:被忽略的永嘉学派,被忽略的精神面向
永嘉(郡)之于中国精神的历史贡献,山水居其一。山水二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有着特别的意味。山水不等于自然风光,后者可以举足而至,进而反过来悦我目、洗我肺、健我身、欣我心、怡我神。然而,我们对风光只是看,可看的风光有看头,而山水需要观,可观的山水可观。山水滋润心灵,提撕意境(生存意义境界),构成中国精神传统一个独特的向度。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至南朝刘宋时代,山水诗滋兴。山水之滋,首推谢灵运(385—433)。谢公谪守永嘉郡,其文心诗兴与山水形胜相与激荡,诗赋歌咏不得不作。这些不朽的诗篇,一方面,令永嘉山水文气钟灵,不断滋养在此休养生息的一方人杰;另一方面,则令永嘉山水不复仅为永嘉所有,而是超越地域限制,汇入文化的洪流,为中国文化开启新的精神向度,滋养中国人的心灵一千六百余载。
然则,永嘉之于中国精神的历史贡献,除山水之外,断断不可忽者,乃两宋思想史上的永嘉事功学派。精研浙学的董平教授述其发展,勾勒了一条由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1124—1181)、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叶适(水心,1150—1223)等代表人物前后相续而构成的脉络:
两宋永嘉之学实由王开祖初导其源,而由“元丰九先生”,尤其是周行己与许景衡奠其基础;中经郑伯熊之私淑周氏而重振,又经薛季宣之考核经制而改其学风;陈傅良承薛氏经制之学而致其广大,影响被于暇迩,世人始以功利之名归于薛、陈,而叶适实总其大成。[注]董平:《宋明儒学与浙东学术:董平学术论集》,贵阳:孔学堂书局,2015年,第130页。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宋孝宗励精图治,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大胆而自信地推行百家争鸣的思想方针,诸儒彬彬辈出。其荦荦大者,除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和心学两派之外,叶适集永嘉之学之大成,“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全望祖语)[注][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序,载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然则,从后世的流传来看,众人对水心的注目远不及朱陆。笔者虽生于楠溪江畔,复以治中国哲学为业,但对于永嘉之学也是一直没有上心。近两年来,因种种因缘,有幸聆听浙江大学董平教授教诲,结识有志于永嘉学派当代重建的吴龙灿教授,及种种理论和时势的牵引,得以初览乡贤遗文,抚卷之余,不胜感慨:永嘉之学,理论意涵丰厚,实践意义深远,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思想宝库。笔者限于学力,仅就王开祖《儒志编》管窥永嘉之学的豪杰面向。谢灵运为山水诗之祖,王开祖则为永嘉学派之祖。
二、失落的“豪杰”:王开祖《儒志编》两种提要辨证
叶适为永嘉之学的集大成者,推溯其源,则为北宋初年的王开祖(字景山,人称儒志先生,生卒年未详)。南宋绍熙二年(1191),学人陈谦即尊王开祖为“永嘉理学开山祖也”[注][宋]陈谦:《儒志学业传》,载[宋]王开祖:《儒志编》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引《儒志编》,用文中注,不再注版本信息。。如上所引,董平教授也主张“两宋永嘉之学实由王开祖初导其源”。王开祖英年早逝,享寿三十有二。著作多湮没不传,仅有讲学语录辑佚本《儒志编》行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当时濂洛之说犹未大盛,讲学者各尊所闻。孙复号为名儒,而尊扬雄为模范。司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扬雄。开祖独不涉歧趋,相与讲明孔孟之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儒志编提要》)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儒志编》书前提要与此稍异:
开祖当北宋仁宗时,濂洛之说未兴,讲学者犹家自为说,虽贤如司马光,犹不免有《疑孟》之作,而开祖独毅然奋起,以讲明圣道为事,虽其立说未必有尽归精当,而阐明理道,不惑歧趋,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二种提要的差异,除了繁简有别之外,更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书前提要中的“豪杰”在《总目》提要中失落了。从编纂过程来看,各书前面的提要由四库馆臣所撰,它们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补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综合、平衡,并在文字上加以润饰”[注]中华书局影印组:“出版说明”,参见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关于总目提要与书前提要的比较研究,可参见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江庆柏:《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与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王娟:《〈四库全书总目〉与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比勘研究: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基础》(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等。学界目前的研究以文献学为主,哲学义理的向度尚有待开展。。“豪杰”的评价在加工过程中失落,着实发人深思而令人扼腕。[注]关于二种提要差异的发现,得益于和学生吴陈浩的讨论。笔者曾在课上论及此差异,研究生丁宇提出数点意见:除了书前提要、总目提要之外,尚有更为原始的四库提要分纂稿;比较分纂稿与总目提要的差异,更能见出四库馆臣之间的思想差异(包括汉宋之争);从书前提要到总目提要的修改,相当大一部分要考虑编纂体例变化的因素;就《儒志编》而言,总目提要虽无“豪杰”二字而实承认其豪杰精神。
《儒志编》由明代新安理学家汪循(1452—1519)任永嘉地方官时搜访辑佚而成。[注]书前提要及《总目》提要均作“王循”,误。《总目》提要云:“据其原序,乃明王循守永嘉时始为搜访遗佚,编辑成帙。”然原序文末署名则是“新安汪循”。书前提要所述“循”之爵里、著作,亦与汪循合。关于汪循,可参见解光宇、王凡:《论新安理学家汪循》,载姜广辉、吴长庚主编:《朱子学刊》第18辑,2009年,合肥:黄山书社,第233—241页。四库本书前提要在文末不忘表彰汪循:“循,字进之,休宁人。弘治丙辰进士。所著有《仁峰集》。其笃行好学,亦有足称者云。”实际上,“豪杰”的评价就出自汪循原序:
士有起于邹鲁不传之后,濂洛未倡之先,卓有所知而能自立于世者,其豪杰之士矣乎!……矧能真见天人性命之理,入道胜复之功,措之言语文字之间,平正精实,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景山者,不谓之豪杰之士,可乎?[注]周子《易通》即周敦颐代表作《通书》。宋潘兴嗣撰《周敦颐墓志铭》云:“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1页)朱熹则认为:“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宋]朱熹:《太极通书后序》,可参见[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44页)(《儒志编》序)
王开祖的同时代人陈襄(1017-1080)曾致函王开祖,写道:“某谓今圣天子在位,不当有豪杰之士尚在山野,心常忧焉。近者窃不自揆,思欲攟拾天下遗逸之士,而书其所谓德行道艺者。……如足下者,固某夙夜所欲致诚尽礼、惟恐求而弗得者。”[注]陈襄:《答王景山启》,《古灵集》卷1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陈襄系宋神宗、仁宗朝名臣,他在信函中实际上已经将开祖视为豪杰之士。
豪杰二字,对于永嘉之学无疑有着特别的意味。中国传统的儒者无不以成圣为人生第一等事,但对于何为圣人却有不同的理解。以程朱为代表的正统理学家追求醇儒之境,而永嘉学派似乎不约而同将豪杰标举为理想人格。如薛季宣《与沈应元书》:“须拔萃豪杰,超然远见,道揆法守,浑为一途,蒙养本根,源泉时出,使人心悦诚服,得之观感而化,乃可为耳。”[注]参见[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艮斋学案》,《宋元学案》卷52,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52页。王开祖学宗孟子,而薛季宣也用“豪”字为孟子点赞:孟子有功于孔门,“气豪而辞辩”[注]参见[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艮斋学案》,《宋元学案》卷52,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54页。。又如郑伯熊、郑伯英“惟以统纪不接为惧”,二人“性行虽不同,然并为豪杰之士”[注][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周许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32,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4册,第429—430页。。叶适也用“儒豪”等词评论永嘉人物。如谓郑伯熊、郑伯英在大道隐遁的艰难时世,“能以古人源流,前辈出处,终始执守,慨然力行,为后生率”,真乃“瓌杰特起者”[注][宋]叶适:《归愚翁文集序》,《水心文集》卷12,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6页。;而“自二郑公后,儒豪接踵,而永嘉与为多”[注][宋]叶适:《归愚翁文集序》,《水心文集》卷12,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3册,第217页。。
然则,何谓豪杰?
三、豪杰:豪气,逸气,英气,卓识
豪杰之士豪气干云,虽文弱之书生,对于文化使命的传承与担当却是当仁不让。如孔子在匡地遭拘禁,险恶的处境激发孔子道出了斯文在兹的自信与豪气:“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孟子深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参见《孟子·公孙丑下》)。王开祖则说:“孟轲死,道不得其传,而当今之世,如欲继往圣之绝学,舍我其谁?我岂不自知固陋,然深畏道之不传,不得已也。”“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我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极之门,吾畏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儒志编》)
如果说,豪杰对道统的领会是一种知,则此种知必是“动力之知”(knowing-to),[注]关于动力之知(knowing-to)、能力之知(knowing-how)、命题之知(knowing-that)三者的辨析与讨论,参见黄勇:《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抑或动力之知》,《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必驱使豪杰慨然行之,“惟以统纪不接为惧”。既以道统不接为惧,如碰到与道相合的见解,自然从善如流,开放包容,不问出处。如周行己虽从程颐游而服膺其理学(洛学),但同时对苏轼的蜀学也极为倾倒,“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浮沚集提要》)。另一方面,如碰到与道相违的见解,哪怕它是绝大多数人所持的见解,哪怕它是权威人士所持的见解,哪怕是最亲近人所持的见解,也是慨然不敢苟同。[注]赵钊已在硕士论文(董平教授指导)中指出,永嘉学派敢于批判否定、勇于开拓创新,不拘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赵钊:《王开祖〈儒志编〉研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44页)。与王开祖同时而齐名的丁昌期(经行先生)有子三人。“兄弟好古清修,自相师友,各以所得,质于其父,不为苟同。曰:‘此理天下所共,不可为家庭有阿私也。’”[注][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6,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317页。《四库总目》评薛季宣,言其持论“不必依傍先儒余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浪语集提要》)。汪循言王开祖“能不以近代儒宗之所习者为师,超然心领神会于千载之上”(《儒志编原序》),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王开祖超然心领神会于千载之上,故能不囿习见,不迷信权威,不以近代儒宗之所习者为师。不迷信权威,是英气,是独立人格在理智上的体现;不囿习见,是逸气,是风流人格在理智上的体现。逸气和英气令豪杰之士的理智德性呈现出别样的气象。[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伦理学和知识论不期然都发生了某种“德性转向”(virtue turn)或“德性复归”(virtue return),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与德性知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一时成为伦理学与知识论当代发展的新方向。德性知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为理智德性或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与知识相关的德性。德性知识论的两条不同的进路对理智德性的理解有所不同:可靠主义把它理解为认知能力(cognitive powers,包括准确的感知力等),而责任主义则把它理解为人格特性(character traits,包括认知勇气等)。可参见刘梁剑:《德性民主:在德治之外超越民主》,载方朝晖主编、翟奎凤副主编:《大同》,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美]迈克尔·斯洛特:《情感主义德性知识论:超越责任主义与可靠主义》,李妮娜译,《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逸者,溢也。牟宗三释魏晋名士之“逸”,其论甚妙:“精神溢出通套,使人忘其在通套中,则为逸。……逸则不固结于成规成矩,故有风。逸则洒脱活泼,故曰流。故总曰风流。风流者,如风之飘,如水之流,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适性为主。”[注]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78—79页。我们不难看到豪杰精神中的风流面向。豪杰挥斥逸气,溢出惯性思维框框和行为模式。王开祖明确主张溢出“庸庸之论”“规规之见”:“胶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轮不能致千里之远,拘庸庸之论者,无通变之略,持规规之见者无过人之功。《诗》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儒志编》)
汪循所讲的“近代儒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了孙复、司马光:“孙复号为名儒,而尊扬雄为模范。司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扬雄。”然则,从经学史上看,司马光疑孟,却参与开创了经学上的变古创新思潮。如皮锡瑞承王应麟说,指出“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具体言之,“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而北宋庆历年间,诸儒群起议经,包括欧阳修排《系辞》,[注]《儒志编》亦有一条辨《系辞》是否出于孔子,主张《系辞》为孔子所作,但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羼入,读者当善于辨析:“或曰:今之所谓《系辞》果非圣人之书乎?曰:其源出于孔子而后相传于《易》师。其来也远,其传也久,其间失坠而增加者,不能无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若此者,虽欲曰非圣人之言,可乎?其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幽赞神明而生蓍。’若此者,虽欲曰圣人之言,可乎?凡学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欧阳修、苏轼、苏辙毁《周礼》,李觏、司马光疑《孟子》,苏轼讥《尚书》,晁说之黜《诗序》,王安石作《三经新义》。[注][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0—221页。皮锡瑞所讲的“不凭胸臆”,在经学论域内意味着笃守旧说,其思维上的特点,则是不能独立思考,不能为自己思考。相形之下,司马光的疑孟,已表现出独立思考、凭诸胸臆的特点。而王开祖于此时尊孟,不是在经学上复古,固守汉唐旧注,而是进一步力图在思想上逆潮流而动,在思想范式层面开风气之新,表现出极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理论首创精神。
逸气不囿习见,英气不迷信权威,但它们还需要跟独立思考的能力相配合方能产生卓识睿见。若无独立思考的能力,则逸气、英气难免变异为狂气,发乎言则难免不流为疏阔之论。依《宋元学案》,王开祖能以豪杰之姿而“见道早”,在周敦颐、二程之先阐发天人性命之微。《学案》简择其金句曰:
先生见道早,所著有《儒志编》,言:“《复》者性之宅,《无妄》者诚之原。”又言:“学者离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恶?”又曰:“使孔子用于当时,则《六经》之道,反不如今之著。”又言:“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今将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开皇极之门,吾畏天者也,岂得已哉!”[注][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6,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318页。
《学案》表彰开祖以尊奉孔孟、讲明道学为己任,在实质内容上亦着力突显开祖在形上理论层面努力会通《易》《庸》,尝试对后世理学孜孜探讨的天人、性情关系给予精微的说明,得周敦颐《通书》之近似而开理学风气之先。
然《学案》所引过短,实不足以完整准确地反映王开祖的卓识。其性情论,如仅观《学案》所引“学者离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恶”,容易产生重性抑情的印象。实则,开祖的主张是不可贼情、情可动而不可乱:“学者之言曰:性善也,情恶也;莫善于性,莫恶于情。此贼夫情者之言,不知圣人之统也。夫情本于性则正,离于性则邪,学者不求其本,离性而言之,奚情之不恶?……贤者之于情,非不动也,能动而不乱耳。”(《儒志编》)开祖的观点,近似于程颐《论颜子所好何学论》“性其情”之说:有性则有情,“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注][宋]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文集》卷8,见[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7页。。又如“《复》者性之宅,《无妄》者诚之原”二句,开祖紧接着说:“《大畜》者道之归也,《颐》者德之施也。故君子复足以知性,无妄足以立诚,大畜足以有容,颐足以育物。知其复则能知性,知性则能立诚,立其诚则能畜德,畜其德则能发育万物而与天地配矣。《中庸》之言推乎人性賛天地而育万物,其原于此乎!”只取前二句,不啻断章取义,至多反映了王开祖三分之一的思想。开祖重心性内圣,同时也重事功外王,且心性涵养(成己)还必须展开在事功(成己成物)的过程之中。正是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永嘉学派特有的精神取向,同时也构成了永嘉学派豪杰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注]董平教授已指出,王开祖“要求个体不以其自身之道德学问的涵养为满足,而必欲将其内在之德性外向展现于经世事业的开辟之中,乃与后来崛起的永嘉学派是有点本质精神之共性的”(董平:《宋明儒学与浙东学术:董平学术论集》,第118—119页)。值得一提的是,叶适述永嘉学统,以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四人为典范:“永嘉之学,必克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宋]叶适:《温州新修学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8页)。叶适通过对四个人物的评价,实际上也指出,永嘉之学存在两个不同的思想面向:其一,治心修身的面向,其二,治世平天下的面向。可以说,叶适的分析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体现了史与思统一的特点。再如王开祖论以诚成人:“诚者,成也,所以成人也;人而不诚,禽兽奚择焉?……夫诚者,?也;诚于心,人莫之见也;接于物,亦莫之见也;由人服而物化之,然后见焉。及其至也,充乎天地之大,此其著可知也矣!”(《儒行志》)诚以成人(成就与禽兽有别的本真之人“人”),除了涵养心性之外(“诚于心”),还要发用显现为“成人”与“成物”(“人服而物化之”),及其至充乎天地之大,正是“推乎人性赞天地育万物”。
然则,正因为强调心性涵养(成己)必须展开在事功(成己成物)过程之中,王开祖所试图推动的新的思想范式似乎有别于宋明时期后来居于主流的理学思想范式。《学案》推许开祖“见道早”,汪循、四库馆臣推许开祖倡鸣道学,然开祖所见之道、所倡明之道学似有别于《学案》、汪循或四库馆臣所理解的“道”或“道学”。此中消息,耐人寻味。
四、失落的豪杰:孟子绝学,贵民轻君
王开祖毅然以讲明圣道为事,此等豪杰精神本身已是上接孟子浩然正气。然则,王开祖学宗孟子,所宗者何?上引性情说,实发孟子性善论之微。《学案》、汪循及四库馆臣当已见于此。然则,统观《儒志编》,其重心所在,却是抉发孟子贵民轻君、挺立士道尊严的思想。相对于儒家对于君臣大义的正统理解,孟子思想的这一面向无异带有浓厚的异端色彩。
开祖谓君子立身,或出或处,皆心系天下万民,并以此作为与君相交的出发点。心系天下万民,这是君臣相交的道义基础。就理想状态而言,“古之所谓君臣者,或相歌颂,或相称德。御下者不敢有其尊,奉上者不获惧其威,道交而心接,朝廷之间至和乐也”(《儒志编》)。臣非君私人所有,这是臣应有的自我理解;有此自我理解,自然不会以奴妾之道事君。孔子高弟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卫国内乱,子路怀着“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信念,为救孔悝而遇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在王开祖看来,子路为孔悝而死,并不算得其正命:“或曰:子路在卫结缨而死,正乎?曰:正则吾不知也。卫乱,子路可以无死。死而结缨,惜乎在不正之后也。不正之正,君子不由也。”(《儒志编》)
臣非君私人所有,这也是君应有的理解;有此自我理解,自然不会以奴妾之道待臣。“君不敢有也,故能成其道。”臣应心系天下万民,君也应心系天下万民:“或曰: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不亦乐乎?曰:中有乐乎耳,非乐乎有天下也。乐养天下也。”养天下乃是君的本分:“天之立君以养人也,非使之掊天下以养己也。”如君不能爱民,则无君之实,臣民不以君视之可也:“有民而不爱,非吾君也。辟如行路之人,为行路之人复仇,是亦必无而已矣。《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夫不施于人而人报之者,未之有也。”无君之实而居君之位,则是小人窃取天位,其内心必然“惴惴焉,惟恐人之一蹙而覆已也”。王开祖甚至说:“吾观孟子有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之说,则知神尚有责况于人乎。夫为人而无责,则是无耻也。无耻,斯禽兽夷狄矣。”这里可谓隐含了大逆不道的想法:人如不能尽责,则为无耻之徒;社稷之神如不能尽责,则变置社稷可也;君如不能尽责,造反可也。实际上,王开祖完全认同商汤吊民伐罪、诛杀暴君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其君残贼于天下,故不得已而伐之者,汤也。……伐暴吊民得天下,其心若汤可也。”(《儒志编》)
王开祖于臣谏君非、君纳善言之道再三致意焉。他对伯夷的隐居行为做了别致的理解,认为这是为了非武王而救万世之民:“伯夷自谋曰:……吾亦何为哉?吾其救万世之民乎?于是非武王而去之。武王犹非,况不至武王乎?其救万世之民也如此。”他讲“孝莫大于格亲之非”“罪莫大于逢亲之恶”,我们不难引申出,“忠莫大于格君之非”“罪莫大于逢君之恶”。实际上,孟子就说过:“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孟子·告子下》)王开祖对于“舜为天子,尽得天下之善言”心向往之。他称许东汉申屠蟠识时变,不像范滂那样天真妄议招来杀身之祸,其背后却隐含着一丝悲凉,臣不得谏君非、君无意纳善言,如之奈何。[注]《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记载申屠蟠对于太学清议不容于朝廷的先见之明:“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王开祖对此评论说:“知进退,识时变,临物而不惑者,其惟申屠蟠乎!太学之兴也,士之盛也,莫不振衣引足愿居其间,吾独指秦以为病焉。及群党坐于徽棘之中,我独优游于外,人皆以妄死,我独保正命以没,可谓独立君子达吉凶之命者也。”(《儒志编》)
贵民轻君、挺立士道尊严构成了豪杰更为深层的本质内容。自孟子没,此种思想久不见于中国传统,真绝学也。开祖能超然心领神会于千载之上,令贵民轻君、挺立士道尊严这一湮没已久的豪杰精神重新显露,真豪杰也。然王开祖所表彰的这一孟子绝学似乎一开始就落在汪循、四库全书馆臣对“豪杰”的理解之外。在此意义上,豪杰的失落,早已发生在从《儒志编》书前提要到《总目》提要的转变之前。
五、结语:试问豪杰今安在
唐宋两代,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结构等方面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如黄仁宇写道:“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到10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上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士人。”[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17页。与之相应,儒家学者积极建构新的思想范式。在儒学大转变之际,周敦颐、王开祖所开创的理路,似乎代表了重建思想范式的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周敦颐的进路为程朱陆王所光大,成为宋明理学的正统;而王开祖先于周敦颐所开创的进路虽有永嘉后学赞其成,然相对于程朱陆王仍属旁枝歧出。永嘉豪杰精神在事功中展开心性的面向似乎已多多少少失落在历史长河之中。然则,某一思想的意义,只有放在历史延长线上才能获得估定,而随着历史延长线长短之不同,其意义亦将有所不同,有时甚至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
居今之世,数百年来高歌凯进的现代文明已经到了某个临界点。展望未来,中国文明在挺立自信之后亟待进一步的觉醒?严中西之辨,忽古今之别,在人类的后经学时代以经学方式“弘扬”儒学,或为今日儒学发展最大之歧趋。人类整体如欲向死而生,必须在根本处转变思想范式,创造出有别于现代性的新的思想范式。时代召唤着豪杰之士毅然奋起,以其豪气、英气、逸气与卓识回应时代的召唤。
尝试论之。现代文明的转变,有待于意欲方向的根本转变,有赖于观物之法的根本转变。就前者而言,当代文明的曙光,有赖于人们从爱牡丹转向爱莲花?周敦颐《爱莲说》将莲花与富贵花牡丹区分开来,在世人通常追求的富贵之上建立另一种“至富至贵”,以道充为贵,以身安为富。得此富贵,则享孔颜之至乐,“常泰无不足”。如此,意欲的方向自然从“轩冕”“金玉”那里离开。如此,当下即是永恒,无需不断地进步到未来,不断地将当下牺牲在未来的黑洞之中。意欲方向的根本转变,必然引发观物之法的根本转变。孔子之乐水离不开他的观水之术。周敦颐庭前草不除,以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周敦颐之“观”物与孔老之观水相类,而与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看”物大不相类。这里似蕴含着两种分别,不妨以两种不同的“观法”与“看法”之分对应之。其一,狭义上的“观法”,我们将孔、老、周子之观物称为“观法”,而将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看”物称为“看法”,从而标识二者的根本差异。这样的观法可以联系“可观”“壮观”“观止”这样一些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沿用的语汇来获得某种理解的线索。观法常常关联着学于物(learn from things),而看法常常关联着研究物(study things),或了解物(learn about things)。其二,广义上的观法。我们把孔、老、周子之观物与现代人之看物之间的差异称为观法上的差异;而把孔、老、周子因观物而产生的差异,或现代人因看物而产生的差异称之为看法上的差异。易言之,在同一观法层面(perspective)可以有不同的看法(opinion),从一种观法到另一种观法(如从“以我观之”到“以物观之”到“以道观之”,如从孔、老、周子之观物到现代人之看物),意味着视角的根本转变,及主体心灵结构的根本转化。由此出发,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发现永嘉学派被忽略的豪杰面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