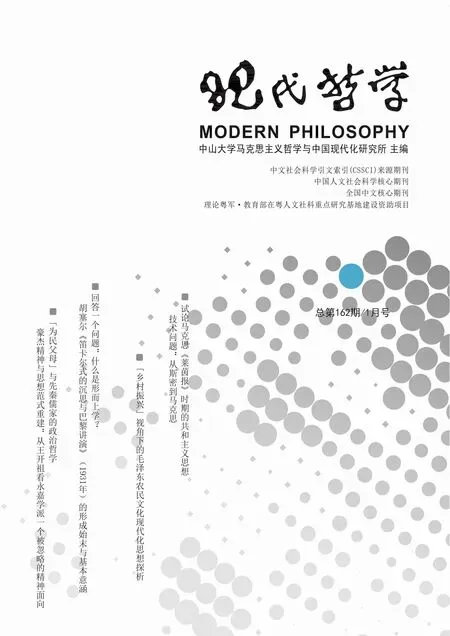马克思第一次宗教批判的背景、逻辑与意义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政治哲学解读
周 阳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1839年到1840年之间马克思为准备自己的学位论文所摘录的七册笔记。笔记二、笔记三中就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的评述(以下简称《评述》)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宗教问题给出的系统的理论阐述。[注][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另一方面,《评述》也有其独特的文献学研究价值。《评述》篇幅之长,远超笔记二、笔记三中的其他部分。《评述》中的一部分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5—88、923页。还被无名氏抄录在一张和笔记本里的纸一样的纸上保存了下来。一直以来,这份抄件都是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片断》发表的。但新MEGA编者指出,这份抄件并不是现存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可能是马克思在1839年底或1840年初草拟的一份独立的稿件的片断。所以,新MEGA编者就在一个新编辑标题下,将这一片断作为独立的部分发表了出来。[注]Karl Marx, “Fragment eines Entwurfs nach dem dritten Heft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 in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IV/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151-152.马克思曾希望将《评述》中某些部分进行加工后单独发表,他对《评述》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但是,《评述》相关内容最终却未能独立成篇,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中断”,对于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研究来说,这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第一次宗教批判的背景
尽管新MEGA编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指出,《笔记》的思想史语境是“围绕黑格尔体系的论战”,这是与魏斯(Christian Hermann Weisse)、小费希特(Immanuel Hermann Fichte)等人的思辨有神论的兴起相关的[注][德]陶伯特:《马克思1841年3月至1843年3月间世界观的发展问题》,熊子云编译:《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93—94页;[德]陶伯特、拉布斯克:《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新认识》,《哲学译丛》1979年第1期。,而他们背后更大的社会思潮则是位格主义与实证哲学(die positive Philosophie)。但除了布雷克曼、周嘉昕等少数学者外,很少有人继续循着这条思想史路标去探索《笔记》与位格主义、实证哲学等泛滥于19世纪初期德国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注]周嘉昕:《法、自我意识和国家——重访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黑格尔转向”》,《现代哲学》2017年第4期。姚远:《解读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9页。最近引起国内热议的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其背后的核心关切正是“位格”问题,而上述近代思想史背景,则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条件。[德]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徐震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正如黑格尔派米希勒(Karl Ludwig Michelet)所说:“关于上帝之人格的讨论已经主导了最近十年哲学史的发展”。人格或位格(person)问题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关注,是与复辟时代普鲁士的政治气候相关的。为了对抗革命时代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复辟时代的保守主义者纷纷投向了位格主义的政治神学。位格主义不等于向传统的封建主义的回归,它不再强调建立在封建等级关系上的共同体温情主义,而强调君主的绝对威权。在神学上,位格主义强调上帝的位格的根基性意义,强调它是超越于人类之上的个别性的实体,这样的上帝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在位格主义者看来,人是对上帝的模仿,因而人也是个别性的,也就是说,个人与个人之间、人与世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绝对超越的(人对自然的这种绝对关系正是财产权的神学基础)。只是人对上帝的模仿也仅仅是一种类比,在上帝与人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在位格主义者看来,上帝与个人的这种类比与差异也同样体现在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当中,君主就是尘世中的上帝,君主是通过颁布上帝的神圣意志而成为国家的化身,它对臣民具有绝对的威权。在这个意义上,位格主义政治神学就呈现为宗教、君主制、私有财产三者神圣的三位一体。[注][美]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13、16、129页。[英]桑希尔:《德国政治哲学:法的形而上学》,陈江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 266、270—271 页。
谢林的实证哲学(或译为“肯定哲学”)与位格主义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注][美]蒂利希:《蒂利希论谢林选集》,杨俊杰编译,香港:道风书社,2011年,第53页。谢林指出,实证哲学不像黑格尔的“否定哲学”那样,将现实当作思想的产物,而应该反过来将现实当作思想的起点,但这里的现实也非日常经验中被给予的存在,而是必须从上帝的、个别的“绝对意志”出发来思考的超越存在的东西。[注][德]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60页。[美]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5、66页。王建军:《灵光中的本体论:谢林后期哲学思想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3—94页。将谢林实证哲学政治化的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的国家哲学。施塔尔反对作为自然法学说、契约论的基础和表现的原子式个体主义,因为个体主义抹杀了上帝与人、君主与臣民之间的本体论差异。施塔尔认为,上帝并非一个理性实体,而是一种位格化的绝对意志,这种绝对意志才是人类生活与人类政治的统一基础,是合法的与恒久的政治秩序的来源。[注][美]特夫斯:《法律的内在发生与超验目的——萨维尼、施塔尔与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意识形态》,载吴彦编:《观念论法哲学及其批判——德意志法哲学文选(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193—195页。
面对位格主义、实证哲学的冲击,青年黑格尔派起来捍卫一种普遍主义的“主体”概念,以此来“反对将‘位格’这种人的特殊属性当作主体本身”的观点,即以“主体”概念反对 “个体”概念。[注][英]桑希尔:《德国政治哲学:法的形而上学》,陈江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66、271 页。如上所述,位格概念与特殊性、个别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而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这种意义上的“具体人格”甚至并不等同于上帝,因为它既然与“特殊性”相关联,就只能是一种概念的抽象产物,或者更具体地说,位格主义在这里事实上进行了多重的抽象与颠倒,位格其实是从人这里抽象出来的一种属性,而位格主义者却将这种人的属性直接等同于上帝的属性,进而甚至将上帝本身等同于他的某一属性。[注]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及至马克思探讨“主谓颠倒”问题的历史语境。徐长福:《马克思哲学中的“主谓颠倒”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马天俊、孙杨:《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一个隐喻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因此,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位格的这种特殊性、个别性就与上帝的普遍性、人的普遍性相悖了。
二、第一次宗教批判的准备
马克思与位格主义、实证哲学的思想关联可能早在其“柏林法学计划”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到《评述》时期,他才藉由对普鲁塔克神学的摘录和批评等,对位格主义、实证哲学进行了直接批判。笔者认为,七册《笔记》的思想认识过程是分成三个阶段的:笔记一到笔记三是一个阶段,笔记四到笔记五是第二阶段,笔记六、七以及几个增补片断属于第三个阶段的文本。[注]周阳:《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最初探索——〈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与〈博士论文〉中的“时间”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评述》处在《笔记》的第一阶段,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伊壁鸠鲁原子的固有矛盾,即原子本质的辩证运动与其固化的表象形式、现象形式之间的冲突,具体地说,这是原子本质的普遍性与其存在形式的个别性之间的矛盾。伊壁鸠鲁原子普遍性与个别性之间矛盾问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为批判普鲁塔克及其所影射的位格主义在普遍性与个别性、神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所做的理论准备。
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科本)一样,马克思也强调伊壁鸠鲁哲学中普遍性的维度,尽管其普遍性与个别性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在笔记一中,马克思也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仅仅是停留于“表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38、39、41页。——在黑格尔那里,“表象”仍然没有上升到真正的“观念”[注][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9、70页。——马克思也同样指出,这种表象哲学与伊壁鸠鲁强调的“感性确定性”相悖:就其“感性确定性”而言,“个别”(“最抽象的个别之物是原子”)是相互外在的,而在这里,“表象”则已具有(虽是形式的)“普遍性”,在伊壁鸠鲁那里,就是“观念性”。在《笔记》当中,“观念性”是与“普遍性”等值的。不过,在黑格尔看来,伊壁鸠鲁只是将感性确定性与表象之间、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直观地呈现在那里,而正是由于这种直观性,伊壁鸠鲁事实上是直接退回到了感性、直觉、个别性的立场上去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则认为伊壁鸠鲁事实上直接面对了上述矛盾,并且主张扬弃“感性确定性”、个别性,走向“观念性”、普遍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马克思首先是在对原子体积进行分析时,发现上述“观念性”、普遍性的:原子是有体积的,是可分的,既然可分,那就说明原子还可以分为比它更小的各个部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比最小还小的自我否定性,就是“观念性”,就是普遍性。然而原子的这些“部分”却是作为某种“内部存在的共性”“同时”并存着,这种“同时性”就成了“与表象相类似”的东西:因为“比最小更小”是非经验性的,是不可能在感性时空中存在的。因此,在体积规定的分析当中,伊壁鸠鲁原子概念的根本矛盾就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原子一方面具有观念性、普遍性这样的否定性维度,这种否定性从根本上说是对自身存在基础的彻底否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原子自身的分解,是原子向更进一步规定发展的出路;但另一方面原子又具有直接存在的特征,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普遍性与个别存在性的矛盾贯穿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始终。
三、第一次宗教批判的展开
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虽然始终未能解决普遍性与与个别性之间的矛盾,但伊壁鸠鲁直面矛盾的态度本身就值得赞赏;相反,普鲁塔克则回避了矛盾,他始终站在“普通人”、“经验的个人”的立场上,将普遍性与个别性、本质与经验、神与人都毫无批判地混同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位格主义、实证主义就是当代的普鲁塔克主义。
在关于对神的恐惧问题上,普鲁塔克认为恰恰是因为对神及神罚的恐惧,人不敢为恶。普鲁塔克论述的是经验的恐惧,是“经验的恶”,经验的恶的实质就在于个人沉溺于自己的经验本性而“违背自己永恒的本性”,并进一步将这种“永恒的本性”经验化,即置于“孤立状态之中、存在于经验之中”,视为“自身之外的经验的神”。在这个意义上,“神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集经验恶行的一切后果之大成的共同体”。普鲁塔克重视人与神的分别,但这种分别本身却不过是人自身的“经验”规定而已,也就是说,普鲁塔克在把神变成人的同时,也就把人的特定经验变成了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页。。
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也有同样的伦理主张,即“勿行不义,免得经常担心受到惩罚”,但伊壁鸠鲁得出这一主张的依据却与普鲁塔克不同:前者把这种个人同不动心的“内在关系”,视作同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神的关系,于是普鲁塔克的 “内在的恐惧”在这里就被“置入神的遥远的意识中去”了,它被看作已经预先存在于这一意识中的某种状态,而 “状态”在伊壁鸠鲁那里本身就是无关的偶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页。
马克思对这场论战作了总结:伊壁鸠鲁关心的是神,或者说是普遍性,而不是人,不过,伊壁鸠鲁强调的是“无差别性”,伊壁鸠鲁的神就是“直接同一”的,是对一切个人的规定性、判断的彻底否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伊壁鸠鲁“在神身上发现了象虚空一样的纯粹的‘宁静’”。相反,普鲁塔克 “感兴趣的只是个人,而不是神”,但普鲁塔克保留了神的规定与人的规定之间的差别。普鲁塔克重视这种差别,不过,他只是将这些“差别”毫无批判地混杂在一起,进而将这种“毫无批判地、经验地混杂”本身视为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84、85页。在普鲁塔克这里,快乐与痛苦、善与恶都是这样混杂在一起的,而最能展现这种“混杂”性的,毋宁说就是普鲁塔克对生与死的混同:普鲁塔克试图给群众以“最甜蜜的希望”,即灵魂不死的允诺,但普鲁塔克的人不过是“经验的存在”罢了,它沉溺于利己主义、经验主义的“自爱”之中,并不能面对“死亡”(人的本质问题)而执着于“原子论形式”的个人存在,而这样的“经验存在”其实也无所谓存在的内容,而仅仅执着于“存在的个别形式”,只要存在就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7、78、88、89页。
在马克思看来,和普鲁塔克一样,位格主义、实证哲学貌似关心经验的个人,但其经验个人概念本身却只有通过设定超验的神才能成立,而他们所谓超验的神也无非来源于人的特定经验(譬如自私、自爱)的设定。
四、第一次宗教批判的限度
尽管在《笔记》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的神学论争,甚至希望将《评述》单独成篇,但在《博士论文》中,他完全放弃了《评述》的论述结构。笔者认为,这和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期待与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相关,即依靠伊壁鸠鲁的朴素辩证思想,无法从原子的简单规定发展到更进一步的规定。所谓“进一步规定”的最终目标是推出“哲人”规定:“哲人”规定“最彻底地表现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中”,直到笔记七,马克思仍希望能从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推导出伊壁鸠鲁自己的“哲人”概念,虽然这始终未能实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63—169页。
马克思认为,希腊哲学就是围绕“哲人”转的,它既以哲人始,又以“在概念中表达哲人形象的初次尝试”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3页。尽管如此,哲人规定的重要性却并没有引起重视。[注]新MEGA编者认为关于“哲人的规定”的讨论与伊壁鸠鲁哲学研究无关。“Hefte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 in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IV/1, Berlin:Dietzverlag,1976, s. 726. 转引自鲁路:《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概念”只能是在“概念判断”意义上才能被理解。“哲人”是实体的观念体现,但同时是对这种实体的“认识”的独立化。“哲人”规定讨论了实体与独立化了的 “对实体的认识的形式”(即观念性)这两者之间不断进行统一与分裂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最高阶段就是实体与观念性、普遍性之间的自由关系。(1)在苏格拉底之前,尽管观念性本身发展到活生生的理论,即“主观精神”,“观念性本身通过自己的直接行使即主观精神而成了哲学的原则”,但观念性本身还是独立的抽象,它是与实体外在对立的。(2)到了苏格拉底,实体与观念在运动中达成了统一。
但概念的辩证运动并不会就此终止,这个统一体由于概念的运动又会陷入新的分裂:“由于和实体相对立的是它自己的观念性,所以实体分解为无数偶然的有限的存在和成规。这些存在和成规的合理性,统一性,同实体的同一性,转化为主观精神。因此,这种主观精神本身就是实体的保存者,但是这个观念性是与现实相对立的,所以它在头脑中客观地表现为应有,主观地表现为意向。这种自己内部的观念性的主观精神的表现是概念判断[das Urtheil des Begriffs],对于这种判断来说,个别事物的标准是自身中被规定的东西,目的,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6—67页。马克思直接使用了两次“概念判断”(das Urtheil des Begriffs)。Karl Marx, “Hefte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 in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IV/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s. 42-43.
所谓“概念判断”,黑格尔的界定是:“概念的判断以概念……亦即以普遍事物和它的全部规定性为内容。……主词,(一)最初是一个体事物,而以特殊定在返回到它的普遍性为谓词。换言之,即以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否一致为谓词,如善、真、正当等等”[注][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3—354页。,“概念在其中是基础,并且因为它在与对象的关系中是作为一个‘应当’,实在对这个‘应当’可以适合,也可以不适合。”[注][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33页。在概念判断之前,主观性与实体或者说主语与谓语之间已经通过在主语、谓语与系词三个层面上进行的判断活动实现了统一,建立了客观的概念,但这个统一的概念仍需进行自我判断:判断的主语与谓语都是或者包含了那个统一的概念,因此是概念自己判断自己的个体状态(即主语)是否符合概念本身(谓词就是概念的个体与概念本身的关系),如若符合即 “应当”、“善”,也就达到了主体与实体在更高的统一,建立起一种更高的普遍性。[注]Ioannis Trisokkas, Pyrrhonian Scepticism and Hegel S Theory of Judgement:A Treatise on the Possibility of Scientific Inquiry, Berlin: Brill, 2012, p. 322.
在马克思这里,(1)在古希腊实体中,个体与实体已经实现了统一,这就是概念判断的第一阶段,即主词(个别事物、主观精神)通过中介活动与谓词(实体)初步统一的阶段;(2)但概念自身的运动仍然会将自身推向第二阶段:作为主体-实体统一体的希腊伦理实体仍然会走向自我分裂,作为这个统一体的个体方面的观念(即苏格拉底)仍然需要对它自身与作伦理统一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决断,这是“应当”、“善”的问题。
由此看来,伊壁鸠鲁原子论规定的不足就非常明显了。“哲人”是由“实体”概念本身发展出的,是实体的观念体现,在概念运动的更高阶段,“哲人”会和“实体”相统一,但随着概念的发展,“哲人”还要批判“哲人-实体”这一统一体。而在伊壁鸠鲁原子规定虽具否定性,但却是抽象的,它根本无法向更进一步规定发展,不存在发展为“实体”的可能,更不用说发展为“哲人”概念了。
五、第一次宗教批判的意义
在《笔记》第一阶段,由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期待与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解决,他在批判普鲁塔克及其隐射的位格主义、实证哲学时,没有能从伊壁鸠鲁哲学本身推导出一种更好的哲学蓝图,因此,第一次宗教批判未能最终完成,这是他最终没有将《评述》单独发表的一方面原因。而《评述》没有单独发表的第二方面原因则是马克思对批判对象位格主义、实证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新认识是在他摘录笔记五时期形成的,时间在1839年8月中旬左右。这时,“围绕黑格尔体系的论战”有了一些新动向:部分黑格尔派向实证哲学、位格主义妥协,导致黑格尔派的分裂,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839年卡尔·舒伯特(Karl Schubarth)的反黑格尔宣言。[注][美]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由于黑格尔派的分裂,使马克思认识到,原来被视为普遍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其自身逻辑当中竟然也暗含着向位格主义、实证主义转变的危险;而从正面看,实证哲学本身因而也就是可能在观念哲学的框架内解决的问题了。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在笔记五中的哲学史论述就不是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它是马克思的“借古喻今”,是对当时思想斗争形势的理论总结。它将黑格尔派哲学在当时论战中的立场类比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上的处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四部分第一卷前言》,姚颖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8页。,阐发了黑格尔“自由派”(马克思也是其中一员)的理论立场,即对普遍性、主观性的追求;进而在哲学史意义上,解释作为主观性、普遍性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柏拉图哲学何以会转向基督教实证主义,以此回应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的《柏拉图主义中的基督教成分》。
在笔记五中,马克思重申了笔记二中的“概念判断”逻辑:当作为个别性的苏格拉底作出关于实体的概念判断,他就会被判断为罪人,因为目的、善——即实体与主观性的关系——对于实体来说就是法官,实体在这种自我判分中走向死亡。到了柏拉图那里,实体本身就以观念的形式进入到柏拉图的意识里,只是这种“实体与观念的统一”仅仅是在“理念”层面上的,“善、目的”等观念变成了“翱翔于现实之上”的理念,因此,柏拉图不仅将观念本身的运动性排除掉了,观念与实体也就变成不相联系的两个领域。在柏拉图那里,个别性的“善”重新变为“一般的和观念的活动”,而这种一般的和观念的活动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则又成为“概念的单一性”,于是新一轮的“概念判断”又展开了。首先,在前一阶段,“哲学在自身中上升到具体,把抽象的原则结合成统一的整体”,这是“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的环节,即“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但这一整体是内部分裂的,因为这一整体的精神是自由的,既然其普遍性达到了极点,那么其分裂也是普遍的,“只有当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是整体的时候,世界的分裂才是完整的”,精神在这一“整个机体的具体形态中形成差别”。作为这一分裂的结果,“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以前作为成长过程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已变成了规定性;而曾经是存在于自身中的否定性的东西变成了否定”,这里的否定、主观性已经具有自身独立的形式,它就“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外部世界”,而“转变为与现实的实际关系”,这种具有独立的形式的个别性的主观哲学就是伊壁鸠鲁哲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66、67、70、135、138页。
在接下来对鲍尔的批评中,则可以看到,由于“围绕黑格尔体系的论战”新动向的刺激,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哲学史的认识:在笔记五中,柏拉图哲学本身是观念哲学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实证”倾向本身也不再是与观念性外在对立之物,而变成观念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本来,哲学与宗教是根本对立的:一方面是哲学意识,另一方面是“经验个人”,两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尽管作为哲学发展最高阶段的柏拉图哲学的宗教性最深刻,而作为宗教发展最高阶段的基督教的哲学主观形式最高,但在这两者中,哲学与宗教的对立、冲突却却是最强烈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8、139、141—142页。既然对立如此明显,为什么鲍尔的柏拉图“要竭力给哲学所认识的东西找到一个‘实证的’,首先是神话的根据呢”?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因为柏拉图对绝对的东西不能作充分的否定解释,不得不代之以实证的解释,其形式就是神话和寓言。在哲学作为一方,实证的现实作为另一方,同时实证的现实又必须保留下来的地方,“实证的现实就成了一种中介[Medium]”[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4页,译文有改动。Karl Marx, “Hefte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 in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IV/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105.,调和哲学与实证之物,这就是神话,但事实上,哲学、绝对的东西在这种中介中与自身相异,而实证的东西也由于哲学而与自身相异。
简言之,马克思对“实证哲学”的批判就在于后者将“实证的现实”这种非中介的东西作为中介,试图调和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我们看到,如果说在第一次宗教批判中,普鲁塔克的“个人神学”、实证哲学与伊壁鸠鲁的普遍哲学、观念哲学还是一种外在对立关系,那么到了笔记五,马克思就不再停留于对实证哲学的外在批判,他试图解释实证哲学产生的根源,认为它是观念哲学的产物,因而也就能为观念哲学所克服——第一次宗教批判的理论任务才能完成。[注]新MEGA编者没有理解马克思批判实证派的动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四部分第一卷前言》,姚颖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由于观念哲学与实证哲学的这种内在亲缘性,使得马克思开始反思主观哲学(即黑格尔哲学)本身,进而重新研究、审视黑格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这就开启了马克思本人一个新的思想进程。[注]周阳:《异化逻辑与事件哲学的相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
六、结 论
马克思的第一次宗教批判正面批判了位格主义、实证哲学这类德国复辟时代的政治神学,它并没有抽象地讨论宗教问题,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的,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封建王权、神权思想斗争的坚决性。尽管第一次宗教批判还存在外在批判的痕迹,但是,通过对第一次宗教批判本身的反思,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其批判对象实证哲学的产生本身有其必然根据,由此,马克思也开始重新审视作为其批判工具的(黑格尔)观念哲学,这为他此后发现并批判黑格尔观念哲学本身的“实证”倾向(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对普鲁士王权的辩护)做了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