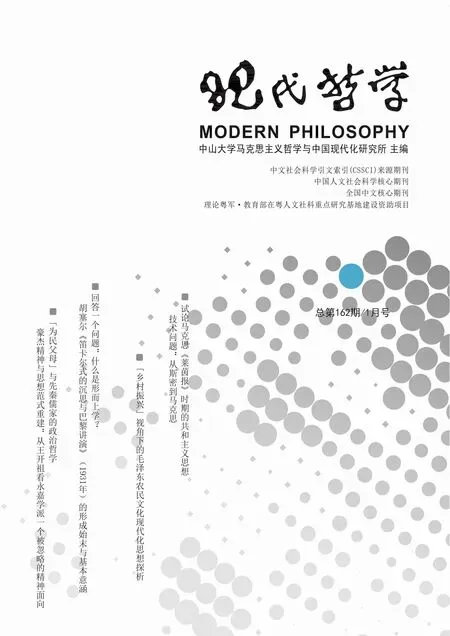人生计划、运气与美好人生
邓伟生
一、引 言
受教育的人早年可能都写过“我的志愿”之类的作文,现代大学教育也常常强调要培养学生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鼓励学生尽早做好职业规划等等。职业选择,恋爱或婚姻的打算,生儿育女的计划,购买人寿保险或教育保险等等,说到最后,都是对人生作某种规划。这些日常想法的背后,似乎都有一个预设:一个人,特别是成年人,唯有尽早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好好规划,然后努力实践,才有可能过上美好的人生(good life)。
这种预设的理据,或许可以在罗尔斯《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注]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以下文中括号内的页码,皆指此书。译文则同时参考了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和谢延光译《正义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而作了修改。中的价值理论(theory of good)[注]在本文中,我们把good与value视为可以互换的词语,而good按文意翻译成“好”或“价值”,不采用通行的“善”,是因为在现代汉语里后者主要指道德上的好。找到完整的论述。根据他的理论,一个美好的人生是按人生计划来过的,而好的人生计划,就是一个人在有充分信息和具有慎思理性(deliberative rationality)的情况下会选择的人生计划,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生计划。一个人如果在实现他理性的人生计划,那就是过着美好的人生,不过,即使他最终不成功,他也没有理由后悔,也没有理由责备自己,而可说是无负此生。
罗尔斯的理论,受到过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大致可分为强和弱两种:一,人生计划这观念本身即是错的。人生一计划就不可能过得好。这是强的批评。拉莫尔(C. Larmore)的部分批评就是这样[注]Charles Larmore, “The Idea of a Life Plan”, Social Philosophy &Policy, Vol.16. No. 1, 1999, pp. 96-112.。二,人生计划观念本身没有问题,但某种人生计划理论有问题,如罗尔斯的理论。这是弱的批评。威廉斯(B. Williams)的批评[注]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in his Moral Luck: Philosophical Papers 1973-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0-39.和拉莫尔的部分批评可以归入此类。本文尝试论证,强批评很难成立,弱批评则有些能被罗尔斯理论恰当回应,而有些则是有效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放弃罗尔斯的理论。我们认为,某种特殊的人生计划理论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说是有理论困难的,例如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但这并不表示人生计划本身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二、罗尔斯论理性的人生计划与美好生活
一样东西为什么是好的?特别是它为何对一个人而言是好的?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罗尔斯首先用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好或有价值。他认为,对“好”(good)的定义有三个阶段:
1. A是一个好的X,当且仅当,在已知人们使用X的特定目的或意图(以及任何其它恰当的附加因素)的条件下,A具有人们能理性地要求于一个X的那些属性(程度高于平均的或标准的X)。
2. A对于K(此处指某个人)是一个好的X,当且仅当,在已知K的境况、能力及人生计划(他的目的系统),因而考虑到他使用X意图去做的事,或任何其它恰当的附加因素的条件下,A具有K可以向X理性地要求的那些属性。
3. 与(2)相同,但要加上一个条件,即K的人生计划,或与当前情况有关的那部分人生计划,本身是理性的。(pp. 350-1)
例如,一只好的表,就意味着它具有一些属性——这些属性是人们可以理性地要求一只表应该具有的,如计时准确、轻、耐用等等,并且它们超过平均水平。
罗尔斯对定义的第一阶段作了几点说明:首先,一般来说,如果人们的利益所在(interests)和环境相似,从而能够确定公认的标准,那么说某个东西好,就是传达了“有用的信息”(useful information)。这种价值判断是有客观性的。其次,只有在某种背景即先决条件下,我们才说某些东西是好的,而用不着进一步说明。基本的价值判断是按照人的视角做出的判断,而人的利益所在、能力和环境都是已知的。如果出现复杂的情况,那个东西是为了用于特定的需要和情况的,我们就转向这个定义的第二阶段。再次,这个阶段对好的定义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好的间谍,即是说,如果考虑到间谍要去做的事的话,他具有可以向一个间谍理性地要求的那些属性。这并不意味着间谍所做的事是道德上正确的。(pp. 351-4)
以上只讨论了关于好或价值的定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还没有涉及到目的的理性问题。然而,我们常常要评价一个人的欲望是否理性,第三阶段考虑的问题是把关于好或价值的定义应用于人生计划。为了使问题简化,罗尔斯从一对定义开始:
第一,一个人的人生计划是理性的,当且仅当(1)在理性选择原则适用于他的情况下,他的人生计划是符合这些理性选择原则的,(2)在符合这个条件的那些计划中,他以充分的慎思理性来选择的正是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他在选择时充分认识到有关事实,并对选择的后果经过了仔细的考虑。第二,如果一个人的利益和目标是理性的,当且仅当,它们能够得到对他来说是理性计划的鼓励和保证。(pp. 358-9)
依据上述定义,需要说明的是以下这几个概念:一、理性的计划;二、理性的选择原则;三、慎思理性。
罗尔斯认为,理性计划对关于好或价值的定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理性的人生计划定义了一种基本的视角(basic point of view),据以做出所有有关特定个人的价值判断,并最后使这些判断协调一致。(p. 359)对于理性的计划,罗尔斯做了几点说明:
第一,与时间结构有关。一个人生计划会指向很遥远的将来,在时间上越往后,计划就越不具体。并且,我们计划时要对未来不确定的事情做准备。一个理性选择原则就是一个延迟 (postponement):如果我们希望在将来做几件事之一,但现在不知该做哪件,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我们现在的计划,就应该使这几件事都有被选择的余地。罗尔斯并不认为一个理性计划就是整个一生行动的详细蓝图。它是由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计划组成的,比较具体的子计划要在适当的时候补充。(p. 360)
第二,一个理性的计划是有一定的结构特性的,它会反映各个层次的欲望,从比较一般的到更具体的欲望(from the more to the less general),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制定计划有些像制定时间表(schedule)。我们把自己的活动按照某种时间顺序来安排,以便一系列互相有关的欲望能以有效而和谐的方式得到满足。我们慎思的目的,是找到能够最好地安排我们活动的计划,以便卓有成效地达到我们的目标。在一个理性计划中,会剔除那些妨碍其他目标的欲望,会鼓励本身令人愉快并有助于实现其他目标的欲望。因此,一个理性计划是由按照某种层次而适当安排的子计划组成的,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考虑了互为补充的比较长远的目标。由于只能够预知这些目标的大致轮廓,那些子计划的具体部分是随着我们实施计划而最后独立确定的。在较低层次进行的修正和改变,通常不会影响到计划的整个结构。(pp. 360-1)
罗尔斯的理性选择的原则(principle of rational choice)意味着什么?他列举三个选择原则,用它们最终取代意思不够明确的理性的观念(conception of rationality)。假定这是一种短期选择的情况,例如制定度假计划,那么就有三个理性的选择原则:第一个原则——有效手段(effective means)原则:如果一个人接受达成某个目标是可欲的,并且他可以从两种达成目标的方法之间作选择,其中一个较另一个更为有效,假设其他的一切相同,则选前一种方法是更合乎理性的。这个原则也许是理性选择的最自然的标准。第二个原则——包容性原则(principle of inclusion):如果做A与B两个短期目标,A能够达成甲乙两个目的,而B只能达成甲一个目的,则一个理性的人会做A而不做B。举例来说,假定我们正在计划一次旅行,我们必须决定是去罗马还是去巴黎。两个地方都去看来不可能。如果经过认真的思考,我们能够在巴黎做我们希望在罗马做的一切,同时还能做些别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巴黎。第三个原则——或然率较高的原则(greater likelihood):假定两个计划实现的目标大致相同,那么,哪个计划更有可能实现,就应该采用哪个计划。(pp. 361-2)
现在,让我们考虑长期计划,甚至是人生计划。这种情况下的包容性原则有如下述:如果某个长期计划能鼓励和满足另一个计划中的全部目标,同时又为鼓励和满足另外的目标创造了条件,那么,这个计划就比另一个计划好。罗尔斯认为,应该选择这种包容的计划:它包含了第一个计划的全部目标,同时还包括了至少另外一个目标。如果把这个原则同有效手段原则结合起来,那么,它们就能一起把理性定义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选择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有效手段,而如果这种愿望能够实现,则还要使广泛多样的目标得到发展。(p. 362)
最后要说明什么是慎思理性(deliberative rationality)。罗尔斯对慎思理性的说法是:“一个人具有慎思理性,当且仅当,他在选定计划时,会根据全部有关事实,通过认真的思考,考虑了执行这些计划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确定最能实现他的基本欲望的行动方针。”
按照这个定义,有以下几个假定:
1.他的计算和推理都没有错误,事实也得到了正确的评估。
2.他对于自己实际需要什么没有任何误解。就大多数情况来说,在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时,他不会觉得但愿他做了别外的事情。
3.他对自己的情况和执行每个计划的后果所具有的知识是准确的和完全的。应该考虑的有关情况也无一遗漏。
这样,一个人的最佳计划也就是他在掌握全面知识的情况下可能采用的计划。这是他的“客观上的理性计划”(objectively rational plan),它决定了他的真正的好(real good)。与此相对照,如果当事人尽最大努力做到了一个有理性的人以他的知识所能做到的事情,那么,他所采用的计划就是“主观上的理性计划”(subjectively rational plan)。(p. 366)他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但是,果真这样,那是因为他的信念有错误,或者知识不够,而不是因为他草率地判断,也不是因为他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要。就这种情况来说,一个人是不应该由于他的表面的好和真正的好(apparent and real good)的任何差异而被批评的。(pp. 366-7)
慎思理性明确之后,罗尔斯引入了一个有关动机的原则,用来说明一个人会选择什么样的目的作为他的理性的人生计划。这个原则他称之为亚理士多德式原则(Aristotelian Principle):“在其他条件相等时,人们喜悦于(enjoy)运用他们的实现了的能力(realized capacities)(他们的先天的和后天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实现得越多,或者说,这些能力越复杂,这种喜悦的程度就越高。”(p. 374)这个原则背后的直觉观念是,如果人们对做某件事越熟练,他们就越喜悦于做这件事,如果有两种活动他们能做得一样好,他们总是选择那种需要更全面、更复杂、更敏锐的辨别力的活动。例如,国际象棋是比跳棋更复杂的游戏,需要更高的能力,因此,如果某个人都懂得它们,他一般会宁愿下国际象棋,而不愿下跳棋。为什么亚理士多德式原则是正确的呢?罗尔斯的理由如下:首先,复杂活动之所以更值得喜悦(enjoyable),是由于它们满足了体验变化和新奇的欲望,并给发明创造留下了空间。其次,复杂活动还产生了期待的快乐和惊喜,而且活动的整个形式(overall form of the activity),它在结构上的展开(its structural development),也常常是激动人心和美的。最后,复杂的活动容许甚至要求个人的风格和个性的表现,因为不可能人人都用同一种方式从事复杂的活动。罗尔斯认为,以上每一个特征都从国际象棋得到充分的证明,国际象棋大师们在下棋时都有独特的风格。(pp. 374-5)
总的来说,一个理性的人生计划就是在满足了上述那些条件即理性的选择原则、慎思理性和亚理士多德式原则的情况下会选择的计划。因而,罗尔斯强调,对价值或好的判断标准是“假然性的”(hypothetical)。(p. 370)如果问,做某件事是否对我们好或有价值,答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以慎思的理性所选择的计划。
罗尔斯认为,理性的人生计划有一个特征,就是一个人在执行这个计划时不会改变心意,不会但愿自己做的是别的什么事情。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后悔(regret)采用了这个计划。(p. 370) 一个理性的人生计划,是符合理性的选择原则和慎思理性的,那么,罗尔斯认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不管这个计划最后结果如何,他都没有理由责备自己,也没有理由感到后悔(regret)。因为只要他的人生计划是理性的,他当时做决定时就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不如意,那并不是他的过错,不是他的责任。(pp. 370-1)
罗尔斯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理性的人生计划进行顺利,他的比较重大的愿望正在实现,同时他又确信自己的好运(good fortune)将会持续,那么他就是幸福的(happy)。既然人的天赋和环境等等的不同,决定了可以理性采用的计划因人而异,不同的人就从做不同的事中找到了幸福。一个人能否做到这些,很依赖于他所处的环璄。幸福的实现需要一定程度的好运。(p. 359)
按我的理解,罗尔斯有关理性的人生计划与美好人生(幸福)的立场可以这样概括:一个人如果按他理性的人生计划来生活,并且能够实现这个计划和得到好结果,那么,他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而一个人如果按他理性的人生计划来生活,但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而不能够实现这个计划或得不到好结果,那么,他说不上有一个美好人生,但这种人生或许可以称为“无悔的人生”或“值得过的人生”。
三、对罗尔斯的批评
在讨论对罗尔斯理论的批评之前,应先尝试指出他的理论的几个优点。首先,他的理论很容易解释人们行动的动机。设想一个外加的或独立建立起来的客观理论,它会告诉你什么是你的美好人生,但你却可能不感兴趣,因为你对这种人生并不喜欢,对你没有吸引力。对你是美好的人生,你却没有欲望去追求,这似乎有点奇怪,而且很难说明你为什么有理由追求它。但按照罗尔斯的理论,一个对你而言是美好的人生,就是你会理性选择的人生,那么,上述难题就不再存在。其次,他的理论与价值多元主义兼容。由于天赋和环境的差异,每个人的理性人生计划各有不同,因而可活出不同却一样有意义的人生,亦即有不同的美好人生。第三,他的理论尊重个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这个现代的基本价值,因为选择是个人自主的内在构成要素。一个理论给予选择关键地位,亦即给予个人自主关键地位。第四,但与此同时,它不是纯主观的理论,因为所加的理性选择的条件以及亚理士多德式原则,都规定了这个选择不能是完全主观任意的。最后,他的理论似乎能说明日常经验中人们对那些悲剧英雄或努力却最终失败的人的评价。例如诸葛亮,如果说他的人生计划是帮助刘备复兴汉室,那么,他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人们好像也不会觉得他的一生就是没意义的,不值得过的。自然,他也不用过于自责。
虽然有这些优点,但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仍受到不少批评。上文已提到,这些批评可分为强和弱两种,其中强批评很难成立,而弱批评则有些可以成立,有些能被罗尔斯理论恰当回应。我们的结论是,某种特殊的人生计划理论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说是有问题的,例如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但这不表示人生计划本身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下面先讨论拉莫尔提出的强批评。拉莫尔认为,人生计划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人生不是计划的对象。人生计划的错误,关键在于它“对人生的基本态度”(the basic attitude toward life)。人生计划的想法,有一个主导性的假定(guiding assumption): “我们应该掌控我们的生活,尽最大可能把它纳入我们控制之下。”(we should take charge of our lives, bringing them under our rule as best as we can)但拉莫尔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按照计划去过,那么有一些好东西就会远离他。除了按计划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一个有些“预期之外的价值”(unexpected good)[注]郝忆春副教授曾建议把unexpected good译作“不可预期的价值”。我经过考虑,认为“不可预期”有点太强了,因为这里的“不可”只有解作“不可能预期到”才能与文中的翻译区别开来。但从拉莫尔文中用养育小孩作例子来说,我想,养育小孩让一个人认识到预期之外的价值,这很好理解,但说她“不可能预期到”这种价值,则似乎太强了,不容易成立,因为即使拉莫尔也承认,我们事先可能对它们有一些粗略的了解。见Charles Larmore, “The Idea of a Life Plan”, p. 110. 所以我仍用原来的翻译,但非常感谢他的意见。出现的人生是更美好的。换句话说,一个完全按计划生活的人生,其实美好程度比不上一个这样的人生:它既有一些计划,但同时随时让预期之外的价值来丰富它,甚至修正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注]Charles Larmore, “The Idea of a Life Plan”, p. 97.也就是说,按拉莫尔的说法,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完全按计划过的人生,不可能是他最好的人生。由于构成真正美好人生的这些好或价值是预期之外的,所以,人生本身(life itself)不是计划的对象(the object of a plan)。虽然这样,但人生之内可以作计划,而且计划在人生中也是重要的(planning has an important place in life)。[注]Ibid., p. 99.
拉莫尔的上述批评是不成立的。首先,有预期之外的价值,只是表明有些价值不由人生计划来决定,并不能由此推论出人生本身不是计划的对象。其次,当拉莫尔承认计划在人生之内是重要的,但又说人生本身不是计划的对象时,那么,我们会期待他清楚区分这两者。可惜,在他的论文中,他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区分标准。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似乎并不作这个区分,或者即使区分,但认为两者都是计划的对象。再次,说一个有些预期之外的价值的人生是更美好的,这个比较是如何可能的?如果将一个按理性计划过活并且实现了计划的人生,跟一个按理性计划过活而且实现了计划的、再加上有些预期之外的价值的人生作比较,那么,人们当然很容易判断后者比前者人生更好,因为它拥有更多的价值。但按拉莫尔自己的想法,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比较的,因为后者包括了一个人生计划。如果这种比较不可能出现,那么,他文中所说的更美好的人生断言是怎样得出来的,其实没有他想象中清楚。一旦如此,其实并没有理由说,一个人按理性计划过活而且实现了计划的人生一定不是他最好的人生。最后,无论罗尔斯或其他提倡人生计划观念的人,都不需要接受拉莫尔所说的人生计划观念背后的预设。当他们说要“掌控”自己的人生时,要计划时,他们清楚意识到,人生有很多东西在人们的控制能力之外,所以,这里说的“掌控”,如果属实,那也只是说,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去努力掌控,并且对意料或预期之外出现的价值、际遇做足面对的准备,即让预期之外的价值来丰富它,甚至修正人生的计划。在这个假定下,实在看不出一个接受人生计划观念并按理性计划过活的人,无法接纳拉莫尔所说的“预期之外的价值”。
拉莫尔在论文中曾指出威廉斯对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的批评是不彻底的,因为他没有质疑人生计划的观念本身,而只是质疑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注]Ibid., p. 109.如果本文的上述论证成立,那么拉莫尔对罗尔斯的强批评就是不成功的,人生是计划的对象。而威廉斯的不彻底其实正是他的优点所在,因为他没有因咽废食。
下面就讨论对罗尔斯理论的弱批评,看看哪些是他可以回应的,哪些是他难以回应的。这里讨论两种弱批评:一,拉莫尔认为,人生计划并不决定什么对个人是好的或有价值的。二,借用威廉斯道德运气的想法而提出的批评。[注]其实威廉斯和拉莫尔都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批评过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这些批评背后假定的有关实践理性的想法会引起太多争论,不一定可以说服同情罗尔斯理论的人,而且在有限的篇幅中也不可能梳理清楚双方的争论并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所以只能留待另文处理。再者,如果本文接着下来的批评是有效的,那么,我们不一定需要引入充满争议的实践理性的想法,也有理由反对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
拉莫尔认为什么对一个人是好的或有价值的,并不像罗尔斯的理论所言,由他的理性人生计划决定。他认为,有些东西构成我们的价值的一部分,但并没有促进我们理性目的的实现,甚至还与它们相冲突。新的经验可能会推翻我们已有的计划,提供理由去修正甚至重铸我们对应有的目标的理解。因为它能够揭示新的人际关系的模式、生活或行动的方式,它们的价值,即使给予我们所有已知的东西,都不会猜想得到的,例如养育小孩带来的幸福(happiness)[注]Charles Larmore, “The Idea of a Life Plan”, p. 110.。一个人往往是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价值,回过头来修正其人生计划。可见,至少某些东西对一个人有价值,是可以先于或独立于他的人生计划而确定的。
拉莫尔这个批评,可以说是部分成立的,而部分则能被罗尔斯理论恰当回应。需要事先区分清楚的是,一个东西本身是否有价值,与这个东西是否对一个人有价值并且构成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追求,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罗尔斯《正义论》的价值论讨论的其实主要是后一个问题,虽然没有说得足够清楚,因而引来误解。罗尔斯如果说,所有东西的价值,都要诉诸某个人的人生计划才能决定,那么,这是一个太强的立场,拉莫尔的批评因而是成立的,因为日常经验中,我们会承认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构成我们的人生计划中的一部分,例如,我承认一个人能演奏钢琴是有价值的,但由于我自身的人生追求并不是成为一个音乐家,加上时间及其他条件的限制,我并没有学习演奏钢琴。就此而言,一个人能演奏钢琴是有价值的事情,并不需要、也不能诉诸我的人生计划来决定。因此,一个东西本身是否有价值不需要诉诸某个人的人生计划来决定。[注]至于如何不诉诸某个人的人生计划而证成一样东西本身有价值,则有各种理论,例如斯坎伦的理论。参见Thomas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陈代东等译:《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价值”。到此为止,拉莫尔对罗尔斯的批评都是有效的。但是,当我们问同样这个东西是否对某个人是有价值的,并且构成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追求,则必须诉诸他的人生计划才能决定。即使这个东西是改变他人生计划的,也要纳入到新的人生计划才能说明它对他而言是有价值的。因为即使是拉莫尔也同意,如果那些东西是真有价值的,当事人必然有能力把它整合到一个新的目的系统中。也就是说,根据新出现的好或价值修正后的人生目的之下,他会视它为值得追求的东西。[注]Ibid., p. 110.如果区分开一个东西本身是否有价值与它对某个人是否有价值,那么,罗尔斯就可以部分地回应拉莫尔的批评,即就一个东西对某个人是否有价值并且会成为他的追求,需要诉诸当事人的人生计划来决定。
如果说上面拉莫尔提出的弱批评罗尔斯理论可以部分地回应,那么,另一种弱批评——就是借用威廉斯有关道德运气的思想而提出的批评——则是有效的,令我们有理由放弃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
威廉斯认为,一个人要为他的行动或选择辩护,有些只能事后用成功来辩护,而一旦失败,就完全不能辩护。显然,成功与否,依赖于运气。他区分两种运气:“内在运气”(intrinsic luck)与“外在运气”(extrinsic luck)。威廉斯举了高更的例子。高更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为此他不惜抛妻弃子。当他去塔希提岛时,如果途中因为遇上台风而受伤或死去,使他最终成不了一个伟大的画家,那么,他所受的运气的影响就是一种外在运气,因为这些环境因素与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他如果因为这些原因成不了伟大的画家,他可以说,自己的选择不一定是不好的,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但如果他一切顺利,外在运气很帮忙,但经过努力却最终还成不了一个伟大的画家,因为他其实缺乏绘画的天赋,那么,他所受的运气的影响就属于一种内在的运气,因为一个人天生是否有绘画的天赋,跟他能否成为伟大的画家有内在的紧密关系。高更最后成功了,他就可以为他当初选择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的计划辩护。但如果他成败了,那么,由于他是受内在运气的影响而失败的,他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注]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pp. 24-26.
如果威廉斯的观点成立,而绝大部分的人生计划都受到运气的影响,那么,就表示绝大部分的人生计划都需要事后来证成选择是否是对的或合理的。一旦如此,就基本上不可能在计划之初决定其合理性,因而也不可能保证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后悔和责备自己。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计划因内在运气而失败,他就有理由感到后悔和责备自己。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人生计划,都不可能做到罗尔斯的理论所说的那样,在计划之初就能保证,无论最后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理由感到后悔和责备自己。
按罗尔斯理念也许可以说,那是因为选择时对相关的事实理解不够,因而这个不是理性的人生计划,当然可以自责或后悔。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在运气的问题,是因为当事人在选择时,或者缺乏相关的知识,或者是相关信念出错了。但按威廉斯,可以这样反驳:有些信念的对错在选择时是不确定的,也不可能预先确定或知道,要努力尝试过才能知道,例如有没有绘画的天赋。同时,人生中产生影响的运气,很多时候是跟另一个人相关的,如威廉斯举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沃伦斯基的恋爱的例子,这表明,内在运气可能通过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的特定的人对其产生影响,因而处在他的理性计划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外。因此,上述罗尔斯理论的回应并不成立。威廉斯对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的批评,是一个很根本的批评。因为如果内在运气存在,当事人在计划时其实不可能保证将来不后悔及不自责旳。这是对罗尔斯的一个重要的内部批评,因为理性计划没有办法达到其目的,即保证当事人不后悔和不自责。
人们可能会认为,选择过一种德性的生活,不就可以避开运气的影响了吗?或者即使受影响,但至少可保证不会后悔和自我责备。这类选择是某些宗教或道德学派会提倡的人生计划。但是,就人类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要过一种德性的生活,其实避免不了运气的影响。想想那些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战争中被打死的人,就知道要成就一个德性的人生,需要多大的运气。不过,这个反驳对于不后悔和不自责两点没有效果。因为即使在那些极恶劣的环境下,一个想成就德性人生的人,他在死之前,虽然知道自己失败了,但如果他是真正追求德性人生的人,就不会为此前的人生计划感到后悔和自责。这样的考虑好像会逼出如下的结论:唯一能避免后悔和自责的人生计划——因此是符合理性的人生计划——只有成就德性的人生。这明显是罗尔斯所不同意的,因为他的正义第一原则就是保障人们有自由的权利选择过哪种美好人生。也就是说,即使这个回应在理论上成立,但它不是罗尔斯能接受的。因此,即使假设这个回应成立,也不能为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辩护。
另外,顺着威廉斯的思路,也可以说,罗尔斯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处境,即我们的选择是有“机会代价”的,因为我们本可以选择另一个或许会成功的计划,或者另一个很不一样的计划。到事后回顾时,可能因此而感到后悔和自责。当我们原来的人生计划最终失败了,以上说法自然会成立。即使这计划成功了,也还是可能感到后悔和自责,因为可能到那一刻,我们才惊讶地发现,错过的可能是更好的人生选项。正如拉莫尔所说的:“我们即使明智地过一生,仍然可能正确地责备自己。在回顾时,我们或许会希望,我们情愿自己在激情之下行动,让我们被某时刻的激情带离日常,而不是非常严谨公正地衡量各种选项,因为只有那样,某种好东西才会成为我们的好东西,而它的好只有现在才能欣赏到。”[注]Charles Larmore, “The Idea of a Life Plan”, p. 108.* 本文曾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杂志合办的“第二届心性、秩序、生活论坛:心性与美好生活”学术会议上报告。谨对与会者的批评致谢,特别是评论人郝忆春副教授。另外,本文也受益于与刘满新先生和马天俊教授的讨论,谨致谢意。当然,文中如有错误,责任在我。
按照威廉斯的思路,或许还可以这样说,人生实难,我们当然会计划自己的人生,并且会尽力发挥理性能力把这个计划做好。但理性的力量并没有罗尔斯所说的那么强大,能让我们可以超越运气对人生选择的可辩护性的影响。直面这个现实,接受挑战,成功了为自己庆贺,失败了就承认,就后悔和自责,这更符合人的心理现实,好过提出一种貌似能“自我安慰”的想法,让自己活在虚假的希望中。没有什么能保证一个人“无负此生”,即使他很理性地计划。这有点残酷,但总好过自欺或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