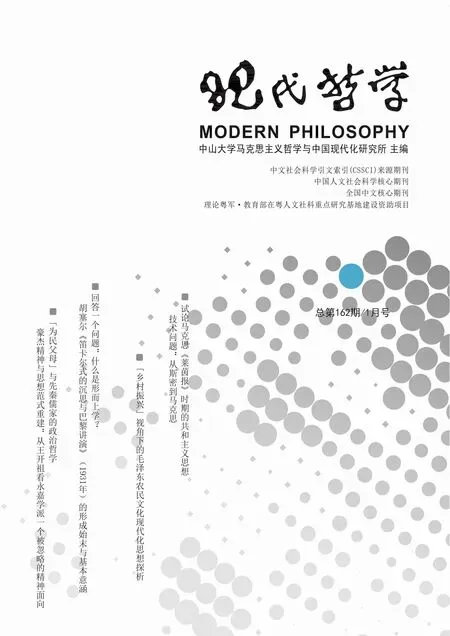试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
鲁克俭
对于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列宁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教科书式说法。马克思最终转向共产主义是没有疑问的[注]当然,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节点尚有争议。列宁将转变的时间节点定位在《德法年鉴》两篇论文,但如果列宁在世时读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转变的时间节点前移。,问题是如何称谓马克思的前共产主义时期。“革命民主主义”是带有强烈雅各宾主义色彩的说法,最早出自普列汉诺夫,后被列宁所沿用。实际上,通常与“共产主义”相对的概念是“自由主义”。科尔纽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态度,“革命民主主义”的说法和“自由主义”的说法被他不加区分地运用。阿尔都塞把1842年之前的马克思思想看作是“理性自由主义”。英国马克思学家塞耶斯专门撰文批评那种把马克思变成自由主义者的作法[注]参见[英]塞耶斯:《作为自由主义批判者的马克思》,《哲学动态》2015年第3期。。但塞耶斯所批判的,是将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变成自由主义者。本文的观点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自由主义总体上属于自由主义的左翼,即自由共和主义。
一、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早期从自由主义到共和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在1843年10月写作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提到,“1842年,青年黑格尔派成为公开的无神论者和共和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0页。,“鼓动家们自己也要放弃共和主义的宣传,他们由于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哲学结论,现在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1页。。恩格斯提到了赫斯、卢格、马克思、海尔维格。由于受列宁关于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说”的影响,恩格斯的这一说法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这里,恩格斯透露两点重要信息,一是马克思最迟1843年10月已经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一时间节点可以确定在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即1843年春夏两季);二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1842年成为了共和主义者。
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来说,184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1842年3月布鲁诺·鲍威尔被波恩大学解聘,是青年黑格尔派走向激进的关键事件。同一时期,随着普鲁士新国王伪自由主义专制面目的彻底暴露,卢格率先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逐渐放弃了黑格尔立宪君主制的改良主义幻想,走向共和主义。鲍威尔着力研究法国大革命,在鲍威尔的影响下,马克思1843-1844 年一直有写作《国民公会史》的计划。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使用德文的“共和主义(Republikanismus)”一词[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93页(不过Republikanismus被译成了“共和政体”)。。在此之前,恩格斯两次使用过英文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1、59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许多“共和主义”的说法,原文其实是“共和主义者(英文是republican,德文是Republikaner)”,并非“共和主义(英文是republicanism,德文是Republikanismus)”。。恩格斯这两处使用英文的共和主义,都是在以英语发表的文章中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在恩格斯那里英文的共和主义和德文的共和主义具有同等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多次使用德文“共和主义者(Republikaner)”一词。马克思首次使用“共和主义者”一词,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一文中。马克思说:“扎勒特是个共和主义者,如果你大肆宣扬他搞保皇主义,你算是他的朋友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9页。第二次是在1843年5月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自由的人就是共和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恩格斯更是大量使用“共和主义者”一词,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广泛使用“共和国(Republik)”一词。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写到:“基督徒生活在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里,有的在共和政体的(in einer Republik)国家,有的在绝对君主制(in einer absoluten)[注]die absolute Monarchie(英文是absolute monarchy)应该译为“绝对君主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都将其译为“君主专制”。实际上,德文中专门有一个词“despotisch”意指“专制的”(其对应的英文词是despotic)。“绝对君主制”是“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是起源于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统治的国家形态,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兴起密切相关。霍布斯是绝对国家主义理论的主要倡导者。马克思经常提到这种介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就是基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而讨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国家,有的在立宪君主制(in einer konstitutionellen Monarchie)的国家。”[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共和国(共和制)看作是“特殊国家形式”。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共和主义者(或共和主义、共和国)的语境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共和主义首先是与君主制(包括绝对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相对立的共和制度,其参照物是法国大革命后根据1793年雅各宾宪法建立的共和国。
在前引文中,恩格斯提到包括他和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1842年转为共和主义者,恩格斯指的是他们从黑格尔的立宪主义转向雅各宾派的共和主义。表面上看,列宁与恩格斯并没有本质差别,因为他们都指向雅各宾派。但列宁强调的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而恩格斯共和主义的说法则蕴含着有别于民主主义的公民共和主义的可能性,因为在政治立场上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宪主义总体上属于属于自由主义。如果说公民共和主义在恩格斯那里还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就成了事实上的存在,尽管马克思首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首先,马克思明确把《莱茵报》称为“自由主义报纸”:“《莱茵报》也没有片面地反对官僚制度,相反,它承认它所发挥的作用:(1)反对毕洛夫-库梅洛夫;(2)反对浪漫主义思潮。相反,它是唯一既承认官僚制度的好的一面,也承认旧普鲁士立法的好的一面的自由主义报纸。”[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9页。。
其次,马克思《博士论文》所隐含的政治哲学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旨并非纯粹的自然哲学,而是蕴含了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呼应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唯物主义自我意识哲学,有别于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哲学。参见鲁克俭。,其出发点是宗教批判,但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蕴。马克思强调原子偏斜的偶然性,也就是强调任性的自由,这是典型的消极自由(摆脱外在束缚),有别于黑格尔基于理性的积极自由。马克思强调“抽象的单一性”,强调立足于原子式个体的“契约”,这是一副典型的市民社会画面,具有浓厚的霍布斯“自然状态”[注]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确实提到了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说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3页。色彩,属于英国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也与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唯物主义自我意识哲学相一致。
第三,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注]所谓《莱茵报》时期,是指马克思1842年政论文章写作时期,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并非全都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早期发表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两篇政论文章(即《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注]该文1842年2月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1卷上发表。和《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注]该文连续刊登在1842年5月5、8、10、12、15和19日《 莱茵报》第125、128、130、132、135和139号。),鲜明体现了马克思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按照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自由、安全、财产等是“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新闻出版自由是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基本内容,如1793年宪法第122条就规定了“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注]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引用了这一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通过比较马克思与黑格尔以及康德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态度,能够清楚地看出马克思这两篇政论文章的自由主义立场。作为德国观念论传统的开创者,康德翻转了英国的经验主义自由传统,将自由引“外”入“内”,最终诉诸人的“自由意志”。因此康德的自由主义(如果可以将其称为自由主义的话)首先是思想(理性)自由主义。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由人的“自由意志”推演出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权看作是人的先验(天赋)权利。但是,康德并没有从“自由意志”推演出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内的政治自由。康德认为,只存在大学教师课堂上有限的言论自由(而且仅限于对哲学和科学的言论自由),不应该随意谈论宗教和政治。尽管黑格尔经常批评康德,但在私有财产和言论自由方面,黑格尔与康德立场接近。反而是费希特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大力鼓吹言论自由[注]在对私有财产的证成问题上,费希特和康德、黑格尔没有本质区别。。
费希特1793年在《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的演讲中疾呼:“民众,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献出,只有思想自由不能。”[注]《费希特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1页。费希特所谓的思想自由还包括传播自由思想的自由:“你们允许我们思考,因为你们无法阻止它;但你们禁止我们传播我们的想法;就是说,你们并没有夺去我们的自由思考这一不可出让的权利,你们只是占有了传播我们的自由思想的权利。”“如果我们对道德规律没有禁止的一切都有一种权利,谁能够指出道德规律有一条不许说出自己的信念的禁令?谁有权利禁止别人说出自己的信念,而将这些信念看成对他的财产的冒犯?”[注]《费希特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9页。“我诚然可以传播真理,但不可传播错误。”[注]《费希特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2页。问题是谁有权规定“什么是我们应该作为真理接受的”[注]《费希特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7页。,费希特说,君主们“无权给我们的研究规定对象或设置界限”[注]《费希特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64页。费希特还嘲讽专制主义对人的精神奴役:“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坟墓里更安静了”[注]《费希特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61页。。
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两篇政论文章中基本采用了费希特关于“思想传播自由”的证成思路。费希特的证成思路是这样的:首先,思想自由(自由思考)既是人的本质又是人的自然权利。其次,自由的思考包括对真理的探讨,而对真理的探讨是没有界限的。第三,人既有权利吸收别人的真理,也有权利给予别人真理。这就是说,人有传播真理(自由思考的结果)的权利。马克思的证成思路是:首先,自由是人的本质。其次,思想自由与真理有关。第三,探讨和表达真理的风格是完全个性化的,不应由官方来规定。饶有趣味的是,费希特和马克思都把自由与幸福联系起来。
马克思与费希特的不同在于:首先,费希特主要是从其知识论出发推出思想自由,马克思主要是从理性出发推出思想自由。其次,费希特侧重的是思想的“传播”(这是一般的言论自由),马克思强调的是思想的“表现”(这是特殊的言论自由,即以报刊为媒介的言论自由,也就是新闻出版自由[注]体现新闻出版自由的报刊就是“自由报刊”。马克思强调,“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于一方面的有权是否应当成为另一方面的无权。问题在于“精神的自由”是否比“反对精神的自由”享有更多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第三,费希特笼统地说“思想自由”,而马克思则区分了“现实的自由”和“观念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
当然,这两篇政论文章所体现的自由主义与《博士论文》所体现的自由主义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这两篇政论文章中的自由主义是基于理性、类和普遍性的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注]马克思说“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而《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是基于原子式个体的任性自由[注]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明确批评了“任性的偶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换句话说,这两篇政论文章中的自由研究开始萌发向共和主义转变的因素[注]再举一例: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说,自由“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第181页)。
当我们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发生从自由主义向共和主义转变时,并非仅仅从表面上谈的。如果把共和主义与共和制度划等号,那么恩格斯的上述自我指认就已经足够了。当列宁把《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指认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时,列宁更多是基于马克思所秉持的理念,即为争取底层群众[注]包括农民(即小资产者,如捡拾枯树的农民和葡萄种植者)。的权利而进行政治斗争。我们指认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发生了向共和主义的转变,与当下人们对共和主义内涵的新理解有关。
“共和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只不过被近代自由主义的锋芒给遮蔽了。近几十年来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出现了共和主义的复兴。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这波共和主义可称之为新共和主义或公民共和主义。新共和主义的代表性研究学者包括剑桥学派的波考克、斯金纳,以及《共和主义》一书的作者佩迪特等。“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字面上讲与“共和国(republic)”密切相关,因而共和主义通常被追溯到古典古代,特别是希腊城邦(如波考克的“新雅典传统”)。不过斯金纳强调古代共和主义的源头是罗马人(即所谓的“新罗马传统”)。政治思想史学者对共和主义的理解差异很大。有的学者强调共和主义的“自由国家”方面(如斯金纳)。按照斯金纳的说法,共和主义被用以捍卫城市共和国的传统自由,以对抗绝对主义。有的学者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强调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如波考克)。还有学者强调共和主义的“非支配的自由”即“第三种自由”(如佩迪特)。当然,贡斯当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二分,是思想史学者挖掘被近代自由主义所遮蔽的共和主义思潮的背景性前提。
波考克在考察公民共和主义时提到了马克思,不过他是把马克思看作是自由主义者。现在有西方学者开始把马克思看作是共和主义者。较早主张这种观点的是艾萨克,他在《政治狮皮:马克思论共和主义》中明确提出并论证了这一观点[注]载《政体》(Polity)1990 年第22 卷第3 期,中译文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后来布雷克曼在《废除自我》[注]参见[美]布雷克曼《废黜自我》,李佃来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Moggach在《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和政治学》[注]cf. Douglas Moggach, 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Bruno Bau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利奥波德在《青年马克思》[注]参见[英]利奥波德《青年马克思》,刘同舫、万小磊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也先后把马克思看作是共和主义者。
马克思在科学共产主义阶段之前有一个哲学共产主义阶段,而在哲学共产主义之前还有一个共和主义阶段。可以说,《莱茵报》时期两篇政论文章之后的马克思既是一个制度共和主义者,也是一个公民共和主义者。实际上,从马克思的相关文本来看,马克思似乎没有像恩格斯那样仅仅从制度角度来理解和使用“共和国”及“共和主义者”[注]恩格斯晚年(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仍然将卢梭的共和主义与立宪主义相对:“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末,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完全不越出思维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5页)。
马克思1842年3月5日致卢格的信中写到:“Respublica一词根本无法译成德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Res publica是西塞罗第一次用拉丁文来翻译希腊文politeia,而且根据西塞罗的解释,Res publica意思是“人民的事业(事务)”[注]根据维基辞典,拉丁文publicus(形容词中性,其阴性是publica,阳性是publicum)源自populicus,而populicus源自populus (意即“人民”)。。实际上,英文中通常以“commonwealth”来翻译Res publica,比如霍布斯、洛克[注]参见万健琳:《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一种观念史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7页。。“publica”的含义就是“公共的”[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纲》以及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多次提到古罗马的“公地(ager publicus)”。。马克思1837年给父亲的信中谈自己构建法学体系的计划时,就用了拉丁文“jus publicum(公法)”。马克思之所以说Res publica无法译成德文,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德文的“Freistaat”一词不能与西塞罗所说的“Res publica”对应。而德文的“Republik”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词,即中古法语 republique(来自拉丁语 res publica[注]参见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re publica是res publica的夺格形式)。显然,马克思这里是从“公共性”意义上来理解“共和国”的。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写这封信时,正是写那两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政论文章时期。他写这封信时对共和国(Freistaat)的理解,首先是国家制度而非公共性,但显然已经蕴含了“公共性”的新维度。
马克思还将共和国与自由联系起来。在中学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马克思写到:“当人们变得柔弱,纯朴风尚消失,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的时候,独裁者倒可能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共和国与自由国家[注]德文的“自由国家(Freistaat)”也有共和国的意思。(其对立面是绝对君主制)一语双关地联系起来。马克思说:“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马克思的这一用法,与斯金纳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被用以捍卫城市共和国的传统自由,以对抗绝对主义的说法是一致的。
马克思将《莱茵报》称为“自由主义报纸”。但马克思对莱茵省现实中的自由主义有诸多不满和批判。马克思曾经对各种自由主义反对派做过批判。在《莱茵报》早期,马克思批判了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性。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批评了作为新闻出版自由辩护人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将自由囿于精神领域。在自由主义反对派看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头脑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心脏去过问”。对他们说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异国的'植物,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业余爱好'来同它打交道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自由主义反对派试图“说服人们相信意志自由是人的天性”,这表明“自由主义的立场已变成什么样子,自由主义在人的身上体现到怎样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马克思将这种自由主义称为“生来软弱无力的不彻底的自由主义”。马克思还批判了“虚伪自由主义[注]“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把学术才能同地位扯在一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以及“要求在省议会中有智力的代表的自由主义”[注]“智力不仅不是代表制的特殊要素,而且根本不是一个要素;智力是一个不能参加任何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机构的原则,它只能从自身进行划分。不能把智力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只能把它作为一个起组织作用的灵魂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3页)。、“通常的自由主义[注]认为“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等级会议这边,而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在政府那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9页)。”、“慎重的自由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从前的自由主义者”[注]“只知道维多克的‘不是囚犯就是狱吏’这个二难推论的不久前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这样,马克思就把自由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联系起来了。而不彻底的或假自由主义,是可以与君主制(至少是立宪君主制)相容的。
不但如此,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的两篇政论文章之后的政论文章中,公民共和主义因素逐渐增强。实际上,体现为理性、类、普遍性的自由就已经开始向公共性靠拢了。而对私人利益的否定,则是马克思走向公民共和主义的关键一环。
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对待私人利益的态度就开始变化:“有一种心理学……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写到:“私人利益非常狡猾,它会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把自己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私人利益希望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1—262页。当马克思在《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中辩解说,《莱茵报》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在批评莱茵省等级会议时针对各等级的私人利己主义,强调政府的普遍的英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9页。时,这种自由主义[注]马克思说《莱茵报》“强调政府的普遍的英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辩护的策略性语言,显得言不由衷,但批评“各等级的私人利己主义”,却是《莱茵报》自由主义的真实立场。显然就是当下人们所理解的共和主义。
强调公共性,批判利己主义,是公民共和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此外,共和主义还强调国家促进人的自由的积极作用,这有别于英国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国家定位。按照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的说法,国家是“理性自由的实现”,“不是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应该根据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现代国家的目的是“使有道德的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实现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国家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总之,个体要服从理性(人的理性,即社会的而非个人的理性),从而服从整体,服从国家。
二、马克思《莱茵报》时期从自由主义转向共和主义的内在理路
当马克思强调出版自由时,马克思是在捍卫个人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更进一步,当遇到财产自由问题时,马克思发现财产自由不但没有体现出黑格尔所强调的“自由的最初定在”,而且体现着利己主义。在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上,马克思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分道扬镳了。这就是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用“难事”一词的德文原文是“Verlegenheit”,意即“窘境”[注]“Verlegenheit”是在介词短语“in die Verlegenheit”中,其英文译文是“in the embarrassing position”,意即“在窘境中”。按照德文原文,“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意思是“来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窘境之中”。。
所谓窘境,就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内在紧张。按照我们的理解,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有两个传统,一是马基雅维里开创的共和主义传统,二是稍后由霍布斯开创的自由主义传统。斯特劳斯的现代性研究早期突出霍布斯,后来则转向了马基雅维利。其实,这是两个差异很大的传统。如果说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共和主义则强调公共自由(共同体自由)。如果说自由主义与古代传统有某种断裂(比如霍布斯就经常忍不住以亚里士多德为批评对象),共和主义则带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印记(公民共和主义通常被称为公民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传统,而共和主义则是欧洲大陆的传统。当贡斯当区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时,英国自由主义以及与其相伴的社会契约论已经成为主导性政治思想话语。比如尽管卢梭属于欧洲大陆的共和主义传统,但是他的社会契约论也是以个体自由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然而,卢梭的自由主义与英国的自由主义有很大不同。这也是卢梭在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显得另类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与法国启蒙运动相伴生的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长期被英格兰契约论传统所遮蔽,不被思想史研究所重视,后来因为哈耶克的努力才引起思想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哈耶克的问题意识是强调苏格兰启蒙思想的“自生自发的秩序”思想,以对抗法国启蒙思想中的“理性建构主义”。哈耶克所谓的“理性建构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卢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无疑具有理性建构主义倾向,但英国的经验主义契约论传统(从霍布斯到洛克)就完全对理性建构主义免疫了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难道霍布斯的“利维坦”不是一种理性建构的产物吗?其实,英国经验主义并不是不强调理性,只是经验主义的理性有别于欧洲大陆的先验理性。在我们看来,仅仅强调“自生自发的秩序”并不能把苏格兰启蒙学派与英格兰契约论传统区别看来,关键是二者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
卢梭确实是太超前了。在法国需要大力强调私有财产自由的时代,卢梭就开始警惕文明的负面效应,忧心私有财产的异化现象。这正如老庄所谓“有机巧必有机心”,带有强烈的复古主义色彩[注]卢梭的社会理想就是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
卢梭通常被看作是民主主义者。卢梭的民主主义的主要含义是平等。当然,卢梭的平等并非结果平等,而首先是“自由的平等”[注]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使用了这种关于资产阶级平等的说法。。比如平等的政治自由,平等的财产权。卢梭关于平等的财产权主要体现的是个人在财产自由方面的平等,即每个人都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但卢梭也反对私有财产数量的悬殊。这一点体现了他早期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关于私有财产的态度[注]应该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相对缓和了对私有财产的批评态度。。因此,卢梭的民主主义既有自由主义的因素,也有共和主义的成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0年代使用民主主义一词时,很难说是直接取自卢梭[注]德拉-沃尔佩显然认为马克思深受卢梭民主主义(特别是平等主义)的影响。参见[意]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他们更多是在英国宪章运动语境下使用“民主主义”一词的。比如恩格斯在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说:“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7页。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对私有财产的态度,马上受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的批评。可以说,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就是直接针对卢梭的。作为弗格森的学生,斯密进一步发展了基于私有财产的商业社会理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和“利己人”假定,预示着后来边沁“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学说。到了边沁这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与卢梭对待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的态度已经泾渭分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分野已经彰显,卢梭共和主义的面相就越发清晰起来。显然,马克思对这一思想史语境是心知肚明的。卢梭对于马克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共和主义而非民主主义方面。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窘境,鲜明地体现在1842年10月写作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这是马克思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系列论文的第三篇。第二篇论文没有在《莱茵报》发表,也没有流传下来。对照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和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的思想在多个方面发生了微妙变化。首先是对待私有财产和私人利益的态度,此点前文已有论述。其次是对偶然性的态度。马克思为了批评立法者对待私有财产的知性(即非辩证性)态度,不惜诉诸穷人的习惯法[注]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既维护穷人的习惯法,也提到了特权者(中世纪贵族)的习惯法。对于后者,马克思是明确反对的。因此不能认为马克思诉诸穷人的习惯法就是站到他不久前刚刚批判的“法的历史学派”的立场上去了。,强调与普遍性和理性相对的偶然性的地位,以及偶然性向法律合理性的转化。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窘境,根源于私有财产与利己主义的内在关联。从霍布斯到洛克,自然权利都包括财产权。但洛克和霍布斯回避了私有财产与利己主义的内在关联。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打消了人们对利己主义的道德疑虑,从而自由主义与边沁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可以相容了。康德和黑格尔则是另一种进路。康德是将“德”与“福”分开,黑格尔则将私有财产看作是抽象权利,看作是人的自我实现的中介。康德和黑格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有财产与利己主义的内在冲突。将私有财产看作是人的自我实现的中介,这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采用(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进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尚未形成这种认识,尚处于青年黑格尔派大氛围的影响之下。根据布雷克曼以思想史研究语境方法在《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一书中对青年黑格尔派激进社会理论的考察,在德国19世纪上半叶的语境中,新教的“自我”(人格)概念意味着私有财产,也就意味着利己主义。德国思想界围绕“自我”(人格)概念的抽象争论,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蕴。随着德国反利己主义氛围的增强,青年黑格尔派变得越来越激进,“废黜自我”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共识,“共和主义”也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必然结论。在这种思想氛围的挟裹之下,马克思本能地拒斥利己主义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当然,这种对利己主义的拒斥与马克思本来的自由主义世界观是有冲突的。马克思的窘境由此而来。而窘境带来的是马克思思想向共和主义倾斜并最终转变。
实际上,私有财产、物质利益、利己主义是三个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恩格斯对于“利益”问题认识的发展很有代表性。1842年年底,恩格斯刚到英国之后所写的文章[注]参见恩格斯1842年11月30日写的《国内危机》一文,载于《莱茵报》12月9、10日。中,先是嘲笑英国人从物质利益出发,并因德国人从原则出发而自豪。但随着对英国社会认识的深入,恩格斯转而肯定英国而否定德国。同一时期,马克思也是先从原则出发,随后遭遇了“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窘境”。否定个人利益和利己主义,就会走向“自我牺牲”。这倒与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一文的气质非常吻合。当施蒂纳以《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真正的利己主义(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批判赫斯等人信奉“自我牺牲”时,赫斯反驳说,共产主义者已经超越了自我牺牲与利己主义的对立。赫斯这种对共产主义道德的言说,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说明了共产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区别。当然,赫斯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已经是科学共产主义[注]实际上,赫斯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提法,而更早使用“科学共产主义”概念的是魏特林。。“哲学共产主义”时期的赫斯(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是反利己主义的。在面对自由主义时,哲学共产主义与共和主义是同路人。马克思是首先通过共和主义这一桥梁走向共产主义的。而随后哲学共产主义与共和主义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国家问题。
公民共和主义要以制度共和主义为保证,因此共和主义的共和国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如洛克社会契约论的共和国),它不是消极国家(守夜人国家),而是积极国家(即体现理性、自由和普遍性的全能国家)。因此,共和主义必然出现对国家的迷信和崇拜。这种迷信和崇拜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得到最好的体现。
黑格尔主张立宪君主制,但从公民共和主义角度看,黑格尔是一个典型的共和主义者。黑格尔的政治理想是古代城邦。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一方面不信任,另一方面又认为必不可少。黑格尔试图以理性国家克服市民社会的消极方面,从而保持市民社会的积极因素。因此改良主义的黑格尔是最大的国家崇拜者。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无疑是国家崇拜者。但是,到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开始把矛头转向这种国家迷信和国家崇拜。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批判“共和制”,把“共和制”看作是“民主制的抽象国家形式”,是政治国家的最后形式。而在马克思设想的“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政府)已经消亡,国家如果存在,也已经变成了非政治国家(即现实的物质国家,也就是“人的社会”),因此特殊性与普遍性重新实现了统一。这是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的初步表达[注]马克思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唯物史观,才达到科学共产主义。在此之前的共产主义(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甚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都属于哲学共产主义阶段(至少具有哲学共产主义因素)。。
对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思想转向(转向哲学共产主义)的内在理路,这里不做深入探讨,这里只需强调一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共和主义时期实际上很短暂,也就是《莱茵报》时期不到一年时间。有国外学者(包括受其影响的国内学者[注]比如邹诗鹏关于马克思的激进主义在《德法年鉴》停留的观点,以及王代月、朱学平的相关论文。)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也看作是共和主义者,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进行了双重批判。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而主张“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的积极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但这种积极自由的实现不是靠国家(共和国)。因为共和国(政治共同体)在理论上只是“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的目的是市民社会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自由主义主张“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共和主义却不承认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危及公共自由,是不许可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但是,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现象。如果说英国自由主义直截了当地把国家看作是手段(守夜人),那么法国大革命的共和主义只是在实践上显得国家是目的本身,而这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只是一种例外。但是,“实践只是例外,理论才是通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马克思还说,“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于是私有财产与利己主义之间就被建立了强联系,从而私有财产就被马克思彻底否定[注]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批判,或者是基于绝对命令的应然要求。。但是,马克思此时对自私自利和私有财产的否定已经是基于共产主义而非共和主义立场。一个可作对比的例子是,共和主义者鲍威尔尽管反对利己主义和市民社会,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私有财产。当然,鲍威尔把人的德性完善(人的解放)寄托于共和国理想的公民政治生活(类似于古代城邦)。施蒂纳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完全倒向了市民社会和利己主义的“唯一者”[注]按照赫斯在《晚近的哲学家》中的说法,鲍威尔是要国家而不要市民社会,施蒂纳是要市民社会而不要国家,而费尔巴哈试图将市民社会和国家结合起来。。施蒂纳退回到了英国的自由主义,尤其是边沁的自由主义。
饶有兴趣的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再次批判了雅各宾派的共和主义,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对共和主义的彻底清算。马克思写到:“在圣茹斯特的另一个报告(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中,共和主义者被描写成完全具备了古代精神即刚毅、谦逊、朴质等品质的人。”“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十分明确地谈到古代的、‘人民本质’所独有的‘自由、正义、美德’。”“罗伯斯比尔明确地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称做‘自由人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5—156页。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谈及雅各宾派时,强调的是其共和主义方面,而非其革命(激进)民主主义方面。
余 论
马克思青年时代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更准确说是对自由共和主义的批判。根据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即使国家消亡,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仍然存在,因此仍然存在个体自由与共同体(公共自由)的关系问题。按照佩迪特的说法,斯金纳主张的共和主义自由是“工具性自由”,在斯金纳看来,个体自由才是目的。问题是个体自由到底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如果是个体的积极自由,那么马克思也是把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赫斯则把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看作目的本身,而把个体看作是手段。赫斯的观点在当代共社群主义中得到复活,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既不是社群主义,也不是共和主义,更不是自由主义。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新社会契约论”。
另一方面,超越了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的科学共产主义并非没有道德哲学。人的潜能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我实现),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就是最大的善。科学共产主义是对共和主义的扬弃而非彻底否定,它保留了共和主义弘扬公民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