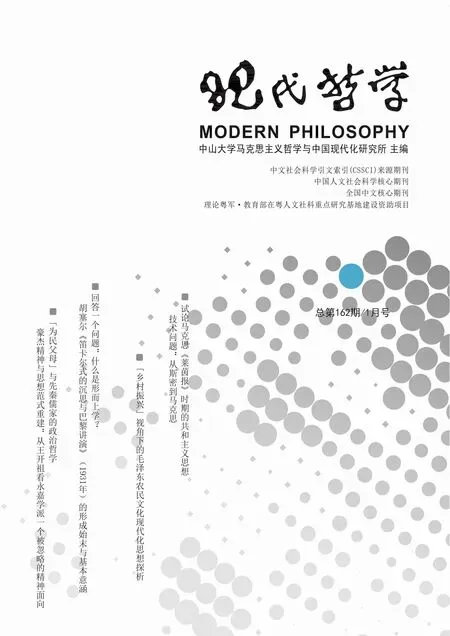技术问题:从斯密到马克思
[德]埃伯哈德·伊尔纳/著 鲁 路/译
一
为了理解像李嘉图或马克思这样的19世纪伟大经济学家,需要对他们的思想前提略说几句,因为早在18世纪,一些核心问题就焕然一新地提了出来。在启蒙进程中,一颗新星近乎不知不觉地冉冉升起于天穹,这就是崭新的、经验性的、理性的知识。它逐步排挤了打上宗教与传统烙印的旧知识,这是某种“文化创新”。它对人的崭新认识来自市民阶层,而不依附封建特权。它仅仅依靠理智贯彻下来,是在科学院和大学中形成的。随后,大约在18世纪,它在广泛的市民社会中掀起讨论。这是它最重大的成就所在。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人,即使他们不属于科学界,也在追踪并讨论新生事物。对此,英国科学史家西科德(James Secord)在其著作《科学远景》(2014年牛津版)中曾援引多方实例加以描述。
当时,对进步的信念建立在经验与归纳基础上。按照哲学家休谟所说,那时人人争当最优秀的人物。经济学家斯密认为,科学认识的数量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成败。这样,决定现代社会的,就是一个新因素:不停歇的、生机勃勃的理性。这种不停歇的特点构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在这方面,人们大多是以古典的方式援引韦伯关于(带有新教特征的)西方社会“心志性”经济理性的论点。但我不想拾人牙慧地重复这一脍炙人口的论点,而想以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蜜蜂寓言为例,描述货币社会的变迁过程,因为从这个故事可以直接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首位理论家斯密的思想。
荷兰医生曼德维尔1693年迁居伦敦,在他的讽刺诗《不知足的蜂箱或曰变得诚实了的人们》中描述了一个“权力与财富无与伦比的蜂箱”。其财富的由来无非就是其居民的可购买性。律师挑唆纷争,给自己找活儿干;官员贪污受贿;医生操心自己的收入,而不关心病人的健康;士兵为金钱和军衔而战,而不是出于爱国心而战。尽管如此,结果却是一个充满活力且富裕的社会。后来,灾难发生了:蜜蜂们决定回归道德之路,贪婪、虚荣和欺诈受到鞭挞。但是,回归道德导致悖谬性结果,什么都不灵了:经济萎缩、人口锐减、蜜蜂都简陋地居住在空洞的树干上。这首诗的教训是:“不要抱怨品德在庞大的国家中没有一席之地……为了国家繁荣,高傲、奢侈和欺诈必不可少。”
这首诗的实际由来是对丘吉尔(John Churchill)的理论的批评。此人是西班牙王位战争的军队领袖、马尔博罗公爵、英国武装干涉大陆政策的支持者。据说就是他为了发财致富,特别是为了给战争筹措军款,于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曼德维尔意在回敬那些批评者,因为在他看来,选择清教,会令英国积贫积弱。为了避免这点,就要接受可购买性,作为经济繁荣的代价。这样,曼德维尔就触及到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的核心。1714年,他修缮一新地发表了自己的诗作,题目是“蜜蜂寓言,或曰个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注]Bernard de Mandeville, Die Bienenfabel oder Private Laster, Öffentliche Vorteil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8, 1980.。
曼德维尔为自己的教喻诗选择了寓言这一文学体裁。在寓言中,特定的动物扮演典型人物的角色。人类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既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友善秉性和温柔气质,也不是人们依靠理性和自制获得的实际品德”,而毋宁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它天生什么样,品德就什么样”。这一结论反过来意味着,为了让社会取得乐观结果,最佳道路在于促成每一名社会成员的虚荣、贪婪和自私。这个极端性结论在各地都引起众怒,曼德维尔的诗和寓言遭到禁止,但他的悖谬性论据切中了时代精神。当时经济繁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就连农村妇女也到交易所去投资。企业与金融因素的革新呼唤人们对此做出某种论证,而曼德维尔看来提供了这种论证。
无论如何,格拉斯哥大学伦理学教授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论著《国富论》[注]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中考察了这一思想形态。他给曼德维尔悖谬性论证做出的隐喻是“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操持着,让个人“往往恰恰因追寻个人利益而持久地促进社会,就好像个人当真有意这样做似的”。这一隐喻如此著名,以至于在那一时期,例如为了自由主义的缘故,政治观念和学说都接受了某种个人生活。支持这种行为的抉择不可归咎于个人,而是说这样一种抉择是“受体制决定的”,因为经济价值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传统的社会关系因富有活力的货币关系的缘故而解体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晰地揭示了蕴含于资本主义之中的那种“创造性地摧毁”旧制度遗留格局的力量:“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问题是,哪儿来的力量与活力,导致自古以来简简单单的市场参与者在18世纪末变成着眼于个人利益的竞争者?而且,仅在能够生产并在市场上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之际,才有利益可言。对此,斯密加以解释。他指出分工带来生产效益,并以大头针的生产为例描述这种效益。通过对各个生产阶段予以专门化和分隔,最终就能够生产出较以往更多的产品。当然,他尚未理解机器带来的好处,以及机器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在以农业为主的偏远的苏格兰,他对此根本形成不了直接的认识。那里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只有小作坊。
在这方面,“交易所之星”李嘉图这位领衔的国民经济学家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注]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Reprint published by Dent, 1969.(1817、1819、1821)中做得更进一步。原先李嘉图认为,使用机器会给企业主和工人带来同等利益。但经过同自己的同行进行深入的探讨,他修正了这一结论。在1821年出版的第三版中,李嘉图增添了一章论述机器,指出要使用机器,必然要花费高额投资。如果企业主为机器支付费用而降低工资的话,就会带来工资上的竞争,并且首先带来工人收入的降低。“机器与劳动始终彼此竞争,只要劳动不增加,机器往往得不到使用”。当然,从中长期看,作为改进机器的结果,企业主纯收入的提高会带来资本积累的增加。把节省下来的资本再度投入,会带来对劳动的需求,以至于原先受到削减的劳动会寻找到新的用武之地。由此,从长期来看,工人的状况会得到改善,即他们的购买力会随着产品的生产费用更为低廉而有所提高。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经过改进的机器,“相对费用优势”法则会发挥更大作用。相对于那些使用机器的国家来说,谁拒绝使用机器,谁就处于劣势。
另外,李嘉图高瞻远瞩,他关于生产越来越机器化会导致自动化的思想,甚至得出了一个致命性结论:“如果机器可以做今天工人做的所有工作,就没有对劳动的需求了。谁不是资本家,不能购买或雇佣机器,就没有资格消费任何东西。”
二
李嘉图通过费用核算与市场核算,讨论机器对企业主利润与工人工资的影响这一问题。英国数学家拜比吉[注]一译巴贝奇。——译者(Charles Babbage)则分析了在技术性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与机器使用所造成的影响。拜比吉既是作为第一台自动机械计算器的发明人,也是作为计算机的先驱人物而闻名于世的[注]彼得·布罗德纳盛赞拜比吉这一成就,Peter Brödner, “Charles Babbage-ein Vordenker der Moderne”, in Charles Babbage, Die Ökonomie der Maschine,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1999, S. XV-XXVIII.。这位有着学究式敏感、心绪不安且四处张罗的唯我论者[注]关于拜比吉的传记,参见Anthony Hyman, Charles Babbage, Philosoph, Mathematiker, Computerpionier, Stuttgart: Klett-Cotta Verlag, 1987.对什么都感兴趣。他的各项发明、模型运算和设计方案涉及从金属加工的最早精确计算到计时器,从统一邮资设计方案到收入税模型,从数学编程程序到铁路公司的建筑工程。此外,他细致研究了当时的币制体系和支付体系,分析了英格兰银行每日的转账往来,出于简化演算的理由主张英镑采用十进制。他基本上是“顺带着”发现,海洋潮汐的动力有可能充当动力源,预言煤炭开采会面临枯竭。
上述在今天看来显然让人感到杂乱无章的见识,对于英国受进步信念鼓舞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来说是典型的。许多技术发明都出自一系列有天分的手工业者。就像拜比吉一样,谁拥有坚实的、系统的思维能力,并且是数学教授[注]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Reprint published by Dent, 1969.,谁就理所当然要解决复杂的工业应用问题。
就应用数学来说,它首先是准确无误的数学表格运算,就像天文学表格、年历、对数表格等。例如,航海上借助天文导航仪确定方位时,这些表格极其重要。对于英国这样的海洋强国来说,军舰与商船航行在正确的航线上,是至关重要的。当拜比吉从自己的友人数学家赫歇尔那里得到一份新计算出来的天文表格供他核查,并从中马上发现错误时,他宣布“我当真希望借助于蒸汽机来进行演算!”这样,他不仅表述了自己终身的宏大使命,即用机器(因而是准确无误的)演算函数,而且更进一步表述了我们迄今还在深入研究的一个工业化的基本问题,即在实践中对经验性自然科学认识予以具体的技术应用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他的著述《机器经济与大生产》出版了[注]参见Charles Babbage,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2.。1832年的第一版印刷3000册,同年出版第二版,1834年出版第三版,1835年出版第四版。这本书成为畅销书。该书第一部分即“一篇论述机器运用于大工业以及机械工艺的总体原则的论文”[注]Encyclopdia Metropolitana, London, Thomas Tegg, 1829。1832年,它与论述企业内部管理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的第二部分合在一起独立成册出书,书名《机器经济与大生产》。
显然,拜比吉的这本书触动了时代的神经,因为1833年此书受普鲁士行业协会委托,由弗里登堡翻译成德文,1833年和1834年翻译成法文,1834年翻译成意大利文,1835年翻译成西班牙文、瑞典文和俄文。它在欧洲范围内被广为接受,其检测发明与创新的构想对一代又一代技术人员和企业人员产生了深刻影响。拜比吉的理论也影响了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举办方案。
这本书有三重目标:1.研究因使用工具与机器而产生的效果与益处;2.将不同的效果予以分类;3.最终研究使用机器以取代人力之技巧与力量的原因及其结果[注]Charles Babbage, Die Ökonomie der Maschine,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1999, S. 15.。这样,拜比吉一板一眼地描述了那个年代在英国飞速发展的种种事物。这本书是他那个优劣并存的时代的产儿。他以乐观的基调宣传使用机器所带来的经济益处,即它为更高的生产力和日益富裕奠定基础。当然,他清楚地看到资本所有人与工人彼此利益不同,认为提高产品数量,产品价格就会降低。需求增加、供应商彼此竞争,长此下去就连社会底层人士最终也能享受产品,因而改善生活条件。但是,这只是一种抽象的、泛泛的考察。他清楚地意识到,并非每名工人都明白这一趋势。因此,他主张采取绩效工资(按数量计酬),以便在个人投入与个人回报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关系,形成直接有效的刺激。
我们来谈谈他的分析的核心,即劳动分工对生产过程管理的影响。拜比吉的论点是,劳动分工与机器的发展这两项发展可追溯到同一种认识,而科学史家彼得·布罗德纳曾对此加以描述:
将各个因素予以分析性分解,并将其综合性重组为一个合乎目的地运作的整体。在劳动分工当中,各项专业化劳作构成那样一些因素,它们在协作中共同制造整个产品。为了做到这一点,在设计时,相互协作的劳动过程就要设计成各项因素合乎目的的相互作用。同样,伴随着机器的发展,各项处理(或泛泛地说:各项功能)构成那样一些因素,它们合起来就带来可重复性运动的过程。在这里,关于彼此接合的运动过程的总体构想构成实质性综合。它需要在实际使用之前就对机器做出恰当的功能性描述,如以绘图、运动示意图或表格的形式来加以描述。拜比吉不遗余力强调它们的意义,并对描述它们的方式多有见解。夸张地说,在对机器的描述中,机器已跃然纸上;而在电脑中,机器则作为虚拟加工物而格外醒目。[注]参见 Peter Brödner, “Charles Babbage-ein Vordenker der Moderne”, in Charles Babbage, Die Ökonomie der Maschine,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1999, S. 23.
这一基本区别可以依据纺织机的发展来典型地予以展示。在18世纪纺织过程机械化的进程中,1733年凯(John Kay)发明了所谓的“飞梭纺织机”。作为对此的反应,1764年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了“珍妮纺织机”(1770年获得专利)。在哈格里夫斯看来,纺织机工作的机械化要求相当高:织纱是在所有织梭上同时进行的,随后成纱彼此分开地缠绕起来。此外,织工再不能用自己的手指添纱,而要对织机的运作形成一种感觉,织机是用像爪子一样的钳子工作的。这样,对织工技能的要求显著提高了。总地看来,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以织工(主要是妇女)经过大量的训练及其技巧为前提条件那些手工业者看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受到更为迅捷的“珍妮纺纱机”威胁,便捣毁了自己的工厂。此后,哈格里夫斯于1768年离开自己的家乡兰开夏的奥斯沃尔特威斯尔,前往诺丁汉,在那里的密尔街开办了一家小工厂,就在其出色的对手、“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的工厂附近。彼得·布罗德纳阐述阿克莱特做出的显著技术飞跃时说:在某种意义上,“珍妮纺纱机”是行将没落的手工业时代的最终回声。它还是用于提高熟练手工劳动生产力的高度复杂的工具,而“水力纺纱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独立的、由外在动力(大多是水力)驱动的机器设计出来的。它能够完全取代手工劳动。纺织的全过程被分解为抻拉、扭转、缠绕等基本运作,同手工过程相比,纺织过程借助于机械功能承担物而完全变样,最终组合成一个受外力驱动、持续不断且自动运转(也是机械性)的过程[注]同上。。这样,从“珍妮纺纱机”过渡到“水力纺纱机”,恰恰完成了向独立运作的机器的飞跃。
拜比吉没有回避机器发展的社会联系:“如果为了完善一个项目所必须的任何一个过程仅仅保留为一个个体的事情,那么更可能的是,其未加分散的注意力就会致力于完善工具,或该工具更为合乎目的的应用,而不是让纷至沓来的事情持久分散注意力。”[注]Charles Babbage, Die Ökonomie der Maschine,,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1999, § 224, S. 136.这样,我们就接触到所谓的“拜比吉原理”。他从斯密讲的实行劳动分工的大头针生产出发,指出斯密忽略的那一项最为重要的经济益处:“随着工作被分为多个过程,而每个过程要求不同程度的技巧与力量,工厂主便看到,自己对这两种素质的要求是随每一过程而定的。相反,如果一名工人要完成整个工作,那么他就要掌握如此之多的技巧和力量,一方面适应最为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适应最为劳累的过程。”[注]Charles Babbage, Die Ökonomie der Maschine,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1999, § 225, S. 138.换言之,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只需要购买不同艰难程度的各个环节分别需要的要素即可。
拜比吉的研究的一个优点在于其广泛的经验性基础。为了自己的项目,他周游全国,考察工厂并写下详细的工业调研。有意思的是,他运用的方法在今天属于经验性社会研究的范畴,即标准的调查问卷与访谈问卷,以便取得迅捷和细致的数据,为进一步的统计计算奠定基础。这些方法可提高可信性,提高数据及其演绎的可信度。重要的不仅是数量,数量仅构成生产运行的框架,而生产随时可以扩大。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细致地观察各个生产过程,确定特定的工业生产质量区别于简单手工产品之处。他这本书第一部分研究工厂实际生产过程,第二部分研究工业和贸易组织管理,如科学性劳动组织管理或科学性基础研究在工业中的应用。恰恰在这一方面,他极具创造性:他阐述了各种管理方法,如分门别类的劳动分工、根据协议而定的费用核算和工资体系。由于他自认是发明家,便同时界定了发明对于生产过程来说的作用。在第27章《机器的发明》中,他首先确定,当时绝大多数发明仔细看来并非真正的发明。它们并不成熟、不够实际、花销过大、过于昂贵,而且质量不佳。真正的发明应当是“那些既效果准确又操作简单因而令我们叹为观止的,只能在最为幸运的天才发明中找到”。但是,一名资本家如何能够检测一项推荐给自己的发明呢?在拜比吉看来,关键是根据绘图确定可信性[注]“实际上,任何发明、任何改善都要事先借助于绘图得以直观。”§ 319, S. 195.:“我们能给一项机械的发明者的最佳建议是,雇佣一位认真的绘图者。如果他专业经验丰富,那么有他帮忙,马上就可表明,那是否是一项新发明,随后他就可完成产品的制图了。首要的步骤是,确定这项发明在何种程度上可配得上新颖这一称谓,这一点始终是最重要的。对于艺术家与科学家来说,有效的基本法则就是,谁先前勤勉地钻研同时代人的认识,然后却不止步于再度发明此前很久或许就已经做得更好东西,谁就是在借助于新发现追逐财富与名誉。”[注]同上,§ 327, S. 199.换句话说,仔细地了解专业文献,可以掌握实际上此前已然由他人做出的“新发现”,随后,还要消除弱点,消除错误的尝试与测验。但恰恰在这时,由于工具或机器不完善,也会再度出现错误。这些错误会悲剧性地导致正确的理论考虑因错误的检测而备受非议。有时,成熟的机器得不到应用,是因为其费用相对高于其他方法。
总之,早在19世纪30年代,居住在伦敦并私下忙碌的拜比吉已然在广泛的经验基础上,提出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形式的理论。经济学家熊彼特论述拜比吉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将掌握某种简单的、却是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同细致地认识工业技术以及相关商业过程结合起来。这种近乎独一无二的组合使得他不仅可以列举大量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可以同其他作者相反地对这些事实做出解释。他还出色地塑造了概念:他对机器的界定和他的发明概念取得了当之无愧的声誉。”[注]Peter Brödner, “Charles Babbage-ein Vordenker der Moderne”, in Charles Babbage, Die Ökonomie der Maschine,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1999, S. 23.
三
大约在拜比吉的著作取得成功后10年,马克思也开始阐述工业生产问题。他的出发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资本运营方式问题、工人阶级作为在资本主义中受剥削的社会阶级的作用。1844年夏,马克思泛泛地研究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他生活在巴黎,自1845年起生活在布鲁塞尔,那时他讲法语比讲英语流畅,阅读英国作者的著作,当然读的是法文译本。就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而言,他也是透过麦克库洛赫的有色眼镜去读的,而后者片面且偷工减料地反映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直到在伦敦时,即自1851年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马克思才写下汗牛充栋的关于《原理》的笔记,包括1821年版新的第31章《论机器》,以及拉姆赛论财富分配的论文[注]参见Maxine Berg, 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3. Hans-Peter Müller, Karl Marx über Maschinerie, Kapital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Exzerpte und Manuskriptentwürfe 1851 -1861,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2, S. 120 ff.。这些笔记显示,马克思写下笔记时,机器问题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他着眼于自己的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和利润理论,感兴趣的只是作为经济学范畴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在他的笔记本中,拉姆赛只出现在“机器对劳动需求的影响”这一栏目下。他并不重视拉姆赛的看法,即李嘉图30年前关于工业发展的旧观点已经过时,因为这一期间技术进步呈现出一个飞速的过程:机器发明出来,种种改进已经做出,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劳动组织管理相应地细化。马克思评价拉姆赛的贡献时,将拉姆赛当作对立于斯密的进步理论家。但是,拉姆赛讲述从手工作坊到工厂的进步,并没有针对斯密,毋宁说针对的是李嘉图。拉姆赛的目的是,在工业发展的内部展示这种发展。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工业生产的物质因素及其在技术飞速发展这一进程中的变化所起的作用,马克思相对来说兴趣阑珊。
马克思接受拜比吉著作的情况也相仿。他使用的不是英文版,而是1843年的法文版,后来也不曾知晓德文版在1833年就出版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马克思写《资本论》草稿时,还仅仅援引法文文本。这显而易见在阅读中无足轻重之事有什么结果呢?马克思决没有认识到普鲁士行业协会自20年代起对英国工业发展的深刻观察和分析,而这种深刻观察和分析决不限于拜比吉著作的翻译。在德国和奥地利各种专业杂志中,都可找到大量前往英国的视察员的巡视报告,以及对科技展览和企业展览的深入观察和分析[注]这在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秘密档案馆的展览目录中一目了然:Klosterstrasse 36. Sammeln, Ausstellen, Patentieren-Zu den Anfängen Preuβens als Industriestaat, Berlin: GSTA, 2014.。1845至1846年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从尤尔(Andrew Ure)的百科全书中参考纺织业技术与蒸汽机技术。这部百科全书反映的是大约1820年的技术情况,相对于20年之后的技术发展,毫无疑问完全过时了。他真正对技术的研究[注]Akos Paulinyi, “Karl Marx und die Technik seiner Zeit“, in LTA-Forschung, Heft 26/1997, Mannheim: Eigenverlag Technoseum, S. 7 ff.在1851年肇始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主要是研究伯珀(Johann Heinrich Moritz von Poppe)筛选的《18世纪的机械》(1807年派尔蒙特版)、《普通科技教材》(1809年法兰克福版)、《应用于艺术的物理学》(1830年图宾根版)、《数学史》(1828年图宾根版)、《科技史》(1807-1811年哥廷根版三卷本),这些都是较老的著作。他手中唯一较新的著作是卡尔马士(K. Karmasch)和费伦(F. Heeren)编辑的三卷本《技术辞典或企业知识手册》(1843-1844年布拉格版),而它是以尤尔1839年的手册为基础的。马克思主要是从这部著作中摘引了论述蒸汽机、铁路、纺织业的一章,此时他的主要兴趣也是技术变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直至1862年他研究技术问题的第三阶段,涉及撰写《资本论》第12、13章时,他才在《资本论》中实质上中肯地描述了从技术史角度看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取得的具有决定性的进步,即工具机技术的推进。此时,为他奠定基础的,是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之后出版的概览式著作《民族工业》(1855年伦敦版),尤其是其中第二部分。他认识到,为工业扩张奠定基础的,并不像恩格斯与他本人1845年还在认为的那样,是蒸汽机的使用,而是自动化车床的发明。自动化车床可以独立于人力技巧,以机器的方式,以迄今为止从未企及的精密性、速度和熟练性生产机器部件,尤其是替代部件[注]工具机是用于塑造物质对象形态的工作机,这种形态的塑造始终形成于工具机与工件之间所谓的相互运动中。在手工劳动时,例如一名旋工锻造切削加工用的刀子或削切工具时,这取决于工人的技巧。它与塑造物质形态的机器劳动的区别在于,后者通过机器的相互运动来使用加工工具。这里的进步在于制造工件时的更高精密性,以及制造更多工件数量时保持的加工的可靠性。这自然首先是一个生产合理化方面,它可以在竞争条件下带来利润。它的效果是明显的:在改善质量的同时确保更高的数量。作为功能的承担者,在制作和加工工件时,工人精力与技巧有限。这限制他做得更好,即在塑造时无法取得更高的效能和更高的准确性。因此,工人被排除出劳动分工的生产过程,被更加胜任的机器所取代。参见Akos Paulinyi, "Die Umwälzung der Technik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zwischen 1750 und 1840", in Propyläen Technikgeschichte, Bd.3, hg. von Wolfgang Känig, Berlin: Propyläen Verlag, 1991, S. 269-513. Akos Paulinyi, "Kraftmaschinen oder Arbeitsmaschinen, Zum Problem der Basisinnovationen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in Technikgeschichte, 45, Stuttgart, 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1978, S. 178-188.。只有借助于这些崭新的金属加工技术,大量投入动力机和工作机并因此拓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才畅通无阻。但是,他最终对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关键性技术发展做出中肯分析,晚了大约20年。早在1841年,著名的机器制造者詹姆斯·内史密斯就描述了金属切削部门取得的这一基础性进步[注]参见James Nasmyth, “Remark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lide Principle in Tools and Machines Employed in the Production of Machinery”, in Robertson Buchanan, Practical Essays on Mill Work and other Machinery, Revised into a third edition with additions by George Rennie, London: Robertson Buchanan, 1841, pp. 393 -418.。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幅难以想象的景象:马克思生活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在大英博物馆研究过时的技术文献,尽管他原本同例如住在不远处的伦敦曼彻斯特区Dorset大街的拜比吉这样一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很容易就工业问题直接交谈,交换意见。
据不完整的工业统计,1851年,大不列颠有76500名机器制造工,其中55%在伦敦、兰开夏郡与西区(West Riding),20000名在兰开夏郡即棉花工业中心工作。自1841年起,那里就有115个机器制造公司、17000名工人、1个交易所,资金150万英镑。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的机器制造者都没有完成手工业教育的学业,例如莫兹利(Henry Maudslay)、罗伯茨(Richard Roberts)、福克斯(James Fox)、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和惠特沃斯(Joseph Whitworth)。他们天生就是独立的发明家。19世纪,缓缓地冲破种种阻碍后,工程师才成为受认可的职业。几十年后,工程师才成为模范人物,主要由于矿业、战争与经济中越来越多的机械化而声名鹊起。这是一个由受过专门教育的专家组成的特殊职业。除了建筑科学院外,他们在传统的国立学术院校之外的多学科行业协会中获得职业技能。在这方面,英国因1771年设立了国立工程师协会而遥遥领先。由英国占主导的机器制造的初始阶段终结于19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切削工具机都研发出来了,在1851年和1862年的两届伦敦世界博览会上骄傲地展示于世人。而马克思对世界博览会只是冷嘲热讽[注]英国资产阶级“举办这个博览会,就会使它从法国到中国的所有仆从面临一次严重的考验,使他们在这次考验中必须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就连全俄罗斯的万能沙皇本人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许多臣下参加这次重大的考验”。对于世博会的德国参观者,马克思也大加讽刺。(参见马克思:《国际评论(三)》(1851年5月),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02—503页;参见《流亡中的大人物》,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9—380页),尽管某项对那里展示的技术更为详尽的分析肯定给了他对“机械”的考察以具体的直观感。但是,马克思毕竟是位理论家,他从其他人的著作中有所选择地汲取自己的知识,并在10年后才认识到,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1863年,他致信恩格斯说:“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做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韦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在那里也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属于直观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17页。
除了维沃尔(William Whewell)于1841年出版了教材《工程机械》(1841年剑桥版)之外,罗伯特·韦利斯算是剑桥大学里机械方面尤其是机器工程师培训方面的权威教员。当然,马克思参加为工人开设的6课时讲座,对于机械入门来说无论如何足够了。换句话说,这名初学者了解了当时的机器制造。
因此,马克思把工具机现象同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置于一种逻辑性的、尤其可经验性追溯的联系中来研究。对他来说,“机器化”总地来说以生产过程的不断革命化为结果,因为它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劳动。从机器或者新技术的发明,到令劳动变得多余的“自动化工作坊”,种种细化都不会改变这种“合目的性”。资本的“运动形式”的果实只会落入资本家的怀抱。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技术的发展最终只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内在崩溃。
马克思将经济与技术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愈发导致“机器”概念模糊不清这一结果。“机器化”是劳动的一切物质条件与社会性变迁的论证性表征。这样,马克思虽然在经济与技术之间建立起联系,却是以得出抽象的、隐喻式机器概念为代价的,而这一概念很难同高度发展的工业阶段的现实相吻合。
最后,我们来看看电子领域内的发明和创新,并且追问恩格斯对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态度。
在19-20世纪之交,电子成了一个咒语,它在列宁的语汇中登峰造极,即苏维埃政权加电子导向共产主义。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通向技术天堂的道路显得畅通无阻。1890-1910年间,电子的魅力变得无以复加。它可储存、传输,并显然是清洁的,具有无限力量,却可细致分配,以至于所有家庭都可借此照明。前提当然是复杂的分配系统。只有当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和政治通力合作时,这一系统才可建立起来。
在弱电技术领域,包括自1835年起的摩尔斯电码,初始阶段的发明之路相当低调,并受制于应用。但尤其在英国和美国,为传递信息而对此加以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以至于电缆公司和电讯公司迎来高潮。受惠于英国股票法,人们将近乎25%的资本股息用来抢购它的股票。就连最冒险的规划,只要它是电子方面的,就被人不加怀疑地接受下来并给以投资。在法国,人们讲的“英国电气公司”不久就因破产和1882年的电气照明法而令人空欢喜一场。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强电技术的电子化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过程,因为在直流电与交流电系统的竞争中,公众舆论被当成工具。1866年,西门子发明自励直流发电机之后没几年,就可以铸造可应用于工业的不断提供直流电的机器。今天,人们可以使用非常明亮的弧光灯,比月光亮得多。1880年前后,伦敦、巴黎、底特律的公共场所就有各式各样五光十色的霓虹灯。
1882年,在慕尼黑国际电子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德普勒(Marcel Deprez)借助直流电在慕尼黑与米斯巴赫之间首次成功实现了电力传输。此后,热衷于这类技术发展的恩格斯谈论这一实际试验的影响说:“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线输送到迄今连想也不敢想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致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愈来愈不能胜任。”[注]恩格斯1883年3月1日致伯恩施坦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45—446页。虽然恩格斯关于极遥远的水力应用的预言为时尚早,但20年后纽约州就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建造了水电站。不过,他关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愈来愈不能胜任这一预言迄今尚未应验。在这一点上,他是拘泥于资本主义内在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对今天来说,利用像数字化这样的进步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这一问题仍然在议事日程上。对塑造未来世界的社会来说,这一问题是核心性的。我们这里进行交流的每个人,都要好好研究创新的技术含义。这在18世纪是劳动分工,在19世纪是工具机问题,在20世纪是自动化,在21世纪将是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