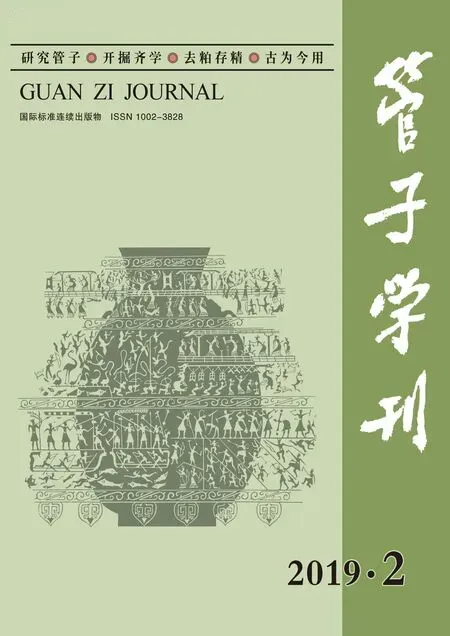论《晏子春秋》的拟托性质
——兼谈拟托文与小说的联系与区别
苗江磊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本文所界定的拟托文,是指托名于真实历史人物而编造相关事迹的战国书体散文。它的基本特点包括:其一,拟托文的叙事围绕历史真实人物展开;其二,拟托文的情节与内容存在虚构成分;其三,拟托文属书体文本作品。本文拟以《晏子春秋》为考察对象,通过研究相关拟托文的性质及其与文学小说的联系与区别,揭示拟托文作为战国盛行的一种独特文体的存在意义。
一、《晏子春秋》成书年代与流传
《晏子春秋》一书,《汉书·艺文志》载其卷数乃是八篇,并未涉及创作者[1]1724;《隋书·经籍志》则著录此书为七卷,撰作者题名是齐大夫晏婴[2]997。作者容后再论,先考《晏子》一书的成书时间。或有学者提出是书乃是战国之时所成;还有学者认为此书应作于秦末汉初之时,如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认为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3]23,写于秦统一六国之后;甚至有人以为此书乃六朝人伪造,如管同《因寄轩文初集·读晏子春秋》曾道:“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然则孰为之?曰:其文浅薄过甚,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欤?”[4]419。然而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之中发现了《晏子》竹简,此墓年代为西汉初年,使六朝伪作之说不攻自破。董治安先生于《说〈晏子春秋〉》一文中,着重借助汉人作品中多见的《晏子春秋》材料及词汇、《左传》记述内容同《晏子春秋》的区别、《晏子春秋》书中的文辞可借助参订秦汉时期作品内容等因素,判定出《晏子春秋》应当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注董治安先生所论《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说已渐获学界认可,本文遵从此说,“现在通行的《晏子春秋》,应该就是刘向所校录过的本子”[5]。对战国成书之说,高亨先生亦持肯定意见,并进一步提出《晏子春秋》当是“齐人或久居齐地的人所作”[6]292-309。而《晏子》成书于战国时一说亦能从出土文献方面得以证实,简本《晏子》的内容与传世今本庶几相同,在文章规模、篇目特征及语句词汇上都十分相近,故而今传《晏子春秋》必不可能是后人伪造拼凑之作,而应“与刘向整理前、汉代前期流传本是一个本子”[7]88。
对此书流传情况,司马迁于《史记·管晏列传》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8]2136司马迁直言“曾读《晏子春秋》”,并提及“其书世多有之”,则此书应是以文本形式传播的。且《史记》所录晏婴两轶事皆见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所录御者妻劝御者事与《晏子春秋》之记叙几无一字更替,刘向《晏子叙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9]1司马迁所谓“轶事”,应是其见版本中未含此文,而刘向参校众书时见此两篇,可知此书当时应有不同抄本流传。所见抄本各异,再加上前所提银雀山简本《晏子》与今本在篇章上存在些许差别,如简本《晏子》第十篇与今本内容相同,但今本分作两章,这些现象都说明,《晏子》其书世多传本,确有其事。此书流传之广泛,从其他文献对其援引中亦可证明。如《韩诗外传·卷九·第八章》齐景公纵酒,醉而乐,使人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景公愿晏子去礼,晏子言“君言过矣”,恳词以谏,引《诗》“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景公悟而改其行[10]313,其文近于《晏子春秋·外篇·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仅更少数词句。相似之例不胜枚举,就《史记》《韩诗外传》等书记事与《晏子春秋》文字大略相同、极少更替之情况来看,此书自战国成书后便应是付诸文字、著成书体而流传的,所以引述晏子故事时基本与《晏子春秋》所载一致。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将此书归儒家之类。至唐,柳宗元提出《晏子春秋》一书当是墨家学者之作品。因为书中于记述晏子其人其事过程中,体现出了许多墨家学派的思想,且文中又多有“墨子闻其道而称之”等类似之言。因此,柳宗元提出《晏子春秋》应为墨家学派为增高己术而作,“为是书者,墨子之道”[11]113。此说后世亦不乏拥趸者,譬若宋代晁公武即是。而至《崇文总目》中,《晏子春秋》复而归入儒家类,并著录存有十二卷,“原释晏子八篇今亡,此书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12]127。这一观点在元朝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中得到了因袭。是以可知,入唐后,《晏子春秋》具有托名创作的可能已经逐渐被学者发现。直接提出此书存在托名性质的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总目》判定此书乃是题名晏子的依托之作,后世之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13]514。惜诸书未详释托名晏子之情况,既知此书为战国书体作品,便须回归此书具体篇章中进行考察。
二、《晏子春秋》含非实录之文考辨
何以说此书非晏子自撰?因书中记有晏子死后之事,《内篇谏上》有《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章,直言“及晏子卒”,景公为失晏子之谏而泣,此文显乃晏子卒后追慕之作。《外篇》亦有《晏子死景公弛往哭哀毕而去》《晏子死景公哭之称莫复陈告吾过》,皆记景公闻晏子死,往而吊唁,念晏子对其忠谏之语,哀泣痛哭。更有《晏子没左右谀弦章谏景公赐之鱼》,乃“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感慨“不复闻不善之事”,弦章答“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景公以鱼五十乘赐弦章,弦章辞而不受[9]219。上文涉晏子身后诸事,绝非晏婴自撰。
《晏子春秋》一书的215篇中,其内容见于《左传》记载者仅15篇,与先秦子书记载相合或类似之文有9篇,而余者多不见于史书及他书记载,且其文时有乖悖时间、历史、社会环境之处。
首先,书中多有时间错乱之事。《内篇谏上》第十一章《景公欲废适子阳生而立荼晏子谏》,景公爱孺子荼,“欲废公子阳生而立荼”,晏子以为不可,止景公曰“夫以贱匹贵,国之害也;置大立少,乱之本也”,劝君勿废阳生,并预言后世将以此作乱“恐后人之有因君之过以资其邪,废少而立长以成其利者”,但景公不听其言,则终成祸乱,“景公没,田氏杀君荼,立阳生;杀阳生,立简公;杀简公而取齐国”[9]15。但据《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景公欲立公子荼之事在景公五十八年,而晏婴于景公四十八年卒[8]1505,已去世十年,何来以上劝谏及预警诸言。
例如,《内篇杂下》第八章《晏子使吴吴王命傧者称天子晏子详惑》,吴王夫差见晏子时,故意命傧者通报“天子请见”之言。当傧者三呼“天子”之名时,晏子便表示疑惑,自己为齐侯遣,出使吴国,但却不慎入天子之朝,不知吴王何在?吴王愧然悔改,道:“夫差请见。”仍然执行诸侯礼仪召见晏子[9]157。但晏子与吴王夫差并非同时之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十二诸侯年表》又载齐景公五十三年才为吴王夫差初年[8]671,可见文中两人相见之事不实。
《内篇问下》第二十八章《曾子问不谏上不顾民以成行义者晏子对以何以成也》,曾子与晏子关于隐士是否称行义者的问答,《内篇杂上》第二十三章《曾子将行晏子送之而赠以善言》,晏子临别时赠言曾子,望其择善而从[9]120、142。这些都记有晏子与曾子会面。但孔子乃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参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言曾子少于孔子“四十六岁”[8]2205,可知曾子大抵出生于齐景公四十三年(即鲁定公五年),曾子五岁之时,晏婴已经去世,而曾子尚且年幼,又如何能有此二人对答、赠言诸事?可见其文不真。
《外篇》中有《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致问》一篇。弟子问孔子,为何在齐国拜见齐景公却不见齐相晏子。孔子答道:“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9]208此言为晏子所知后,晏子对孔子困于陈、蔡之事大加嘲讽,“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9]209,晏子指责孔子尚未与他见面就对他的顺君之行有所非议。然而,晏子所言“孔子困陈、蔡”一事悖于年时。“孔子之齐,晏子讥其穷于宋、陈是也。鲁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齐,至哀公三年孔子过宋,桓舱欲杀之,明年厄于陈、蔡断粮,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后,今晏子乃于之齐时递以讥孔子,岂理也哉?”[14]134可见此文确有非实之处。
其次,书中存在乖悖史书之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15]2092,梁丘据与裔款进言,君此病为祝史之罪,欲诛祝固、史嚣,公以此告晏子,晏子举范会之德治劝说齐景公,因范会族内事务井然,所以祝史向鬼神陈言无愧;又因其家无猜疑之事,所以祝史亦无祈言,继而晏子进一步向景公阐释鬼神是否飨其国,与君主德行相关,劝谏齐景公修德,于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15]2093。此事亦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章《景公有疾梁丘据裔款请诛祝史晏子谏》,此段与《左传》记载完全相同,仅于最后多“公疾愈”[9]185一句;而《内篇谏上》第十二章《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虽本景公欲杀祝史以悦于上帝之事,但下文内容与上述两则材料有一定差距。齐景公召会谴、梁丘据、晏子问诛祝史“以说于上帝”之事,会谴、梁丘据赞同,晏子先沉默不对,经景公再三追问,答曰“夫祝直言情,则谤吾君也;隐匿过,则欺上帝也”,以为诛祝史无益,不愿齐景公刑无罪,但其阐释中未引“屈建问范会之德”为据。景公大悦,加封晏子:
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会谴毋治齐国之政,梁丘据毋治宾客之事,兼属之乎晏子。晏子辞,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为有力,邑孤与谷,以共宗庙之鲜,赐其忠臣则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请赐子州款。”辞曰:“管子有一美,婴不如也;有一恶,婴不忍为也,其宗庙之养鲜也。”终辞而不受。[9]16
景公罢会谴、梁丘据,将齐国之政、宾客之治皆属晏子,后又赐重赏,晏子辞拒,这些描述均不见于《左传》中。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晏子春秋》外篇叙事同于史载,内篇此章却多有增创情节。史书的记载,往往多遵于历史实事的本来面貌,应当鲜有随意地增删、改创。就此推断,该文与《左传》相异之处应非实录。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饮酒乐,羡慕上古之人能长生不死,以“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紧接对答,当初爽鸠氏居此地,死后季荝承其遗志,其后逢伯陵继之,再后蒲姑氏袭之,再至大公承袭,因承续、复奠其业而其志不朽,此所谓之古者不死,但爽鸠氏诸人所求之乐并不同于景公所言之乐,“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15]2094。《晏子春秋·外篇》有《景公问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谏》一文,同于《左传》记载;而《内篇谏上》第十八《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亦以景公悲叹“使古而无死”开篇,晏子进谏之言却变为:若古而无死,则先君贤臣将长有齐国,君将不得此位,“君将戴笠、衣褐、执铫耨,以蹲行畎亩之中,孰暇患死”[9]25。下文更视角一转,再叙晏子劝谏二事:梁丘据暑日疾驰景公赞赏,晏子却反对,此乃行事“同于君”而不为“和于君”,于君无益;日幕后景公睹彗星之象,召人禳去之,晏子曰此乃天教[9]26。且“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一事见载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与齐侯羡“古而无死”并非同年之事,此文与史载多有不合,并非完全实录。
再次,《晏子》一书中还有不少重复叙事之作,这些作品常常体现出利用相近或雷同的故事情节与内容。譬若,《内篇谏上》有两篇作品皆提及晏子故意出走劝诫齐侯。譬如书中《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和《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两篇。前文中,晏子因齐景公沉迷饮酒,不准自己的发粮救民之请,愤然出走,“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景公悔悟而追回晏子,自言有罪,“愿夫子之幸存寡人”。晏子于是返回齐国[9]7。后文中,晏子劝说齐景公不要信谗近佞无果,只得出走,“鞭马而出”。齐景公便派遣韩子休追回晏子,令韩子休代言其悔过之意:“夫子休国焉而往,寡人将从而后。”是以晏子复返归国[9]12。两文中皆袭用了“晏子出走”的情节,但晏子再三凭借出走之法激将景公,未免不合情理,难信其实。而且后文更加入了晏子与其仆的问对之事,仆役问晏子为何再度归齐,晏子答道:“公之言至矣。”[9]12然而,两人于马上的隐秘对话如何传出?此处更像是创作者着意增创的细节描写。两文中“晏子出走”的情节如此类似,不似皆实事。
聊举数例,以资反三。《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与《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两则,都套用了晏子极力劝止齐景公废礼的情节,颇为类同。又有,《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无宇致封邑晏子辞》与《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辞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三则,都记叙了晏子辞拒齐景公封赏的情节。但三者并非单纯内容重复,前两文是借助晏子与景公的对话架构篇章,第三则是利用晏子与田桓子的问对展开叙事。此三者显然有据相似情节而另立新意的创作主题。这样存在叙事相近、情节类似的篇章,在《晏子春秋》中不胜枚举,其文多重复,并非以实录为目的记载晏子事迹。
除异文相似之外,还有一篇之内言辞重复之文,《内篇问下》第十二《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称不敢与》叙景公饮酒,邀晏子、司马穰苴及梁丘据三人,其应对为:
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前驱款门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盅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戈,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穰苴对曰:“夫布荐席,陈盅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乐哉!今夕吾饮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9]132-133
晏子与司马穰苴的对答之辞竟如出一辙,何能默契至此;且景公夜至晏子、司马穰苴、梁丘据之家,应无史官随行,即便晏子有门人宾客记下此事,又如何能往来于司马穰苴与梁丘据之家记其二人言行。于事理难通,应非为遵史实录。
可知《晏子春秋》虽多记晏子言辞,但却不同于《论语》《孟子》等语录体子书,并非实录晏子言行,其书约有近八成的篇章是围绕晏子创造的非实录之文。
三、《晏子春秋》拟托文属性辨
正因为《晏子春秋》一书存在非实录的篇章,后世多有人疑其为伪作,但从传世文本及出土文献中皆可证明,此书成书于战国时。我们认为这些记录晏子言行的特殊篇章,正是有意虚拟而造的拟托之文,是假借晏子之名而虚构创作的一类作品。
拟托文是托于历史人物的作品。晏子“名婴,平谥,仲字”,为齐相,历三朝“事齐灵公、庄公、景公”[8]2134。此书托晏子之名,以其为中心创作,基本符合晏子的活动年代。晏子辅佐灵公、庄公与景公三代,达五十余年,此书皆记叙晏子于灵公、庄公及景公治下的相关事迹,涉灵公与晏子的相关故事有1篇、庄公6篇、景公有157篇。而与晏子同朝为臣的齐国崔杼、司马穰苴、梁丘据,曾与晏子相交的叔向、陈桓子,于齐“严事”晏平仲的孔子[8]2186、及其亲友门客等人,都见著于此书之中。关于叔向与晏子的问对之辞便有11篇,与陈桓子相关之事2篇,书中还有多篇孔子赞赏晏子行事之文,《景公出田顾问晏子若人之众有孔子乎》《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等,都是晏子与孔子的相关故事。可见此书行文确实是遵循了晏子所处时代及其交往关系,按晏子齐相之身份创作。
而拟托文又是存在虚构成分的作品。前举书中诸多不合时间、地点或历史记载的非实录之处,正是战国时着意创作的结果。这些拟托文或托晏子之名架构对话,或基晏子身份而虚造行事。此书拟托文中,有不少以虚构人物对话、谏言为主之作,譬如前举无从发生的晏子赠言曾子一文,假托晏子谆谆叮嘱“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9]144,以论君子择处之道。再如《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晏子对以桔》等文,叙述晏子使楚之事,于史无征,且仅取入楚轶事,非为实录,应是托名晏子而拟造相关言辞。前者中楚人欺晏子身小而令其入小门,晏子对以“使狗国者,从狗门入”;后者记晏子面对楚王挑衅,答曰“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9]158,又以“桔生淮南为桔,生淮北为枳”应对“齐人坐盗”之事[9]159,彰显其外交辞令机敏。而且,拟托文还擅于用多种修辞手段与进言方式虚构晏子谏言、辞说,《内篇谏上》有《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晏子谏》和《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一篇为野人骇景公所射之鸟,“公怒,令吏诛之”,晏子以“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无仁义之心,是以从欲而轻诛”进谏[9]34,景公释之;另一篇为景公之爱马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9]34,晏子先止景公肢解人之刑,后以“三数圉人之罪”巧言令景公感慨“勿伤吾仁”[9]36,释放圉人。两篇中,唯有景公所爱之鸟与马两物的不同,而情节结局基本雷同,不应皆为实事,正是托晏子而着意创造进谏之词。第二篇中晏子先反问景公“古时尧舜支解人,从何驱使”[9]35,令景公惧然;后正话反说,举圉人当死之三罪,“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使公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当死罪三也”[9]36,以使景公悔悟。这些虚构对话的拟托文,托晏子之口展现辞说,或婉言、或讽谏或至于直斥,深入刻画了的晏子贤良与忠正。
还有虚构事件或情节的拟托文,如《内篇杂上·庄公不说晏子晏子坐地讼公而归》,庄公不喜晏子,令乐人奏歌示其意,晏子北面坐地而讼,直言“好勇而恶贤者,祸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谓矣”,归而东耕于海滨,数年后果有崔杼之难[9]123。但崔杼弑君后,晏子哭尸,并未东耕,且庄公之难缘于其好色,此文不合史实,是假托晏子虚构此讼公之事,作品已具情节起伏与前后因果。另外,《晏子春秋》中重复叙事之文,亦存在对情节的虚构,《内篇谏上》有《景公饮酒酲三日而後晏子谏》《景公饮酒七日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皆以景公饮酒多日后晏子进谏为题,同事异词,应为托名拟造之文。《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中弦章痛心景公饮酒数日之逸,以死劝君废酒,公告晏子弦章之言,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景公自然不忍比于桀纣,于是废酒[9]6。此类拟托文假托晏子而虚构情节,有些作品叙事首尾完整,已具稚拙、简略故事规模。
而拟托文这种虚构并不同于史传文学的想象,史书想象往往遵循历史事实展开,是对事件的一种补充描述和添加扩展,如《左传·隐公三年》“郑伯克段于鄢”,详述郑伯“寤生”惊其母姜氏、姜氏宠爱其弟公叔段、郑伯对其弟不义之事“放任”、后攻克其弟以及郑伯与姜氏“大隧相见”和好等情节,是“史书借用了说体故事才使得记载生动”[16],是为了增加叙事的完整性。但拟托文虚构对话与情节,本无从发生亦无可考证,是借用历史人物名气、身份而进行的着意创作;并且这种虚构创作也不受事实背景、情理逻辑或情节完整的局限,常常选取片段展开叙事。
由上,《晏子春秋》中确有一批托名晏子而编造对话或情节的拟托文,创作者的着意为之使其具有相当的非真实与不合理性。而正是这种虚构的特性,使拟托文成为文学走向自觉创作之前的重要一环。
四、《晏子春秋》拟托文与小说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肯定,拟托文的确与文学体裁的小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种含义,一是于《庄子·外物》中最早提出的小说一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已远矣”[17]177,指的是琐屑言谈,后来所谓小说家一类,其所搜小说就是传闻杂说故事等,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18]69,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1745此以琐屑丛杂为特征的小说概念,在古代目录学中一直沿用;“小说”另一含义,是指唐以来对平话、演绎、拟话本的称谓,如宋代罗烨《醉翁谈录》用“小说”作为说话艺术的总称,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19]3。可见“小说”一词,“有文学性文体的部分,也有非文学性文体的部分”[20]3。但无论是“道听途说之所造”残丛小语,亦或大盛于宋代的平话、话本,其所暗合的都是作品中存在无中生有、虚构想象的特性,这一点与近现代文学性小说的概念是有共通之处的。小说正是以虚构反映人生,“一部小说表现的现实,是它对现实的幻觉,使读者产生一种仿佛在阅读生活本身的效果”[21]207,虚构化创作使文学小说区别于实录作品,着重于展现文中的人物命运、生活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小说基本特征定义为“以散体文的形式表现叙事性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关系、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体的艺术描写”[22]1085。《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的创作,其虚构对话、事件,都有近于小说的虚构因素之处。
二者在虚构因素上的相合,也使拟托文的创作表现出相当大的自由,行文叙事会出现夸张离奇,甚至不近情理之处。比如《内篇谏下》第二十四《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勇而无礼,晏子劝景公杀此三人,景公以三人刚猛,明杀暗刺都难成事,晏子献策“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令三人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以己曾搏猏复搏乳虎,“援桃而起”,田开疆道曾接连击退敌军,亦“援桃而起”,而古冶子自言尝从君渡河,遇大鼋衔车左边之马以入水流,于是他潜入水中,逆流百步,顺流九里杀鼋,左手握马尾,右手提鼋头,鹤跃而出,人皆谓其曰:“河伯也!”并责让前二人拿出桃子。公孙接、田开疆以功不及古冶子,却贪桃而食,皆返桃自尽,古冶子亦愧而自杀[9]63。古冶子所言搏鼋救马、鹤跃出河奇异怪诞,应为虚造情节。再如《外篇》第十三《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详对》,景公以“东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枣,华而不实”询问晏子,晏子对答曰从前秦缪公乘龙舟巡视天下,用黄布裹蒸枣。至东海时弃黄布,故而海水呈赤色,又因是蒸枣,所以开花而不结果。景公曰:“吾详问子,何为对?”曰:“婴闻之,详问者亦详对之也。”孙星衍云:“详问,《文选》注作佯问。”[9]215晏子知景公虚设其事,故意编造另一传说来回答,其言荒诞不经。上述拟托文在虚构中存在明显离奇、神异色彩,如同小说般文辞生动。
但《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与文学性小说仍不能相提并论,二者在许多方面仍然异大于同。
首先,就二者创作目的而言,文学具有审美特质,须取悦受众,作为文学文体中的小说一类,是走向自觉后的纯粹文学性活动,是为了供人阅读、欣赏而存在的,不论是仍与历史人物有关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还是《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世情小说,亦或是“三言”“二拍”之类的话本小说,其作品之创作都以愉众审美为目的。
晏婴乃齐国贤相,德行昭彰,后人思慕敬仰而作其相关事迹;而同为齐国之相的管仲,亦有人作《管子》一书刻画其行事及言辞,这种看似的巧合实际都指向齐国稷下学宫的兴盛繁荣,与稷下学士的创作应有密切关系。学者曾提出《晏子》或为稷下学宫学者而作[23]。稷下学宫设于齐桓公田午时:“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24]341稷下先生以讲学和著述培养弟子,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8]1895故而,稷下学士的职责仅是议论与品评时事政局,“不治而议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记载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8]2346稷下之士们,在议政劝君的同时,常常凭借他们对政事看法而著书立论、立说,“著书言治乱”。所以我们看到《晏子春秋》之中,许多拟托故事都是在着重刻画君臣之间的奏对与进谏事迹。这些作品用相当的虚构色彩,展现治国之道抑或谏君之策。《晏子春秋》的拟托文很可能是稷下学士在演练、模拟议政的过程中,借晏子之名创作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晏子春秋》中有很多情节、对话类似之文,因为稷下学士常有“据同题”“据同事”而另立新意的模拟议政创作。譬如,《内篇谏上·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与《外篇·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皆为景公饮酒不顾礼,晏子进谏后悔悟改行。这般基于同题而作晏子行事与言论之文,或为人借晏子发论,与稷下学士之议论政事风气有关。可见,《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并非产生于单纯的审美与欣赏需要,或兴德政、或吁民生、或倡廉吏,每篇拟托文都有具体议政主旨,借晏子之名欲以阐明其议政内容或道德理念,不是仅为供人观赏。
其次,从人物塑造而言,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老舍先生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怎样写小说》),所谓创造,便要造其外貌、情感及心理等诸多要素。《晏子春秋》拟托文托于真实人物晏子,并未于创作中凭空虚构人物;且其文中少有具体描摹人物心理活动、刻画情感起伏之笔,多直接遵于史书中对此人的形象记载,展开相关创作,并未达到虚构人物的境界。
最后,就其具体内容及情节而言,《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故事较之于后世小说更显得稚嫩朴素。小说叙事必要有起因经过,又要具备高潮结尾,多关注内容细节,将人物置于完整背景下描述其行为活动。若《搜神记》中《三王墓》从干将、莫邪铸剑被杀讲起,及其子长,遇客为其复仇,客持其头献楚王,一步步推向高潮,煮头三日,王临镬视头,客斩王头与己头并落锅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前后叙事完整,亦有细节之笔,如莫邪子自刎奉头及剑予客,“立僵”,至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扑”[25]128,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但《晏子春秋》中拟托文多仅靠语言推进情节、塑造晏子形象,不少篇章说辞便占一半以上,虽有初具故事情节之文,但更多还是截取片段以成篇章。如前举《外篇》中《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详对》《景公问天下有极大极细晏子对》,仅以问对之言便成一篇,并无前因后果之交待。
足见,《晏子春秋》中拟托文虽有编造对话、情节的虚构成分,但仍不具备完整的小说要素,仅是含有虚拟创作因素的战国散文作品,不能将《晏子春秋》等同于后世小说文体。
要而言之,《晏子春秋》中存在为数不少的带有议政、说教、训理及追慕晏子之目的创作而成的拟托文。拟托文既与历史史实和虚构创作相联系,又是区别于史书及后世小说文体之外的一种创作,它体现着文学在走向自觉过程中的尝试与过渡。举一反三,战国时其他著作如《庄子》《战国策》等书中,亦有颇多托名历史人物而拟作其事之文。这种拟“虚”而托“实”的创作现象,“于战国散文作品中已成风气”[26]。可见战国虚拟创作蔚然成风,的确值得我们深入关注、探究与挖掘。
——晏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