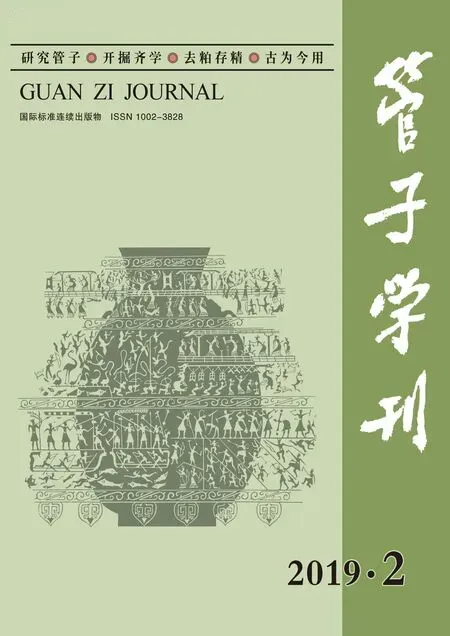唐宋沿海港口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
——以广州、泉州、明州、登州为中心
胡 方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河源 517000)
中国古代沿海港口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促进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陆上和海上两条通道,与亚洲、非洲、欧洲许多地方进行包括丝绸贸易在内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海上丝绸之路起自中国沿海各港口,或向东经东中国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交通;或向南经南中国海连通东南亚各地,进而西进印度洋,与印度洋乃至地中海沿岸交流。唐代以前,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唐宋时期,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连通中国与亚、非、欧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渐兴盛,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也因之迅速发展。城市空间作为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空间载体,随着城市的发展自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沿海港口城市所具有的经贸口岸、交通枢纽、文化窗口等职能,使得其城市空间形态及其演变,与内陆城市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来自政治军事因素的推动。而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虽然也受到政治统治、军事控制等方面的影响,但经济贸易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往往会大于一般的内陆城市。唐宋之际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变革期。沿海港口城市突出的经贸交通功能,使其在这一变革进程中得风气之先。唐代,登州、广州分别是南北海上交通最为重要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和“广州通海夷道”的始发港[1]1146;宋代,朝廷在重要港口设置市舶机构以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明州(庆元府)的市舶机构最为持久稳定。基于此,本文拟以广州、泉州、明州、登州等港口城市为切入点,对唐宋时期沿海港口城市的空间形态及其演变予以探讨[注]相较于唐宋沿海港口城市在海上交通贸易中的地位、作用等方面,学术界对海港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曾昭璇的《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周霞的《广州城市形态演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高宁的《南汉时期兴王府城形态结构初步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邢君的《宋代广州城市工商格局》(《华中建筑》,2008年第6期)、孙翔、田银生的《宋代广州城市空间形态初探》(《华中建筑》,2010年第1期)、庄景辉的《泉州子城址考》和《泉州罗城址考》(庄景辉:《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泉州海外交通史调查组的《泉州城南宋元中外贸易繁盛区的调查》(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1983年)、付君的《泉州古城空间形态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唐勇的《宋代明州(庆元)港城研究》(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高源的《登州城兴衰之地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董韶军等的《试论蓬莱水城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等对唐宋广州、泉州、明州、登州城市规模、形制、布局的考证、复原等。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体城市的个案研究方面,而对于沿海港口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类型,其空间形态的整体性特征,则关注较少。。
一、城垣空间的拓展
唐代海上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兴起,这首先表现为其行政地位的提升。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作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的行政统治中心而建立的。秦代开始推行郡县制度,地方各级行政治所实际上成为区域的各级中心城市。城市的地位、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行政级别的高低。唐宋时期沿海的主要港口城市,除了广州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岭南东部的行政中心,其他如登州、泉州、明州等,虽然在秦汉魏晋时期就已在海上贸易中崭露头角,但直到唐代才成为州一级治所,城市也因之有了新的发展。
登州,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始置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治文登县。贞观元年(627年)废。武周天授二年(691年),又分莱州(治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置登州,治牟平县。神龙元年(705年),迁州治于黄县蓬莱镇(今蓬莱市),并设蓬莱县以为附郭,也进行了相应的城池建设。所建登州城北临大海,城垣“(东)西一里,南北一里”,城周四里许[2]72。
泉州,位于今福建省南部晋江入海口附近,始置于唐武德五年[注]以唐景云二年(711年)为界,此前所称“泉州”,治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景云二年,改泉州为闽州,辖境以今天的福州为中心;又在闽南设泉州,辖境以今天的泉州为中心。。当时称丰州,治南安县(今福建省南安市丰州镇)。贞观九年废。其后几经置废,至久视元年(700年),又置为武荣州。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开元六年(718年),州治向晋江下游迁移,并析南安县置晋江县(今泉州市),以为泉州附郭[1]1065。
明州,位于今浙江省东部甬江入海口附近。开元二十六年分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置明州,治鄮县(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大历六年(771年),鄮县县城迁至三江口(今宁波市),州城仍在原址。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州治也迁至三江口,改鄮县治为州治,并营建了新的州城[3]1091。
古代城市作为地方行政治所,其设置和择址,虽然直接受到各种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登州、泉州、明州等在唐代相继设为州治,与海上贸易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三座州城城址的选择和变迁可以看出这一点。登州由牟平迁至蓬莱;泉州由南安迁至晋江;明州由小溪镇迁至三江口。三城城址的变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逐步趋近海滨。泉州、明州是河口港,通过晋江、甬江连通大海,因而城址都沿河道向下游迁移,逐步靠近入海口;登州是海湾港,城址在诸处港湾中选择,最终“临海立州”[2]152,把州城确定在港湾深阔的蓬莱湾畔。
登州、泉州、明州等城市设立之初,城垣规模普遍较小,大体一里见方,城周四里许。广州虽然长期是岭南重镇,但其城垣沿袭六朝规模,城周也只有四里左右。唐五代以迄两宋,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这些港口城市的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城垣空间不断拓展。
广州城在唐末南汉两宋几经增拓,由唐代的一城拓展为中东西三城,并建成了由城垣延及珠江(时称“小海”)岸边的雁翅城,城垣规模大幅扩展。唐末,清海军节度使刘隐“以广州城隘,凿禺山益之”[4]263,凿平广州城南的禺山,将城垣向南拓展。宋代广州城又多有营建。庆历四年(1048年),广南东路经略使魏瓘在唐南汉广州城基础上加筑城垣,即子城(又称中城),周长五里许。子城主要是官署行政区以及与之配套的居住商业区。熙宁二年(1069年),经略使吕居简在子城东侧兴建了东城,城周四里。熙宁四年,经略使程师孟又在子城以西兴建了西城。西城规模比子城、东城都大,城垣范围达十三里。西城是商船由珠江进入广州的主要停泊地,也是唐代蕃商聚居的蕃坊所在,因而成为广州最重要的商业区和蕃商居住区。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又在城南修建了直抵珠江岸边的东西雁翅城,用以围护珠江沿岸的商铺住户。广州城经过多次营建,呈现出子城(中城)、东城、西城三城并立,雁翅城南面拱卫的空间格局。
唐宋泉州城也屡有增拓,逐渐形成子城、罗城、翼城重城相套的格局。唐代泉州仅有子城。至唐末,刺史王延彬始在子城外围增筑了罗城。南唐保大年间(943-957年),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又对泉州城加以营缮,在唐末罗城的基础上,重加版筑,建成周长二十里的城垣,使泉州形成了重城相套的格局。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知州游九功又依托罗城南垣沿晋江岸边修筑翼城,使城垣延伸到晋江岸边,把晋江沿岸的商业区和蕃商居住区括入城内。
明州迁治三江口时,所筑州城“周围四百二十丈”[5]4960,约三里许。乾宁年间(894-898年),刺史黄晟在城外修筑了罗城,“周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计一十八里”。五代时期,吴越国又对明州城予以增筑,“城郭增壮自此始”[6]5102。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曾巩知明州,修葺城垣,并特意营缮了通往城外码头、“当高丽使者出入”的两座城门[7]794。南宋时,明州以地近临安府,被视为“浙左股肱之郡”[8]5417。庆元元年(1195年),升格为庆元府,地位日重。宝庆(1225-1227年)、宝祐至开庆(1253-1259年)中,知府胡榘、吴潜等,又相继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更新了通往城外码头的灵桥、东渡等城门。
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的蓬勃发展相比,登州的海上贸易则由于宋辽对峙的形势,从北宋中期开始衰落。宋初,登州仍是重要的外贸口岸。《文献通考》载:“祖宗(指宋太祖、太宗)时海中诸国朝贡,皆由登、莱。”[9]8629北宋中期,由于宋辽战事,宋朝封禁了登州口岸,“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10]2637-2638登州海上贸易由而陷入停滞,城市建设也朝着战备需要发展。“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自景德(1004-1007年)以后,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11]2424庆历二年(1042年),又在城北建刀鱼寨,驻扎水师,以为京东海上捍屏。
唐宋时期海港城市空间的拓展,主要是商业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发展的结果。由于原先城市规模较小,已经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的需要。在城垣拓展之前,基于就近交易的便利,在城外的港口码头周边就已自发形成了人口稠密、贸易兴盛的商业区和居住区。唐宋时期修建的外城,主要是为了把城外商业街市括入城内。如广州城西在唐代就已形成了繁盛的商业街区,但一直未能括入城垣之内。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侬智高乱,兵至广州城下。广州知州仲简“婴子城拒守,城外蕃汉数万家悉为贼席卷而去”[12]5767。城西的商户、居民损失惨重。此后修筑西城,就是为了保卫城外的商业街区。明州未筑罗城之前,城外居民的安全也无以保障。“此郡先无罗郭,民苦野居。”至唐末黄晟筑罗城,才得以“绝外寇窥觎之患,保一州生聚之安。”[6]5102这些海港城市城垣的拓展,实际上就是把原本地处城外自发形成的商业区和居民区括入城内。由于这些城外商业区主要集中在水运码头和航运河道附近,因此城市拓展呈现出向码头、水道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广州和泉州,还修筑了直抵江滨的翼城,将江岸地带括入城内。
二、功能分区的明确
作为地方各级统治中心,中国古代城市职能以行政功能为主。但城市作为行政治所建立之后,又以其人口集聚、交通便利的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商品集散的枢纽,从而兼具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双重职能。与之相应,城市空间也需要具有行政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合理配置。对于交通转运和商业贸易功能突出的沿海港口城市来说,尤其如此。
相对于城市的双重职能,沿海港口城市在营建之初,城市空间的功能配置并不协调。由于城垣规模较小,城市布局主要是为了满足行政职能的需要而规画的,城内大部分区域被衙署、官舍、兵营、学宫、仓库等设施所占用。如广州子城,“其中甚隘小,仅可容府署仓库而已”[13]466。随着城市人口的日益稠密,官衙学宫等建筑逐渐被市声喧哗、居人冗杂的闹市民居所包围,出现城市功能分区交错混杂的局面。北宋前期,本来地处子城西部的广州州学,就由于“迫近市廛,喧哗冗杂,殆非弦诵之所”,缺乏读书治学的氛围,只好于绍圣年间(1094-1098年),“择地而徙”,搬迁到子城东南隅[14]2453。城市空间的扩大,使得行政功能和商业功能得以具备各自的运作空间,改变了原先交错混杂的局面,促进了城市功能配置的协调和完善。广州中、东、西三城并立:子城(中城)、东城作为行政功能区;西城和雁翅城是商业贸易区和商人聚居区。泉州、明州则是子城、罗城相套,形成以子城为行政区,罗城和翼城为商业区的功能格局。沿海港口城市形成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既宜于政府运作和行政管理,也有利于城市商贸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城市空间运作的效率。
由于各自承担职能的不同,子城、外城空间布局大相径庭,呈现出不同风貌。子城作为行政功能区,一般都位居整个城市的中心位置,其布局也遵循以官署为核心的中轴对称模式。“天下郡国,自谯门而入,必有通逵,达于侯牧治所。”[15]228子城布局往往以仪门(官署正门)前大街为轴线,直通谯门(子城正门),贯穿全城,把官署建筑和整个城市布局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形成以地方最高官署为核心的城市空间。这与中国古代以中央集权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以中为尊的社会观念相符合,旨在彰显官府权威,强化礼制秩序。
庆元府衙署仪门作为子城轴线的端点,正门居中,两侧各有翼门,“列戟其中”,以示官府的威严肃穆。仪门前大街向南延伸,相继布置有庆元府门、奉国军门等[6]5106。门上都建有高大的谯楼,南北呼应,气势恢宏,由其所构成的城市轴线统御全城,凸显出地方最高官署在城市空间中的核心地位。广州子城布局也如出一辙,以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司衙署仪门为起点,“上起层楼,以壮丽谯。中为复门,以列棨戟。……由是出焉,洞重扃,逾谯门,以抵城门,以临涨海,其袤三里,其径如矢。”[16]280轴线南北纵贯全城,彰显出官署对整个城市的统领作用。
与子城相比,作为商业功能区的外城的布局就自由得多。外城是在码头、航道附近自发形成的商业街市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其街道也基本沿袭既有格局。由于这些商业街道多是出于货物装卸、就近交易和商户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自然发育而形成的,基本上沿航运水道两岸就势取便,随机布列。明州罗城西南隅有日月湖,“湖之支派,缭绕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6]5117,呈现出以水道为骨架的街道格局。在广州城西的南濠两岸,因航运物流而聚集的店铺鳞次栉比,唐代就已形成繁华的街市。西城建成之后,南濠自然构成了西城的商业轴线,商业街基本沿南濠及其支脉伸展,分布在濠涌沿岸。运载货物的船舶沿水道进入城内,在码头装卸、就近交易,水道两岸就是繁华的商业街市。街道上商品交易的繁荣,引起人流的聚集,也带来了诸如酒楼、茶坊、旅邸等服务设施;娱乐服务性设施的发展,反过来又吸引了人流的集中,更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隆。商业街区就是在这种街道与水道相依相生、相辅相成的作用下,随机发育,持续发展。
由唐至宋,沿海港口城市基本形成了以子城为行政功能区,以外城为经济功能区的功能分区模式。行政与商贸功能空间配置的明确,使城市工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得以拓展,满足了大量流入城市的工商业者经商和居住的需要,为城市商贸的发展提供了更充足的空间。原本处于附属地位的港口商业区演变为综合港口交通与商贸为一体的城市经济活动中心,更适应沿海港口城市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双重职能的需要。商业功能区街道和水道相依相生的街道布局,与子城规整秩序的传统街道布局大相径庭,看似凌乱无章却热闹兴旺,体现出城市商业社会生态自然发育的结果。
三、城——港格局的完善
对于港口城市来说,港口承担着水陆联运、贸易集散等职能,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港口在城市空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与城市建设相配套,广州、泉州、明州、登州等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航道和码头设施建设,形成了结构较为完善的城——港格局。
广州的城港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南的珠江北岸和城西的南濠两岸。一是城南雁翅城与玉带濠的建设。珠江水大浪高,船舶驻锚江岸,时有风涛之患。《南海志》载:“(广州)三城南临海(珠江),旧无内壕。海飓风至,则害舟楫。”[17]70为了解决船舶避风的问题,宋代在城南珠江北岸开凿了玉带濠。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知州邵晔以“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遂“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18]12697嘉定三年(1210年),经略使陈岘又修筑了南雁翅城,把玉带濠括入城内,使濠岸商户有了更好的安全保障。开庆元年(1259年),经略使谢子强又对玉带濠予以修治,“广斥至二十丈,深三丈余,东西坝头高甃以石”,利用水闸调节水位,大大加强了玉带濠航道的通行能力。二是西城与南濠的建设。广州城西的南濠南通珠江,是内外商船的重要停泊地。唐时南濠尚在城外,但两岸已形成街市。宋代修建西城,将南濠括入城内,并对航道加以疏浚,以便商船通航停泊。景德年间,经略使高绅疏凿南濠,“纳城中诸渠水以达于海……维舟于是者,无风涛恐。”嘉定二年,陈岘又对南濠予以修治,“自外江通舟楫,以达于市。旁翼以石栏,自越楼至闸门长一百丈,阔十丈,自闸门至海长七十五丈。”[17]70-71玉带濠与雁翅城,南濠与西城,城港建设相辅相成,使得广州的港口码头与城垣相衔接,船舶可以直通城内,既方便了停泊贸易,又可避免风涛之患。
泉州城于景云二年(711年)迁至清源山南麓后,距离晋江尚有一段距离。开元二十九年(740年),泉州别驾赵颐正开凿运河,“通舟楫于城下”,建成了由泉州城通往晋江的航道[1]1065。五代时,留从效增筑泉州罗城,罗城镇南门已经临近江岸。宋代,随着泉州海上贸易的发展,以镇南门外南关水运码头为中心,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市。绍定三年(1230年),游九功在城南江滨修筑翼城,“沿江为蔽”[19]7,把南关码头周边的街市括入城内,形成城、港紧密联接的商业街区,进一步推动了南关地带商业的繁荣。“一城重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20]7
作为外贸港口,沿海港口城市不仅具有航运和贸易职能,还承担着口岸职能。唐朝就曾在广州派驻市舶使以督办海外贸易和税收。宋代,海外贸易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朝廷在多处港口设置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18]3971,其中尤以广州、明州、泉州为重。
广州主管海外贸易的市舶机构就设置在珠江北岸港口码头附近。唐朝在珠江码头上建有海阳馆,又称“市舶使院”。市舶使在此宴请外国使节客商、管理海外贸易[21]3098。宋代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并在珠江码头上建有市舶亭和海山楼。“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海外商船到港后,“泊于市舶亭下,五洲巡检司差兵监视”[22]17,由市舶司官员在市舶亭查验、征税。明州的市舶机构也临近水运码头。负责“监收舶商搬卸”的来远亭就建在城东奉化江边的码头上[23]5864。市舶务建在城内,“左倚罗城”,紧邻城垣,与来远亭和江边码头距离甚近。为了方便市舶管理,还专门在市舶务左侧的城垣上开辟了“市舶务门”(宝庆三年更名为来安门),平时紧闭,“惟舶货入则开”[6]5103,以便于市舶官员往来于市舶务与来远亭之间。
与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商贸港建设形成对照,登州港则在宋代建为军港。庆历二年,登州城北建刀鱼寨,以为水师驻泊之用。刀鱼寨地处蓬莱湾畔丹崖山内侧,顺海岸用沙土、栅栏等在海湾西北隅围成水寨。这里背山面海,背靠丹崖山,面向蓬莱湾,形成一处水寨式港口,用以“教习水军,以备北虏”[11]2424。登州城紧临海岸,城港相依,以港为州城屏障,以城为军港后盾,既可相势进击,又可凭城据守,形成较为完备的城港攻防体系。
唐宋时期,沿海港口城市的城、港建设相辅相成,建成了城垣与港口码头相互衔接的城港体系,形成了以港口码头为枢纽,集外贸管理机构、贸易区、船舶修造机构于一体的港口功能区。码头周边的商业街市得益于转运和贸易的便利,成为城市中最繁华的商业区,呈现出航运、商贸相得益彰的繁荣形态。港口功能区作为港口航运功能与城市功能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港口城市独特的经济地域综合体,体现出港口、城市之间相互吸引、相互作用的紧密空间联系,也是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港口城市空间的投影。
四、社会空间的变化
唐宋时期沿海港口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不止于拓展了城市的实体空间,也拓展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子城、外城并存的格局,使得沿海港口城市的民间社会在相对开阔而自由的外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外城多是基于既有的自发形成的商业街市而建设的。这些商业街市形成已久,有相当规模的人口聚居,其中不乏富商大贾。对于附城而居的商人来说,能把身家产业括入城内,不仅是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更意味着真正列入城市居民范畴的心理认同。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商人集团大都积极介入城市建设,藉以提高自己在城市社会中的地位。北宋熙宁年间修筑广州西城时,居住于城西的蕃商就希望能够捐助资财,“进钱银助修广州城”[18]14121。虽然此举未获当局许可,但也显示出蕃商介入城市建设的强烈愿望。随着城外商业区括入城内,商人融入城市社会的动机与力度也相应强化。由于他们住在城内,生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得到保障,因而能够更大程度地参与各类城市社会活动。在城市建设上,这些商人资财富足,所居多为高屋华舍,使城市景观更显富赡华美。如《桯史》所载广州蒲姓蕃商,“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由于要长期在广州生活、经营,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这些商人经常参与地方官员的活动,与官员士绅宴饮交游。蒲姓蕃商就经常与广州地方要员聚会饮宴,蒲氏“以合荐酒馔烧羊,以谢大僚,曰如例。”[24]87商人与官员的结交,自然会对地方当局的城市方略有所影响。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修筑泉州城时,知州邹应龙就曾募集蕃商资金用以修城。“以贾胡簿录之赀,请于朝而大修之。”[19]2由此可以看出商人在城市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及其对城市建设介入程度的增强。
城市的拓展,使基层的民间社会在外城获得了自己的位置,与子城的官府社会共处一城而又内外有别。南宋后期,庆元府子城城壕因“民居跨壕造浮棚,直抵城址”,有碍子城的安全和威严。淳祐三年(1243年)春,知府陈垲下令拆除沿壕浮棚,修缮子城,以“限隔内外”。庆元府子城谯门两侧,左有宣诏亭,右有晓示亭,用以颁布官府文告,发布时令节气[6]5106。子城正门作为官府向市井百姓发布文告的场所,也喻示着子城城垣分隔出内、外两个城区,分辨出城市中官府和民间两类社会。
子城作为地方行政中枢,城内活动自然受到官府的严格限制。外城作为商业功能区,官府的管制相对宽松,城市社会生活因而获得了较为活跃的发展空间。外城空间无论是人口数量、人口构成、职业门类,还是社会活动的多样性,都比内城丰富多彩。由于子城是行政功能区,城内居民主要是官员、士卒及其家属,居民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相较于子城,外城居民则复杂得多,既有汉人,又有蕃商,既有富甲天下的富商巨贾,又有社会底层的贫苦市民,七行八作,形形色色,纷繁多样而极富流动性。与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子城相比,外城市民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更多的自由,体现出开放性、平民性的特征。广州西城的南濠两岸就是市民活动的中心。由于濠岸街道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为保障安全,岸边特意“翼以石栏”[17]71,以为围护。由于人流密集、生意兴隆,各种服务业、娱乐业设施也大量涌现,街市上酒楼、茶坊栉比相望,市民生活热闹兴旺。各行各业的市民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主角,体现出浓郁的商业氛围和世俗色彩。
港口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难免与传统的规制产生冲突。外城的开辟,为城市商贸活动与传统秩序的冲突提供了调和的空间。这里既是城市的一部分,又有别于传统城市的秩序和等级,充满着自由与活跃,体现着城市商业街区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城市中以工商业人士活动为主的外城和港口区能够与官僚、士绅活动的子城相并列,形成一种多元的城市社会空间。子城内外,呈现出官府社会与民间社会两种不同的风貌。外城凌乱而热闹的情景与子城威严肃穆的气氛互融共生。
结语
港口促进了人口、商贸活动的集聚和城市的发展;不断发展的城市为港口航运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依托。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港口在城市空间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城市空间的拓展方向发生着强烈的引导作用。由唐至宋,沿海港口城市的城市空间呈现出向港口码头延伸的拓展趋向,逐渐将原先依托港口自发形成的城外商业街区括入城内,形成综合航运交通与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城市经济功能区。整个城市空间也因而呈现出功能明确的复合式格局:子城保持着以官署为核心的规整布局,体现着官府社会的礼制和秩序;外城则是街道沿水道自然发育而成的随机布局,社会生活也体现出开放性、平民性的特征。
在唐宋时期沿海港口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进程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了城市实体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变革。中国古代,政治因素是决定城市兴衰的直接因素。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等海港城市蓬勃发展之际,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却由于宋辽战事而被迫封港,城市朝着战备需要发展,反映出政治、军事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强烈影响。但是,在政治因素对城市发展直接而鲜明的影响背后,经济因素仍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虽然登州由于宋辽战事而趋于萧条,但海上贸易发展的势头却难以遏制。山东半岛南岸的密州高密县板桥镇(今山东省胶州市)代替登州,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港口。海陆商贾,“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12]9956。元祐三年(1088年),朝廷在板桥镇设置市舶司,并改板桥镇为胶西县。在宋金南北对峙时期,胶西县仍是北方的重要港口。因山东粮食价高,多有南方船户“兴贩前去密州板桥、草桥等处货卖”[25]9242。因此可见,政治因素对城市形态的影响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则是潜在的、根本性的。
唐宋时期沿海港口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表明了在礼制宗法观念和政治统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城市传统中,经济功能的发展引起的城市空间形态的变革。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在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制衡作用下的革新,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由强调礼制秩序向注重城市经济发展的演变,启示了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需求的演进方向。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