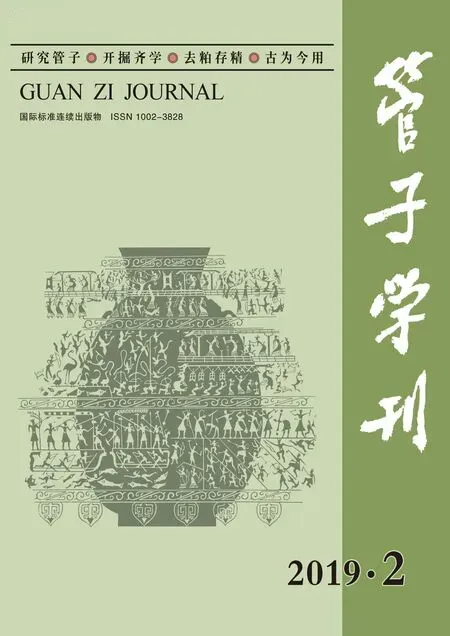从“卮言”论《庄子》“齐物”概念所蕴含的子学精神
[韩]朴荣雨
(成均馆大学 儒教文化研究所,韩国 首尔 03063)
前言
本文以庄子“卮言”概念作为解读《庄子》哲理的基本方法,基于此方法而探索活在新科学革命时代的新子学精神及其意义。新子学运动起自方勇教授2012年4月所发表的《新子学构想》一文注方勇:《新子学构想》,《新子学论集Ⅰ》,叶蓓卿编,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22页。方勇教授自此连续声明如《再论新子学》《新子学申论》《三论新子学》《新子学提出的前后脉络》《新子学与中华文化运动》等多篇论旨。此处所列之方勇教授诸篇论说中,后三篇登载于同编集人所篇之《新子学论集Ⅱ》,2017年,第1-26页。又,前三篇论文则亦登载于金白铉教授所编《神明文化研究》第三辑,神明文化研究编,2014年,第5-43页。方勇教授最近又发表一篇论文,题为《新子学:目标、问题、方法》,收于《神明文化研究:第六次新子学国际学术大会特辑》第四辑,金白铉发行,社团法人神明文化研究院,2018年,第6-14页。其重心旨趣集中于普及一股与新时代可交融的“子学精神”。新子学所向往之焦点则在于“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也是借重我们自身的智慧与认知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1]11这般抱负。
章学诚对子学出现于历史舞台的缘故,描绘得淋漓尽致: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
章学诚文中指出,“诸子争鸣”乃由周朝王官学直到战国时,露出“文弊”“道息”的衰落局面,而冯友兰则赋予孔子以子学之开山之地位,以孔子为初开私人之“专讲学”之故也[2]22。章冯二氏之此般评断,更可溯源于孟子: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已普遍暴露“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混乱世情。世情已到所谓“世衰道微”之时,总是有人站出而呼吁“天子之事”,由己而举,坦承“知我罪我”的历史重任,甚至举起替天行道之旗帜。
我们先暂不谈孔子究竟是否真有作《春秋》其事,然而我们须所着眼之处乃在于,当世事遭逢“世衰道微,邪说暴行”的悲惨局面笼罩整个时代,同时代人总难免思起“覆巢之下无完卵”(《世说新语·语言》)的下场。先秦诸子学之兴起,显在这种时代特色中露其面貌,孔子也不违其路,杨朱、墨翟难逃其圈,孟子本人更复如斯,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一概均是无不如此。司马谈对诸子百家之蜂起明述:盖“治”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战国子学之所以蜂起,先有了上述般之历史条件。至此之时,所谓的常道世界面临其支配力量之衰落,从而历史卷入正统性危机局面。为解决这般危机局面,有志之士万般提出其脱离危机之方。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之齐放都缘于此,而为天下之治殚精竭思,不遗余力。子学此等不回避时代艰难之精神,为时代的新走向而肩担重任,实为难能可贵。本文执着这种“提出脱危之方”的精神,分析一番新高科技革命时代应有的哲学型态。分析的材料则仅采《庄子》“语言”概念中所蕴含的哲学方法论,尤其紧扣“卮言”一词的哲学意涵。
一、卮言理路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论
《庄子·寓言》一文等于是《庄子》一书的范例,提供阅读《庄子》的方法论进路,有“寓言”“重言”“卮言”,称其谓庄子三言。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寓言”界定《庄子》一书所采取的叙述特征。司马迁对《庄子》所下的此般定义影响千古,庄子语言观自此成为以“寓言”为切入其思想脉动的门路。
理所当然,“寓言”确实具有其思维方法论上的功能和意义。然而,我们从《庄子》文本自己的脉络重新阅读,即可发现《庄子》的语言观显以“卮言”最为根本的话语策略。庄子三言乃阅读其文本的方法论,自然地,“卮言”也是一种方法论。在本节中,先举出《庄子》三言观的诠释理路和其意义,以备将为下一节所要讨论“万物齐同”思想的方法论根据。
《庄子·寓言》开宗明义阐明《庄子》一书所以叙述的特色“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是三言之纲领[注]宋林希逸著《庄子鬳斋口义》云:“此篇之首,乃庄子自言。其一书之中,有三种说话。”语见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中华书局,2009年,第431页;王夫之曾在《庄子解》之《寓言》云:“此内外杂篇之序例也。”见王夫之著《庄子解·庄子通》,台湾里仁书局,1984年,第246页;张默生在《庄子新释》中云:“《庄子》的钥匙,就藏在杂篇的《寓言》篇和《天下》篇里。”又云:“(寓言、重言、卮言)这三种言,可以说是三位一体。”见张默生著、张汉勋校补《庄子新释》,齐鲁书社,1996年,第12-13页。本文为称谓之简便,承用“三言”字眼。。“寓言”与“重言”以数字比率的形式界定。然而“十九”与“十七”是各表其百分比,那么其中须有互相重迭的叙述部分,寓言式叙述中含重言式叙述,重言式的叙述中亦含寓言式[注]钟泰云:“卮言之中而有重言焉,有寓言焉。”见钟泰著《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49页。。
(一)以“寓言”包括三言的说法
《寓言》对“三言”的整体说法有如下: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
“寓言”是“藉外论之”,“重言”是“所以已言”,而“已言”者历来有两种释法,一是过去所发生者,另一是“停止”之义。围绕《庄子》三言,赋予“寓言”以含括另两语言式的统辖权者,乃是史迁:
庄子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司马迁文中,采择“空语无事实”“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等界说予以表明“寓言”的意义。史迁此般藉说,颇近于《诗经》“兴”的功能,“引彼喻此”。若按照《寓言》作者的阐述,史迁这些界说理应与“藉外论之”的界定范围互应才是。史迁对“寓言”一语以“空语无事实”加以界定,而此般诠释是比《庄子》文本自身所界定的语境范围显有超格,嫌失妥实。“空言无事实”是一种抽象形式的符号,犹如朱熹对周易的卦辞爻辞界定为“空底物事”般[3]886。庄子文本对“寓言”只以“藉外论之”释之,而“藉外论之”是一种比喻法。如《诗经》之“兴”,借彼喻此。正言直说,易惹是非,不如取迂回转折的方式,得到心中本来预期的效果。而史迁以“空言无事实”扩大其词之外延,实则属于过度的诠释。
王叔岷《庄子校诠》云:“寓言者,假托人物以明事理之言也。《史记·庄子传》:‘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即‘寓言十九’之意。”[4]1090又云:“重言者,借重人物以明事理之言也。《淮南子·修物》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卑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谓托古是也。”[4]1090又云:“‘卮言’即浑圆之言,不可端倪之言,下文所谓‘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是也。和犹顺也……以犹其也。此为立言之态度。浑圆之言不主故常,顺其自然之分而已。”[4]1091王叔岷对“寓言”概念的诠释随文本之语脉而做,但些许有狭隘之嫌。《庄子》文本释“寓言”以“藉外论之”,不必仅限于“假托人物”中“人”之范围。所谓“藉外”之“外”,应包含“人”与“物”。因此,庄周梦蝴蝶,既是寓言,亦是卮言;北冥之鲲化为鹏,既是寓言,亦是卮言。颜回心斋,既是重言,亦是卮言。杨子居至梁而遇老聃,既是重言,亦是卮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要之,全篇《庄子》所采则的语法形式,以“卮言”为本,至于“寓言”“重言”皆由“卮言”话式演变而成的两个特性。就说得过分一些,“寓言”“重言”乃是“卮言”无数的表达形式中最突出的两种表达形式:“卮言之中而有重言焉,有寓言焉。”[5]649
(二)以“卮言”含蓄三言的意义
史迁将本是“藉外论之”的“寓言”概念释之以“空语无事实”,是显有诠释的过度,因而也有其诠释上商榷之处。后来郭象释“寓言”为“寄之他人,则十言九见信”[6]947。至宋,吕惠卿初次提出以“卮言”涵盖“三言”的说法:
寓言十九,则非寓而直言之者十一而已;重言十七,则非重而直言之者十三而已;至于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则寓与非寓,重与非重,皆卮言而已矣。[7]518
在《庄子》三言中,唯独“卮言”从其语用学(pragmatics)的脉络上界说之。比起前二言式,界定“卮言”概念的语用学方式最合乎对概念做界定的一般叙述模式。它提供了前两言模式之界说所未提供的信息。
依笔者浅见,“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一语是当我们阅读庄子一书的方法论上极其重要的线索。它不犹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般以数字比率做界定,造成读者从此信息中难以取得其线索。当然,“藉外论之”的“寓言”和“所以已言”的“重言”在解读《庄子》文本时,一定含有其固有的价值,理当不可忽略。只是将这两种语言表达式理解为发挥“卮言”表达式的特出典型即可。
“卮言”在《庄子》文本中的确比两种语言表达式更得重视,在《齐物论》和《天下》两篇中反复重申,更使人关注其在《庄子》文本中所占据的阅读功效。
其实,史迁对“寓言”一语所下的界说“空言无事实”,理应移至“卮言”的语用特征,更为妥当。至于,史迁之所以如此释明,显由其“寓”字的语义功能推演出来。将“语言”视如“空屋”“空壳子”,犹如在这般空屋中人住来住去,各色各样的人寓于这同一栋“屋”里往来不断,以致无穷。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世界里所使用的语言,就如“屋”而人寓于此屋中般。语言符号的记表(signal, significant,或言“能指”),正如“屋”般,可以包容无穷多的记意(signification, signifie,或言“所指”)。许多“记意”寓于一个“记表”中,以完成一个完整符号的语言功能。许多时候,《庄子》连“记表”都没有固定下来,使一个做为“记意”的“道”寓于无穷多的“记表”中。这就是“道无所不在”的语言形式。这个“道”与“言”自己本身是完整而且没有隐蔽的,但人在具体生活中就无法避免由具体生活世界所带来的“障碍”与“偏避”所遮蔽的情景。因此,在生活中的每个人都为各自的生活环境与利害关系所限隔,进而遮蔽“道”与“言”原貌的全样,进而各自发出的生活语言各不相同,引起争辩。由此导致你非我是,你辩我驳的情况中冲突。这都由“道隐”与“言隐”所致。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那么为超脱“道隐而有鷇音之真伪”和“言隐而有儒墨之是非”,人类主体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脱离“真伪是非”乱舞的红尘纠缠?《庄子》所提出的办法便是“逍遥游”与“齐物论”所提示的路途。
《庄子》整部书中的种种哲理,都是为摆脱这个“道之隐蔽”与“言之隐蔽”状态而设置。反过来言之,脱离“道”与“言”的“隐蔽”状态,是《庄子》整部书所向往的目标。要达成此项目标,《庄子》三言表达式乃是关键方法论,本文取“卮言”乃其中最为基本的思维原理,它涵盖“寓言”“重言”两种模式的基础性表达式。
(三)“卮言”的语用学模式
本文从语用学(pragmatics)的角度照射《庄子》语言策略,尤其集焦于“卮言”的话语功能在揭露文本中所蕴含的哲理表达方式。方勇曾说,张默生之前无人如此强调《庄子》“三言”的价值,他证说:
张默生虽亦倡导以庄解庄,但其解庄的视角较为特殊。他认为寓言、重言、卮言(“三言”)是《庄子》的钥匙,其中寓言式言在彼而意在此,重言是借重古先圣哲或当时名人的话以压抑时论,卮言是漏斗式的话、无成见之言,它们三位一体,交互错综,类似《诗经》的赋、比、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默生是第一个较为详细论述“三言”且从“三言”角度解庄的现代学者。[8]672-673
其实,张默生在强调“三言”的互相关系是“三位一体”之外,其中还赋予“卮言”以最核心地位。张说:“卮言者,无成见之言也。虽卮言日出,要在和以天倪而已。《庄子》全书皆卮言,故不顾以数计之,寓言、重言,莫不在其范围之内也。”[9]622张默生这番察觉,实属精辟的识破。张氏将《庄子》三言表达式和《诗经》赋、比、兴作比对是研究《庄子》语言策略的新的贡献。本文也接着张氏此般的贡献而进一步分析《庄子》语言策略所指涉的方法论意义。
《庄子》中所言的语言行为基本上以“卮言”模式述说。如上所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指出语言有社会面相的功能与个人面相的功能。前者称之为“语言”(language, langue)而后者则称其为“言语”或者“话语”(speech, parole)。“语言”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一般规则语原理,而“言语”或“话语”则由每一个体在日常生活里实际使用的成分[10]67。个人的“言语”须在“语言”的一般规律中进行发话。然而“言语”“话语”经常脱节“语言”的一般规矩,这是一种谬误,但它的出现也是一种创造的一刻。
索绪尔除上述的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区分外,还有阐明语言使用上极其重要的语言结构。一个语言符号由“记表”(signal, signifiant,能指)与“记意”(signification, signifie,所指)两个符号因素所组成[10]65-70。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每一个话语都有“音符”与“意象”(或概念)的符号功能。在词汇集或在辞典中所规定的每个语词都原由长久以来发话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而定。而在“记表”与“记意”之间的关系式取决于偶然契机,因此在“记表”与“记意”之间没有必然性的关系,故而“记表”与“记意”常发生失联状况。因为此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因此一个“记表”可以与另一个“记意”结合而产生新的“语词”,反之亦然。如此一来,人类每遭遇新的经验、陌生的世态时,“记表”与“记意”之间就会发生符号意义的调节工作,由此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世界得以扩张,人类文明据以进展。这就是“隐喻”式思惟的由来。
人要是使用新的语词,发挥新的创意,必须经过“隐喻”思维才能得偿所愿,否则人类的语言生活和文明生活,只好原地打转。《庄子》一书创意性十足的文本,它借用“寓言”“重言”“卮言”这三种发话形式而舒展“为道”的心怀。照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语言意义的变化或者扩张,须由两种符号因素之变动而来:一是“记表”的转移,一是“记意”的更动。在《庄子》中都有属于此两种的语言使用之例子。《寓言》篇有一段按照“卮言”模式勾勒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性”不断变化的过程:
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为,死也。劝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阳也,无自也。而果然乎?恶乎其所适?恶乎其所不适?天有历数,地有人据,吾恶乎求之?莫知其所终,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这段话是说人格主体性之转变,子綦的人格同一性从一年到第九年,一年接着一年更动变化。“子綦”做为一个“记表”经过九等不同经验而扩张,达至“大妙”的“子綦”一定不同于刚进于“野”阶段的“子綦”。做为“记表”的“子綦”犹如一盏“卮”,不断更新其“记意”。经历了九年的经验之后,“子綦”的自我同一性比起第一年“野”的阶段“子綦”多了八种自我认同类型。《庄子》这种哲理是经过“卮言”表达式而呈现的。
《庄子》在《寓言》篇开宗明义提出“寓言”“重言”“卮言”这三言表达式以把持使人能“化”“忘”“游”的方式达至于“逍遥游”的境界与“万物齐同”的相忘境界。本文认为,庄子文本中蕴含的基本逻辑是“卮言”表达式。“寓言”形式的“藉外论之”和“重言”表达式的“所以已言”都是“卮言”表达式的两种典型。“卮言”是“日出而和以天倪”的表达式。“藉外论之”亦是“和以天倪”的独特形式,“所以已言”亦是“和以天倪”的一种形式。
其实,在《庄子》对于三言所做的说明中对“卮言”的分量最多。《齐物论》中已有《寓言》篇所述的“卮言”界说,《天下》篇亦有“三言”而对“卮言”的说明居多。我们从酒器“卮”的功能中就得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的日常语言的特征。“卮”有“满则倾,空则仰”的特色,既不固定且随变而应,应变无穷。我们人类的日常语言在生活世界里活用的情景正如“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日常生活语言的使用,也叫做“语用”,它并不是完全遵照词汇集中所指称的辞典内容而活用。一个词汇的使用,其实天天放置于不同时空条件与生活语境中展现。相同的“记表”指称不同的“记意”,同样的“记表”改天又指称另一个“记意”,以此类推,层出不穷,反之亦然。例如,一对夫妻,有时叫呼对方名字,有时叫小两口仅知的“爱称”或“昵称”,又有时叫“冤家”,如此等等,一个语言符号的使用意义,在许多情况里,都不取决于辞典语法,而语词真正的意义都取决于“具体语境”。语言使用的这种特色就是“卮言日出,和以天倪”的“卮言”表达式的特征。有的时候以“寓言”的方式,而有的时候则以“重言”的方式增加“和以天倪”的效果。
二、卮言与万物齐同的模式
“卮言”以现代的话语而言,类乎一种广义的“隐喻”表达。在现代隐喻语言学领域中广义的“隐喻”可包括诸如“明喻”(simile)、“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寓言”(allegory)、“模拟”(analogy)以及“隐喻”(metaphor)本身等。所述此般各种“比喻”类型,不仅仅属于文学修饰的修辞概念,而更是人类的“思维形式”[注]Metaphor is pervasive in every life, not just in language but in thought and action. Our ordinary conceptual system, in terms of which we both think and act, is fundamentally metaphorical in nature.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Afterward in 2003, p.3.。“隐喻”的逻辑推论式是“A=B”,都不同于演绎逻辑推论追求“知识”的表达式。它只要汲取到了某种“意义”(meaning)就心满意足,所得来的“意义”不为“真理”规则所拘泥,也不为它犯了“谬误”而感到恐惧。“隐喻”最重视的不是“真理”而是“意义”。“隐喻”句式“A=B”,前件不含后件的内涵,可以转变无穷,扩展无尽,由B而C,由C而D,由D而永无止境。因而产生出无穷的别创新格。最值得注意者,个体之转变为另一个体的过程中,无须拘束于遵循“因果关系”与“科学逻辑”的负担和压力。《庄子·寓言》对“卮言”有如下的定义: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卮言”有四项语言功能:“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卮言日出”是表示《庄子》文本的意涵应该以“日常生活”中加以入手,即从“众窍”发出的音声去掌握其“咸其自取”的完整性。“因以曼衍”要有“吾丧我”的心境才能无边际的流动。“和以天倪”在我们日常生活上的语言行为,大部分是无心之言,我们一般人若能脱离自己的“成心”所教唆的心智特征,而又能不知不觉说出“无我”之说,便毫无争辩可言。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能这样做而过安身立命的生活。其实“无心之言”的能力每一个本来具备的,问题是一般人经常返回到其“众窍”的自我时空世界,进而追求其中的利害关系,结果经常陷于“朝三”世界而折磨自己的生命。若一个人天天能遗忘自己,脱离“成心”,说出无利害、无是非的话语,他就颇为可能达到万物和自己的“穷年”境界。《齐物论》业已申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三项特征: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化声之相待”,郭象《庄子注》云:“是非之辩为化声。夫化声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6]109是负面的意思,而王夫之则取正面的脉络释之。王夫之《庄子解》云:“天籁曰化声,气所化也。”又云:“詹詹如泠风,炎炎如飘风,皆化声耳。化声者,本无而随化以有者也。”[11]28王先谦《庄子集解》则云:“随物而变,谓之化声。……是与不是,然与不然,在人者也。待人之为是为然而是之然之。与其无待于人而自是自然,一皆无与于其心。如下文所云也。”[12]24焦竑《庄子翼》云:“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异同亦皆无辩。然之与是,复自相对,又均于变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声者,有声声者。化者之化非声,则不显;声者之声非化,则不彰。此化声之相待也。然而声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统乎声,非声之所能识。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声于两物,若合万化为一,则相待之迹,无由而生。夫声者常声,不待而后声,闻者自因声而生听耳。化者常化,不待声而后化,见者自因声而生识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13]33-34要做“若其不相待”就遵循“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即是说,要遵循“卮言”的话语方式去交流,如此做才能“穷年”。这还不足,更推进于“寓诸无竟”。要“寓诸无竟”须从“忘年忘义”入手。
对“卮言”义涵的重视,在《天下》篇又有申说: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成玄英《庄子疏》云:“卮言,不定也。曼衍,无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故以卮言以况至言。而耆艾之谈,体多真实,寄之他人,其理深广,则鸿蒙、云将、海若之徒是也。”[6]1100吕惠卿《庄子义》云:“卮言,道也。道之应,日用而无穷。重言与寓言,所以趋时,时不知吾言之信,故称古昔以为重,重言则有其实者也,故以重言为真。以重言不足以论,而后有寓言,故以寓言为广。”[7]604王叔岷《庄子校诠》云:“卮言,浑圆之言,曼衍,无边际。卮言浑圆无际,故‘为曼衍’,重言托古取信,故‘为真’,寓言十有其九,故‘为广’。”[14]1346由诸如此类的注释可见,“寓言”与“重言”在“卮言”曼衍无际的流动中通合为一。
《庄子·齐物论》谈到极其著名的对话。有天弟子颜成子游侍奉老师南郭子綦,发现南郭子綦之坐法不若往常,“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目睹子綦此般姿态使得颜成子游顿然吃一大惊,便不禁冒出恐惧与疑惑。于是问起“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可能与否,继而两人一连串的问答下去: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子綦回答虽是淋漓尽致,然此实乃露出体道者的苦衷无奈万般。子綦主要以“地籁”之情景去教导子游,说了半天,尚在求道者修为过程中的子游犹止于一知半解“吾丧我”的究竟要义。于是,子綦万般无奈的说破“天籁”究竟要义。子游所提出的“吾丧我”究竟要义是,“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的天籁境界,然而还是以反问式予以终结,“怒者其谁耶”?可见,“天籁”是无以言状的东西。
《庄子》藉由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师弟之间的这场对话,彰显自己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式是“和以天倪”“因以曼衍”的“卮言”式的表述形式。天下万物与人类都是“众窍”之一份子,因风之吹来而发出自己固有的音声。庄子以“风”喻“道”,以“众窍”喻各种各样的“物论”。“风”无处不入,无所不至,遍在宇宙万事万物之中,而道亦如是,使万事万物据以生长消灭。“众窍”则居其所,守其分,力主自养,而儒墨之是非亦属众窍之一呈显。要注意者是,庄子将“众窍”描绘如千态万象千变万化。这正合乎“因以曼衍”的森罗万象绵延不绝,层出不穷的流动相。“众窍”每当遇到“风”之一吹,便应之以“卮言日出”,就像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形式即触即发般,许多“发话行为”(locutionary act)[注]欧斯汀将人的语言使用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功能:一、实行式语言(performatives),二、表达式语言(constatives)。Austin, John Langshaw (1911-1960),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11.欧斯汀又指出,人的发话行为由三种不同功能所推行。一、发话行为(locutionary act),二、发话内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三、发话效果行为(perlocutionay act)。“发话行为”指说话者在日常生活中合乎语言习惯而发出的具有意义的语言行为;“发话内行事行为”是指发话者在特定语境中赋予有意义而发生效果的发话行为;“发话效果行为”是指说话者的“发话行为”或者“发话内行事行为”在听话者身上所产生效果的发话行为。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pp.94-108. 欧斯汀所述的语言规则专以“语用学”的角度去分析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效果。所发出的语言几乎都不经深虑而发出。这种日常语言的使用情景,正与《庄子》“卮言日出”的界说吻合。“卮言”乃是成玄英所言“无心之言”:
卮,酒器也;日出,犹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于自然之分也。[6]947
“卮言日出”但要朝向“和以天倪”的交流效果。“众窍”能够得以“和以天倪”须由“吾丧我”入手。当人之心智活动以“吾丧我”迎接“吹万不同”时,便能达至“咸其自取”进而得以“和以天倪”的和平效果。
“卮言”的价值不在尊崇“语意学”(semantics)也不在遵循“词汇集”(lexicon),有时更改“句法”(syntax)等语法规则,“卮言”经常颠覆语法程序所遵循的字面意义。就广义的用法而言,“卮言”最靠近于“隐喻”表达式。其逻辑形式就是“A=B”。这种逻辑推论方式与西方逻辑学基本推论法则完全不同。演绎逻辑中所得出的结论不可出于大前提所涉及的范围之外。亦即古典逻辑推论三式,诸如同一律“A=A”,矛盾律“~(A∧~A)”,排中律“A∨~A”,都不外乎“A”所涉及的外延。而“隐喻”表达式的这种逻辑形式,很可能带给演绎逻辑主义者以谋种荒唐无稽之感,这都由“卮言”经常发出“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所致。他们肯定辩驳道“失去了逻辑严密的意义”。然而,可以设问,随着隐喻式的表达方式真的毫无意义可言吗?演绎逻辑是追求科学知识的推论法式,而隐喻逻辑的推论方式是要追求生活与生命的“意义”。隐喻推论模式对追求科学知识毫无意义,是没有错,但科学推论模式对生活意义而言很多情况里也不大受用。“卮言”就是专门针对“生活意义”和“生命活动”提供“意义”的表达式。
牟宗三在《庄子〈齐物论〉演讲录》中,精辟地分析《庄子》何以要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
虽然名、言在一起,但是,名与言不同,名是term,言是一个sentence。一个sentence才有是、非。庄子说:“言恶乎隐而有是非。”言被遮蔽了,因而有是有非。那么,有没有不被隐避因而无是无非的言呢?我们实际生活中都是有是有非的言……不被隐蔽因而无是无非的这种“言”在哪里呢?那种语言是甚么语言呢?[15]
所谓的“儒墨之是非”是由于“隐”而来。在心中原原本本完整公允的语言意义,当脱口而出时,就要经过“众窍”所处的时空与存有环境。那原原本本完整公允的语言意义,便被其“时空环境”的条件所遮蔽。当对方听话者听到脱我之口而发的话语时,由于我的原本话语被我的存有环境所遮蔽,便会导致他仅仅听到其中的一部分的意涵。这种语言交流,很可能促使听话者一知半解,甚至于误解,进而引起“隐而有是非”。“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齐物论》)“道之隐蔽于小成”“言之隐蔽于荣华”都是由于生活主体拘束于其存有条件之限制而隐蔽,促使诸子百家各自的小成与各自华丽的言辩与口号,日以嚣张,月焉猖狂,终至“道”“言”皆隐蔽而不显。又说:
“恶乎存而不可”言怎么说都可以,都对。究竟有没有这种言呢?……怎么说都对的这种话一定是无是无非的,最好的话。那么,被隐蔽了而有是有非的话就不能是“恶乎存而不可”,就不能怎么说都对。现实世界都是有是有非的语言,有所隐蔽的语言。……譬如说,有儒墨的是非那就是负面。[15]
“言恶乎存而不可”,就是因为其有“隐蔽”完完整整的原本意义。去掉这个“遮蔽”,我们就能见到那“原原本本”的词话了。如何去除此种“遮蔽”?牟宗三接着说,庄子是由“明”概念入手: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这是一整句。接下去进一步说:“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固定。则莫若以明。”想要达到“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最好的办法是“莫若以明”。“明”这个地方就代表那个不隐蔽的道、不隐蔽的一言?下面接着就把这个“明”烘托出来。这就是“齐物论”,就是把是非化掉。从“明”这个层次返过来就可以了解那个不隐蔽的道、不隐蔽的言。这就是庄子的思路。[15]
“言之遮蔽于荣华”,我是你非,你又辩驳回来,“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但“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牟宗三接着阐明如何去“莫若以明”之法:
依照庄子的想法,你要真正达到“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你所肯定对方所否定的这个肯定要能肯定得住,你所否定对方所肯定的这个否定要能否定得住,你所采取的相对的立场就不能有。所以,最好是“莫若以明”。那么,这个“明”一定比相对的立场高一层。“明”下面就是是非等对。“明”一定在是非、善恶、美丑以外、以上。就是beyond truth and false, beyond goodness and evil, beyond beauty and ugliness。姑且言之,这就是“明”。究竟“明”是甚么意思,你先不要管。[15]
我们所要使用的语言形式是去除“隐蔽”的语言。去除“隐蔽”的办法是由“明”入手,要人去“莫若以明”。“明”是超越一切的二元对立式的分解局面,进而达到“超越”各种相对性“物论”。那么,这种“不被隐避因而无是无非的言”的语言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语言呢?牟宗三几乎讲到了这是什么语言,他的结论则如下:
庄子的讲法高一层,他是说,你想你肯定的能肯定得住,否定的能否定得住,你得采取这样的态度。要说的对,就通通是对。光说我对,你不对,这肯定不住的。要能否定得住呢?那就是要说不对,通通不对。不单单你不对,我也不对。这是很聪明的办法。这就是智慧,这个就是“明”的层次。在“明”的层次,要是通通是,要非通通非。通通是,那就是没有非与它相对;通通非,那就是没有是与它相对。结果是无是无非。无是无非就是把是非相化掉了。无是无非的这个“言”就是“恶乎存而不可”的言。“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那就是言隐蔽于相对的系统,那才有是、有非。那么,要是通通是,要非通通非的那个“言”就是无是无非之言。无是无非之言就是没有隐蔽之言。那么,你想一想,这种言是一种甚么状况的言,究竟有没有这种言呢?这不是成了和稀泥了吗?也不一定是和稀泥嘛。一步一步地辩,那还是在是非之中嘛。最后要把一步一步辩之中的那种是非也化掉。这就是庄子所想的。佛教的禅宗也有这个境界。[15]
牟宗三由“莫若以明”的层次推论“无是无非”的“言恶乎存而不可”的语言,但全篇讲录中都未赋予它适当的命名。依照《庄子》文本内里所隐含着的表达式而言,这种语言非“卮言”莫属,“恶乎存而不可”的言就是“卮言”。能够说得“通通对”,说得“通通不对”这种话,正合乎“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的“卮言”界说。这就是“不被隐避因而无是无非的言”的“卮言”特色。
三、卮言模式在新子学运动中的方法论脚色
自2012年起至如今,新子学思想运动起步已有多年。其间“子学精神”的大方向朝着“子学复兴,诸子会通”与“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1]10-11而掌舵。进而,“发扬多元并立”的“子学精神”[16]22,诸如此般的声明都可以共认的旨趣,毋庸置疑。大方向与大目的有所共认了,那么须是要斟酌其具体实践路数的时候了。这是实践的方法论议题。此般努力多多益善。《庄子》在《齐物论》点出“万物齐同”的办法。我们也可从借用《庄子》所使用的方法做起,以使吸取于中的智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我们要脱离“道之隐蔽于小成”“言之隐蔽于荣华”的红尘小我,须依靠“因是已”才能“两行”。这里的“因是”当然是“以明”层次的“顺任道而行”。《庄子》所言之“两行”,以“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之一行与“道通为一”而“不知其然”的一行,合为两行。前者乃生活世界层次的“日常行”,是“众窍”层次的“地籁”生活,也是“喜怒为用”的“朝三”的现实生活世界;而后者是超越层次的“道行”,透过无为自然的“因是已”而却“不知其然”的超凡层次的“天钧”境界。“日常行”层次的“地籁”生活,须与“天钧”生活和而为一、通而为一,才是“两行”。只有“道行”不能“与世俗处”,而只有“日常行”残留于红尘小我世界打转。每个人能“两行”,“万物齐同”因之实现。“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修乎天钧”,是“万物齐同”的关键。
“‘两行’之可能”首先因为“道”有“无所不在”的遍及性(ubiquity)。道之遍在性,《庄子》中,总是离不开“卮言”式的发话行为。我们寻常目睹“卮言”式的语言活动。在《知北游》“东郭子问道”的片段里,就可读到“两行”从扣着“道”的面向去归纳物理世界的情景: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庄子·知北游》)
一个“道”从语言符号的活动流程上而言,庄子就透过诸如“蝼蚁”“稊稗”“瓦甓”“尿溺”来赋予“道”以无数多的“变奏”。犹如“道”做为一盏“卮”器般,经过无穷的“倾仰”,透射出诸如上类的方方面面,事事件件。
在《至乐》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一个“记意”涉及无穷多的“记表”。所描绘者,“自我转化”无穷连锁的风景: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馀骨。乾馀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车兄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从“水之继”一连串的化为“蛙蠙”“陵舄”“乌足”“蛴螬”“胡蝶”等;“胡蝶胥”化为“鸲掇”、“乾馀骨”、“斯弥”、“食醯”、“颐辂”与“食醯”、“黄车兄”与“九猷”、“瞀芮”与“腐蠸”之间有生成关系;“羊奚”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如此种种的转化情景,实在是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尤其,最后庄子以“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来总结。对此自然物的转化连锁,史华兹说:“这里所赞美的是大自然之轻快的不可穷竭性以及善于变形与转化的特点。”[17]228《庄子》文本使读者得到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的无尽头的转化过程。这岂不是由“卮言”的“倾仰”使然?
鲲之化为鹏,庄周之梦见“蝴蝶”,颜渊的“心斋”与“坐忘”等与道冥合的领悟状态,正由“卮言”无止境的倾仰所致。总之,《庄子》经过“相忘”与“物化”及“两行”过程,使人得以“自我转化”“咸其自取”。其最终目的希望,在于“无穷转化”过程得到“天人合一”的逍遥和齐物的精神境界。
要之,新子学运动从《庄子》可吸取的智慧,总不外乎三种“境界”:一是“游”,二是“忘”,三是“化”。“游”“忘”“化”三种境界都以“卮言”为其发话的出发点,而以“万物齐同”为最终归宿。因此,“万物齐同”与“逍遥游”之境界,以“卮言”做为思维的入手处,以“寓言”为扩张“卮言”的范围,以“重言”为强化“卮言”的力量。如此看来,“卮言”不仅仅是一种话语的表达式,而更是人类心智能力本有的“思维形式”。“卮言”可以使人物我相忘,可以超脱“众窍”现有层次的时空界限而优游于两行,更可以“化而为蝴蝶”“化而为鹏”“化而进入坐忘”“化而得到心斋”以至“化而为至人真人”。职是之故,使人的思维创进无穷的“卮言”,正与提倡“多元平等”“贵多元共生”“多元并立”的“子学精神”[18]20-24相符,正是适合新子学运动的思维、话语、实践的方法论。
结语
本文从《庄子》三言表达式中,扣紧“卮言”作为解读《庄子》文本的关键钥匙,探寻“万物齐同”概念据以实现的方法论。“卮言”层出不穷的倾仰流动,使人得以实现“吾丧我”,得以达到“坐忘”,得以“心斋”,得以“物化”。“卮言”涵容“寓言”与“重言”于其自身中。《庄子》语言表达式以“卮言”为最基础,最典型,“寓言”与“重言”乃是“卮言”许多表达功能中最具独特性的两种类型。
“卮言”这种表达式,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式,更是人最深层的思维能力。正如现代认知语言学家所说的广义的“隐喻”特征。本文认为,“卮言”表达式显得做为一个解读《庄子》的“方法论”毫无逊色。《庄子》所向往的“逍遥游”的境界与“万物齐同”的理想,透过“卮言”的方法论得以实现。笔者认为,“卮言”表达式除解读《庄子》外,还可以解读其他“诸子书”与儒家“经书”以图找回“经书”与“子书”原原本本的初始样貌。所谓的“原儒”“原百家学”只能经过让文本本身自己说话,让文本自己朗显出自己本来的“原初意义”(original meanging)。
一个学术运动或者一个学术流派,理当要有其大方向、思想目标、思想内容。大方向的定向,最终目标的设定,思想内容的奠定,都要有其方法论,否则其完整的目标难以实现。笔者认为,目前的新子学运动理应多讨论并且努力寻找,几项可以使我们实现上述核心内容的方法论。学术运动之所以成功,盖取决于对“方向”“目标”“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进行。
自新子学运动之起步后,所历多年。其间为重建新子学的学术规模,无数多的学者参与与着墨,提出珍贵的高见。于中有的提出新子学的大方向,有的为新子学的内容与精神付出心血,有的则为新子学所要达至的最终归宿而着想。更有的专家者提出新子学可以采用的实践方法论。这些意见都是新子学运动可以参考或者直接拿起使用的共同资产。本文的初衷是为解读《庄子》而寻找一个适切可用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既是可以解读《庄子》文本,进而可以适用于解读其他经书和子书的文本。若更可以适用到新子学运动的实践方法,则固诉愿也,不敢请耳。
※本文于2018年11月1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所召开的第七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发表并会后经由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