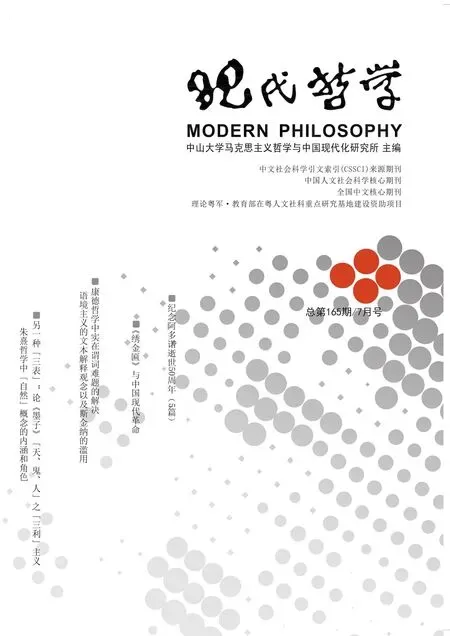试论荀子“和合”思想
李记芬
近年来,因张立文先生创立和合学,对和合思想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但就儒家层面来说,《论语》《孟子》都没有提到这一概念,《荀子》是最早使用它的儒家典籍,可见“和合”在荀子思想中的重要性。
一、欢欣与和合
“和合”一词出现于《荀子·礼论》。《礼论》篇讨论了礼的起源、功用等,其中着重突出礼与人情的关系,指出礼义文理的制定就是为了养情。人生而有很多情感,比如喜生、哀死、好利、恶等。在荀子看来,如何使这些人情得以恰当长养而不丧失,是礼最重要的功用所在,即“礼者养也”。在所有的情感中,荀子最为看重的是人在生死变动中产生的情感,所以《礼论》反复强调“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基于对喜生、哀死情感的看重,荀子对丧礼的制定和功用等进行了细致论述。正是在对乐生、哀死之情和丧礼的考量中,荀子引入了对“和合”概念的探讨。“和合”指向的是人的一种内心情感。荀子道: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诡、唈僾而不能无时至焉。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荀子·礼论》)
此段是讲人在祭祀时产生的思慕之情,此情之深会让人时时悲伤、感动。忠臣和孝子在“欢欣之时”常常有此种悲伤,尤其是想到君主或亲人已不能再有此种欢乐时。“和合”与“欢欣”在此处并列出现。因为“和合”,所以人会产生欢欣之情。依王天海的注释,“此言人之欢欣团聚之时,忠臣孝子感触而生哀伤之情”[注]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06页。。也就是说,欢欣之情指的是人在团聚中而自然产生的欢乐。人在父母生时,对父母有仁爱亲近之情,因为没有别离而能生活相聚在一起,所以人是欢乐的。
这种欢乐之情与人在思慕时产生的不能与君主或亲人再次团聚而有的哀戚之情相呼应。根据《荀子》原文之意,“欢欣和合”正好与“志意思慕之情”相对,前者指人在相聚时的欢乐、欣喜,后者意为人在生死别离时产生的哀痛、思慕。思慕的产生,是人的欢欣之情的深入体现。生人会有对死者的想念,尤其是在日常生活有相聚时会更思念与死者的相聚;在丧期之后,人会继续自己的生活,但仍然怀有对死者的敬慕、悼念。在这种敬慕、悼念中,生者期待还能与死者有某种形式的“相聚”。这种相聚会令人产生一种更深层次的欣喜之情。从思慕的角度理解,“和合”注重人的生与死的合一。荀子反复强调,生死两全才是人道最圆满的表现,正如《荀子·礼论》所说: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
故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
人不仅应当重视在父母生时如何爱亲、事亲,还应当重视在他们死后该如何敬、如何事的问题。比如,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能和父母、兄弟、君主等聚在一起生活,得现实相聚之欢,还能在死亡别离后与逝去的人尤其是家族祖先有联系。通过安葬、祭祀和书写铭、诔、族谱等形式,现实中的人对逝去亲人的爱敬之情得以进一步表达。在爱敬的表达中,人得以和先祖相连、合聚,进而得生死两全之欢。如此,人才可以真正被称为是孝子。
人在表达对祖先的思慕、敬爱之情时,也会丰富和加深对自我的认知。人因为思慕先祖的生活故事、行为方式、为人之道等,从而对于自己的家族既能有历史性的、根源性的了解,也能对自己当下的生活做出更进一步的认识和反思。在这种了解和反思中,人因为与先祖的靠近而产生一种同一感和一种更深层次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份同一感和认同感,带来的是一种更深厚的人生欢乐之情。
综上而言,“和合”指的是与父母亲人在生时的聚合,这一聚合在死后也能继续延续下去。虽然在世的人与逝去的亲人、先祖等有实质的别离,但在精神和情感上并未别离,仍然有着精神上的聚合。在这种聚合中,人与先祖能够相连,从而在根本上能加深人对自身的认识。这样便可以更好理解荀子所说的“先祖者,类之本也”(同上)。
“和合”在《礼论》篇的出现并非偶然,与荀子对礼之功用的理解密切相关。不论是欢欣还是思慕,荀子认为都需要礼去规约和引导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和合”作为人生中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情感,是礼的制定中必定十分关注的。一方面,礼要通过恰当形式去表达人生活中的欢欣之情;另一方面,在生命的大变动中,礼也注重将人的欢乐以不同的形式进一步深化。如此,人情才得以完全、深入地长养。
二、乐合同
如果说荀子在《礼论》篇提出的“和合”概念主要还是从“合”的角度来突出人在生死层面上的“聚合”“同一”,那么,该如何理解“和合”这一概念中“和”字的意义呢?对“和合”概念,荀子虽然仅在《礼论》篇提到1次,但对“和”与“合”在《乐论》等篇中的分别论述,能为理解 “和合”概念提供进一步说明。荀子将“和合”与“欢欣”放在一起讲,彰显了“和合”之义中所有的欢乐,此种欢乐是人必不可少的一种情感。情感的生发往往又会在人的声音、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来,使得和合之乐更为凸显。此种“和合”之乐与荀子对音乐的理解密切相关: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荀子·乐论》)
欢乐之情人人都有、不可缺少,且这种情感会在人的声音和行为举止上有进一步的体现。比如,人内心有欢乐之情,便会咏叹歌唱、手舞足蹈等。声乐就是对人的内心欢乐之情的一种外在抒发和表达。“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同上)对这种情感的表达,荀子认为需要人去导引。如果不加以导引,就容易导致乱的产生。“故乐者,所以导乐也。”(同上)对于如何导引,荀子指出: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同上)
先王制定《雅》《颂》之乐对人进行导引,使得咏叹歌唱之声可以恰当展现人的欢乐,使得乐章清晰明白、通顺,使得声音、文辞在曲直、繁简、刚柔、节奏变化中可以感动人的善心。反之,如果不用如《雅》《颂》的正乐来引导人情,就会使人放纵欢乐之情、乐章窒碍不通,也不能使声音、文辞的变化感人善心。
音乐可抒发人的情感,也可通过外在的声或气对人的内在情感产生熏习或渗透作用。“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同上)乐分奸声和正声:奸声如郑、卫之音,正声如《雅》《颂》之乐。如果用奸声来导引人的内心情感,那么人身就会有逆气、逆情产生,进而通过声音和行为表现出来,呈现出乱的景象;反之,则是顺气、顺情和治的景象的产生。因而,乐的选择对内在性情是非常重要的。乐之所以能导引性情的发展,是因为乐可以感动人心,通过人心对性情有所作用。荀子说: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
在此,“和”与“合”分别出现,是“和合”概念在荀子性论思想中的进一步展现。荀子指出,性是人生来如此的东西,从阴阳之气自然相互“冲和”的角度来讲,人性也可称为精气之性[注]“性之和所生”,依杨倞注,“和,阴阳冲和气也”,“言人之性,和气所生”。从“和气”的角度,物双松、冢田虎、王天海等学者将这种性理解为阴阳冲和而使人生而自然有的性。(参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885页。)。精气之性通过耳目精灵等与外物“合遇”[注]“精合感应”,依照杨倞注,“精合,谓若耳目之精灵与见闻之物合也。感应,谓外物感心而来应也”。依冢田虎注,合即是“合遇”:“言人之精气与物合遇,而所以感应乎视听,乃是所生于性之和气,而不事之而自然者,亦谓之性也。”(参见[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12页;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885页。)。在合遇中,天官与万物有自然感应,从而目能视、耳能听;而作为天君的心能征知万物而生情,“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同上)。心可以令耳知物之声、令眼知物之形等;心知万物,进而或应之以好、喜之情,或应之以恶、怒之情等。这与《礼记·乐记》“物至知知,好恶形焉”的思路是一致的。具体到乐,如果人心感知奸声则内有邪情产生,人心感知正声则有顺情产生。人心发挥知的作用而能产生不同的情,更为重要的是,人心还能对不同的情进行选择,即发挥思虑的作用去导引情的发展。为了使情最终合于善,心需要对于其所交接的乐声做出恰当选择。人心可以选择正乐,使情最终合于善。这就是所谓的正乐可以导引人走向“和齐”:
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荀子·乐论》)
正乐可以导引人心向公,在行为举止上齐同于公道的追求,而不是仅仅关注于私欲的满足。如此,就能实现天下大同:君在外征诛讨伐,可以使民听从而归服;在内治国,民都能行揖让之礼而服从君的治理。不管是外民的归服还是国民的服从,不管是“和而不流”还是“齐而不乱”,都是指正声雅乐最后可以导人走向大公、大同和齐同,实现和齐之乐、齐同之乐。齐同之乐通过“合同”的方式达成,与“别异”的方式相对而言: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
在荀子看来,礼以“别异”的方式展现事物的清晰条理,从而依理可以调节人欲的不同;但音乐则是以调和、合同的方式,“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同上)。“和”即正声雅乐调和人心,所展现的是世间万物的和乐之景。如果没有正声雅乐的导引,人的内心就会流于私欲的追逐而放纵不止,行为举止不能得其同而为小人;“小人乐得其欲”,会使民风民俗也不能得大公、大同之善,从而失去真正的乐。如果有正声雅乐的导引,可使人志气清明、血气和平、欲望得其治,从而行为举止能得其正而成为君子;“君子乐得其道”,也会影响民风、民俗,使其一同行公道从而得其善。这便是声乐的合同导引功用带来的最大的欢乐,指向的是一种更广范围的和乐之境。在这种和乐境界中,荀子十分强调“和”与“同”的关系。《荀子·乐论》: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
音乐有和同之功用,具体而言即是君臣同听(乐)以和敬、父子兄弟同听(乐)以和亲、乡里长少同听(乐)以和顺。不论是和敬、和亲还是和顺,都是在同听(乐)中可以达成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和”即“和同”。这与《尚书·泰誓》中对于“同心同德”思想的强调是一致的:君臣之间如果能同心同德、上下一心,那么国家就能得到好的治理。“审一以定和”意思是通过审查乐声的正邪,就可以知道民之和同是否可以达成。进一步地,这种和同功用的达成之方,在于乐的节奏之合,即“比物以饰节”和“合奏以成文”[注]王天海指出,“比物以饰节”意思是指“协合乐器以调整节奏”(依《乐记》郑注“以成文,五声八音克谐相应和”);“节奏合以成文”即是“言其节奏协和以成乐章”的意思。(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813页。)。不管是通过协和不同的乐器以调整节奏,还是进一步协和声音节奏以成乐章,“和”在这里都主要是指“协和”,即协和不同之物以得其同。
总之,荀子在《乐论》中进一步推进了对“和合”意涵的探讨。“和”即调和人心以得其同;“合”即合同。(声)乐以调和、合同的方式使人合于公道,最终得和乐之境界。这种通过调和、合同人心而达成的乐是公道之乐,与合聚之欢相呼应。人因为与亲人生死相聚而得人生整全之乐;而公道之乐则是这种整全之乐在社会这一更广范围内的进一步展现。
三、群居和一之道
乐的功用是合同,礼则是别异。但礼别异的思想仍是以和合为最终目标。在这一和合目标中,重要的是人合群而能和睦相处。荀子十分强调“明分使群”(《荀子·富国》),但其中所追求的还是“群居和一之道”(《荀子·荣辱》)。
“合”在荀子指的是亲人家庭之间的聚合,放到更广意义上的社会自然来说,也可指人类的聚合,与自然中的其他生物比如草木禽兽的行为相对而言。正是从人类的合聚意义上而言,“合”也可指向“群”——合群。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正是因为群才使得人在自然中能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同上)因为人能群,所以人在自然面前能够变得强大,从而能够使自然资源为我所用,维持人类的生存发展。
与“群”相对的则是“离”。如果人与人之间离居相处,那么在自然面前人就会变得很弱小:“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同上)“离”会使人不能很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的生活起居等基本自然需要,即会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扶养之道。“离”不仅会破坏自然对人类的扶养,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养也遭到破坏。如果人与人之间离居相处,那么人与人之间便不能聚合在一起共同协作。没有协作,就无法满足人的种种生活需要,也不能使人与人相互帮助以共同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灾难等。如此一来,人类自身的发展,尤其是长远意义的发展也就无法得到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明确指出“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
人需要合群,但并不是指人简单地聚合、聚集在一起,其中还有特殊的意涵。如果仅仅是从聚集的角度而言,动物也有群。但人的群之所以能区别于动物的群,是因为人的合群中有“分”、有“义”:
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
通过制定礼义,群体中的人得到不同的角色、职能等,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有所分别。人遵守各自社会角色、职能等的要求并各司其职,进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角色和职能可以相互调和、调剂,并汇集成一股共同的、更大的社会力量。换言之,人通过礼义来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了不同,但不同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和”、是“一”。人在群中能够各司其职、和睦相处,便可以化多人的力量为一,使彼此之间同心同德相互扶养,最终人人都能得到共同长远发展。荀子主张“和”与“一”,也就必然重视“合群”。在荀子,能做到合群的人才可称为君子。君子不仅能使人聚集、合聚在一起,还能使人人得以长养: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荀子·富国》)
真正意义上的合群,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人相互帮扶长养、共同富裕。君子能统合百姓之力,满足所有人的生活需求;能汇聚所有人的财富在一起,使民获得更多的财富;能聚集百姓在一起,使民众生活安定;能使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使人类得到更为长远的发展。这也是君主治理国家之道。“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荀子·君道》)总之,不管是仕人、君子还是君主,都重视合群之道,使人与人能和睦相处。
人能合群,因为人本身就是“合”的代表。“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既有水火的气,又有草木的生,还有禽兽的知,更有它们没有的义。气、生、知、义的结合,使人处于万物之中而能成为万物之总(同上)。人分不同的伦理角色、职能等,通过相互协作,人便能总括万事万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同上)正是因为君主懂得群居长养之道,所以人人都能得其养,甚至天下万物也能得到适宜的长养,这就是人与自然的相互扶养之道。通过群,一方面能满足人的各种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能使万物都能得到适宜的长养,从而人类与自然万物最终能和睦相处在一起。
正是从人与万物之间相互扶养的角度出发,荀子反复强调人的“群居和一之道”: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慤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
人有各种不同的生活需求和欲望,需要自然提供资源来满足,但同时万物自身也需要长养。从使人与自然万物能够相容的角度出发,人应该对人欲自身做出调节,具体方式是通过礼义的教化。先王制定礼义,以区别人与人之间的角色、地位、智能等,如此人便能在各自的角色、地位、能力范围内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如此,人合群居住在一起且能和睦相处;而这种和睦使人既能从自然获取一定的资源满足生活需求,也能在调节自身的需求的同时使自然万物的生长各得其宜。这便是更广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一”既是人人和睦群居住在一起,也是人与万物和睦相处。
制礼义使人能合群且和睦相处,是“乐合同”功用的最终追求。荀子反复强调社会的治乱和礼乐密切相关。“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圣人看重礼乐、正声,注重感化民心于善,通过礼乐而化民心、导民俗,才能使得民能够和睦相处。乐的功用在于合同,合同人心以得其同、得其公,从而民能够和睦安定的生活。这与制定礼义使人“群居和一”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群居和一”是人的“欢欣和合”之情的全面展现。人人协和而居,从而使得合乐得以实现。国家治理中,君与臣有不同的职分而能协和相处,使得君臣能和敬而合(群)一国;家庭中,父与子、兄弟等有不同的角色而能协和相处,使得父子、兄弟等能和亲而合(居)一家;乡里之中,长少各有辈分不同却也能协和相处,使得长少们能和顺而合(聚)一乡。同理,宗族管理中,人与先祖有很远的距离也能在思慕中协和相处,使得人与先祖能和敬而合(存)一类。不论是生死之合聚,还是协和不同声音以合同人心、制定礼义使人“群居和一”,都是从不同层次突出和合意涵中的欢欣快乐。生时的群居之道,就是协和聚居以得人与自然之和睦相处;死后的相聚之道,就是通过思慕得生死合聚之全。这种和睦与生死之全,使得和合内涵中的欢乐之情更为圆满地体现出来。
四、荀子和合思想的意义
和合在荀子既有“和”又有“合”。从“和”上说,“和合”即调和人心以得其同。具体到修身,(声)乐以调和、合同的方式使人心好公道而得和乐之境界;进一步从治世而论,和合即是“群居和一”: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人甚至与万物能合群居住,最后达到一种和谐、和睦相处的状态。从“合”的角度而言,“和合”主要是指合聚、联合。聚合不仅是指现实生活中多种不同事物会合在一起,更多是指向生死两隔后精神的联合、聚合。这体现了荀子在讲“合”时,不仅仅强调在场事物的相互交往,也注重强调与不在场事物的关联。死后对祖先的思慕,是对生时与父母合聚的状态进一步的拓展与抽象。在与先祖聚合中,人的自我同一达到源初意义上的完全与整合。
总之,荀子的“和合”既有对生的考虑,也有对死的理解;既有对个体人身修养的探讨,也有对整体人群之道的考量,是人生大乐中很重要的一面。因而,“和合”在荀子那里是一个有着全面和深层次内涵的概念。近些年,“和合”思想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荀子“和合”的基本意涵研究,既有助于进一步展现中国哲学中“和合”思想的丰富性,也能为推动“和合”思想在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和合”在荀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荀子重视“和合”思想,与其对礼义思想的重视相辅相成。从人心引导方式而言,“和合”路向的凸显集中体现在乐教。荀子重视礼义,也重视乐教;乐教与礼义思想两者毕竟是相辅相成的。“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乐重在以和同的方式感化人心,其优点是快速、深入[注]“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荀子·乐论》),且能直指欢乐和美的境界;礼则以明理的方式明心化性,其优点是能给出具体的方式(比如明分使群)指导人更有效地达成善。两者虽然方式、路向不同,但都是对人心的治理与引导所不可或缺的方面,相辅相成才能达到美善相乐的境界。
如此的和乐之道,使得“和合”概念也具有德性的意涵。以乐导心,人人同心协力于道,最后德性就可以彰显。这正是《国语·周语》中所说的“和同之道行,则德义可观也”。人人同心协力于道,最终获得的是一种大乐。在和合之乐中,荀子既强调修身意义上的生死两全之乐,也强调治国意义上的美善相乐,从而是一种整全、深远的人生之乐。
荀子“和合”思想的提出有其历史意义。不论是从“和”还是“合”,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在“和合”概念中更加注重同的一面,体现了对“和合”概念的一种深入理解。在古代社会,“和合”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既有对于“和而不同”的强调,比如《国语·郑语》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也有对于作为整体的“和同”的强调,这不应该被忽视。比如,就在《国语·郑语》史伯讲“和实生物”句的前面,就阐发了合“和”与“同”为一的“和同”的思想,指出在异姓婚配、财富聚集、选拔人才、治国之策,都应追求和乐为一的“和同”景象,体现了对和同价值的肯定[注]对于“和同”概念中“同”思想肯定的一面,不仅在《国语·郑语》中有体现,而且在《国语·周语》中也有体现。(参见向世陵:《“和合”义解》,和合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河北邢台,2017年11月,第50—58页。)。荀子继承这一“和同”思想,并且从修身和治世的角度分别对同的价值给予肯定。荀子既强调合同人心的状态,也强调人与万物和一的大同境界,从而使得“和合”概念中“同”的地位和意义得以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