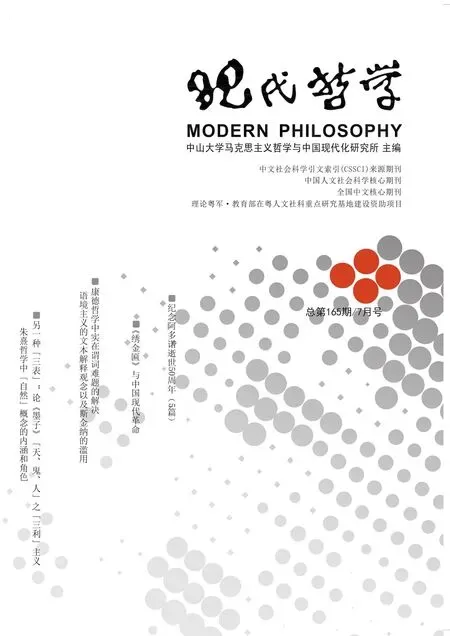社会批评如何应对实证主义的挑战?
——以《批评理论的理念》为中心的考察
杨顺利
雷蒙·盖斯(Raymond Geuss)想通过他的《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汤云、杨顺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下文简称《理念》)将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早期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工作介绍到英语世界。这本书已成为批评理论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现代经典,出版于1981年,按照盖斯的说法,“它当时以严肃的方式支持了那些在哲学和政治上即将失去吸引力的观点”[注]同上,第XX页。。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崩溃,意识形态批评有可能在长期被压制之后重新获得生命力,我们可以透过《理念》重新思考该独特的左翼话语在当下的效力及限度。
一、批评理论vs实证主义
在《传统理论与批评理论》中,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将时下以各种不同方式认可了社会现实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称为“传统理论”,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称为“批评理论”[注]Max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 pp. 188-243.。“批评”一词既表明与马克思的继承关系,又区别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有两个思想前提,“其一是将社会的主要经济结构当成社会压迫的根本肇因,其二是真切地将现代个体经受的社会苦难表达出来”[注]Stefan Muller-Doohm, “How to Criticize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Paths in Critical Theories of Society”, Gerard Delanty eds.,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6, p.171.。
批评理论认为马克思发动的思想革命的性质必须从认知层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类极其新颖的理论类型;要想对它的重要特征做一种恰当的哲学阐释,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关于知识性质的传统观点”[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12页。。马克思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都是观念上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具有相似的认知结构。前者要消解社会统治表现出来的“第二自然”幻象,后者要破除精神病患者自我施加的内在强制,二者都具有鲜明的解放与启蒙的意图,是批评理论这一解放的科学的两个范例[注]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pp. 274-300. 不同于早先的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的借鉴更多是方法论的,他看重的是它的认知结构而不是实质内容。。如果说精神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近亲”,那么实证主义就是它的“天敌”。实证主义代表了现代人对知识性质的典型看法,它指的是“(1)对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解释是恰当的,(2)所有的认知必须在本质上和自然科学具备同样的认知结构”[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14页。。科学理论与它指涉的对象之间有清晰的区分,它是“客观化的”;批评理论必然是它指涉的对象领域的一部分,它是反思性的。[注]同上。坚持反思属于有效知识范畴的批评理论,难免会遭遇到实证主义强有力的挑战。
二、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评
只要某类制度安排能够证明与人们所持的某个世界图像处于正确的关系中,即便它明显有损于人们的利益,也会得到人们的接受、认可。该世界图像阻止人们认识自身的真实利益,因此我们说它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正是意识形态欺骗的存在使批评理论及意识形态批评具有必要性。这里,我们在批判性、否定性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它可能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理念》主要根据词语的褒贬色彩,将意识形态分成描述性的、积极的、消极的。
(一)描述性的意识形态,也可称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关于人类社群的经验性研究。这层含义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描述性的意识形态是中性的,此时说某一群体有某种意识形态,对该群体的成员并无褒贬[注]同上,第5页。。说每个群体都有描述性的意识形态,无非是说人类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各种概念性中介与世界打交道。
(二)积极的意识形态,即最能够满足群体成员的需求并表达其真实利益的意识形式。积极意义的意识形态促使某个群体达成更好的自我理解,它不是等着被发现的或者给定的东西,需要人们把它建构、发明出来。譬如,根据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说法,改善福利待遇的“工联意识”是给定的,谋求彻底改变社会游戏规则的“阶级意识”只能通过特定的智识阶层把它构建出来[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8—304页。。
(三)贬义的意识形态及对它的意识形态批评。这是批评理论考察的重心。使人们对自身的真实旨趣存在错误理解的意识形式,称为贬义的或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根据意识形式具有的三种属性,我们可以断定一个意识形式具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1.根据其认知属性,断定一个意识形式是贬义上的意识形态,或是因为人们误解了组成该意识形式的信念的认知属性,将价值判断当成事实判断;或是因为人们犯了一类特殊的“客观化错误”(objectification mistake,又称“对象化错误”),将作为人类活动之产物的社会现象当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或是因为人们将某个亚群体的特殊利益理解成整个群体的普遍利益,等等[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22—25页。。人们犯这样的错误,不是因为理论的疏忽或思维的漏洞,而是与社会制度的根本运作有关。
2.根据其功能属性,断定一个意识形式是贬义上的意识形态,或是因为该意识形式支持、稳定或合法化了某些社会制度或社会实践,或是因为它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最大化,又或是因为它将社会次要矛盾当成主要矛盾,等等[注]同上,第25—33页。。简单地说,一个意识形式如果被证明促进了压迫性的社会建制的维系,它就是贬义上的意识形态。
以“转移社会矛盾”为例。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分配不公被看成是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一些左翼学者不同意自由主义的诊断,认为当下的社会矛盾在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相关,将政治思考聚焦于“分配范式”实则有效地掩盖了结构性的社会矛盾。通过这一思路,盖斯揭示了罗尔斯(John Boudley Rawls)正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根据他的说法,围绕《正义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产业,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内部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日益恶化。问题是,一个左翼的分配理论何以在右倾社会流行开来?对于盖斯来说,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此类分配理论实际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效应。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呼吁社会资源的分配尽可能地向最不利者倾斜,它要求的其实只是细枝未节的调整。社会愿意在资源配置上向穷人妥协,是为了维系根本制度框架的长治久安。提高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使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变得合法,这才是差别原则真正传达的东西。罗尔斯的理论没有真正为改变世界做出贡献,而是沦为单纯的理论思辨。这并不是盖斯批评的重点,其批评要点毋宁说是:此类论说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最重要的议题转移开来,使得人们不再能够严肃探讨根本的结构性问题[注]Raymond Geuss, Outside Eth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8.。
3.根据其发生学或谱系学特性,断定一个意识形式是贬义上的意识形态,或是因为它代表了某些人特定的阶级立场,或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是某个阶级的特殊经验的表达,等等。在发生学意义上追溯意识形式的来龙去脉,是谱系学考察的工作。它信奉尼采的“只有没有历史的东西才能被定义”,认为概念有其自身的历史,我们每一次使用概念其实都是在对它进行新的阐释和限定[注]参见[英]雷蒙德·戈伊斯:《政治中的历史与幻觉》,黎汉基、黄佩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谱系学考察将概念分析与历史溯源相结合,认为“普遍的”“必然的”及“自发出现的”等东西其实都是权力行使的结果。试图给予历史性事物以本质性定义,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就是谱系学考察的经典案例[注][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按照尼采的揭示,基督教起源于怨恨、嫉妒、仇恨等,这是历史事实,但基督教却声称是爱而不是恨构成基督徒的动机的可接受性标准。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基督教的自我宣称与历史事实何以相互冲突,这就是关于基督教的谱系学问题。我们不去询问基督教教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真的,而是提出“原罪、责罚、教会这样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约束力并获得普遍适用性的”[注]Raymond Geus, Outside Ethics, p. 158.的问题;不去追问基督徒身份是否是获得救赎的途径,而是提出“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使得人们发展出这一特殊身份”[注]Ibid., p. 158.的问题。只要我们像尼采那样关注偶然的权力如何在抽象事物的产生过程中起作用,我们就是在做谱系学考察的工作。
综上,我们将一个意识形式斥之为贬义的意识形态,并对它进行意识形态批评,或是因为它包含着错误信念,或者是因为它发挥了压迫性的功能,或是因为它在来源上有问题。不过,认知的、功能的与发生学的维度之间并无清晰界限:如果某个意识形式将社会的次要矛盾当成主要矛盾,这种错误不也是认知性层面的吗?对意识形式的谱系学考察,不也具有认知属性吗?三个维度之间彼此纠缠,难以截然分开,关键是需要知道哪个维度最根本。
在哈贝马斯看来,说一个意识形式是虚假意识,就是说它是人们在知情的、无强制的情形下不会接受的东西,简言之,是“扭曲的沟通”之下的产物。给予根本社会建制以合法化证明的意识形态世界图像之所以继续被人们持有,就是由于社会的“扭曲的沟通结构”在发挥作用。在自由的、无强制的讨论中,该世界图像会被人们抛弃,它被证明只能形成于强制的情形。如果我们接受意识形态就是扭曲沟通之下的产物,那么认知维度无疑是最根本的,其他维度都可以还原到认知维度:在发生学维度,说一个意识形式在起源上有问题,就是说它唯有在强制之下才能形成;在功能性维度,因为某个意识形式发挥了稳固现有体制的作用,我们断定它是意识形态,如果了解它的这一属性,就不再继续持有它。归根结底,“使得意识形式成为意识形态的,是它提供了虚假的合法性这一事实”[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139页。。
三、意识形态批评的认知地位:内在的还是先验的?
我们何以能够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批评理论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反思。这里说的反思有特定涵义,是指社会批评家在与所针对的社会群体的密切互动中,参与构建群体成员的认知原则,并将一套规范性的认知原则赋予他们。
反思与认知原则在这项批判计划中份量很重。如何界定反思的认知属性,批评理论内部存在内在、先验两种立场之争。一派以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为代表,认为我们必须从给定的历史、文化形式出发,从人们在追求自身的“好生活”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压制、挫败出发,主张既然内在批评的实质性标准包含特定的历史内容,那么它的有效性、真实性就是历史的,因此必然会被取代[注]同上,第126页。。另一派以哈贝马斯为代表,因为担忧内在化会导致相对主义最终取消反思的认知地位,哈贝马斯放弃早期的历史取径,试图通过“理想言谈情境”这一反事实、非经验的先验演绎推理,来寻求一个独立于任何特定语境的阿基米德点。在阿多诺、盖斯这样的情景主义看来,该先验论所预设的真理的共识论及合法性的认可论,均是很晚才出现的,并不享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有效性;哈贝马斯笔下就公共议题相互辩驳的康德式主体,同样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可能在前现代社会发现其踪迹[注]同上,第133—135页。。
内在取径不是外在于批评的对象,根据高悬的、抽象的标准来衡量它,而是从当下出发对现状进行批评。这种黑格尔式反思知识从当下的生活形式、社会实践出发,指出其匮乏、欠缺之处,通过批评使之不断改进,哪怕只是把当下的状态往前推进一点点。先验取径欠缺现实介入,不能指出一条如何从当下走到未来的道路,难免会陷入黑格尔批评过的“抽象反思”。不过,因为与批评的对象贴得太近,内在批评总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过拘泥于具体语境,因此在批评的视野及深度上都有所欠缺,最根本的是它不具备难以被化约的超越维度。相反,先验批评基于某个抽象理想对具体的现实进行批评,至少在理论上能够维系理想、现实之间的张力。
“内在”“先验”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其争论延续至今,犹未有定论。我们似乎不应该将二者教条式地对立起来。理解内在-先验之争的关键,是提出一条既从当下出发又未丧失超越维度的思路。
四、意识形态批评的实际操作:破除客观性幻象
社会批评的目的是要促成社会由被强制的初始阶段向自由的最终阶段转化。最终阶段的到来的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内部,激烈的政治对抗并没有如社会批评家所希望的那样发生,而且试图彻底改变现有经济-政治系统的“革命冲动”越来越淡薄。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类特殊的态度与信念,觉得当下的社会建制不是人能够控制,甚至不是人能够施加影响的。人们将社会实存放置到不可变更的、无可逃避的对象领域,这一信念中包含的认知错误就是“客观化错误”,其性质是将“客观必然性”赋予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社会制度安排,因此这一错误具有典型的实证主义意味。
行动与信念内在地相互关联。信念是关于可能的行动领域的划分,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行动是可能的,什么样的行动是不必要的。如果我相信自由市场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社会提供了很多证据让我接受相信它是真的,那么,对它施加给我的限制我就不会认真对待,而它给我带来的后果是我要去承受而不能合理抱怨的[注]Raymond GeusGeuss, “Dialectics and the Revolutionary Impulse”, Fred Rush, 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6-117.。如果人们相信社会的根本建制是历史客观规律的体现,他们就会自愿接受社会秩序,哪怕知道它会使自身利益受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被诱使去系统性地对他们的社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态度,这一态度固化了自身行动的可能性”[注]Ibid., p. 121.。
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个流行的定义是,它是对现有统治关系的合法化与辩护。然而,该定义对“客观化错误”并不适用。一个当成“自然的”“神圣的”“客观的”来理解的社会建制,其实根本不需要合法化。“我不需要为飓风、洪水或其他自然现象寻求合法化论证;我只要求那些在我看来是我有能力通过我的行动改变的东西的合法化论证。”[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143页。“客观化”的实质,是将社会建制放到必然性领域从而免除关于它们的辩护,而不是对权力关系给出虚假的辩护。如果社会结构被认为是人们无力控制甚至无力施加影响的,当然也就不会成为人们用自由的语汇谈论的对象[注]划定自由领域、必然领域之间的界限,辨识社会-政治现象的“自然性”或“人为性”,似乎永远是政治领域中最关键也是最微妙的事务,这提醒我们防范任何关于自然/人为的区分背后可能隐藏的意识形态风险。。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犯的致命错误,就是将人类的经济活动“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6页。。盖斯在《理念》中补充说,在“自然权利,自然法,人的本质,商品形式,人性”[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146页。等概念对象上,人们最容易犯这种“客观化错误”。当下,将某些特定的社会安排当成必然领域的一部分已经是普罗大众的一般看法。譬如,流行的丘吉尔式观点将民主体制理解成“最不糟糕的”,流行的撒切尔式观点将自由市场理解成“没有别的选项的”。对社会行为者而言,社会建制的基本运作仿佛是一个外在于他们的对象领域。
人们犯上述特殊的“客观化错误”绝非自身偶然的过失或疏忽。使特定的社会安排以自然的、客观的形态呈现,是社会根本建制正常运作的结果。批评理论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反思促使社会行动的无意识决定因素进入意识层面,揭穿社会根本建制获得的“客观有效性”表象,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关系的强制性是自我施加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待社会安排的消极的、“静观的”态度被转变成为积极的、反思性的态度。
对于精神分析来说,只要能将“患者”无意识层面遭到压制的内容带入意识层面,促使他重组一个更融贯的心智结构,态度转变之后,患者自然就痊愈了,这一理论也就得到经验性证实,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人从中作梗。批评理论面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客观性幻象继续维系合乎特殊阶层的利益,该阶层成员必然会从自身既得利益出发,竭力阻止赋予特定社会安排以合法性的相关世界图像成为自由讨论的对象。社会总是分裂成利益相互冲突的不同群体,“社会对抗”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根本事实。即便世界图像的虚假性被揭示出来,相关的社会压迫也不会自然消失,客观性幻相的消解会遭到在规范性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中占优势的统治阶层的阻挠。要想废除社会压迫,只是改变人们的意识结构是远远不够的,根本上还需要可能一个可能相当漫长的政治行动过程。
五、内在批评的限度
以上勾勒了意识形态批评操作的完整过程。批评理论要想在过程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被人们接受。它要成为一个解放与启蒙过程的自我意识。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说批评理论被人们接受了?关键要看被压迫者承不承认他们的欲望如批评理论所说的那样遭到挫败,如果他们明确否认这一点,社会批评将变得极为困难,很可能一开始就无法启动。
对人类历史的考察表明,意识形式的挫败在表现形式上相当复杂,是最复杂的一类,我们甚至不能合理地称之为“挫败”:(1)标准情形:人们既知道自己承受着挫败,也知道挫败的制度性根源;(2)人们知道自己承受着挫败,但对其根源形成错误的认知[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161—163页。;(3)从表象上看,人们似乎对他们的生活并无不满,但对其情绪反应、行为模式的考察表明,这是因为强大的社会控制已经剥夺了人们直接的痛苦体验,我们还是能在他们身上窥察到“无以言表的痛苦,无缘无故的不满,和非理性的行为模式”[注]同上,第163—164页。等被压制的挫败痕迹[注]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64, pp. 59-86.;(4)从表象上看,人们很满足,深层看也没有显示出“任何隐藏的挫败的痕迹”[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164页。。
上述“挫败”情形将人类受压迫的类型都概括进来,(3)(4)体现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4)尤其值得关注。在情形(4)中,社会行为者面临的问题是生活意义的匮乏,他们只能在各式各样的消费品中寻求替代性满足,因为社会阻止他们形成无法在当下社会框架中得到满足的欲望。(4)其实就是虚无主义社会的情形,它不单是困扰法兰克福学派的 “噩梦”,对社会中任何一个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人恐怕也是深重的噩梦。在这一情形下,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发自内心地喜欢上自身奴役状态的“快乐的奴隶”,假如他们身上并没有显露出任何挫败的痕迹,“我们”(社会批评家)将很难断定他们的欲望受到“挫败”:“如果人们真诚地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并且,如果我们没有他们隐藏其挫折的证据,那么,我们以什么为标准判断他们的生活为‘贫瘠的’或‘浅薄的’且需要被启蒙呢?”[注]同上,第165页。
如何面对这一棘手情形?根据盖斯的建议,批评理论应该坚持内在批评的有效性,这一次它要诉诸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内容”。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它不可避免地负载了乌托邦成分。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使人们的视域受到人为限制,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人为地限制在某个特定地平线之内,因此意识形态欺骗也是对人们的道德-政治想象力的一种剥夺,它诱使人们的欲望、偏好、需求等在一个被严格限制的、诱导性的框架内得到表达。另一方面,在表达这些欲求时,意识形态又不能不负载完美的、理想化的内容,这使它一开始就有一个“乌托邦内核”。从社会的及社会行为者的自我理解中,批评理论提取出规范性的、理想化的标准,通过这种方式将意识形态中的乌托邦要素释放出来。于是,区分“基本的、真实的需要、价值、愿望和它们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178页。就成为意识形态批评的积极任务。
激活“乌托邦内核”的观点提出一条极其关键的社会批评思路[注]它启发了我们如何为乌托邦进行辩护。鉴于乌托邦主义的名声颇为不佳,有必要区分积极的乌托邦主义与消极的乌托邦思维,能够得到辩护的是范导式的、抽象的乌托邦思维,而不是建构性的、具象的乌托邦主义。以消极形式表达出来的“良善生活”及“良善社会”激发我们关于政治与道德之可能性的想象。,下文对这一思路会有重要发挥,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它的局限性。它试图从社会内部提炼规范性的评判标准,这一思路没有充分考虑情形(4)中的特殊性。内在批评试图诉诸社会内部的实质合理性要素,在情形(4)中,合理性标准是形式化的,因此不存在可供提炼的实质性文化资源。
六、对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
内在批评诉诸社会的自我合法化方式,根据社会提出的理想、标准来批评它自身。不管传统形而上学-神学的世界图像在何种程度上发挥着“麻醉剂”“鸦片”的作用,它提供的自由、平等、公正诸理想是内在批评得以展开的必不可少的资源[注]参见杨顺利:《自由的辩证法:阿多诺论大众文化》,《哲学研究》2012年第4期。。在将社会压迫合法化的同时,传统意识形态也给出有待实现的实质性理想,因此它被说成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感情”。
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体现为不同的形式,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它不再体现为“客观精神”,也就是不再包含构成传统意识形态的实质合理性要素。社会合法性从实质性的、规范性的向形式化的、可量化的文化形式转变,意识形态的性质同时发生变化。排他性地诉诸技术效率来证成社会秩序的历史阶段,哈贝马斯称之为“后-意识形态”:“在证成社会秩序的时候只参照技术的功效,而将任何道德原则、规范或‘好生活’理想的诉求当作‘意识形态’(消极意义上的)加以拒绝。”[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136页。在这一时期,唯一被接受的合理性是技术合理性,唯一被认可的世界观是科学世界观,对于社会行为者来说,唯一合法的自我理解形式是形式化的、可量化的。显然,一个被实证主义思维支配的社会将不再能够提供实质性文化资源[注]盖斯早期赞同的“内在批评”观点是:内在批评告诉我们,通过对包括罗尔斯理论在内的当下流行的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的考察,我们既能够揭示“错误的”思考方式与“错误的”社会形式,又能够借以达成对社会更好的自我理解,也就是说,对这些理论的内在缺陷的批判性理解给我们提供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认知”。但他后来的批评计划实际上已经偏离这种早期观点,而是倾向于认为,通过对现有的思想素材的内在批评来提供关于社会现实的洞见的空间已经被关闭了,这些理论本身不再包含任何“理性的”因素。如蒙克所指出的,“盖斯不相信罗尔斯、哈贝马斯、德沃金或今天的任何其他伦理学家还能够给我们提供批判性考察的材料”。盖斯后来对内在批评的保留态度无疑与实证主义语境的笼罩有关。(Christoph Menke, “Neither Rawls Nor Adorno: Raymond Geuss’ Programme for a ‘Real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8:1, p.147.),传统内在批评在这一情形中可能会失去操作空间,其中的道理已清楚明了,“意识形态批评要对具体的某个对象展开内在批评,也就是用它自身的标准、理念来评估它,因此,意识形态自身包含能够成为批判材料的理性因素,应当是这一工作能够进行的一个前提”[注]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0, p.106.。
更致命的问题是,在一个被实证主义思维支配的社会内部,不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难以开展,事实上,任何严肃的批评、反思都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必然会包含规范性评价,而实证主义认为规范性评价欠缺理性的、客观的理据,只是表达主观的偏好、任意的决断。如此,那些最重要的社会议题就被实证主义从理性讨论的范围内驱除了,实证主义“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意识形式中的重要部分的指导,因而也就将整个生活领域留给了纯粹偶然的趣味、任意的决断或彻底的非理性”[注][英]雷蒙·盖斯:《批评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及法兰克福学派》,第52—53页。。
以形式化方式将自身合法化的社会,本文称之为“实证主义语境”,它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只有外在于它,意识形态批评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化约掉。所谓的“外在于它”,就是回到之前的社会合法化的“狭义层面的意识形态阶段”:“给予自身一种完全论述性的解释,能通过诉诸普遍的规范和原则、可普遍化的利益以及‘好生活’的解释来将社会秩序合法化。”[注]同上,第136页。这是基于“意识形态阶段”的实质性思维来批驳“后意识形态阶段”的形式化思维。意识形态批评不能不诉诸社会的实质性合理性,它仍然体现为内在批评,却不是内在于实证主义语境,而是尽可能抽象地内在于启蒙现代性。
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社会当下经历着由实质性向形式化的合法化方式的转化。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转化会是彻底的,我们不可能处在一个完全由形式化思维支配的社会系统中,无论如何残存的实质性思维总会在生活实践中发挥作用,都不可能完全被排斥在外。问题的实质,不是形式化思维如何挤压实质性思维,而是形式化思维垄断了启蒙理念的解释权。在争夺启蒙理念的解释权的竞争中,形式化、量化的解释模式暂时获得优胜,将其他解释模式亦即实质性模式斥为消极的意识形态加以排斥。
所以,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如何看待启蒙理念与其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理念的抽象性可以这样来理解:既然是抽象的,我们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它的理想化身。在这个问题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对待现代性理念的辩证思路颇为可取。在其《本真性的伦理》中,泰勒既驳斥了放任无为的文化悲观论,又谴责了拥抱现实的技术乐观论,指出它们均不是真正的现代性批评。在他看来,积极而又现实的做法,是将“成为你自己”的本真性理想作为现代性的伟大成就加以捍卫,把它从各种扭曲的表现形式中拯救出来。泰勒将现代性事业理解成理念的不同诠释模式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它的较高的与较低的实现形式之间展开。现代性事业应该体现为何种形式的问题,永远是争议性的,我们最好把它理解成“一个或许是永不停息的战斗的场所”[注][加]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30页。。泰勒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强调该问题的开放性:“如果最好的东西不可能明确地担保,那么衰落和浅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自由社会的本性是,它将总是较高和较低形式的自由之间的战场。”[注]同上,第94页。“战场”的提法再明确不过地表达了泰勒对甚嚣尘上的“自由终结论”的反对,以及对关闭可能生活的想象空间的“客观化企图”的抵制。
慈继伟在他的《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中提出一个与此类似的思路。在他看来,对现代性理念的解释是一场开放性的竞争,这场竞争不应当终止于它的某个具体形式;我们应当在接受现代性条件约束的前提下为现代性理念的更好的实现形式而斗争;当务之急,是要防止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思想观念的一时胜利逐渐“固化成为现代社会坚不可摧的硬壳”[注]Jiwei Ci, Moral China in the Age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04.。
维系自由、平等诸理念与它们的各种现实表达形式之间的张力,把这些理念从自由资本主义地平线对它的捆绑中解放出来,是当下坚持意识形态批评最有前景的一条路径。这一层面进行的意识形态批评就是一场反对各种自我夸耀的“道成肉身”的斗争,并且,只要某一理论探究具备了这样的思想特性,我们甚至不必纠结于它是否以“意识形态批评”的名义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