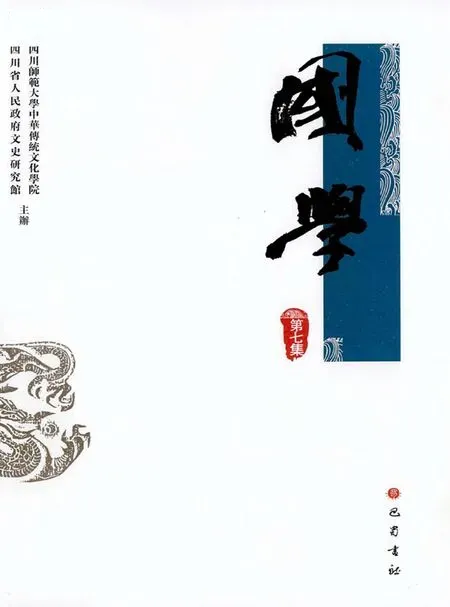跟隨方國瑜先生學習古籍整理與研究
鄭志惠
方國瑜(1903—1983),字瑞臣,雲南麗江人,納西族。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雲南大學教授、雲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全國人大民委委員等。1923 至1936年初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求學和工作期間,完成了《廣韻聲匯》《困學齋雜著五種》(包括《隋唐聲韻考》《廣韵聲讀表》《慎子考》《慎子疏證》《論學存稿》) 《説文聲彙考》《釋名聲彙》等傳統文字音韻學著作的寫作以及《納西象形文字譜》初稿。從1933年到麗江調査麽些文字,1934 到南京“輯録雲南地方史資料”,開始專攻科目傾嚮雲南史地之學起,至20世紀80年代,他寫下了《滇西邊區考察記》《抗日戰争滇西戰事篇》《雲南民族輯録》《雲南民族史講義》《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彝族史稿》《滇史論叢》《方國瑜文集》,主編《雲南史料叢刊》《雲南地方史講義》,與歷史系其他教師合作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南部分、編寫《中國少數民族史講義》等傳世之作。著名史學家徐中舒稱他是“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方國瑜先生不僅是雲南地方史、中國民族史的學科巨擘,更重要的是一位獨具魅力的老師,學術研究的無私奉獻者。他在雲南大學執教近50年,謙虚謹慎,平易近人;奬掖後生,扶持青年,誨人不倦,為後學師表。回想1980年3月我大學畢業留校,至1983年12月24日先生去世,短短近三年,先生對我的耳提面命,記憶猶新,其後伴着先生著作繼續學習古籍整理與研究,是他將我引進了古籍整理與研究的隊伍;是他為雲南歷史研究建造一座“磚瓦廠”的宏願,影響着我一直堅守在古籍整理這條“冷板凳”上,踏實工作,無怨無悔;是他“不淹没前人,要超過前人”的精神,激勵着我認真思考學術研究問題,明白古籍整理與歷史研究的意義。總之,我的成長離不開方先生對我的培養與影響。
一、注重培養從事古籍整理堅定信念
1.資料員工作的重要與意義
記得1980年3月4日,是我第一次到方先生家,第一次近距離聆聽他的談話。先生的一席談話,影響了我一生,成為鞭策我前進的動力。那天是歷史系總支副書記劉西芳老師帶我到方先生家,徵求是否願意接受我到地方史研究室作資料員。方先生説培養年輕人他很高興,問我:“你喜歡資料工作嗎? 學過目録學嗎? 資料工作很重要,也很艱苦,要抄書,但不要怕。抄書對於打基礎很好,抄一遍,頂讀十遍。要學習顧炎武一天抄書一萬字,樹大、根深、葉茂。今年學校衹准留資料員,但我要把你當助教培養,今後要在資料、教學、科研上做出成績來。不要怕,無論做什麽工作,衹要有信心、耐心、細心、恒心、雄心這‘五心’,就會做出成績來。現在徐文德、木芹二位老師與我正在編纂的《雲南史料叢刊》,就是為雲南歷史研究提供資料的磚瓦廠,你今後就好好跟着木芹、徐文德二位老師學習,參加這項工作。”那一刻,對於十分惶恐的我,還没弄明白資料員該幹什麽、自己該怎麽做,面對名師的指點,真不知説什麽好,但他的一席話給我信心和決心,“樹大、根深、葉茂”成為我後來學習、工作的動力與座右銘。
2.樹立知識公有、為雲南歷史研究建“磚瓦廠”的資料公有思想
方先生認為史料對於歷史研究十分重要,它猶如建築高樓大厦的磚瓦,猶如工農業生産的基礎建設一樣重要,“工業基礎是勘探地質,農業是治山水,如果没有高質量的基本建設,就不可能奪得高産”①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而資料工作是一項十分繁重的農田基本建設基礎工作。中國是人類歷史發展文脈唯一没有中斷的國家,所保存的古籍也是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據2009年統計,中國現存漢文古籍近20 萬種②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如何從浩瀚的書海中將有關雲南歷史資料發掘出來,並運用目録、版本、校勘等學科知識選録、整理,按一定的科學方式編排起來,供讀者研究使用,這在一般人的眼裏是費力不討好,“智者不為”的事,是一種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每一位學者都花很多的時間去從浩瀚的書海中收集自己所需的文獻資料,勢必延緩他最閃光的學術思想的形成,尤其是“舊社會個人觀念重,每個人都做基礎工作,問題研究好了,把基礎的稿子毁掉,拿出來的成果,衹要‘綉罷鴛鴦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成瞭風氣”③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了概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方先生指出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這是造成中國學術所以發展緩慢的一大原因。”①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因此方先生要打破知識私有的惡習。他説:“社會主義時代,要徹底批判這種惡劣作風,要多搞基礎工作,為大家用。”②同上。他認為“所有知識都是屬於社會的,來自社會,歸於社會,非個人所得而私有。”③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在整理雲南歷史資料方面,前人也做出過一些成績。如師範《滇系》、王崧《雲南備征志》、秦光玉《續雲南備征志》、趙藩等《雲南叢書》等,可惜收録有關雲南歷史資料未為完備,或未完工。“像這樣網羅史料,匯編成書,少數人出力,多數人應用,對於研究雲南歷史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④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卷1 《前言》,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他要為雲南歷史研究建造一個磚瓦廠,因此他主編了《雲南史料叢刊》。也正是他的這種“少數人出力,多數人應用”知識公有思想,深深地影響着我,成為我在這浮躁的社會氛圍中安於清平、不計得失、默默奉獻、做好工作的静心丸,培養了我甘於坐“冷板凳”的工作作風。
3.古籍整理者必須具備嚴謹的學風
古籍整理最需要的是嚴謹的學風,稍不留意,就會出錯。方先生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後時間裏對《雲南史料叢刊》編纂傾注了大量的精力,我也從中獲益匪淺。方先生每周都會到雲大老圖書館306 雲南地方史研究室來檢查我們的工作,我和徐文德、木芹老師都要將自己一周的工作嚮他匯報,尤其是我,必須將所寫的閲後記讀給他聽,有讀錯或評價不當的地方,方先生憑着驚人的記憶,都一一指出。如我寫整理董慶善撰《雲龍記》一書後記時,認為《章實齋叢書·節鈔王知州雲龍記略》本更好,方先生批評我:“不是這樣説,不是這樣説。書没讀遍,不要隨便下結論。”經考證,王鳳文在雲龍做知州,得到此書,對董氏之書稍加文字修改,讀起來文從字順而已,就改作“王鳳文《雲龍紀往》”,而章學誠又將王本收入他自己的叢書中,加“節鈔”二字,並改“往”為“略”,就變成了章氏的整理本,其實他並没有删除王書的内容,二人都是鈔襲,怎麽能説章本好呢?
方先生的每一個學術觀點都是在詳盡佔有資料,認真考證分析史料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對學生的不同觀點,不是强制打壓,而是與之探討,幫助分析,以期形成最佳觀點。如關於南詔的社會性質,方先生的觀點與學術界相同,認為是奴隸制。當木芹老師最初提出“南詔前期(8世紀南詔統一洱海地區) 其社會最基礎為農村公社”⑤(唐) 樊綽撰,嚮達原校,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同時還保留着原始社會的痕迹(最為明顯的是平時為民,戰時為軍的鄉兵制等)”⑥同上。,即使是後期也不是奴隸制,而是“封建領主制在南詔社會中逐漸居於主導地位”①(唐) 樊綽撰,嚮達原校,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時,方先生不贊成,兩人差不多用了大半年的時間討論,最終方先生終於同意了木芹老師的觀點。
從以上兩件事中,可看出方先生嚴謹的學風,而這種嚴謹的學風也在潜移默化中影響着他的每一位學生。
4.古籍整理者必須堅持“不淹没前人,要超過前人”的精神
古籍整理是一項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溝通歷史與現實的文獻整理工作,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係子孫後代的工作”。我們今天看到歷史文獻整理成果不外乎匯編、校注、注釋等形式,這是一種在儘量保持古籍原貌的基礎上,重新加以編撰、翻譯注釋,形成一種適合於今人利用、閲讀的新版本,是很難超越前人的。在古籍整理中如何把握學術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實在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而方先生提出“不淹没前人,要超過前人”的思想,將繼承與創新有機地融為一體,為古籍整理工作作出了榜樣。他説:“我們一方面不淹没前人,另方面又要勝過前人;衹有不淹没前人,纔能勝過前人。”②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要勝過前人,必須對前人的成果作實事求是的評價,須在收集研究史料中注意“三不”,即“前人不對的,你改過來;前人不够的,你作補充;前人不曾説到的,你提出來,使之更上一層樓”③《雲南史料叢刊編纂緣起》,昆明:雲南大學歷史系地方史研究編印,1965年。。他為《雲南史料叢刊》製定的編纂原則是“搜集資料,求其完備”“得此一部,衆本咸在”“信得過,用得上”④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卷1 《前言》,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從收録史料的數量來説,《從刊》也是最多的,全書所收史籍400 餘種(篇、部),文物資料考説200 餘篇,其中收録碑文、墓志銘近60 篇,包括校勘記、注釋和方先生所作解題及徐文德、木芹等先生所作的後記,總字數達1300 萬字。這是以前任何一部有關雲南史料的書籍未曾達到的數字,遠超被譽為“滇中掌故之尤著者”的清代王崧《雲南備征志》收録史籍(64 種,60 萬字) 的數量。《雲南史料叢刊》不僅是對前人彙編史料的一種補充和完善,同時也是一種超越。他開創前有概説,後有後記的新體例:“概説”是方國瑜教授對該篇史料源流、價值、真僞等考辦,“結合史事,發抒意見”;“後記”則是纂録整理者對各史籍的版本流傳、鑒别和選擇作出説明,也補充了些“概説”中未提到的意見,評論長短得失,既為研究者提供參考,又為初學者指引門徑。兩者互有照應,相得益彰,起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對史料所進行的全面、系統的考證,使《雲南史料叢刊》成了融資料性、學術性、思想性為一體的巨著,真正成為“不淹没前人,但要超過前人”的雲南古籍整理成果。
二、古籍整理與研究必須具備的基本專業知識與能力
整理歷史文獻的傳統方法,可用“類、考、釋、纂”四個字來概括,具體來説,就是對歷史文獻進行分類、考證、注釋、編纂四大系統的工作。所謂分類,即對歷史文獻進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録分類與檢索利用;所謂考證,即對歷史文獻的實證,包括版本、校勘、考據、辨僞、輯佚、補遺等文獻工作的内容與方法;所謂注釋,包括對歷史文獻的斷句、音韵、訓詁、注疏等;所謂編纂,也就是今天所説的匯編,包括叢書、類書、資料匯編、長編等。衹有掌握這四大系統的基礎理論知識,纔能較好地完成古籍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
從西漢劉嚮劉歆父子第一次大規模整理中國圖書開始,目録、版本、校勘等内容皆統一在校讎學之中,也稱之為傳統的目録學,是從事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1.具有目録學專業知識
目録學是讀書治學的門徑。清代歷史學、經學、文獻學大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説:“目録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由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在卷二説:“不通《漢書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户也。”有了眉目,即有了頭緒,有了條理,纔有進入門户的條件。張之洞《書目答問》第一條又説:“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為什麽學者們如此强調目録呢? 就因為它是打開知識、提供史料寶庫的鑰匙。因此,在我第一次見方先生時,他就問我學過目録學没有,我回答説没學過,他説,目録學對歷史研究很重要,是讀書治學的門徑,一定要補上。在我後來的學習工作中纔領會方先生要我補目録學的重要性。
學習雲南文獻整理,首先必須瞭解雲南有些什麽歷史書籍,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群書中找出雲南史料,這些史料之間的關係如何,真僞如何,都需要有人指點。木芹教授給我找了一位最好的老師,就是讓我學習方先生的《雲南史料目録概説》。
《雲南史料目録概説》是“以讀書要求為主,結合各家,求其完備”①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略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的雲南史地專科目録,是方國瑜先生留心“記載滇事之書”近50年的結晶,為治雲南史地之學提供了讀書門徑。全書十卷,分文獻資料和文物資料兩大類。前五卷著録漢代至清代記載雲南史事之書或專篇專節581 條,後五卷充分吸收和利用了考古發掘與民族調查的成果,著録漢至清時期雲南文物240 通。如你想知道漢晋時期雲南有些什麽書,翻開《概説》第一卷,收録傳記之屬有《史記·西南夷列傳》等10 餘種書,地理志之屬有《漢書·地理志》《水經注》西南諸水等11 種(篇) 書,地方志之屬有楊終《哀牢傳》《華陽國志·南中志》等6種(篇),辭章及雜載之屬有《喻巴蜀檄》《廣志》(摘專條) 等6 種(篇、條),漢晋之作共計30 餘種(篇、條)。
目録學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問。如何將雜亂無序的群書編制成便於檢索的目録書,核心是分類。鄭樵《通志·校讎略》卷七十一“編次必謹類例”説:“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又説“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方先生認為:“所謂‘書’ 即史料,‘類例’ 即目録”①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在目録編排中,他根據史料的多寡立目分類,通過類例來反映雲南的學術情況。如文獻部分,漢晋、唐宋、元時期各類僅立二級目録,明、清時期史料内容豐富,增設三級乃至四級目録。以地理志的著録為例,漢晋、唐宋僅有“地方史志”“地方風土志”二級目録,地方志書是保存地方歷史文獻的主要資料庫,明清兩代地方志書的編撰迅速發展,明代九次修省志,流傳至今五部;清代有康熙、乾隆、道光、光緒、續光緒五部官修通志,明清兩代所修地方志流傳至今者有200 餘種,明代二級“地理志之屬”下設有“總志”“省志”“郡邑志”“專志”四個三級目録。至清代,除有與明代相同的四個三級目録外,在“省志”下細分“官修省志”“私人修省志”兩個四級目録。又在“專志”下設“賦役志”“山川志”“礦産志”“民族志”“武備志”“學校志”六個四級目録。從漢晋時期的“地方史志之屬”二級目録到清代“地理志之屬”二級目録下有三級、四級目録的設立,清楚地反映了雲南方志學的發展綫索,説明方志學在清代的迅速發展與成熟。“如此條分縷析,將史料按不同層次有機地組織起來,不僅具有綱舉目張、執簡御繁的作用,而且能收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的效果。”②張振利:《試論方國瑜對中國目録學的貢就》,載《雲南大學本科優秀畢業論文》,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2.版本的知識
“版本”一詞,出現於雕版印刷盛行的宋代,主要是為了區分手鈔本與雕版刊印的書籍的不同,將雕版刊印的書籍稱為版本,後泛指同一書籍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流傳下來的不同樣式的各種本子。版本學是研究各種版本的用紙、墨色、字體、刀法、藏章印記、款式題跋、行款版式、封面裝幀、文字内容等,以辦明版本的真僞,分清版本精粗優劣的學問。掌握版本學知識,可避免誤讀古書,鑒别判定古籍的文物價值和使用價值,為校勘、輯佚、辨僞等學科的理論研究和具體實踐提供可信的底本。如我在前面提到的董慶善作的《雲龍記》一書,經方先生考證王鳳文《雲龍紀往》、章學誠《節鈔王知州雲龍記略》是僞書,雲龍縣教育科1957年油印的董本,纔是最接近原書的本子。
3.校勘的知識
所謂校勘,是糾正古籍在流傳的過程中産生訛、脱、衍、倒的字、句錯誤。所謂訛,即誤。誤是指文字字形失真,即古諺所説:“書三寫,魚成魯,虚成虎。”形近、音近引起字訛的現象比較普遍。如師—帥、穴—内、比—北、確—榷、舅—舊等。脱,是指古書在傳鈔、傳刻過程中漏字或漏句。衍,指古書在傳鈔、傳刻過程中多寫了字句。倒,又稱錯簡,指古書在傳鈔、傳刻過程中,字句、篇章順序顛倒錯亂。
校勘的方法,一般先廣泛搜集各種本子和相關資料,並辨析他們之間的淵源關係;對校各本,列出異文,發現疑誤;分别疑誤的類型,進行分析,舉出根據,説明理由,校改謬誤;撰寫叙例,寫出校記,清楚準確表達校勘成果。校勘的目的是“擇善而從,版式歸一”,形成最接近歷史文獻原貌的最佳版本。方先生主編的《雲南史料叢刊》,就充分運用了校勘的方法。
4.綜合研究分析史料能力
方先生針對漢文文獻中有關雲南歷史文獻“一少、二不確、三多歪曲”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用馬列主義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歷史觀分析研究邊疆民族地區歷史文獻的理論和方法,將傳統的考據學、辨僞學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方先生精闢的闡述:“……批判地研究史料,要從説明史料來源入手,明確史事之時間、空間、環境與撰人之活動,而後確定史料之歷史意義,闡明歷史實際。其來源過程,有在史料本身已説明,亦有未具,則當多作考究。”①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略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因此,方國瑜先生研究雲南歷史文獻主要從以下四方面入手。
第一,通過考訂作者的生平事迹、作者的時代、作者的學術等問題,考證史料來源,以確定一書的價值。如考訂《史記·西南夷列傳》,依據《史記》中司馬遷的《自序》《河渠書》《南越尉佗傳》《漢書·武帝紀》等資料肯定元鼎六年司馬遷為中郎將,並為經略西南,親至西南調查研究寫成的《史記·西南夷列傳》是一部“信而有徵,非尋常可比”的重要資料。對於樊綽《雲南志》的史料價值,前人有不同意見:胡渭《禹貢錐指》以樊綽没有親自到過雲南而貶低其書的價值。馬長壽《南詔國内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前言》認為樊綽親自到過雲南,對南詔的軍事、政治上的報導,是他親耳所聞,親目所見“真是第一手的可靠資料”。方先生以其嚴密有據的考證指出:“樊綽《雲南志》十卷中之大部分材料,為親歷目睹之記録。”②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樊綽主要採録袁滋的《雲南記》,而《雲南記》又採用了南詔文臣編纂之地方志與檔案資料。所以這部書大體保有第一手的記録,但樊綽並没有親自到過雲南。
第二,通過版本和它書記載,考證史料來源,鑒别史料的真僞。方先生認為古籍流傳“在長時期中,輾轉傳鈔、翻刻,以及注解、評論,見於各家著録之傳本,知其大概。”①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略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如明代學者楊慎自述《滇載記》是自譯白文《白古通》《玄峰年運志》,“稍為删正,令其可讀”。萬曆《雲南通志》也説是楊慎翻譯《白古通》等書而著《滇載記》。實際上《白古通》《玄峰年運志》諸書早有漢文譯本,衹是語言不够流暢通達,經楊慎修改潤色而已,就謊稱是他翻譯的。所以方先生批評楊慎有“喜歡造假”的惡習,戳穿其“自述史料來源及其所作僞説以欺世人”的騙局。
第三,用“洞察史料之社會性、階級性”的方法,分析研究歷史文獻,以闡明歷史真相。雲南地處西南邊陲,社會經濟基礎發展不平衡,且少數民族雜居,長期遭受反動階級“内王外霸”的大民族主義政策統治,以及各部族統治者之地方民族主義,時有争端,造成雲南歷史現象錯綜複雜,而“所得歷史資料既奇缺,且大都誣衊”。為闡明歷史真相,方先生强調研究史料“更重要者,則為洞察史料之社會性、階級性”,“結合歷史事實,作適當分析,提出問題,纔有助於研究歷史”②同上。。因而對封建文臣儒士把雲南説成是“别種殊域”的“化外”之地的記載,方先生持批判態度,一一指出;對企圖分裂中國,分割雲南的外國漢學家,則給予有力駁斥。如《宋史》把大理列入“外國傳”,南宋儒生臆造“宋揮玉斧”的典故,方先生依據昌慤《議買大理馬》、楊佐《買馬記》、郭松年《大理行記》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朝野雜記》《玉海》《文獻通考》諸書言大理馬事,從分析南宋所處的形勢、經濟狀況入手,闡明南宋時西南與内地加强聯繫,是歷史發展之必然,以販賣大理馬一事可以知之,宋太祖劃大渡河為界並非事實。且强調指出,宋王朝勢力微弱,不能致力經營雲南,但宋王朝不等於中國,不能把大理排斥在中國之外。大理三百年的歷史,與全國歷史緊密聯繫,為中國整體一部分。再如出版於1904年法國伯希和所作《交廣印度兩道考》,把雲南劃為“中國官廳勢力所不及”③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的地區,以南詔為專用之地名,置於中國之外,把南詔、大理説成是中國之外的獨立國家。方國瑜先生據1958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發掘唐代長安城大明宫故址出土之“雲南安撫使印”封泥④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以及《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等文獻記載貞元年間唐朝設雲南安撫使統領南詔的歷史事實駁斥説:“漢朝以益州郡為政區名號,唐朝以雲南安撫使司為政區名號,而滇王與南詔則為世襲世職,不得為地名也。”⑤同上。“ ‘雲南王’ 為地方官職,與其他地方官職之政權在形式上有差别,而同為國家版圖之内。”①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伯希和自負熟悉雲南歷史,其書為帝國主義所賞識,我國學人亦有推崇者。其惡劣影響至今未完全揭穿,其謬論之基點即‘以南詔之名,名其全國’ 之謬説,毫無根據,且違反歷史實際,不可不辦明之。”②同上。從這些論述中,説明方先生並非僅僅着眼於著録雲南史料目録,而更通過著録研究,進而揭示歷史的真相,回答歷史和現實提出的問題,維護祖國統一與民族團結。
第四,説書與論史的結合,確定歷史文獻的史料價值。方國瑜先生在著録雲南史料目録時,不僅注意對史料的來源、流傳認真考核,去粗取精,去僞存真,而且確定史料的歷史價值,注重結合歷史事實進行評述,以求闡明歷史真相及發展規律。如概説《元史·賽典赤傳》,不僅歷叙賽典赤個人身世,而且考校有關建立雲南行省的大事,諸如“建立統治機構”“建立社會制度與發展生産”“傳授儒學開科取士”,指出元代在雲南按田畝、人丁徵賦税,為前代所未有,説明雲南部分地區已是地主所有制,或由大土地所有制嚮地主所有制過渡,清查田畝,定賦税,保證私人佔有土地為生産資料所有制一大變革。書中幾乎每一篇“概説”都結合歷史事實進行評述,使《雲南史料目録概説》成為既是一部有關雲南史料的專題著録,又是一部對雲南歷史發展的若干問題進行論述的學術專著。在雲南歷史文獻學和歷史學上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提供了整理邊疆民族地區古籍的原則與方法。
綜合分析史料的能力,就是通過各種古籍整理研究的方法,對古籍進行一種綜合性的全方位考證,對歷史文獻的去僞存真,這就是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原則,即恢復或保持古籍的原貌,不能隨意篡改。
三、古籍整理與歷史研究重在闡述“中國歷史發展整體性”
1.“中國歷史發展整體性”理論的提出
方國瑜“ ‘中國歷史發展整體性’ 理論來源於他長期研究祖國西南邊疆及中國少數民族史的‘邊疆視角’。”③潘先林:《家國情懷書生本色方國瑜先生的中國邊疆學研究》,載《西南古籍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對封建史家“異内外”的“春秋大意”“夷夏大防”思想的深刻認識,對居心叵測外國漢學家企圖分割雲南、分裂中國野心的高度警惕,醖釀了他“中國歷史發展整體性”理論。1944年他在《雲南政治發展之大勢》一文中首次指出:“今日之雲南,為中國之一部分,自有歷史以來之雲南,即為中國之一部分,故雲南之歷史為中國歷史之一部分。”①方國瑜:《雲南政治發展之大勢》,載《邊政公論》,1944年第3 卷第2 期。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963年4月,在雲南大學校慶40 周年之際作了《論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的學術報告②方國瑜著、林超民編:《方國瑜文集》第1 輯,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這一思想,整體思想的核心,一是“歷代王朝史與中國史應當有所區别”③同上。“王朝的疆域,並不等於中國的疆域;王朝的興亡,並不等於中國的興亡。”④同上。“中國歷史,既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各民族人民的歷史,就應該包括他們的全體歷史,不能‘變更伸縮’。中國歷史是有其整體性的,在整體之内,不管出現幾個政權,不管政權如何不統一,並没有破裂了整體,應當以中國整體為歷史的範圍,不能以歷代王朝疆域為歷史的範圍。”⑤同上。“統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權而言。……政權的統一與不統一,衹能是整體之内的問題,而不是整體割裂的問題。”⑥同上。二是“中國歷史上不在王朝版圖之内的民族關係,應該放在中國歷史之内來處理,不能以異國的關係來處理。”⑦同上。因為“秦漢以來中國形成比較穩定的多民族國家,以漢族為主幹,漢族與其他各族聯繫為一個整體”⑧同上。“中國歷史之所以形成整體發展,是由於有它的核心起着主幹作用。這個核心就是早在中原地區形成的諸夏族,後來發展成為漢族的人們共同體。……以漢族為主流的文化的發展和傳播,形成中國體系的文化,在中國整體之内,起着主幹作用”⑨同上。“這種以漢族為主幹的與全國各地各族的聯繫,由點而綫而面,成為中國整體的社會經濟結構。這一聯繫的面,就是中國的領域,也就是中國歷史的範圍。”⑩同上。
2.西南歷史發展是中國歷史發展整體的一部分
方先生在考釋西南歷史地理時,將西南歷史地理看作中國整體的一部分,主張研究西南史地:“必須把它提到全國範圍之内來考慮,因為自古以來,這個地區是偉大祖國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政區設置的地名以及幾次大的改變,都是與全國整體性是息息相關的;如果離開全國形勢,孤立地談論這個問題,必然談不清楚,也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⑪方國瑜:《雲南政治發展之大勢》,載《邊政公論》,1944年第3 卷第2 期。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西南地區,為統一多民族的偉大祖國組成部分,自有歷史以來,生息在這地區的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偉大祖國的歷史。西南地區之所以成為祖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不是由於歷代帝王的好勤遠略,乃是各族勞動人民緊密聯結共同發展的結果。”⑫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略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那些視南詔、大理為“獨立發展”的國家,或“忽必烈滅大理,雲南開始成為内域”①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略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乃至1956年編印的中國歷史地圖,違反歷史事實地將“元代以前各圖幅,把西南地區的全部或局部劃出國界外,即明清圖也不免有這種情況”②同上。等等,都是“所謂春秋大義形成王朝本位的概念,以王朝政治活動來限制中國疆域,為王朝服務的歷史資料,不符合歷史事實”③同上。。“這是遵循反動統治者之衹有王朝,不知有中國的謬論”④同上。,必須“嚴格批判”。
方先生對西南歷史研究不局限於文獻的字面解釋,更多的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其深層含義。他説:“歷史上的地名,是歷史活動的空間符號,離開歷史則地名没有意義,不從歷史活動來考釋地名,則未必能準確。”⑤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秦統一中國,經略此諸地,開道置吏,並非偶然也。”⑥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南朝雖未能切實統治其地,仍不斷任命寧州刺史……至唐天寶初年之爨守隅,王朝任命爨氏為刺史、為都督,亦凡二百年。”⑦同上。南詔、大理“雖衹加封號,為西川節度兼雲南安撫司,不設直接統治的州、縣政權機構,仍是邊州性質的一部分”⑧方國瑜著、林超民編:《方國瑜文集》第1 輯,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屬中國版圖,為中國史的一部分。元明清的“土司政權的存在,並不以民族特徵為基礎,而是以社會特徵為基礎的。並改土歸流也不是以帝王的主觀願望所決定,而是以社會發展階段決定的”。“在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地區,建立政權有不同的形式(土官或流官),而國家的完全主權的没有差别的,在統一的國家之内,並没有‘半獨立性’ 的政權存在。又在多民族的國家之内,並不以政權的改變而否定民族區别。這些歷史事實,是不容歪曲的。”⑨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方先生以確鑿的歷史事實,令人信服地證明:西南各民族人民自秦漢以來,就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西南歷史的發展,統一在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之中。
3.古籍整理與歷史研究中的家國情懷
為什麽當西南邊疆危機時,方先生毅然轉入西南史地研究,並提出“中國歷史發展整體性”的理論? 這與他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鄉土文化中“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有名不負此生”的思想與儒家經典著作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等儒家文化精髓已深深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報效國家、回饋鄉梓的使命在他的人生旅程中愈來愈清晰。同時,方國瑜先生醉心於雲南歷史文獻的分析研究,從中獲得千百年地方文化根脈的涵養,獲得“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鄉邦”的知識補充與思想源泉。當國家、民族遇到危機時,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直接上升為國家意識。正如林超民教授所説:“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學説的提出,體現了一個學者真摯、赤誠、廣闊的愛國主義情懷,體現了他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國家的統一、民族的進步、社會的發展、為政府解決祖國邊疆民族問題孜孜不倦工作的精神。”①林超民:《整體性:方國瑜的理論貢獻》,載《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0 卷第5 期,2013年9月。納西族木芹教授認為:“先生的史地之學源於極强的國家情結……納西族從來就有維護國家統一之心。”②木芹口述,張昌山、木霽弘撰文:《回憶方國瑜先生(上)》,《雲南日報》(文史哲),2012年2月24日。潘先林教授認為:“國家情結是方國瑜先生西南邊疆研究的基石,他的論著始終以濃烈的家國情懷著稱於世。我們衹有對此有深刻的認識與體察,纔能與方國瑜先生産生共鳴,纔能更好地學習和閲讀他的論著,從而在更高的起點上推動中國邊疆學搆築的嚮前發展。”③潘先林:《家國情懷書生本色方國瑜先生的中國邊疆學研究》,載《西南古籍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我們可以説衹有熱愛家鄉、熱愛祖國,纔可能産生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纔可以在歷史研究與整理古籍工作中體現自己的家國情懷,而家國情懷正是整理古籍與歷史研究工作者所追求的最高學術價值與思想境界。
結 語
回想跟隨方先生學習古籍整理與研究的里程,我的每個成長都離不開方先生對我的培養與影響,離不開木芹、徐文德、林超民老師對我的幫助與指導。今天在這裏無論講從事古籍整理的堅定信念,古籍整理與研究必備專業能力,還是講“中國歷史發展整體性”理論,都不能把方先生文獻學及歷史研究的治學理論説清楚、講透徹、説完全,但方先生的一切都深深地影響着我,我一直是這樣想的,先生們甘於坐冷板凳,從不計較自己得失,在古籍整理崗位上無私奉獻,我有幸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也就照着他們這樣做,我雖没有創新,但也從來没有覺得喫虧,衹覺得自己在古籍整理這個崗位,就應該這樣做。正是積極努力安心做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做好了,工作也就成就了我的今天。
——盐业古籍整理新成果《河东盐法备览合集简注》出版